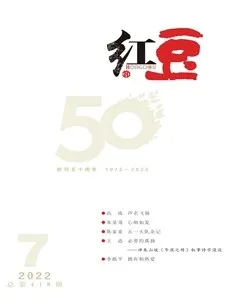声名飞扬
2022-12-29高涛

孟浩然说啥也没想到,父亲孟一鸣会以那样的方式“死”去。那种“死”并非真死,而是脑死亡,可看起来跟真的死简直没啥两样。父亲到“死”都喜形于色,甚至得意忘形,父亲“死”了,可脸上的笑依然活着。那层面膜一样的笑容把父亲装饰得格外幸福。
这让孟浩然无比难过又倍感安慰。
医院的结论是过度兴奋所致。孟浩然回想起当天的情景来。
那天是重阳节,秋阳和煦,天蓝云白,护城河水清如镜。孟一鸣作品研讨会在唐都市凯悦酒店举办,国内文学评论界大腕名流呼啦啦来了三四十人,电视台、报社、网站等媒体记者也蜂拥而至。某评论家一再感慨:“如此强大的阵容实属罕见!”
孟一鸣退休前是市图书馆的收发员。同事们叫他“老孟”“孟师傅”,不认识的则喊他“师傅”“老师傅”,有的干脆喊他“哎——”,他的大名孟一鸣几乎无人提及。一个收发报刊信件的,他姓牛姓马谁会在意!
默默无闻了大半辈子的孟一鸣退休后在老年大学练过书法,拉过二胡,弹过古筝,吹过笛子,还参加过“老来俏”合唱团,但坚持时间最长的也没超过三个月。后来某天,孟一鸣却老夫聊发少年狂,信誓旦旦要写一部比砖头还要厚的长篇小说,立志要给文坛制造一枚潜水炸弹,将文坛炸响。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孟一鸣真的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了!
一夜成名者在当下的中国不乏其例。孟一鸣不止一次叮嘱过儿子孟浩然,他将来的墓碑一定要做成书的造型,扉页上他只写“来过,又走了”这一句话。
起初,家人都以为他写长篇小说只是说着玩,过过嘴瘾,过不了几天,不用别人费唾沫,他自个儿就把这事给忘了,因此并没当回事。他想上天揽月,也得有那能耐才行啊!
孟一鸣写过打油诗,编过“三句半”,他写的“三句半”还在市总工会组织的职工文艺会演中获过优秀奖,奖品是一个舞女造型的水晶奖杯,舞女长发飘飘,裙裾如伞,腰细腿长,曼妙婀娜。那是孟一鸣大半生得过的最高荣誉,他至今还把奖杯摆放在客厅墙柜最醒目的位置。他每次坐在墙柜对面的沙发上读书品茶时,看着那亮得晃眼的奖杯,心里都亮堂堂的。
孟一鸣突发写书的念头时已年过古稀,这时的他已能清晰地望到人生的彼岸,越发急切地意识到人活一世,总该给身后的世界留下点什么,不然的话,像白活了。龙归晚洞云犹湿,麝过春山草木香。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那些在旅游景点乱涂乱写“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了,无非是想刷刷存在感,告知后来者,我是谁,我来过。
能留下什么呢?他想起作家莫言说过的话——文学与人的关系,就像头发与人的关系。多年以后,人的肉体没了,可头发依然在。看看那些世界文学名著,有的作者已作古几百年,可是其作品至今还在被人们传阅、评说。看来当作家能被人记住,这真是个不错的选择。他所供职的图书馆先后出过两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一位是光头牛耕,一位是美女云雀。好几次,他看见牛耕或云雀在图书馆门口被路人拦住,路人热情地问,某某老师您好!我能和您合个影吗?这个时候,他常常会被临时抓差帮忙拍照。有些人拍完了,客气地冲他点点头,微笑着说声“谢谢”。但也有些无礼的,连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就好像那是他孟一鸣的职责和义务,那时他就深感落寞。在别人眼里,他只能是“师傅”,没名没姓的“师傅”。“师傅”这顶帽子太缺乏辨识度了,扣在谁头上都合适。
在图书馆工作等于坐在书堆里上班,只要你愿意,什么样的书读不到啊?图书馆最不缺的就是书,就像植物园最不缺花草一样。孟一鸣热衷阅读各类小说,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他读过上百本呢。他自己也尝试着写小说,短篇、中篇都操练过,也天女散花般地投过稿,可无一例外,皆泥牛入海。他要么骂编辑有眼无珠,要么怨伯乐难遇。他把退稿信编好号码锁进抽屉,故作轻松地自我安慰:“嗨,伟大的作品都躺在抽屉里。”孟一鸣不会打字,向来都是手写。后来他得知有个老师因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而声名飞扬,就不再写那些几千上万字的中短篇小说,更不屑写那些一千八百字的“豆腐块”了。他再也看不上那些小鱼小虾了,他想要钓大鱼。
他买来几摞方格稿纸和三大盒圆珠笔,拿出他儿子孝敬他的好烟,关门写起小说来。
孟一鸣关掉手机,拉上窗帘,他要把一切世俗干扰挡在外面。他一再警告老伴,只要天没有塌下来,千万不要乱敲门,那样会打断他的思路。他说写小说和蒸馍是一个道理,中途万万不可漏气,否则,蒸出来的馍就成了麻子脸。他还举例说,指甲花捣碎加上明矾染指甲,一定要用构树叶子缠裹严实,这样,指甲才又红又亮。否则,那红就寡淡寡淡的,一点也不好看。
他一头扎进他虚构的世界里,那里真假难分,那里虚实难辨,那里亦真亦幻。在那个世界里,他是无所不能的王,他是调兵遣将的帅,万千气象、百态人生,任他摆布。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书桌前的孟一鸣伏案疾书、激情澎湃、思绪激扬,他时而喃喃自语,时而嬉笑怒骂,时而懊恼沮丧,时而得意忘形。有一次,他竟然趴在书桌上号啕大哭。老伴吓坏了,慌慌张张地跑过去擂门。擂了半天里面没有反应,她猛一拉门,屋里的烟雾扑面而来,被呛得直咳嗽,嗓子眼像卡着一根鸡毛。见孟一鸣泪眼汪汪,老伴问,这是咋的了?大白天咋还哭上了?孟一鸣哽咽道,菲菲她……她……忽然又冲老伴吼,没看见我正写到兴头上?老伴哪里知道他是在为小说里一个叫菲菲的女子的死而悲痛欲绝?偶尔,屋里会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呓语般的嘀咕,大多时候,是深山月夜般的寂静。老伴再也不敢贸然敲门,做起家务来也轻手轻脚。老伴把饭做好了也不敢去喊他吃,放在锅里,待他饿了再热给他吃。孟一鸣边吃边作沉思状,他不发话,老伴也不敢问话,他们像演一幕哑剧。
四室两厅的大房子,就他和老伴住,儿子孟浩然是浩然地产的老总,住在城南曲江池畔的别墅里,十天半个月回来照个面,打开汽车后备箱拎出一大堆好吃好喝的,一顿饭的工夫后又抬屁股走人。这天孟浩然临走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爸呢?母亲竖起食指,说,把自个儿关在屋里写书呢。孟浩然失笑。母亲又小声说,这回啊,看样子是铁了心,说非整个炸弹出来不可。儿子再次无声地笑。临出门,他又回头说,那我走了。母亲挥手让他走。
孟一鸣从雪花纷飞的冬天一直写到第二年银杏叶金黄,一部摞起来有一尺来高的手稿总算完稿了。孟一鸣怆然泪下,心中五味杂陈。为了这部书稿,本来就瘦的孟一鸣几乎成了一根竹竿,揽镜自照,唏嘘感叹“为伊消得人憔悴”。人瘦了,头发、胡子却荒草般疯长。孟一鸣自嘲这是“马瘦毛长”,头发扎起来居然有半尺来长,蓬松的胡子如一丛杂草,这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成就斐然的艺术家,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形象竟在不经意间完成了。
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货真价实的艺术家,他专门定做了几身款式不同的唐装。他要把自己打造成有个性的艺术家。
一个月后,孟一鸣带上他的书稿去了一趟省作协。省作协大院里他只听说过四个人的大名:马千里,高原红,羊吃草,牧云郎。这四个人被称为省作协的四棵大树,在全国也是赫赫有名的。省作协的门卫问他找谁,他说找马千里。门卫说,马千里不在。他又说,那就找高原红。门卫说,高原红也不在。他不解地问,这不是省作协吗?他俩不是在省作协上班吗?门卫说,在作协上班没错,但个个都是大忙人。他低头徘徊良久,不肯离去。门卫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自己写了一部书稿,想让高原红或马千里提提意见。门卫指了指正坐在门房圈椅上读《参考消息》的省作协副主席马六甲说,这位是省作协副主席马六甲老师,你可以请他看一下嘛。孟一鸣略加犹豫,心有不甘地说,那也行。说着就把手中的黑色提包放下来,从里面抱出一沓稿纸递过去。马六甲放下报纸翻看了几页,把书稿还给孟一鸣说,你是想出版?孟一鸣连说就是,就是。马六甲说,那你得去找出版社,北大街十字路口那里有一家出版社,你不妨去看看。孟一鸣一脸不屑地说,那家出版社啊,我看就算了,我想在津城的大出版社出。马六甲说,出版社名气越大收费越高。孟一鸣说,自己掏腰包出有啥意思?出了还不如不出!出了也是垃圾!我不分昼夜地写了一年多,出版社当然要付我稿酬!我的书稿你也看了,咋样?孟一鸣的口气相当自信。马六甲面无表情地说,好着呢,好着呢。孟一鸣有些激动,说,看看,连你都这么认为!好看的姑娘还愁嫁吗?
孟一鸣走后,门卫问马六甲,那老汉写得真的好?马六甲哀叹一番说,也就是中学生的水平。什么年代了,还是记流水账式的写法。门卫说,那你还说好?马六甲说,老汉年纪那么大,兴致那么高,你让我说啥?一盆凉水当头泼下去吗?又说,不管老汉写得咋样,这种精神让人动容!
拎起手稿,孟一鸣心满意足地走了。
出了省作协大门,孟一鸣就给老友老丁打了个电话,邀老丁来省作协对面的外婆印象喝酒,他知道老丁家离作协不远。他上二楼要了一个小包间,把包间房号发给老丁,然后就问服务员要过菜谱翻看起来。
老丁把门推开一道缝,孟一鸣正低头看菜谱,老丁瞥了一眼又闪出去,以为走错了门。出了门打电话问孟一鸣包间号。孟一鸣说,不是给你发短信了吗?202。老丁再次推门进去,孟一鸣还盯着菜谱看。他喊了声“老孟”,孟一鸣抬头说,进来啊!发啥愣哩!老丁咋呼道,真是你啊老孟!我以为认错人了。又说,你咋变成这副德行了?孟一鸣说,这副德行不行吗?老丁说,行是行,就是觉得一下子不适应,你看起来倒像个名士。又说,有些日子没见你了,打过几次电话都关机,好好的你关啥机?玩消失啊?!孟一鸣拍拍一旁的座椅说,坐下说,坐下说。
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孟一鸣这才说,这一年多来,我弄了件大事。他就把写书的事说了,不无得意地拍拍身旁椅子上的黑提包说,都在这里呢!还说了去省作协的事以及那位副主席对书稿的高度评价。老丁说,以前只知道你写过“三句半”,没想到这次整出一个大家伙啊!孟一鸣说,文坛沉寂得太久了,该扔一枚炸弹了,我要炸它个人仰马翻!
两个人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一直说到黄昏时分。
回到家,孟一鸣脚底发飘,稀里糊涂地往床上一倒,吼叫着让老伴为他脱鞋,还说高力士当年就给李白脱过靴子、磨过墨。他觉得他如今有资格提那样的要求了。要知道,他这枚炸弹扔下去,一夜成名是铁板钉钉的事。那时候,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人一眼认出。哇塞!这不是孟一鸣老师吗?能请您签个名吗?能跟您合个影吗?那些求签名的人中自然不乏青春靓丽的美女,他甚至想借机零距离地拥抱一下美女。当然,肯定还有不少商家、厂家慕名找上门来,以不菲的价格要他做产品的形象代言人。
他把书稿先后邮寄给津城和海城两家知名出版社。书稿寄出后,他有些忐忑,按理说一女不能嫁二夫,他心知肚明,但又存私心,想看看哪家开出的条件更优渥。若是两家同时相中,他该选哪一家呢?是给津城的华文出版社还是给海城的文艺出版社?他拿不定主意,电话咨询懂行的人。懂行的人说,要我说首选津城的华文出版社,人家的名头明摆着呢。他满怀期盼地等待着。有一天,他接到津城的电话,接电话时手不由得一颤,却是向他推销房产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愤怒地把电话给挂了。
三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出版社音信全无。炸弹丢进水里,不但没有掀起惊涛骇浪,反而成了哑弹。问题出在哪里?他打电话过去,人家说,若是自费出版还可以考虑,然后就报了一个高得吓人的价格。什么狗屁出版社!什么狗屁编辑!眼里除了一个“钱”字还有半点文学和良知吗?!
接下来的半年里,孟一鸣一直忙着给书稿找婆家。他一心想将书稿嫁入豪门,可是豪门的冷淡和傲慢让他一次次万箭穿心。
书稿完成后,他一直保持着艺术家的做派,唐装,长发,蓬松胡子。家属院里有人听说他写了一部书,想先睹为快,他不厌其烦地解释,等书出版了再送大家签名本。他请人刻了一枚寿山石章。他当然不会让他们先睹为快,新媳妇不到入洞房那一刻说啥也不能先揭红盖头,犹抱琵琶半遮面最好了。那些平日里一口一个老孟的人纷纷改口称他为“大作家”,因为他们发现凡是改口的每人都会得到一盒软中华。孟一鸣一律点头微笑,作谦谦君子状,这使他看起来更像大作家了。有时候,大家围在一起争论某一社会话题,见他过来,有人老远就喊,来来来,请大作家给咱们说道说道。
在外面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孟一鸣回到家却变成另一副模样。他时常魂不守舍、丢三落四,几次出门回来都找不见钥匙,炒鸡蛋时把蛋壳里的蛋液倒进垃圾桶却把鸡蛋壳倒进炒锅。老伴一再劝慰说,不就是一部书稿嘛,至于那么作践自个儿吗?他撇嘴道,那只是一部书吗?那是我老汉的一条命!老伴连连感叹,原本好端端的一个人,咋魔怔成这样!
但他并不完全灰心。这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世界有时候像个癫痫病人,谁说得清?《飘》被拒绝三十八次才出版,出版后好评如潮。《洛丽塔》《白鲸》《包法利夫人》《尤利西斯》这些世界名著哪一部没遭遇过退稿呢?远的不说,阿来的《尘埃落定》不是也屡次遭退稿吗?
孟一鸣时而沮丧,时而期待。
孟浩然回家后,母亲不无担忧地说,要不把你爸带到医院好好查查?最好做一下脑部检查。孟浩然胸有成竹地说,我自有办法让他回归日常。
没过几天,一位自称叫库清的美女出版商找孟一鸣长谈了一次。库清接过孟一鸣的手稿后说,孟老师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库清很快就找到省内评论界大腕黑白。黑白曾多次担任国家级文学奖的评委会副主任。她请黑白在凯悦酒店共进午餐,孟一鸣的书稿自然是主题,她想请黑白给书稿做个鉴定。临走时,她把装有两瓶茅台酒和两万块钱现金的礼品盒塞给黑白,戴着礼帽的黑白一再表示会认真拜读。
一个星期后,库清收到黑白发来的短信,黑白说,书稿已拜读。
库清当即打电话约黑白晚上六点在凯悦酒店面谈。黑白到酒店的时候,库清已在酒店门口恭候。
酒菜上好后,库清便开门见山地问,黑白老师,书稿到底怎么样?
黑白沉吟了一下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库清微笑着点头。
黑白说,书稿还谈不上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故事陈旧,叙述拖沓,语言直白,缺少文学性、艺术性,有好多话都是口号式的或语录式的。总体而言,尚不具备出版水准。
库清说,黑白老师,书稿我也读了,您的意见很中肯。但是作者现在却坚信不疑自己写出了一部重磅力作,他几乎活在自己的臆想中。我想,既然如此,还不如让他在臆想中幸福终老。写出一部轰动之作成了老人家的一大愿望,我想问问如何能让老人家的美梦成真。至于费用,不是问题,今天请您来,就是想听听您的高见。
黑白说,看来只好另请高手,动大手术。故事需打碎重组,结构也要推倒重来,不过还署原作者之名。书稿完成后,遵照作者意愿送津城华文出版社审读,贵公司以资助文化事业的名义给出版社捐赠一笔款项,可以搞一个隆重的捐赠仪式,相当于给贵公司做一个广告。出版社再按照合同规定的版税支付作者稿酬,当然了,稿酬相比贵公司的捐赠微不足道。书出版后,由我出面,邀请国内顶尖的评论家开一个高规格的作品研讨会,再邀请国内影响力大的电视台、报社、网站进行宣传报道,这个事情要有专人策划,要制造新闻热点。开完研讨会,紧接着再搞一个场面气派的作品签售会。当然了,签售会来的人要多,越多越好,人越多越能制造出一书难求的气氛。
这么一番搞下来,孟一鸣不出名恐怕都难。不过这一切都需高度保密,确保万无一失。否则,就成了一场同样轰动的闹剧、滑稽剧,甚至是丑闻。
库清说,黑白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大概理出个头绪来了。至于请哪些评论界大腕,请谁执笔重写书稿,就拜托您了。联系出版社、媒体和办读者签名售书会的事我委托省报一位记者朋友去做。
六个月后,孟一鸣收到华文出版社寄来的出版合同,合同中约定按定价的百分之十的比例支付作者稿酬,作品首印二万册。
出版社的合同成了一颗定心丸。大喜过望的孟一鸣像被注了兴奋剂,拿着合同四处张扬。看到的人在祝贺一番后就起哄说请客,这么大的喜事能不出点血?孟一鸣说,请,请,请!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一身酒气。老伴有一次对孟浩然说,真让你说对了,你爸那病果然不治自愈。
孟一鸣居然叼起烟斗,他慢条斯理地吐出烟圈的样子相当有派头。人们都在私下议论,孟一鸣越来越像个艺术家了。
重阳节那天,孟一鸣作品研讨会在唐都市凯悦酒店恺撒大厅举行,全国三四十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出席了研讨会,其中从津城来的大腕就有二十几名。四五十家电视台、报社、知名网站进行了现场报道。
研讨会由省作家协会主席马千里主持。马主席慷慨陈词,今天是文学的盛会,是我省文学界的盛事。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这里一下子来这么多国内一流的文学评论家还是头一次。说老实话,孟一鸣先生我此前闻所未闻,不但我没听说过,在座的诸位恐怕都没听说过吧?他曾是我市图书馆的一名收发员,大半辈子籍籍无名,我没想到他会写出这么一部厚重大气的作品来。作品大家都看了,他把名利场上各色人物的纷争和内心挣扎写得淋漓尽致,人物刻画形象传神,我看后很惊讶也很兴奋。惊讶的是我们唐都市竟然深藏着这样一位功力深厚的作者,兴奋的是这样的好作品竟然出自一位民间作者之手,还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他真是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再次祝贺孟一鸣先生!
马千里发言后,名家依次发言。黑白在发言中说,孟一鸣是我们唐都市文坛的一匹黑马,他虽然大器晚成,但他的作品却很成熟。虽说他写作时间很晚,但起点很高,别人是一点一点爬向山峰,他是一下子就站在高峰上。他对小说结构的布局,对小说节奏的掌控,对小说技法的运用,对小说人物内心的刻画,无不显示出大家气象!
来自津城的文学界大腕野水先生说,都说唐都是藏龙卧虎之地,这话绝非妄言,孟一鸣的横空出世就是例证。一个从未发表过小说的人,一个已年过七十的老者,一出手就霹雳有声、电闪雷鸣,这真令人惊诧。我好奇的是,他怎么能把如此纷繁的场景呈现得如此丰富有序!都说高手在民间,此言不谬!
大家的溢美之词如天女散花,会场里不时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照相机按动快门的咔嚓声此起彼伏。
研讨会的盛况第二天就在省内外的几十家媒体集中亮相,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更是占据各大报纸、网站的显著位置。《唐都日报》以“我市七旬退休职工写出惊天巨著终了愿”为题进行了报道。
十几家媒体记者追踪到家属院对孟一鸣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采访。
第二天,当孟一鸣出现在家属院的时候,大家纷纷祝贺,一口一个大作家地叫着。孟一鸣嘴上说,什么大作家不大作家的,还是叫老孟吧。他此刻才意识到孟一鸣这个名字暗含的飞黄腾达之意。
没过几天,市文化局的周局长在图书馆馆长的陪同下来到孟一鸣家,把一块“德艺双馨”的镀金奖牌颁发给他。周局长当场拍板,要把孟一鸣作为市里的重点作家广泛宣传,让孟一鸣这个名字成为市里文化系统的一张名片。周局长甚至还当面承诺启动“孟一鸣文学馆”建设。
孟一鸣作品签售会安排在省图书馆报告厅,五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排队买书的队伍一直排到到门外走廊上。孟一鸣埋头签了两个小时还没签完。有美女用散发着香味的纸巾在不停地擦拭孟一鸣额头的汗珠。电视台、报社的记者跑前跑后选角度拍摄。 刚签完,还没来得及歇息,几位美女上去给孟一鸣献花,那一束束各色鲜花真好看。一位有着酒窝的美女还偎依着孟一鸣合影,接着七八个美女把孟一鸣拥在中心再次合影。孟一鸣笑啊笑,笑起来根本停不下,有点像刹车失灵的轿车。
嬉闹烟花一样地绽放。
谁也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劲,直到孟一鸣倒进一位旗袍美女的怀里起不来,人们才发现不对劲,几个人上去又是抱又是拖。
孟浩然当然知道那些美女的来路。父亲出事后,他埋怨过新聘的秘书库清,整那么多美女干吗?库清一脸无辜说,还不是为了哄老爷子高兴?没想到,老爷子那么不经逗。
孟一鸣被随后赶到的120救护车拉走。
孟一鸣就那样瘫了。
孟一鸣成了轮椅上的一道风景。
只是那荡漾在脸上永不消逝的笑让人不忍多看一眼。
责任编辑 蓝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