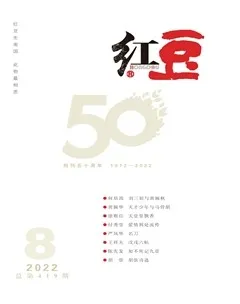脸谱
2022-12-29朱以撒
我在这个节奏明显慢下来的城市住了几天。夜幕拉下的时候,我很悠闲地坐在前排,看了三次变脸。那首配合迅疾变脸的曲子,像一群狂奔的马,充满着急切和躁动,有些咄咄逼人,似乎在追赶着什么、追问着什么。演员在急管繁弦中亮相,做了一番坚韧的身手功夫的铺垫,就要变脸了。那首急切切的歌曲,把看戏的人的情绪都鼓动起来了。到了最后,我只能听懂其中的两个字:“变脸!变脸!”一张面具在一刹那消失了,换成了巨灵神;一个甩头的动作,又变成了风神;接着是灵官、火神、王朝马汉……每个人都盯着他的脸,试图发现某些破绽以便评说,可是徒费心机。视而不见——真的要相信有这么一种状态,视觉的能力远远地辜负了心灵的期待。的确有快得让人双眼都察觉不出的速度,让你茫然不已。而且随着鼓点的密集,脸谱不断地翻新,令人兴奋地站了起来。一位变脸人进入人群,最后的一张脸谱落下,竟然是一位眉目清秀的女子。顿时掌声四起。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回头,一张色泽鲜艳的财神脸谱又回到她脸上。听懂行的人说,倒回来的这一张脸才是最见功夫的。这几个夜晚着实让人感到神奇,躺在床上,眼前是变幻不定的脸谱,耳畔是激越铿锵的锣钹声响。一个陌生的地方、一种陌生的民间艺术,在脸谱上如此经营,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如果最后那张脸谱没有落下,在这层薄薄的遮掩中,我们始终不知脸谱后的那张脸是什么样子的。
对于脸谱,我是充满兴趣的,这大概源于少年时生活在木偶之乡——木偶的表情就是人的表情的缩小,人的表情是木偶的基础。天下最生动的表情见之于脸,这是不会有异议的。这也使脸谱急剧增多,即便繁衍至千万也远远不能穷尽。脸谱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的善变,心灵是其善变的根源。这也使民间艺人从很早的时候就捕捉到了——利用脸谱之变来表达人心的幽深难测。变脸是以速度胜出的,对方还没有提防,脸色已变,猝不及防,看到一个莫测的江湖。脸谱当然都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的,五官俱在,只是都被渲染了——双目比常人大且圆睁,以至于如炬之目光,裂眦而出,令人胆战心惊。两颊往往是血红的两坨,显示出此人气血旺盛,而双眉则若喷火扬起,又浓又重,显示一个人盛怒时的狂躁。如果与一般人相同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为什么人要夸张自己的脸谱来起到震慑人的效果?我以前就琢磨这么一个起于江湖的问题。我以为是江湖险恶,人空虚无助,借助这么一个虚无的形式——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脸是像脸谱的,由于不像才产生威力;也由于没有人像他有多重价值,才值得去往离奇深处发展。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戴上脸谱,把真实的相貌藏在脸谱后,他可能就以为自己是恶煞了。我是恶煞我怕谁?他可以反弱为强,甚至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也是如此,凶徒戴上脸谱在夜间作案,显得得心应手,因为对方已被脸谱的凶险所吓倒,余下的就变得顺利多了。所谓的闹鬼往往也与脸谱有关,鬼多行于夜间,飘忽不定,加之老宅的幽深古旧,透风漏雨,很容易使人感到有一种浮游的力量回旋,摸不到,看不真切,以为灵异之物现身。由于脸谱的作用,夸张变形,脸部的正常成为非正常,也就使人把握不住,就是警方一时也难以明辨而陷入僵局——经常会运用这个词来表明束手无策,因为真实被隐匿起来,虚假站到了前面。
有谁能揭起一个人的脸谱呢?我每天不停地行走,尤其是在外地行走,不断地遇见陌生人,和陌生人说话,可是我完全不清楚脸谱之下什么是真实——在脸谱上全然看不出来,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复杂深奥,人的里外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这样的怀疑成为习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就会降得很低,不信任的情绪满天飞扬,而戒备却成为每天都要披戴的盔甲。媒体每天都有关于受骗的报道,尤其是老人的受骗率最高。由于眼力退化,他们甚至看不清对方的脸部标志,只是大抵觉得亲和恳切,于是就相信了,接着解囊。有阅历的人通常认为脸谱是不可靠的,它是一种伪饰,使人捕捉不了眉宇间的微妙。脸谱与心灵在许多时候是错位的,内心含恨,脸上却绽开笑容,让对方不知其真实用意。而笑容通常是人们处理社会、人群关系的最先释放的一个表情,至少这个表情不会让人讨厌,笑容中的讨好成分,甚至可以使事态顺利一些。一般地说,人们不会过分地琢磨对方的表情,往往是事后回味,才感到当时对方表情的确有些异样。往往两个人翻脸了,那些脸谱上的假惺惺成分才被抹掉,真实显露出来。以前我骑自行车上班,见到有人吵架,就停下来观看,看他们充满血色的脸,比工匠正在上油彩的脸谱更为生动。一个人在工作室里是做不成多少让人惊叹的脸谱的,他应该更多地走到街头巷尾去观察,尤其是乡野山村,生活的艰辛使人的表情变得十分沧桑。由于脸皮厚了、硬了,让人觉得比较固定,像一尊有泥土味的塑像。他们笑了起来,或者嘴角动一下,好像费劲地扛起一袋稻谷。我想,一定是风霜把脸上的神经硬化了,使得表情之变有些不畅。当然,我记忆中的乡野山村主人们都是过去的人物了,他们很多人已经不在,只是脸上的表情已进入了我的内心,使我时时品咂,没有因时日的过往而有所模糊。我记得当时与他们交往真是轻松之至,不需要提防他们。当然,他们也无须提防我。用不着小心翼翼地看着对方的脸,而是直来直去,对于解决问题是很有效的。这是我个人与人交往史上最美好的时光。田野劳作很苦,却由于与人交往不必费心机,苦日子里也有快乐。
整容是对脸谱本能的颠覆。古人是不赞成对肌肤给予损伤的,认为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成分,甚至是一须一发,都在爱护之列。战国初期的杨朱就是卫身的典范,即便拔一毛而利天下,他也不干。大部分人都循此而行,爱身、护身使之完好无损,也就成了一种自觉行为。人身任何一点伤害都会让人心疼得龇牙咧嘴,躺在医院或者家中休养几天。如果是容颜受到伤害,那就与性命关联在一起了——痛不欲生就是如此。其他部位受到伤害,以衣饰包裹可使外人不知,可是容颜不行,容颜是必须赤裸以应对外部世界的。如果一个人把容颜遮蔽起来,反而会让人联想到许多不着边际的原因。的确有这么一些不幸者,譬如妍美的容颜遭遇了热烈的火、可怖的硫酸,瞬间转化为丑陋。每个人都是近妍美而远丑陋的,因此无人或少人与丑陋者交往,这是非常正常的,不能责怪他人的寡情。曾经对自己出众容颜而暗生得意者,现在丑怪的程度,在我们的体验之外。甚至经过一次次手术刀的切割,历尽千辛万苦,可还是找不回来以往的那张脸谱。整容技术的出现弥补了相貌平庸者的内心焦灼,她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脸型,或者直接以某一明星的容颜为范,让自己在皮肉的痛苦中,内心无比地喜悦。变脸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一个人对于容颜的不断追求是呈递进状的,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在细部上落实,没完没了。时间久了,她身边的人也把她本来的平庸容颜忘记了,以为她本来就是如此美貌,很欣赏地接受了她。当代整容技术修改了许多容颜,说起来就是伪容颜。在修改容颜的同时,内心想法往往也被修改。按常规,人们把容颜之变寄托给整容,对外在太重视了,对内在就太不重视了,以为整容可以替代许多修炼。但是把整容说成是虚荣,我还是不同意的。我倾向于这和涂脂抹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以柔软的肌肤去贴近柔软的粉饼,是普遍的行为。就是魏晋时的男人们,也熏衣剃面、施朱傅粉,然后出门会友。如果当时有整容术,也会有人乐意以柔软的肌肤去迎接锋利的刀片。没有很强烈的爱美勇气,他还真是不能坦然地躺在手术台上。
不过,我还是赞成容颜的自然而然的进化,不必人为地去改变,也没有那么多的不幸,去遭遇烈火或者刀锋,而是如同一方红酸枝长案,时日长了,面上就泛起包浆。一个少年脸上的稚气,如果在一个中年人脸上还出现,那就有些不正常了。所谓扮嫩,就是逆时光而走,这已经被注定是不可能的了。每一个时段都有自己的色泽,很细腻的、逐渐充实的,变得厚重的,以至于让人远远看到,就大抵能够判断这个人的年龄、身份,甚至生活状态的辛苦。高海拔的黄氏家族是我见到的一个比较辛劳的家族,从脸色上看的确是古铜色的,不知是哪一位作家细致观察之后第一个以这样的色泽论说一群人。古铜色的脸代表了一种生活的艰辛和沉重,就像一个烙印,烙在脸上长久不灭。这一群人是谈不上有多少丰富的表情的,要捕捉他们的微妙变化实在困难。一个人没有表情可以吗?一般人是觉得匪夷所思的,因为人是活的,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肯定要体现在脸庞上的。如果没有,那就像某些政客,戴着墨镜,永远难以在脸上读出他的温度。如果是克制,或者刻意,首先他自己就很不舒服。而真正没有表情的这群人,我觉得是自然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表情,肢体的举止已经很清楚地传达,用不着再搭上一张脸。表情的丰富的确会让人觉得生动,甚至亲和,而实际又并非如此。表情是可以训练的,就是一个笑也分三六九等。训练好了,可以为公司的利益服务,也可以为以后跳槽做准备。我看到一些在台上又笑又跳的孩童,以为是成年人的缩影,如果和他们讲话,他们脸上过于热烈的表情,是仿成人的,失去了童趣和自然。如果拿他们和山村儿童相比,我会更接受朴素的,甚至怯生生的表情,像极了山间小路旁细小的野花,不可能绽放得很大朵,只是浅浅的、淡淡的一种流露。也许只要持有这样的一种分寸,已经足够表达内心的愿望,就不需要再扩张,泛滥了就是伪饰了。我没见过他们久别相见时那种大呼小叫抱在一起的黏糊劲,更没听说“我想死你了”。这是城里人的一种做派,表演给别人看的。他们只是淡淡说几句,邀请到家中坐坐,吃饭、喝酒。这时气氛可能活泼一些,但在外人来看,这就像是一杯泡过多遍的茶,太寡淡了。我觉得很受用,因为我也是一个脸上表情寡淡的人。有时候想给人解释一下,说明自己内心还是很丰富的,但最终没有开口——一个人表情如何,完全是自己的事。
在我供职的学校里,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其中一位是我的学生。那时我每周教她写字,顺便讲一些如何写得逼真的道理。面对一个人的时候,辨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她的姐姐来了,两人亲热地说话,不断变换位置,只一会儿,我就弄不清楚谁是谁了。所谓逼真就是如此。奇妙的是,如此的相似纯乎自然。很早的时候,古人对于相似之物就感到辨识的棘手。尽管天下树叶没有一片是相同的,但是差别太微弱了,还是让人的眼神有所飘忽,定不下来。《吕氏春秋》认为:“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由于太相似,辨人辨物都出现差错,以至于酿成不少事件。人发明了细致入微探查的仪器,可以明辨毫无舛错,可是这么一来,生活太理性了,没有一点诗意,也没有一点荒唐可以玩味。“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是多么有联想韵味的变化啊,由真假之别而衍生出许多谈资,滋润茶余饭后的庸常生活。天下有些人容颜的确相近,这使他们有了被利用的价值,由此形成一种职业,让自己成为另一个人。所谓特型,不知对于自己是福是祸。他们出现在屏幕上,化妆之后像极了死去的这个人、那个人。这些人生前都执掌着权柄,图王定霸,不可一世。他们死后仍不寂寞,有人打扮成他们的模样,走到我们中间,反而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他的替代品。扮演者除了容颜的相似外,还要沉浸在这些已经过往的人的世界里,用心触摸那些没有边缘的感受,想象那个人是如何沉思、说话、抽烟、喝酒,还有霸道耍威风骂人,眼角眉梢都是他人风情,渐渐地有点逼肖了。一次次地廓清自己从娘胎里带来的印迹,不断地取他人之形神,整个过程就是舍我非我的强化——自己渐渐不存在了。说起来这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是当代的东施效颦,却想不到会赢来了掌声,都认为是死人复生。这样,有的艺人的后来生活都被改变,专门饰演一个人,这很像文学研究机构有人专门靠研究《文心雕龙》《红楼梦》吃饭,做一个文雕先生或红楼女士,余下的作品就不涉猎了。当代对于容颜的粉饰功夫太高了,它和战国时代易容术的残忍有所不同,要温柔得多,在温柔中改变一个人。一个经过粉饰的人,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久远的历史空间,看他卷舒风云、推波挽澜。触摸那些我们陌生的人物、事件,通过科技声色的配合,最大限度地弥补我们的无知。所谓还原历史,说起来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时光如流水,流过了就不会再回头,尤其是那些玄妙无着的细节,根本无从提取。而今,都可以被制造出来,如同有人当时就在现场。归根结底,是由一张明显的脸牵引着进行的。而对于扮演者个人来说,不仅容颜发生了变化,还有他的内心——他需要天天沉浸在他扮演的那个人的氛围中,甚至那个人非常琐碎的生活也不可放过。我想,如果是我,内心肯定是非常不快活的,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呢?
我的母亲在最后的十年中,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以前她看到我时怜爱的神色,还伸手摸一摸我的脸,这十年内都消失了。她对这个世界似乎也不热烈,很淡然地面对人群,从不像有的女邻居一脸夸张、大呼小叫。腿脚还可以的时候她就去做礼拜,平静地诵经唱诗,平静地奉献钱款,回到家里则平静地读《圣经》,抄《圣经》。她是从来都不串门的,更不聊天,甚至也不倚着门框看人。四周房子盖得太紧密了,加强了街坊邻里间的串联,甚至谈兴来了,两个老太婆可以说上半天。可是对母亲来说没有什么作用,她在房间里做自己的事,外边的事与她无干。过年都是别人来拜年,她是不会去给别人回拜的。这种脾性传到我这里,我稍有修改,但也还是没有心绪与人闲聊,尽管现在的人际关系是那么重要。我觉得与人说话是很费劲的事,费心力也费时日,不如静默独处。说话要配合表情,要不别人就觉得索然无味,这于我也是一种负担。不愿意通过刻意训练来改善自己,在集体活动中就显得自以为是。还好现在有了手机,独自阅读手机中的一些信息,也算是很有趣味的独处——我在手机里储存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书法图片,我阅读之后产生快乐,但也越发静默不语。母亲晚年的表情是否也写在我未来的脸上呢?一脸凝固,一年甚过一年。我内心期待母亲有所缓解,滋润出笑意和我说话,就如同一场春梦醒来,待从头再说起。可惜,没有。想想一个人,在他的少年时代,会对周围充满了好奇,去发现自然界中的许多趣味并且融入草木中去,这是一段多么值得留恋的时光啊。人和草木、昆虫、鸟雀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后来有了电视,电视里有了许多频道,母亲也就只是欣赏《动物世界》。她琢磨动物的乐趣远远地胜过对于人的琢磨。母亲往往在看《动物世界》时才表情欢悦,随着各种动物的行止姿态,表情也发生一些变化。母亲也喜欢我们坐下来看,而面对那些炮火连天的战争片,她很快走开,她说打来打去很没意思。母亲喜欢动物世界,喜欢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员,但是对于鳄鱼搏角马、狮子捕羚羊就不太喜欢。我认定母亲有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在目击这些动物时会自然而然地快乐着。只是后来,树木渐渐被砍光了,盖上了楼房,清晨就不再有鸟儿的鸣唱了;野草也没有了,那些蜻蜓、蚂蚱、金龟子不知去了哪里,而空气中的草木气息、野花苦涩的气味,从此不会再被敏感的母亲鼻息所捕捉。还是读《圣经》吧,还是抄《圣经》吧。在我收藏的母亲遗物中,就有一沓手抄的《圣经》,阅读时让我感伤也让我心事恬淡。母亲晚年目力很差,坐在楼上大厅,远处恍惚一物,便问我是否有一只猫蹲在那儿。我说是,她就笑了。其实那是一户人家装在楼顶的一个太阳能热水器。
(原载《红豆》2013年第12期)
责任编辑 蓝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