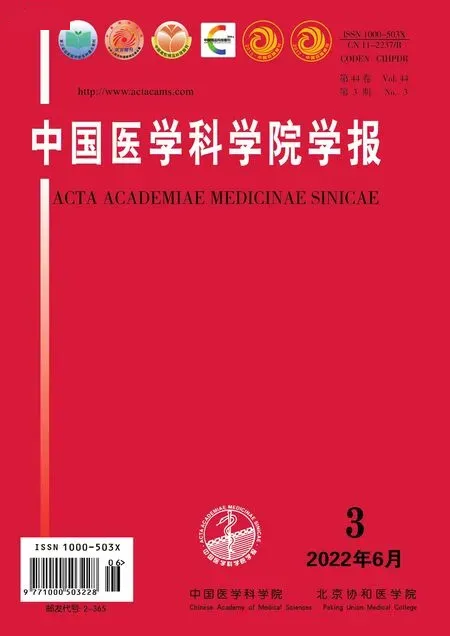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体细胞突变及其意义
2022-12-29张梦露陈婉淑
张梦露,陈婉淑,韩 冰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北京100730
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aplastic anemia,AA)大多数为自身免疫性T淋巴细胞攻击造血干细胞及祖细胞(hematopoietic stem/progenitor cell,HSPC)所致。人们很早就发现,AA患者可出现克隆造血(clonal hematopoiesis,CH),其中,可导致糖基化磷脂酰肌醇(glycosyl phosphatidylinositol,GPI)锚定蛋白缺失的PIGA基因突变十分常见,此突变可以维持AA的造血,这可能与免疫攻击下的生存选择有关[1-2]。此外,AA的发生与特定的组织相容性抗原有关。10%~17%的AA患者出现6号染色体上包含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等位基因的区域缺失,这些发生6号染色体短臂杂合性丢失(6pLOH)或体细胞突变(somatic mutation,SM)的细胞通过克隆性扩张维持造血[3-6]。然而,一些常见于其他髓系肿瘤的SM也可见于AA,在长时间骨髓衰竭(bone marrow failure,BMF)背景下,部分突变基因可以获得选择优势,甚至与AA患者不良的预后有关[1-2]。
获得性AA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都是造血干细胞(HSC)异常的克隆性疾病,也都是骨髓衰竭综合征(bone marrow failure syndrome,BMFS)之一。两者都可表现为血细胞减少,造血功能衰竭,然而在临床表现上两者又有较大差别。部分AA患者在病程中转变为MDS;而部分MDS患者还会向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AML)转化。但在一些不典型病例中,获得性AA与MDS难以区分[1]。近年来,由于分子检测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这些疾病的分子发病机制逐渐有了一定的了解。从分子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找到疾病转化的内在联系,鉴别这两种疾病,从而更精确地判断预后。
本文将综述近年来关于获得性AA体细胞性改变(SM与细胞遗传学改变)的文献,阐述这些改变的意义,并分析其与MDS的分子联系,以说明体细胞性改变在疾病转化中的可能作用。
AA的体细胞突变
70~79岁的正常人群中,约有10%检测到SM,并随年龄增长进一步增加。这种与年龄相关的克隆造血(CH)称为不明潜能的克隆造血(clonal hematopoiesis of indeterminate potential,CHIP)[7]。虽然AA中SM频率可以随年龄增加,但在儿童期发病的AA患者中,大于60%的患者都存在SM。因此,AA患者的SM并不总与年龄相关[3,8]。一些突变是一过性的,可能与疾病状态相关;但另一些突变却有致病性,并对疾病结局有预测作用。AA中也有一些CHIP相关SM,如DNMT3A和TET2突变[2]。然而,AA中出现这些SM时结局却与CHIP大相径庭。一方面可能与诊断时克隆大小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BMF背景下克隆的选择性扩张相关[9]。
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研究表明,AA的平均等位基因变异分数(variable allele frequency,VAF)约为10%,远低于MDS(约30%)[2]。与WES相比,靶向二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对较低VAF的SM检出率更高。众多NGS研究显示,AA中SM频率为5.3%~73%[2-3,8,10-12]。而在各类MDS患者中,细胞信号通路(RNA剪接、DNA转录、信号转导和表观遗传学调控等)中基因的SM频率高达78%~89%(平均每个患者存在3个SM)[13]。
AA中最常见的5个突变基因为PIGA、BCOR、BCORL1、DNMT3A和ASXL1。PIGA和BCOR/BCORL1突变者对免疫抑制剂治疗(immunsuppressive theray,IST)反应更好,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及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更长;而DNMT3A和ASXL1突变在AA和MDS/AML中都较常见,当其在AA中出现时,可能与克隆演变和预后不良相关。与MDS相比,AA中PIGA、BCOR和BCORL1突变频率更高,TET2、剪接因子基因、JAK2、RUNX1和TP53突变频率更低[2]。
理解基因的功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了解疾病转化的机制。例如,PIGA突变导致HLA等位基因功能缺失,使得突变细胞能够逃避免疫攻击[1];而DNMT3A突变时,细胞由于失去分化能力而在骨髓中积累[14];ASXL1突变通过改变组蛋白修饰,在白血病发病中起到关键作用,并增加了MDS转化的易感性[15]。
AA中最常见的体细胞性改变与其免疫发病机制有关
AA中最常见的2种体细胞性改变是PIGA突变[产生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paroxysmal nocturnal hemoglobinuria,PNH)克隆]和HLA等位基因的缺失,它们的出现提示患者的BMF可能由免疫介导,且对IST反应较好。虽然PNH克隆扩张的具体机制仍不清楚,PIGA突变的PNH克隆可以逃避T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攻击,而一定程度上挽救其BMF[1]。HLA Ⅰ类等位基因的选择性丢失有两种发生机制[3-5,8,16]。一种是6p染色体臂主要组织相容复合物(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区域的有丝分裂重组,以消灭HSC上携带致病性HLA等位基因的单倍体型。这是一种拷贝数不变的杂合性丢失(CN-LOH),在约11%的AA患者中发生[2,4-5]。另一种机制是HLAⅠ类等位基因的功能丧失型突变。通过联合靶向NGS和单核苷酸多态性阵列(SNP-A)可以检测到17%的AA患者存在上述两种机制造成的HLA丢失[3]。这些HLA等位基因的丢失不是随机的,通常发生于小部分导致AA易感的等位基因[3-5,16]。缺失HLAⅠ类等位基因的克隆可以扩张,通过逃避自身反应性CD8+T细胞的识别,为HSPC带来生长优势[3,6,16]。PIGA和HLA等位基因的缺失是免疫介导的BMF的疾病特征,它们在MDS患者中相对少见,且与AA免疫发病机制相关[1]。
Babushok等[3]的研究显示,携带HLAⅠ类风险等位基因的患者发生MDS相关CH的风险更高,从而提示了HLAⅠ类介导的自身免疫在AA中的作用。尤其在成年人中,相较于未携带者,携带HLAⅠ类风险等位基因的AA患者MDS相关驱动突变和染色体重排更多[3]。可以推测,类似于已知的AA发病率的种族差异,未来可能发现人群中与遗传有关的免疫变异造成的AA长期结局的差异。
含有8三体的HSC表达高水平WT-1(Wilm tumor gene 1)抗原,诱导CD8+T细胞对WT-1多肽产生应答,通过旁观者效应抑制非8三体的HSC[17]。同样,del(13q)克隆在IST后扩增,虽然这一免疫逃逸过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18],但8三体和del(13q)都与较高的IST反应率及更好的PFS和OS相关。最近有研究表明,IST前MDS患者8三体的克隆负荷大于AA患者,AA患者的8三体克隆动态演变方式较为多样,且在IST后8三体克隆未发生明显扩增。另外,8三体克隆的增减对AA及MDS患者IST疗效无明显影响[19]。
除HSC外,增殖过程中细胞毒性T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也可能在调控生存和免疫的基因中积累SM[20]。STAT3基因在40%的大颗粒性T淋巴细胞(T-LGL)白血病患者中发生突变,并有助于在不明原因的血细胞减少患者中诊断该病[21]。STAT3突变也可能存在于小部分AA患者中,且预示着对IST的反应较好[22]。
AA与增殖相关的SM及其结局
全基因组分析发现71%~85%的AA患者造血细胞中存在CH[2-3,8],这一发现揭示了AA与CH的紧密联系。约1/3检测到SM的AA患者有多个独立的突变,有时这些突变甚至发生在同一基因[2,9]。与健康对照相比,AA患者在JAK-STAT信号通路(SOCS7,STAT3,PTPN2),MAPK信号通路(KRAS,PTPN5,TP53),以及其他关键的癌症存活途径中发生的SM更多。这些SM可产生增殖优势,对交叉反应的HSC触发免疫抗肿瘤监测,促进免疫逃逸,或引发二次突变打击,因此与疾病发病机制密切相关[8]。
SM的发生和疾病持续时间关系密切。对AA患者晚期并发症的前瞻性研究发现,AA患者MDS/AML转化率随疾病持续时间增加而升高。IST后5~6年MDS/AML的转化率为2%~4%,随访10年后上升至15%~26%[23]。虽然AA进展为继发性MDS(sMDS)是AA的晚期并发症,但IST 6个月后通常就会发生SM。即使VAF很低,许多患者在诊断时的骨髓标本中已能发现SM[2],在诊断时就检测到SM的患者疾病进展所需的时间更短[10]。随访7~8年后,40%有预后不良SM的患者进展为sMDS,比无此类突变患者的MDS转化率(15%~25%)高,更高于PIGA、BCOR、BCORL1突变的患者(<5%)[2,12]。
此外,SM的发生还与AA患者的端粒长度缩短有关,这种端粒缩短可能是造血应激造成的,而非引起先天性BMF的如TERT和TERC等端粒维持基因突变造成的[10]。多个研究评估了AA患者克隆演变中的端粒磨损。所有患者中白细胞端粒长度处于最低25%部分的初治患者的疾病更严重,细胞遗传学演变更频繁,生存更差[10,24-25]。治疗初期AA患者的白细胞端粒总长度反映了淋巴细胞的端粒长度,而淋巴细胞端粒较短与T淋巴细胞激活和进入S期相关[26]。另外,淋巴细胞端粒长度较短还是AA对IST反应不佳的预测因子,并且与复发有关[27]。具有7单体或SM的患者端粒长度更短,在细胞遗传学改变发生前端粒磨损率更高。此外,一旦端粒达到一个临界长度,端粒磨损本身也可能导致染色体不稳定[10,24,26]。
JAK2/JAK3、RUNX1、TP53、SMD1和TET2等不太常见的突变也可能出现。通过NGS和基于SNP-A的核型分析,在<3%的AA患者中还发现了SRSF2、U2AF1、ERBB2、MPL等罕见突变[2]。与细胞遗传学异常一样,AA患者的结局可能受到特定SM的影响。DNMT3A、ASXL1、JAK2/JAK3及RUNX1突变的患者IST反应和OS较差。DNMT3A或ASXL1突变的AA患者中约40%可能进展为MDS,这远高于在无此突变的AA患者中观察到的MDS发病率(约10%)[2,9]。
亚克隆的结局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克隆大小变化不大;有的(如ASXL1或DNMT3A突变的克隆)会在病程中显著扩张,甚至可以作为MDS/AML进展前的预测指标。典型的如ASXL1,DNMT3A,RUNX1和U2AF1突变的克隆在克隆演变的患者中就趋于增大[2,28]。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AA患者的HSC减少,CH在部分AA中仅反映了受外部压力损害减少的干细胞池中的寡克隆造血,有些会在造血恢复后消失,因此必须与本质上有缺陷的恶性/前恶性克隆(如MDS/AML)的真正克隆/亚克隆扩张相区分。尽管某些SM高度可疑,但由于对克隆选择对理解尚不明确,且对这些SM的预测也并不一致,因此大多数专家不建议将克隆疾病的存在或克隆的大小作为治疗决策的决定因素[29]。
AA向MDS转化时的SM和细胞遗传学改变
与sMDS/AML转化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疾病持续时间较长,AA发病时年龄较大,端粒磨损增加,存在不良预后SM和细胞遗传学改变,以及发生多个SM(尤其是发生在病程早期和VAF较高的SM)[30]。
AA和MDS突变谱的比较提示,尽管大多数AA中发现的SM不会引发MDS,但特定基因中的SM可能与sMDS的发生有关[31]。早期检测出有害克隆有助于更好地识别高危克隆演变患者,并尽快采用干细胞移植。需要注意的是,AA中的SM通常具有较低的VAF值,但VAF与疾病结局的相关性并不绝对,即增大的有害克隆不一定预示着MDS/AML的进展;在骨髓恢复过程中,突变的克隆可能只是短暂出现,然后被再扩张的正常HSC池稀释[2,29]。这些证据表明,CH高度动态可变,且不一定对疾病结局具有最终决定作用。
诊断AA时的年龄是MDS相关突变CH的最强预测因子之一。相较于成年人(<80%),MDS和血液恶性肿瘤相关的驱动突变率在儿科AA患者中(≤60%)略低[2-3,8]。在一项AA克隆造血的研究中,82名20岁以下的AA患者中,有22%发现了MDS相关突变,这明显低于357名成年AA患者使用同样的高灵敏度NGS分析时显示的39%[32-33]。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较小的北美队列中,该研究采用WES分析,显示在儿童时期发病的AA中MDS相关SMs的比率明显较低。与成年发病的AA不同,儿童患者的CH主要由HLA缺失、PIGA突变以及儿童特有突变组成[3]。MDS相关改变随年龄的增加与HSPC突变的随机积累相一致,MDS相关驱动突变的克隆扩张也与年龄有关[7]
AA中最常见的体细胞性改变(PIGA和HLA等位基因的体细胞缺失)以及BCOR/BCORL1突变,与sMDS无显著联系。这些改变在较为稳定对中小型克隆中出现(如BCOR,BCORL1突变),或者与一些独立克隆的扩张有关(如PIGA,HLA等位基因的体细胞缺失)[2-3,6,16]。
与AA患者总体相比,其中进展为MDS的患者,在其处于AA时期时MDS相关SMs发生率更高(44%~65%比20%~25%)[10,12,31]。一些研究组在AA患者中发现了MDS相关的高风险SM,特别是高VAF值的ASXL1、RUNX1和剪接因子基因突变[2,10,12,31],而常见的与衰老相关的SM(如TET2突变)却并未显著影响MDS进展的风险[12,31]。另一项研究显示,携带RUNX1和剪接因子基因等突变的AA患者恶性转化率增加[2,10,12,31]。与健康人不同的是,AA中ASXL1突变明显提示不良预后[2,10,12,31],而在健康人群中却没有这样的提示作用[32]。
此外,细胞遗传学异常也有重要的提示作用。Negoro等[31]的研究中,约1/3 的AA患者没有MDS相关SM,但仍进展为sMDS,这些患者绝大部分都有7号染色体全部或部分缺失。有文献显示,诊断时存在7号染色体异常和复杂细胞遗传学改变者克隆演变率更高[34]。AA后sMDS的细胞遗传学异常中,最典型的变化是7单体/del(7q)[35],能在20%~60%进展为MDS的AA患者中检测到。原发性MDS中的7单体通常与TP53突变和复杂核型有关;而AA后sMDS中7单体则表现为孤立或结合了SM(最常见的是RUNX1和ASXL1突变)的细胞遗传异常[2,10,12,31]。
AA的SM和细胞遗传学异常在预测IST的疗效和患者长期生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目前的检测手段可以发现与疾病潜在进展有关的SM,但由于其随着病程的动态变化及意义未确定性等因素,在疾病进展中的意义仍难以完全预测。但密切连续监测SM,并结合临床来评估预后仍可能指导治疗[35]。未来可开发包括SM、细胞遗传异常、端粒磨损和外周血计数等预后特征的信息风险评分系统[36],可能会对更好地识别高危克隆演变患者有所帮助,从而及早地进行异基因干细胞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