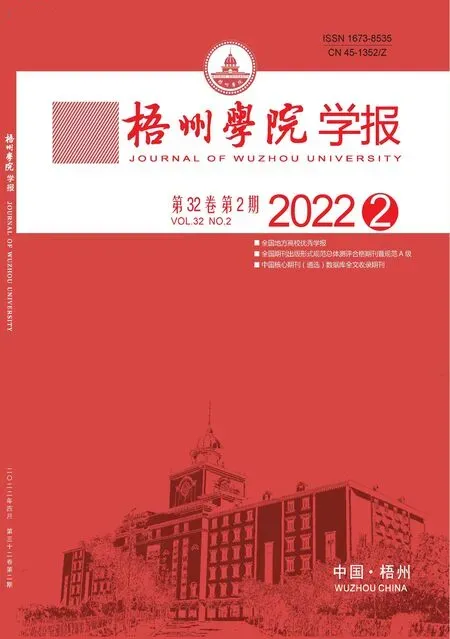论《篡改的命》写作中的“实”与“虚”
2022-12-28甘林全
甘林全
(1.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2.百色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文学是人学,是对人心隐秘之处勇敢的探险。文学同样也是生活之学,既是对生活的无穷尽的可能性不懈探索,也是生活的一种回归。文学模仿超越现实,现实同样也在模仿和呈现文学。作家进行创作,需要处理好现实与虚构的关系,虚构源于对现实的想象和超越,是作家去发现现实生活更多可能性的体现。“也许,文学所记录的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包括在某一个时代‘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将成为保持记忆、反抗遗忘的‘记事簿’。因为,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作家都无法斩断与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共振的心弦。这样的作家都是从‘现实’中走来,再经由自己的文本回到现实中去”[1]。从现实来看,近年来,媒体对被人顶替上大学的报道[2],恰恰就是东西小说《篡改的命》的“文本回到现实中”,文学的真实性和想象虚构性在这部小说中得到非常好的体现。
作家东西关注底层,书写底层。他的小说《篡改的命》也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所谓的“底层写作,是指以城市平民、农民工,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主要写他们陷入困境的生存状态和人生体验”[3]286。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东西看起来似乎是以绝望的态度,让其笔下的主人公汪长尺做命运如困兽之斗一般的挣扎。汪长尺在自己希望通过读大学来改变“农村人”这个身份无望之后(后来发现其实是有人顶替了他上大学,篡改了汪长尺的命),几乎承受了所有底层人民所承受的苦难,而为了实现成为城里人这一个祖辈遗留下来的愿望,最终通过把自己亲生的儿子送给了城里的有钱人,而这个有钱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自己的仇人林家柏,由此,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就完成了从农民工后代到城里富三代的跳跃,也就实现了成为城里人的历史遗愿。
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不断描摹出人在底层社会里的种种现实困境,并由此来探寻人类生存之路,可以说,这是一部虚实相结合且具有寓言性质的小说作品。
一、现实之“实”
很多的当代小说家的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内转”,以呈现一己之私,小情小爱的“闺房写作”①(1)注:① 指的作家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来对抗反拨20世纪50~70年代的“宏大叙事”。然而,小说家沉迷于这样的写作之时,外界在不断批评质疑文学脱离了现实,不能对现实发言,如《南都周刊》于2006年5月12日刊登的文章:《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这篇文章中列举了一些学者们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主要观点是“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物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突出的矛盾”。当然,这篇文章的观点存在着偏颇之处,不过它在某种程度指出了小说家写作过于强调“向内转”,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对丰富的现实生活、矛盾的反映和书写而存在的弊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批评质疑也是一种激励,更是一次反思的良机。很多的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外界对于过于注重“向内转”而忽略了广阔的现实的批评建议,并进行自我反思,写作重新注重“向外转”,即把写作的视角视点投向普通芸芸众生和无边的现实生活,尤其是投向那些在底层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人,表现出他们对于现实的关注和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底层写作也成了小说家们“向外转”,关注和反映现实矛盾最直接的体现。“总的来说,文学关注底层,为底层人呼吁,并为改造底层、提升底层而表达切实的精神关怀,这是作家和文学的现实精神的体现”[3]287。文学终究是反映世道人心,由“世道”(现实)而抵达人心。现实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千变万化、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不过是世间百态、芸芸众生喜怒哀乐的想象性呈现,文学创作犹如高飞的风筝,而牵住风筝的那根线就是扎实的现实生活。
在《篡改的命》中,作家东西给我们展示了以主人公汪长尺为代表的底层人民的生存与价值观之困境,掩卷沉思,哪怕是炎炎夏日,依然让人觉得后背发凉。我们之所以发凉,源于作家本人对于底层人民的逼仄的生存现实、心理活动等真实全面的展现;也源于汪长尺以为通过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而最终被证明那不过是无功而返的徒劳,甚至还付出了生命;更源于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以经济为核心的物质优位价值观念逐渐侵蚀人心,冲击着传统观念,也进一步加剧了乡下人在城里的困境。
(一)逼仄的生存现实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汪长尺的家庭可以说是不幸的,而不幸的直接根源:一方面在于他的父亲汪槐,当年被副乡长的侄仔冒名顶替了招工名额,无法实现由农转工,从而导致了他的儿子汪长尺输在起跑线;另一方面在于汪长尺两次高考的落榜,没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通过小说的叙述,汪长尺其实第一次高考成绩已经过线,并且已经被录取了,只是被牙大山的父亲通过特殊运作,最终让牙大山冒名顶替了汪长尺上了大学。汪长尺由农民变成农民工,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还是身处社会底层。汪长尺一心要改变命运,不想重复他父亲的悲剧生活,然而命运就像一张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死结的网,越反抗挣扎,伤得越重越惨,又不会出现改变或好转的机会,从而造成了一系列悲惨事件的发生。最后,汪长尺为了彻底改变他儿子汪大志的人生命运,他选择跟林家柏签订了永远消失的协议,最终跳江自杀。
从底层写作的角度来看小说《篡改的命》,其中呈现的底层人民生存困境是具有典型性的,比如农民工被包工头、开发商拖欠工资,主人公汪长尺就是在当建筑工过程中,被林家柏拖欠了工资,哪怕是用身体强行堵住林家柏的豪车,要求其发被拖欠的工资,也没有办法实现,维权无门;比如因为家庭收入不高,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拼命赚钱,哪怕是靠出卖身体也在所不惜。小说中的贺小文,原本是一个善良、淳朴、漂亮的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进城之后,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汪大志有更好的成长保障,由半推半就到享受其中地加入到出卖自己肉体的队伍。
在小说种种底层生存的困境中,应该说城乡、阶级的差距是最明显的,也是最难以改变的,甚至还存在着代际轮回的可能性。很多年前,从汪长尺一家来说,认为只要他拼命读书,通过高考上大学来改变命运,就可以成为“城里人”,如果真的考不上,可能是自己真的不够努力,或者天赋不行,但命运就像跟他们家开了一次玩笑,是明明考上了,被录取了,却被别人通过特殊运作截留了录取通知书,被冒名顶替了上大学,汪长尺一家的命运就此也被篡改了。很多年后,当林家柏非常傲慢地跟汪长尺说道:“傻瓜,像我们这种家庭,即便是白痴也能上大学。我不帮他,他外公也会帮他”[4]294。对比如此鲜明和强烈,汪长尺的“拼命”远远比不上别人的“家庭”,他可以考赢很多人,却也考不赢别人的“背景”。“‘胆子也太大了’,汪长尺嘴里喃喃,’我听说改年龄改民族改档案改性别的,却想不到还有敢改DNA’”[4]181。而“由于没有城市户口,进幼儿园都得托人找关系。托人找关系不是领导作报告,只讲空话套话,而是要送真金白银。兴泽说好的幼儿园起码要送五万或十万,差的至少也得送一万或两万”[4]192。从小说的一系列的对于底层人民生存现状的呈现,可以看到,上层阶级中权力、金钱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也正是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林家柏”,才会不断地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汪长尺”。当最后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之路都被别人无情堵死之后,“汪长尺”们不得不接受代际间的命运轮回,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固化了。
如果说经过反抗,而失败了,最终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还有点悲剧英雄的色彩的话,那么选择认可接受当初所反抗的一切,那似乎就是彻底妥协,被征服了。小说中的前半部分汪长尺一心想要改变命运,想着要过跟他父亲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也进行了诸多的抗争,有无奈,不过也有悲剧英雄的色彩在其中;而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彻底选择妥协,去认可当初他所反抗的一切的汪长尺。如向生存现实低头:“我以为我会跟我爹不一样,没想到还是一样……”[4]189甚至“汪长尺说当初我不知道现实这么狠,斗了几个回合,才明白它是关羽我是华雄”[4]242。如果生存现实过于残酷,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低头,是无奈之举,但是正如《老人与海》里所说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里的“打败”既是指身体生理性的,也包括意志精神上的。意志精神、价值取向的被“打败”才是最后的被征服。小说中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细节:当汪长尺看到自己亲生儿子汪大志被车撞伤之后,马上不顾一切地把他送去医院治疗,第二天还送去一束鲜花的时候,反而被汪大志(林方生)诬陷是汪长尺撞倒的,理由是汪长尺来看他,是因为做贼心虚。这个时候汪长尺并没有做解释,也没有生气,相反,他高兴和兴奋:“多少年啦,我一直盼望着他变成他们,现在他终于脱胎换骨,基因变异,从汪大志变成了林方生。他变成了他们,只有彻底变成了他们,他才不会吃亏,才不会输给任何人。他的心肠越硬,我就越高兴,爸,我们成功了,我们终于在城里种下了一棵大树”[4]289。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汪长尺他已经完全认可了以林家柏为代表的阶级理念、做派,并以此为乐事,哪怕这其中有很多是非常不合理的地方,换句话说,汪长尺原有的传统价值观沦陷了,已经被征服了,他已经彻底妥协了。
生存现状、改变命运如此艰难,阶级差距如此之大,逼仄的生存困境之下,作者东西在小说中也给读者真实地呈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
(二)心理的“真实”
人的喜怒哀乐,都是源于生活的点点滴滴,生活现实的变迁也会通过人的心理活动呈现出来。对于小说家来说,真实细致地描摹人物心理活动,这既是塑造鲜明人物形象的需要,更是小说为时代现实生活作证的需要。阅读东西的小说,我们时常会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凉感,一种似乎是从骨子里生发出来的绝望的痛感,让人永远无法轻松抹过。这种痛感却常常以一种看似荒诞不羁的轻喜剧的形式呈现出来,以乐写悲,就更让人觉得绝望之痛深不可测,因为我们会感觉到连以痛苦的姿态去表达痛苦绝望的资格都没有了,只能以笑代哭,这就意味着有多么的荒诞轻松,就有多么的真实绝望。小说《篡改的命》也是这样的,披着荒诞轻松的语调外衣,却呈现人物心理真实的绝望心情。小说的章节的命名,基本都是直接采用了当时的一些网络流行语,诸如“死磕” “弱爆”“屌丝” “拼爹”等,言为心声,作家的遣词造句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人物的心声。如开篇,汪家父子为了大学录取名额、复读等问题的“死磕”,是他们在无权无势却有理的背景下而进行的英勇悲壮的反抗,在这过程中,老一辈的汪槐最坚决,也最悲壮。一开始,他手举着一张写有“上线不录取,谁来还我公道”的牌子,盘坐在教育局操场,没有人理他,后来,爬到楼上,最后从教育局的楼上摔下来,双腿残废,只能在轮椅上生活。汪槐的坚决悲壮,也是一种无奈的反抗。这是因为,一方面以汪槐为代表的世代农民心中,坚信人心是善的,有理走遍天下的古朴道义;另一方面他也确信自己的儿子有读书的天赋,对他通过高考而改变农民身份,成为城里人非常有信心,是典型的望子成龙的心理呈现。这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的心理活动,让我们看到一个既执拗又无奈、淳朴又卑微的农民形象,也看到一个爱子如命、为儿子的前途而不顾一切的父亲形象。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家东西对很多流行语,或者诗词进行活用,如提到林家柏父亲的时候用“他爸是林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等;当汪长尺劝说自己的妻子贺小文不要再去出卖身体的时候,贺小文不愿意,回了他一句:“我也想干净,但你养得活全家吗?你要养得活全家,我就买一水缸酒精来消毒,从此做个幸福的人,劈柴喂马周游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4]207。这就以不无调侃的语调把贺小文的无奈和矛盾的心理刻画了出来。
小说作为人性、人情和人存在的语言艺术表达,必然需要小说家跟着人物形象走,贴着人物来写,用自己之心去体会、感悟其笔下的人物的悲欢离合,同悲同喜,感动自己方能感动别人。作家东西在《篡改的命·后记》中说到:“我依然坚持‘跟着人物走’的写法,让自己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写到汪长尺我就是汪长尺,写到贺小文我就是贺小文。以前,我只跟着主要人物走,但这一次连过路人物我也紧跟,争取让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准确,尽量设法让读者能够把他们记住。一路跟下来,跟到最后,我竟失声痛哭。我把自己写哭了,因为我和汪长尺一样,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每一步都像走钢索我们站在那根细小的钢丝上,手里还捧着一碗不能泼洒的热汤。这好像不是虚构,而是现实”[4]311。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东西不仅仅通过细致入微的细节、对话等来呈现主要人物形象的心理世界,而且也刻画出诸如林家柏、方知之、刘建平、张惠,甚至是普通的村民如张五、刘白条等人物的心理世界。当汪长尺问林家柏怎么监督和保证汪大志的幸福的时候,林家柏非常淡定从容,甚至不屑一顾地说:“用钱保证。什么承诺什么感情,统统都不可靠”[4]293。因为在林家柏这样的有钱人的心中,没有什么是金钱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对自己的经济实力非常自信。相对应的就是,他认为除了金钱以外,什么都不可靠,当然,为了金钱,其他东西都可以轻松舍去抛掉,包括尊严,甚至别人的性命。通过一个简单的对话,作家就把林家柏的这种极端的自私自利,枉顾他人尊严和性命的金钱万能论者的真实心理世界呈现出来。
到了小说的结尾部分,当汪槐为汪长尺做法事而问大家:汪长尺要投胎了,往哪里投胎的时候,青云、直上、刘建平、小文、刘双菊等,包括全村的人都是一个声音,那就是“往城里”。这样简单又充满荒诞性的细节刻画,却让我们看到农民对城市的无限向往之情,以及成为城里人的真实心理,反映出来的是城乡之间的鸿沟差距的现实困境。
文学是心的写作。作家要有世俗之心,关注芸芸众生喜怒哀乐,要有包容共处之心,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当作家“让自己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包容。作家“以自己的文学文本,描摹、建构出现实生活的镜像,表达出对一个时代心理、精神、灵魂状况的真实理解和富有个性化的判断。我相信,好作家都会克服自己懦弱的天性,直面现实,去书写时代的隐痛,而不是‘明察秋毫’之后的隔岸观火”[1]。《篡改的命》,让我们看到了底层人民的真实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真实的心理状况,作家东西都作了详实的描绘,他看似轻松荒诞文学语调,为真实而沉重的底层现实生活作证,这是小说创作真实的一面,也是小说能够被人信服的重要原因。
二、虚构
亚里士多德曾说:“叙事的虚构是更高的真实”。从本质上来说,任何的文学创作都是一种虚构,小说作品的创作更是离不开虚构与想象,它是一种真实现实的延伸,可以天马行空,万千宇宙大可应有尽有,但不能胡编乱造和信口开河。“小说以虚构和想象为皈依,文本之中无不是变形、虚拟、夸张等元素铺叙叠加,但越是挥洒自如的构思,就越有滴水不漏的推演,以生成难以阻遏的命运,塑造无法复刻的形象。”[5]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到,在小说《篡改的命》中,作家东西已经呈现了非常多的对于底层人民来说具有真实性的生活状况,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的心理感受等。我们认为,小说创作是真实性与虚构性相统一的,那么这部小说的虚构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一方面指的是“虚拟”,虚构描摹出了一系列具有超经验性的生活现实情景;另一方面指小说虚构出一种物质优位的价值观。
(一)虚拟现实
这里所谓的“虚拟现实”,指的是一种通过夸张的想象、心理暗示等手法,想象虚构某种在特定的情形之下可能出现的现实生活场景。通俗来讲,就是作家运用想象,建构出某种超经验性而又有一定现实依据的故事情节、场景。在小说《篡改的命》中,作家东西通过夸张的想象,建构了一系列的超经验的而又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场景。这些虚构出来的生活现实场景看起来显得荒诞和不可思议,不过从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逻辑来看,一切也都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这也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内在的真实。
小说中,当小文决心放弃腹中的胎儿,去医院人流的这天早上,汪长尺“一进工地心就发慌,总觉得好像要出事,看哪哪都不对劲,就连空气里都飘荡着馊味”。作者使用了“蒙太奇”组接:当小文在住处拿钱时,汪长尺在工地感到胸口刺痛;小文提着包走出住处时,汪长尺唇干舌燥,口渴难耐;小文到达医院时,汪长尺忽然感到头晕,眼前一黑,从脚手架栽了下去,一堆砖头倒下来砸在他身上。最终,被砸伤的汪长尺被送到医院,被等待堕胎的小文遇见,得以保住腹中的胎儿。这样的一种想象虚构,是有其合理性的,虽然看起来有些荒诞。一方面从人物性格来看,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它把汪长尺对于作为孩子“父亲”这样的角色的期待和责任的担当意识刻画出来;另一方面,从整个故事发展逻辑来看,保住胎儿并顺利产下汪大志是具有必然性,这样才会有后面故事的反转。因此,这样通过所谓的心灵感应而虚拟出汪长尺因受伤被送去医院,正好碰上去医院打胎的小文,最终保住了胎儿的生活现实,让读者信服,信服不仅源于表面生活现象的真实,更源于作家体验过艺术真实。
在小说结尾部分,当汪槐为死去汪长尺做法事,让他重新投胎,问大家往哪里投胎的时候,包括汪长尺的母亲刘双菊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回答“往城里”,而最终汪长尺的灵魂“一直飞到省城,飞到人民路,飞进人民医院产房”,成了林家柏与吴欣新生的男婴。这同样是一种看起来显得荒诞,有悖于现实秩序和逻辑的不可信服的生活现实,不过如果从整部小说来看,尤其是从汪家人对于改变农村人身份,成为城里人的执着追求,而这种追求似乎永远不能在现实中实现的绝境来看,在汪长尺重新投胎的时候,众人帮忙一致呼喊“往城里”,认为可以增加投胎于城里的机会,最终一劳永逸地实现了成为城里人的理想。这样的虚拟情节,是合情合理的,它更加直接形象地表明了以汪家为代表的农民对于成为“城里人”的无限渴望,而这种渴望是真实可信的。对于真实的理解,余华在《我能否相信自己》中认为:“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6]。汪长尺投胎成为林家柏与吴欣的儿子,这是非常巧妙而又富有隐喻性的情节,也是通过小说前面铺垫伏笔,顺理成章而来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成为城里人是包括汪长尺在内汪家多年的愿望,现在有机会重新投胎,那么一定是选择“往城里”的;另一方面,从汪长尺对于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诬陷为撞伤肇事者,而不是救助者,他没有任何解释和不高兴,相反,反而觉得汪大志已经脱胎换骨,基因变异,真正彻底变成了“他们”(城里人)了,不会吃亏,不会输给任何人而高兴不已。成为林家柏的儿子,这也再次表明汪长尺已经完全认可了以林家柏为代表的城里人的价值理念。换句话说,他已经被征服了,传统的农村文明伦理道德之根在强大的、无坚不摧的现代城市文明的侵袭之下被连根拔起,最终完成篡改的命。
谢有顺说:“没有作家所看见的真实,只有作家所体验到的真实。”[7]可以说,小说作品中千奇百怪,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塑造,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故事情节的开展,千变万化、沟壑万千的环境氛围的营造,那都是作家本人对于现实进行体验和感悟之后,用文学的语言表达他们眼中和心中的“真实”。因此,我们可以说,作家永远是现实主义者,因为,真实的就是现实的,虚构也是更高的真实。
(二)虚构的价值观
我们认为:好的小说作品是作家在作品中实现了隐藏自己与表现自己的平衡,“表现自己”是为了让读者能懂自己,“隐藏自己”是不希望读者轻易把自己看透,所以要追求二者的平衡。这其中的“隐藏自己”部分,自然包括作家的价值观,当然,小说作品中隐藏的,或者直接明示出来的价值观是经过虚构,艺术加工的,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中作家本人的价值观,它代表的是小说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价值观。那么,在《篡改的命》中虚构的,或隐或现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作家东西在这部小说中虚构呈现出的物质优位价值观,而且这种价值观并成为人生唯一追求和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以及轻而易举地放弃原有的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价值观,这都是扭曲的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作家东西对现实的思考与发现,为此,焦虑不已,于是用几乎绝望的笔调写下这个带有喜剧精神的悲剧[8]。他知道要想解决现实问题并摆脱困境,首先必须要实事求是,勇敢地不留情面地把问题和困境呈现出来,而不是刻意回避掩饰,这是一种智慧与良知,也是一种有勇气和担当的体现。东西坚信:“不顾一切的写作,反而是最好的写作”[9]。曾攀也认为东西“不顾一切的写作”就是一种担当的勇气,小说所记忆的,哪怕是这个时代里“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应该是作家良知的体现[5]。
关于物质优位,是指“一切从物质需要出发,物质决定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消费意识形态衡量一切、表达一切的出发点”[10]。小说《篡改的命》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恰恰体现出了物质优位的价值观,以城里人的生活作为理想追求和衡量一切的标准,金钱物质至上,物质代表一切。有钱有权者占尽所有的优势,完胜一切,包括地位名声、荣誉,甚至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相反的,底层人民如汪长尺一家,却常常到处碰壁,苟延残喘般活着。
有钱有势的代表人物——林家柏,他可以让警察对他点头哈腰,明明他是被告人,在法院却像是在自己家一般,为了胜诉官司,甚至可以“篡改”别人的DNA;他可以趾高气扬地骂无权无势没本事的汪长尺“就是一个寄生虫,你有本事生,却没本事养,去死吧,你这个人渣”[4]291;他可以说出:“像我们这种家庭,即便是白痴也能上大学。我不帮他,他外公也会帮他”[4]294的大言不惭之语。小说中,还叙述了林家柏的尿液都是“金黄透明”,而屌丝汪长尺的却是“浑浊偏黑”,通过对比,从而让汪长尺立刻心生自卑。
另外,有权者,也是物质优位拥有者。他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别人录取名额,从而让自己飞黄腾达,让别人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中。如,汪槐的招工名额被副乡长的侄仔顶替,汪长尺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牙大山的父亲通过特殊运作截留,并冒名顶替上大学等,可以说一顺百顺,赢者通杀。
相反,底层人民,因为象征着物质权力、势力、金钱等的匮乏,只能苟且活着。如,作为汪长尺妻子的小文,也在家庭的经济压力之下,一步一步地走上出卖身体之路,一开始有过挣扎,痛苦,慢慢地就接受了,甚至是乐在其中了。还有,汪长尺,更是遭遇了太多太多的痛苦,甚至为了改变自己亲生的儿子的命运,实现成为“城里人”的目标,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他送给林家柏。
小说中这些不无夸张嫌疑的故事情节的设置,恰恰是作家东西为了凸显两个阶层的人悬殊的生活状况,强调现实社会中城乡差距大以及社会上对于物质优位价值观的过于推崇,甚至成为唯一的人生目标,从而造就了无数的汪长尺式的悲剧而采取的写作策略。读了这部小说,我们感到后背发凉,我们伤悲不已,但是正如谢有顺所说的:“只要我们还能悲伤,世界就还有希望”[11]112。平凡的我们,还会悲伤是因为我们的同情心,恻隐之心未被世俗,如小说中所体现出的物质优位的价值观所泯灭,我们还心存善良之心,我们还能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我们还会为他人的困境伸出援助之手,因此这个世界还是温暖而有希望的。小说中有极端的故事情节,那就是汪长尺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了林家柏,但是这一“送”并非绝情,恰恰充满了对孩子的爱,一种变形的爱。汪长尺这一送,除了绝望,还夹带了些许希望,因为他觉得只要孩子进了林家柏这样的家庭,将来就会幸福,而只要孩子幸福,他什么事都可以干。真的是父爱如山。作家东西也是相信这个世间还是有爱和希望的,他曾说:“绝望的书写恰恰是不想让人绝望,我虽然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11]111。是的,小说不需要提供廉价的乐观与希望,真正有力量的希望从来不会轻易出现,必须经过凤凰涅槃般的历练才能出现。阅读《篡改的命》,我们会感到绝望的,我们也会泪流满面,但是我们依然有爱,毕竟“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文学终究是与人为善的事业,也是给人温暖和希望的伟业。作家东西在小说《篡改的命》中,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以乐写悲,运用轻松的笔调呈现了让人绝望的底层人民的现实和价值观悲剧,以荒诞呈现严肃思考,又以绝望呈现希望,这是一种有写作难度的灵魂叙事,也是他对芸芸众生深切关怀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