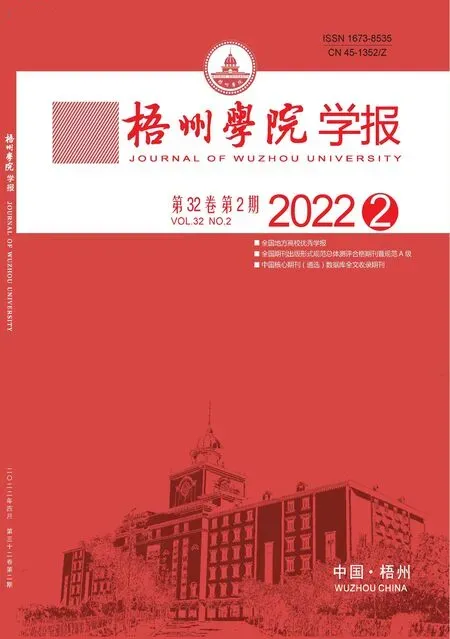论《狂人日记》叙事策略中的衔接艺术
2022-12-28谭为宜
谭为宜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河池 546300)
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是当之无愧的,作品展示了鲁迅先生作为时代知识分子“立人”的责任担当,表现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的人性关怀,我们不仅从作品中能够领略到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张扬人性,批判封建文化思想的烈烈文风,同时也能从作品中欣赏到一位小说艺术家高超的叙事策略。《狂人日记》虽是鲁迅白话文小说的开篇之作,但出手不凡,因此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众多文论家的关注。如,吴虞的《吃人与礼教》(1919年)、傅斯年的《一段疯话》(1919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郎损(茅盾)的《读〈呐喊〉》(1923年)、张定璜的《鲁迅先生》(1925年)[1]等,都从不同角度作了评价,此后的评论家更是不计其数。而纵观这些评述,多是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封建礼教“吃人”的宏大主题,或是在创作手法上探讨作品的结构特色,或是揭示开头小序的作用与内涵,或是赏析叙事策略对于西方文学的借鉴与拿来,却较少有顾及作品中细微的语句衔接技巧,而这恰恰是鲁迅“辛辣的讽刺,冷峻的幽默”的语言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狂人日记》表情达意的手法是多样的,而且作者的观点十分隐蔽,“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2]。鲁迅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一个个语言的细节中,在作品文字的表面上是一个“狂人”思维的再现,这杂乱无章,语无伦次的叙述在塑造“狂人”形象的同时,也在为主题的揭示做铺垫,读者首先看到的是语言的深刻中有几分浅易,严肃中有几分俏皮,泛指中有几分特指,流畅中有几分错愕。正是在语句的衔接上作者的用心良苦,利用转接与顺接来进行“疯话”的布局,读者正是在作家精心设计的导引下,由错愕而生疑,由生疑而探求,由探求而大悟,语句衔接上的转接和顺接从一个小的侧面表现出了鲁迅先生在叙事策略上的匠心独运。
一、异于常规的“转接”叙述
为文章者,是十分注重叙述的顺序的(小而言之也就是语序的安排),在文意上常常会致力于前后的顺承与照应,正如《文心雕龙·章句》中所说:“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3]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如果作者有意而为之,在叙述过程中突然改变了常规的顺序,似乎前言不搭后语,然而又与全文的意旨相暗合,这种特殊的叙述手法造成了阅读的错愕,却达到了作者所要暗示的表达效果,同样起到了“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的作用,这种异军突起的叙述手法我们姑且将之命名为叙述的“转接”。
(一)章节的转接
《狂人日记》中语义大的“转接”处约有9处。第一处就是文言的序言与白话文正文的转接,这是一种章节的转接。对于这段“序言”,学者们进行了颇多发隐和阐释。
《狂人日记》包含了两重观点和两重叙述:一种是“日记”的叙述,“狂人”的感受;一种是“小序”的叙述,对“日记”的否定。《狂人日记》两种叙述观点是异常鲜明和强烈的对立,所以两种叙述语言是相反的:一种是文言,一种是白话[4]。
小序和正文的对立还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人性思考。狂人只有在发狂时,才能挣脱了社会的束缚和文化的压抑,才会恢复本性,揭示封建礼教的本质,成为一个反封建文化的斗士;狂人精神病一旦痊愈,精神恢复正常,他就会慑于封建的专制,回归到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群体,从而丧失了叛逆性、反抗性。
而文言与白话文的对立,彰显了白话文运动的主张,生活化的、平易、清晰的白话文更能适合于阅读的大众化,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同时,文言文作为书面语,是整理而修饰后的语言;而“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日记方符合“狂人”出自“心言”的实录,将两者作一鲜明区别,我以为这也许正是鲁迅要做这一“转接”的另一个重要目的。须知小说家的所有表达策略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读者确信,所读到的都是真实发生的。
(二)语义的断接
小说中叙述的转接还体现在语义的断接——叙述中由A突然转到B,而A、B之间本是毫无关联的(本是断开的,被作者强行接上了)。我们看小说开篇第一节的“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一下由见到久违了30多年的某人引起对自我反省的历史性,再一下跳到了眼前“赵家的狗”可怕的现实性,就是在这种“语无伦次”的思维再现中,狂人的人物特征一下就显现出来了;同时又为下文要揭示“吃人”这一核心事件的叙事作了很好的引导和铺垫。
最典型的断接表现在小说第三节的末尾,也是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处,大家对这一段话都已耳熟能详:“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历史没有年代”:既暗指这些历史是浑浑噩噩的,并无确切的年代;同时又指不需要确切的年代,“从来如此”。先是用小锤敲改,最后大锤搞定——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这冠冕堂皇的大纛成了封建卫道士的遮羞布,充斥了他们书写的每一个年代。然而这些所谓的“仁义道德”都是“歪歪斜斜”的,不正经的,从而在狂人的内心里导出了它的对立面,原来就是“字缝里”(骨子里)的“吃人”——一锤定音。“仁义道德”与“吃人”的对立是断接,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本质上居然是统一的,他们正是用“仁义道德”来掩盖其“吃人”的本质,这又仿佛是一种顺接了,作家对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柳叶刀似的解剖,就是借助这段精彩的文字来实现的。
(三)语义的转接
语义的转接也可以说是一种异常的语义的转折关系。第二节,头一段先说赵贵翁和七八个路人“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然后在第二段来一个转折,“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交代了对于企图加害自己的人的疑惑和恐惧,然而又似乎显得毫不在意,这异于常人的“走路”,是因为疯子在用他的思维看出了常人的“异常”,看出了他们眼神的怪异,以及他们笑声中掩藏的凶险,只有突破了表象看到了本质,才会有所发现,于是才激起了他思维中对于外来的“迫害”的抗争性反应。
这种语义的转接好似“指桑骂槐”,在叙述中,把原句的本来意思引向“歧途”——如同向心力一般的指向主题。这还表现在第三节的第三段,是写一个妇人的言行,“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由指向小孩的娇嗔的语言转接到指向“我”的暗藏杀机的异常神情,一下把一个平常妇人责骂孩子的言行导向了“吃人”的主题,这种只有狂人才会产生的联想,正是作家一步一步精心设下的“局”,这才符合“迫害狂”狂人的精神特征,这才是作家要的艺术效果。
(四)反衬式的揭示
在第十节中,在狂人劝大哥不要“入伙”“吃人”的队伍的一番对话后,小说的情节发展是,大哥开始发怒了,对着围观者(此后“围观者”在鲁迅小说中成为常态的“看客”)“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用“大哥”的“正常语言”来反衬疯子思维和语言的“反常”的“错接”,其实是为了揭露封建卫道士是永不肯悔改的,他们顽固地“以名杀人”。我们可以推而广之,什么“三从四德”,什么“万恶淫为首”,什么“僭越犯上”,等等,都是为了安上一个罪名,以便名正言顺地“吃掉”的借口。
(五)逆向的语义延伸
语义的延伸其实是多向的,有顺向的延伸、逆向的延伸和发散的延伸。小说中就出现了逆向的语义延伸。我们来看第四节的第五段,之前交代了一个披着“医生”外衣的“吃人的人”被“我”识破了,便笑得十分快活,充满着“义勇和正气”,以致于“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照此推理,他们似就应该有所收敛了。然而小说写道,“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这一转接的真正目的,就是交代了“吃人的人”为何要“吃人”,作家继续对封建礼教的本质和现象进行揭露与批判,那就是封建统治者对民众觉醒的恐惧,对突破囚笼的精神的扼杀,对于叛逆者的疯狂镇压,对“异端”思想的侵吞。
再来看第八节的第二段,这时换来了一个“满面笑容”的年轻人,但是依然被狂人识破了,狂人看出了他的笑并不是“真笑”,小说写道,“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来人很自然地加以否认,“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然而就是这一句看似平常的话,让狂人听出玄机,来了个“疯”味十足的对话延伸,“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对来人步步紧逼,使来人逐渐窘迫,穷于遮掩;狂人继而追问“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样的语义延伸逼得此人只好遁形。这又是小说的一个高潮,作家用了一柄大斧,砍下去的是对一切旧有的所谓“存在”的权威发起哲理性的挑战;同时又是一记棒喝,让“铁屋子”里沉睡中的人们惊醒,向“从来如此”宣战,这是多么需要“狂人精神”的呀。
最后一个语义的逆向延伸是到了小说的最后一节第十三节,这一节只有两行,16个字,却是通篇的最后一个高潮,鲁迅先生借狂人之口喊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光明的大背景下的,他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正因为这样,疯子有了一个异于前文的期盼式的判断——“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但接着又有一个急转——“或者还有?”疯子担心已有或将有“吃过人的孩子”,于是就有了惊雷般的“救救孩子”的呐喊,用一个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触点,催促人们的觉醒和行动。这段叙事是转接——转接——顺接的,用陡转的情势来结束全篇,实在是发人深省。
二、常规中顺接叙述的机趣
从语言技巧上看,《狂人日记》中叙述的顺接比转接似乎更见功力,后语看似紧承前言,但是又要能琢磨出前言不搭后语,正所谓“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3],鲁迅先生真可谓得了《文心雕龙·章句》的精髓,因此小说也更有“狂人”(疯子)的特征,从而也就更有幽默的机趣。
(一)跨越式的推理
这种顺接出现在第二节,狂人想起早上出门时赵贵翁等人的奇怪表现,进而联想到20年前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古久先生很不高兴”,于是有了后面的判断,“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这种看似平常的推理,其实有很大的夸张的成分,眼前的事为何能与20年前的事相连?既不认识,赵贵翁为何要“代抱不平”,甚至还要“约定路上的人”——太不可信了,这真是疯子的思维呀,颇有些荒诞,但仔细推敲,疯子的思维只是将常人的思维路线简化了,将散点用直线连接起来,于是看似不可信的推理就顺理成章起来了。
另一处是在第五节的第二自然段,先是借“大哥”讲“易子而食”的典故,和“食肉寝皮”的成语,以及佃户炒食恶人心肝的传闻,继而由疯子引入现实,通过“狂人”式的推导实现了新的跨越:“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几千年的封建礼教被潜移默化了,习以为常了,人们甚至会接受这种反人性的封建伦常,于是“吃人”也就披上了“仁义道德”的外衣,只有狂人才能看破这“皇帝的新装”。
另外再看第七节,疯子思维的跨越式的跳接几乎让读者眼花缭乱,作家先由伪善者企图逼对手自戕,再吃对手的“死肉”,从而延伸出了一种叫“海乙那”(即鬣狗)的动物,是一种连肉带骨头都能嚼食的凶兽,十分恐怖,“想起来也教人害怕”;然后顺接的是“‘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这种跳接又是那么“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结尾跳落到前文的老医生的身上,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又确乎有某种联系,简直让读者分不清这是疯子的思维,还是作家的诙谐和幽默。
(二)剖析式的演绎
前文提到了,在第三节中有一个妇人在责骂孩子时说了“咬你几口”的话,疯子联系到佃户们打死了一个恶人炒其心肝来吃的话,都是“暗号”,接着有一段生动精彩的描写,“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把一切言语一切表象都往“吃人”这一命题上引,进而对“白厉厉”的牙齿作了一个荒诞的联想,这正是“语颇错杂无伦次”的意识再现,俏皮、诙谐、荒诞的疯子思维和语言,与严肃、认真、深刻的主题巧妙地结合起来,获得了强大的艺术效果。
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疯子终于发现,由于生活在一个“吃人”的大环境里面,因此也在无意中吃了人,“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在教育了“大哥”后,狂人又开始反省大“我”(有4000年吃人履历的)和小“我”(狂人),其实也就是“旧我”和“新我”,只有对旧“我”的彻底改变,才有前途,否则“难见真的人”!在这一番超常的疯话演绎中,让人读出了作品的“微言大义”。
再看第十一节的第四段,疯子想起了妹妹的“被吃”,针砭的锋芒再一次对准了封建伦理中的那一套说教,举譬的虽然是“割股疗亲”的愚孝,实则是对“大哥”那样的封建卫道士所进行的深刻的揭露和抨击,同时对于“母亲”的形象描写也十分耐人寻味,她既然赞同“割股疗亲”,那么“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刻意轻佻的演绎所造成的幽默,反而会激起沉重的回味。妹子死的时候,母亲只会一味地哭,“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为何伤心?疯子没说,有可能因为母亲对于妹妹的被吃所持的麻木、容忍和纵容的态度而产生的懊悔所致。
(三)双关语的暗合
小说第四节写的是一名老医生前来诊治的故事,是有具体情节的,狂人把诊治过程中医生的把脉、医嘱的语言、医者的神态都赋予了“双关”的含义,并且都像土匪的暗语被狂人一一识破,因此特别理直气壮,形成一种诙谐的气氛,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又耐人咀嚼。我们不排除人物形象在这里还有暗喻的成分,被狂人揭示出来,单从语义上看,狂人把医者看成是“刽子手”一般,只见“他满眼凶光”,但又“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谁知瞒不过狂人,识破了他“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于是才有了一段针锋相对,又语涵双关的精彩对话,读者不妨再读读原著,文中对老医生诊病神态的描写,对狂人动作反应和心理的描写和对两人的语言对话的描写,都惟妙惟肖,符合各自的身份状貌。我们单是从狂人的一句斩钉截铁的“可以”,就仿佛看到了当时那滑稽、尴尬的情态,会自然而然地投来会心的笑声。然而狂人一步一步顺接的思维和言行,跳棋般地与庸常生活中的诊病交替发展,又会让我们去寻找这简单的字面下所掩盖着的鲁迅先生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语言艺术,结合后面的疯子的心语,“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这正是“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5]。这样的思维衔接十分巧妙。
(四)探因寻果式的构建
我们来分析第六节的两行字,第一行是即景:“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第二行是顺接的议论性抒情:“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第一行有狂人的病态,才至于说“不知是日是夜”,进而扯出赵家的狗;第二行则是一种哲人的思考,谓之“大愚若智”或“大智若愚”似乎都可以,并且将狮、兔、狐的凶、怯、狡并列起来,既是抨击的鹄的,又是国民的“病苦”;既可单指,也可复指。从整篇小说的篇章结构来看,又有了节奏的变化,语言的表现力也更为丰富了。
(五)碎片连接式的深度劝谕
第十节是整篇小说篇幅最长的,详细地描写了疯子劝大哥不要吃人的对话情节,但作家要在一番说教式的语言中表现出疯子的思维特征,便把语言敲打成历史的碎片,用“吃人”的概念串起来,这些语言是顺接连片的,但思维是跟不上的,甚至有的相互抵牾,还有语病,似乎混乱的思维中没有理清人、猴子、虫子变来变去的逻辑关系,似乎“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语焉不详,但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又能让读者意会,让读者能够进入到狂人的思维中去,这就十分巧妙。接着狂人历数了“吃人”的历史,最后劝大哥道,“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减租”时说的话,被疯子在“吃人”这件事情上等着了,我们不必哂讥疯子的荒唐,其实这颇似相声中的“包袱”,是一种语言的机智。
(六)定盘式的“收官”
这种顺接出现在文末,也就是第十三节,读者诸君此时也许要笑我的昏聩了,前文已将之归入到了“转接”中的。是的,从本段的语序上看是转接,但从全文来看,这是一个最大的“顺接”,就像围棋中进入收官阶段,这是全盘的最后一颗辉煌的“官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一方面,出于“呐喊”的需要,“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6]Ⅸ;另一方面,深受“进化论”影响的鲁迅,主张“希望是在于将来”[6]Ⅷ的,“孩子们”就是社会的将来,希望的将来。
日记中的狂人其实是一个精神上十分健全的反封建斗士,鲁迅先生之所以要给读者一个“狂人”的外形,其实是为了借“疯话”来揭示一个病态社会的内质,这个社会的病态存在于鲁迅归结的“从来如此”,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思维的惯性已被层层包裹住了,需要“疯话”予以揭露和痛击。同时这也是小说创作艺术审美的需要使然,作为“疯话”,它就首先应该让读者明显感觉到这就是“疯话”,在这一前提下,鲁迅才借助于叙述的“转接”和“顺接”,从而形成了“错接”,为“疯话”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在病态社会里的疯话,其实是最本质、最健康、最具真理性的表达,从而使《狂人日记》成为一部思想和艺术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