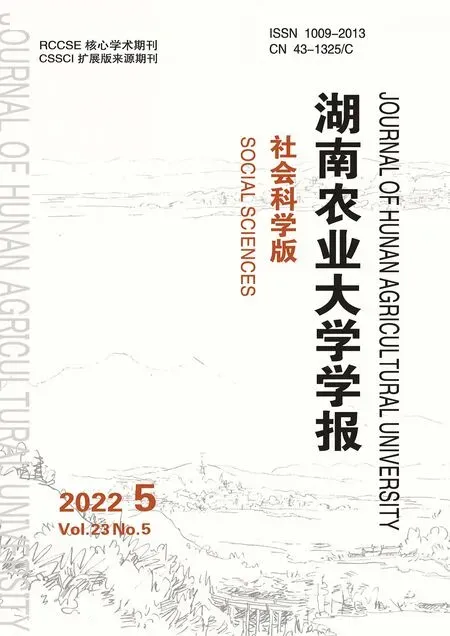乡村振兴视角下庙会的文化转型及其资本价值——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分析
2022-12-28马慧马蔚
马慧,马蔚
乡村振兴视角下庙会的文化转型及其资本价值——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分析
马慧1,马蔚2
(1.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
庙会这一民俗活动是中国乡土文化的具象形态与实际载体,在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其结构与功能发生了转变,由民俗表象转向文化资本。蒙陕边界村落的庙会在并存与联结的现代转型模式中激发出了庙会文化的现代活力,形成了促进乡村振兴的文化资本价值。在本体层面,庙会作为文化资源和资本,以其产品资源形态使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在结构层面,庙会民俗以其古镇场域空间优势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文旅产业集群;在自生层面,庙会作为结构遗产,以其自生结构合理配置乡村资源,形成了边界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资本优势。
乡村振兴;庙会文化;资本价值;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将“繁荣兴盛农村文化”“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列为重要内容,同时,“支持农村地区……民间文化传承发展”也被纳入乡村振兴战略[1]。庙会作为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乡土文化的具象形态与实际载体。20世纪末以来,庙会逐渐由民俗活动的表象衍化为文化遗产的形态,并成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如何发掘这一遗产资源的新功能,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更好地适用于乡村振兴,是当前研究庙会文化的重要议题。
20世纪以来,大量海内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对中国庙会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2-5],包括庙会的起源、演变轨迹、内容特征、功能、类型及基本结构等。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学者们开始转向关注庙会的现代转型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第一,庙会组织方式的转型。古代庙会是由地方士绅与民众自发组织的宗教活动,国家不直接干涉[6],现代庙会中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组织者,肩负安全管制、财政支持等多重任务,国家在场意义明显[7]。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庙会是由不同纽带维系起来的,是村民、政府、剧团表演者、商业经营者多重关系网络共同构成的庙会团体[8]。第二,庙会活动内容的转变。一些研究表明传统庙会是集仪式、宗教信仰、贸易和表演为一体的活动,当代庙会已演变为地方政府支持的大规模文化活动[9],宗教内容被淡化,经济交流、休闲娱乐和民俗旅游成为主要内容,且保留了中国庙会传承的祈福、崇尚和美的文化内涵[10]。庙会经历了早期的祭祀祈福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乡物资交易会,再到当前的民俗文化节,形成了庙会内容从宗教到商业贸易、再到文化旅游的转型脉络[11]。第三,庙会结构、功能的转型。在现代化、非遗化的大趋势下,庙会从传统的农村型、商业型转型成集宗教、民俗、商业、旅游、娱乐于一体的现代都市型文化庙会[12],这一转型使庙会发展经济和服务社会的功能成为重点,在假日经济和旅游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13],成为传统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14]。
目前关于庙会转型的研究主要是揭示庙会的传统功能弱化与文化旅游价值,其研究深度和现实价值有待进一步提升。首先,对庙会结构、功能的探讨还停留在事实表面,未能对其深层结构进行理论探索,无法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研究的话语体系。其次,就现实价值而言,庙会与乡村振兴的关联研究相对较少,且并未对庙会转型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因此,笔者尝试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分析庙会这一民俗现象,探讨传统庙会的现代转型及庙会文化遗产对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新价值。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个案
庙会作为中国民间活动及节庆习俗,盛行于全国各地。传统庙会以民间信仰、商业贸易为主,现今的庙会大多已经变成一种旅游、娱乐的形式。但传统庙会的现代转型并非简单的古今对比,而是要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挖掘庙会的新功能、新价值,进而实现庙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乡村振兴大趋势的推动下,探讨传统庙会的现代转型、挖掘庙会的社会经济价值是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重要动力。张继焦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解释了传统与现代动态的关系,认为“人们既不必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遗产,也不必一味完全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特征”“传统和现代是并存或联结的‘连续谱’”[15];并倡导以本体结构—外在结构—自生结构三个维度分析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本研究将利用这一理论探讨当前庙会文化现代转型模式下带动乡村振兴的内源型发展路径。
因此,综合以上理论,本研究认为,庙会在当前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其内容已经发生结构性与功能性转变,从民间信仰衍化为文化遗产。发掘这一遗产资源的新功能,使其更好地适用于现代产业发展是庙会民俗现代转型的重要航向。从并存与联结的庙会文化转型新模式中,挖掘转型庙会的新功能,实现传统与现代并存、保护与利用联结的融合发展路径,对促进乡村振兴有重要作用。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分析庙会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资本价值,认为庙会民俗作为文化资源本身具有可开发利用性,把其放入古街区、古镇等场域中可形成更大的产业链,以其自生结构合理配置这些乡村资源,能够形成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发展路径。
本研究以内蒙古准格尔旗长滩村庙会开发为个案,对庙会及其所在古镇空间内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商旅发展展开考察。该村位于百里长川最南端,是该旅游线路上的重要节点,汉代已有人口居住,明清时形成村落,是“走西口”的重要通道,历史悠久,遗址古迹颇多,有清代康熙年间所建正觉寺(吕祖庙)、咸丰年间墓碑、解放初期牺牲烈士纪念碑等。该村包含10个自然村,总面积69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4万亩,林地面积38.5万亩[16],常住人口632户2113人[17]。近年来,随着驻村企业的增加,长滩村人口流动加速,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在庙会期间,游客人数大幅增多,为该村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据统计,每年庙会四天可接待游客四万余人,创收数十万元。因此,对该村庙会进行个案研究,了解庙会资源如何创造经济动力,如何利用其现代转型实现乡村振兴与内源式发展,可以为广大边缘乡村利用地区特色文化遗产实现乡村振兴与内源式发展提供新思路。
三、并存与联结:庙会文化转型的新模式
庙会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依托寺庙,以民间信仰形式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它能够延续至今而未消逝就在于这一文化固有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庙会天然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特征使其能在继承传统内容的基础上,取得社会认可的时代变异,达到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调和[18]。它的这种自行调适功能使传统庙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形成时代变异,从而创造出庙会文化结构转型的新模式。
(一)并存:“旧”与“新”的二元耦合
庙会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已存在数千年,从三皇五帝原始信仰到商周宗庙祖先崇拜再到汉唐佛道神祀,直至遗存于今的庙会民俗,它融合了中国社会“旧”与“新”的多种文化元素,构成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二元交织的文化生态。可以说,它的一头连接着过去和传统,一头连接着现在和未来[19]。故而,兼顾其文化形式的“旧”与“新”,有利于实现庙会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形成庙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之间并存的创新型关系。
从纵向的历史维度来看,庙会文化产生于过去,是传统文化的代表,集聚了诸多旧时的文化内容;同时,当前庙会文化作为中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内含了很多新的时代色彩。庙会文化这一“旧”与“新”的内容耦合决定了其时代转型就要囊括传统与现代,既要延续传统,又要迎接未来,通过继承与发展才能使它拥有新的生命力,成为活态的优秀传统文化。庙会文化不是过时的旧物,而是时代的遗产。“没有传统,现代化没有发展的根基;没有现代化,传统就失去了新的生命力”[20]。因此,庙会文化转型不应该恪守传统,漠视时代变化,在脱离现代生活中生存;也不能只关注现代,将传统遗弃,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是应该综合“旧”与“新”的文化元素,在二者耦合的基础上适应时代需求,实现文化转型。
从横向的社会功能来看,庙会文化转型的目的在于解决其本质的传承性与发展性问题,无可避免地涉及“旧”与“新”的关系讨论。庙会文化要实现其传承与发展,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其“旧”的根基,旧的内容是庙会文化的本原与力量,脱离了它,庙会文化的发展将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次,在“旧”的基础上创“新”,在传统的根底中发展是解决庙会文化转型中继承性与发展性问题的关键,也是创造性转化庙会文化时代功能的重要手段。只有在“旧”与“新”的二元耦合中促成庙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的重组,才能调动庙会文化新的时代需求,才能让人们在参与庙会民俗中体会到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强烈体验感与幸福感。
“旧”与“新”的二元并存是实现庙会文化转型的关键。这种传统资源、仪式活动与现代文化、时代发展相结合时,两者碰撞所产生的是一席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盛宴,这将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与转型[21]。立足当下、尊重传统成为庙会文化转型的生成逻辑。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分析,庙会作为旧时乡土社会的文化需求与生活空间,其结构已从生活方式转变为民俗文化,其功能也从精神需求转向时代需求。庙会民俗的这一转型不仅承担起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也肩负起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重任。
(二)联结:“保护”与“利用”的二重统合
遗产不被利用,仅仅是保护,那就只能是遗产;如果将其用于今天的生活,为今天的生活服务,那么遗产就会变成可供社会发展的资源[20]。文化遗产存在的功能不仅是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表征而被保护,还在于其担负起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时代重任。庙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价值不止于静态的保护,更多的是它的活态形式对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化部针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明确强调,要“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2],这才是传统文化遗产存在的时代价值。
保护和利用的本意和实质是一致的。保护不单是为了维持庙会文化的原貌,更重要的是为了最大化地激发庙会文化的现实功能,使其能为当代地方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可以说,保护是发展的隐性话语,而利用是发展的显性表述。保护隐晦地说明了其对发展的要求,而利用则是表达了激活庙会文化遗产价值、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增值的目的。保护与利用本就一脉相通,是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避无可避的走向,中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文件中也都提到过“保护本真与完整,实现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内容。所以,庙会文化的保护与利用相辅相成,互为依托,脱离了开发、利用的庙会文化是闲置的文化遗产,它无法将其自身内容转变成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与资本,无法诠释其潜在的能量与价值;同样,缺失保护的庙会文化遗产是无根基的时代快餐,它没有内在的文化逻辑,只是表象的、雷同的文化产品,它所能提供的社会价值也非常有限。庙会文化要想实现现代转型,必须将保护与利用二者联结,实现其结构上的统合,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
庙会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其实就是要在庙会文化传承的基础上,统合“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形成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经济开发相互联结的状态。在文化转型的这一过程中,搭建文化与经济的桥梁,避免经济诉求与文化本位的冲突,实现其发展的调和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任务[23]。因此,要在保护与利用二重统合的前提下,关注庙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保护其文化逻辑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合理地引导庙会的文化资源开发,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四、本体、外在与自生:庙会在乡村振兴中的资本价值
庙会的现代转型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过去生活与未来生计、文化遗产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创造性联结。这一传统与现代的联合式发展使庙会民俗文化资源得到开发,资本价值得以发掘,融合古街区、古寺庙等场域形成了新的文旅产业集群,通过自生结构合理配置这些乡村资源,走出了一条乡村经济的内源式发展道路。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域下,庙会文化的资本价值是庙会遗产本身资源价值、所在场域空间价值以及资源整合形成的自生价值的综合体现,它们共同作用于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一)本体结构:以庙会文化的资源与资本价值实现乡村振兴
在当今社会,“遗产”已不仅仅是“遗产”,其已经转化成可以观看的历史知识、景观,再利用和再挖掘的生产技艺等[20]。庙会民俗已不再是过去式的标签,而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产业资源,这一文化遗产利用其资源的产品形态,驱动庙会本体向文化资本转化,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的文化发展之路与经济运行模式。因此,挖掘庙会的文化资本价值要从庙会本身的遗产资源入手,实现其结构转向,使庙会能动地转化自身资源为资本价值,从而持续为乡村振兴助力。
首先,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源的结构转向中诠释遗产价值。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产物,是静置的文化,其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联系较为松散,要想使其活态化,融入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就要让这些文化遗产成为推动未来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的资源,成为新的文化生长的种子和基因[24]。庙会文化遗产资源化结构转向的这一过程,就是将村镇范畴内已有的、静态的文化遗产进行活化,使其变成一种文化产业的资源形态并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生机。在这一结构化转向中,庙会已不仅是历史的文化遗产,也是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源。长滩村四月八庙会是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它是随着康熙六年或更早之前正觉寺建成而发展起来的一年一度的民间习俗。最初时规模较小,明朝以后随着山西、内蒙古商旅的频繁往来,晋北、陕北人定居于此而逐渐繁华起来,尤其是咸丰年间集镇建成后,庙会迅速发展,规模逐渐扩大。这个经历历史洗礼的古村落庙会,留存着历史时期的古遗址、旧风俗,从而形成庙会民俗文化发展的基点。历史保留下来的清朝商贸古镇及其承载历史记忆的“后牌界”j,新中国早期的供销社厂址,吕祖庙(正觉寺)寺院,三百年树龄的老榆树,赵家大院、韩家大院等古民宅,解放长滩烈士纪念塔,铁索吊桥等都成了这一村落宝贵的遗产资源,这些遗产资源在该村庙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庙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产业资源,其自身的遗产价值已经成为该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其次,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功能转化中形成资本价值。在庙会民俗的调整改造、内容革新及结构转型、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语境下,庙会民俗文化资源成为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重要部分,而被社会各界关注并成为一种文化资本要素。长滩村庙会中蕴藏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的文化遗产是该村庙会资源的基本形式,如民风民情、特色饮食、晋剧表演、吕祖信仰等满足了人们的生活和文化需求,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过去,特色饮食是当地村民为数不多的体验生活、满足消费的需求,一般只在庙会、交流会的时节才有,平时人们无空闲享受生活,店商也不常制作这些吃食;晋剧表演则是附近村民唯一的文化活动方式,人们会在傍晚从地里回来,不知疲惫地跑去村里看戏,直到深夜;吕祖信仰是当地的民间信仰,以求医问药为主,是医疗不发达时期村民们寻求帮助的主要去处,直至现在还流传着“四月八,吃了庙里的素斋,一年无灾无病”的说法。在长滩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庙会文化资源的这些传统功能已经逐渐转变,饮食、手工艺、戏剧、寺庙祭祀等地方文化不再以满足本地村民为主,而是从“封闭”的乡村走向了“广阔”的市场,成为对外宣传的名片和乡村经济发展的依托。长滩村凭借其优厚的文化资源,将庙会民俗打造成一个乡村旅游视点,使其集聚游玩、观赏的文化资本价值,成为该村发展的重要渠道。这一文化资源的功能转化也是凸显该村庙会文化资本价值的重要元素,通过这些资源的产业化将庙会文化的资本价值最大化,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发展。
继承是获取文化资本的主要途径,文化资本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资源支持、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只有当族群成员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所处场域内的正统文化相匹配或相适应时,才能发挥文化资本的作用[25]。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功能转化中,文化资本的内在属性成为主导,它调配着庙会文化的遗产资源,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其资源优势,成为提高庙会文化竞争力、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枢纽。在这一功能转化中,庙会民俗的现实意义日渐成为“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乡村与城市”“市场与国家”互构共生的新基点,在其文化资源与资本的张力中提取到了促进乡村振兴的相关元素和内容。
(二)外在结构:在庙会民俗的场域空间中形成乡村振兴的竞争优势
庙会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不仅需要其本体资源发挥价值,也需要外在结构的补充。把庙会文化遗产放在古街区、古镇等“场域”和乡村振兴、地区发展等“结构”中分析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资本内涵是凸显庙会当代价值的关键。庙会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价值功用可大可小,既可凭借其民俗活动进行商品营销,也可因其遗产资源形式的聚合发展出一条集吃、住、行、游、娱、购、宗教文化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作为文化资源的庙会遗产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场域或结构中能创造性地发挥其资本价值。
首先,在场域中形成多元要素融合的乡村发展之路。布迪厄在场域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事实上就是一个一个的场域,有着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26]。把庙会放在乡村古镇街区的场域中,以庙会与古街区等旧物为依托,融合其他外在元素,相互衬托可形成一种新的功能,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长滩村自庙会民俗形成以来,以正觉寺祭祀、免费素斋饭、古商铺店面、手工作坊、铁索吊桥为基础,邀请了山西晋剧团来此表演戏剧,又吸引外地商贩与本地商户开展物资交流活动,形成了一种多元要素融合的乡村发展之路。这一融合多元要素的庙会民俗节一般举行四天,四月初八这天最为热闹。从活动内容来看,这一天是释迦牟尼的诞辰,寺内会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仪式,全天供应素斋饭,基本集中了庙会活动的主要内容。从举办地点来看,是以寺庙为轴心,利用寺庙对面的戏台、寺庙旁边的凉亭、临近寺庙的街道将人群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喧闹的场域空间。从人员构成来看,不仅有附近村落村民参加,也有外地闯荡的打工人回来探亲,还有附近市区往来的游人以及外省商贩。可以说,每年的庙会活动既是文化艺术节,又是热闹非凡的物资交流会,其利用本地的遗产资源,综合场域内多种文化资源与相关要素走出了一条以非遗为基点的文化资本转化的内源性发展道路。这一利用场域结构中多元要素融合发展起来的庙会民俗,成为乡村文化传统、乡村民俗融入资本的鲜活样本,这为提升该村的竞争优势创造了条件。
其次,通过场域空间的再生产提升庙会民俗的资本优势。庙会民俗文化节是年度性的节日,周期较长,资本价值的实现较为有限,而将这一村落再生产成一个文化展示的旅游试点,准备特色产品,随时接待游客,将进一步扩充其资本效应。长滩村将该村的自然风光、生态种植、红色记忆、寺庙建筑、民俗风情等进行了结构和功能的改造。一是以长滩村古镇这一历史记忆为主题,挖掘其历史故事,重现咸丰以来古镇商铺林立,油梁、油坊、银匠、铜匠、铁匠、豆腐坊等手工作坊并排竖立十华里的盛况,将这个“十里长滩”打造成一个古色古香的旅游村落。到2021年,这里成为自治区级特色景观旅游名村,荣获“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的称号。可以说,以庙会为牵引的村落文化遗产转型以及文旅融合给该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和竞争优势。二是以民俗风情为窗口,由村委会牵头,各大网站、抖音、快手、公众号等媒体宣传,当地村民自发制作特色饮食,共同将这一场域空间再生产为一处热门的乡村旅游景点。另外,长滩村还通过古寺庙和传统文化馆参观、网红玻璃桥、蘑菇窑采摘基地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庙会民俗发展的资本优势。由此,这一村落利用其固有的庙会民俗活动与古镇、街区场域的联结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吸引了很多附近城镇的游客前来。长滩村这种在保留古镇街区结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村庙会民俗旅游,创造性地发挥了其资本价值。
场域或结构是一个空间体系,庙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与古街区、古镇等场域或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有着乡村传统文化根基的庙会文化遗产,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要通过古街区、古镇等场域空间的再生产提升其资本优势,并成为乡村发展的竞争性资产,为乡村振兴、地区发展提供重要力量。从外在结构分析,综合庙会文化遗产、古镇和乡村振兴的关系,发现庙会文化遗产在古镇变迁、遗产要素融合、场域空间的再生产中明显发生了“结构—功能”的转变,其资本的价值愈发凸显。这表明庙会的结构价值是在一定外在场域空间影响中实现的,与外在场域变化息息相关,综合外在场域空间才能实现其资本价值的最大化。
(三)自生结构:以庙会结构性遗产的整合促进乡村振兴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文化遗产在一个地方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结构性,成为可以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因素,因而被称为“结构性遗产”[27]。庙会作为一个地区长久存在的文化活动,以其自身的文化遗产结构特征,对乡村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庙会遗产的这一结构能动性,使其拥有了自生结构,进而利用其发展庙会产业经济,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内源型动力。
首先,在庙会文化结构遗产的整合中形成自生的结构逻辑。庙会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结构遗产,囊括了三种具体形式的遗产类型。一是以节庆活动为代表形成了庙会的制度性结构遗产,这一遗产经过长久历史传承,其自身拥有一套制度性体系,从举办时间、地点到活动内容等都有明确安排。二是作为庙会民俗组成单元的物质性结构遗产,通常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形式再现出来,是体现庙会民俗文化遗产客观化的结构体系。例如人员构成层面的寺庙住持、和尚及从事表演的人员,设施建设层面的举行祭祀祈福活动的古寺庙及其配套佛殿、屋舍,举办社戏社火的戏台、观众席,旅游观光层面的街区、古宅、凉亭、索桥、玻璃栈道,日常生活层面的古村落居民生活区等。三是庙会文化中内隐的风俗性结构遗产,这类遗产通过不同的维度和形式为庙会文化添砖加瓦,让这一文化活动更具吸引力,如长滩村庙会中长久流传下来的歌曲戏剧方面的山西晋剧艺术、地方性的二人台曲目、民族融合的漫瀚调即兴对唱等多元艺术表演,手工艺方面的传统剪纸、书法过程展示,饮食方面的美味豆花、碗托、糕圐圙等地方民族特色,休闲方面的绿色农业基地采摘项目。这些结构遗产的整合不仅丰富了庙会文化的内容,造就了如火如荼的庙会民俗旅游,更是强化了庙会民俗文化的自主能动性,使其以制度结构汇聚人群,吸引了附近村落居民以及外来游客,使常驻一百余人的冷冷清清的古镇街区在庙会期间人山人海,最多时一天接纳近万人;以其实体结构营造出供人观光、游览的乡村旅游景点,满足游客游玩、观赏需求,为庙会民俗的开展奠定了根基;以其风俗结构成全了游客吃、住、体验的需要,使游客在寺庙仪式活动、特色饮食、传统手工制作和民俗艺术表演中体验到庙会文化的乐趣,活化了庙会文化的现代旅游价值。各类文化遗产在一定原则和秩序的组织下被整合为一体,形成了庙会民俗的结构遗产,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庙会的这种自生结构。它以“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动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形成了庙会结构遗产的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28,29]。
其次,在庙会文化遗产的自生结构中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内源动力。庙会文化遗产的自生逻辑以其内在的自主能动性,将庙会的遗产资源凝结在一起,对其进行自我配置,在观光旅游的规划和设计中塑造出诸多别具一格的乡土风情,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村落发展的特色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扩大了庙会的资本价值,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资源。长滩村通过合理整合、调配乡村遗产资源,使游客在参观游览古镇景观之际,体验到寺庙的仪式和素斋,享受到乡村特有的美食和歌曲,既满足游客玩乐的需求,也传承了地区与民族特色。长滩村以其自生的庙会民俗使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乡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发挥出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内源价值。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来看,具有鲜明乡土特色的庙会民俗越来越多地发挥着“结构遗产”的内源动力,通过文化遗产的自生结构将庙会与旅游深度融合。
作为结构遗产的庙会在乡村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新的结构与功能,将制度性、实体性、风俗性结构遗产整合起来,形成地区独具特色的产业链,提升了庙会的资本优势,使庙会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元素。同时,庙会以其自生的结构整合了古镇、村落的遗产资源,以文化动力驱动了庙会民俗的资本价值,发挥了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内源动力,使传统村落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也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范例。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传统庙会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累积中形成的,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与资本。它的转型实现了中华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并存与联结,这种趋势活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驱动了传统民间文化带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导向。庙会作为乡村民俗文化的一种表征,表面来看,是重要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文化资本建构。它将乡村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以资本再现的形式融入庙会活动中,利用这类遗产资源形成乡村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又以其民俗活动的文化产品形态激发了庙会的资本价值,凭借古街区、古镇等场域实现了文化资源的资本转化,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和地区发展。庙会民俗的这一现代转型使传统的庙会文化遗产在乡村发展中展现出新的结构与功能,实现了传统节庆文化融入现代文旅产业的新动能,整合了乡村资源,形成了以民俗活动为中心的现代文旅融合产业链与产业集群,探索出一条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传统民俗文化的转型发展也成功诠释了其内在的资本价值,其继承性与时代性创造性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民间文化的持久魅力。可见,弥散着成千上万中国农村乡土气息与生计样式的民间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内含着中国文化强国的具体实践路径。
① 相传“后牌界”是山西河曲汉人向蒙古人买地时,汉人连夜将原置界碑向北运行十里重立,称为“后牌界”。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8-02-04.
[2] 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 高占祥.论庙会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4] 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庙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
[5] 吉发涵.庙会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J].民俗研究,1994(1):48-94.
[6] 黄景春,张开华.“国家在场”与都市庙会的转型——以浦东圣堂“三月半庙会”为例[A]//晏可佳,葛壮.宗教问题探索:2011-2012年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 郁喆隽.江南庙会的现代化转型:以上海金泽香汛和三林圣堂出巡为例[J].文化遗产,2018(6):76-82.
[8] 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M].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9] ZAKHAROVA M.Temple fairs in contemporary China[J].Problemy Dal'nego Vostoka,2010(1):136-142.
[10] ZENG YL,DAI SQ.Evolution of the temple fair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the republic to the contem- porary[A]//CHANG T.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form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ERMI 2012),2013:416-420.
[11] 乐慧英,高薇薇,梁欢,等.古镇开发中民俗文化节的转型与发展——上海三林镇圣堂庙会调查[J].城市治理研究,2017(2):68-81.
[12] 李琦.浦东圣堂三月半庙会的当代转型考察[J].民间文化论坛,2013(3):57-64.
[13] 王建光.张力与裂变:地方性视野中的庙会文化及其转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31-137.
[14] 梁方.庙会及其现代转型[J].湖北社会科学,2001(6):42.
[15] 张继焦.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从“二分法”到“四分法”[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7-23.
[16] 郭浩.准格尔旗将打造百里长川文化旅游产业带[EB/OL].准格尔旗人民政府网,2018-03-12.
[17] 王皓锋.文明乡风入村来长滩古镇焕新颜[EB/OL].准格尔旗人民政府网,2014-07-29.
[18] 高有鹏.狂欢季节:庙会中的信仰与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19] 高艳芳.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与文化成因[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35-144.
[20] 方李莉.论“非遗传承”与后现代文化模式的再生产[J].人文天下,2015(9):40-45.
[21] 张继焦,吴玥.民族八省区的文旅融合发展——以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现代”转型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20(7):113-120.
[22]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EB/OL].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2010-11-10.
[23] 毕曼.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规律与策略研究——以恩施土家“女儿会”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78-85.
[24] 方李莉.有关“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J].艺术探索,2016(4):59-67.
[25] 宗喀·漾正冈布,王振杰.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20-29.
[26]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
[27] 张继焦.新功能主义: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的新价值[J].青海民族研究,2018(4):61-66.
[28] 张继焦.换一个角度看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新古典“结构-功能论”[J].西北民族研究,2020(3):178-189.
[29]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1992(5):3-17.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apital value of temple fai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eoclassical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MA Hui1, MA Wei2
(1.College of Ethnology & History,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750021, China; 2.Xingzhi Colleg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321000, China)
Temple fair, a folk activity, is the manifestation and carrier of Chinese rural cultur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have changed from folklore presentation to cultural capital. The temple fairs in the border villages of Mongolia and Shaanxi have stimulated the modern vitality of temple fair culture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mode of coexistence and connectivity, and formed the cultural capital value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e ontological level, the temple fair, as a cultural resource and capital, transforms cultural capital into economic capital in the form of product resources;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the temple fair folklore forms a competitiv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 with its spacial advantages in the ancienttown; at the self-generated level, the temple fair, as a structural heritage, rationally allocates rural resources with its self-generated structure, forms an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villages, and provides capital advantag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emple fair culture; capital value; neoclassical“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10.13331/j.cnki.jhau(ss).2022.05.008
C911
A
1009–2013(2022)05–0068–08
2022-08-28
马慧(1994—),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曾凡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