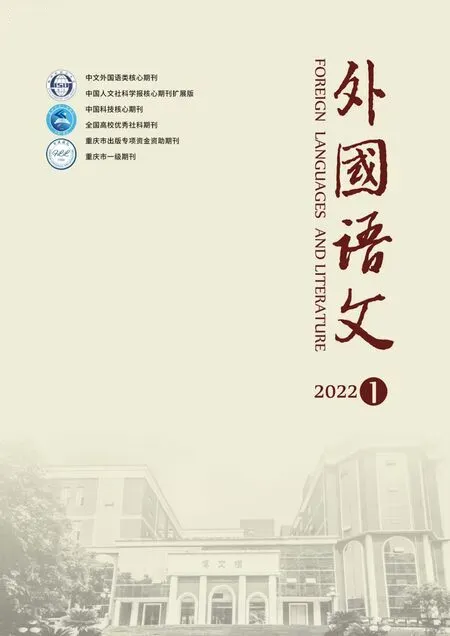翻译修辞视角下的译本认同建构
——以《保卫延安》沙博理英译本为例
2022-12-27李克朱虹宇
李克 朱虹宇
(山东大学 翻译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0)
0 引言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成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关切,建构“他形象”(管文虎,2007)并赢得认同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形象与自身强大发展实力相匹配的举措之一。国家翻译实践是对外宣传与形象建构的载体,其成果产出——制度化译本以微观路径服务宏观目标。为更好实现国家形象的建构,提升制度化译本质量成为不可忽视的环节,而读者认同则是评判标准之一。对此,修辞学中对受众的关注能够为提升译本质量带来启发,结合翻译与修辞双重视角成为应有之义。本文从翻译修辞视角出发,以国家翻译实践中《保卫延安》沙博理英译本为例,探究制度化译本中体现的翻译修辞痕迹,为建构译本认同进而促进建构国家外部认同提供借鉴。
1 翻译与修辞的共生统一
翻译与修辞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语言研究领域,却在理论与实践运行上存在理念和方法重叠,如两者在目的性、交际性、语言性、受众性、语境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等方面皆具有相通之处(陈小慰,2011),其融合发展的趋势不可谓不明显,因此关于翻译与修辞的交叉研究日渐增多,“翻译修辞”也已成为一个新生术语在两个研究领域散发活力。为何翻译与修辞能够共生统一,构成良好的互补互用的研究生态?我们认为,修辞行为与翻译行为的融通、修辞受众与翻译读者的相似、新修辞学认同观与译本认同的统一等因素促成了两者的结合。
1.1修辞行为与翻译行为
修辞从“言说的艺术”或“说服的艺术”发展而来,“一旦出现了语言叙述,也就出现了修辞问题”(胡范铸,2010:35),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言语行为就是修辞行为(马睿颖 等,2008;陈小慰,2003)。修辞使得人类通过语言表达思想与观点,将内化思维流动转换为外化语言形式。修辞者在修辞目的的驱动下做出修辞行为,尽管修辞目的是根据具体修辞情境而产生的具体目标,但是在性质上修辞目的都指涉通过言说达到劝服受众或获得受众认同,而修辞行为影响范围不仅限于修辞者与受众,同时作用于社会发展,表现在“言说是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基本能力,而用说服取代强制与暴力作为协调群体行为的主要手段,则是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和人类社群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刘亚猛,2018:1)。
翻译是“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转换行为”(方菁 等,2020:94),翻译的进行由翻译目的驱动。翻译目的涉及范围广泛,从宏观来看,权力关系、文化背景等都是影响翻译目的的因素,从微观来看,译者通过翻译文本传达原作者意愿并触动读者,以此产生由文本至读者的影响链条,同样可被称为翻译目的。由此可见,翻译行为总是带有目的性并由此衍生出劝说性,即劝说读者经由译本做出态度、观念或认知等方面的改变。因此,翻译行为与修辞行为可被视为同一视阈下的两种活动范式。
言说者采用修辞思维与修辞手段,呈现带有特定目的的文本,因此,修辞成为“任何作者接近、争取赢得读者的唯一途径”(刘亚猛,2018:279)。在此意义上,翻译也具有“修辞特性”(陈小慰,2018:144)。在译文等可视成果呈现之前,译者在头脑中已率先对需要翻译的对象根据自身理解能力和经验背景进行“再造”,并在此基础上使用语言再现这一经过再造的信息系统,输出显性翻译成果。这表明翻译是一种包含隐性和显性两个阶段的修辞行为,即译者身兼原文的修辞接受者与译文的修辞调适者两职(朱肖晶,1998),也可被认为是纯粹意义上的译者与修辞者的兼容,这体现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调节话题与受众的关系,寻找情境中最合适的修辞表达”(France,2005:268)。
对原文的修辞接受体现于原文对译者的影响,这种影响因人而异,不存在两个译者拥有完全等同的修辞接受程度,这是译者结合自身条件形成的关于外界事物(即原文本)的认知,是一种在翻译被“形式化”之前发生于译者头脑中的隐性语言及思维转换。而译文的修辞调适则是译者在与原文相对应的译文基础之上,根据译者个人翻译水平、受众、外界压力等多个方面进行的对译文文本的“显性修辞”,该修辞形式显露于文本之中。不过,这两个过程并非对立关系。根据西塞罗(Cicero)的翻译与修辞观念,弗朗斯(France)总结道,“译者照搬原文,言说者享有自由”(France,2005:255)。虽然此处的“照搬”已不适用于现今的翻译观,但在一定程度上,原始意义上的译者与修辞者在自由程度上的差异仍较明显,而两种角色经过调和,形成翻译修辞者,充分发挥对原文的忠实与自由。
1.2修辞受众与翻译读者
修辞受众指修辞者在进行修辞活动时有意识“针对”的群体,该群体具有被修辞行为影响的潜质,修辞者以或深或浅的修辞痕迹劝说特定范围内的受众接受修辞行为并由此作出改变,因此修辞行为的目的性体现在对修辞受众的影响上。受众意识在修辞研究中成为基础理念,佩雷尔曼(Perelman)等修辞学家皆以影响受众为重点对修辞行为做出阐释。修辞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并不避讳所谓“针对性”,而恰是该种目标意识促进了修辞研究的细化,并归纳出面对不同受众做出不同修辞反应的情境。
翻译研究经历了以原文本为中心、“文化转向”和“译者转向”几大转向之后,愈发注意到读者的重要性。当然,对读者的重视在文化转向之时已初显,但是并未对其进行系统挖掘,多是伴随原文、译文、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出现,其重要性与特殊意义并未得到应有凸显。奈达(Nida)首次将读者反应作为一个系统观点提上台面,但是对读者反应的重视仍以译本为中心,这种现象与以读者为中心的研究之匮乏不无关系。受众研究在新修辞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该理念为翻译研究中的“读者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得研究从一个崭新而具有启示意义的视角探究译文读者,即翻译修辞中的受众成为可能。
受众意识与传统意义上因顾及读者理解能力而删除晦涩之处、调整语言难度等手段不同,而是从整体意义上与读者构建和谐统一关系,其目的不论是获取经济效益、传播译文、宣传文化还是产生政治影响等,都表现出各自目标驱动之下的“作者—原文—翻译修辞译者—译文—翻译修辞读者”的动态交融。“作为修辞的翻译,是一种以在受众身上产生影响和效果为核心,以语言象征为手段,精心选择言语资源的行为。”(陈小慰,2013:19)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借鉴修辞学的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受众意识”(张雯 等,2012:38),采用翻译策略说服读者,关注受众反馈,提升译本的接受度及普及性(张晓雪 等,2020)。由此可见,当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之中借鉴修辞受众概念时,翻译读者的角色更加凸显,译本的目标性也更加清晰。
1.3认同观与译本认同建构
古典修辞学中修辞的核心为“说服”,而新修辞学中修辞的最大关切是通过言语劝服他人在心理或行动上做出改变。美国新修辞学代表人物伯克(Burke,1969:21)提出的“认同”成为当前修辞学所追求的修辞者-受众关系标准,当“拥有共同的感觉、概念、想象、观点、态度”之时,人们就会“共同接受”并走向“认同”。成功地建立认同体现出语言的基本交流与传播功能,也是社会构成与人类生存的前提之一。不同的文本类型内嵌有不同的修辞目的,然而在追求受众认同上却趋于一致,如政治性文本以向受众传播某种观念形态为目的时,通过使用修辞手法将受众的思想与心理状态容纳于文本之内,推动受众的认同与接受;再如文学性文本,虽其书写形式迥然各异,目的却都包含促使读者进入作者所述或虚或实的文本世界,以实现内容与思想的传达和内化,这种读者意识在翻译中也日益突出。
译本传播,究其根本,是通过译本获得译入语读者对源语作者、价值形态甚至文化背景和国家观念等的接受与认同。影响认同的因素包括译本背后权力关系的制约、源语国家文化在译入语国家是否适恰、原文本作者是否得到认可等,然而当认同体现在文本层面时则成为译本如何赢得读者认同。译本是读者接触原文本作者及源语文化等的直接窗口,因此也是建构认同的直接依据,译者需要付出一定的翻译努力,在翻译过程中以实现认同为指导原则之一做出翻译选择。
译本认同虽然贯穿于翻译过程,但其并未得到翻译研究的凸显,而修辞认同观则启发我们译本认同可通过修辞理论加以延展,成为一个提升译本质量与吸引读者缘的路径。为了达成译本认同,译者需要诉诸两个层面:第一层为译者认同原文作者,如此才能达到与原文作者的和谐并进而实现译本与原文的统一;第二层则为译者争取译文读者的认同,此时的译者成为翻译修辞者,具有目标受众(读者),受众的认同即是译本认同。修辞中的认同观与译本认同建构具有同源性,在理念上都关注修辞或翻译文本如何赢得受众或读者认同,修辞认同观更加突出修辞者的努力,将受众认同提上研究议程,但是翻译中却将赢得认同与对读者趋向性、译本传播、文化传播等结合,难以区分出具体的译本认同理念,因此修辞认同观对这一现象的明晰具有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修辞行为与翻译行为、修辞受众与翻译读者、新修辞学认同观与译本认同三个方面的相近性与融合性说明翻译与修辞两个学科可以相互借鉴,尤其修辞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将译者视作修辞者,由此带给译者以较大的主体性,并凸显了译本在对外传播与形象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苏联学者科米萨罗夫“在其《翻译语言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修辞学’,从语言角度考察结构、规范和习惯等现象,同时进行了翻译分类”(陈小慰,2019:44-45)。魏永康提出“修辞翻译方法”,修辞翻译的本质为考虑译语受众,具体表现为以受众为转移进行必要的改写,突出受众想了解的内容,尊重读者的理解能力,尊重读者的自我。(陈小慰,2013:201)“翻译修辞学”(陈小慰,2019)这一新学科门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全面剖析了其前景和发展方向。不过,就目前对翻译修辞学的研究来看,多聚焦于伦理探索和理论建构,结合实例进行整体分析的成果尚不多见,而只有将理论应用于具体分析,才是验证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的最佳途径,也才能体现“翻译的超学科本质”(谢柯 等,2018)。哈里克(Herrick)提出的四种象征资源作为“翻译修辞话语的实现途径”(陈小慰,2017:20),为我们探究修辞视角下的翻译实践带来启示。接下来我们以《保卫延安》沙博理译本DefendYanan!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译者通过翻译修辞手段在译本认同的建构上做出的努力,进一步阐释翻译修辞的适用性。
2 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制度化译本
国家翻译实践是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进行的翻译实践活动,“融国家行为、话语实践、传播行为为一体”(任东升,2019:73),其理念为“国家作为翻译行为的策动者、赞助者和名义或法律主体”(任东升 等,2015:92),是一个“融合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意义的现代翻译学概念”(蓝红军,2020:117)。国家翻译实践具有“自发性、自主性和自利性三重属性和民族性、系统性和权威性三种特征”(任东升 等,2015:92),在内容上承载着国家意志,形式上承载着国家规范,成果上承载着国家目标,是主权国家通过翻译对外建立民族形象、树立国家“招牌”,对内巩固意识形态、传输指导意旨的中间手段。
“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个话语过程”(党兰玲,2018:99),制度化译本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中制度化译者的翻译产物,是普通国外大众了解我国情形及国际局势等的途径之一,因此带有深刻的政治和外宣性质,成为国家对外树立形象的重要路径。然而,除却政治性文本,文学翻译也是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关键组成,且因其文学性、娱乐性、大众性等特点,传播范围甚至广于政治性文本。
制度化译本的品质直接作用于外国读者对文本传递的文学现象、价值观、民族精神等的理解,具有“使文本回归现实世界”(胡牧,2011:5)的内在推动力。有鉴于此,译文素来被赋予重要意义,译者也因此担负着借由文字传递国家话语及意旨的艰巨任务。译文读者在普遍意义上为所有具有阅读和理解能力的受众,译文也应在最大程度上面向最广大群体,如此一来,译文的多个方面都受到关注。在这一思维背景之下,以沙博理为代表的制度化译者群体所产出的制度化译本受到外界审验,读者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对制度化译本传播效果与长远留存产生影响,而作用于读者接受的关键因素就是译本品质。在毫无原文背景或者甚少知晓源语社会、文化环境的情况下,读者主要信息来源为译本,文本自然成为读者对其中所呈现的社会甚至所属国家认知体系建构完整或恰当与否的依靠。
《保卫延安》为现代作家杜鹏程于195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作品,它“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连队参加青化砭、蟠龙镇、榆林、沙家店等战役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1947年延安保卫战的历史画面,塑造了解放军各级指战员的英雄形象,揭示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战争胜利的内在力量这一思想命题”(萧枫,2010:379)。此外,延安为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更是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也始终是促使中华民族牢记先辈教诲、不忘历史使命、实现伟大复兴的推动力,是中国国家形象“历时性、稳定性”(赵微,2018:5)的见证。该书所承载精神的特殊性与民族性使其带有符合时代特色和宣传伦理的文本潜质,因此被筛选为国家翻译实践原本之一,由沙博理执笔翻译。
英译本DefendYanan!(Shapiro,1958)作为典型的制度化译本,高度还原原文风格与内容,且在修辞上不乏“源于原文,高于原文”的译文雕琢之工。在实践层面,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对制度化译本的高度要求,在学理层面,流露出修辞与翻译的共生统一及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这在建构制度化译本认同中彰显无遗。因此,我们从翻译修辞的视角,以制度化译本代表之一《保卫延安》沙博理译本为语料,挖掘译者在译本认同建构中倾向于读者的修辞努力以及为增进外部世界认同做出的修辞考量。
3 制度化译本中的认同建构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制度化译本的支撑,将翻译上升为“国家事业”,并使其“达到‘运动’的规模并产生社会化效果”(任东升,2016:1),这就决定了制度化译本的国家代表性,其中体现出的修辞努力关涉建构国家外部认同,完善国家形象。若深入探究这种修辞努力,需要根据清晰可靠的框架或者分类依据,哈里克提出的四种修辞象征资源比较恰当地呈现出《保卫延安》的英译本认同建构考量。这四种象征资源分别是论辩内容、诉求策略、话语建构方式和美学手段。陈小慰(2013:119)对其表示充分肯定,并指出可利用哈里克提出的这四种象征资源,展开对修辞翻译实践的研究。该四种象征资源对内容、形式以及阅读效果等都予以关注,较完备地涵盖了修辞作品的重要方面,能够体现出译者“通过有效的修辞使自己的译作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的文本”(贾英伦,2016:122)的努力。经过分析发现,《保卫延安》沙博理译本对这四种资源皆有指涉,是译者翻译修辞意识的证明。我们将从这四种象征资源入手,分析《保卫延安》沙博理英译本中的修辞手段,看制度化译者如何通过象征资源塑造认同,进而提升译本宣传效果,推动翻译目的的达成。
3.1论辩内容
论辩内容是“当一个结论被理由所支持”(Herrick,2001:13)时产生的,那些支持结论的理由,就成了论辩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论辩内容是促使读者对文本产生认同心理的关键,其合理性、清晰度等都影响认同效果。但是,由于翻译存在固有的对原文本的依附性,其对论辩内容的阐释多呈现出并不明显的细微调整。同样,制度化译者沙博理在处理论辩内容过程中,在符合文本主旨和整体呈现的前提下做出合理调整,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建立心理认同。在原文第二章第五节中,主人公周大勇问村民李振德的话语可暗示出这一点:
(1)原文:你大闺女出嫁到哪里?(杜鹏程,1979:104)
译文:Where does your daughter live?(Shapiro,1958:104)
原文中的这句话体现出强烈的中国封建时期的思想观念,即已婚妇女依附于丈夫。结婚是女子从原生家庭“嫁”到丈夫家庭的一个步骤,出嫁到哪里,哪里就是该女子今后的归属地。然而,在当时的西方社会,虽然女子结婚之后使用丈夫的姓,也体现出一定依附性,但是在居住地上灵活性较大,“丈夫”是谁和“住处”在哪是两个概念。因此,此处沙博理在译文中并未体现出“嫁”的含义,这是制度化译者向西方意识的一次靠拢,也是在取得读者认同的考量基础上对论辩内容所作的调整。
除了与原文相对应的译文的改动,译本中相应原文内容的缺失也是醒目之处,对内容的删减在根本上属于调整论辩内容。这些被删减的内容小到字词,大到段落。经过比对发现,译者并非随意省略,而是经过了详细审慎的考虑,作出了不影响整体叙事框架和进展的细致删减选择,也就是对论辩内容做出改动。如在第三章第五节中,主人公周大勇正在写日记,指导员王成德走来一把夺过日记本看了起来,小说中还原了周大勇的两篇日记,但是译本中却只出现一篇,第一篇被删除,择一而译,其中必有缘由。我们发现,两篇日记在内容上略有不同,以下两点或许能够说明译者舍前取后的原因。第一,第一篇日记前半部分客观描述陇东战役的局部情况,后半部分描写政委鼓励作战疲劳的战士。第二篇日记则集中于主人公周大勇的读书情况,是用政委的话激励自己坚持读书、克服困难的心理实录。从论辩内容角度来看,前者侧重客观描述,后者则加入更多内心想法,后者在战争小说中更加罕见,将其保留有助于提升小说内容的丰富性。第二,第一篇日记中第一人称“我”的出现次数为0,第二篇中的“我”却出现了五次。日记本身即是个人的心理流露,第一篇的“日记色彩”淡薄,以政治描述为主,第二篇则更加符合读者心目中对日记的常规认识,偏向私密与感性,读者对最基本的文体认同由此建立,而且避免了不恰当的政治术语翻译无法“契合读者的认知水平”(谭莲香 等,2018:73)这一政治文本外译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体现了制度化译者通过调整论辩内容,推动建立读者认同的翻译修辞意识。
论辩内容是翻译尤其小说翻译中读者所要汲取的重点信息,如果将其他三种象征资源比作文本外壳,论辩内容则是文本内在,其质量高低决定了对读者的直接影响力,即读者认同的程度。《保卫延安》沙译本中,译者以严格遵守制度化译者行为准则为前提,在不违背主题的条件下,使用删减、改译等翻译手段对译本相对原文的论辩内容做了调整,是制度化译者翻译修辞意识的体现。
3.2诉求策略
论辩内容作为基本固定的文本内涵,对其做出改变的途径数量有限,总体包括改、增、删几种范式,而且有时为了维持原文本的完整或受限于原文本作者或出版社等多方要求,译者并不能随意更改,此时诉求策略就成为其重要的提升译本认同度的诉诸手段。诉求策略指“那些旨在激发情感或者促使听众产生忠诚或允诺的象征策略”(Herrick,2001:13)。它是一种具有渗透性的修辞翻译现象,译者在措辞中时刻流露着对引领读者认同的努力。文学作品中,情感诉诸感染力最强,作者能够以少量文字完成撼动读者情感的效果,高效地实现写作目的,这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作品。翻译的整个过程是一场译者对读者接受的诉求。对诉求策略强调最多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他将修辞中的诉求策略分为情感诉诸、理性诉诸和人格诉诸,晓之以理并动之以情才可达到最佳说服效果。在翻译中,情感诉诸多见,因为情感可寄托于一字一词,而对原文措辞造句的翻译,则可体现出译者带有修辞意识的情感诉诸手段。这也印证了“媒介话语修辞的力量不是压迫性的,而是在情绪、情感的交流、引导、涵化中完成的”(丁云亮,2018:113)。《保卫延安》作为红色小说,感情色彩浓厚的描写较多,尤其体现在歌颂解放军战士不畏艰险、英勇抗战的红色精神上,如在《沙家店》第五节中,解放军队伍的旅长向在暴雨中行军的战士们说:
(2)原文:我们走着一条血的道路。中国人民的苦难,都集中地表现在人民战士身上咯。可是不管怎样流血牺牲,忍饥受饿,我们总是勇往直前,相信胜利,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杜鹏程,1979:383)
译文:We are travelling a bloody road. All of the suffer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re crystallized in the lives of the people’s soldiers. But no matter how bloody the sacrifice, we still go forward bravely, confident in victory, confident in the justice of our cause.(Shapiro,1958:307)
该部分描述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刻画出一位慷慨激昂地鼓励战士奋勇前进的旅长形象。沙博理精准把握原文蕴含的情感色彩,使用对应词语再现旅长对战士们的期望,如“bloody road”“crystallized”“go forward bravely”等皆忠实还原情感内涵,旅长的爱国情怀与为人民献身的勇气展现无遗。由此可见,译文精准传递出原文的情感诉诸,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符合作者的修辞意图,将建立读者认同放在翻译过程的显著位置。在整本译作中,这种还原情感诉诸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是,译本中也有多处删除了原文的情感用语,如在同一节中的“我们要胜利,旧社会一定要打碎,新社会一定要在我们手中建设起来!”(杜鹏程,1979:383-384)被删除。译者酌情删除情感诉诸用语的背后,是对读者阅读心理的观照。原文中情感色彩浓厚的用语较多,过多的情感描写反而对读者带来频繁的心理冲击而致最后达不到最佳阅读效果。因此,沙博理深谙情感诉诸的用度需谨慎,在翻译修辞意识的引领之下,合理删减,拉长读者情感波动周期,同时也提升了情感波动效果,是高级的调控情感的翻译修辞手段。虽然对个别之处内容的删减可被称为是对论辩内容的改变,但是取其核心来看侧重的则是对诉求策略的调整。“修辞化内容能催动人的情绪、情感,调节人的认知,强化人的意志,甚至于超越原文本固有的话语意义。”(丁云亮,2018:114)沙博理通过对情感诉诸等的使用,合理调试了原文本话语意义,在不改变整体内容的基础上调用翻译修辞资源,较充分发挥了译者对建构译本认同的作用。
3.3话语建构方式
话语建构方式关涉文本信息组成,“为达到最佳的说服、清晰或美感效果,将信息有计划地排列起来”(Herrick,2001:14),其中文本信息排列指信息的出现顺序以及前后信息的关联方式。在小说话语中,信息出现的先后将直接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对小说构事框架的评价。通过分析译文对原文话语建构方式的改动,不仅显示出译者的修辞策略,并且可结合社会、文学以及个人经历等背景,揭示其修辞动机。
《保卫延安》原文共八个章节,但是沙博理译本中只有六章,“消失”的分别是第四章《大沙漠》以及第七章《九里山》。不过这两个章节并非被全部删减,原文第四章以六个小节的形式出现在译文第三章最后,第七章同样以六个小节的形式被嵌入译文第六章的开头。原文的章节安排在译文中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文本的话语建构方式发生了变动,这一变动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从叙事主题来看,《保卫延安》的九个章节中有八个章节以解放军和敌军战斗的地点为题,针对为何单将“大沙漠”与“九里山”嵌入其他章节,我们发现不论是“延安”“蟠龙镇”“陇东高原”“长城”还是“沙家店”,都能够在网上找到和当时战役相关的记载,而“大沙漠”和“九里山”两处战役却甚少有资料记述。这表明译本所呈现的战役皆流传范围较广,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广为人知的解放军与敌军的战役。西方读者本身对这些中国战役熟悉程度不高,对被“埋没”的战役更是无从知晓。因此,为节省文本空间,减轻阅读压力,使阅读效果达到最优化,译者选择只着重呈现相对著名的战役,而将其他部分嵌入主要叙事框架,这是一种通过改变话语建构方式赢得读者认同的翻译修辞策略。
相比于论辩内容和诉求策略,话语建构方式的调整需要译者对文本更深入的理解和对翻译目的更精确的把握,同时对译者的逻辑能力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保卫延安》中涉及话语建构方式调整的案例并不多,但是以上提及对章节叙事结构的更改属于谨慎且凸显的翻译修辞努力,在较大程度上对译本整体认同产生积极影响。
3.4美学手段
文学作品不仅能够传递信息和思想,同时能带给读者美感,这种美学体验的刺激方式指代不同美学手段。修辞中的美学手段指“在象征性表达中增加形式、美感及力量的因素”(Herrick,2001:14)。文学作品翻译中,美学手段包括文本修辞之美与呈现方式的视觉修辞之美等,《保卫延安》沙译本不仅通过诗歌翻译还原了原文的音律美,还加入六幅单页图片,使整部译本更为生动,也方便读者汲取信息,加深内容理解。
沙博理的诗歌翻译可谓整部译本的点睛之笔。作为制度化译者,沙博理行走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不仅较好还原了诗歌表层含义与潜藏深义,还在形式上注重诗歌音律美,甚至部分诗歌音律之和谐与严谨超过原文,沙博理的美学修辞意识从中体现无遗,使译本在实现“表情达意”基本功能的基础之上,还带有“赏心悦目”这一有助于建立认同的重要附加功能。如第二章第一节中,解放军李江国在战士们的鼓励下随口唱道:
(3)原文:彭副总司令撒开满天网,咱们转移到山头上;敌人钻进网里来,又捉俘虏又缴枪。(杜鹏程,1979:70)
译文:General Peng has spread a big net, In the mountains we hide and wait, When the enemy troops stumble into the net, We’ll have prisoners and guns in spate!(Shapiro,1958:71)
原文诗歌的尾韵节奏为AABA,译文尾韵节奏为ABAB,译者力求达到诗歌押韵规范,但并未严苛按照中文模板,而采用模仿形式(Kelly,1979:192-193),呈现“一定的节奏或押韵,使读者能够感知诗的韵律”(文军,2016:95)。该灵活译法展现出译者通过翻译做出的修辞努力,使译文更为符合大众审美视角下的诗歌韵律结构,对诗歌框架的认同由此建立。
除了音律方面,译本在视觉效果上也与原文本不同。《保卫延安》为纯文本类型小说,原文中除开头部分插入一张陕甘宁地区地图之外,他处并无插图等副文本内容,但是在译本中却出现六张插图,分别在第一、三、四、五、六章。单看六张插图,就可明晰其筛选是经过审慎思虑的,因为在脱离文本的情况下,六张图片所含信息已较丰富,分别描述了解放军与普通百姓的孩子亲切交谈,炊事班长孙全厚给正在睡觉的连长和指导员送水,战士们在牺牲的通讯员身边面色沉重,战士们在战场上不顾炮火勇往直前,部队夜间侦探作战以及战争胜利时两个战士热烈相拥的场面。图片构成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给读者提供了初步的阅读引领,使读者在未读文本的情况下就可获取解放军热爱军民、英勇作战等信息。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无须多加描绘即可在认知上构造出作者通过文字所传递的语境。但是对西方读者而言,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其在理解文字表述过程中易出现偏差,并且《保卫延安》属于描写真实历史事件的小说,为了还原历史现实,确保传递真相,给读者留下过多的想象空间并非好事。这些插图的使用对西方读者来说是直观认识中国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建立小说与读者之间的共同文本想象空间,减缓读者对带有强烈异国情调的纯文本内容的排斥心理,进而提升读者对小说的接受与认同。这种认同建立于视觉铺垫之上,看似其目的为引导读者想象,实则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划定于一个稳定空间,在最大程度上推动读者正确理解文本,不仅建立认同,更建立了正确认同。同时,该手段还充盈了小说叙述,读者心理在看图与理解文字的过程中得到满足,有助于巩固与提升前面三种象征资源的使用效果。
4 结语
国家翻译实践通过制度化译本,推动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国家外部认同的建构。沙博理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制度化译者,在翻译上取得显著成功,曾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和“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其制度化译本中体现出明显的修辞意识,成为促进建立读者认同进而推动译本传播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修辞学家哈里克提出的论辩内容、诉求策略、话语建构方式和美学手段四种象征资源,对制度化译本进行了深入剖析,发现制度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酌量译本宣传效果而诉诸翻译修辞手段,为建立译本认同、传播中国文学及中华民族形象做出了一定贡献,通过对这些修辞翻译方法的再现和探究,可开辟国家翻译实践探究中的修辞视角,为提升制度化译本在海外受众群体中的认同与接受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