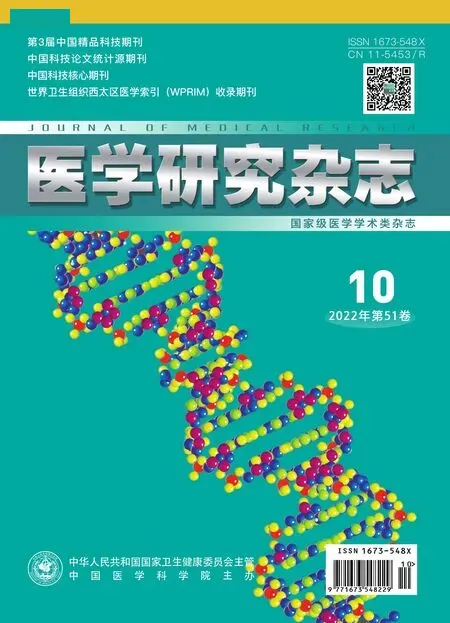中国死亡教育发展现状与思考
2022-12-27王流芳胡志民
王流芳 胡志民
世界上的一切有机体都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和生死更替的进程之中,人作为一种高级的有机体,也遵循这种规律[1]。 随着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人们对死亡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目前,医学界判断是否死亡最常用的标准是“脑死亡综合征”,它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死亡定义审查委员会于1968年在《JAMA》杂志上发表的成果,被称为“死亡”医学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但即便是如此权威的“里程碑”也存在着诸多质疑。 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和意识的消散,是一种作用于现实、个体不可经验、不能逆转的历史性过程[2]。 人们对死亡认识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待生活、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 从古至今开展的教育更多的是引导思考这一辈子该怎么做才能活得有意义,却很少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活得有意义。
一、死亡教育的定义
死亡哲学最早起源于西方,其中海德格尔提出的“向死而生”的积极死亡观受到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西方后世人在对待死亡方面变得更加坦然。 西方宗教文化中的生死观使西方人并不避讳谈生死,死亡教育也得到了发展[3]。 死亡教育是围绕“死亡”这个核心主题开展的有关情感、思想以及行为来促使人们认识死亡现象和了解死亡本质的教育,通过引起进一步思考,形成对待死亡的正确态度以促进对生命的珍惜,从而提高生命质量,这是一种基于人道死亡观念服务于医疗实践和社会的教育,目的是引导人们科学地认识及对待死亡,坦然地接受这种生命过程,在心理层面上认识和接受生老病死是一切自然生命过程中的必然[4];减轻或者消除民众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谈到死亡就焦虑的心理;引导民众思索死亡相关问题,挖掘、探讨死亡时刻的心理活动,为面对亲人死亡和自己死亡做好情感准备[5]。 我国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死亡教育是一门教育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怎样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社会性学科。
二、死亡教育发展历程
1.国外死亡教育的发展历史:美国开始发展和实施死亡教育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28年,作为国际上第一个开展死亡教育的国家,其课程覆盖面涉及各年龄阶段和各教育层次[6,7]。 英国将死亡教育知识融入宗教改革相关内容,于20 世纪50年代发动了“死亡觉醒”思想运动。 在这之后,英国还把死亡教育知识与医学人文等内容进行了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开展渗透式教育。 1976年帝国理工学院成立了世界上首个死亡教育机构,并且面向民众在全社会范围开设远程教育课程[8]。 死亡教育走进日本人视野是在20 世纪70年代,出版了相关的教科书、论著以及磁带,1983年在社会团体大力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背景下,日本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生死研究会”应运而生,继此之后死亡教育登上了日本高校教育体系的舞台[9]。 进入21 世纪以后,日本研究者以居家临终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开展访谈式的死亡教育,分析居家临终关怀下死亡教育的效果,取得预期效益[10];美国研究者提出了在癌症患者中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死亡教育方案[11];韩国推广社会全员教学计划,汇集多个学科团队合力研究开发的死亡教育课程模型DACUM(developing A curriculum)正在绝症患者死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2]。 另外,韩国研究者还在乳腺癌患者中开展了以ADDIE 模型为指导的死亡教育模式,包括分析(analyse)、设计(design)、开发(develop)、实施(implement)和评估(evaluate)等5 个步骤[13];尼日利亚研究者在癌症患者及其陪护亲人中开展合理情绪疗法RET(rational-emotive therapy),得出以认知行为疗法为核心的癌症患者死亡教育能缓解患者死亡焦虑情绪的结论[14]。
2.我国死亡教育的发展历史:20 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死亡教育。 1991年,段德智教授在武汉大学开设了选修课——“死亡哲学”,开始在高校系统地讲解死亡有关话题。 接着,崔以泰等出版了《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一书[5]。 孟宪武等的作品《话说临终关怀》于1995年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发表,继而又出版了《中国临终关怀研究》、《人类死亡学论纲》、《优逝:全人、全程、全家临终关怀方案》等书籍对死亡教育进行科普[9]。 1997年,我国医学院校编著的第一本关于死亡教育的教材《人的优逝》出版。 2004年12月辽宁省教育厅出台《中小学生命教育专项工作方案》。 2005年6月上海市印发《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对开展生命教育进行指导[5]。2008年,广东药学院正式开设死亡教育课程,而且制定了专门的死亡教育教材。 2016年,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召开以“探究死、珍惜生”为主题的我国首届当代死亡问题研讨会,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成立“华人死亡研究所”的倡议[9]。 2020年5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新冠疫情后加强全社会生死教育的提案》。 同年12月,国家教育部官网出函答复,表示将认真研究委员的建议,推进相关工作取得成效。
三、我国死亡教育发展相对缺乏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看重吉祥和好运,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生”,所以,活着的人很少刻意去思考死亡,更别说让其在活着的时候去体验死亡的感觉了。 二是神话传说和宗教的影响。 传自印度的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是对我国死亡文化影响最大的两个宗教,例如道教追崇容颜永驻、长生不老,以及追求修身养性、修炼成仙等的影响[3]。 佛教的鬼神之说以及对死后地狱的宣传,为“死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三是社会舆论的压力。 部分人将临终关怀和“孝道”联系起来,对病入膏肓无法挽救的老年人放弃救治、送入临终关怀机构、告诉老人让其淡定面对死亡等行为都被视为“不孝”[5]。 四是对死亡教育缺乏认同感。 说到在全民范围开展死亡教育,有人认为儿童年龄过小,身心皆不成熟,草率开展死亡方面的教育和实践活动可能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4]。 而在濒临死亡的老年人和癌症患者中开展死亡教育,谈及死亡这类敏感而悲伤的话题,也是残忍和不人道的。 五是教育体系有所欠缺。 我国开设的死亡教育课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死亡教育融进医学人文社科类课程之中[9]。 这也就导致以下问题突出:死亡教育还没有形成规范化的教育体系,没有统一的教材[5,15];在教学形式上也大部分是以老师讲授理论、学生集中倾听为主;课程内容方面大多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老师一般都是通过自己对西方死亡教育的概括来谈体会[9,15]。 另外,对死亡教育的实施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大多是通过杂志、学术期刊、专著等方式对于死亡和死亡哲学的有关概念进行解释和明确,缺乏宣传教育的特色[9]。
四、推动我国死亡教育发展的建议
1.死亡教育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现代社会各种媒体信息鱼目混杂,人们对各种事物都保持一种警惕心理,尤其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死亡教育对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是没有接触过的。 另外,我国对于在患者中开展死亡教育的具体方法和实践依然处于探索阶段,此项教育的开展离不开患者家属、医生、护士以及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 由于我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民众对我国政府权威部门的政策信息高度信任。 所以要想在中国开展死亡教育,最主要的前提是要让广大民众觉得开展“死亡教育”是经过权威部门认可的,是国家支持的,这样,才能为死亡教育的下一步开展实施提供政策保障。
2.不断完善死亡教育体系:死亡教育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家庭、学校、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开展。 逐步在死亡教育领域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设立死亡教育科研项目,鼓励科研人员致力于死亡教育科研工作,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方式,形成科学规范、完整成熟的教育模式;选拔专业人士成立教材编写小组,统一教学内容;补充教育师资力量,在高校内开设单独的死亡教育知识传授以及实践体验课,明确课程考核标准;在各大医疗机构,不定期开展专业人员死亡教育培训,充分发挥继续教育的作用,提高医护人员的人文素养。
3.逐步倡导开展全民终生死亡教育:认识死亡、走向死亡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不可避开的过程,我们只有在内心深处情感层面真正接受死亡,打消对死亡的恐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活着是为了什么,应该怎样去活好这一辈子。 一个人从生下来到生命终结的过程中,都有接受死亡教育的必要。 人们对生命安全意识的匮乏一般体现在以下方面,例如,对危险的警惕不够,危机处理能力不足,生命情感的冷漠,生命价值的迷失等。 因此,脱离死亡教育的生命意义教育是不够全面和深刻的。 开展全民终生死亡教育应该包含两方面,即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普及教育主要面向社会民众,专业教育主要针对医学专业人员。 国外针对不同人群常见的死亡教育方法有讲授法、阅读指导法、欣赏讨论法、模拟想象法、亲身体验法、随机教学法和自我教育法。 在我国死亡教育实践的探索中,对于绝症患者,目前开展的研究有个性访谈生命回顾和以生命意义为基础的死亡教育,引导绝症患者回忆一辈子中有纪念意义的经历,鼓励患者讲出自己的正向感情,体验生命的价值,使患者树立正确的死亡观,指导患者以科学正确的态度看待死亡[16,17]。 实行终生死亡教育的一个好处是,从小就无形中接触和谈及死亡类话题,在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时,就能将死亡观囊括在内。 在深刻认识“死”的基础上定义“生”的意义,从而更加懂得珍惜和尊重生命。
4.将死亡教育纳入医学心理学范畴:虽然目前死亡教育是生命教育中的一部分内容,但是生命教育更多关注的是青少年,而对老年人的临终关怀关注较少。 另外,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一般重视的是通过对患者疾病本身的治疗来达到延迟死亡的目的,很少把注意力放在调节患者对待死亡的态度上。 说到态度,这就涉及了心理学层面。 医学心理学(medical psychology)是一门旨在通过医学的观点来诊断、研究、治疗以及预防人的身心疾病和精神障碍及其相关问题的应用学科,此学科融合了医学和心理学的特点,重视心理因素在疾病病因、诊断和治疗、预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解决人类在健康、患病或者疾病和健康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心理问题。 医学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和死亡教育的需要不谋而合,所以,建议将死亡教育纳入医学心理学范畴,成立生命教育学科和医学心理学学科交叉的“死亡教育”机构,专门负责死亡教育开展。
5.逐步进行文化引导:中国人对“死亡”的忌讳还需要在文化层面上进行宣传和引导,在全社会范围内打造积极的死亡教育环境,宣扬正确的、科学的死亡文化。 通过新闻媒体、报纸、期刊等形式落实普及死亡观;社区可结合各时间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死亡教育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引发民众对于死亡进行深入思考。
综上所述,对于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死亡教育都尤为重要,它是一种关乎所有人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广大民众合力完成。 在汲取国外经验的同时,中国研究者更应该致力于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死亡教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