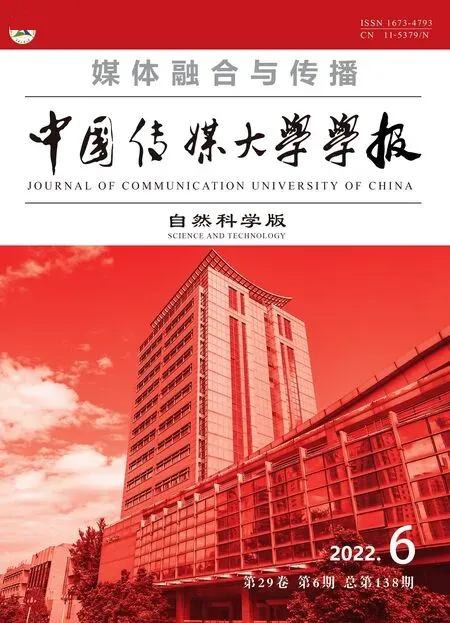计算传播视域下的受众效用函数构造探析
2022-12-26甘浩辰
甘浩辰
(四川大学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1 引言
在当今复杂网络与大数据背景下,受众研究是以传播学为主要代表的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将受众视为一种动态的、社会的、结构的存在[1]。在对受众研究的过程中,客观经验主义范式形成了垄断[2]。而在经验主义下的实证研究中量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期受众量化研究主要基于社会学与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出发,运用基于问卷调查的描述推断性统计或者控制实验因果分析等方法有效地研究受众的各类议题。而除了上述两种方法以外,基于数理建模与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引入其中,例如博弈论、多主体(Agent)系统建模与仿真、复杂网络与社会网络等。得益于新的研究工具,交叉学科背景下的受众量化研究成果得到了进一步扩充。
然而,这些新兴方法却在与受众研究理论接洽的过程中产生脱节,阻碍了受众理论的发展。传统的受众量化研究中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手段主要是“概念操作化”[3],即对理论中的概念操作为变量,它能够将理论与研究议题转化为可量化的实证指标并得以计算。但是对于复杂网络与大数据来说,概念操作化的理论实证结合方法却难以发挥作用。第一,从统计原理来看,概念操作化只是确立了用于描述理论的变量,而整个理论的逻辑联系则需要先验的概念基础或因果联系,因此,单纯统计分析只是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方法本身缺乏对这种相关关系的逻辑总结,导致不时出现诸如“伪回归”或“内生性”问题[4]。第二,从复杂系统来看,基于数据驱动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有什么数据做什么研究”,相当多的受众仿真研究是基于流行病传播理论与阈值模型,媒介理论、市场理论或心理学理论在其中难以铺展。除此之外,在建模仿真时,现有的受众理论本应用于刻画主体(Agent)的属性,但对这些理论进行概念操作化时,只能解析出理论中的变量,并未刻画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如果脱离现有理论,又会与其他大跨度学科理论产生重叠(例如上述的流行病传播理论与模型),虽然不至于陷入还原论的境地,但会削弱传统理论的地位,例如有学者曾批评方法滥用现象导致了理论的失衡[5]。这些情况使得复杂网络背景下的受众量化研究陷入囹圄,难以前进,间接也导致对受众的计算面临着方法维度的巨大挑战[6-7]。
为何会产生上述现象与问题?从系统哲学角度而言,贝塔朗菲(Bertalanffy)曾指出,对于系统科学的体系建构,存在两种可能的入门方式。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径直接受某一种合用的系统模型和定义,严密地推导出相应的理论。……另一种即本书的方法,就是从各种不同学科所出现的问题出发,说明系统观点的必要性,然后用实例或详或简地介绍[8]。系统科学家艾什比(Ashby)则提出了“从下到上”的经验性方法和“从上到下”的概念性方法,前者考察已知世界的所有系统并进行总结,后者是从逻辑概念出发推导所有可能的系统,艾什比认为,系统科学应该从抽象性和普遍性向下开展工作[9]。毫无疑问,现有的受众研究正是由于受制于经验性问题从而难以发展。而艾什比虽然并非传播学者,却从系统哲学的高度准确地抓住了这一潜在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之道。
那么,如何使用一种具有通用性、协同性与简约性的理论分析方法以弥补复杂网络系统背景下的受众研究缺陷?为此,可以基于艾什比的观点,开发一个严密的系统逻辑结构,使得所有形式都能在其中找到它们的关系和位置。对于受众研究而言,需要找到一种具有公理性与基础性的方法以补充“概念操作化”的缺陷。为此,提出一种数理建模“效用化”方法可将受众理论进行量化。
2 “效用化”在多学科中的历史
2.1 社会科学
效用这一概念已在诸多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使用。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效用主义的创始人边沁(Bentham)和密尔(Mill)将其融入到了经济学中,马歇尔(Marshall)将基于效用主义的经济学原理进行系统整理,推广成为经济学基础,后又得到萨缪尔森(Samuelson)的进一步数理化,进而依托效用主义,形成了消费者偏好、效用与需求理论,使得计量经济学有了经济学理论支持。由肯尼斯·阿罗(Arrow)、布坎南(Buchanan)和阿玛蒂亚·森(Sen)等人基于效用方法所创立的社会选择、集体决策、福利分析数理模型已经在政治投票、制度设计与政策分析中得到了充分应用。
2.2 认知科学
在心理学基础的认知科学或神经科学中亦有基于效用的研究。早期德国生理学家与心理学家韦伯(Weber)与其学生费希纳(Fechner)对心理进行了数理化表述,确定了韦伯-费希纳定律(Weber-Fechner Law),明确了“阈值”、“心理量”等概念。在当代,卡尼曼(Kahneman)与特沃斯基(Tversky)依据效用基础建立的“前景理论”[10]。神经科学家达玛西奥(Damasio)于1994年创立的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Marker Hypothesis)的过程中又对效用最大化进行了分析[11]。除此之外,司马贺(Simon)则对理性有限性与主观期望效用进行分析与批判,并创立了“超凡模型、行为模型、直觉模型”等心理决策研究理论。国内学者喻国明亦提出了一种基于认知传播研究媒介用户体验的效用进行测度的方法[12],其中即使用了效用概念。
2.3 数学与计算科学
从数学与计算科学角度来说,最早的效用概念出现于18世纪,数学家伯努利(Bernoulli)提出了期望效用这一概念以研究圣彼得堡悖论(St.Petersburg paradox)[13]。冯·诺依曼(Neumann)与摩根斯坦(Morgenstern)发展出了一套公理化和数理化的基于不确定性的效用理论,即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理论(VNM Utility Theory)[14]。他们的效用理论不需要经济学中的货币收入约束或价格条件等,只需存在理性的偏好关系和一些基本假定即可。这一套效用理论的建立使得博弈论在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得到了发展,并使得计算科学出现了基于博弈论的信息传播行为研究,在此基础上,博弈论(Game Theory)与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又得到了结合。杰克逊(Jackson)以及埃斯利(Easley)就认为,在预测社会网络图谱、模拟信息扩散等社会网络分析问题中应该使用博弈论[15-16]。目前已有较多学者提出可以利用博弈理论来研究信息传播与扩散[17-18]以及基于博弈论的信息传播者主体竞争问题[19]。
2.4 传播学
传播学领域并未明确提出效用理论,但是仍然可以从经典受众理论中发掘出与效用相关的端倪,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在改进“使用与满足理论”过程中所崭露出的效用表述。“使用与满足理论”由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于1973年做出了系统总结,是传播学研究受众的重要理论[20]。而在1974年时,布鲁姆勒(Blumler)和卡茨还对理论作出了一些描述与适用范围的假设。同时,其他同期研究者开始运用社会心理学对“使用与满足理论”进行建设,分析受众动机的来源、外部影响等[21-22]。另一部分学者则考虑模型的适用性、约束条件与定义。由此布鲁姆勒开始尝试着识别“使用与满足理论”中的“大量的意义”[23],鲁宾(Rubin)也简化了媒体的使用特性[24],并在之后提供了一个理论的适用假定[25]。在这一系列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效用(Utility)的概念开始出现,例如布鲁姆勒就提出,受众的“积极行为”存在“效用”,即指“媒体对人们有用,人们可以那样使用媒体”。比奥卡(Biocca)也提出,受众主动性存在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使用的主动性表现在特定的媒体满足自己的需要[26]。实质上,诸多学者已试图使用一种公理化表述的形式以确定效用的概念,但随着传播学受众理论的发展,对相关概念进行公理化工作并未继续深入下去,从而也丧失了将本拥有控制论、信息论、一般系统论基础的传播学数理化方法进行深入推进的机会。
据此,本研究将对“使用与满足理论”进行公理化叙述,基于公理化构造受众效用函数,并尝试在研究案例中初步应用效用函数,分析受众效用函数在传播学受众研究的可行性。
3 “使用与满足理论”假设的分析
3.1 卡茨—布鲁姆勒—古尔维奇假设(KBG假设)
卡茨等人率先提出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一理论的基本形态是,由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产生了需求,这种需求又导致了人们对大众传播或其他信源的期待,这种期待引起了不同类型的媒介接触等行为,其结果导致需求的满足和其他后果。卡茨等人提出了5个经典假设。可将其概括成五个假设,动机化假设、主导化假设、竞争化假设、理性人假设、非规范假设。
动机化:受众是积极的,其媒体使用行为是目标导向的。
主导化:对需求的满足和对特定媒体的选择之间的联系,是由受众决定的。
竞争化:媒体需要与其他能满足受众需要的信源竞争。
理性人:人们对自己的媒体使用、兴趣和动机都有足够的自知之明,同时也能够向研究者确切地描绘其媒体使用情况。
非规范:应该暂时不考虑受众将需求和特定媒体或内容相联系时的价值判断。
3.2 鲁宾的基本假设
鲁宾在卡茨等理论的基础上,改进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5个前提假设,同样将其概括为五个假设:动机化假设、主导化假设、竞争化假设、外生性假设与动态性假设。
动机化:受众的传播行为,包括媒体的选择与使用,是在一定的动机驱动下的有目的的行为。受众选择特定的媒体或内容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这是一种功能性行为,会产生某种后果。
主导化:选择和使用传播媒体的主导权在使用者手中。受众具有不同程度的主动性,他们决定使用什么媒体和如何使用,而不是被媒体所使用。
竞争化:即媒体与其他形式的传播行为相互竞争。
外生化:社会和社会心理的因素引导、过滤或影响着传播行为。即外部因素会影响上述传播行为。
动态化:由于受众的传播行为会决定媒体的行为使用方式和后果,而媒体又会对其他受众也产生影响,进而还会影响到社会,又最终影响到传播行为。
3.3 对KBG假设和鲁宾假设的简要讨论
除了保留动机化、主导化和竞争化以外,鲁宾假设废弃了KBG假设中的理性人与非规范,取而代之的是外生化和动态化。例如,考虑一个地区的受众因为文化传统而喜爱观看某特定电视节目,使得该节目收视率升高,进而该节目在该地区收费提高,又使得受众被迫花时间去工作,进而减少收看时间(动态化)。鲁宾假设虽然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但KBG假设无疑更具完备性和严格性,一方面,理性人假设保证了“使用与满足理论”框架中的受众行为是明确的,它使得“动机化”的结果对于受众来说是“好”的,即存在价值判断。不过这一问题可以被“非规范假设”解决,从而在研究中不需要衡量其价值判断。例如在下面的例子中,受众对节目的选择具有理性,并在收费上升后减少观看时间,这一分析过程也是非价值判断的,研究者无法对受众进行道德评判。
综上,本研究采用KBG假设作为出发点构成公理化基础。
4 基于效用的KBG假设公理化描述与性质
4.1 效用的基本含义
边沁对“效用”的最初定义为“有关快乐和痛苦的经验”,它“指出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我们将要做什么”。[27]因此效用有了某种“享乐”(hedonic)的性质,后来则被卡尼曼称之为“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当代社会科学中,效用定义实际是一种“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它是指对某项选择结果所赋予的权重,而这由人们的选择行为显示。效用是序数(ordinal)而非基数(cardinal),效用的简单加总是无意义的。
4.2 基于效用偏好的KBG假设再演绎
下面基于效用偏好,对KBG假设进行再叙述。
动机化:受众的信息与媒介接收行为都具有动机和目的,在基于效用主义的引导下,动机化能为做出这一媒体选择的受众带来效用。
主导化:受众能自主决定效用是映射于自身偏好的,受众可被观测的行为反映了偏好。主导化肯定了“积极受众”的存在,而“积极受众”观点是目前受众理论的主流。
竞争化:对于传播主体而言,竞争化是指谁能生产更能满足受众动机的媒介产品或信息。但对于受众来说,受众资源有限,不可能完全收获所有媒介产品或信息。竞争化保证了约束条件的存在,使得受众在有无限动机与主导权的情况下依然要做出选择。
理性人:理性人假设被许多研究者批判,的确对于一个受众而言,他不可能明确的知道自己对于媒体或信息的偏好排序。但对于研究者来说,理性人假设的意义在于从公理角度设定了客观上“受众具有明确的偏好排序”这一特性,而受众实际上是否真正明确或动态改变了自身的偏好排序并不属于假设的一部分。许多“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就将重心放在了“什么导致受众的内在偏好结构发生了变化”,但这本身是一个实证的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偏好发生变化时会影响偏好结构,而偏好结构再影响到受众的选择和决策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情。所以应当只考虑给定(given)偏好而非偏好变化的情况。
非规范:非规范假设使研究专注于观察偏好的客观存在,而偏好的来源和道德问题不纳入考虑范围之中。
4.3 KBG假设的公理化性质
基于偏好关系的公理化是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理论数理化的基本方法。将KBG假设公理化需要引入一种“偏好关系”,偏好关系在传播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验证,例如有研究者分析了社会网络的传播者和受众的偏好一致性,发现偏好的作用对用户转发行为有较大影响[28]。
当一个受众对媒体或信息的“偏好关系”,满足以下两个性质,就可称这一偏好关系为理性的。
(1)完备性(Completeness)
对于所有在受众选择范围内的备选媒体(或信息)X集合中,其中任意两个媒体∀x,y∈X,受众对于其的偏好排序是,要么x≻y要么y≻x,要么x~y。在这里,≻表示“严格偏好于”,~表示“偏好无差异”。也就是说,受众的偏好存在完整排序,不存在一些超脱于偏好关系的性质。这是由理性人假设与动机化假设所建立。
(2)传递性(Transitivity)
对于所有在受众选择范围内的备选媒体(或信息)X集合中,其中任意三个媒体∀x,y,z∈X,如果x≽y且y≽z,则x≽z。≽表示“弱偏好于”,理解为“至少一样好”。
上述两个性质是基于KBG假设的动机化和主导化所建立,它保证了受众在进行选择时是理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完备性与传递性的表述与传播学的认知不协调理论也是具有一致性的。
(3)单调性(Monotonicity)
所有在受众选择范围内的备选媒体(或信息)X集合中,x∈X,若y∈X,且x≥y,则x≽y且y∈X,则可说这一偏好关系≽具有单调性。
单调性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单调性是弱单调的(weakly monotone),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多量信息与单一信息的偏好选择是无差异的。第二,数量维度上单调性的假设是良好的,但是单调性难以解释受众对完全不同质的信息或媒体的需求偏好。因此还需引入第四个假设。
(4)凸性(Convexity)
若对于x∈X,存在y≽x和z≽x,则对于任何α∈[0,1]都有αy+(1-α)z≽x,则可说≽这一偏好关系具有凸性。
多样性则是由KBG假设的竞争性所确定。凸性可以理解为受众偏好媒体(信息)的多样性的基本倾向。凸性能与单调性相配合,解决“信息获取倦怠”,若受众偏好是凸性,则多性质信息优于单一性质消息。
5 受众效用函数的构造
在基于上述偏好关系的公理化假设的情况下就可以尝试构造一个基于媒体(信息)的受众效用函数。给出选择集合X={x1,x2,...,xm},以及定义在X上而且满足上述完备性、传递性、单调性和凸性的偏好关系≽,若存在效用函数u:X→ℝ,并且∀x1,x2∈X,都有:
则可说u(x)是个能代表偏好关系的效用函数。
对u(x)存在性的证明较为简单,可参照冯·诺依曼—摩根斯坦定理,此处不再赘述。
某个偏好能否由效用函数表示,与其对偏好的假设有关,下面给出一个命题并予以证明。
命题:只有理性的偏好关系≽才能用效用函数u(x)表示。
首先证明完备性。因为u(x)是定义在X上的实值函数,所以∀x1,x2∈X,要么u(x1)≥u(x2),要么u(x2)≥u(x1),由于u(x)是表示偏好关系≽的函数,这意味着要么x1≽x2,要么x2≽x1。其次证明传递性。假设x≽y且x≽z,由于u(x)能代表≽,那么u(x)≥u(y)且u(y)≥u(z)。因此u(x)≥u(z)。
只要受众的选择满足假设时,就可以通过观测行为逆推出受众的偏好倾向。由此,受众效用函数的适用性就得到了初步证明。
6 受众效用函数在传播应用问题研究中的范例
下面以“受众个体对媒介的选择与规划”“、受众互相影响的媒介选择”与“社会网络分析下的受众网络关系”为例分析受众效用函数如何与计算传播方法相结合。
6.1 受众个体对娱乐分配与规划问题
给定一个男孩有60分钟可供娱乐,他的选择集如下:游戏、电视。构建一个具有良好性质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

其中,x代表游戏投入,y代表电视投入。无论是游戏或是电视,其消耗的时间是等价的,此时只能假定游戏与电视的单个效用与时间是具有相关性,即“受众选择游戏时间越多代表受众越喜欢这个游戏”。这看似符合逻辑但实际上会存在外因的干扰,例如难以剥离游戏类型偏好的影响,因为男孩可能是为了想要融入同学的社交而游玩;也可能是受到了内心本身的需求影响。为此,在效用函数的意义下,上述因果关系可转换为“受众选择这个游戏的时间越多,则该游戏在男孩心里的偏好排序超过电视”,而偏好如何产生即无需考虑。
现在,将这一函数采用单调变换。在等式两侧施加对数化处理。lnu=lnxαyβ进而转换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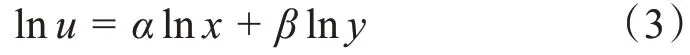
这表示成了一个形如回归模型的形式,此时,理论与实证就形成了结合。其中可以通过统计方法,测度出α的大小和β的大小,最终得到u(x,y)的具体形式。假设通过计量方法已经获得了两个系数的数据,如果令α=3且β=2,则可以得到一个模型:

对男孩的行为做进一步约束。假如男孩每天都需要观看一集20分钟的电视剧,但总娱乐时间只有60分钟,那么男孩的媒介选择行为应当如何?下面用效用函数对其进行解答。


此时就可以运用拉格朗日乘子法(Lagrange Multiplier)或线性规划(Linear Programming)解出答案。结论很显然,男孩的媒介选择策略是:20分钟投入电视,40分钟全部投入游戏。进一步地,即可以使用效用函数结合动力学方法对男孩的媒体选择和规划做出仿真而不失“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要求。
6.2 受众互相影响媒介选择问题(媒介选择博弈问题)
性别战(Battle of Sex)博弈中,希望合作的参与人意见却并不一致。一个具体情形是,男孩与女孩选择看电视节目,但是男孩想看球赛直播,而女孩想看演唱会直播,收益矩阵如表1。

表1 BOS博弈收益矩阵
定义效用函数,使用u1(男孩选择,女孩选择)来表示男孩参与到媒介中的效用,u2(男孩选择,女孩选择)来表示女孩参与到媒介中的效用。可以注意到:

矩阵只呈现收益结果,没有表现内在偏好,但根据这个效用结果与数学知识可以反推偏好构成。以x1代表男孩的选择变量,x2代表女孩的选择变量。x1=A或B,x2=A或B,并且A(球赛)=1,B(演唱会)=0,由此可以构造出两人的效用函数。

在构造了效用函数后就可以看出BOS博弈的本质是参与双方互相影响。这与受众互相交流的现象极为相似。例如受众之间的媒介选择同样会影响到各自的媒介选择,他们之间的偏好也互相影响了对方的决策。同时,这里只是构造了男孩和女孩两个人的效用函数,如果构造N个体或N媒体的效用函数,那么即可对大众传播中的媒介选择行为进行仿真,且同样可用效用函数的性质予以分析。
6.3 社会网络中的受众关系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社会网络个体可分为5类:意见领袖、活跃发言者、被动跟随者、纯粹旁观者、非用户,其中后3种被定义为受众[29]。然而,传统的社会网络方法不能描述个体节点的行为(例如理性和智能性行为),也不能模拟这些节点之间的策略性互动[30],而这恰恰是传播学的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所需考虑的问题。在基于效用函数设计下,这一问题能得到解决。国内非传播学界的学者也尝试过基于效用函数与博弈论,构建传播者和受众的信任关系的信息传播模型[31],但同样缺乏传播学理论依托。
以案例2的男孩女孩媒介选择为例,建立一个基于受众的媒介选择网络(见图1与图2)。

图1 效用为3的媒介选择网络(有效网络)

图2 效用为0的媒介选择网络(无效网络)
很明显,当评价这一社会网络的整体效果时,应当考虑的在这个网络中,所有参与人的效用最大化,如果这个网络能使得u=u1+u2数值最大,则这个网络应当是有效率的。从之前的效用分析可以看出,当男女选择同一活动能达到效用最大化。而剔除了男孩与女孩的连接,无论双方做出任何选择,其效用都为0。
7 总结
基于KBG假设已经可以初步构建一套有理论意义的受众效用函数,受众效用函数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作为基本公理,并基于“自上而下”的系统化路径证明其适用于数理化计算和分析,为计算传播研究提供了相应的数理化方法基础,部分地解决了计算传播方法研究中概念数理化的问题,并提供了一套具有通用准则改进空间的数学表达式。一定程度上,“效用化”实现了学者在计算传播研究过程中“计算中心”[32]的转移,构建了自传播学理论到工具的转换。
但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效用函数并不总是存在的,即不是所有的受众的“偏好”都可以用效用函数来表示。正如前文所说,第一,偏好必须具有理性,第二,有部分偏好即使理性,甚至满足单调性与凸性,也无法构造效用函数,例如字典序偏好关系(Lexicographic Preference Relation)满足了公理,但无法构造效用函数。同时,目前的受众效用函数仅适用于“受众”,对于“信息生产者”或“渠道传播者”而言是否适用尚不可知。因此效用化方法能否得到进一步推广,还有待考究。除此以外,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受众效用函数并不能支撑计算传播中的内容文本分析理论基础,仍需要基于现有的传播学理论扩展效用函数的适用性并作出更多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