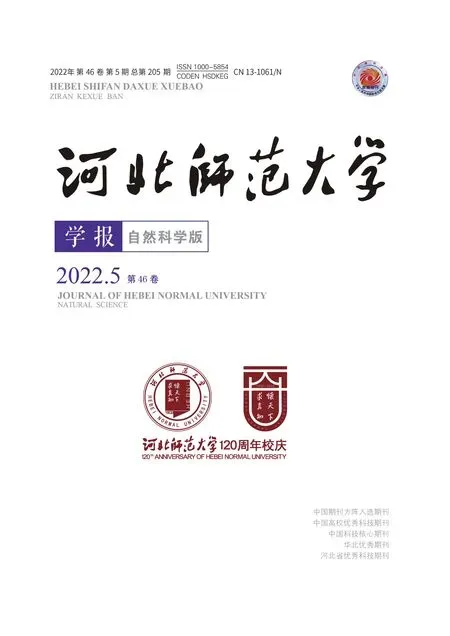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方法研究进展
2022-12-25闫海明杨会彩姜群鸥
闫海明, 张 瑜, 李 炜, 杨会彩, 姜群鸥
(1.河北地质大学 土地科学与空间规划学院 数字国土实验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31;2.河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3.北京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学院,北京 100083)
近几十年来,生态补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高度重视与广泛应用[1-3].生态补偿能够有效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给,其有效性已在美国Catskill流域生态补偿项目、哥斯达黎加的PSA项目等大量生态补偿项目中得到了证实[2,4-7].目前,生态补偿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8-9],并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等项目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中国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且远落后于项目实践,这也是中国生态补偿未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5,10-11].因此,开展更深入的理论探索对设计完善中国及其他国家生态补偿项目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12-14].
生态补偿研究涉及生态补偿的概念、标准、方式等议题,其中补偿标准是其核心与难点问题[15].虽然已出现了大量的生态补偿案例研究和理论探讨文献,但其多为现象描述或案例罗列,缺少对生态补偿本质内涵的深入辨析,对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方法等核心内容的系统性总结也相对匮乏[16-17].本文中,笔者回顾了已有的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方法,系统总结了已有方法的优点与不足,深入辨析了生态补偿的本质内涵,并深刻探讨了生态补偿标准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的本质关系,以期为探索更加合理可行的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方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方法研究进展
生态补偿标准主要涉及2个重要问题,即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及生态补偿标准的差别化[18].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依据生态资本理论,从投入、产出角度已经探索出多种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并相应地认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上下限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机会成本,但总体上目前依然缺少比较公认的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方法[18-21].
1.1 基于投入角度的估算方法
生态补偿的投入可简单划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是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开展相关谈判的重要基础[15,17].直接成本是指为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而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成本[17].直接成本很明显是生态保护的必要投入,它的核算有地区财务数据作支撑,比较容易量化[15],部分学者也认为应以直接成本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值,但是直接成本并没有体现出生态补偿的激励性,与主流的狭义生态补偿的基本理念不一致[7,16].另外,依据直接成本确定的生态补偿标准往往偏低,对受补偿者的自愿性造成很大负面影响[2,16].但是,生态保护的直接成本也可能非常高.例如,河北省截至2015年投入数百亿元用于保护滦河水资源,向天津市无偿供水累计近200亿m3,并累计实现供水效益超过500亿元,但实际上只在2016—2018年得到了15亿元的生态补偿[6].很明显,仅依靠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者承担直接成本也是不公平的.所以,直接成本不属于狭义的生态补偿,但直接成本依然应该归入广义的生态补偿,在生态补偿项目的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考虑,并且理论上应该由补偿者承担.
间接成本又称机会成本,是指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者为保护生态环境而付出的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17],目前主要有3种核算方法,即问卷调查、实证调查和间接计算[19,22].而基于机会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依据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机会成本进行确定[23],其核算方式简便、操作简单易行且相对公平,目前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生态补偿标准确定的主流方法[18].但是,机会成本法难以全面量化成本,且不同的方法得到的机会成本可能差异较大,一般都会导致生态补偿标准偏低,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可持续性[23-24].另外,机会成本法对受偿区域内部的差异性考虑较少,容易导致补偿标准偏高或偏低等问题出现,严重影响生态补偿的公平性与效率,甚至可能导致与预期相反的效果,限制了基于机会成本法的生态补偿标准的准确性与适用性[2,12,22,25].为解决机会成本的异质性不足问题,国外学者已经提出了多种改进方法,如Kosoy等[26]在2007年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的土地租金等机会成本的代理变量[18].总体上来说,以机会成本法为主的成本估算法虽然存在公平性与效率不足的问题,但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目前依然是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方法的主流[15].
1.2 基于产出角度的估算方法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生态补偿的重要依据.基于产出角度的生态补偿属于直接激励,能够有效提高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正确认识[18,27].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产出的角度量化生态保护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而估算生态补偿标准,但对生态效益与生态补偿标准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争议[7,23,28-29].
1.2.1 基于价值总量的估算方法
早期研究一般试图准确估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并将其作为生态补偿的标准[17],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主要有直接与间接两种核算思路[4,30].直接核算的思路采用价值量法,一般是基于土地面积与价值当量,包括条件价值法、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假想市场法等[31].实际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各类土地面积之间远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且价值量法的结果受研究人员主观性影响较大,导致价值量法的估算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存在不能准确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异质性等问题.间接核算的思路是利用能值法、物质量法等估算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量,进而采用影子价格法核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5,12].其中,能值法由于计算过于复杂已经很少使用[12,32-33];而物质量法能够利用InVEST,ARIES,MIMES等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定量估算不同种类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能准确直观地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量,并实现空间显性和动态化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从而为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12,19,34-35].尽管如此,由于目前生态系统服务指标选取、价值量估算方法等方面依然缺乏统一标准,进而导致估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已有研究中的估算结果往往都远超现实的补偿能力,导致其只能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上限,难以应用于实践操作[10,12,19,30].
1.2.2 基于特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的估算方法
学者提出了多种改进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生态补偿标准的思路,以期提高生态补偿标准的实践可行性.例如,由于生态系统服务是受益依赖的(benefit dependent),人们对受益的偏好决定了其关注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范围[2],因此,部分学者提出选择主导生态系统服务类型进行生态补偿[15].实际上,大部分已有的生态补偿项目也已经根据不同的生态补偿主体的需求有目的地选择特定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补偿[36],如已有的生态补偿项目一般只针对特定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1,37],但可能会对非人类需要的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造成破坏[2].
1.2.3 基于调整系数的估算方法
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补偿标准应结合生态效益与经济发展水平确定[7],并据此提出了利用调整系数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估算生态补偿标准的思路[4].例如,中国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土地利用数据与Costanza、谢高地等的研究成果估算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总量,并利用社会经济系数予以修正,从而得到比较可行的生态补偿标准[37-39].目前,常用的调整系数有市场逼近系数和支付意愿系数[4,20],以及基于恩格尔系数与皮尔曲线的新型的社会支付意愿系数[7,40].调整系数法比较充分地考虑了补偿者的支付意愿及支付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生态补偿标准的实践可行性;但是,这种方法本质上反映了生态系统服务总量在补偿者与受偿者之间的分配博弈,而因为受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因素影响,两者的博弈能力差异较大,可能会导致确定的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存在很大不确定性[4,40].最重要的是,调整系数法对生态补偿的激励作用体现的不够充分,与生态补偿的本质目的并不完全相符.
1.2.4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的估算方法
生态系统服务实际上有存量和增量之分[41-42],部分学者提出应以生态保护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作为生态补偿标准[7,18,23].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的生态补偿能反映其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的效率,但是目前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的估算依然比较困难[15-16];另外,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补偿标准应介于机会成本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之间[7,18,23],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是趋于减少而不是无限增加的,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可能低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的机会成本,会对供给者的自愿性产生很大负面影响[16,43].
实际上,这种观点可能是源于对生态补偿的额外性的误解.部分学者认为,额外性是生态补偿干预前后因生态补偿干预而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增量[18,44-45],但在实践中,生态补偿并不能一定保证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增加,甚至仅能保持其稳定;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补偿的额外性是指没有生态补偿就没有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状况[46-49],这种额外性不仅和生态系统服务量相关,而且和“无供给概率”,即部分学者所提到的不实施生态补偿而导致的不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概率相关[46],但国内的很多学者往往忽略了后者.另外,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缺乏额外性的情况是花了钱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从而导致生态补偿的效率低下[18],但实际上缺乏额外性的情况是指针对无论如何都会采取的实践活动,也给予了生态补偿,其关键特征在于生态补偿是否会导致特定的实践活动,而非生态补偿的效率[50].总体上,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估算存在数据匮乏、成本过高、具有争议等问题,目前额外性的定量估算依然非常困难,实践中许多案例仅进行了定性评估[44-45].
2 生态补偿的经济学本质研究进展
2.1 生态补偿的经济学本质辨析
已有相关研究的诸多不足实际上都源于没有真正理解生态补偿的地租本质[2,51].生态补偿的经济学本质界定直接影响补偿标准划分、目标区域范围划定等关键问题[36].已有研究对生态补偿的经济学本质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界定.其中,狭义的生态补偿仅包括对生态保护活动的正外部性的补偿,而广义的生态补偿还包括对环境污染者的收费.目前后者使用的更广泛[37].但已有的两种理解都没有揭示生态补偿产生的根本原因及经济学本质,已有研究也缺少对生态补偿的本质内涵及外延的深入辨析,导致后续研究中的诸多争议.
生态补偿一般是基于明晰的产权,通过生态系统服务消费地区(一般是流域下游发达地区)支付补偿费用以获取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区(一般是流域上游欠发达地区)供应的生态系统服务,从而体现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2,37].实际上,在实施生态补偿之前,下游地区已经长期免费获取了上游地区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另外,如果上游地区没有人,则依然有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但实际上上游地区的人有能力去破坏或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生态补偿的目的是防止这些上游地区的人破坏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甚至促进其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供给[51].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际上只是生态补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生态补偿的根本前提与充分条件实际上是土地产权(所有权或使用权)归上游地区的生态系统管理者所有[51-52].换句话说,生态补偿本质上是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者向供给者交纳地租以获取上游地区的部分土地使用权,从而保障上游地区对下游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是地租理论在生态领域的应用[51].因此,建议将生态补偿进行如下定义:一种通过获取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的部分土地使用权,从而保持甚至增加特定生态系统服务消费者所需要的特定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给的特殊地租.另外,建议将生态补偿重命名为生态地租(land r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以促进相关学者及公共管理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实际上目前已有少数中国学者做了相关研究[51],但依然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2.2 基于地租理论的生态补偿标准估算
实际上,由于生态补偿的本质是地租,所以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也应基于地租理论.地租包括绝对地租、级差地租,而生态补偿也可以类似地进行划分与估算.政治经济学中的绝对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获得的地租,类似地,生态补偿中的绝对补偿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凭借其供给能力垄断(实际上也与土地使用权垄断相关)所取得的地租,即生态补偿项目中绝对地租也源于土地产权,因此,生态补偿项目中的绝对地租可根据土地产权派生的机会成本进行估算[16,43].实际上,如果受益者提供的生态补偿标准低于供给者的土地产权所派生的机会成本,则供给者参与生态补偿的自愿性会很低[16,43].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生态补偿标准中的绝对地租是为了保证生态补偿项目参与者的自愿性,从而使生态补偿项目的参与者保持土地利用方式现状,对保证生态系统服务存量的供给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并不能保证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一定得到提升.
政治经济学中的级差地租是由于耕种土地的优劣等级不同而形成的地租,包括级差地租Ⅰ与Ⅱ,而在生态补偿项目中的级差地租可定义为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性而形成的生态补偿,也可以类似地分为级差补偿Ⅰ与Ⅱ[51].政治经济学中级差地租Ⅰ的形成是源于不同地块的生产力差异,而级差地租Ⅱ是源于同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产生的超额利润转换而来的地租.在生态补偿项目中,这两种差别也会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别性(体现为时空异质性),从而产生生态补偿项目中的级差地租Ⅰ.而各个连续投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产生的超额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会转化为地租Ⅱ.例如,通常情况下,促进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补偿标准要高于避免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补偿标准[18],也就是由于促进土地转换一般需要增加投资进而有效地产生生态系统服务增量[51].另外,由于生态补偿标准中的级差地租源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异性,因此可以根据具有明显空间异质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其中,级差地租Ⅰ的确定可以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与调整系数相结合的方法,而级差地租Ⅱ的确定可以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估算的方法.此外,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都会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产生重要影响,补偿标准既应覆盖级差地租Ⅰ,也应覆盖级差地租Ⅱ;而实践中,基于机会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仅覆盖了级差地租Ⅰ,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增量的生态补偿标准仅覆盖了级差地租Ⅱ,都会导致生态补偿标准偏低[16,43],如中国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与生态系统服务脱钩,广泛使用“一刀切”的生态补偿标准没有体现出级差地租,这是导致这些生态补偿项目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生态保护制度的作用长期受到制约的关键原因[7].
3 结 论
1)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依据生态资本理论从投入、产出两种角度探索出多种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方法,但由于目前对生态补偿本质内涵的真正理解依然匮乏,依然缺少比较公认的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方法.
2) 学者对生态补偿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但都未揭示生态补偿的根本起源与经济学本质.笔者提出,生态补偿的本质内涵是地租,并建议将生态补偿定义为一种通过获取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的部分土地使用权,从而保持甚至增加特定生态系统服务消费者所需要的特定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给的特殊地租;另外,建议将生态补偿改为生态地租,以更清楚地揭示其本质.
3) 生态补偿标准不仅覆盖绝对地租,也应该覆盖级差地租;生态补偿标准中的绝对地租源于土地产权的垄断性,可根据土地产权派生的机会成本估算;而生态补偿中的级差地租源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异质性,可根据时空显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生态建设与保护成本属于广义生态补偿,不可用于确定狭义的生态补偿标准,但理论上依然应由补偿者承担;更重要的是,生态补偿标准与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博弈能力密切相关,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