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文化心理对早期装饰纹样的审美指向性影响
——以连续植物纹的肇始为例
2022-12-22郭昕GuoXin
郭昕 Guo Xin
社会文化心理是社会群体在社会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稳定性、阶段性特征的共同社会意识,它支配和约束着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判断等社会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社会群体的审美指向。[1]审美指向是主体对审美对象的选择和导向。在一个时代或地区广为流传的审美对象,体现出相对稳定的审美指向性,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社会文化心理的必然产物。连续植物纹就是这样一种审美对象。
连续植物纹以植物的花叶、枝干、藤蔓作为纹样主体,往复相连,构成二方或四方连续图案,较为著名的连续植物纹包括缠枝纹、忍冬纹、卷草纹等。连续植物纹广为流传、变体众多、历史古早、传承至今的属性,使之如同一本无字的史书,能真实折射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成为装饰纹样中的“活化石”。多年来不少学者从装饰艺术发展史的角度,对富有代表性的连续植物纹的纹样流变、图式特征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明确连续植物纹的构成特点包括:以植物的花叶枝蔓为内容要素,以连续、反复、曲线为形式要素;同时连续植物纹并非我国所独有的传统纹样,跨越广阔的时空可以发现各种既满足连续植物纹基本构成要素但又各具特色的图式,如古埃及的莲花纹、古希腊的莨苕纹、古印度的忍冬纹、阿拉伯的蔓草纹等,这些纹样在今天的装饰艺术中依然被大量运用。在这些研究中,对连续植物纹本体的形式特征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它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会广为流传、为什么会变体众多,这些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尚未被阐明。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原始文化心理的角度剖析连续植物纹样产生之前及产生之初,决定其表层图式特征产生、传播的内在因素,从各民族早期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连续植物纹变体丰富的原因,既可揭示社会文化心理对早期装饰纹样的审美指向性具有的深层次影响作用,也对更好地理解、传承、创新连续植物纹样有着积极意义。
原始时期,在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类的器物上就有了各种或抽象或写实的纹样,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纹样在产生之初多具有象征或叙事的意义却未必具有审美意义[2],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纹样孕育了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和后世装饰纹样的构成要素。
一、原始文化心理对连续植物纹样形式要素的审美指向性影响
南非布隆伯斯洞穴中出土的75000年前的赭石石刻上已经有了连续折线型抽象几何纹样(图1),东欧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指挥棒”上同样有布满棒体的波状纹和螺旋纹,我国新石器时代也有各种折线纹网格纹,甚至到近现代的原始部落里,也能看到类似纹样。更有意思的是,将这些纹样并置在一起,这些跨越了数万年的时间线和纵横亚非欧各大洲的纹样,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度。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原始纹样的产生和具体的地域、时间几乎没有关系,决定它们形态高度相似的是一些共同的内在因素。这种因素就是原始社会特定的文化心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简单、认知水平低下等共同特征,形成相似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相似的文化心理决定了原始纹样的构成特征,导致世界各地原始纹样的高度趋同性。

1.赭石石刻,出土于南非布隆伯斯洞窟(约75000年前)
原始社会的人类在以采集、渔猎为主的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对昼夜的更替、四季的往复和生命的始终有了初步感知,这种感性认知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自然世界中秩序、节律、循环、绵延等规律的普遍存在,而原始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微乎其微,他们的生产、生活只有与自然的规律相吻合才可能获得相对顺利稳定的生存繁衍。在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遵循自然的节律、群落的秩序、生命的循环、种族的绵延,不仅是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他们的精神信仰。而节律、秩序、循环、绵延等特征也渐渐抽象出来,在原始文化心理中形成了一种强烈而持久的结构样式。同时,从原始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来看,水波荡漾的江河湖海、连绵起伏的山脉丘陵、动物植物的花纹肌理这些自然对象都包蕴着连绵、反复而富于韵律的曲线,这与原始文化心理的“力的样式”是趋于一致的。
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当客体对象与主体心理产生这种结构上的同一时即为异质同构,审美就产生于异质同构。也就是说,自然对象具备的连续性、曲线性、重复性等特征与原始人类的文化心理中的相关结构特征契合时,便形成同构对应的格式塔,使原始人类对具备这样形式特征的外部样式产生心理上的接受与认同;同时,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原始人类也会根据其文化心理特征有意识地去寻找与之对应的客体对象,来表达自己的审美指向,而对于不符合格式塔的形式特征的对象,要么无视其存在,要么通过整体变形或者提取某一局部进行再加工的方式,使其满足原始文化心理的需求。格罗塞曾在《艺术的起源》中提到“装饰艺术完全不是从幻想构成的”,“原始民族的装饰,大多数都取材于自然界;它们是自然形态的模拟。”[3]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这里格罗塞所说的模拟并非目之所及的随意模拟,而是在原始文化心理的主导下,在自然世界中有指向性地寻觅、摹仿、提炼、加工格式塔所需要的力的样式。在这一过程中,被选择的对象逐渐脱离自然形态呈现出人工形式。这些人工形式由于符合原始文化心理的特征,被广泛地创造出来并反复地使用、长久地传承成为一种必然。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世界各地的原始纹样中都隐含着秩序、节奏等高度相似的形式美的基本规律,也包含了连续、曲线、重复等连续植物纹样形态的造型要素了。
二、原始文化心理对连续植物纹样内容要素的审美指向性影响
受文化心理的影响,在早期原始纹样中,已经有了指向连续性、重复性、曲线性的特征,从形式要素上为连续植物纹的出现做好了铺垫,但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内容元素,那就是以植物作为纹样表现的主题。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认为所有的植物图形装饰在原始艺术中都没有萌芽,他还说:“文明民族的装饰艺术喜欢取材于植物,而原始的装饰艺术却专门取材于人类和动物的形态。”[4]我们在原始纹样中确实可以看到大量写实的动物和人物图样,也可以看到大量的抽象纹样,而且很多抽象纹样还能清晰地找到从动物纹样逐步简化、抽象化的过程,如鸟纹、蛙纹等。但动物类纹样的广泛存在并不能说明原始时期就没有以植物为主体的纹样。问题的关键在于,植物在什么条件下才有机会成为原始纹样的表现对象。
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认知是:人类从渔猎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才会有从动物纹样到植物纹样的转变。也就是说当新石器时代原始农耕出现,植物成为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的时候,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农作物发生了密切的联系。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使社会心理也发生了改变,原始人类对植物有了更多的亲近和关注,于是原始纹样开始选择以植物为塑造对象。这个认知看似有理,从目前已知的出土文物来看,的确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大量的植物纹样。但是这里仍有存疑:如果是农耕的出现导致了人类对植物的依赖与兴趣,那么早期出现的植物纹样必然应该以农作物,尤其是农作物可供食用的果实部分为表现的主要对象。但在已知的原始纹样中除了不多的稻穗纹和种子类纹样,还有数量和变体都远多于此的各类花瓣纹和叶形纹。花和叶作为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对象,是否真的在农耕时代才被人们所关注呢?在此之前,它们对人类意味着什么?是否真的如有些研究者所说:“植物(包括花朵)刚开始不仅不是美的,而且可能还是恐怖的,因为这些植物之中可能隐藏着凶狠的动物”,认为进入农耕时代之前植物对人类来说是恐怖的,所以植物没能进入人类的纹样世界。[5]分析到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个事实:第一,在原始时期,令人可怖的对象往往使人产生敬畏之心,进而成为原始人类崇拜或者图腾的对象,并加以图示化用于宗教、祭祀等活动中,既然“凶狠的动物”可以成为纹样的主题,那么“恐怖的”植物也理应相同。第二,在进入农耕时代之前,并不是植物远离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渔猎时代以及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采集一直是原始人类非常重要的生产方式之一,也是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可以这样说,渔猎时代因食物来源不稳定,人类出于生存的压力,与植物的关系之密切并不亚于农耕时代。哪些植物的什么部位可以食用,哪些植物必须远离,类似的这样的经验既需要数代人的积累,也需要将经验代代传承。因此对于植物的外形特点,尤其是具有标识性的局部特征,原始人类必定积累了大量敏锐的观察、深刻的记忆。同时,我们也知道,植物的花叶枝蔓从纹理到造型都非常丰富,其中有很多是契合前文所提到的原始文化心理的“力的样式”的。既然如此,植物也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早期原始纹样的重要内容要素之一。这就不难理解出土于我国河北兴隆县13000多年前的刻纹鹿角上为什么不仅有水波纹、8字纹等曲线纹样,还有连续叶纹了(图2)。而新石器时代的植物纹样更加丰富了,包括花形纹样、叶形纹样、树形纹样等。作为原始人类长期观察、识别植物的必然结果,与我们上文的分析相吻合。这些植物纹样大多选取和提炼植物富有特征的局部加以构形。这一时期常见的植物纹样有卷花纹、勾叶纹等,以花瓣或叶片为表现主题,每一种纹样又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和各种变体,形成种类繁多的植物纹样,并逐渐定型,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带有连续、弧线、重复特征的植物纹样,比如我国庙底沟的花叶纹(图3)。

2.刻纹鹿角,出土于河北兴隆(旧石器时代晚期)

3.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庙底沟村(约前4400-前3500)
至此,已经清楚地看到,在原始文化心理的推动下连续植物纹的形式要素和内容要素均已具备,虽然我们永远无法确切考证连续植物纹样在何时何地最早出现,但可以推断连续植物纹样的出现是原始文化心理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必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的早期文化中都有可考的连续植物纹。
三、各民族早期文化心理与连续植物纹样的审美特征分化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各地域的文化特征不再具有原始时期的高度相似性,文化特质的分化导致文化心理的分化,这就直接导致了不同文化区域的连续植物纹出现了各自不同的审美特征。
古埃及是植物纹样较早的发源地之一。古埃及艺术的重要特征是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服务。古埃及人相信灵魂是不死的,人死后只要保存好身体,灵魂有归宿,就可以到达另一个永恒的世界去获得永生。不管是他们具有标志性的金字塔还是正侧面的人物构图,都是在为他们追求永生的信仰服务。从古埃及时代留下的壁画和其他物品上,可以看到在古埃及早期的艺术中由花、叶、梗构成的图案就已经较为常见,其较为常见的连续植物纹样是莲花纹。古埃及的莲花不是荷花而是埃及睡莲,这种睡莲当时分布于北非的水域中,包括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睡莲随着太阳的升降而盛开、闭合,因此古埃及人认为,太阳从莲花中升起,又落入莲花中;莲花成为重生和复活的象征,被放置在木乃伊里。莲花生于绵延的水波中,其根茎又在水面下绵延相连,其装饰的对象——壁画、亡灵书等也具有横向延展的尺幅特征,因此古埃及的工匠们提取出波状与曲线的线性几何形状联结莲花单体植株,使莲花纹从形式要素上呈现出二方连续特征[6](图4)。这些莲花纹对称均衡绵延反复无限延长,表达了对生命重生与绵延的信仰与渴望,呈现出一种庄严感和神圣感,其形式要素和内容要素相互平衡相互结合满足了古埃及社会文化心理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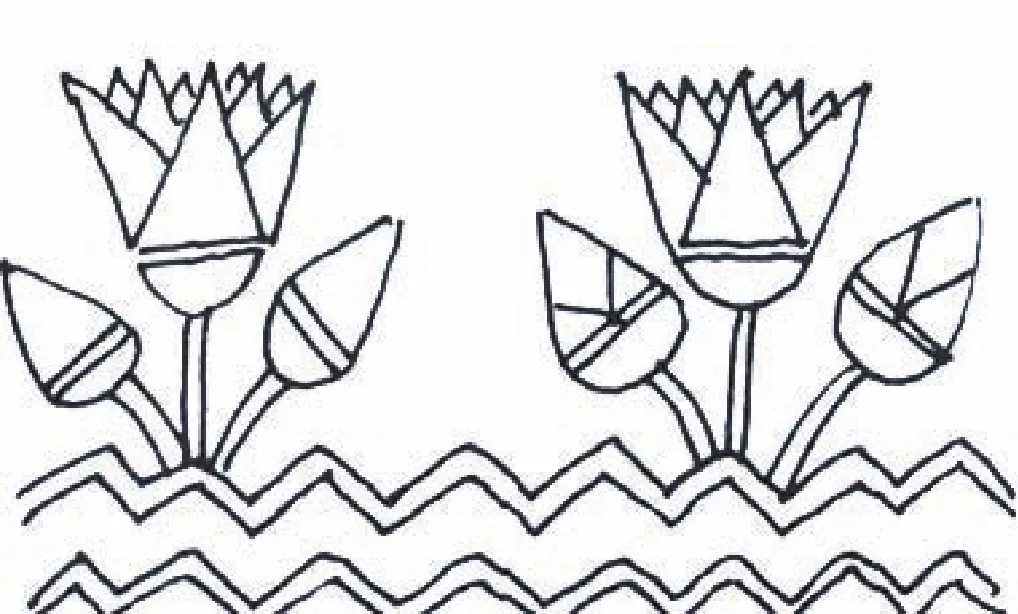
4.古埃及的莲花纹
如前所述,古埃及以其对莲花的崇拜以及装饰的需要为装饰史贡献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连续“花”纹,而与之邻近的两河流域则为装饰史创造出了同样影响巨大的连续“叶”纹。两河流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关系密切,其连续植物纹样不论从植物的单体造型还是将单体植物联结在一起的方式都与古埃及莲花纹有着较多的相似。但两河流域受巴别神系的影响有信仰“生命之树”的社会文化特征,棕榈、无花果等树木以其强健的生命力、多汁的特征成为当时人们所崇拜的“圣树”,是生殖、生命甚至光明、繁盛的象征。在亚述时期的尼姆鲁德的浮雕中可以看到棕榈圣树的典型造型就是以肥厚丰茂的棕榈叶由藤蔓状的枝干彼此连接环盖树身(图5)。对棕榈树的崇拜使得扇形棕榈叶成为两河流域古文明广泛使用的装饰纹,与埃及的莲花纹一样,出于装饰的需要不断优化,由象征性走向装饰性,形成了程式化的的连续棕榈纹。棕榈纹和莲花纹为连续植物纹样贡献了叶和花的内容要素和连续反复的形式要素,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古希腊植物纹样。

5.两河流域亚述时期的棕榈纹式样
作为典型海洋文明代表的古希腊民族,其文化心理具有自由勇敢、浪漫热烈、兼容并蓄、求真求美、追求现世生命的价值等特征。古希腊的连续植物纹样受莲花纹与棕榈纹的影响,并创造发展出了莨苕纹。莨苕是一种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植物,其旺盛的生命力、强盛的繁殖力、勇于生长的生物特性与古希腊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力的样式”相契合,使之在希腊装饰中与莲花纹、棕榈纹相结合,被大量应用。莨苕纹在形式上花叶交错、反转往复,呈现出自由活泼、舒展繁盛之态(图6),尤其是作为连接部分的卷须式样充满流畅自由的律动,彻底改变了过去连续植物纹样的单调呆板僵化,强烈表现出了古希腊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从世界装饰史的角度来看,连续植物纹样在其发展传播过程中,受经济政治交流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使各地区各民族的纹样特征呈现出相互影响交融的态势,但差异性依然明显,印度、西亚、中国、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连续植物纹样各有其特色化的形式要素与内容要素[7],这种差异性正是社会文化心理对装饰纹样审美指向性的影响造成的。

6.古希腊时期莨苕纹饰装饰的建筑柱头
结语
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连续植物纹样的源起进行研究,有利于在艺术设计中使用这一类装饰纹样时,既继承又创新,既体现出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符合当今世界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的人民群众普遍的审美心理的需要;同时以此为例,举一反三,在装饰纹样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中,以社会文化心理为深层次的考量因素,推动对纹样的深入研究。本文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肇始阶段连续植物纹样的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的趋同与分化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连续植物纹样的出现是原始文化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最后以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等为例指出该纹样之所以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发展演变出不同的表现内容与形式特征,其内在深层次原因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性。
注释:
[1]张玉能:《深层审美心理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4页。
[2]倪建林:《论原始装饰艺术的涵义》,《山东工艺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4-7页。
[3][德]格罗塞:《艺术起源》,译者:蔡慕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0-91页。
[4]同[3]。
[5]陆军、吴清芳:《浅议原始彩陶装饰方面的研究》,《景德镇陶瓷》,2016年第5期,第25-26页。
[6]刘蕊:《忍冬纹样造型的源流探析》,西安:西安工程大学,2014年,第17页。
[7]倪建林:《从忍冬到卷草纹》,《装饰》,2004年第12期,第61页。
图片来源
图1 [美]帕特里克·弗兰克:《艺术形式》(第11版),译者:俞鹰、张妗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9页。
图2 《中国美术史图库》https://m.douban.com/note/334049371/
图3 张道一:《中国图案大系1》(上册),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31页。
图4 邱凤香:《古埃及传统装饰图案创意应用研究》,《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153页。
图5 刘蕊:《忍冬纹样造型的源流探析》,西安:西安工程大学,2014年,第23页。
图6 倪建林:《中西设计艺术比较》,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