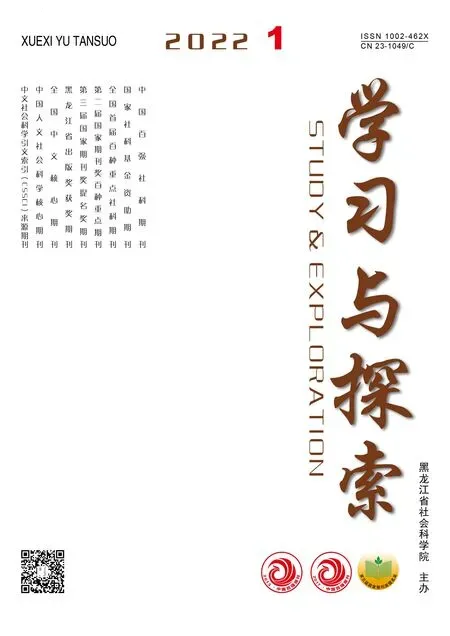“赞天地之化育”与“人是对象性活动”的比较与汇通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的本体论”建构论纲
2022-12-18王南湜
王 南 湜
(南开大学 哲学系,天津 30007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哲学层面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而要使这一结合得以深入进行,便须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结合得以可能的契合点。由于本体论在全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最为重要的便是须有在本体论层面上两种哲学结合的契合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这种突出人与其周围世界“天地”“赞”“参”互动所构成的“事”的世界视域,可视为一种“事”的本体论;与之相映照,马克思的“人是对象性活动”之命题,亦将人对自然的生产性之“赞”“参”的关系作为其本体论之第一原理。这两项本体论基本命题在直接语义层面的显著相似,启示着我们不能不思考,这其中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真正深刻的契合点,并由之而探讨是否可通过两种本体论的比较、互释、汇通而构造出一种深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的本体论来。
一、“人是对象性活动”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第一原理
与古代及中世纪哲学以超验的终极存在或最高存在为追问对象不同,现代哲学的主导倾向将目光转向了人,以“人是什么”为其总问题。将目光转向人,追问“人是什么”意味着现代哲学不再沉迷于从神或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看世界,而是开始从作为现实存在的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及自身。这种看问题的眼光被称为人类学立场或视域。如邓晓芒教授所言:“在西方,首次从人类学的立场来研究一切哲学问题的,要算休谟和卢梭。这两个人也是首先推翻了对上帝存在的一切理性证明(本体论的、宇宙论的、目的论的),而把上帝归结为人的情感需要(道德情感的证明)的人。”[1]当然,只是在康德那里,才明确地提出了系统的人类学哲学的纲领:“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作什么?(3)我可以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2]不言而喻,康德的全部哲学体系便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这里不难看出,康德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基于人的立场而作出的。人,在康德这里,无论在哪一方面的问题上,相对于绝对的、无限的上帝或自然,其根本特征都是作为受限的存在的有限性,亦即“有对性”。作为有限性的存在物,他自然只能与其限制者共存,从而不可能像古代及中世纪哲学所设想的那样,超越其有限性而达致与其限制者合一之境界。就此而言,康德的哲学革命便不能仅仅理解为对于主体能动性的弘扬,而是必须同时将之理解为对于人的有限性的揭示,因而这种能动性便只能是有限的能动性。但同时,这种有限的能动性却也指明了人类存在的开放性、未完成性,从而亦表明了人的尽管有限但却能够自我创造性生成的可能性。
康德哲学所描述的这种有限的能动性虽然是对人类真实处境的真实揭示,但却与西方思想从古代到中世纪关于人在本质上能够通过理性或信仰而通达绝对者,从而在本质上内含无限性的理解有根本性的不同,因而在康德之后,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论在其进展中便力图超越康德而消除这种有限性。这种超越有限性的消除趋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一种向古代和中世纪思想的回返,它虽然保持了主体的能动性,但却一步步地消除了其有限性,而使之成为无限的、绝对的东西。如此一来,现实中的人的有限的能动性在这种体系中也就被消解了,人在其中成为了“理性的狡计”的玩偶之类的非真正的能动者。费尔巴哈看到了这种无限性主体的唯心主义虚妄性,提出了“人是对象性存在”之命题:“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3]他认为“自我在对象中的实在性,同时也是对象在自我中的实在性”,而“一个实体必须牵涉到的对象,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它自己的明显的本质”[4]。这就是说,人作为主体,其本质乃是为其对象所规定的,从而这样的主体便只能是有限的存在物。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的“人是对象性存在”的命题,乃是向康德所揭示的人的有限性亦即对象性原则的复归。
但费尔巴哈的这一向人的有限性的复归是有严重缺陷的,因为它不仅抛弃了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主体的无限能动性,而且也抛弃了康德那里作为主体的人的有限的能动性。这样一来,既然人的本质是为其对象即自然所规定的,那么,作为对象的自然便成为绝对的规定者,而人作为主体则只是服从于自然的被动的衍生物。因此,必须将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能动的方面”导入到作为有限的存在物的人的规定中去。这便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人是对象性活动”命题所意谓的事情。这一命题意味着马克思在这里开始了一种本体论上的变革,那就是把人的活动、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视为对于人来说最为切近世界存在的方式。马克思接过了费尔巴哈的命题,认为人当然是对象性存在物,但却不是消极地存在于世,而是能动地与对象世界相互作用着的。但这种相互作用并不是人作为某种异于自然世界的超验之物而发生的,而是自然世界内部之事。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它“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5]167。从自然主义方面看,“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这是说,在这个东西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本身对于第三者说来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5]167-168。而从人道主义方面看,“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5]96。人的独特性便在于:“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97这就是说,在人的存在方式中,彻底化了的自然主义与彻底化了的人道主义不再矛盾,而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5]97。于是,在马克思看来,人正是通过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而参与到世界自身的生成性发展之中去的。这种对象性活动既是人的能动的活动,同时也是自然或世界自身通过人的活动的发展:“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5]167
马克思这一“对象性活动”的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其中的关键之处便是将现实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形态变化发展引入到“对象性活动”的内容中。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还是在一种普泛的意义上论及的,那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提出了一个考察对象性活动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必须“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6]54。这一方法论原则首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系统的体现,即运用这一方法描述了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以之对“人是什么”这一现代哲学的总问题作出现代唯物主义的回答。首先,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6]67其次,是对象性活动的社会结构方式:“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6]71再次,是对象性活动的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式:“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6]88最后,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取决于由生产力和分工发展所决定的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并据此描述了从部落所有制到古典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到现代的资产阶级所有制[6]68。
上述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即须把“对象、现实、感性”“把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必须“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6]77,从而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6]76。这也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的世界视域中,我们周围世界被视为纯粹客观的“对象”“物”等,并非如费尔巴哈眼中的那种纯粹的客观之物,而正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之结果,亦即人参与到其中之结果。如果我们把这种由于人的参与才能构成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一种“事”的存在方式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新哲学所体现出来的本体论便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哲学本体论传统的“事”的本体论。这种“事”的本体论,为何最终会为国人从诸多“西学”之中择选出来而衷心接受,这是需要我们予以深入探询的。
二、中国哲学“赞天地之化育”的“事”的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作为“西学”之一种传入中国,最终能够从众多“西学”中脱颖而出,获得主导性地位,毫无疑问与其能够切中中国社会之实际,从而能够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紧密相关。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众多“西学”中为中国思想所选择性地广泛接受,亦当在体现着深层思想结构的哲学层面,特别是在哲学之最基础性的本体论层面有其独特的为中国思想所中意的缘由。这缘由非他,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之“事”的本体论之间所具有的极为深刻的亲和性。
与西方哲学本体论之追问“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则是一种不离现实的人与其世界之关联互动的“事”的世界视域或“事”的本体论。杨国荣教授指出:“哲学层面关于心物、知行关系的讨论,其本源也基于‘事’,哲学上一些基本的问题讨论,都可以从‘事’中找到源头。这一意义上的‘事’,是中国哲学中的独特概念,在哲学上,似乎没有十分对应的西方概念。”[7]就此而言,若与西方古代及中世纪哲学之以超验的终极存在或最高存在为追问对象相较,这种“事”的本体论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对于中国传统的哲思而言,“人并非如笛卡尔所说,因‘思’而在(所谓我思故我在),而是因‘事’而在(我做故我在)。‘事’既包括做事,也涉及处事。做事首先与物打交道,处事则更多地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体上说,‘事’在人的存在过程中,具有本源性的意义”[7]。因此,与西方哲学相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与人相关的“事”这一概念便具有一种奠基性的意义。在中国思想中,所谓“事”,很大程度上是与“物”相对而言的。冯达文教授指出:“依《说文》释:‘事,职也,从史之省声’,‘史’则‘记事者也’。依此,‘事’固属具体的(殊相的),也具外在性(已显示出来,已对象化的),但毕竟与‘物’不同。‘事’作为一‘职’,是人干的,与人的活动与行为相关的。”[8]故而,“‘事’可以理解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9]。总之,“事”的本体论意味着中国哲学的世界视域必然是与人及其活动相关的存在,这一视域同西方哲学须是“无人身”的“理性”才能把握的抽象的存在物的世界视域显然是极不相同的。
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事”的本体论之思想,初次在《易传》中得到了明确表达:“《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易传·系辞下》)而“易”之书也被解释为圣者悟道之作:“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易传·说卦》)这一对人在天地之间作用的强调,在《中庸》中则有着更为突出的表达:“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22章)这一以“人道”而“赞”“参”天地之道的“三才之道”,便是周汝昌先生所盛赞不已的“三才主义”:“人是天地的一个精灵的凝结的代表”,“因此,人参天地,共为三才——这是中华文化思想的一大总纲”[10]。
《易传》与《中庸》中的“三才之道”的论述虽然极为简略,但却是一个极富创生性的理论纲领,蕴含着极其广阔的发挥空间。而要将之构成一个本体论体系,尚需创造性发挥,将其内蕴的至大之“道”充分展现出来。而这个“道”的关键之处,乃在于作为天地之生物亦即有限存在物的“人”是如何“赞”“参”于天地之化育的。所谓“赞”“参”者,一方面意味着人虽作为天地之生物而能够“赞”“参”天地之化育,但却也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通过“赞”而“参”于天地,而达到人与天地之间的一种新的统一性。如果说人作为天地之生物,乃是被动地从属性地统一于天地,是一种消极的统一性,那么,通过“赞”而“参”于天地,便在某种意义上乃是能动地达致一种积极意义上的统一性。这是说,人与天地之间乃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即从作为原初的天地生物而消极地从属于天地的统一关系,进而通过这种人对于天地的“赞”“参”之行动,达成一种至少在有限积极意义上的统一关系,并由之而推动世界之变化发展。因此,对这一至大之“道”阐释发挥的关键,便在于如何描绘人与天地之统一性,亦即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以何种方式达成。更具体地说,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这一至大至极的“三才之道”发挥发展的关键,便在于如何描绘人与天地之关系结构,或者用学术史上更为通常的说法,在于如何描绘这一“天人相与之际”的关系结构,特别是“天人合一”的实现方式。(1)人们通常将“三才之道”与“天人合一”等同视之,但亦有论者持不同见解,认为“把儒家的基本思想总结为‘天人合一’,特别是把‘天人合一’的来源归结于《易经》的说法并不准确,是一种误导。《易经》的‘天、地、人’三才思想较之于‘天人合一’更为符合儒家思想的本旨”。参见李晨阳:《是“天人合一”还是“天、地、人”三才——兼论儒家环境哲学的基本构架》,《周易研究》2014年第5期。据此,中国传统哲学之发展变迁,便亦可看作是对于这一问题描绘或解决方式的发展变化的历史。
“所谓‘天人相与之际’,实际上就是关于人与天如何统一的问题。从哲学讲,这就是如何将人的自觉、自愿的应然性与天运行的必然性和强制性和超越性力量统一起来。”[11]33以康中乾教授之见,“两汉哲学明确提出了‘天人之际’的问题,将先秦哲学中所孕育的本体论问题明确地展露在了天与人合一的形式上”[11]33。但汉代以“董仲舒的目的论和王充的自然论”为典范的“两个极端”,前者“实际上是把人所具有的目的性、意志性转移到了人之外的‘天’身上”,而后者则“解掉了人的目的性和意志性;同时,这就把一切都导回到了人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的自然存在。所以,尽管董仲舒的目的论和王充的自然论在哲学形式上都有‘天人合一’的本体论意味,但都未能完成这个‘天人合一’的真‘合’”[11]34。而郭象作为魏晋玄学的整合者,虽然建构了一个作为宇宙本体论的“独化”论,但“在这种宇宙本体论中,人像别的存在物一样只是一个存在者而已……这里还未明确为人的存在建立一个本体论”,因而这种“宇宙本体论还不是真正‘天人合一’式的形而上学、本体论”[11]34。而从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到禅宗,隋唐佛学则建立起了一个心性本体论[11]36-39。这样,“在汉代关于天人问题的宇宙发生论的形式和开端下,魏晋玄学完成了宇宙本体论的建构,隋唐佛学完成了心性本体论的建构。前者是对天的存在本性的揭示,后者是对人的存在本性的揭示。有了对天、人存在本性的揭示,即有了关于宇宙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的建立后,现在就逻辑的有可能和需要将这两种本体整合、统一起来而建构一个完整形态的和完全意义的本体论,这就是……宋明理学的哲学任务”[11]39-40。
理学之为理学,“理”自然便是其核心范畴:“理者,实也,本也。”[12]125正是通过这个“理”范畴,理学实现了宇宙本体论与心性本体论的统一,亦即达成了“天人合一”之理论建构。在理学家那里,不再偏废于“天”或“心”,而是以“生生”之“理”,将“天、地、人”看作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将人之存在纳入到天人一体的“理”之运行之中。“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12]29。在这样一个生命有机体之中,“人”便既不是独立于“天”之外的“主体”,亦非单纯地从属于“天”的消极存在物,而承担着自身的“赞”“参”天地化育之使命。对于这一“赞天地之化育”的“赞”字,朱熹对之作了这样的发挥性阐释:“盖天只是动,地只是静,到得人,便兼动静,是妙于天地处。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论人之形,虽只是器,言其运用处却是道理。”[13]这一阐释径直将人视为“天地之心”,对于人在天地间位置的定位,不可谓不高。人与天地相较,高就高在人能为天地所不能为之事,或者说,人之能在于他能将天地之间本不存在之事物创造出来,将世界之存在推向新的形态。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人亦有天地所不能者:“‘赞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间,虽只是一理,然天人所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种必用人;水能润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辅相,须是人做,非赞助而何?”[14]1570但这一“三才主义”并非只是强调人之能为天地所不能者,而是认为“天是一个大底人,人便是一个小底天”[14]1426。或者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凡语言动作视听,皆天也”[15]。在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16]这样一种天人一体而又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在张载“民胞物与”说中得到最为充沛的表达:“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7]62王新春教授评论说,这是“基于性命的大宇宙亲缘之视域,张载进一步解读出了一部活生生的宇宙大家庭之《易》”[18]10。既然天地间的人与人、万事万物都构成了一个“宇宙大家庭”,而一个“家”乃是父母子女皆不可少的“吉祥三宝”,那么,人与天地万物便是一体的,天地间的万物便不可能是抽象的纯客观存在,而必定是与人相关的“事”。所谓“天人合一”便不是说将原本相分的人与天合在一起,而是意识到天、地、人原本就是一个“宇宙大家庭”或者说“生命共同体”,从而以“报本反始情怀”对之“敬畏感恩珍视善待”[18]12、13。因此,“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17]65。可以说,“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最终建构,它是对由先秦摊出的、将天与人统一起来以建立哲学本体论这一理论任务的最终回应和完成”[11]40。
三、“人是对象性活动”与“赞天地之化育”之比较
我们前面概要地描述了马克思的“人是对象性活动”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赞天地之化育”的“事”的本体论,可以说,这一描述已经总括地展现了两种本体论之同与异,但就我们的目的在于探讨两种本体论汇通何以可能之问题而言,这一展现还过于笼统,且更多地是展现了两种本体论之同。汇通的目的乃是思想之“生生”,故汇通得以可能之前提固然是某种意义的“同”,即无“同”不可“通”,但无“异”则本为同一,则亦无汇通之可能与必要,不足以展现中国哲学精神的“生生”之德。因此,必须进一步在本质性层面上通过比较而规定两种本体论的差异,方可能具体规定这一汇通之“同”何以可能的问题。
要比较两者之“异”,首先须有一个使得比较得以可能的共同的参照系或参照平面,否则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是无法比较的。这里遇到的问题首先便是学界讨论已久的关于中西哲学中的“本体”及“本体论”范畴是否处于同一思想层面,从而是否具有进行比较所需的共同参照平面的问题。虽然在直观上“对象性活动”与“赞天地之化育”两个命题有着极为明显的相似性,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属于西方哲学之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并无实质意义上的交集,(2)那种将中国传统哲学说成是马克思哲学之来源以说明其间亲和性的论说,似太过玄幻,难以让人认真对待。因而要进行两种本体论的比较,首先还须说明这一比较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
若就中西两种哲学中“本体”之意谓的普遍性而言,诚如邓晓芒教授所指出的,是处于不同层面的,(3)邓晓芒教授在论及关于中西哲学中“本体”这类概念的意义之别时写道:“从这些概念和范畴在两大文化中各自都代表最大普遍性这点来看,这种翻译的确是对等的;但从它们各自的形成方式来说,却具有层次上的不可比性,就是说,希腊文on、英文的Being和德文的Sein等等所表达的意思首先就借助于语言形式而超出了日常经验事物,它们的普遍性不是在一切经验事物中所现成包含着的无所不在的普遍性,而是需要在语言中说出来的普遍性。所以在西方形而上学中,凡是不具有语言中的普遍性的都不是真正的普遍性……而语言中的普遍性也不是某个具有实在意义(所指)的实词的普遍性,而是代表语言行为本身的那个系词‘是’的普遍性。”参见邓晓芒:《论中西本体论的差异》,《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因而是不可比较的;但若就两种哲学中的“本体”是如黄裕生教授所说的都意指某种“绝对原则”的,(4)黄裕生教授认为:“‘哲学’就是一门探求本源与确立绝对原则的学问,它的使命或任务就是为人类生活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而使人类过智慧的生活。就我们这样所理解的‘哲学’而言,在中国古典文化里,当然有哲学……在众多古老民族中,实际上只有四个古老民族有真正的哲学:这就是古希腊民族、汉民族和印度民族、犹太民族。后两个民族的哲学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古希腊民族与汉民族的哲学是独立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只有中国人和希腊人是单独靠哲学思想来为生活确立理由,为世界确立根基,因而,靠哲学而在天地之间站立起来。”参见黄裕生:《什么是哲学与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则又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因而也就应当是可比较的。而且这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人是对象性活动”的命题,正是从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上来构建其本体论的,这里的作为“绝对原则”的“本体”便并非那种超越于一切经验的普遍性,而正是一种人类生活世界之中的普遍性,其本体论所描述的亦正是一种人与其世界互动关系所构成的人类世界的本体论。因此,即便中西“本体论”是处于不同层面的,但至少就马克思哲学而言,其本体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之“事”的本体论是全然出于同一层面的,因而也就是能够对之进行深度比较并进而探讨其间之异同以及综合创新之可能的。
从上面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的概要描述可以看出,两者虽然从根本上说同为关于人类世界的本体论,即都持有一种将人对于天地之“赞”“参”或人与其世界的互动视为首要之存在的“事”的世界视域,但两者对于“事”的构成的规定却有着重要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涉及中西两种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传承性影响,更重要的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时代主导的哲学精神,必定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匹配的,亦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存在方式必然会有与之相应的哲学精神。这当然不是说哲学的精神生产或创造是为社会存在方式所机械地决定了的,而是说,尽管精神生产是能够自由地进行的,即人们可以任意地创造出其思想观念,但最终哪种哲学观念能成为一个时代主导性的精神,却是为社会存在方式所决定的,即那些能够成为主导性的哲学观念必定是与一个时代主导性的社会存在方式相适应、相匹配的,从而为该时代的社会存在方式所选择作为其精神表达的。
前面我们概述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从发生之时的人之“赞”“参”天地之化育,到汉代魏晋之偏向“天”之宇宙本体论,隋唐之时发展起了心性本体论,再到宋代方复又全面回归“三才主义”之本体论的思想历程。那么,何以会如此变化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易传》《中庸》成书的战国时期,正是传统宗法社会秩序解体、新的社会建构正在酝酿的社会大变动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无疑是需要思想创新的时代,活跃于此时的自然便是那些适应于大变动时代的对于人之能动的创造性给予弘扬的思想。因此,这一时期才会产生强调人对于天地之“参”“赞”的“三才主义”。而随着汉帝国之建立,不仅对于社会秩序的需求成为主导性的,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宗法贵族制解体之后,汉代又逐渐发展起了一种新的贵族制,并于魏晋时期达至极致。这样一种社会存在结构的社会秩序整合方式所需要的便是一种“人”从属于“天”的意识形态,于是,汉代哲学本体论在天人关系中自然便转向了对于“天”的强调。而于中唐开始的“唐宋变革”,其本质在于门阀世族社会结构的彻底解体,中国社会至宋代成为高度中央集权下的高度平民化的社会,这意味着,这一社会结构中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的解放或自主性的增强,从而社会整合以形成社会秩序的方式亦随之变化。这便是适应个体自主性之变化,社会整合需要个体更多地自律或自觉履行。这一点可从宋儒将《大学》章首之“亲爱于民”的“亲民”一词改为“新民”,强调“每个人的身上都内在地具有‘明德’,具有天命所赋予的‘仁义礼智之性’,这使得每个人不论贵贱贫富,都有被觉悟的可能,也就是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尽管每个个人事实上由于其气禀的差异,并不现实地就是圣人”[19]而见出。这便是宋明理学之回归原始儒家,重新强调人对于天地之“赞”“参”的“三才主义”的社会存在根由。因此,宋明理学中对于人之“赞”“参”的说明,虽然也有提及日常生活以及生产活动,但更多地是从适应良好社会秩序之形成的伦理道德方面着眼的。
马克思哲学之“人是对象性活动”本体论的建立,则是处在一种全然不同的社会存在条件之下,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生产方式并获得较大发展之条件下,因而其之“事”便必定有着十分不同的内涵。西方封建贵族制社会之解体,虽然大致上亦发生于比“唐宋变革”稍晚时期,但与中国只发生了门阀世族贵族制的解体不同,西方社会在封建贵族制解体不久后,由于种种因缘际会在英国率先发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后果。首先,从社会结构的存在方式上看,从一种“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转变为了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20],这意味着社会整合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次,资本主义意味着能动地改变自然世界的工业生产取代顺应自然的农业生产成为主导性的生产方式,从而使得在古代世界被视为低贱的人类活动方式的创制或物质生产活动成为最主要的人类实践活动。再次,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所推动的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看世界的方式,其特点是从伽利略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开始的全新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是一种符号理性主义。它是笛卡尔区分‘心灵’和‘外部世界’的真正结果。它真实地表达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悖论,即据信足以理解这个世界的心灵被预先设想为与这个世界相疏离。我们并非直接接近这个世界,而是通过概念(它们是对抽象的抽象)来接近,与此同时,我们把概念解释为与世界直接相接触”[2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巨大变化,便是马克思时代的“事”的世界。而马克思建构其“人是对象性活动”本体论便必须面对这个世界,即将具有这些前所未有的存在方式的世界把握在其哲学思想之中。
马克思把握这个世界的方式,首要的一点,便是如前所指出的那样,就是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必须“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6]54。而这个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实践”,首先便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6]78-79。对于现代世界具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在马克思之先和之后的哲学家那里无疑是有所关注并在各自的体系中赋予其以重要意义,前者如黑格尔,后者如海德格尔。黑格尔给予生产劳动特别是工具性活动以高度评价,但归根到底生产劳动只是其绝对精神发展之一个环节,因而只是一种如马克思所批评的“精神劳动”。海德格尔虽然颇为深刻地将改变世界的技术活动视为现代科学之本质,但他却只是将其视为现代世界之存在的遗忘方式。因此,就真正的哲学是为时代精神之精华而言,唯有马克思将物质生产劳动视为“第一个历史活动”方是真正把握住了现代世界之精神。其次,基于物质生产劳动之为“第一个历史活动”之原理,马克思将“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或“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视为社会的“现实基础”,而将“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视之为“竖立其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亦即“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2]。再次,马克思将现代科学视为思维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构造,(5)关于作为科学对象的“具体总体”之为思维抽象构造的产物,马克思写道:“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并以其《资本论》研究展现了这一科学对象构造的唯物主义辩证方法,特别是在《资本论》第1卷的《商品和货币》篇中对于如何通过对于劳动二重性的分析,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现实主体行动的逻辑建构起关于商品生产的客观结构的逻辑,同时也就揭示了人们现实的商品生产活动如何转变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6)马克思关于这一“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写道:“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89页。亦即由主体行动所关涉的关系性的“事”转变成单纯客观的“物”的方式。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看到,两种哲学虽同为关于人类世界的本体论,但在本质性层面则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那么,这些根本性的差异能否通过两种本体论汇通而成为中国哲学精神在新时代“生生”之动力或助力,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四、两种本体论的汇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的本体论之建构
前面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事”的本体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的概述,已展现出两种本体论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启示我们,能够从“事”本体论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即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亦理解为一种“事”的本体论。如前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人是对象性活动”,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以“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72等命题加以发挥发展的命题,可视之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23]。而说“人是对象性活动”,即是说人是参与到周围世界之中去的,人的存在方式便是与周围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互创造,亦即“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92。如果我们对比于前述中国哲学之“三才主义”的“事”的本体论,简直就如同是说,人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吗!前面我们曾推测性地指出,如果我们把这种由于人的参与才能构成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一种“事”的存在方式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新哲学所体现出来的本体论便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哲学本体论传统的“事”的本体论。至此,我们则可以确定地说,马克思的哲学亦可理解为一种“事”的本体论。当然,反过来说,如前文曾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人是对象性活动”之思想乃是对于康德之人类学哲学之改造发展,即马克思哲学乃是一种现代的人类学本体论,那么,与之具有亲和性的中国传统哲学便亦可以说是一种古代的人类学本体论。如果马克思哲学亦是一种“事”的本体论,而中国传统哲学亦是某种意义上的人类学本体论,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亲和性,那么,这种深刻意义的“同”便不仅说明了何以中国哲学精神在诸多“西学”中选择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同”亦构成了两种其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的本体论通过汇通而重建中国哲学“事”的本体论之基本前提。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汇通之目的是重建中国哲学“事”的本体论。所谓“重建”便是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之“事”的本体论乃是适应于传统社会之哲学本体论,而需在当代条件下予以重建,以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相匹配。但既然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现代哲学,而两种本体论汇通以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之内容,从根本上说便是“存同纳异”,即保持两种本体论之“同”,并以之为基础而吸纳马克思哲学中体现着现代社会之精神的“异”,从而实现中国哲学之现代“生生”。具体说来,就是站在当代中国精神的立场上,回答“人是什么”这一人类学哲学的根本问题。
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三个分支问题的顺序是:(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作什么?(3)我可以期待什么?这一顺序乃是基于其认识论立场的提法。但如果从“三才主义”的“事”的本体论或人类学本体论出发,认为人乃是可以“对象性活动”之方式“赞”“参”于天地的存在物,因而是一种开放性的存在,即不是被某种外在的力量预先规定成为某种存在的,而是自己能够成为自己所欲成为的存在的,那么,这一“人是什么”的问题,首先要追问的便当是“人能够成为什么?”亦即“我可以期待什么”之问题。这一问题便是人之价值理想是什么之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的回答乃是“自由王国”之中所有人的自由发展,而中国传统哲学的回答则可以张载的“民胞物与”为典范代表。初看上去,这两种回答几乎毫无关联,但若看两种回答所针对的问题,便不难见出两者的相通之处。“人的自由发展”所针对的乃是以往社会中人的发展受到种种严重限制的“异化”状态,其目标是使人的发展不再受到“异化”的社会力量的束缚。“民胞物与”所针对的亦是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物的间隔状态,这种间隔亦是一种束缚,人处于其中感受到异己力量之压抑,而“民胞物与”之状态则是解除了这种束缚、压抑,使人感受到本心自适之状态。就两者都是意指解除异己力量束缚而言,其内涵是类同的。因此,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便可以“民胞物与”来解读“自由王国”之人的自由发展。事实上,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已经作了中国式的解读,如将之解读为“大同世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等。
从人类学本体论或“事”的本体论来看,价值理想作为对“我可以期待什么”问题之回答,实质上乃是给回答“我应当作什么”问题提供一个理想性的准则。在这一问题上,“人的自由发展”与“民胞物与”之理想,都是作为终极价值准则而对于回答“我应当作什么”问题之前提性奠基。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这种价值理想在某种意义上是超时空的,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且一般只限于伦理道德方面。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将“自由王国”之理想放置在为物质生产方式所限定的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上,即“自由王国”作为终极理想若要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中,还须据之而具体化。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便把共产主义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而划分的一个基本标准则是“生产力的增长”所带来的“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第一阶段中,基本的主导性价值原则便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只有到高级阶段,方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对于“我应当作什么”的回答中包含着“各尽所能”以促进“生产力的增长”这一方面的“应当”,亦即包含着以物质生产劳动或技术实践改变世界以使之合于价值理想方面的“应当”。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比之中国传统哲学的回答更具现实性,因此当将之吸收进来,将“民胞物与”之价值理想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现实化。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三世”说,当可将之加以改进,赋予其具体历史内容,以将终极价值理想具体化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回答“我应当作什么”的价值原则。
而“我能知道什么”之问题,在马克思“人是对象性活动”的“事”的本体论视域中,则是一个从属于改变世界的技术实践的问题。这是因为在马克思哲学中,作为人类认识之典范的现代科学乃是对于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一种抽象建构,因而它在生活实践中有其根由。这也就是说,自伽利略以来的现代科学所追求的客观性实乃一种抽象的建构,而非通常所理解的是对自然世界纯粹客观的直观或反映。对于这一问题,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关于现代科学与生活世界或“在世”之关联的有关论述,亦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深刻与超前。(7)胡塞尔晚年也在其“生活世界”理论中对近代科学的本质进行了一种重建,认为“生活世界是原始明见性的一个领域”,而科学作为一种客体化,“是方法论的事情,并且是奠基于前科学的经验被给予性之中的”;亦即科学所理解的自然,并非直接直观的世界,而是对这一原始基础的观念化,是其“观念的构造物”,但近代哲学却误解了科学的这一实质,将这一“观念的构造物”视为唯一真实的自然。参见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239页,第256、265页。海德格尔亦认为,“认识是作为在世的此在的一种样式,认识在在世这种存在建构中有其存在者层次上的根苗”,这样“也就取消了纯直观的优先地位。这种纯直观在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同现成的东西在传统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相适应。‘直观’和‘思维’是领会的两种远离源头的衍生物”。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版,第75、180页。在如何理解现代科学对象的客观性这一方面的问题上,处于前现代科学时代的中国传统哲学自然是欠缺的,因而须将马克思的观念吸纳进中国哲学之“事”的本体论中来,使之能够在现代科学条件下合理地回应“我能够认识什么”这一问题。
至此,通过对马克思哲学的“人是对象性活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赞天地之化育”的“同”与“异”的分析,勘察了两者之间汇通与交互吸纳的可能性,提出了一种对于现代哲学之“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式的回答,初步建构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事”的本体论框架。就这一“事”的本体论存在的可能性之广阔而言,毫无疑问,这里所揭示出来的还只是一个极为粗糙的轮廓性框架,但正因此,这个简单的框架却也蕴含着能够进一步发展充实自身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生”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