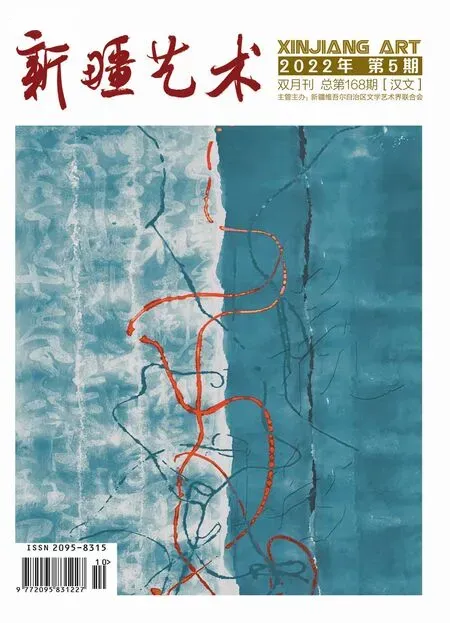新疆库车“赛乃姆”个案研究与话语形式
2022-12-17吴晓璇
□ 吴晓璇

库车赛乃姆
新时代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科学化和多元化,促进了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效保护和发展。随着时代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库车赛乃姆作为民间舞蹈、民俗仪式、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与传承,与当代舞蹈的身体、话语形式与文化背景、哲学思想紧密相连。研究者可以从其呈现的文化入手,找准其文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通过舞蹈认识文化,促进该文化的和谐发展和有效保护。
“赛乃姆”流传于天山南北,是维吾尔族集歌、舞、乐、诗为一体的民间艺术形式。这种表演方式与中国古代乐舞一体的表演形式极其相近,不仅舞姿优美动人,人们通过这种乐舞抒发情感和思想,其蕴含的文化也得到了传承与发展。“赛乃姆”原是乐曲与节奏的名称,清代《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十》“乐伎附”中记载:“携诸乐器进,奏斯纳满(赛乃姆)、色勒喀斯、察罕、珠鲁诸乐曲,以为舞节。次起舞,司舞二人,舞盘二人……次呈杂技”。“赛乃姆”还是节日庆典、民间集会、麦西热甫及一般欢聚时刻的自娱性舞蹈形式。“赛乃姆”除了是歌曲舞曲名字之外,还有“每个人心目中美丽的女子”和“美丽的偶像”之意。在生活中歌舞艺术是对美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综合艺术,歌舞通过具体的事物来展示或表现生命的有机形式。通俗地说,“赛乃姆”是维吾尔族民间舞蹈的统称,现如今的维吾尔族舞蹈无论是舞台表演、舞蹈教学还是与群众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广场舞,大部分动作元素和风格表演都归属于“赛乃姆”。研究其内在价值和风格对于当下艺术实践和民间传承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维吾尔族赛乃姆
库车赛乃姆,顾名思义是库车地区的“赛乃姆”是维吾尔族民间舞蹈支系之一,它不仅包含了赛乃姆音乐和舞蹈的表演方式,而且还蕴含着库车地区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由于库车位于天山南麓中部,塔里木盆地北缘,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要塞之地,因此,各地文化在此不断交融、碰撞、发展,从而造就了库车赛乃姆兼具喀什赛乃姆(西部赛乃姆)端庄大气的气质和喀群赛乃姆(山区赛乃姆)高傲挺拔的姿态,又温婉端庄。库车赛乃姆除了充分吸收了南疆其他地区赛乃姆的特色之外,保持自身已有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库车赛乃姆独有的“靠肩对舞”动作和温婉端庄的舞蹈风格被视为库车特色。在新疆赛乃姆表演形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库车赛乃姆的话语形式
库车赛乃姆非常注重肢体对话,形成一种独特的“双人对舞”方式,这与当地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密不可分。这里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塞,也是龟兹乐舞的发源地。历史上东、西方文化在此形成了库车赛乃姆大气包容、舒缓厚重的舞蹈风格。如今,库车县依靠农牧业、石油工业为主要产业,人们通过农业劳作、工业劳作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新的情感,这些都融入到民间舞蹈之中。亚里士多德曾宣称:“一切人类知识都源于人类本性的一种基本倾向,这种倾向就表现在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和反应之中。人类感官生活的整个范围都受制于这一倾向,并充分体现这一倾向。”恩斯特·卡西尔教授在《人论》中也强调:“人的显著特质,他的辨识标志,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或生理本性,而是他的劳作(Work)。正是他的劳作,人类各种活动的体系,定义并决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都是这个圆周组成部分。”库车地区主要依赖于农耕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其独特的人文环境。
当人们舞动库车赛乃姆时,成双成对的人们面对面,在彼此舞动的过程中产生跳、转等舞蹈动作元素,形成“双人对舞”的固定形式,这种形式在类似秧歌、花灯等中国民间舞蹈表演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形成“双人对舞”的因素在于民间活动的本质是重视每个人的参与感,民间舞蹈的宗旨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融入到活动之中抒发自己的情感和感受,并得到他人的情感回应,这就形成了赛乃姆的对话方式。无论男女老少,在舞蹈参与过程中多以即兴表演为主,人们在舞蹈时能力有强弱之差,所以每一次的活动也是人们学习和提升舞蹈技艺的一次机会。大多数民间舞蹈都伴有即兴表演,他们存在一些惯有动作或者是代表性动作,但整体表演布局并没有完整的套路或者设计,仅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贯穿始终。不管是传承人还是普通百姓的表演,其舞蹈动作都来源于自己对赛乃姆的认知与理解,他们用自己认为优美、华丽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库车赛乃姆以“男女两人对舞”的即兴表演形式为主,这体现了人们运用肢体艺术交流的方式,它也是民间文化沟通过程中双人舞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乐舞表演中通常会存在“程式表演”和“即兴表演”两个模块,对于这两种模块,民族民间舞蹈的“即兴性”是在“程式表演”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即兴性”是在一个大的环境下存在的,“即兴性”讲究的是在大环境之中鼓励个性,每个人不同的情感和表现可以展现出现不同的舞蹈风格,这也体现了民族民间舞蹈的生命力量。
库车赛乃姆的“程式表演”亮点是“靠肩对舞”动作。从与其他地区赛乃姆的对比中发现,唯有库车赛乃姆在对舞时运用靠肩这个动作,而为什么选择这一动作,当地的传承人是这样解释的,自己学习时就是这样跳的,他们认为这是本地特色,在传承过程中强调了这一动作。丹纳说过:“艺术的目的是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表现事物的某个凸出而显著的属性,某个重要观点,某种主要状态”。显然,这种“靠肩对舞”动作即是库车赛乃姆的主要特征,它反映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人民情感的互通和人人平等的理念。肩部处于身体中较高的位置,在中华文化中其涵义有所延伸,如“比肩”“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男女对舞的过程中,靠着肩膀对舞动作,一则充分展现了人们之间沟通过程的亲昵与自然。其二,在乡村文化中还存有一定的男尊女卑意识,库车赛乃姆舞蹈中男女的“靠肩”动作或许也是在展现男女平等的社会意识,体现对女性的尊崇。库车赛乃姆提升了女性的舞蹈表演地位,推崇女性在歌舞过程中尽情地展现自己、表现自己,塑造了自信、端庄的女性形象。
二、赛乃姆对话模式——身体与情感的对话
(一)赛乃姆舞蹈的身体语言对话
语言学通常将“对话”理解为强调双方的互动及交流,将“对话”解释为“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谈话、接触或会谈。”库车赛乃姆对舞的形式犹如对话,如果是长辈和晚辈之间一起对舞,就是一种更贴切舞蹈传承的“对话表演模式”“对话教学模式”“对话欣赏模式”,其促进了民间舞蹈的教学与发展。库车赛乃姆对舞的形式,一般贯穿歌曲演奏的整个过程,人们先从各自的位置中走到舞伴面前,行礼之后开始舞动,直到歌曲结束,两人再次鞠躬行礼,结束舞蹈。这一过程中,舞者与舞者之间产生了“我——你”之间的对话关系,造就了二者之间的表演模式,而这一关系构成了人类关系的本质,即“我——你”共同参与、互相影响、互相造就,使对方的存在成为自我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民间舞蹈交流的言语部分,是舞蹈的内在结构部分,这种对话是固定的,是规范性的,是共时性的产物。
对于身体的认识,刘青弋教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世界观即身体。身体动作语言形式的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并非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表象’。并不仅仅是“形象”和“名称”那么简单,理论研究需要深入“形象”乃至“本质”的关系链条之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以此推动事物的发展。“教育家弗朗西斯·德尔萨特所建立的‘表情体系’,通过长期观察人的动作,发现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动作具有某种紧密的对应性,即人体的动作、姿势与人内心欲望密切相关。”正是因为德尔萨特教授发现的“表情体系”,让我们对于身体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身体反应出人们的情感时,我们也会再进一步思考除了情感,身体还可以表现什么?或者身体语言之中还蕴含着什么?
从身体语言层面看,库车赛乃姆的身体语言是属于端庄、内敛的舞蹈风格;是双人对舞,群舞或者圈舞的表现方式;在表现过程中有平稳、欢快的节奏变化和情绪互动。在丰富的舞蹈表现过程中,我们可以感悟其中的文化内涵。正如诺贝特·埃利亚斯教授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及的“身体的个性化、理性化和社会化过程,这种视角对物质文化或‘技术化’角色也非常敏感。我们更关注身体文明一系列过程,涵盖了一个社会中内部安定的程度;习俗精致化的程度;社会关系中自我约束与反身性的程度。”刘青弋教授也提出:“舞蹈学研究应始终将舞蹈艺术现象视为社会文化现象,将其放置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中进行研究,从而使舞蹈学研究既是艺术学的舞蹈学,也是生物学的舞蹈学,又是社会学的舞蹈学。”

库车民间艺人在进行赛乃姆演奏前的准备
(二)赛乃姆舞蹈的情感对话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艺术领域中的情感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艺术交流情感范式也在逐步确立。根据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自我不仅是个体自我更是对话自我。艺术交流的情感对话离不开对话者之间的身份确认,“身份是社会性的,即个体是对话的自我(Dialogical Self),多声音的自我中有着他者的位置,与他者的对话在自我身份的构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身份不是个体的内在特征,是在社会实践中构建起来的持续过程,身份在人际互动中不断协商从而浮现,在实践语境下与他者的对话中得以实现。”
赛乃姆舞蹈语境之中,通常存在两种双人对话模式,一种是固定的双人对话模式,一种是集体圈舞之中舞者随机与其他人建立双人舞蹈关系的对话模式。根据两种不同的对话模式,我们也能看到不同对话中自我的表现。例如,在固定双人舞蹈对话语境之中,自我的表现相对自然、轻松,甚至会有人依据对话时对方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回复”动作。而在集体圈舞的对话模式中,由于大家都是圈舞,只有随机的一对或者两对出来对舞,在这种被凸显的情况下,对话者情绪更加兴奋,情感更加丰富,舞蹈肢体语言更有张力,舞者内心非常强烈地想要表现自己,引起更多的观众或者舞者的关注。

库车民间艺人表演维吾尔族顶碗舞
其次,库车赛乃姆舞蹈的表演,必然有观众观看,这又形成了另一层面的对话模式,可称之为“表演对话模式”。无论是传承人还是普通人民群众,每一位舞者在表演过程中都存在和舞伴的表演对话模式,和观众的对话表演模式。舞伴是“我——你”之间的对话者,故每一个动作、体态、韵律都存在表演的成分,让“你”观看,让“你”接收舞蹈讯息并予以反馈。同时,每一个舞者也在与观众对话,让观众观看到自己的舞蹈动作,让观众有自己接收舞蹈讯息的过程。表演对话模式中也产生了演员与观众之间双向的情感交流,形成了艺术共鸣。
三、赛乃姆对话模式——历史与文化的对话
库车赛乃姆的传承教学是在每一次的活动之中潜移默化完成的,这就是民间舞蹈的魅力所在,它更多地是在实践中让人们获得属于自己话语特色的舞蹈。在“对舞”中往往也有老少搭配的二人组合,这种组合是一种老艺人传帮带年轻人的传承方式。表演时年轻人能够迅速捕捉到老艺人简单、内敛、厚重的动作,但对动作背后的含义了解甚少,教学过程重复而漫长,当年轻人一次次地观看、模仿、展现、再观看、再模仿、再展现之后,就会有所反思和提升,从而获得具有价值的文化讯息。

库车当地民间艺人表演的“靠肩对舞”
赛乃姆语言符号的不变性与永恒性,取决于语言学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当我们在学习和传承民间舞蹈时,其实并不会思考太多的信息问题,而是会自然而然地接受和发扬。在此之后,思考和完善才变得重要起来。
四、赛乃姆对话模式——心理与审美的对话
赛乃姆对话模式中包含了对话心理的成分,主要包括表演者们心理接受、心理输出和观众对话欣赏等方面。“对话心理接受”和“对话心理输出”都是舞者或是表演者的内心感受,其实可以简单理解成两人对话过程之中的“你来我往”。对舞时,无论哪一方都在传递信息和接受信息,这些信息不仅仅是表演情绪,也是一种具有舞蹈文化展示的心理话语。巴赫金认为交往与对话之中“时刻存在着主体、文化、语言、文本、话语、表述、理解等。”在赛乃姆舞蹈过程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双人舞者之间的问答、肯定与否定、保留与发挥,这就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舞蹈对话模式。
看似简单的一个“靠肩”动作,拉近了双人舞蹈的表演空间,从空间学角度来看,可以将库车赛乃姆舞蹈分为现实空间、舞蹈空间和心理空间。现实空间承载人物的行为,是舞蹈空间的一种现实状态。构成于人物的行为之“做”,也承载着人的行为之“做”。现实空间中库车赛乃姆主要流传于民间场域,在广场、或者家庭院落之内,双人舞中无论哪一方先侧身把肩部交给对方,另一方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一侧肩部贴合上去。有意思的是,靠肩动作都是以自身左边肩部去贴合对方的左边肩部,这是库车赛乃姆独有的。心理空间则承载着表演者的内在经验,是舞蹈空间的一种心理状态。当“靠肩对舞”发生时,表演者或者参与者的心理空间存在两个感官,一个是自我的感官激动、高兴,另一个是对他者的情绪和整个活动氛围的感官。这里的心理空间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延的,展现了民间舞蹈娱乐性与表演性高度融合的状态。

维吾尔族赛乃姆
“对话欣赏模式”则是来源于观众,虽然脱离了“对舞”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建立了第二种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这种对话模式看似是单线模式实质上是双线交流,看似是表演者向观众传递舞蹈讯息和舞蹈情感,实质上观众在获取讯息的同时也在传递自己的讯息,在观看舞蹈的过程之中观众总会受到感染,其必然会传递出自己的感受,哪怕是一个掌声都是有力地“对话欣赏模式”的双线交流。
结语:交融中的传统文化
当库车赛乃姆形成一种对话语境之后,舞蹈本身的意义就被提取出来,那就是“文化的传统与交融”。一旦我们在舞蹈的交流过程中达成共识,舞蹈肢体的动作就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变成一种在共识的基础上,不断被赋予个人的创造力、理解力和传播力的舞蹈肢体语汇,从而完成文化融合。李泽厚先生在谈及原始文化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萌芽时期时指出:“原始艺术的符号图像化知识观念亦是物态化活动的符号和标记。但是凝聚着这种符号形式里的社会意识、情感和心理,恰恰使这些图像形式获得了超模拟的内涵和意义,使人们对它的感受取得了超感觉的性能和价值,也就是自然形式里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感性自然中积淀了人的理性性质。”传统舞蹈中的文化组成是一体多元的,在多种因素的发生、发展、融合之中,建立自身的文化风格。而在传承中如何保持、发展?这是当代舞蹈发展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当代艺术从业者仍需克服用单一思维和视角看待传统舞蹈形式,应该从多元文化中寻找答案和内涵,同时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营养,促使传统舞蹈文化的保存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