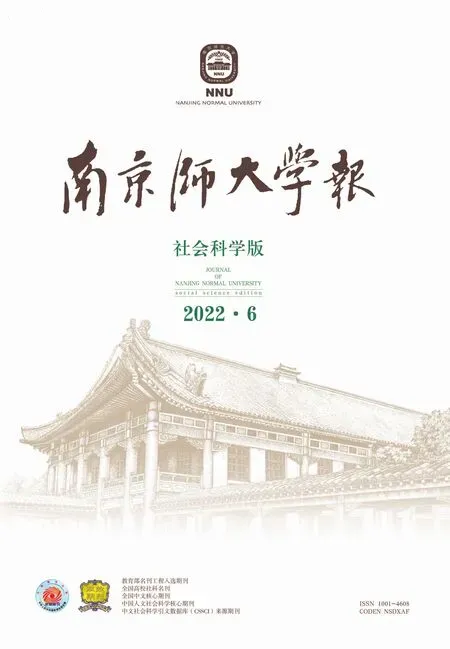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新尺度、新挑战与新方向
2022-12-17李鹏
李 鹏
引 言
产教关系是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探索最优的产教关系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职业教育产教关系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中会有不同的职业教育产教关系。(1)田志磊、李俊、朱俊:《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治理之道》,《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年第15期。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产教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因为工业革命不仅仅是技术的革命,也是产业模式的革命(2)唐世平、赵俊杰:《产业模式的新革命:视窗英特尔主义和合同制造网络》,《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8期。,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建构了新的产教关系。中国职业教育产教关系在社会变革中不断演化,从产教结合走向了产教融合。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出“产教结合”;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制度”,职业教育产教关系从“结合”走向“融合”。其间,1996年《职业教育法》确立了“产教结合”的法律地位;2017年《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正式推动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规范化。2022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四条、第四十条等多条目、高频词、大力度对产教融合的制度化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规制。(3)《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年,第3、11页。不过,在实践层面,中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却依旧面临政府与市场失衡、治理模式落后、体系建设不畅、落地措施不实、学术漂移现象等现实障碍与制度性困境。(4)李政:《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障碍及其消解》,《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9期。事实上,产教融合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则性、宏观性及全局性的政策指导阶段,而是要以制度实践的方式应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5)E.E.Lehmann & M.Menter,“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regional wealth”,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Vol.41,No.6,2016,pp.1284-1307.因此,在全面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关系要从产教融合规范化迈向产教融合制度化。(6)郁建兴、秦上人:《制度化:内涵、类型学、生成机制与评价》,《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本研究跳出政策法律的传统制度框架,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框架建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的新标准与新尺度;然后,立足于新尺度与新变化,分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最后,面向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高适应性和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探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的新方向与新路径。
一、 新尺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的标准与表征
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也到了新起点,在实践层面已经从松散链接逐渐转向实体嵌入。(7)郝天聪、石伟平:《从松散联结到实体嵌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困境及其突破》,《教育研究》2019年第7期。但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中,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又必须超越实体嵌入,走向战略、组织与文化的多重嵌入,从政策驱动转向行动自觉。
(一)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制度:从政策驱动到文化认同
现代意义的制度体系包括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等多种类型和要素(8)R L.Jepperson,“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effects,and institutionalism”,in W.W.Powell & P.J.DiMaggio(eds.),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43-163.,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也是国家产教融合政策、规范和文化-认知等多方面要素组成的规则系统。不过,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还受到更深层次制度的影响。一方面,产教融合的政策深受产业政策的影响,产业政策却受制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基本制度的约束(9)唐世平:《产业政策不能与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混同》,《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第22期。;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是跨界的教育,在国家治理体系和经济社会体系之中呈现出“双重嵌入”的格局。(10)李鹏:《嵌入性变革:中国职业教育管理的历史、问题与反思》,《江苏高教》2021年第1期。事实上,国家之间的异质性会形成不同技能导向的校企合作关系(11)托马斯·雷明顿、杨钋:《中、美、俄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年第2期。,产教融合也就不会有统一的国家模式。因此,中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不仅包括规制、规范与文化-认知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还包括产教融合政策体制之外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政治体制等更上位的制度。如表1所示:

表1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体系
可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等是产教融合制度体系的基石性因素,因为国家技能形成体系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等体制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12)许竞:《试论国家的技能形成体系——政治经济学视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二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引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方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共同富裕”“双循环”等宏观经济政策会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引领着职业教育办学与社会服务的方向。三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影响产教融合实践的成败。其中,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法规、政策文件是国家层面的政治理想和愿景表达,确立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行动指南;规范性制度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即组织的行为受社会价值观、道德要求等方式的影响,在实践层面引导产业界(企业)与教育界(院校)的具体行为。在非正式制度层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内部的劳动文化、就业文化、地域文化、面子文化等,虽然在明面上未能影响产教融合,但是在个人行为决策中却发挥着基因层次的决定作用。(13)E.U.Weber & W.M.Michael,“Culture and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The constructivist turn”,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Vol.5,No.4,2010,pp.410-419.
(二)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标准:从实体嵌入到文化嵌入
职业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之间的合作治理机制有市场治理机制、政府治理机制、自组织治理机制、以市场为中心的共治机制、以政府为中心的共治机制以及多中心共治机制等6种类型。(14)陈星:《以市场为中心的共治: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治理机制改革探析》,《教育发展研究》2019年第23期。虽然这6种类型的表现形式各异,但是在实质关系上都是嵌入(embeddedness)关系。(15)M.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No.3,1985,pp.481-510.事实上,大多数人类行动几乎都嵌入在关系网络之中。从嵌入的类型来看,事物间的嵌入关系有认知性嵌入、利益性嵌入、结构性嵌入、文化性嵌入等多种模式。(16)S.Zukin & P.Dimaggio,Structures of Capital: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979-996.其中,认知性嵌入属于意识思维层次的融合,利益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属于组织性融合,即是实体嵌入,而文化性嵌入则属于深层次融合。在高质量发展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新标准是从实体嵌入转向文化嵌入,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推动利益嵌入、组织嵌入和文化嵌入。通过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嵌入方式的深入和升级,实现产教融合的规范化、制度化。
从职业教育产教互嵌的程度来说,认知嵌入就是产业界与职教界在认识层面意识到要产教合作、互动与融合,代表性的行为就是签署合作文件、合作谈判,甚至包括制定和出台产教融合的文件等;利益嵌入就是产教双方因为各自利益的需要开展了一些具体形式的合作,订单班、现代学徒制、集团化办学等等;组织嵌入(实体嵌入)则从利益合作上升到组织机构融合,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企业、产业学院等都是很具体的产教融合组织形式;文化嵌入则是超越利益嵌入和组织嵌入,产教融合发展成为产业界与企业界的自觉认同与行动,走向一种“职责”与“使命”的自主行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职业教育在追求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要提升服务经济社会的适应性。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制度化必须进一步深化嵌入关系,从利益嵌入、结构嵌入转向文化嵌入,从松散共同体转向利益共同体,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摆脱政策依赖,走向行动自觉,实现契约型制度化和建构型制度化,最终的目标是形成产教深度融合命运共同体。
(三)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时间、空间与价值演化
制度化是制度与组织、行动体系等多个层面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表现为从规则到行为走向规范化、常态化的过程,发挥出约束性、引领性和扩散性的作用。(17)郁建兴、秦上人:《制度化:内涵、类型学、生成机制与评价》。在本质上,制度化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对人与组织的观念、价值、行为进行影响,进而达到认知与行为规范、行动协调(使其导向既定方向而非其他方向)、权威服从与文化认可的过程。(18)M.E.Smith,Europe’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6.在外在效果上呈现出三种维度的演化(19)F.V.Kratochwil,Rules,Norms,and Decisions: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63.:时间维度的过程性与持续性、空间维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价值维度的规范性与约束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化建立在新制度体系和新融合目标之上:一方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在时间、空间和价值维度发生演化,走向规范化、常态化;另一方面,产教融合制度在实践中起到了约束、引领和扩散的效用,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从认知嵌入走向实体嵌入,从实体嵌入转向利益嵌入和文化嵌入。
在时间维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化关注制度体系在规范行为、统一行动、持续引领职业教育和产业界走向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在空间维度,关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在不同场域、范畴中的稳定性作用,产教融合的政策制度、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平台载体、保障机制是制度化能够稳定、扩散的关键,因此,这是一个等序变化的过程,以产教融合的短时段、具体效果为观测尺度。在价值维度,职业教育产教制度化关注于关系、互动模式的程度与深度,这是一个等比变化的过程,从一致性的认同与决策中找到不同程度嵌入的观测尺度。不同维度、不同尺度的产教融合制度化标准为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找到了发展方向和改革目标。规制、规范与文化-认知三重制度在时间、空间、价值三个维度的交互作用,演化成规制型、契约型和建构型三类制度化。
二、 新挑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的问题与困境
制度化的过程需要制度自身不断进行完善、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激活制度体系内各要素共同发展(20)丁志刚、于泽慧:《论制度、制度化、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期。。然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化却存在着制度体系不完备、实体组织不作为、合作机制不高效、制度环境不友好等问题。
(一)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不完备、不协同,政策引领作用开始发生反向偏移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的基础是产教融合制度体系不断完备、不断健全,充分发挥制度体系的引领作用。然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体系建设还停留在颁布政策、出台办法层面,非正式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共171部。其中,《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国家政策制度奠定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基础。(21)李海东、黄文伟:《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高教探索》2021年第2期。不过,虽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制度不断完善,但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规范性文件并未很好地激发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22)方益权、闫静:《关于完善我国产教融合制度建设的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年第5期。一方面,产教融合的制度体系不完备、不协同。首先,非正式制度建设滞后于产教融合的发展。因为文化-认知和职业教育外围环境的不友好,在迈向共同富裕、助力“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中,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自组织制度体系建设没有与时俱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还停留在依赖正式制度的约束与引领的阶段。其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针对性有待提高、时效性有待提升、体系有待完善(23)潘海生、宋亚峰、王世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框架建构与困境消解》,《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特别是职业院校学生的劳动准入制度、合作企业税收减免政策、院校国有资产与私人资产合作制度等现实问题没有相应的政策制度去破解。最后,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丛林”中,各类政策之间的协同性问题突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部门协同逐渐形成了以“国务院-教育部-发改委-省市级人民政府”的政策网络,虽然部门协同度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平均政策力度提升不显著,政策目标间的协同不均衡。(24)王坤、沈娟、高臣:《产教融合政策协同性评价研究(2013—2020)》。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引领作用开始出现反向偏移。公共政策引领的职业教育项目制、评价体系建设与职业院校深耕校企合作之间的冲突(25)李俊、穆生华:《职业教育公共政策的两难困境——北欧职业教育的现状、改革与启示》,《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法规引领中,职业院校日益从区域发展的子系统转变为全国性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迎合政策”办学取代服务区域经济的产教融合,政策效用开始出现反向偏移。
(二)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组织不够用、不作为,实体嵌入制度逐渐走向奖项竞赛
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企业、产业学院等都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体组织,也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嵌入的重要载体。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全面规划产教融合的新格局,先后确定了天津、上海、深圳等21个首批产教融合的城市,遴选了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等24家先期重点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各省市也在孵化区域内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加上此前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等产教融合组织模式,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基础性制度单元已经有了框架性的布局。但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组织不够用、不作为问题突出:一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体组织不够多、不够用。虽然国家遴选了一批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企业,也在逐步推广产业学院,但是,相对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辐射面来说,产教融合实体组织相当有限,根本不够用。相对于全国6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50多万家规模以上企业、9800多所中职学校、1400多所高职而言,目前的产教融合型城市、企业与产业学院建设都还是“星星之火”,远远没有形成“可以燎原”的规模效应。二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组织不作为,运行机制的形式主义严重。在实践中,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大多停留在合同或协议的层面,校企合作项目以“短平快”居多,“订单培养”“跟单培养”“企业奖学金”等是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主要方式,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企业还没有发挥实体嵌入的作用。调查发现,仅有较少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同审议学校的办学方向(12.5%)、发展规模(15.3%)、专业建设(23.5%)、师资队伍建设(35.5%)等重大决策和问题(26)石伟平、李鹏:《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8》,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7页。。三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体组织从组织制度逐渐走向奖项竞赛。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企业、产业学院、集团化办学等是落实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重要制度单元,但在实践中,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体组织从组织制度逐渐走向奖项竞赛,各地逐渐开始以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多寡作为衡量产教融合成效的指标,把产教融合的实体嵌入变成了资源争夺与关系链接,距离实现文化嵌入的制度理想任重道远。
(三)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方式不高效、不经济,互动共享机制中间出现传递失灵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既需要制度体系建设,也需要制度与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更需要制度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和谐共生,以建构产教之间的高效、经济的合作机制。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践规律来看,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和社会公众是最重要的四类主体。从2014年产教融合战略提出以来,各级各类企业的参与状况明显改进,但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不高效、不经济,行政治理失灵,企业参与脱节,政校企之间的合作共享机制出现传递失灵难题。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传递中“加码”与“过滤”并存,政府参与往往陷入“解铃-系铃”的治理困境,“政府悖论”(27)D.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20.的问题相当突出。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受认识、资源、权力等因素的限制只能加码执行或者变通执行,层层加码,又层层过滤,进而“政府调不动企业”“院校管理者调不动教师”的行政治理失灵现象比比皆是。(28)陈星:《以市场为中心的共治: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治理机制改革探析》。最终,以政府为中心的共治成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无法深度融合的重要缘由,政府又不得不通过以政府为中心的共治推动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另一方面,校企双方的平行互动之间,因为制度、利益分配等原因,出现了横向传递失灵。中国职业教育历经资源整合、管理归属与行业“脱离”等变革,使各院校走上了综合性发展道路。如今,在标准化的体系建设中,各办学主体的行业特色逐渐消失,地域性特色越来越少。在实践中,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往往依靠人情关系、利益共享或者资源交换进行沟通合作。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学校系统和产业系统实施部门与部门的对接时,经常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师资互动层面,因为企业与学校属于不同的系统,在“编制”的框架中,人员流动、人员工资、人员管理问题重重。在利益、责任的分担上,职业院校多为国有资产,企业单位多为私人资产,两者在合作项目的风险责任分担上能力和意愿相差悬殊,进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也障碍重重。
(四)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环境不友好、不积极,文化-认知行动多陷入漏斗式格局
以文化-认知形塑的非正式制度是制度化进程中“看不见的力量”,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不仅需要正式制度、组织实体与运行机制的常态化、规范化,更需要非正式制度促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文化-认知发生改变。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推动下,职业教育从“层次”转向“类型”的认知已经成为共识(29)李鹏、石伟平:《中国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的政策理想与行动路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内容分析与实施展望》,《高校教育管理》2020年第1期。,工匠精神、劳模精神、技能强国等也是全国上下推崇的职业教育文化。但中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陷入了“漏斗式治理的困境”: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然而,地方或者具体组织单位则相对缺乏参与产教融合的热忱;学校领导、企业领导积极参与产教融合,但是,职业院校的教师、企业职工则往往不如领导们那么积极参与产教融合;理论界积极倡导产教融合,然而,实践过程却面临着产教融合的各种困境。所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文化-认知陷入到了“漏斗”格局,边沿但相对较高层的部门与群体非常认同产教融合,中心但底层的部门与群体并不热衷或者认同产教融合。“漏斗式格局”的文化-认知有三种类型:一是升学导向的社会文化让职业院校“去技能化”问题突出(30)杜连森:《“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与教育的“空洞”》,《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升学让路。读中职也要尽量“中高贯通”或者“中本贯通”,读高职也要“专升本”。然而,过于关注升学必然会影响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不仅学生不愿意参加校企合作,而且企业因为难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准员工”也不愿意接受职业院校学生来实习实践。二是“重论文、重评奖、轻市场”的学校评价文化使得不少应用型科研成果束之高阁,产教融合的转化效益偏低。我国职业院校及相关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能够与企业签约转化的不到30%,其中,转化后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大约只占被转化成果的30%,只有10%的科研成果能取得经济效益。(31)石伟平、李鹏:《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8》,第118页。部分职业院校囿于自身办学实力和科研实力,只能选择“天女散花”式分散的产教融合项目,未能形成合众之力,更无法生成有价值的实践效益。(32)郝天聪、石伟平:《高职院校的科研锦标赛:表现形式、形成机制及改革建议》,《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11期。三是不够规范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不够成熟的职场制度文化,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对产教融合开展技术研发、培养职工的动力不足。一方面,我国对于校企合作的知识产权保护尚无规范制度,在校企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后,不仅经常出现产权争议,更是常常出现“山寨”“仿制”等类似技术或产品;另一方面,尽管不少企业已经面临“招工难”“技工荒”等问题,但是,员工跳槽频繁、忠诚度不足,企业之间“恶性挖人”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因而,企业对于参与产教融合培养人才也并不积极。
三、 新方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的对策与建议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在新时代遇到了新挑战,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经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常态化、规范化、自主化任重而道远。因此,面对现实挑战,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强化实体组织、变革合作机制、提升供给质量和夯实保障机制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的新方向。
(一) 从政策制定转向政策执行与协同性调试,优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设计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首先要优化相关的制度设计。如今,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体系中,政策制定成效突出,政策颁发已经进入了“丛林”状态(33)S.J.Evenett,“The trade policy jungle:A survival guide for academic economists”, World Economy,Vol.31,No.4,2008,pp.498-516.,因此,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重点是从政策制定转向政策执行,强化政策协同,形成产教融合的政策合力,优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的顶层设计。首先,在宏观层面优化国家产业系统与职业教育体系之间的融合机制。进一步调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政策制度,重点围绕新时代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优化学校治理和企业治理制度,积极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双方的资源、人员、技术、管理、文化全方位融合,围绕生产、研发、培训等关键环节,出台具体的制度规范,明确权利与义务,保护双方利益和合作产出,以制度设计引领产教融合。其次,细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执行举措,从“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教育结构”设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施制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政策执行要在新技术发展中分析中国产业经济的新结构,在新的产业结构中,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中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对职业岗位、职业能力、现有劳动力基础进行深度分析,并将结果落实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以此引领职业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最后,以地市级区域为行动单元,不断完善“国家-区域-院校”布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三位一体”的政策实施行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实施的重点是在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区域内,分析并确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供需情况,推动区域内职业教育实体单位(要素)与产业体系单位(要素)的实践行动。优化产教融合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强化产教融合的规制型制度化,推动产教融合在时间维度的持久性、空间维度的广泛性以及价值维度的一致性。
(二) 从试验项目转向大规模推广与跨界链接,强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体组织
实体组织是落实产教融合制度、推动产教融合具体工作的核心力量。制度走向实践就必须进入到组织场域(34)郭毅、徐莹、陈欣:《新制度主义:理论评述及其对组织研究的贡献》,《社会》2007年第1期。,产教融合的制度化从规制型制度化到契约型制度化、从认知嵌入到实体嵌入都必须强化实体组织建设。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企业、产业学院等作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试验项目,试点项目范围小,实际贡献并未形成规模效应,而且已经引发了各地的奖项竞争。因此,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需要从试验项目转向大规模推广与跨界链接,强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体组织建设,以产教融合实体组织的规模化、实用化撬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嵌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来说,一是建构产业学院和专业学院协同发展的“双院制”模式。采用“军区+战区”的模式,在职业院校内部成立产业学院。专业学院继续按照职业门类培养专业门类的人才,在职业院校内部成立“产业学院”,对接地方经济形成一个产业“战区”,让专业学院的学生到产业学院中进入实战学习。(35)吴金铃:《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产业学院建设探析》,《教育与职业》2019年第18期。二是降低产教融合型企业准入门槛,扩大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试点规模。政府可以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允许企业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教学,扩大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规模。允许企业融入人才培养各个环节,举办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独立或参与举办工作室、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等,参与学校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等。(36)李克:《企业对产教融合的认知、需求、满意度及政策建议研究——基于吉林省538份企业调查问卷的分析》,《现代教育管理》2019年第3期。三是依托企业,举办“企业大学”,并将企业大学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行业龙头企业牵头,联合职业院校、高等学校组建实体化运作的产教融合集团(联盟),在产教融合型企业中开展学徒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探索校企共建产教融合科技园区、众创空间、中试基地,面向小微企业开放服务,建设校企合作示范项目库。四是整合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两类组织实体,建构跨界协同的产教融合组织体系。立足于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双轨制”“双通制”体系,设计“学术型二元制教育体系”及“学徒制二元教育体系”(37)谢笑珍:《“产教融合”机理及其机制设计路径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年第5期。,实现“产教”两个系统之间的一体化融合。
(三) 从层级传递转向平行传递与网式合作,加大产教融合的互动传递机制建设力度
制度在特定场域外显为行为结构,各种行动之间的协同性是确保制度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因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从规制型制度化到契约型制度化,从实体嵌入到文化嵌入有必要优化行动者网络。(38)B.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64-71.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复杂博弈过程,其间又存在着复杂的信息传递机制。不过以政策引领、政府主导的产教融合治理模式往往是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层层传递信息咨询,这种信息传递机制经常出现产业系统和职教系统之间传递失灵现象。因此,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需要转变互动合作机制,从层级传递转向平行传递与网式合作,提升产教融合的有效性。具体来说:一是建立政府部门主导的校企合作供需双向对接服务平台。成立省级的产业研究院,建立省级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通过服务平台汇集区域和行业人才需求、校企合作、项目研发、技术服务等各类供求信息,向各地各类主体提供精准化产教融合信息发布、检索、推荐和相关增值服务,不断健全完善供需信息共享传递制度。二是发挥行业协会和企业作用,鼓励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企业提供产教融合供需双向对接服务。鼓励以提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服务为主要业务的中小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将产教融合服务组织、企业纳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指导目录,定期向社会公布。三是推动职业院校、本科院校、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协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学科专业建设,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和产业化链条。
(四) 从产业需求主导转向职业教育主动供给,提升职业教育参与产业合作的能力
企业和产业不愿意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职业院校能力与水平不够,职业院校所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产业和企业的需要。因此,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需要聚焦课堂,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维度夯实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能力基础与质量保障。具体来说:一是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结构动态调整机制,因地制宜尝试学制与专业体系的变革。坚持“普职协调发展”的原则,逐步灵活变革职业教育学制,探索“3+2”、中高贯通、中本贯通等“升学导向”与“就业导向”兼顾的区域性学制,大力培养“复合型”职业技能人才。二是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服务创新链的专业体系。瞄准区域产业链上延伸的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和人才紧缺产业设置专业,以产业群打造专业群;精准调适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把产业企业的技术、标准、工作过程、文化等元素融入培养方案;校企共建研发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混合式师资团队(39)许淑燕、何树贵、吴建设:《解码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产教融合》,《职业技术教育》2019年第1期。。三是致力于高水平课堂的打造,通过课程、教材改革,加强教师教学能力建设,为职业教育优质课堂的建设打好基础。拓展职业教育课堂空间,从传统的第一课堂转向第二课堂,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过程中,探索“项目主题式课程”“对分课堂”“设计-体验教学”等新的教学方法,提高职业院校教学效益,助推产教融合。四是以实践导向、能力本位为价值尺度,引导职业院校课堂学习知行合一。整合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全面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高水平的学生资源。在技术类专业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以生产性实训为关键环节,探索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五是重点推动企业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构建规范化的技术课程、实习实训和技能评价标准体系。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各类产教对接活动,推动院校向企业购买技术课程和实训教学服务,建立产业导师特设岗位,推动院校专任教师到企业定期实践锻炼制度化,促进校企人才双向交流。
(五) 从政策规则制度化转向文化-认知制度化,健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保障机制
制度化的实现需要平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校企合作结构(40)肖凤翔、陈凤英:《校企合作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江苏高教》2019年第2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不能仅仅依靠政策和机制的推动,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全国上下实现文化-认知的自觉。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还需要从政策规则制度化转向文化-认知制度化,打造友好积极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环境,健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保障机制。第一,调整职业教育评价体系,重塑职业教育质量信号。建立省级职业教育发展预警机制,重点监控专业结构和区域产业发展;让区域性行业协会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到职业教育立交桥的升学渠道宽度、标准的制订过程。第二,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科研、产权保护制度。一是深化职业院校教学体制和科研院所科研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允许科研人员和专业教师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征得学校同意,到企业兼职或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二是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通过研究与创新开发新技术,建立支持企业开展各种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体系,激发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三是建立健全产权制度,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41)R.Grimaldi,M.Kenney & D.Siegel,et al.,“30 years after Bayh-Dole:Reassessing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Research Policy,Vol.40,No.8,2011,pp.1045-1057.,明晰各方参与主体的产权归属和所享有的相关权益,通过综合性法规来协调各种权责关系。第三,对产教融合型企业、产教融合型城市进行激励与奖惩。允许符合条件的试点企业在岗职工以工学交替等方式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校企共招、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对成效明显的地方和高校在招生计划安排、建设项目投资、学位(专业)点设置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第四,优化中国劳动制度,保障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学生、劳工权益。学习德国《手工业者保护法》《劳动促进法》,保障企业与员工的权益。通过评价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奖励激励制度和劳动制度,优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