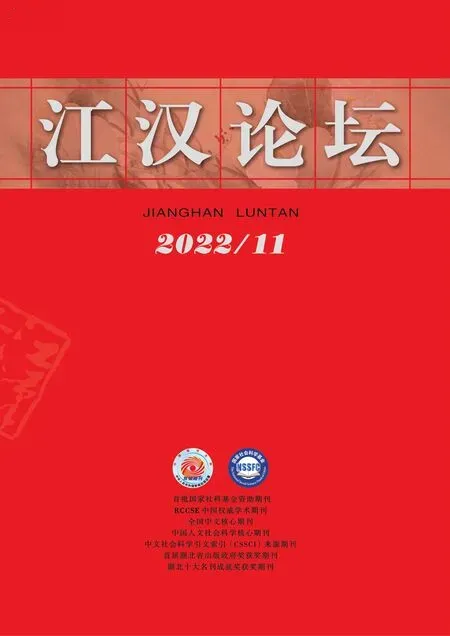国际商事调解的法律性质及其制度构建
2022-12-16费秀艳
费秀艳
调解,作为可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之一,在20世纪上半叶曾为国际商事主体所青睐。①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商事调解并未像仲裁那样得以长足发展,部分原因在于国际商事调解领域欠缺像《纽约公约》那样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的保障机制。近年来,国际社会重新注意到调解对于友好解决国际商事争议、节省国家司法资源的重要价值,试图构建并促进国际商事调解发展、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的相关机制。经过多年努力,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2018 年6 月批准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即《新加坡调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国曾参与《公约》的谈判与磋商,但尚未批准《公约》,未批准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与之衔接的国内法。
当前,我国学者多从《公约》的条文角度来探讨中国应如何构建商事调解制度。②毋庸置疑,《公约》一方面根植于调解的一般性质,另一方面重塑了调解在国际商事领域的法律性质,促进了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在全球的统一与发展。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的制度构建不仅应对接《公约》,还应关注《公约》重塑之下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性质,从根本上规制国际商事调解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
一、国际商事调解的法律性质
《公约》项下的国际商事调解是指与国际商事相关的调解,其中“国际”的含义与我国法律中的“涉外”含义基本相同,只要双方当事人在不同国家设有营业地、或和解协议规定的部分义务履行地所在国不同于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即可满足“国际”要求。③“调解”是指在一名或几名第三人(调解员) 协助下,且调解员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设法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④与国际商事仲裁相比,二者虽然同为可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但国际商事调解具有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和高度自治两个显著特点。
(一) 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
国际商事调解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并非基于法律规则得出是非曲直判断或屈服于调解员权威而服从调解员对争议的处置。当事人在国际商事调解中的各项权利受法律保护,包括当事人享有随时退出调解的权利。比较而言,国际商事仲裁具有准司法性属性,当事人一旦达成仲裁协议,则必须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无论当事人是否愿意,仲裁员均会依据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或规则作出仲裁裁决。国际商事调解则允许当事人随时退出调解,旨在保障当事人追求最真实的利益诉求。诚然,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并不一定公正合理,双方当事人也可能因为利益冲突而无法达成和解,最终导致调解失败。因此,成功的国际商事调解对调解员提出了较高的专业要求,即调解员应帮助当事人认识到自己的诉求是否公正合理及达成和解的可能性。
国际商事调解属于现代调解,不同于古代调解,无需屈服于封建礼教思想或家长权威。古代调解的产生早于法治社会,中国自宋朝以来,乡党宗族所主持的调解即已获得了官府的认可,民间调解已普遍化了。⑤中国古代调解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调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具体权益,而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服务于“以和为贵”、“无讼”的价值取向;其二,调解主要依据宗法和传统礼教思想而作出,调解的过程更像是道德说教过程,调处以情是传统调解的真实写照;其三,由调解所达成的和解未必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可能是当事人臣服于担任调解员的地方官员或家族宗长的权威。⑥
与古代调解相比,国际商事调解是在“法律阴影”下运行的,构成当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组成部分。自20 世纪90 年代中叶以来,国际援助组织已将调解纳入其法治援助项目,作为可替代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敦促法治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在实施法律体系现代化改革中注重采用调解的定纷止争功能,借助调解来实现对法治的更大尊重。具体而言,对于那些法治发展不健全、存在司法腐败或司法独立性欠缺、司法效率低下或诉讼成本高昂的国家,调解为当事人提供了另外一种获得救济的途径。因此,传统的法治援助项目内容是帮助法治落后国家培训法官、建设法庭、公开法律判决、电子化处理法院案卷,当前的法治援助项目则包含对当地调解员的培训、修改国家法律来实现对调解的支持、向当地法官宣传可替代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材料等。
国际商事调解可避免法律对实体和程序问题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帮助当事人灵活便捷地解决争议。“商事活动”区别于“民事活动”,交易中意思自治的程度更高,更注重便捷和效率。⑦调解员和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可多角度剖析争议问题及其根源,探求更符合当事人利益的解决方案,包含延续双方当事人继续合作所追求的未来利益考量,而不仅限于当前争议所涉的权益。比较而言,国际商事诉讼中的当事人通常无权选择应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跨国诉讼中的法律问题和程序问题更为复杂,诉讼费用普遍较高、耗时较长。国际商事仲裁比诉讼灵活,当事人可选择实体法和程序规则。但是,《纽约公约》促进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同时加剧了其司法化进程,国际律师越来越熟悉仲裁的运作机制并引入了大量的诉讼技巧,准据法和程序法问题增加了仲裁的复杂性,导致仲裁费用越来越高、耗时越来越长。⑧
国际商事调解不仅灵活便捷、成本低廉,还可以帮助化解当事人在商业冲突中的误解和偏见,构建和谐的商业关系,这有利于当事人实现长期合作并获得长远利益。虽然国际商事调解主要涉及经济纠纷,不像婚姻或家庭纠纷那样充满情感色彩,但成功的调解要求调解员给当事人以情感关照,理解当事人的想法、感受、行为方式和决策模式。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倾听当事人的指责与控诉,为当事人排解负面情绪提供了通道。同时,调解员帮助当事人分析自己和对方当事人主张的合理性与不足,有利于当事人客观理性地对待争议,避免一叶障目。最终,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可视为各方当事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像诉讼或仲裁那样得出泾渭分明的胜诉方和败诉方,可提升当事人对争议解决的满意度,化解当事人的负面情绪。因此,与诉讼和仲裁相比,调解承载着法律以外的情感关照,有助于消除争议对当事人造成的不良情绪影响,更好地平息争议,从而实现商业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 高度自治、弱化正当程序要求
国际商事调解的高度自治表现在当事人可以全过程控制调解程序,包括选择何种调解模式、调解环节是否采用绝对保密的单方会谈方式、判断调解程序是否正当等。实际上,当事人在国际商事调解中即为争议解决的决断者,同时担任“裁判”和“球员”双重角色,弱化了争议解决中的正当程序要求。
在调解模式方面,便利型、评估型和变革型是国际商事调解的三种模式。便利型调解是最基本的调解模式,调解员通常提出问题、确认并分析当事人的观点和主张、协助当事人发现并分析争议解决方案,但调解员本身不提供解决方案建议或预测法院可能对本案作出的判决,最终通过帮助当事人掌握更多信息和相互谅解而力求达成和解。⑨评估型调解类似模拟法庭,调解员基于法律规定指出各方当事人的争辩弱点、预测法官可能对争议作出的判决、并可能向当事人提供正式或非正式的解决方案供当事人参考。⑩变革型调解强调对调解过程的变革性改变,注重对当事人自信和认同感的激发和提升,从而使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具有安全感并愿意阐释自己的观点和诉求、倾听并关心对方的诉求,最终将争议从一种消极、破坏性的社会关系转变为积极、建设性的社会关系。⑪对于这三种模式,便利型调解是最为熟知和普遍接受的,评估型调解凸显了调解员承担类似法官的职能,变革型调解具有理想主义的倾向。⑫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要求调解员采用一种模式或综合采用两种或三种模式进行调解。
在调解环节方面,当事人在国际商事调解中可以约定采取绝对保密的单方会谈方式,即允许调解员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且不向对方当事人泄露交谈内容。单方会谈具有严格保密性,目的在于帮助当事人卸下防卫心理,坦诚地向调解员表达诉求、陈述与争议相关的战略性信息和附带信息、阐明顾虑和期待获得的利益,从而更清晰地向调解员提供各方当事人的立场和讨价还价的空间,有利于调解员评估各方当事人的诉求是否合理。⑬单方会谈的绝对保密性是国际商事调解中的常用环节,也是其魅力所在。但是,单方会谈的绝对保密性一旦被滥用,则滋生法治风险,侵害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利益。比较而言,国际商事仲裁通常禁止仲裁员私下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因为这可能导致仲裁员有失偏颇,影响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违反正当程序要求。
国际商事调解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当事人判断调解程序是否公正的权利,若当事人认为程序显失公平,可以退出调解。《公约》在起草过程中放弃了正当程序要求,因为和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自愿”这一要素降低了程序问题与和解协议之间的关联性;另外,何为调解所应遵循的正当程序并不明确,难以判断。⑭应注意的是, 《公约》虽然放弃了对国际商事调解的正当程序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恣意妄为。《公约》第5 条允许成员国基于一定的理由拒绝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例如,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状况、调解员未披露可能影响其公正性或独立性的情形、违反公共政策等,这实际上限制了当事人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自治权。
二、国际商事调解法律性质的衍生风险
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高度自治的特点决定了国际商事调解更适合作为实现私人正义的一种手段,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发挥争议解决功能,但由于其在正当程序和法律适用方面的欠缺,决定了调解无法替代司法来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⑮因此,过度使用或滥用国际商事调解容易产生以下风险:
(一) 侵害当事人权益的风险
鉴于国际商事调解的高度自治及调解员缺乏类似法官的裁断职权,调解过程中可能滋生欺骗和欺压行为,进而侵蚀当事人于法治项下所应享有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当事人在国际商事调解中不仅可要求各方提交的材料、调解过程和调解结果保密,还可同意采取单方会谈环节,调解员就一方当事人所作出的陈述不得向另一方当事人披露,这种绝对保密容易导致各方当事人或其律师在调解中的不实陈述难以被对方当事人和公众发现,因此容易产生欺骗行为。⑯调解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欺骗行为有:隐瞒达成和解的最低要价、提高和解要求、夸大本方优势或对方劣势、隐瞒本方在多项诉求中所要达成的最重要诉求、律师故意表示无权就某一要价作出和解决定、故意不向对方披露一些信息等。⑰
若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各方当事人实力不相匹配,实力较弱的一方当事人可能受到强势一方的欺压。⑱例如,一方当事人若急需资金周转,该方当事人可能被迫接受对方给出的较低出价而达成和解;下游企业为获得上游企业所提供的高科技产品,可能同意上游企业的某些不合理要求而达成和解。由于调解员无权调查取证或要求各方当事人质证、亦无权依据法律规定或公平合理原则作出裁定,各方当事人或其律师可利用调解的保密性而采取一些不宜公开的谈判伎俩,甚或作出不实陈述或不合理主张,影响调解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
(二) 侵害第三人权益风险
就未参与国际商事调解但与之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而言,调解的高度保密性容易导致第三人无从知晓并参与到调解过程,当事人可能为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损失转嫁给第三人,甚或采用虚假调解来损害第三人利益。⑲即使当事人不存在转嫁损失的意图与行为,国际商事调解的高度保密性也可能损害第三人于法治项下所享有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若第三人为不确定主体,则挑战对公共利益的权利保障。依据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国际商事调解可能存在以下三种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一是各方当事人均具有主观恶意;二是仅一方当事人具有主观恶意;三是各方当事人均不具有主观恶意。例如,就买卖行为而言,对于一般消费者难以发现的存有安全隐患的高科技产品,经销商和生产企业可能就产品质量纠纷达成和解,生产企业以较低价格持续供货给经销商,经销商继续销售存有安全隐患的产品而不向公众披露产品质量问题,从而实现经销商和生产企业的持续获利,但消费者利益因此受到损害。再如,就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而言,通常牵涉到东道国环境保护、当地居民利益等社会公共利益。若由政府机构代表当地居民或公众参与调解,这首先涉及政府机构问责和法治政府建设问题,还涉及是否剥夺了当地居民或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国际商事调解的高度保密性不符合当前国际社会所发起的提高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透明度改革,能否协调或如何协调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值得深入探讨。⑳
(三) 侵害法治项下的公共价值权益的风险
国际商事调解的当事人可搁置法律规定,按照商业惯例、一般常识或其他准则来进行调解,现行法律所承担的公共价值难以体现。㉑调解程序的保密性导致国际商事调解无法承当公开审判所发挥的教育功能,这挑战了正当程序所体现的“看得见的正义”。经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鲜少提供达成和解的缘由和具体推理过程,无法像判决那样公开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过度采用调解甚或导致国际商事关系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㉒对大陆法系而言,过度采用调解会减抑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应发挥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功能,侵蚀司法所承载的澄清法律含义、统一适用法律的功能。对普通法系而言,过度采用调解不仅会导致前述不良影响,还会减抑法官的造法功能,损害立法的发展。无论对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而言,过度采用调解均会侵蚀法律规范和公开判决为国际商事法律关系所提供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㉓
三、中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构建中的风险规制
对于国际商事调解可能带来的法治风险,一方面需要调解员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需要规范公共主体参与调解所涉的公众利益保护问题,还需要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充分发挥审查职能。对于双方当事人串通或联合调解员共同进行虚假调解的行为,不仅需要追究参与主体的相关责任,还需要结合行业自治、诚信建设、和解协议执行的透明度建设等几个方面来进行综合治理。因此,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构建的风险规制可从调解员准则、公共主体参加调解的特别规定、调解的保密性与例外规定、法院的执行与审查、防止虚假调解这几个方面予以重点规制。
(一) 调解员准则
《公约》未规定调解员应遵守的具体准则,但规定调解员若严重违反适用于调解员或调解的准则、或调解员未披露可能对其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正当怀疑的情形,若前述行为与当事人达成和解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成员可拒绝执行和解协议。《联合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要求调解员为确保其中立性和独立性而应自调解程序开始至程序结束承担持续披露义务,在调解过程中公正对待当事人。调解员保持中立性和独立性、公平公正、避免利益冲突,通常构成各国法律规定的调解员最低行为准则。除了法定准则,美国、欧盟、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调解行业自律方式规范调解员行为,确保调解质量。行业自律内容通常包括相关机构发布调解员行为守则或指南、设立调解员认证制度、定期培训调解员等。
我国目前关于调解员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人民调解制度领域㉔,而人民调解制度定位于民间纠纷解决,这与国际商事调解对调解员的专业性、跨文化沟通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不相匹配。㉕因此,我国有必要对从事国际商事调解的调解员作出最低准则要求,要求调解员遵守中立原则、保密原则和审慎原则。具体而言,中立原则要求调解员应不偏不倚地对待各方当事人,不因当事人的性格特点、价值取向、财务状况等各种因素而对当事人持有偏见;同时,中立原则要求调解员应履行持续披露义务,无论是调解开始前还是调解过程中,调解员有义务向当事人披露其所知晓的可能影响其中立性的任何事项。保密原则是指调解员应按照约定履行保密义务,除非法律作出例外规定。审慎原则要求调解员应确保各方当事人理解调解程序且充分参与到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应尽量避免调解过程中发生不当行为而导致和解协议无效;调解员若有合理理由认为当事人存在虚假调解的可能,应及时退出调解程序。
(二) 公共主体参加国际商事调解的特别规定
我国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公共主体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两类主体。政府是公法人,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政府对公众负责、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接受公众监督,这与调解的保密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部分国有企业承担着类似政府所肩负的公共职能。因此,政府和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商事调解可能涉及公众利益或公共利益,应对二者参与国际商事调解作出特别规定。
1. 严格规定政府参与国际商事调解所应承担的义务。政府参与国际商事调解涉及两种情况:一是国际投资调解,其争议事项为政府作为本国境内投资管理者与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就投资问题所发生的争议,其特点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二是狭义的国际商事调解,其争议事项为政府作为平等商事主体与国际商事主体之间就货物买卖等所发生的争议,其特点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国际投资调解比国际商事调解更复杂,不仅涉及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管辖权,还可能涉及当地居民利益,例如,外商投资矿产资源开发争议可能涉及当地环境污染问题,进而关涉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
就国际投资调解而言,若政府部门参与其中,我国可借鉴2012 年《国际律师协会调解规则》(IBA Rules for Investor-State Mediation) 第 10 条第3 款的适度披露原则,要求政府部门履行适度披露义务,对于调解所发生的事实和调解结果应予以公开,接受公民监督。若调解事项涉及当地居民利益,应准予当地居民推选代表参与调解程序。此外,考虑到调解在程序规范和法律适用方面的欠缺、和解协议不能承载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功能,对于涉及我国投资法律制度和我国政府行使外资管理权是否适当等法律问题,应禁止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此类争议。就我国政府部门所涉的狭义国际商事调解而言,由于其所涉争议相对简单、不直接涉及当地居民利益或公共利益,应允许政府部门采用国际商事调解解决争议,同时要求政府公开其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事实和调解结果,接受人民和社会监督。
2. 分类规制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商事调解所应承担的义务。我国应按照国有企业所承担的职能分类规定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商事调解所应承担的义务。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包含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这几种形式。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政企分开、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不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的原则,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㉖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国有企业主要分为两类:公益类和商业类。㉗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必要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可以由政府调控;商业类国有企业包含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的竞争类企业,也包含以保障国家安全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性企业。现有企业分类基于谁出资谁分类,缺乏统一标准,容易造成分类混乱。㉘有学者提出,实际上,我国国有企业应分为三类:商业类(一般竞争类)、公益类和国家安全类。㉙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应按照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与其他私有企业处于平等地位,无论是关于公司运营还是相关争议解决,均应按照现代企业法人决策机制运作,允许该类企业自主决定是否选择调解方式解决争议。但是,对于公益类和国家安全类国有企业,因这些企业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应参照前述政府参与调解的情况予以规定。
(三) 调解的保密性与例外规定
参与调解的各方当事人不应泄露有关调解的通讯内容,这是调解应遵守的一般原则;但是,绝对保密原则容易滋生欺骗、欺压等行为,存在损害公共利益、第三方利益甚或一方当事人利益的风险。因此,参考外国及我国香港关于调解保密例外的规定㉚,我国应对以下几种情况作出保密例外规定:其一,有合理理由相信,调解所涉的该项披露为防止或减轻对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所造成的损害所必需;其二,该项披露是按照法律规定或法院命令而作出;其三,该项披露是为征询法律意见而作出;其四,该项披露是为研究、评估或教育的目的而作出,且没有直接或间接泄露该项调解通讯所涉的当事人身份。另外,在获得法院许可的情况下,任何人可为下述目的披露调解内容:一是执行或质疑经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二是为指控调解员失当行为而提供证据;三是法院认为有理由支持的其它目的。
(四) 法院的执行与审查规定
法院一方面应便利和解协议的顺利执行,另一方面应在执行过程中确保我国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基于这两点考虑,我国可就执行和审查问题作出以下规定:
首先,关于我国执行法院的级别和地域问题,参照我国关于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㉛,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然而,考虑到我国中级人民法院的任务较为繁重,我国可按照执行标的金额的大小来分流执行,即达到一定金额标准的由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否则由基层人民法院执行。㉜其次,关于和解协议的审查问题,为高效、便捷地执行和解协议,应由负责执行的法院予以审查。借鉴《公约》规定,法院应对和解协议作出形式审查,不应作出实质审查。但是,若当事人提出实质审查要求或第三人提出执行异议,若有初步证据支持当事人诉求,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指定专门审判机构予以查明。㉝再次,参考仲裁领域关于保全措施的实践,考虑到多数国家均承认当事人在仲裁程序进行中有权提出保全申请㉞,我国应在制度设计上允许当事人在申请执行和解协议程序中提出保全申请。
(五) 防范虚假调解
由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不够健全,虚假调解是我国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时必需予以防范的风险。目前,我国的商事调解发展缓慢,有关虚假调解的规定主要散见于法院调解、人民调解、商事调解中。㉟我国应在立法上界定虚假调解的构成要件,同时完善调解行为各阶段所涉的法治建设。
第一,借鉴我国关于虚假诉讼的要素规定㊱,在立法中明确虚假调解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将虚假调解界定为包含以下要件:一是在主观方面,当事人存在恶意和谋取非法利益的意图;二是在客观方面,当事人存在串通、虚构事实、借用合法调解程序的行为;三是在效果方面,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侵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考虑到调解的高度意思自治和调解员并不具备类似法官的调查取证职权,无论调解员是否知晓当事人进行虚假调解,都不应成为影响虚假调解认定的因素。但是,若调解员知道当事人从事虚假调解,但未能及时退出调解程序,调解员亦应认定为参与了虚假调解。
第二,还应从行业自律、加强诚信建设、提升法院执行信息的透明度来防范虚假调解。一是我国应确立国际商事调解行业自律要求,设立中国国际商事调解协会,负责制定《国际商事调解行业准则》和《国际商事调解员行为守则》,监督国际商事调解机构的运营和调解员的相关活动,评估调解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处理公众对调解机构和调解员的投诉等。对于参与虚假调解的调解员,除应追究其法律责任,还应将其纳入失信名单,禁止再从事与调解行业相关的工作。对于前述调解员所在的调解机构(若有),应责令其加强对调解员行为规范培训和监督。二是就调解活动而言,凡由我国调解员或调解机构受理的,应要求调解员、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签署《诚信调解承诺书》,该承诺书应载明各参与人违反诚信调解的法律后果。在调解过程中,若调解员有理由怀疑当事人从事虚假调解,调解员应退出调解程序。三是就和解协议的执行而言,应建立执行信息查询系统,法院在执行前应将执行信息录入系统供公众查询。对于提出执行异议的第三人,若有确凿证据证明执行和解协议有侵害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可能,法院应停止执行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第三,我国未来有关国际商事调解方面的立法应确立长臂管辖原则,保障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良性运作和我国商事主体的海外利益。鉴于国际商事调解的当事人和调解员可能来自不同国家,调解可能通过远程视频等方式进行,这对传统的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提出了挑战。长臂管辖权使管辖规则更富有弹性和灵活性,这有利于应对调解的灵活性和非正式性所带来的法律风险。我国通过确立长臂管辖原则可防止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而选择以调解方式达到非法转移财产的目的,进而防范并打击虚假调解行为。因此,但凡当事人向我国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和解协议,无论当事人或调解员是否来自于我国,无论争议事项是否发生在我国,只要当事人或调解员违反我国关于国际商事调解方面的强制性规定、损害我国相关主体利益或国家利益,我国法院均应享有管辖权。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我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我国企业在境外的合法权益若受到虚假调解或其他不当调解行为的侵害,我国法院亦应行使管辖权,保护我国商事主体的海外利益。
四、结语
《公约》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重要立法,提升了和解协议在国际层面的法律效力,必将推动调解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商事调解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高度自治及其弱化正当程序的特点,能够提高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效率、降低争议解决成本、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商事往来及其长远的商业利益。因此,调解一方面可以弥补仲裁和诉讼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激励二者朝着更质优价廉的方向改革。然而,作为以利益为导向的调解,虽然可以为当事人提供获得正义的另一种途径,但也可能引发欺诈、欺压等行为,侵蚀法治项下的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和公民权利。另外,《公约》项下的调解主要适用于私法层面的国际商事争议,调解所尊重的意思自治与私法的相对自治不谋而合;但是, 《公约》 并不排除适用于公法人所参与的国际商事活动,即便是私人主体之间的国际商事活动也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这意味着《公约》项下的某些调解可能对私法与公法的划分、市场与政府的分界理论提出挑战。如何规制这些涉及公法方面的国际商事调解,是调解理论和制度设计方面的难题。因此,我国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时,一方面应注意对接《公约》规定,推动我国的国际商事调解制度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采纳;另一方面应根据国际商事调解的法律性质及其衍生风险,从国内与国际法律互动视角作出必要的风险规制。
注释:
①S. I. Strong, Beyo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 Policy,2014, 45(11), p.12.
② 参见孙南翔:《〈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中国的批准与实施》,《法学研究》2021 年第2 期;赵云:《〈新加坡调解公约〉:新版〈纽约公约〉下国际商事调解的未来发展》,《地方立法研究》2020 年第3 期。
③ 参见《新加坡调解公约》第1.1 条。
④ 参见《新加坡调解公约》第2.3 条。
⑤ 参见徐胜萍: 《中国传统民间调解渊源究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1期。
⑥ 参见张波:《论调解与法治的排斥与兼容》,《法学》 2012 年第 12 期。
⑦ 石冠彬、彭宛蓉:《司法视域下民法典违约金调减规则的解释论》,《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
⑧ S. I. Strong, Increasing Legalism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 New Theory of Causes, a New Approach to Cures, World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Review, 2013, 7(2), p.117.
⑨⑩ Michael J. LeVangie, Mediation-Evolving Methods: Exploring the Three Basic Types of Mediation, Vermont Bar Journal, 2019, 45(3), pp.47-48, p.48.
⑪Robert A. Baruch Bush & Joseph P. Floger, The Promise of Mediation: The Transformative Approach to Conflict, San Francisco, John Wiley & Sons, 2005, pp.13-15.
⑫⑭ See J. Michael Greig, Stepping into the Fray:When Do Mediators Mediat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5, 49(2), p.250, p.250.
⑬Tobi P. Dres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1988, 10(3), p.574.
⑮ See Ronan Feehily, Commercial Mediation: Commercial Conflict Panacea or an Affront to Due Process and the Justice Ideal?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2015, 48(2), p.319.
⑯⑰ See Jeffrey Krivis, The Truth About Deception in Mediation, Pepperdin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Journal,2004, p.255, pp.253-255, p.1085.
⑱㉑See Owen M. Fiss, Against Settlement, The Yale Law Journal, 1984, 93(6), p.1076.
⑲ ㉒ ㉓ See David Luban, Settlements and the Erosion of the Public Realm,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995,83(7), p.2626, p.2623, pp.2622-2623.
⑳Catharine Titi, Mediation and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in Catharine Titi & Katia Fach Gomez (eds.),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Dispu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35-36.
㉔ 2018 年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的意见》。
㉕ 参见唐琼琼:《〈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㉖ 参见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5 条、第6 条规定。
㉗ 参见2015 年国资委、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1 条规定。
㉘㉙ 韩立余: 《国际法视野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法学》2019 年第6 期。
㉚ 参见新加坡2017 年《调解法》 第9 条、2003 年美国《统一调解法》 第6 条、2017 年香港《调解条例》第8 条。
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21 修正) 第290 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㉜ 参见赵平:《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下的〈新加坡调解公约〉》,《经贸法律评论》2019 年第6 期。
㉝ 参见刘敬东主编:《〈新加坡调解公约〉批准与实施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109 页。
㉞ 杜新丽:《论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与立法完善》,《现代法学》2005 年第6 期。
㉟ 参见严红、陈庆特:《〈新加坡调解公约〉下虚假调解的界定、挑战及中国因应》,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2 年第3 期。
㊱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 条规定: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1) 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 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 虚构事实;(4) 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 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