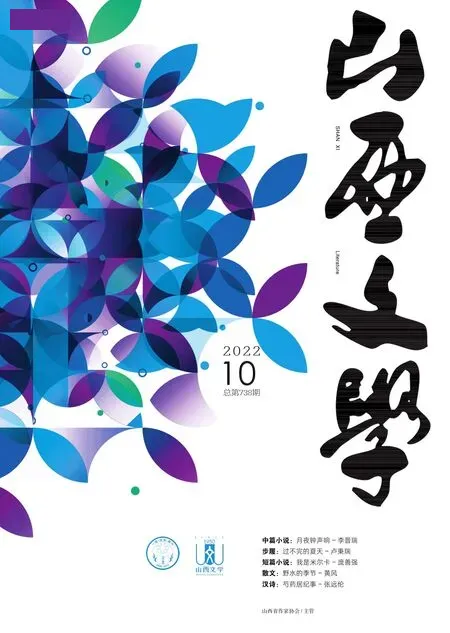我是米尔卡
2022-12-16庞善强
庞善强
我喜欢微醺的感觉。一个人静坐在那里,端端地捧着一本书,以字下酒,便会慢慢进入到一种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对我而言,此时大约是最惬意的时候,我会游离于时空和自己的小圈子之外,猝然变成书中的某个人,或者是其中的某个动物,然后沿着他们的生活轨迹,去继续演绎他们未尽的尘世故事。
有段时间,我一直沉湎于契诃夫的文字。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契诃夫笔下的米尔卡——那条所谓“名贵的狗”。但是,我憎恨曾经的第一个主人——那位自恃聪明狡猾善变的杜博夫中尉,当然也厌恶那个冷漠自私的士兵克纳普斯。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我极度讨厌回忆过去。
我现在的身份是杂耍剧团的一个“演员”,这是今晚我的第二场演出。刚才我歇息了一阵子,感觉到了腹中饥饿,可恶的驯兽师却再次抬起右手食指,频频向我做出摆动指令,我知道该轮到我登台演出了。不过,我已经谙熟了这场上的规矩,知道自己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
“尊贵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每次登台后,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句肢体语言。接着,我还得继续说下去:“噢,首先请允许我苟且学着你们人类的姿态站立起来,通过我竭尽媚献的丑恶嘴脸,以及拙劣而滑稽的肢体语言,向你们真诚地道一声安。我如此故意做作,学着你们的样子,实属无奈。当然,我并没有玷污你们的意思,因为我毕竟是一条狗,没有你们聪明发达的大脑,和悦耳动听的声带,更没有你们能把白说成是黑的卓越能力,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譬如,杜博夫中尉就极其擅长使用这种应变的绝活儿。而我只能以这种虔诚的方式,来表达对你们的热烈欢迎和衷心祝福。现在是晚上九点半,让你们等待了这么长时间,实在对不起。好在你们大约刚从灯红酒绿的奢华场所中走出来,也许借此机会可以消除掉你们胃部的不适,或是可以消除掉你们身上沾染的烟花味道。如此说来,这对你们或许算是一件幸事。”
我前腿抬起,直立地站在台上,频频作揖,不断地变化着声调叫着,我不知道台下有多少观众能听懂我刚才所谓的“话”。不过,我过去的主人大约可以听得懂。譬如,我短而清脆地“汪、汪”叫两声,他就知道我在说“饿了”;倘若我拉长声调用后嗓音“吱吱”轻轻叫那么一声,他知道那是我在撒娇。
不管台下的观众现在是否能听懂,我总得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先向观众问好。我知道,我稍一疏忽,身上随时会落下热辣辣的蛇一样的鞭子。我成了这家动物杂耍剧团的一个“小丑”——不,准确地说,我不过是一只母狗。可是,讨厌的驯兽师喜欢把我打扮成一只绅士般的公狗形象,还要在我的鼻子上架一副杜博夫中尉曾经戴过的那种圆形墨镜。杜博夫中尉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她的父亲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银行家,这便为她提供了阔绰自由的上流生活,也为杜博夫中尉带来挥金如土的机会,有几个妙龄女子自愿成了他的红粉知己。当然,这些隐私你们是不会知道的,契诃夫先生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事情,我就更不该吐露其中的秘密,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的第二个主人常会提起杜博夫中尉,他或许是从我的梦呓中得到了什么消息,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他也有好几个老婆,一个是原配妻子,另外几个是他私下里娇宠的女人。噢,请再次原谅我的幼稚,不该和你们去揭别人的隐私,这或许是我今生注定颠沛流离的原因与宿命。我想,还是说一下这舞台上的事情。我表演的花样繁多,有上刀山、下火海,闯天堑、入地狱、跳阴魂舞,等等。我的每一个动作都随时面临着肢体的损伤,甚至有生命危险。不过,你们莫要担心,我能把各种动作表演得挥洒自如,很少有失蹄的机会——也许是我自作多情了,有人担心过我没有?
接下来,该是我的精彩演出。或许我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自打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就赢得了观众的认可,这点我可以从你们疯狂的呐喊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口哨声感悟到。噢,你们可别真以为我先天就拥有干这么复杂而刺激的演技,我的这些本领当然是经过驯兽师的严酷调教才逐渐掌握的。我说的先天因素是,我除了会很好地表演这些本领,还知道怎样逗观众开心。譬如,在钻连串的火圈时,我的皮毛在要接触到熊熊燃烧的火焰时,我故意显得惊惧畏缩,耷拉着脑袋退了回来,等观众为之或愤怒或失望或惋惜时,我会出其不意地一跃而起,从容地从火光中钻出,此时赢得的观众掌声会格外热烈。当然,我在落地后,还会调皮地再次向观众连连作揖,还会发出几个类似于你们撒情时的飞吻。也许只有此时,我才会忘却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痛苦和不幸。当你们的掌声渐次凝固,当我再回到我的固定居住场所——一个特制的铁丝网笼,我便很快孤独绝望起来。虽然我不用再担心食不果腹,但是我还是决定只要有一线机会就逃出去,我受够了这里嘈杂的环境和驯兽师的虐待。我多么想再回到过去的时光里。可是,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决定,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去流浪,尽管我知道那样的日子,我的生命会朝不保夕。
我现在的名字叫安德烈,我极讨厌这个名字。克纳普斯说得没错,我就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母狗,而并非杜博夫中尉口中公母不分的那条狗,为什么偏偏要我叫这样一个侮辱我性别的名字?我是米尔卡,的确是美丽的米尔卡,为了证明我的身份,这里不得不讲清楚我的一些经历。
我的第一个主人杜博夫中尉是一个颇有戒心与野心的贪婪家伙,也许是因为我真的未能帮助他打猎,他便决定尽快将我处理掉,于是以喝酒的名义约了克纳普斯闲坐。那天的阳光很明媚,我却突然有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果然,杜博夫中尉突然说,要将我卖给克纳普斯,打算卖五十卢布。克纳普斯嫌弃我是一条母狗,为此他与杜博夫中尉展开了唇枪舌剑。事实上,我就是一条母狗,无奈杜博夫只好将我的身价降至二十五卢布。然而,克纳普斯的性情仿佛是因迪吉尔卡河冰冷的六须鲇,他对于母性的排斥和吝啬出乎我的预料,他竟然不愿意出一个戈比。杜博夫中尉在惊怒之余,还在扮演着变色龙的角色,他再次友好地劝慰克纳普斯,“把狗带走吧,白送您了!”杜博夫万万没有想到,就算是白送,克纳普斯也不愿意收留我。当杜博夫以友好和关爱的姿态将克纳普斯送至家门,却依然未能打动他冷漠的心。杜博夫当时彻底崩溃了,他决定将我卖给屠夫,让他们将我剥皮吃肉,还不忘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什么“贱胚子、猪与狗的杂种”。我彻底绝望了,在惊慌之余,趁着杜博夫依然沉浸在克纳普斯跨入门槛的背影,我逃离了他的魔爪。
当我流浪到一家大公司的门口时,恰好遇上了这家公司的络腮胡子老总鲍里斯,他在几个女人的陪伴下悠闲地出来散步。
“多漂亮的一条狗!这是谁家的狗?”一个女人说。
“这可是英国纯种长毛猎狗,是一条名贵的狗。”另一个女人说。
鲍里斯围着我转了三圈,他突然惊喜地叫道:“天呐,米尔卡,是神奇而美丽的米尔卡!”
“米尔卡是谁?”一个女人问。
“她就是杜博夫中尉府里的米尔卡。你看她这嘴脸多迷人多漂亮,一看就是个机灵鬼。米尔卡,过来、过来,上这儿来。哎呀呀,你这个小美人、小坏包、小宝宝、小乖乖。”鲍里斯说。
“可是,杜博夫中尉曾经说,米尔卡是条公狗。”一个女人说。
“为什么杜博夫先生能当上中尉,而克纳普斯永远只能做一名士兵,原因就在这里。”鲍里斯说着,哈哈大笑,“好了,把米尔卡带上,我谁也不给,我的小美人,小淘气,跟我们一起走。”
“那为什么克纳普斯不愿意为她付出一个戈比,甚至将米尔卡白白送给他都不要?”另一个女人说。
“克纳普斯的愚蠢就在这里。世界上所有愚蠢的人,都是如此,他们卑微而单纯的目光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真相,根本不懂得切合时宜的嬗变,所以最终会一事无成。”鲍里斯说。
“可我还是不明白。鲍里斯先生,米尔卡能带给您什么?”
“当然,我不会指望她去帮我打猎,或是去做其他的事情,我需要的只是多一个开心的噱头。好了,亲爱的米尔卡,我们一起走吧。”
我果断地跟着鲍里斯走了,他成了我的第二个主人。
鲍里斯走到哪里,必将带我到哪里,无论去什么地方,我都会得到人们的赞誉和宠爱。鲍里斯带着我和娇宠的几个女人坐豪车,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高档商务酒会。尽管那些奢华的会馆门上总是贴着歧视我们的招牌:禁止宠物狗入内。问题是,鲍里斯绝非寻常之辈,用他的话说:“别惹我,小心我用钱砸死你!”自然,我的身价也非寻常。会馆的门卫根本不敢把我当狗看待,而是把我当作上等的嘉宾迎接进去,安排我在一个环境幽雅的房间,给我吃烤制新鲜的牛排和威士忌。当然,牛排要欧式口味的正宗特色,威士忌要冰镇的,外加上好的绿茶。
按理说,我的日子无忧无虑,我该尽享人世间的奢华。可是,我的一次意外冲动,竟导致了被鲍里斯驱赶出门。
那天,鲍里斯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一位金发飘飘风姿颇好的少妇,袅袅婷婷,像伏尔加格勒池塘里风摆的新荷。那少妇是公司的财务总监,可是她未曾到鲍里斯家来访过,你大约可以想象到,当时我作为狗辈特有的警惕。鲍里斯显然很看重她,破天荒为她倒了一杯威士忌香槟酒。那少妇不知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竟然让鲍里斯异常兴奋。少妇本来坐在鲍里斯对面,忽然脚下生花般挪到了鲍里斯身边,把她丰挺的酥胸贴在了鲍里斯身上,说:“你该怎样酬谢我?”鲍里斯竟被她压在了身下。我哪里能容忍她这样欺辱主人,便猛蹿上去一口咬在了她的踝骨处。没想到,我的举动竟然惹怒了鲍里斯。
“你这条下贱的坯子,猪与狗的杂种,我要让人剥了你的皮,吃了你的肉!”
鲍里斯边骂,边一把抓住我的一条后腿,顺势从二楼打开的后窗将我摔了出去。待我睁开眼时,我发现自己吐了一摊血,但我还能挣扎着站起来。那一瞬间,我恨透了鲍里斯,决定再不登他家的门,哪怕是我去流浪。
我掉落的位置刚好是鲍里斯所在的国营公司,鲍里斯的这套豪华住所就建于公司的前面。我太熟悉这里的环境了,我曾随鲍里斯无数次地来这里巡视过。院子里修缮整齐的草坪和花岗岩马路,以及气派十足的路灯都见证了公司曾经的辉煌。正当我在空荡荡的公司院落失魂落魄地徘徊时,我竟然被人狠狠地踢了一脚。踢我的是公司的一个员工叫尤里,他边踢边骂骂咧咧的:“苏卡(指母狗)!你这个可恶的东西,好端端的一个公司让你们给折腾没了,我打死你!”
尤里年轻时曾练过几年功夫,有人说就算是丈余高的墙也挡不住他飞跃的脚步。可是,尤里在公司里从来不显山露水,甚至在众人眼里有点痴,还有点懦。譬如,公司的职工,见了鲍里斯和我会那般毕恭毕敬,唯独尤里见了鲍里斯和我则赶快低下头并绕道走开。如今,尤里竟然敢这样和我动粗,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现在,什么都变了,主人也不再是我的主人,公司也不是过去的公司,尤里也不再是过去的尤里。但是,我骨子里的尊贵和高傲依然健在,我咋能受得了这样的屈辱。我一边向尤里一个劲地狂吠,一边期待鲍里斯能从豪华的住所里探出高贵的头,哪怕是他给尤里一句呵斥。可是,没有,鲍里斯始终没有出现在那个打开的窗口。
尤里又骂道:“苏卡,你还敢向老子耍疯使泼?好,老子告诉你,老子再不受你们的管制了,老子今天先打死你!”说着,尤里从草坪里捡起一个硕大的土疙瘩,照着我的身子恶狠狠地砸过来。我刚才摔坏的后胯骨越发疼痛了,只得嗷嗷叫着,夹着尾巴一瘸一拐地跑出了公司。我该去哪里?
街道上不时地有人说:“噢,多漂亮的一条狗!”
我在人们的赞誉声中重新找回了自信。我抖落了皮毛上沾染的尘土,高挺着旗帜一般的尾巴,从容地穿行在闹市的繁华处。我相信自己的与众不同,一定将会找到一个更好、待我更幸福的主人。
有两个穿着邋遢的年轻人一直尾随在我的身后。
一个人说:“这该是一条名贵的狗,逮住它卖到狗市,将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另一个人说:“你看它简直就是一个耀眼的精灵,我们得想出最好的办法捕获它,这样我们就有了足够的钱去过圣诞节。”
多么险恶的用心!我暗自诅咒着,便加快了奔跑的速度。穿过一座跨越街道的天桥,我很快就甩脱了那两个可恶的家伙。
在一家商场的门口泊着一辆车。一对穿着考究的夫妇正准备驾车而去,瞥见我便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多么名贵的一条狗!它能否成为我们最快乐的宝贝?”女的说。
男人从车里打开一个食品袋,随手扔给我一个寿司。我看了看那廉价的食品,以及他们那辆寒酸的轿车,便不屑一顾地走开了。
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会招惹来几条蹲守在犄角旮旯的流浪狗向我大献殷勤,它们夹着尾巴的窘态,以及肮脏的皮毛和瘦骨嶙峋的身躯让我感到阵阵恶心。我怎么能与他们为伍?我可以从它们羡妒的眼神里读到什么是敬畏。
一直到傍晚的时候,我才感到饥渴难捱。我想起了杜博夫中尉、鲍里斯,以及鲍里斯经常带我去的那家皇派国际商务会馆,那里有我最爱吃的欧式牛排及冰镇威士忌。我竖起旗帜一样的尾巴,一溜小跑赶到了那家会馆,走进高大的旋转式大门,迎接我的还是那位帅气的小伙子。
“米尔卡,小美人!”小伙子热情地招呼着我。
正当我打算走进那间贵宾间,一个壮实的大厅经理喊了一嗓子:“站住!赶快把这条可恶的疯狗赶出去,要知道她现在已经是条流浪狗,她被鲍里斯先生赶出了家门,她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咬了鲍里斯的贵客。”
天呐,那位道貌岸然的鲍里斯竟是这般毒蛇心肠。我仓皇地躲过了那人飞起的脚,迅速地潜入了街道的人流中。
我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走着,人们的赞誉声依旧。我试着向一对中年夫妇靠近,在他们跟前停着一辆豪华宝马。
女的说:“好漂亮的一只狗!”
男的说:“离它远点,这一定是一条被人抛弃的流浪狗,要知道它的身上有可能携带瘟疫病毒。”
我怎么会有什么病毒?我向那人展示着油光发亮的皮毛,以及健康有力的四肢,我期盼以此来消除他对我的误解。没想到那人大喝一声:“滚开,你这个讨厌的家伙!”
那时,我是多么后悔,我不该离开鲍里斯。我决定还是再回到鲍里斯那里,也许他现在的火气已经消了,也许他已经原谅了我的过失,也许他现在正四处寻找我,毕竟我和鲍里斯之间有那么点机缘和感情。我兴冲冲地跑回鲍里斯的楼下,屋子里灯光明亮,鲍里斯的身影在窗户上来回晃动。我趴在鲍里斯的屋外,用爪子抓挠着大门,像个委屈的婴儿嘤嘤呜呜啼哭起来,希望借此得到鲍里斯的宽恕。但是,大门一直没有打开,里面不断地传出了一对男女的浪笑,淹没了我的凄楚哀鸣。
我再一次走到街上。已经是半夜时分,街道上没了人,风冷冷地吹着。
饥饿感再一次袭来,我禁不住打了个哆嗦。
在一个污浊不堪的垃圾堆上,有一个拾荒者在小心翼翼地翻拣着垃圾,每一个酒瓶、饮料罐、塑料板,以及每一片纸都被他收纳进硕大的编织袋中。拾荒者也许是因为常年操持这种职业,抑或是身体本来有什么病变,他单薄的身躯一直佝偻着,即使是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也只能是努力地挺起麻秆一样的脖子。在垃圾堆的另一边,有三只骨瘦如柴的狗相互撕咬,在它们的面前是一袋子发着霉臭的食物。天啊,这样的东西都可以吃?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随即,我感到一阵阵恶心,但是肚子里已经没有了食物,我没有可吐的东西。沿着斑驳的树影,我缓缓地向前走着,鼻翼里竟窜进了一股酽香的味道,是那股特别熟悉的烤牛排味。我侧脸看时,在一家豪华酒楼的拐角处,一位头发蓬乱的年轻人正在啃食一包东西,他的旁边放着一卷行李,行李旁的一个袋子里裹着一件硕大的伐木工具。我知道,在这座城市北边的山坳里,到处是高耸入云的白桦林,据说那里每年需要大量的伐木工人。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希望从他的手里看到我期盼的那种食物。果然,他在啃牛排,是那种似乎已被人啃食过后丢弃的牛排。那人吃得很仔细,一双强劲的大手很轻易地扳开了一条条肋骨,远远比我的利齿灵巧有力。在靠近牛排脊柱之间的髓腔处,还挂着些许的肉丝,那人先张大嘴嘎巴嘎巴撕咬一阵子,再用手指甲顺着肋骨的边缘细细地去刮上面粘连星星点点的肉丝,每刮下一点点肉便忙着塞进嘴里。每条肋骨啃完后,他再端详一下,似乎又有什么发现。他站起来走到一棵低矮的树下,折下一节小树枝,剔去叶子及树皮,露出一截白花花的木棍,那人用木棍去捅肋骨端脊柱里的脊髓,捅出一点点用舌尖舔舔,再捅一点点,再用舌尖舔舔。我真的很惭愧,想不到牛排竟可以这样吃。我过去吃牛排的时候,需要有人用刀子切割下来肉才可以吃,我甚至忘却了自己还有嚼咬的功能。那人瞥见我蹲守在旁边,先是打量了我一阵子,一脸的惊喜,啧啧嘴,说:“多漂亮的一条狗!”他站起来试图逮住我,或是想友好地向我靠近,我慌忙向后退去。他不好意思地笑笑,顺手扔给我一些他啃食过的骨头,我顿时像是被他戳穿了心,慌乱地跑开了。
我该去哪里?有谁可以提供给我一顿美食——不,只要是干净的食物就可以,我不再奢求得到牛排和威士忌,我不得不降低了我的饮食标准。我顺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着,灯光有些昏暗,而路边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房间里却异常明亮。其中有一扇窗户打开着,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人站在离窗前不远处,他试图再向前一步,无奈他的胳膊似乎被什么东西绑缚着。那人对着窗户大喊道:“请放我出去,我没有病,这些可恶的家伙!”精神病医院牌子上的霓虹灯闪闪烁烁,好像是没有人能听得到他所说的话。
我实在太累了,太饿了,便选了一处僻静的角落躺下。但是,饥饿感折磨得我无法睡去。我的眼前不断闪现着欧式牛排和威士忌,接着又是那个寿司,耳朵里却开始嗡嗡作响,似乎那几条流浪狗依然为那霉臭的食物相互撕咬。我又想起了那个伐木工人,他都能吃别人丢弃的食物,我为什么不能吃?难道他也是流浪狗?不想了,我真的是太饿了,我该放下自以为名贵的架子了,现在只要有人愿意收留我就好了,我心甘情愿为他看家护院,甚至我可以像马驹一样为他拉雪橇干活,只要他能给我吃一顿饱食。但是,街道上还是没有一个人。
大约凌晨的光景,我被一阵闷闷的敲击声惊醒。在马路对面一家饭店门口停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车上装着四个大铁桶,一个人正往桶里倒东西。我惊异地发现,那人竟是尤里。此时,我完全忘记了尤里对我的狂殴,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待我蔫着头走到尤里跟前,他还在吭哧吭哧地搬运那些泔水。尤里见到我先是一惊,但他很快就得意起来。
“噢,可怜的苏卡,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怎么,你也被扫地出门了?活该!早知今日,你当初就不该跟着他趾高气扬的,耍什么威风?”
尤里骂骂咧咧的。见我萎靡不振的样子,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说:“也不能怪你,全怪那个贪婪的鲍里斯,把一个好端端的公司给彻底掏空了。你吃了没?噢,以后我不该叫你苏卡,你是人见人爱的米尔卡。只可惜,你所有的不幸都坏在了所谓的‘名贵’上。可怜的米尔卡,我看你还没吃,瞧你那有气无力的样子。”
尤里举起一桶泔水倒进了车上的大桶子,留下底部黏稠的剩物推给了我:“米尔卡,吃吧,这里虽然没有牛排和威士忌,但也有大鱼大肉的,总比饿着肚子要好得多。”
尤里看我依旧无动于衷的样子,又笑着说:“你这家伙,是不是还嫌脏?我告诉你,倘若我再失去了这份工作,怕是也只能吃这样的东西。”
真是奇怪,我此时竟没有了一点恶心感,反倒急切地想吃到桶里的食物。我完全没有了高傲尊贵的架子,把整个身子探进桶底狂吃起来,那味道似乎远远胜于皇派国际商务会馆的牛排和威士忌。
有了尤里,我很少再有饥饿的感觉,他似乎成了我的第三个主人。不过,因为我每天要探着身子吃桶里的剩物,全身的皮毛已经肮脏不堪,每次靠近人时,都会遭到人们的唾弃或毒打。我开始习惯了流浪的环境,也开始和各种各样的流浪狗玩耍嬉戏,甚至我还和一条奇丑无比的狗做过一次完美的媾和。
我生命里的一次转机是在一个午后。
那天,我照例躲在一个废弃的破沙发里睡午觉。有两个金发碧眼的男人走到我的跟前,捂着鼻子对我指指点点。我已经习惯了应对各种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我并不害怕他们剥夺我做一条流浪狗的权利,或是害怕他们突然给我一顿痛殴。我已经适应了一切,也足可以忍耐一切。
“这条狗的坯子还是上好的!”一个人说。
“应该是只英国纯种的长毛猎犬,还是条名贵的狗。怎么会被主人抛弃了呢?”另一个人说。
我佯装视而不见,懒得去听他们的话。名贵、尊贵、漂亮等等奢华的修饰已经彻底远离我而去,我不再是一条曾经高傲的狗。
“的确是一条好狗,拖回去洗刷干净了,再好好喂养一段时间,一定是一条出类拔萃的狗。”一个人说。
我惊讶地张开了眼睛。难道还有人愿意接纳我?还要给我洗刷皮毛,再喂我好食?我兴奋地抬起了头。
“你看,你看,多么明亮的一双眼!一看这狗相当勇敢,就叫安德烈吧。”
“可她毕竟是一条母狗,怎么能叫这样的名字?”
“在我眼里,狗无所谓公母,我要的是她能创造出价值。安德烈,多么响亮的名字,像是男儿铮铮铁骨,我相信她不会辜负我。”
“好吧,那就叫她安德烈。”
我又有了自己的名字?我是米尔卡,怎么又要改为安德烈?管它叫什么呢,有一个安逸的住所,有可口的食物,叫什么名字都行。我万分感激地望着那两个人。然后,很温顺地钻进了他们张开的口袋。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动物聚集在一起,有猴子、狗熊、八哥、秃鹫、灰狐狸、狼,等等等等。它们各自待在自己的笼子里,神情显得那么颓废。我被一个小伙子带到一处盥洗间,他打开强劲的水龙头对着我一顿猛冲,然后再给我身上打泡沫,接着再冲。待我的皮毛又恢复到过去的光亮,他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在我身上喷洒上香水,再拿一把电吹风吹来吹去。很快,镜子中的我又神气十足光鲜靓丽起来。接下来,我希望得到一顿预想中的饱餐。可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带走了我,把我弄到一个工作台上,固定了我的四肢,然后竟残忍地给我做了绝育手术。我知道,我被诱骗到了一个动物杂耍班子,等待我的将是无休无止的残酷训练,以及一个特制的铁笼。
半个月后,我的伤口愈合了,心里的痛感也渐渐趋于麻木。我开始正式接受各种形式的体能训练,稍有拖沓或是不规范,就会被该死的驯兽师猛抽一鞭子。我是那么害怕鞭子,只得按照驯兽师的指令去完成一个又一个动作。杂耍剧团的老板说,白白捡了这么一个摇钱树,这家伙以后能带来大财运。我俯首摇尾,故意显出真诚遵从的样子,我只祈求他们少一点给予我折磨。
很快,我便登台子了,没想到我第一次出场就赢得了观众的掌声。老板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每天要安排我演出四场,下午两场,晚上两场。其间,我并不能吃一顿饱餐,他们给我的食物总是刚好充饥,我只得通过努力表演,以博得观众的掌声来赚取一点点可怜的食物奖励。
一天,我竟意外地同时见到了杜博夫和鲍里斯,以及坐在他们身边那些风姿颇好的少妇。噢,对了,坐在后边的还有那个士兵克纳普斯。他们似乎完全不认识我,除了脸部的肌肉因兴奋而张合扭曲,看不出一点点对我的惦念和关爱。我不愿意为这些无情无义的家伙出卖力气,所以我当时的表演很糟糕。该死的驯兽师哪里知道我内心的苦楚,他要我给观众下跪,以此来求得他们的谅解。我只得在蛇一样的鞭子环绕下,跪趴在那里,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得意满足,没有一个人为我的屈辱感到悲哀。
再后来,我在表演前,驯兽师总是给我吃一粒白色的药片。这是一种可怕的药,我会在药力的作用下兴奋到了极点,但是那种兴奋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有种奇怪的魔力驱使,我便由不得自己,无论是上刀山或是下火海,我不再顾忌肢体的损伤。尤其是跳阴魂舞时,我的头颅像是被拴了一根魔棒,任由它不停地疯狂牵引来回摆动,直到四肢无力瘫软在地。我隐约听得老板私下里说过,给我吃的药是一种什么兴奋剂。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杂耍剧团,我得离开这里。但是,我在表演之余,一直被困在一个铁笼子里,我如何才能得以逃脱?
尤里又失掉了那份工作。原因很简单,他发现自己每天拉运的那些泔水,竟然被老板制成了地沟油批发给了一些商贩,他偷偷举报了那家鬼作坊。尤里是从满街张贴的野广告上看到我成了动物明星的海报,那上面有我的大幅舞台照,只是我的名字变成了安德烈。虽然我的名字变了,但是尤里一眼就能认出我,就像他一眼能看穿鲍里斯是个披着人皮的狼。
尤里来找我时,我正因拒绝吃那药片而被鞭子抽打。尤里不忍再目睹,他躲在角落里抹眼泪。
或许是因为要过圣诞节,我下午只表演了一场节目就被关在笼子里。杂耍剧团的员工们该上街闲逛的都去闲逛了,留守的几个人聚在一间屋子里喝开了伏特加。尤里一直没有走,他看看铁笼四周无人,便龟缩起身子悄悄爬到我的笼前。我是多么委屈,嘤嘤呜呜地哭了起来,似乎尤里是我唯一的亲人。
尤里说:“可怜的米尔卡,你真是个薄命鬼。如果你在外面四处流浪,危机四伏,又填不饱肚子;若是待在这个剧团里,虽然生活安定,可是每天免不了要遭罪。唉,你说该咋办呢?”
我抓着笼门,吱吱呜呜地哀求尤里放我出去。尤里竟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四下里找来一截撬棍,几下子就撬开了笼门上的那道锁,还伸手把我抱了出来。
我终于自由了。我激动地舔着尤里的手臂及脸蛋,以此祈求他能收留了我。
尤里的两眼早已潮红。他难过地说:“我何尝不想收留你。可是,我好久找不到工作了,妻子又患了尿毒症无钱医治,我现在和你一样,也得四处流浪夹着尾巴做狗。”停顿了片刻,尤里惨然笑着说,“也好,大约就此我的妻子可以有钱治病了。”
多么可怜的尤里!
屋子里突然出来一个人,紧接着那人尖咋咋地喊了一嗓子:“有人偷狗了,逮住他!”
在我仓皇逃遁的刹那,听见尤里说:“米尔卡,快跑!”随后,他便发出了几声狗一样惨烈的哀叫。我躲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看见尤里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他的唇角挂着少许的血。尤里说:“你们别打了,不就是少了一条狗嘛,断不了你们的财路。”尤里抹了一把唇角,又说,“我比那狗的能耐大多了,那狗只会钻个两米多高的火圈,我却能从丈余高的火墙上飞跃而过。我想这样的技能表演,一定能带给你们丰厚的收益。”那些人被尤里的话给怔住了,便把他请进了屋里。
晚上,小广场上早搭起了一堵高约八尺、宽四尺的白桦木墙,并在那木材上浇了油。剧团的人敲响八面威风鼓,鼓声如雷彩旗飘飘。只见尤里裹一身素洁白衣,步履轻盈地走了出来。刹那间,那火墙烈焰升腾灼热逼人。尤里面对火墙高声说道:“好火,好大的火!”随后,他面向苍天放声大笑。
尤里开始活动筋骨,他原地试跳了几次,竟轻盈若燕起落自如。猛然,尤里在人群中发现了我,他向我连连摆手,示意我赶快离去。然后,他倒退了几步,站稳,闭目,深吸一口气。待尤里豁然睁开双目,闪烁如炬,却见他右脚后探尺余,身子作蓄势待发的弓,像一头要骤然出击的狮子。须臾间,尤里脚尖急速点地,双臂挥动,箭一般地跃上了火墙。
熊熊燃烧的火墙轰然倒塌了,火堆里隐约听得尤里的笑声。
此时,我混沌的意识一下子清醒了。我躺在床上,契诃夫的一本书从我的脸上滑落下来。
外面有鸟儿和谐而愉快的叫声,多么明亮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