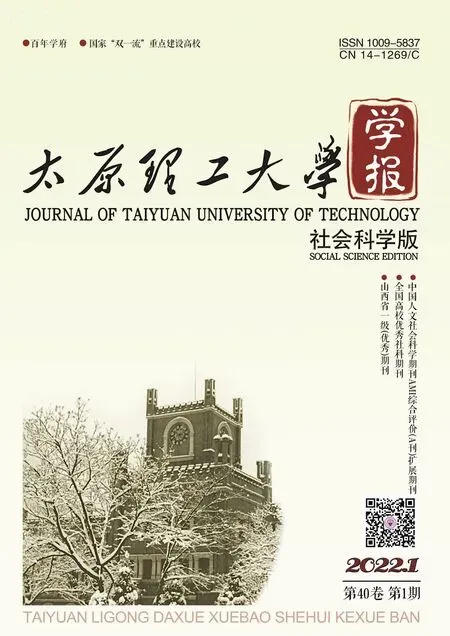遭际生活中的沉思:从当代德国哲学谈开去
——庞学铨教授访谈录
2022-12-16刘晓晓
刘晓晓,路 强
(1.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2.四川师范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8)
采访者:刘晓晓、路强(以下简称“刘”“路”)
受访学者:庞学铨教授(以下简称“庞”)
采访时间:2021年6月18日
采访地点:浙江大学
一、当代德国哲学的重新登场:对日常生活经验世界的关注与沉思
路:庞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德语哲学的译介与研究”顺利结项。当下继续重提德国哲学在我看来是很吃功夫的,因为自黑格尔、马克思以后,以德国哲学为代表的那种体系化的哲学被认为是落幕了。那么,首先我想请教您,在今天这个时代又重提当代德国哲学,其意义何在?当代德国哲学的主要特征又是什么呢?
庞:谢谢!那个项目的顺利结项,得感谢各位参加和支持项目的学者同仁,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对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现当代德国哲学的译介与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及哈贝马斯等几位哲学大家。他们是二十世纪世界级的哲学家,当然值得重点关注,不过,他们的哲学活动一般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前开展的,哈贝马斯稍晚一些。我的哲学学习入门时的方向是古代希腊哲学。1989年,我第一次到基尔大学哲学系进修访学时,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德国哲学界对古代希腊哲学和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文本考证与研究、资料发掘与整理方面,已经做得非常系统、深入、全面。记得当时在图书馆里看到一套希腊大百科辞典的书,摆满了整整一个大书架,目录索引就有十多卷,从目录看,几乎涉及希腊文化的所有方面。同时我也发现,当时一些活跃的德国哲学家对希腊哲学的研究,有一种基本相同的研究方式和路径,就是以自己的理论或观点观照和解释希腊哲学,把古代希腊哲学作为阐述自己哲学理论的思想资源。这种状况在与当时指导我学习进修的老师赫尔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先生及他的两位博士生的接触中有非常直接的感受。先生是德国新现象学理论的创始人,其理论的原则与方法是现象学的,但其许多重要的概念、观点则是对从巴门尼德到德谟克利特,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当然也包括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现象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的重新解读或批判吸收中形成或论证的。那时,国内对现当代德国哲学的译介很少,陈嘉映、王庆节二位先生翻译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刚在1987年底出版,我本人更是没有读过。施密茨的研究方法与路径打开了我原有对希腊哲学肤浅狭隘的认识,也激发起我了解当代德国哲学的愿望和兴趣。通过阅读《哲学信息》《哲学评论》《哲学年鉴》等杂志,我对当时德国哲学研究的情形有了初步的了解,于是给蒂宾根柏拉图学派的创始人汉斯·克雷默教授(Hans Kramer)写信,请他告诉我他认为的德国当代在世的十个重要哲学家的名单及他们的代表作,没想到他欣然应允并很快给我回信,列出了包括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在内的十个哲学家名单。这其中还有一个趣事,就是克雷默教授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名单,为此我写信问他原因,他的回答让我肃然起敬。他说,作为哲学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原创的理论,自己只是研究柏拉图哲学,最多可以算是一个哲学史家。这是德国哲学教授的严谨与谦逊。
我后来分别写信联系了这十位哲学家,请他们提供他们自己认为的一些主要著作。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给我回了信,并且寄赠了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包括哈贝马斯、迪特·亨利希、罗伯特·施佩曼、赫尔曼·吕勃、奥特弗利德·赫费等,亨利希在信中还特别说明,因为他已退休,没有助手帮助打字,所以只能手写。后来,在与我的同事合作主编的两套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中的德国哲学著作有不少就选自这些赠书。于此同时,我也与赫费教授有了较多的联系,并最先将他的《政治的正义性》译介进国内。此后每次去德国,我都有意识地了解这方面的新进展新情况,也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状况的介绍文章。我讲这些,是想说明自己对德国当代哲学的兴趣和了解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在今天重提关注和重视当代德国哲学,是因为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德国当代哲学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和变化,对此,虽然国内哲学界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并做了一些译介工作,但总的看来,了解和研究还是相对较少,甚至可以说还很不够。因此,我们除了继续译介和研究少数几位哲学大家之外,还应该更多地了解、译介和研究当代德国哲学发展的新趋势、新成就,为研究当代德国哲学提供综合的思想资源,拓展理论视野,为汉语哲学界和德国哲学界之间实现实时对话奠定基础。这也许就是你所说的重提当代德国哲学的意义所在。
至于当代德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我的基本认识和判断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变化与发展,当代德国哲学聚焦的问题、探讨的内容和理论的形态,与以往哲学有了很大不同,呈现出实践性、多元化的状况与趋势,其主要特征是哲学的课题和重点出现了向实践方向的转向,面向生活经验世界。虽然没有像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那样的学派领袖人物,但也出现了不少具有创新活力的哲学家和原创性的新理论、新思想,除了哈贝马斯,还有观念论领域的迪特·亨利希、历史哲学领域的赫尔曼·吕勃、法哲学领域的奥特弗利德·赫费、语言分析哲学领域的图根哈特等。当代德国哲学新的形态依然是世界哲学的高地,引领哲学的趋势和发展。
二、德、法哲学对生活世界回归的异同
路:我很认真地读了您主编的《当代德国哲学前沿》丛书中关于生活哲学的著作,对我个人而言,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德国哲学关于生活哲学的著作。我读到这些书之前,更多读到的是法国哲学对生活现象的关注,例如福柯、德里达等,您认为从德国哲学视角关注生活哲学和从法国哲学维度关注生活哲学有什么异同呢?
庞:从这个课题的设计角度来看,我们将整个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分为五个方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哲学。关于德国实践哲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内容,完全值得写一本专门的书来介绍。在实践哲学中有一种相应的理论形态和思想趋势就是生活哲学。我个人觉得,德国哲学维度的生活哲学更多的是运用现象学的原则和方法去考察生活世界,这种考察充分重视和利用了古代希腊以来重要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思想资源,因而更带有德国哲学传统的思辨性、理论性,讲究论述的逻辑性和合理性,总的倾向是建构性、建设性的。而法国哲学维度的生活哲学,关注日常生活的批判,受法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明显,对日常生活现象的描述多一些批判性、文学性和浪漫性,少一点思辨性和逻辑性,尤其是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较深,色彩较浓,因而更多的是解构性而非建构性,有些讨论生活哲学的法国哲学家,本身就主张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所以,从内容上讲,德国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有着更强的理论追求和思辨特征,即使论题很现代、很生活,但讨论和阐述还是基于较抽象思辨的哲思高度的。同样是讨论生活世界的问题,法国哲学家写出的东西,其思辨性的确不如德国哲学家,读一读皮埃尔·阿多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差别,这是理论深度和阐述方法的差别。
路:那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大胆的判断,就是德国哲学对于生活世界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具建构性,而法国哲学则是批判性、解构性更强。
庞:我想大体上可以这么认为。当代德国哲学不管哪一个流派或倾向,都是从传统哲学中寻找思想资源,而欧洲传统哲学的主导是理性主义,这些思想资源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思辨性特征。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古代哲学的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当然包括柏拉图;近代哲学的代表人物就是康德。所以,不管是实践哲学还是现象学的新形态,抑或其他哲学倾向,都有着较深刻、系统的理论思考,有较强的思辨色彩。而法国哲学家们则是继承了浪漫主义的传统,受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解构主义的影响深刻,因此,他们对生活世界的描述也就有了其独特的风格与特征。
三、当代德国哲学的基本特点:运用传统思想资源解决当下生活世界新问题
刘:说到德国哲学,我们总会想到与分析哲学之间存在的那种分歧。今天也有学者指出,分析哲学的高潮已经过去了,甚至呈现出一种明日黄花的状态。我们都知道,分析哲学产生于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乃至否定。如果从比较的视野来看,分析哲学在当代逐渐走向式微,是不是恰恰意味德国哲学传统在当代的复兴呢?
庞:恐怕不能讲分析哲学的式微意味着德国哲学传统在当代的复兴,也不能绝对地讲分析哲学产生于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乃至否定。
从当代德国哲学思潮的发展看,分析哲学在其中确实呈现出比较弱的状况。分析哲学作为英语哲学界的主流,往往被冠以“英美”二字。但分析哲学的奠基者,如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都是用德语写作的。实际上,分析哲学家如弗雷格与德国传统哲学特别是新康德主义有直接的关联。由于纳粹政府将这些分析哲学的先驱们大都赶到了美国,造成了分析哲学在德国的式微,但可以肯定,分析哲学在德国从来就没有被完全遗忘。二战后,分析哲学思想在一些大学如哥廷根大学、埃尔郞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得到重新研究和传播,特别是海德堡大学的图根特哈特(后来到了柏林自由大学),从原来的现象学研究比较彻底地转向分析哲学,他在自己的著作《语言分析哲学导论讲座》中,认为分析哲学是比传统哲学和现象学更好地研究哲学的方法。他对分析哲学在当代德国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表现了欧陆人本主义哲学和英美科学主义哲学汇通与融合的状况与趋势。可以说,分析哲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式微后,在当代德国哲学中呈现出明显的复兴状态。但是,一方面,这种复兴在理论形态上并不是纯粹英美式的,而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意识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的汇通与交融;另一方面,这种复兴与实践哲学的复兴与发展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当代德国哲学出现了五个主要的趋势和倾向,除了分析哲学,还有实践哲学、现象学的新发展,意识哲学的新诠释和跨文化哲学。从整体来看,分析哲学属于其中比较弱的一个趋势。
刘: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当代德国哲学虽然继承了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精神,但是已经不那么体系化了,而是强调对实践生活的解释的有效性。
庞:的确,有人说,黑格尔是最后一位伟大哲学体系的创建者,黑格尔之后,作为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而存在的哲学消亡了。不过也有例外,被人称为“现象学异端”的新现象学家施密茨和结构存在论的创立者罗姆巴赫,仍致力于建构庞大综合的哲学体系。正如当代德国著名现象学家瓦登费尔茨说过的,在当代德国现象学圈子里像赫尔曼·施密茨的多卷本《哲学体系》或者像海因里希·罗姆巴赫的《结构存在论》那样一种对“一门无等级的形而上学”的庞大综合实属罕见。
同样可以说,当代德国哲学注重面向生活世界,强调对实践生活的哲学阐释。其实,当代德国哲学尤其是实践哲学趋势,总体说来,还是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特别是它们的实践哲学的原则和方法也部分地吸取了黑格尔的思想资源,当然,还有现象学的方法,用来对现实生活世界如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问题、全球化的实践问题,以及社会、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伦理等方面的各种重大问题,做出哲学的解释和理论的概括,相应地,形成了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技术哲学、心理哲学等等。
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代德国哲学放弃了原来抽象的东西,而是转向对具体的非常实在的生活的关注,并且以德国哲学特有的理性,严谨看待生活世界。
庞:如果说当代德国哲学“放弃”了什么,那便是放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那些论题、命题和论证方式,以及围绕它们进行的争论。当代德国哲学家们关注的是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是生活世界中具有普适意义的重大问题,并非那些“具体的非常实在的生活”——如果你指的是日常生活层面上的那些“具体”“实在”的事情。当代德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实践哲学家,也是一个技术哲学家,叫汉斯·伦克(Hans Lenk)。他提出当代哲学要承担十项任务:(1)实践哲学可以承担起哲学的一般任务;(2)哲学必须依据社会生活及其变化,提出道德标准,评价道德规范,但是并不能提供道德系统的最终原则;(3)哲学研究不能完全与科学及生活实践分离,必须进行跨领域跨学科的合作;(4)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与渗透,有助于纯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5)审查和批判性地讨论哲学基本前提,对于哲学的特征和思潮的长期作用是必要的,对于其他意识形态摆脱危机是必需的;(6)在追求世界最后根据的形而上学希望落空以后,哲学的迫切任务是充分表达关于社会的指导观念和结合实际的纲领;(7)哲学有必要负起新的社会和公众义务,提出新的纲领性观点,创建专门领域如经济、计划、技术等哲学;(8)哲学要为科学提供一种超越经验科学的方法,描述科学、价值和规范领域的基础问题;(9)哲学家之间要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10)哲学家需要进行一种新的公众工作,去除晦涩的学院式语言表述和德国式的深奥论证。
从这十项任务来看,就是要使哲学(当然也包括当代德国哲学)抛弃形而上学传统,脱离那种抽象、晦涩的体系化的理论形态。这十项任务把德国当代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可能的理论特征都描述出来了。这说明德国哲学家对当代哲学的转向及其可能路径的意识,已经达到了比较自觉的程度。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套丛书中已出版的一些书,无论是论证还是语言,那些晦涩的东西已经比较少见了,很少有板起面孔教训人的东西,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性、对话式、讨论式的论述。
四、打开中西哲学交流的新视域
路:众所周知,曾经的德国古典哲学是拒斥东方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曾明确否定中国有哲学。那么,立足于当代德国哲学的这些新变化,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场域来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或者东西方哲学的相互借鉴呢?
庞:其实当代德国哲学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资源,又突破了古典哲学的局限,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实际上已抛弃了“欧洲中心论”的旧观念,开始意识到了东方哲学——当然包括我国古代哲学的合理性与价值。这种开放的哲学态度,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很明显了,大家都知道他对《道德经》的态度;在当代德国一些哲学家那里这种哲学态度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表现。比如,新现象学家施密茨在讲身体问题、印象问题时,就谈到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学说所体现和象征的整体性印象观念,谈到古代中医以经络为网络和纽带的身体问题,中医的把脉诊病问题,以及中医煎药、喝药讲究时辰问题等。他有一本演讲集叫作《新现象学》,很薄的小册子,其中第一篇文章就专门说到了这些问题,表达了对中国古代医学等的认可。我想,放弃了哲学“欧洲中心论”的旧观念,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这就为我们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提供了新的场域,也为相互借鉴打开了新的可能和通道。现在,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步子在进一步加大,中西、中德哲学交流也更多更顺畅了,不过整体来看,中西哲学的相互了解、交流和对话还不够。无论是德国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还是我们对当代德国哲学的了解,都还不充分,还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相互了解,提供综合性的思想资料,也是我们组织出版这套《当代德国哲学前沿》丛书的初衷。
刘:除了中国哲学以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因为按照传统的理解,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某种“终结”,但是从我个人来看,马克思的哲学毕竟是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继承而展现出来的,因此,我觉得要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完全把马克思抽象出来,而是应该将其放到德国哲学发展的背景中来分析,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浅见。那么从您对德国哲学,乃至于对当代德国哲学发展的了解上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马克思哲学是否能在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呢?
庞:首先,我赞成你说的关于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哲学关系的认识。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来源,当代德国哲学应该也能够为马克思哲学的发展提供启发,或者说“找到新的生长点”。对此,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简单说明。
其一,马克思哲学不仅与德国古典哲学有着思想和逻辑上的联系,是德国哲学发展中的重要环节,而且与包括现当代德国哲学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基本相同的理论目标和哲学史意义,即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进而克服由这种范式所决定的近代哲学的特征和传统。因此,二者在哲学课题与视域、主体与对象关系及主体自身意义等重要哲学问题的转变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可容性,就是说,二者存在着对话和交流的基础,而实事求是地展开这种对话,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我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文章中,比较具体地论述过上述观点。
其二,当代德国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世界,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换句话说,它与马克思哲学仍然有着共同的思想资源,这也决定了二者在理论内容上仍然有着许多共同点,如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意识自主性、自由意志、实践与理论等方面的观点。而且,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些思想、原则和方法在一些重要的当代德国哲学家的理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赫费是当代德国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他在讨论其法哲学和伦理学理论时,便不时地引用马克思的观点。可以说,研究当代德国哲学的一些哲学家有选择性地接受了马克思哲学的许多内容,这实际上是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话在当代的新表现新内容。
其三,马克思哲学必然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就世界范围而言,当代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德国哲学面临着同样变化了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世界,因而也会面对基本相同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无疑会在问题域、理论观点和论证方法上给马克思哲学的新思考新发展带来启发,马克思哲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和发展中显示出自身独特的理论价值。在看待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德国哲学的关系上,我们要有历史主义的视角。
五、哲学交流的基础:深刻关注人的生活世界
路:那么我们回到对德国哲学本身的研究中来谈,立足于您主持翻译的这套当代德国哲学前沿丛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今天的学者去关注的问题呢?特别是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如何从当代德国哲学中找到理论的生长点和创新点?
庞:这套丛书的主体是译著,其中有一本是研究性的文集,定名为《当代德国哲学述评》(以下简称《述评》)。《述评》分为两编,上编分七个方面比较系统地综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概况,包括:分析哲学在当代德国的研究与传播、当代德国实践哲学的发展、当代德国现象学的实践化转向、当代德国哲学中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研究、黑格尔复兴运动、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德国古典哲学自我更新运动和当代德国美学综述;下编是当代德国部分重要哲学家的思想述评,根据现有可能,选择评述了16位哲学家。当然,上述七个方面和人物并没有完全涵盖和呈现当代德国哲学的全部面貌,只能待有机会时补充修订。尽管如此,透过《述评》大体上可以了解和把握当代德国哲学的基本状况,并可以得出这样的研判:在德国哲学的当代转向中,哲学家们仍然坚守着哲学的批判精神,发挥哲学的批判力量,展现出了原创性研究多元化的趋势,在许多重要领域和方向上,继续引领着世界哲学发展的潮流。从总体上看,我觉得当代德国哲学和传统德国哲学有如下几点区别。一是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不同。以往的德国哲学,包括老一代现象学家胡塞尔,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主要是意识,这也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直至康德、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意识论哲学的对象和主题。当代德国哲学则转向了现实生活世界领域、实践领域,是对人的生活世界和实践活动的深刻关注。二是论证方式有了很大转变。传统哲学主要是思辨的、演绎的、抽象的论证方式。当代德国哲学的阐述和论证,虽然也有运用这些方法,但更主要的是采取现象学的描述方法、直观方法,不再是概念到概念的演绎。三是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有很大差别,绝大多数当代德国哲学家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抽象问题的研究和晦涩的学究式的语言表达。哲学从内容到语言,从抽象晦涩的云端回归人的生活经验世界,离现实的人及其生活更近了。
路:如果在这里加入一个法国哲学的视角,是不是也可以说,在当代德法之争变成了德法融合了?
庞:对法国哲学,尤其是当代法国哲学,我了解很少,不敢乱说。当代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曾说过,当代法国哲学有游牧民族气质。我的理解是,在表现形态上,法国哲学追慕偶然性和可能性,试图以狄奥尼索斯式的游戏与放纵突破现有各种约束,是文学化、浪漫化的哲学书写。这与德国哲学,包括当代德国哲学(叔本华、尼采和后期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表达除外)那种严谨的、逻辑性的哲学书写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德法之争,不是泛指意义上的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之争,而是指解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和解构论代表人物德里达1981年的巴黎论争。这次论争深刻表达了解释学和解构论之间的异同,从中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解释学、解构论及海德格尔之后的哲学走向。说在当代德法之争变成了德法融合,恐怕不太恰当,两国哲学始终具有各自独立的创造力、各有特色的语言表达形式和独特的气质风格,彼此争奇斗艳,相互批判也相互借鉴。一方面,当代法国哲学的创造精神及其丰硕成果,引起了哲学界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注意和重视;另一方面,德国哲学中的深刻思想,一旦被法国哲学熟悉和掌握,便被加以改造并转变为新的哲学形态和思想。正是这种相互交流与借鉴,推进了当代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新发展。不过,德、法两国哲学的这种交流与借鉴关系,在当代的表现形式有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德国哲学对法国哲学的影响更深刻更全面。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著名的当代法国哲学家,都从德国哲学中得到过深刻启示,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德国哲学的烙印。换句话说,凡是取得重大创造性理论的德国哲学家,都受到了法国哲学家的重视。其中,对他们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是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进而使他们能够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那儿汲取思想和精神力量。
刘:还有一个问题是想听您给当代年轻人哲学研究的建议,也就是您认为应该着眼于哪些问题的研究呢?
庞:目前国内的外国哲学研究在路径和方式上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著名哲学家的文本研究,包括文本翻译、内容解释、概念诠释及由此引申开来的相关研究,如概念史和思想史的梳理与研究等,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是目前外国哲学研究路径和方式的主流;另一类是关注哲学的新发展,依据生活世界和实践的变化拓展哲学的新领域新方向,包括学科或问题的交叉研究,这一类研究相对较少,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较多。当代德国哲学家中后一类居多,他们以关怀人类当下和未来的情怀,从哲学上深入思考与探讨生活世界新领域和社会实践的重大问题,提出各自的理念和观点,乃至展开激烈的争论。例如,作为当代德国实践哲学最主要的学派之一的里德尔学派,其中许多人物在当代德国哲学舞台上非常活跃,很有影响,但他们对同一问题会提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形成自由而活跃的学术争鸣。所以,如果说建议,我想年轻学者在积累了一定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要多关注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译介和研究其中有影响的哲学家,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和方法,汲取和利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新成果,有意识地关注和研究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实践的变化,对哲学提出新的问题,拓展可能的新领域。这样做对于拓展哲学领域,推进哲学发展,应该是有益的。当然,这要根据各自的兴趣和可能而定。
路:那么,您认为这种问题和研究拓展应该朝那个方向进行呢?
庞:我个人的看法是首先应该关注社会实践领域。实践领域很广,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比如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生活哲学领域的某个或若干个问题。其次关注的领域或方向是伦理学。中国传统哲学特别重视伦理问题。在伦理学方面,当前面临许多新情况,比如观念模糊、规范混乱、行为失范等,需要借鉴当代西方哲学,包括德国哲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来完善乃至重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伦理理论。再次是关注当代技术对人类自身及其未来生活的深刻影响,哲学应该也有可能在这方面起到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