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思想的分析比较
2022-12-14卫蕾
卫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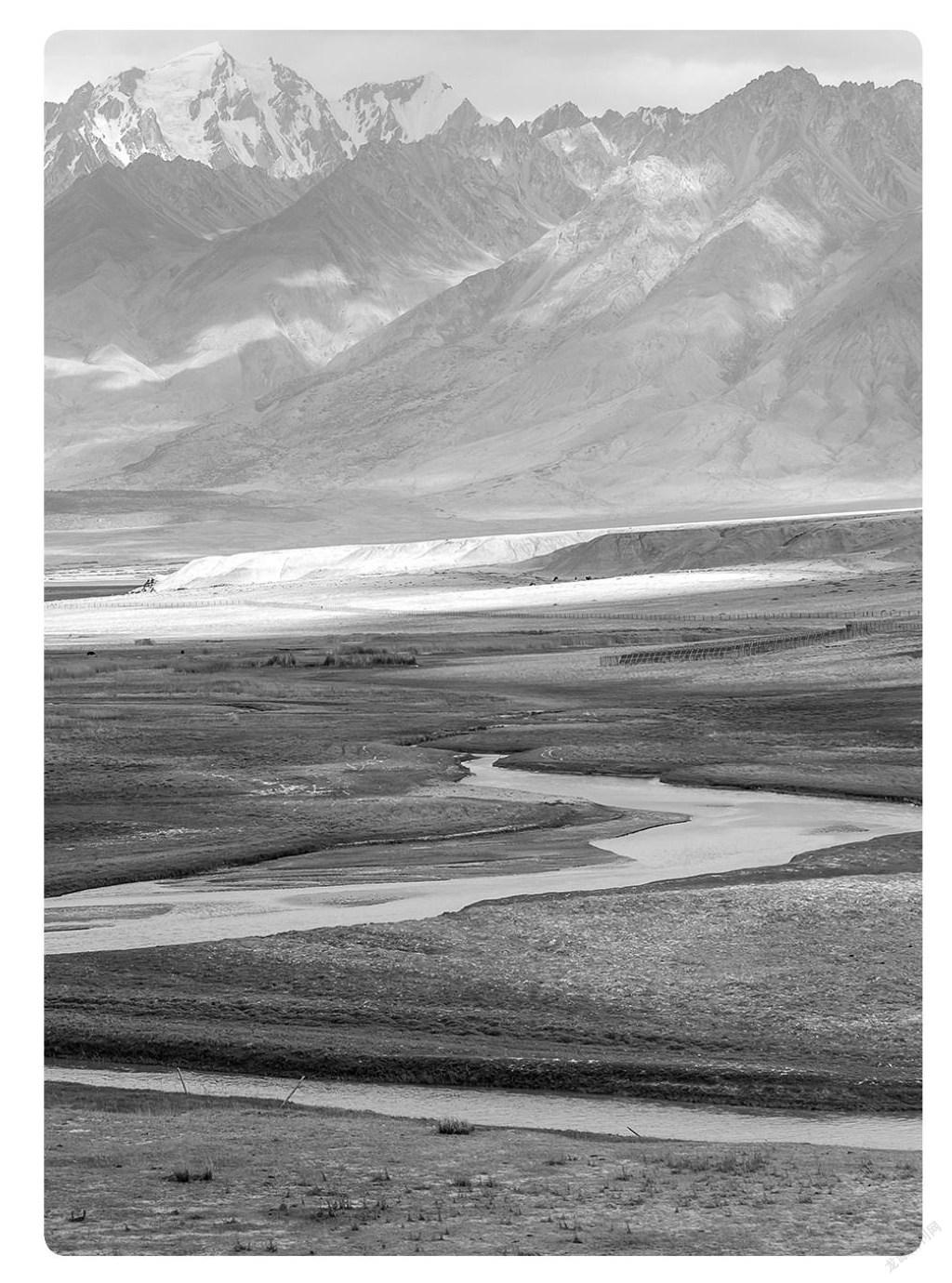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西方女权主义的代表,而张爱玲则是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和女权运动的先驱。作为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女性作家,她们创作了许多女性人物,她们对女性历史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抱以极大的不妥协态度,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张爱玲的主要特征。从她们的著作中对女性主义的剖析和对比,能带给现代女性一些思考,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伍尔夫作品中的女性思想
(一)思想产生背景
伍尔夫出生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典型父系家庭,在很小的时候就遵守着严格的社会礼节。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常常被看作是“家庭天使”,因为她们不得不处理大量的家务和财务。但是,身处于父权社会,男人仍以“女性的最高天性就是为男性服务”这一原则来治理家族。男人对女人的不屑以及母亲的过早死亡给伍尔夫带来了一个自由发展的契机。20世纪初期,英国的妇女意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变革,女权运动已经达到了顶峰。伍尔夫是西方女权运动的见证者,她对妇女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二)女性思想的表现
伍尔夫的《出航》《一间自己的屋子》《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等众多作品中都反映了伍尔夫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伍尔夫通过深入的女性视野,积极寻求女性创作的方式,探寻女性文学创作中不断追寻的女性创作,并由此展开了对女性的精神与内在的两性关系的探寻。伍尔夫对妇女文学传统的重视,对妇女的创作起到了鼓励作用,从而突破了男性话语的统治地位。同时,她对传统的妇女形象提出了批判,并坚定地认为,妇女的创作具有强大的威力。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写道:“一个女人应该有自己的房子。天性是女人独立的象征。因为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力,才能租到或者买下这房子。在这间被锁着的屋子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以往的女性主义运动大都是以男性的社会权力与话语形态为参考,而忽视了女性主义的社会文化。比如,《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简·爱,她在财政上获得了独立,呼吁两性平等。然而,不难发现,她对罗切斯特的感情依恋仍然是父权制社会中妇女的不幸,她寻求的是对男子的平等,或者说,这并非“自觉”的妇女运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正是女性主义的宣言。
伍尔夫注意到,18世纪之前,妇女的著作寥寥无几,而历史仅仅是男人的历史,没有女人的身影。女人不能参与到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去。所以,她认为,女人应该寻找一种独特的创作方法。1928年,伍尔夫在剑桥大学演讲:“女性要想写作,每年要有五百英镑,还有一间可以上锁的自己的房间。”一年五百英镑代表思考的力量,门上的锁代表独立思考的力量。《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最后一页写道:“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但你们不要去锡德尼·李爵士的莎士比亚传里去找她。她年纪轻轻就死了—可惜,一个字都没来得及写……我相信,这位从未写下一字、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还活着。她活在你我之中,活在许多其他女性心中,她们今晚不在这儿,而是在刷洗碗筷、哄孩子睡觉……我相信,等我们再活上一个世纪—我说的是人类的共同生活、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小小人生,等我们有了一年五百英镑和自己的房间;等我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勇于写下自己心中所想;等我们稍微逃离公用的起居室,学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现实的关系看人;等我们学会从事物本身看天、看树、看一切;等我们越过弥尔顿的亡灵,再也没有人能遮挡我们的视线;等我们面对现实,因为这就是现实,我们沒有臂膀可以依靠,只能自己前进,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和真实世界的关系,等到那时机会就来了,莎士比亚死去的诗人妹妹将会唤醒她沉睡的躯壳。她会像她的哥哥那样,从默默无闻的先驱者的生命中汲取力量,然后重生。”
伍尔夫作品的创作意义在于对女性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为女性主义发声,其作品对于现代社会针对女性主义的剖析与对比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于当代读者重新思考女性命运和女性主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参考。
二、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思想
(一)思想产生背景
五四运动时,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成为不少进步女性效仿西方国家的口号,而张爱玲的妈妈则是第一个从腐败的封建官场中逃离出来,成为到英法求学的新女性。但她接受的教育是在父权制的许可下,依赖于家庭的财政援助。所以,她反对男权社会的斗争很不彻底,却给中国女权运动带来了很好的开端,也给张爱玲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张爱玲和她以后的作品都显示出了浓重的女性意识。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张爱玲的书写风格、主题、语言和社会意识,不论是从20世纪40年代还是今日的女性主义者来看,都属于较为温柔敦厚的类型,甚至是相当消极的一种书写。此种张爱玲作品的风格取决于作家本人的虚无精神,以及作家对个人命运的探索态度。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张爱玲目睹了太多的人生变故和匆匆的人生经历。她描绘出来的女子,都是真正的女性,哪怕是丑陋、诡异、压抑、疯狂,但这并不是张爱玲故意的。这一大胆的“女性自我”的写作方式,表明张爱玲的作品突破了“性别错位”的约定俗成,在男性主义中战胜了“阉割”“去势”的内在心理。
(二)女性主义色彩
在中国历史上,以男权文化为主的历史时期,妇女始终只是男权社会的一个客体和附属物。而张爱玲在几乎失语的女性语境中,以一种鲜明的女性意识来进行创作。张爱玲放弃正面的写作方式,是对传统的男性文本的抛弃,也是对当时统治者的叙述的抛弃。在张爱玲的独特的女性写作中,她大量描写了自己的经验、历史、声音和欲望,而不是单纯地跟随着父权制的思想,更不会去模仿男性的文字,这同样是一种反抗、破坏和解构父权制的文本。
她的独特的女性意识与女性自觉,更多的是一种女性的抗争与迷茫。但是,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女性写作的色彩,深刻地关注着女性的生活状况。张爱玲是中国当代女作家,她一改以往以男性或父系为中心的文学传统,从女性的角度描写了女性的内心世界,抒发了自己的情感与想法。她既关心女性的精神世界,又探究了男性权力社会中的奴仆关系。
(三)作品分析
《连环套》里,十四岁的霓喜被贩卖到一家丝绸铺的雅赫雅老板手中,而她与他同居十二年,但一直没有成为他真正的妻子。霓喜的合法请求没有得到丈夫的同意,反而遭到了暴打。雅赫雅得知霓喜和崔玉铭的关系后,身为家长权威象征的丈夫就把霓喜赶出了家门。“你再不走,我就刺瞎你的眼睛!”这是一个男人在“妻子”面前的横行。这是父权制给男人的一种权利,也是女人被虐待的命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充满了对男性社会权威的反抗和嘲弄,她笔下的男性角色被有意识地矮化了,这也反映了经过长时间压迫的中国女性开始对男性引以为傲的地位和体力提出了质疑。
张爱玲的女性形象,无论处于何种文化状态,都是没有逃脱传统社会制度的女性。她们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不用担心自己的生活,但她们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想讨好男人,博得男人的好感。在这样的社会中,对女性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在她的作品中,像《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她是一名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从一开始的独立,到后来逐渐依赖于一个男人,最终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对象。
张爱玲笔下也有很多处于他者、边缘地位,但尚未丧失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形象。例如,《花雕》中的郑夫人不断告诉她的四个女儿:“要好好念书啊,一个女人,要能自立。”《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虽然依靠不少男人,但依旧展现出女性自主的气魄。“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在主体与他者之间,女性的声音摇摆在历史与文化的不确定性之中。她们忽而坚强,忽而歇斯底里,时而作为主体,时而扮演他者。这是一种具有多种特性的女性嗓音,被视为是真实的女性嗓音。蛮荒世界的女人,可不是别人想象中的野蔷薇,她有着一双大眼睛,比男人还要强壮,拿着一条鞭子,一鞭子下去,就能把人打趴下。这只是城市里的人想要新鲜的东西,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未来的荒原上,只有那些破落的砖瓦和破墙,她才能安然无恙地生活,无论在哪个时代,或是在其他社会,她都有自己的家。
张爱玲的创作意义就是揭示了父权制和女性传统的深层意识:以内审意识取代了狂热的口号。这就使她的作品能够深入到妇女内部的创伤之中,孜孜不倦地描绘出中国传统女性的“荒芜”与“干净”。张爱玲的一大成功是:她竭尽全力地揭示了女性意识中的扭曲心理,揭示了女性的自我觉悟,以及她们反复体验的曲折过程。
三、两者女性思想的比較
(一)家庭背景
伍尔夫与张爱玲出身的家族,是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父权制社会的一个缩影。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她们的女性主义观念都是由家族所决定的,她们在菲勒斯中心的压力下,产生了反叛的心理。不同之处在于,张爱玲的妈妈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对张爱玲进行了积极的指导和支持,促使她敢于与封建家族分道扬镳,而伍尔夫的妈妈,则在另一面让伍尔夫感受到了解放妇女的迫切。
(二)时代背景
19世纪到20世纪,妇女们的斗争大多集中于家庭,因此伍尔夫与张爱玲总是将她们的创作重心集中于妇女的家庭问题上。女人要在社会上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就必须放弃对男人的依赖与顺从。在西方,女人常常被描绘成“家庭中的天使”,她们会以“自我”来换取男人的利益。在中国,女人要担当“贤妻良母”的角色,女人要有耐心和温顺。伍尔夫的女权主义主张更多地建立在对西方理性文化的质疑之上,而张爱玲却有意要动摇中国数千年来儒家的统治。
西方近代文明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提倡用理性来压制人类的欲望,追求真理。这一“理性至上”为西方男性化的理论依据。这也为男人们轻视女人提供了一个理由。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描绘了拉姆齐一家的形象。拉姆齐性格古怪,个性僵硬,被认为是父权制社会中最杰出的哲学家和理智的化身。拉姆齐夫人体现了人性的丰富和高尚的品格。与刻板无情的拉姆齐相比,拉姆齐的夫人在客人、朋友和家人之间传递情感,建立稳定的关系。拉姆齐对感情存在的重要性置若罔闻,他对女人的幻想深恶痛绝,却无法摆脱感情的安慰。拉姆齐夫人以人的想象力来支撑这个充满感情与希望的世界,伍尔夫则以一种嘲弄的方式来推翻理智与情感之间的阶级关系。《到灯塔去》里的灯塔正是理智和感情矛盾的终结。在这种类型的作品中,伍尔夫试图寻找一条合理的道路,以实现男女两种不同的情感与原则,从而实现一种有机的协调。拉姆齐依靠他的夫人,这说明他的理性并不能左右他的情绪。理智并非真相。如果没有感情,这个世界就会消失。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认为人、家庭、社会和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天地是一体的。在家庭中,“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将女性囚禁在从属地位上。儒家文化是一种宗法文化,以宗法为外在表现。《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很彻底的人物。她是男权文化的受害者。由于姜二爷的残疾,她“幸运”地嫁到了姜二爷的家,但由于她的出身和她的丈夫,她在这个庞大的封建家庭中一直被鄙视。曹七巧说话粗鲁,举止怪异,甚至引诱了他的小叔子。任何违背父权制文化的事情她都敢做。这就是为什么有一节是关于分家时,当每个人都对九老太爷如何划分保持沉默时,只有曹七巧表达了她的不同意见。曹七巧伪装成一个可怕的女巫和恶魔般的女权主义形象进行她的生存和发展,但她毕竟还是抗争了,在爆发中显示了女性的力量。
伍尔夫与张爱玲都是中西合璧的杰出女性。她们都站在一个明显的女性立场上,真实而又深刻地关注着女性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和肉体体验。尽管她们在性别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是她们对妇女的看法是一致的。伍尔夫通过对女性文学的深入研究,积极寻求女性写作的方式,并由此展开了对女性自身与两性之间的关系的探究。张爱玲在批判男权文化对妇女身心的压制的同时,也从女性本位出发,深入地检视着女性的种种心理疾患和人性软弱。
自女权运动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无论是伍尔夫还是张爱玲,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思维方式,为妇女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