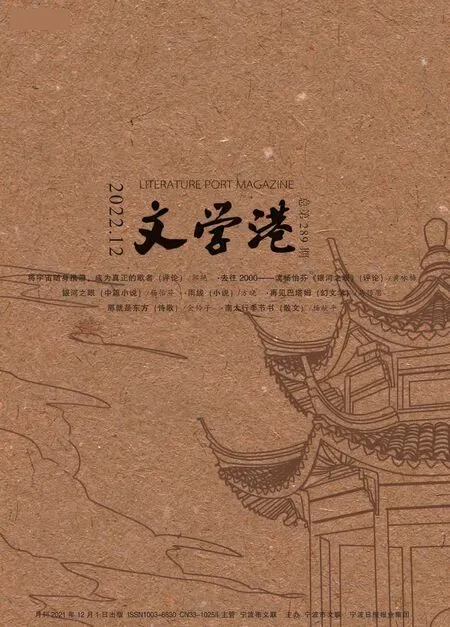梅雨过后
2022-12-13□洛水
□洛 水
江南的梅雨季缠绵了一夜又一夜,就算有几个出晴的好日子,晚上的月亮也是雾蒙蒙湿答答的,像拢了一床奶白色的旧蚊帐。
舒兰就斜躺在这样的月色里,姿势撩人、妩媚。她弯着一只胳膊肘,枕住巴掌脸,另一只手懒洋洋地晾在光线里。一头沉香黄的长卷发,从她右侧脸上散下来,盖住睡意惺忪的眼。窗外栽了一株栀子花,前几日喂饱了雨水,又在黏稠的月光中浸了一夜,显得越发鼓胀。花朵轰轰烈烈,爬满整树枝桠,白的瓣里略带黄的蕊,连花香也像被谁点了把火烧着了似的,从纱窗中溅进来,溢满整个房间。
一双男人的手在她身上游走,悄无声息,像深水中的一尾鱼。背对着月光,她身上只着一件石青色的真丝吊带睡裙,贴在肌肤上,裸露出光滑的颈项和背脊。男人的手一触碰到她,她整个身子都颤抖起来,仿佛血液里暗藏了一道洪流,突然找到罅口,不管不顾地汹涌开来。她压制住颤栗,把脸匍匐到他怀里,接着是整个身体,几乎要把自己的身子镶嵌进他的身体里,以此告诉他内心深处酸的辣的欲望。
她在城区的一所高中教语文,今天有一堂早课。她照例是第一个到,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走廊上,斜对着门望过去,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教室,准备早自习。积了一夜的浊气,房间里闷闷的,她去推临南的窗户,天边刚升起太阳,圆饼似的,红彤彤一轮。照这天气看来,恐怕是要出梅了,她想。她对着这样的好天气发了一会儿愣,将办公桌上一盆龙舌兰端到窗台,放在太阳底下。只要等上半刻钟,天边的胭脂就会融化,暖洋洋地洒到龙舌兰的尖叶子上了。办公室的英语老师陈萍,开一辆红色宝马,从满地的梧桐叶上穿过来,绕到办公楼下的车棚里。她眼尖,一抬头便看到了她。她的宝马车停在舒兰的国产红旗车边上,两辆车肩并肩,她的红旗车自然就显得笨拙而老土。但一想到昨天夜里,想起她的爱情,她的脸上又堆起无声的笑。她对物质倒并不是顶渴望的,她感觉快乐,认为有这种感觉就足够了。
她有些轻蔑地盯着楼下的陈萍。陈萍一只脚先从车里探出来,姿态优雅,趿一双烟灰蓝刺绣布鞋,然后是及肩的卷发下妆容精致的脸。她穿同色系的绸织连衣裙,领襟很大,扭着屁股,从车棚一路走过来,一边走一边从包里捻出一块丝巾,细织花的橘粉色,风一吹,晨光里一照,似乎镀了一层若隐若现的金边。她很是随意地将它绕着脖子打了个结,那大领襟的胸口,便像趴了一只振翅欲飞的鎏金蝴蝶。舒兰突然记起一件事情,同办公室的张美娟有一回曾在背后偷偷骂陈萍不要脸,还要叫她不得好死,仿佛是为了年终评先进的事情。想到这些,她又在心里哼了一声。
她在窗口专心致志盯着陈萍,连王福川从背后悄悄走进来都没发现。王福川是历史老师,坐在舒兰斜对面。在这个办公室里,几个同事当中,舒兰对待王福川的原则是保持适当距离,不近不远,不生不疏。王福川是个有性格的人,异类,教的是历史,却对正统的历史很不以为然,时常冷嘲热讽,书呆子一个。他认为教科书中绝大部分是编出来愚弄老百姓的谎言。这样的想法,一般人在内心里想想也就算了,他却又是个嘴里藏不住话的人,心里那样想,上课的时候,当着讲台底下那么多双求知若渴的眼睛,也忍不住表露出讥讽和不屑,往往兴致一来,便抛开书本,讲一堆对学生升学考试没有多少用处的胡话。那些话传来传去,学校里人多口杂,被别人听了去,免不了在同事之间刮起一阵风,这风吹到校领导耳朵里,他便又遭批评又扣奖金。舒兰总担心他有一天闯出大祸来。
王福川把公事包往桌子上一扔,也走过来往窗口望了两眼,边看边同舒兰打趣说,我知道你大清早的在望谁,你在望我们的小向帅哥是不是?舒兰回过头来朝他笑了笑,也不说话,径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去了。在办公室,她很少开口说话。许多事情,最多云淡风轻笑一笑,就完了。她是一个冷眼旁观者。过度的冷漠使她变得内向、多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忧虑。这点恰好与王福川相反,王福川是个没有心肝无所顾忌的人。
舒兰从小在乡下长大,大部分时间待在方圆几十里渺无人烟的村子里,见得最多的人是父母兄妹和左邻右舍。这些人的面孔是同一个模样,没有多少区别。她父亲,爱喝点酒;母亲,一心扑在儿女身上。她见惯了父亲和母亲的沉默,也遗传了那份沉默。她想只有一点是不能够的,是无论如何都要站出来说话的;她知道他们存了一份私心,到处帮她物色有钱人,但她有自己的想法,她跟她母亲不同,是断断不会为了钱,去找个不爱的男人,把自己的一生就这么不明不白打发了。
她打了半盆子水,浇花,擦桌子。平常他们都是各家自扫门前雪。舒兰抹完自己的桌子,就要去倒脏水,王福川一脸神秘,凑到她跟前,吊儿郎当地说,舒老师,你擦完了自己那张,我的这一张也顺便擦一擦呗,你帮了我,作为交换,我告诉你一件刚刚发生的秘闻。他话未说完,陈萍和张美娟一前一后走了进来。舒兰知道,她在办公室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没有其他几位资格老,她要是帮王福川抹了办公桌,不帮其他几位收拾,肯定又要遭来他们的一通玩笑,他们这个办公室,向来是最八卦的。她把脸一仰,故意大声说,你肚子里能有什么秘闻呀,要是真有,说出来我们大家都乐一乐呀。张美娟和陈萍听说有秘闻,也闹哄起来,几个人凑到王福川跟前去了。王福川点了根烟,卖足了关子,才说,他有个朋友告诉他,昨天夜里,局里有位领导给纪委请去喝茶了,还牵连了几位女教师,市里正准备顺藤摸瓜,好好整顿一下风气呢。
他们办公室总共五个人,二男三女,小向还没有来上班,现在王福川这么一说,倒像是他一个男的故意揶揄她们几个女的。张美娟心思转得快,不等王福川咽下话,就咬牙切齿地说,是该好好查查,把那些狐狸精一个个揪出来,叫大伙儿认识认识。陈萍听张美娟指桑骂槐,大概也在心里想,这种事情,谁都有嫌疑,自己虽然结了婚,孩子都大了,但这会儿要是不站出来,捍卫上两句,难免落人猜疑,于是也慌忙说,现在的人,一个个都是不要脸的,特别是那些小姑娘,为了钱,正正经经的男朋友不谈,宁愿去当什么小三小四。
舒兰本来没在意,听了陈萍一顿骂,脸上也不知怎的,没来由地火辣辣起来。舒兰年轻、未婚、模样又长得好,虽然早已过了二十五岁的年纪,但平时保养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她本来就不善言辞,心里又确实瞒着一些事情,陈萍一骂,那些话像根鱼刺卡进她喉咙里,噎住了。
她回到座位上,怔了怔,发现衬衫袖口的扣子没扣好,散了,又瞥见自己的手腕也露了出来,于是偷偷摸摸地把本来戴在手腕上,昨天夜里男人送她的一块手表撸了下来,塞进抽屉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便拿了课本去上早课了。课间,她回到办公室,一坐下,张美娟便悄悄转过头来,问她,怪不得那位领导来我们学校视察,总要找几个人一起吃饭,你也跟他吃过一次饭吧,难道他真是这么无耻好色的一个人?舒兰一脸尴尬,强忍住内心的鄙夷和厌恶,说,这种事情,外表看看,怎么看得出来。说完,低下头去,不做声了。
往日办公室这几个人,开开玩笑,撮合撮合她跟小向,说说某个学生的成绩降了或升了,看上去也十分轻松和谐,但是这一天,屋内的气氛却有些闷,大家都自顾自,只有微信声音此起彼伏。窗外的太阳光踉踉跄跄,爬到大理石窗台,爬过高凳子、桌子、书柜,在半旧的地板上投下浓重的阴影。龙舌兰边上也有尖尖的、柳叶刀似的影子。风一过,那些影子便像拧了开关,一刀刀切着底下的凉台。到了下午,天变了脸,又开始下起小雨,舒兰将龙舌兰端回办公桌。小向刚上完音乐课,从细雨中跑上来,手里拿了伞,却不打。他是个赶时髦的年轻人,一头短发烫成了卷儿,深一撮,浅一撮,花里胡哨,跟个外国人似的。他走到舒兰边上,把伞往她那儿一搁,抓着后脑勺说,外面在下雨,这把伞你备着。舒兰不回应。办公室几个同事也都不搭话。谁也没想到王福川的一席话,竟像长了翅膀,横生了枝蔓,很快在学校里传开来。没过几天,王福川便倒了大霉,被抓了起来。
王福川被抓的当天,舒兰干了一件大事。那天晚上,她开着车,一个人在路上乱转。外面的雨势并不大,毛毛雨,似雾非雾地飘过来,洒在车窗上,像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车里的空气也同样潮湿、粘润,涂了她满头满脸。她的心被这样的音符敲击着,怅然若失,些许凉意从心底里升腾起来,不知不觉开离了市区,往隧道的方向驶去。不过十来分钟,她在郊区一间小屋边上停了下来。
她默默注视着小屋。屋子是她租来的,看上去像座坟茔倚在半山上,屋前打一圈木篱笆,屋后是毛竹林,一年四季肆无忌惮,蔓延了整片山坡。她喜欢这种没有人声的热闹。有月亮的晚上,她躺在小屋里,人被满山的翠色熏着,就像被一张烟霞织就的云床托着,虽然底下的竹子是空心的,是虚无缥缈的,但感觉却是酥软而快乐的。她想起白天里男人给她发来一条短信,她没有回。她翻出那条短信,看了看。她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做。
童年的记忆中,似乎也有这样一个地方。她们村里有一个废弃的窑厂,窑厂背面倚着一条溪河,溪河边上,芦花恍惚,随风而荡,很有一股蒹霞苍苍白露为霜的味道。只是那味道,却不似诗书里的美。那味道将女人的忧愁和欲望压成了一张笨重的矮脚床。床是陈年里的木头,发了霉。男人不吭一声,一屁股坐到上面,灰尘便散了一地。
她从包里摸出手机,找到白天里的短信,慢腾腾地打了一行字:你在哪里?想了想,删掉,又重新打了一行:我在老地方,你来不来。她看着这条未发出的短信,思虑良久,还是觉得不妥,又删了,想再写点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写。
我还是可以再等一等的,她总是这样想。她已经等了一年了。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花样年华总是这样,一声长,一声短,像黄梅戏里小姐的水袖罗衫。
她坐在车里,听着雨声,忽然感觉心慌。她想起男人吻她的第一次,吻在她眼睛上。她的心柔软得快要流下眼泪来。还有他们第一次做爱,在汽车狭小的空间里,她几乎就要窒息。男人说他第一次见到她,就爱上她了。男人说这话时,眼角眉梢是模糊的,带着青草的欲望和悲恸。他们的车子沿着江边的塘路慢慢滑行,天窗上方的一小片天空也在慢慢地变幻着颜色,她躺在车子后座,看着星星从头顶滑过,还在心里想,原来他早就想把自己搞到手了,这个流氓。但她的这个想法很快被一种莫名其妙冒险的激情替代了,以至于她很快把自己身处的一切也给忘了。
她在家里是从来不哭的,她的心从来也没有变得这么柔软过。小时候,她常常去村里的窑厂边上玩。窑厂的黄昏从来都很荒凉,少有人迹。她从小就偏爱那种荒凉。一个傍晚,窑厂边上挤满了人。一具女人的尸体浸泡在小河里。女人是自杀的。据说是因为跟人偷情被发现,投河自尽了。她认识那个女人,每年,她都要去她的裁缝店里量尺寸。十岁以前,她穿的衣服都是在女人那儿做的。女人的双手,那是多么灵巧的一双手,软得就像刚从棉铃中挣扎出来的棉花。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现在那双手已经被河水腐蚀,连同她抚摸过的剪刀,皮尺,男人汗津津的身体,以及如女人肌肤般丝滑的布匹。
也许人们是可以抵抗一切的,用这样或那样纵身一跃的方式,却唯独不能触及它们中的任何一块。他们只能在自己的身体内部,在关闭的房间之内,徘徊、航行,直至生命干涸、消失。
村里几个胆大的男人,将女人的尸体拖到岸上。没有人哭,大家都在看热闹,也没有人悲伤,大概再没有比一具肉体更为吸引人的东西了,即便她已经肿胀,腐烂,发臭。她跟在别人身后。女人的丈夫也跟在别人身后。他没有动手去捞尸体。他始终面无表情。后来他拐进了窑厂,窑厂的四面都是黑,他在黑色的灰烬里蹲下来,小声呜咽。她也跟着哭了。她哭得很大声,边哭边往家里跑。女人的模样泡在水里太恐怖,她害怕。到了晚上,她仍然哭,父亲闭着眼睛,卧在藤椅里,一口接着一口狠命地抽烟,突然走到她面前,恶狠狠地掴了她一巴掌。那时她还不能理解“哭”,也不明白什么是死。
她熄火,下车,从车后备箱拿出一捆备用的网线,塞到了小屋的床底下,然后打开窗户,透了透气。窗外的栀子花,在雨水中低下颓靡的脖子,风一吹,便“吧嗒”一声,掉了下来。她看着满地白晃晃的花瓣,终于下定决心,给男人发了一条短信,她说,我们谈一谈。男人没有回,她知道男人需要时间,她愿意给他这点时间。她去买了一支大功率白炽灯,最老旧的那种,又顺手牵羊,从柜台上挪走了一把水果刀。白炽灯和水果刀在地下超市的寒光中透着杀气。她付完钱,将水果刀装进皮包里,然后抓起白炽灯,头也不回地走了。有个服务员在她背后小声嘟哝,刀剑不长眼。她当作没听到。
等她再次回到屋子里,男人已经提前到了。比她预料得要早,这是一个好兆头,她在心里想。男人走过来,一把搂住了她。屋子里一点光线也没有。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关上了,于是屋内更黑了。雨慢慢地下大,刮到竹叶上,发出鬼哭狼嚎的沙沙声。黑暗中,她看不到男人的脸。她发现男人身上的气息变得不同以往了。男人似乎套了一件针织的T恤衫,摸上去硬硬的,有些扎手。她很久没有在大太阳底下见到过他了,今天,她准备好好看一看他,把他的样子刻在心里,于是轻轻推了推他,握着白炽灯,说,屋子里的灯坏了好久了,我买了一支新的,你把它换上吧。
男人俯下身,用嘴堵住她。她有些心烦意乱。她不希望男人打乱她的计划。她握着白炽灯的手,用力一推,白炽灯不小心摔了个稀巴烂。
同一天,张美娟和陈萍干了一架。起因是陈萍今天穿的一件衣服有点露,张美娟在背后说了几句,不巧被陈萍听到,两个人吵了起来。陈萍平时喜欢在脖子上扎一块围巾,这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露着个大领子,就赶到学校里来了。张美娟因为年终评先进那桩事情,原本就恨极了陈萍,两个人一争,什么丑话都吐了出来,还把王福川前几天早上讲的秘闻,也添油加醋,一股脑儿朝陈萍身上泼了过去。两个女人当场扭打了起来,场面血淋淋的。舒兰望了两眼,很快事不关己地走开了。
自从王福川讲了那些话,这几天,她心里也很不舒服。她总感觉有人在暗地里偷窥她,弄得她神思恍惚。预感她被人监视了。她第一个怀疑张美娟。张美娟总爱侧着脸,不时回过头,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瞄她。张美娟的电脑屏幕原先是正对着她的,要是她向前伸伸头,虽然屏幕上字小,费点神,多少能瞧见她跟别人的谈话。但这些天,张美娟把电脑屏幕往右一挪,小心翼翼,对着右边的墙壁聊天去了。她不吱声,心里却有了个疙瘩。第二个是小向。小向像一块牛皮糖,她走到哪里,他便也走到哪里。
她只好躲到卫生间里去给男人打电话。她这辈子从来也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只有她跟男人之间这么一段恋情,但就是这么一件,却快要将她给逼疯了。流言蜚语是会淹死人的。流言蜚语还会拆散她跟男人。她站在盥洗台前,对着镜子,开着水龙头,水哗哗哗流着,那水是热的,有一层雾气绕着水龙头飘来飘去,很快在镜子上氤氲开来。她看着那雾气,一只手拿着电话,另一只手抵着脖子,跟男人说起了学校里发生的这么一段荒唐事,讲完了,沉默了会儿,又接下去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有没有想过跟我结婚?她的语调慢吞吞的,喉咙干涩而疼痛。她以前从来没有问过男人这种问题,男人拐弯抹角地说过他不喜欢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要花心思和精力的,他没有那么多心思和精力。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一切都不可捉摸。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她的脸色苍白得吓人。她几乎能够听到男人冷冰冰耸动喉骨的声响。这让她感觉很不舒服。她焦躁不安地等待着。男人沉默得像个入殓师,久久不说一句话。她心里很慌张。男人后来说,我爱你,你要相信我。男人巧妙地回避了那个话题。她嘴角浮起一抹嘲笑,她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陈萍从卫生间里走出来,若无其事地盯着她。陈萍的嘴角也挂着一抹笑,眼角下一块丑陋的淤青张牙舞爪地兀自悲鸣。她内心里又升起一股被人偷窥的厌恶,于是慌里慌张一把按了电话。
陈萍却跟她套起了近乎。她想陈萍一定是听到了她跟男人的电话。她不吭声,不着痕迹地挪开了陈萍的手,低着头,按了水龙头,转身到里间去了。片刻,似乎听到陈萍在外间一个人喃喃自语,什么感情,爱不爱的,那都是假的,玩玩而已,说白了还不是为了那几张钱。
她依旧没有吭声。她感觉有些冷,她穿了一件薄薄的黑色上衣,一条棉布裤子,风从狭窄的窗口吹进来,覆盖住逼仄的空间,以及她与内心缠斗的细微声响。她从窗玻璃的缝隙里,看一簇簇梧桐叶打着圈儿跌到地上。后来她给男人发了这样一条微信,她说,你要是骗我,我就杀了你。

窗外的雨还在不断下大,雨点打在窗棂上,发出“啪啪啪”的声响,就像香港警匪片里子弹冲出枪膛的响声。男人的嘴唇湿漉漉的,浸满了水分,她的嘴唇也浸满了水分,像泡在大雨里。她喜欢这种感觉,温暖而潮湿。气息是迷人的。
白天,舒兰和小向两个人站在一株桂花树下。舒兰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对小向说,小向,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惹人心烦。
小向说,我就跟着你,谁叫你不答应做我女朋友。
舒兰说,我不答应,你就跟着我呀?
小向说,感情就是这样黏出来的呀,要天天黏的呀,不黏的还叫感情嘛,不黏的那都是耍流氓,都是玩玩的。
小向连珠炮似的轰着舒兰。他边上的那株桂花树在风中发出濯濯响声。桂花树后,弧形的泥草地,像张歪斜的床垫,延伸至隐蔽墙角,一脚踏上去,泥沫儿便“噗嗤噗嗤”溅起来。
舒兰违心地说,我可不喜欢被人黏。
小向说,你一定没认认真真谈过恋爱吧。
舒兰说,谁说的,我男朋友——她突然感觉她说不下去了。她望向别处。一些不知名的野草的种子落在她的裤腿边上,像吸血的墨绿色针尖。
小向说,你有男朋友?鬼才相信你有男朋友!
我是没有男朋友。舒兰讷讷地说,突然有点悲伤,还有点痛苦。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舒兰说。她的目光落在倚床的那一面墙上,墙纸剥了一个角,往外翻着,露出积满污垢的黑砖块,她第一次发现,这地方污秽得令人震惊。她又把头转向窗外,栀子花的影子贴在玻璃窗上,在雨中兀自婆娑,像一只只眼睛,要致人于非命。阴影在迅速扩大,最后融成一团,充斥了她的整个胸腔,仿佛一个越吹越满的热气球,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爆破开来。
她感觉疼痛。她从来没有见过男人如此沉默的样子,男人总是滔滔不绝,有时会像个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她的沉默在男人面前显得笨拙而可笑。现在,他跟她一样了。但他的笨拙可笑大概是装的,她想他一定又在犹豫白天里的那个问题了,那种问题是会让其他事情变得无聊和乏味的。
过了很久很久,男人嘶哑着声音说,除了那件事,其他什么我都可以依你。
包括死?她问。
男人的手抖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搂住她,仿佛想要向她证明他的决心。
又过了很久。她说,这地方真安静。
是啊,很静。
可惜没有月亮,太黑了。
你要是觉得黑,我出去买灯。男人说。很快男人又说,我想起来了,灯泡车里就有,我去拿。
她跳下床,跑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夜色像湍急的河流,一下子涌进房间里。男人起身,开门,冲进大雨里拿灯去了。她回到床上,找到皮包,摸了摸那把水果刀,心里又一阵疼,又放下了。
屋子里终于亮起了灯。男人拿来的是一盏橘黄色的白炽灯。她点了灯,又关了灯。窗外的雨已经下小了,快下过去了,空气里弥漫起一股奇特的酸味儿,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灼烧,在腐烂。她整整齐齐平躺在床上,身上没有一丝阴影的皱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