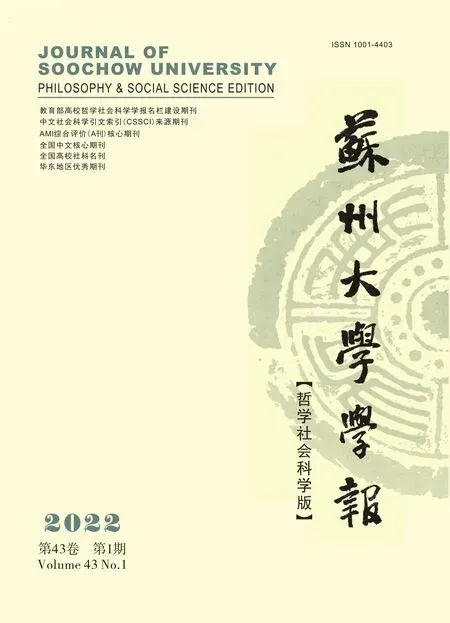清代士人游幕的文学意义
——以乾嘉时期士人的游幕为考察对象
2022-12-07李金松
李金松
(河南大学 文学院/国学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游,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一个人的成长方式,也是其生存或生活方式。战国时代,即有游士;两汉时期,有游侠或士人的游学。隋唐时期,游历更是成为文人的一种风气,如高适、李白、杜甫等,年轻时都有过壮游的经历。清代士人的游幕,与古人之游是相同的,兼具其成长方式与生存或生活方式的性质。清代乾嘉时期,士人游幕极为兴盛。有过多年幕游经历的梅曾亮在《陈拜芗诗序》中说:“诗莫盛于唐,而工诗者多幕府时作”①(1)①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揭示了唐代士人游幕与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对清代士人游幕与诗歌的关系,学界已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如朱丽霞、侯冬与李瑞豪等人的论著②(2)②参见朱丽霞:《江南与岭南:从文人游幕看清初文学的传播与文坛生态》,《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侯冬:《乾嘉幕府与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李瑞豪:《乾嘉时期的文人游幕与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在学界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宏观层面深入地探讨乾嘉时期士人游幕具有怎样的文学意义。
一、情感体验的大力开掘
中国古代幕府制度的发展自两汉到隋唐,主要是辟署制;两宋时期,幕府的主体是命官制,只是某些特别机构可采用辟举制;元代幕府则是命官制与辟举制混用。明代虽然一切官员的任命权统归中央政府,传统的辟署幕府制度告以终结,但军营幕府以及侯王府邸可以私自招聘用人,如徐渭、茅坤进入胡宗宪幕府,谢榛进入赵康王府邸等,这开启了清代幕府的延聘制。清代幕府基本上是以延聘制为主,而以辟署制进行补充,而且后者仅限于军营幕府。清代幕府的这种用人制度,在乾嘉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尽管幕游士人在清代人口所占的比例不算大,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他们对清代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是因为,幕游士人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既依附于官府,又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他们与普通的衙吏以及民众不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知识。对于这样的一个阶层,作为文学史的研究者,关注的是这一阶层在游幕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情感体验。
在清代以前,由于幕府是辟举制或命官制,几乎不存在游幕士人这一阶层;即使有个别的士人的生存方式接近于幕游,如明代的王稚登、方子公等,但那与真正的幕游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像清代幕游士人那样,游幕成为一种职业选择。由于清代的幕府制度基本上采用的是延聘制,当时社会才会诞生幕游士人这一特殊的阶层。在清代的诗文集中,关于这一阶层的记载层见错出,如:
君姓蒋氏,讳廷思……君幼慧,十五为童子师,十九补元和县学生……以贫故,无以养,游四方,南逾岭,北渡河,其客京师最久。①(3)①宋翔凤:《朴学斋文录》卷四《中书舍人蒋君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页。
君讳汝蕃,字西园……少受业于姊婿杨芳灿,为诗文有法度,所与游者皆知名士。好急人之急,坐困无所悔,游幕千里,以赡其亲,岁时必归省。②(4)②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四八《徐君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488册,第378页。
先生姓吴,讳克谐,字夔庵,世居石门之洲泉……伤于贫,客游四方,傭笔墨。中岁,稍自振。③(5)③程同文:《密斋文稿》之《吴南泉先生墓表》,《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君讳璟燕,字紫超,又字友源,号赋梅,姓曰郭,先师南郑公之冢子也……家中落,君客游吴门四年,馆淮北监掣同知李公署二年,客太平郡守陈公署三年。④(6)④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六《郭君友源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1册,第209页。
这类材料不胜枚举。作为幕游士人这一阶层,其成员构成是相当复杂的,既有贫寒士人,也有累世业幕者或希望提升自己的富家子弟,同时也有家道中落、举业无成的官宦子弟,以及与幕主存在亲缘或师友关系者,如阮元官山东学政时,就聘请姐夫焦循以及自己年少时业师乔椿龄为幕宾。然而,在幕游士人的人员构成中,贫寒士人所占比例应该是最大的,如洪亮吉在《伤知己赋》中所举朱筠官安徽学政时幕府之宾僚,张凤翔、章学诚、戴震、吴兰庭、高文照、汪中、邵晋涵、黄景仁、庄炘、瞿华、王念孙等,加上作者洪亮吉本人,除了官宦子弟王念孙与已举进士而待授官职的邵晋涵之外,馀者均为贫寒士人,所占比在83%以上。因此,贫寒士人幕游期间的文学书写,在幕游士人的文学书写中居于主体地位。幕游士人一身而兼具两种身份:一是他们中大部分为寒士;二是幕府中宾僚(他们中有的是现任或失职的官员,如石韫玉在勒保幕府、杨揆在福康安幕府、赵文哲之在温福幕府等),依托幕府生活,同幕府中以及与幕府关涉的人物周旋。幕游士人的这两种身份,决定了其人生体验、文学书写与一般寒士是既有联系同时又是有所区别的。所谓联系,指的是幕游士人曾经的寒士体验;所谓区别,指的是幕游士人经济上有保障,他们的生活同一般寒士比较起来,较为优裕一些,而且交游较为广泛。由于这些原因,幕游士人一方面在自己的文学书写中展现自己的贫寒失志;另一方面,他们抒写自己寄人篱下的无奈之感。如蔡复午与陈韦人二人均以幕游为业。在《陈生韦人哀辞》中,蔡复午这样回忆道:
予亦贫贱就食四方,北起燕赵,南浮楚越,浮贞郁,下沅湘,率一二年与韦人合,合必各抒其湮郁困厄之思。⑤(7)⑤蔡复午:《西赜山房诗文集》文录下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2册,第461页。
蔡复午回忆中“湮郁困厄之思”,显然是他们在幕游期间的感受,只不过在相聚的时候倾诉出来而已。这一事实即充分说明:作为幕游士人,在游幕期间是有强烈的“湮郁困厄之思”的。因此,在幕游期间,他们往往抒写自己的“湮郁困厄之思”。曾有过三十多年幕游经历的李果在其《咏归亭诗钞》的自序中这样称述自己的诗歌书写:
仆非诗人也。仆少孤,奔走衣食三十馀年,有不得已于中,聊以舒其抑塞幽忧之怀,而非实能诗也。①(8)①李果:《咏归亭诗钞》卷首《自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4册,第324页。
李果所说的“抑塞幽忧之怀”,与蔡复午的“湮郁困厄之思”也是相同或相近的。可以说,“湮郁困厄”“抑塞幽忧”基本上是士人尤其是贫寒士人幕游期间的共同感受。这种共同感受,即史善长在《不寐》这首诗中所说的那样:
喔咿就幕府,不啻方而刓。赏音纵偶遇,古调劳强弹。②(9)②史善长:《秋树读书楼遗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26册,第731页。
入就幕府,对幕游士人而言,是“不啻方而刓”。所谓“方而刓”,即将方棱磨去,使之变得圆钝。幕游士人为了能在幕府中生存,必须作出某种妥协,磨去自己性格中颇有棱角的部分;即使偶尔受到幕主的赏识,但仍不得不委曲求全,强颜作态,在幕府中勉强自己做些自己不愿做之事。史善长在这首诗中表达的这种幕游感受,与汪中在《经旧苑吊马守真文》表达的“俯仰异趣,哀乐由人”“纷啼笑其感人兮,孰知其不出于余心”③(10)③汪中著,李金松校笺:《述学校笺》,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42-843页。的感慨是一致的,表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感。幕游士人的诗文集中,关于抒写幕游期间这种无奈感的篇什颇为不少。如沈大成《学福斋诗集》卷二《杂诗十二首偕范瀛山同作》之一,是沈大成幕游北京时所作。沈大成以孤雁自况,“非无远去志,羁旅多苦情”,诗人像孤雁一样,虽然有远翔之志,但是羁旅中的困苦使其无法达成自己的意愿。此诗抒写的正是诗人自己的无奈感。另如陶元藻《泊鸥山房集》卷十八《杂咏二十首》之九:
昔我来京华,庭树低拂辕。今我久淹滞,乔柯不可攀。日月如转烛,无力回天悭。游子在天涯,不如云出山,舒卷浑自得,须臾随风还。④(11)④陶元藻:《泊鸥山房集》卷一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41册,第634页。
此诗前六句诗人抒写自己久客京华,岁月流逝;而后四句,则抒写了自己受到某种束缚,不能像白云一样自由,表现的是自己的无奈感。幕游士人的这种无奈感,可以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与“湮郁困厄”“抑塞幽忧”相关联的是幕游士人的寄人篱下之感。对于寄人篱下之感的表达,乾嘉时期幕游士人在诗文中最喜欢用的一个意象是“依刘”。“依刘”是指《三国志》中王粲“乃之荆州依刘表”这一典故。在这一时期幕游士人的诗文集中,“依刘”作为一个人文意象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借助这一意象,幕游士人表达自己的寄人篱下之感。如从四十五岁起开始幕游的吴翌凤在多年后自叹:“年开六秩白发稠,饥驱千里仍依刘。”(《与稽斋丛稿》卷十《送徐玉山、叶瑞千、张少安、刘云峤、陈叔鲁、良徵之贵阳》)赵良澍曾幕游商丘一年,在其到达商丘时,作有《至归德》一诗,中云:“飘零琴剑且依刘,马首东南至宋州。”(《肖岩诗钞》卷七)而当离开商丘时,赵良澍有《从归德入都》一诗,首联“马卿抱病游方倦,王粲依人赋可哀”(同上,卷八),亦含“依刘”这一意象。詹应甲在赴任竟陵县令前,回忆自己的游幕生涯,曾有诗句云:“平生心迹半依刘,薄宦依然槖笔游。”(《赐绮堂集》卷六)上引诸人诗句中“依刘”这一意象,大多是表现自己幕游期间的寄人篱下之感。
不论是无奈感,还是寄人篱下之感,均是士人幕游期间的真切感受;这种真切感受,是源自当事者自身的生活体验,没有幕游经历,是不可能有这种真切感受的。清代以前幕府中的幕游士人,无论是辟署制还是命官制,一概是朝廷的官员。而清代的幕府基本上采用的是延聘制或招聘制,幕府中的幕游士人,基本上是一介布衣。作为朝廷的官员,其心态与属于布衣这一阶层的幕游士人是迥然有异的。由于这一原因,清代以前的幕游士人很少在文学书写中表现自己的这种无奈感与寄人篱下之感,只有作为布衣的清代幕游士人,才会在文学书写中表现出这种情感。虽然在文学书写中表现思亲怀乡之情,山水风物之赏,羁旅行役之叹,等等,清代的幕游士人与游宦士人并无不同,但是,他们在幕游过程中的无奈感与寄人篱下之感更加凸显,并使这种情感体验由此前的个体性而趋向群体性,从而具有了时代性,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忆。因此可以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清代乾嘉时期幕游士人的文学书写对情感体验的表现具有开掘之功。
二、文学经验的交流
幕府是各类人才的荟萃之地,“为诗人、作家提供了栖身之所和文学交流平台”①(12)①侯冬:《乾嘉幕府与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3页。。幕游士人能够入就幕府,大多是富有才华的,或是行政方面,或是艺文方面,或者两方面兼而有之。沈大成在《金竹山居诗序》中回忆:“余于壬午(1762)之冬,来馆江氏,黄君北垞已先在。鹤亭主人既贤,而喜称诗,一时同人若鲍君海门、程君香南、吴君葑田与北垞,皆博雅闳通,晨夕酬倡,而主人之小阮亦与焉,交相得也。”②(13)②沈大成:《学福斋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第49页。沈大成入就江氏馆第时,同僚中的鲍皋等在他看来都是“博雅闳通”,才华横溢的。幕游士人聚集在幕府,免不了在一起酬唱或开展文宴等群体性活动。在这些群体性活动中,幕游士人之间往往会发生艺文或学术方面的交流。如曾幕游中原多年的李果在其诗集卷首的《自序》中就说:“奔走衣食三十馀年……三十年来,与中原诸公相讨论。”③(14)③李果:《咏归亭诗钞》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4册,第324页。其语中的“与中原诸公相讨论”,其实是叙说自己在幕游中原时同中原人士进行交流,其中既有中原的当地人士,也不乏幕游者。而交流的内容,自然有文学经验方面的。而幕游士人聚在一起的这些交流,对文学创作以及艺术水平的提高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幕游士人在幕游期间所进行的文学经验的交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幕主,一是同僚。幕主相对于幕游士人而言,大多年纪较大,学术与文学地位较高,是属于学术或文坛前辈。如前举安徽学政朱筠幕府,据洪亮吉《伤知己赋》所述幕府诸人,除戴震年纪稍长于幕主朱筠外,其他诸人年纪均小于朱筠。徐经《雅歌堂诗话》曾说:“竹君先生有扬雄奇字之癖,而作书歌咏无一不奇。”④(15)④徐经:《雅歌堂诗话》,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9页。因此,朱筠作为文学前辈,将自己的文学经验同自己幕府中的宾僚进行交流,指点他们的文学书写。在幕游朱筠幕府期间,洪亮吉与黄景仁在诗歌书写中喜欢使用一些奇僻艰深的文字,如《岁暮急葬归里率效述德诗一百十韵呈大兴朱学士》《昭灵宫祈雨词》(《附鲒轩诗》卷四)、《涂山禹庙》(《两当轩集》卷七)等诗,以展现自己的博雅,即是效仿朱筠的诗歌书写,是朱筠文学经验的表达。另如阮元,其官浙江学政时幕府中的宾僚,虽然有年纪长于他的,如吴文溥、朱文藻、钱大昭、孙韶等,但更多的是年纪小于他的,如陆耀遹、陆继辂、朱为弼、陈文述、严元照、端木国瑚、童槐、王衍梅等。这些年纪小于阮元的幕游士人,多尊阮元为师,在文学书写方面亦规仿阮元。如陈文述自述追随幕主阮元后诗歌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鄙人学诗垂三十年,初好为侧艳之体,自奉教于仪真阮伯元先生,又获交于太仓萧樊村,乃一变旧习,归于醇雅。”⑤(16)⑤陈文述:《颐道堂文钞》卷一《王小村江亭论诗图叙》,《续修四库全书》1505册,第557页。其中的“奉教”二字,即意谓阮元与陈文述师生之间关于诗歌的交流。赵翼在进士及第之前,曾馆于汪由敦府第。据赵翼自述:“余自乾隆十五年冬客公第,至二十三年公殁,凡八九年。此八九年中,诗文多余属草,每经公笔削,皆惬心餍理,不能更易一字。尝一月中代作古文三十篇,篇各仿一家。公辄为指其派系所自,无一二爽,此非遍历诸家不能也。”①(17)①赵翼:《簷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页。汪由敦应制类诗文多由赵翼起草,但是他对赵翼的起草进行“笔削”,而且能指出赵翼所作古文的“派系所自”。汪由敦的“笔削”“指其派系所自”,其实是与赵翼进行文学经验的交流。汪由敦之诗“学白、苏,近似查慎行(笔者案:号初白),启示赵翼”。②(18)②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846页。而赵翼之诗,乃是“学苏、陆而参以梅村、初白”③(19)③尚镕:《三家诗话》,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5835页。。赵翼诗歌在艺术上呈现的这一风貌,与汪由敦近似,这显然是得益于汪由敦的启示。
在幕府中,幕游士人往往代幕主起草诗文,而幕主对幕宾起草的诗文进行删改,也是重要的文学经验交流方式。这种幕主对幕宾的诗文进行删改,是难得的文学经验的传授、交流,颇能提高幕宾的文字表达水平。
幕主与幕府中宾僚的文学经验的交流不全是后者对前者的顺从、师仿,也有抗逆的。著名骈文家彭兆荪曾馆王昶三泖渔庄,助王昶编撰著作。王昶出于对晚辈的关切,曾建议彭兆荪少作或不作骈体之文。对王昶的建议,彭兆荪颇不以为然,并拒绝接受,其诗《冬日客三泖渔庄即事九首》之七云:
不薄齐梁作,文章本一途。群公排八代,块独练《三都》。绣段机空织,幺弦调益孤。陵云知庾信,除却少陵无。司寇见示诗,有“文章流别君须记,可与齐梁作后尘”之句。④(20)④彭兆荪:《小谟觞馆诗文集》诗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第598页。
彭兆荪在公开场合可能是唯唯诺诺,没有对王昶的劝诫进行反驳,却在私下的诗作里深致不满,认为“文章本一途”,对散体古文与骈俪之作不应厚此薄彼,并以杜甫对庾信的推崇来反驳王昶,为骈文进行辩护。虽然王昶对彭兆荪的建议、劝诫,没有被后者接受,但彼此之间关于骈文意见的交锋,也是幕主与幕府中宾僚之间的文学经验的交流。这种文学经验的交流,其实是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体现了一个幕府群体文学观念的复杂性。
幕主与幕宾之间进行文学经验的交流,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而足。幕府中的文学经验的交流除了幕主与幕宾之间这一维度外,还有另外一维度,即幕游士人之间。幕游士人在幕府中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彼此之间往往有比较多的交流,其中对文学的讨论或文学经验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嘉庆七年壬戌(1802)冬,刘嗣绾与陆继辂同在曾燠幕府,两人曾就诗歌创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陆继辂作《论诗二首示刘大》。在读了陆继辂见示的诗后,刘嗣绾亦有回复,作《复答祁生论诗》,这是两人就相关问题进行的热切交流。且看陆继辂的《论诗二首示刘大》:
丈夫重立身,诗文固末技。苟复探其源,亦自惩忿始。毁能令公怒,誉必令公喜。人操喜怒权,我受毁誉使。长言发咏叹,岂缘徇名起?万古滔滔来,虚气有时止。
殊方斯异音,适口有独旨。文心矧百变,各各成厥是。陋儒思立名,始辄恣诃诋。及观所叹赏,大率与己似。相需在声华,岁寒讵可恃?每闻标榜交,中道按剑起。⑤(21)⑤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第592页。
而刘嗣绾对陆继辂的回复之诗则是:
陆继辂《论诗二首示刘大》的第一首,主张士人以立身为本,诗文创作乃是末技;而立身当以戒除愤懑之心,不为毁誉所动。第二首指出作者不同,其审美趣味也各不相同,而这不同的审美趣味,成就各人作品的独特风格。针对《论诗二首示刘大》提出的这些诗学主张,刘嗣绾认为诗歌创作应该博观约取,披沙得金;对于近代(当指明代)的诗歌创作,刘嗣绾认为是“往往乖典则”,诗派林立,相互冲突,导致的局面是“家家互相雠”。基于上述认识,刘嗣绾主张诗歌创作的理想境界是“形神贵交融”。他关于诗歌创作的这一主张,与陆继辂《论诗二首示刘大》诗学观点桴鼓相应,是对陆继辂诗学理论的推进。陆继辂与刘嗣绾的一唱一酬,对诗学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是各自根据自己的诗学观念进行的文学经验的交流。
幕游士人之间文学经验的交流,不只是通过诗歌唱酬的形式实现的,还有彼此争论、书函通邮等形式。如陈文述在《吴澹川传》中,记载他与吴文溥关于选诗美学标准的争论:
君姓吴,名文溥,……中年家贫,衣食奔走,出游江淮、秦中……晚归里,依阮中丞于武林……君博览,工古文,力避前人蹊径,尤长于诗,以清微澄澹为宗,源本陶谢,出入王孟,世多以规橅少之,然独到处,不减施愚山、吴陋轩也。
陈子曰:余之始识澹川也,在丁未春,道气盎然,君子人也。及在阮中丞幕府,同覆勘《两浙輶轩录》,余主博大,君主清淳,去取间,持论往往不合。①(23)①陈文述:《颐道堂文钞》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05册,第582页。
虽然陈文述与吴文溥在选诗美学标准上“持论往往不合”,进行诗学观念的碰撞,但这是两人关于诗学问题的文学经验的交流。在《孙莲水传》中,陈文述记载了孙韶与他以书函相邮的形式进行诗学问题的讨论:
君讳韶,字九成,莲水其别字也。世为江宁上元县人。为博士弟子,以诗见赏于钱唐袁大令枚,因师事之……余之识君也,在己未冬同客阮中丞武林节署。同人知君护大令也甚,故于君前摘訾大令诗文,观君龂龂之状,以为笑乐,而君之争也如故。君之客武林也,与余交最善,论诗尤乐于下问。每成一篇,哦吟竟日,改至数十次,不惬意不止。及余客京师,君去江右,犹数千里邮诗相商榷,余所识海内诗人,未有虚怀若君者也。②(24)②陈文述:《颐道堂文钞》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05册,第582页。
无论是孙韶在阮元幕府中为袁枚进行辩护,与陈文述“论诗”,还是他与陈文述之间“数千里邮诗相商榷”,都是在交流文学经验。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幕游士人在幕游期间进行文学经验的交流是十分普遍的。
清代幕府显然是一个文学场域,游幕士人在幕游期间与幕主或同僚之间所进行的这些文学经验的交流,能够促进彼此对文学的认识,提高文学表达的艺术水平,并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
三、文学风格变化的促成
士人游幕,大多远离自己的故乡,从故乡到幕游地,数百里或数千里不等。幕游地的地理环境,大多数与幕游士人的故乡存在很大的差异。幕游士人入就的幕府,“宾客皆一时英俊诸儒”③(25)③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卷二,《笔记小说大观》第2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30页。,多为才华杰出之士;而幕主,如毕沅、朱筠、王昶、胡克家等,均老于文学,对年轻幕游士人而言,他们具有领袖群伦的魅力。因此,新的地理环境与新的人际交往,往往能促成幕游士人文学风格发生变化。
地理环境包括两个方面: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幕游士人由故乡置身于新的地理环境,自然会惊异于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中的自然风貌与人文风情。而对于这些有异于故乡的幕游地的自然风貌与人文风情,幕游士人大多会付予热情,并用笔墨进行展现。如洪亮吉之入安徽学政朱筠幕府,随朱筠游太平府(今安徽当涂)之青山,独自一人登青山之巅。据朱筠记载:“……揖佛海下山去,而同游者独稚存不见。遣人四出登高呼之,良久及舟,而稚存后至,问之,云:‘早起西望青山巅,奋欲登之,不知其远近……比涉巅,穹穹无所有,惟乱石上松子壳狼藉……’稚存可谓好奇,余不及者。”④(26)④朱筠:《笥河文集》卷七《游青山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440册,第222页。在朱筠幕府期间,洪亮吉创作了大量的游山诗作,如《附鲒轩诗》卷三之《齐云山阻雨》《叶岭》《唐坞》《文殊台望天都峰》《游九华至一宿庵》《东岩》等;在陕西巡抚毕沅幕府期间,洪亮吉同样创作了大量的游山诗作,如《卷施阁诗》卷五之《自莎萝坪至青柯坪小憩》《通天门纵眺》《未晓由金天宫西至环翠岩望山南诸峰》等。洪亮吉对这些山峰的抒写能体现奇这一特色,因此,他的诗也被人视作“奇”,如毕沅在《吴会英才集》中称洪亮吉“奇思独造,远出常情”①(27)①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6787、6789页。;张维屏在《听松庐诗话》中认为“先生未达以前,名山胜游诗多奇警”②(28)②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6787、6789页。。在幕游之前,洪亮吉的诗歌创作是取法汉魏的。只是在幕游之后,洪亮吉有机会游览名山胜境,寻幽探奇,其诗歌风格因此而发生变化,趋向于奇了。与洪亮吉相似,吴俊的诗歌创作风格亦因幕游而得以改变。在入就福康安军营幕府之前,吴俊的诗歌创作“取径幽深,精心独造”;而入就福康安军营幕府之后,“崎岖烽火,所见益奇,笔足以发难显之情”③(29)③王昶著,周维德校点:《蒲褐山房诗话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诗歌风格转型于奇峻。吴俊的诗歌风格之所以由幽深转向奇峻,是因为其幕游从军广西、云贵以后所处自然环境呈现出来的审美形态,改造了他的审美趣味而造成的。
除自然环境外,幕游士人所处的人文环境也会促成文学创作风格的变化。幕游士人从故乡到幕游地,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转换,同时也是人文环境的转换。幕游地的人文风情,或多或少与幕游士人的故乡有别。幕游士人对于幕游地的人文风情,除了陋习恶俗不能接受之外,一般会表现出惊异、认可或欣赏的态度,而且也乐于用诗歌表现这些有别于故乡的风俗民情。如陶元藻幕游岭南时,用诗歌展现岭南的风情民俗,作有《截句十二首效东粤摸鱼歌体》(《泊鸥山房集》卷二十二)、《西洋镜屏》(卷二十三)、《潮州竹枝词》(卷二十四)、《题十三国番夷图》(卷二十六)等,这些诗洋溢着潮州民歌的情调,以及岭南濡染的西洋气息,具有岭南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陶元藻的这些诗歌呈现出来的艺术风貌,显然与其幕游燕赵、安徽时诗歌创作沉郁的风格迥然有异。乐钧幕游岭南时,曾作《韩江棹歌一百首》,亦抒写潮州的民情风俗。他对潮州民情风俗的抒写,是“托辞疍女”④(30)④乐钧:《青芝山馆集·诗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90册,第496-497页。的,带有浓郁的当地民歌的风味。由于充满了潮州当地民歌浓郁的风味,《韩江棹歌一百首》呈现出来的创作风格,与他幕游岭南之前的诗歌风格大为不同。陶元藻、乐钧幕游岭南时诗歌风格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显然是对当地民间文艺有益养料的吸收、改造,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诗歌创作风格。换言之,岭南的人文环境促成了他们诗歌创作风格发生改变。
相比较而言,幕主与幕游士人之间的人际交往,对幕游士人文学书写风格变化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而这些在文学书写风格上受幕主影响的幕游士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年纪大多小于幕主,对文学创作还基本上处于探索阶段,因而更容易接受幕主有意或无意施加的影响,从而改变自己的文学书写习惯与创作风格。在乾嘉时期诸多艺文幕府中,以幕主身份而对幕游士人文学书写风格产生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朱筠与阮元这两位。朱筠在当时是青年士人的偶像,孙星衍在《武亿传》中称其“负海内文望”⑤(31)⑤孙星衍:《五松园文稿》卷一,《孙渊如先生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77册,第487页。;王昶在《翰林院编修朱君墓表》对其在当时的影响力有所描述:“承学之士趋风附景,若斗之有杓,芒寒色正,望为归依。”⑥(32)⑥王昶:《春融堂集》卷六〇,《续修四库全书》第1438册,第250、11429页。由于朱筠在当时极具影响力,幕游士人多以入就朱筠幕府为荣。因此,入就朱筠幕府后,幕游士人尤其是年轻的幕游士人大多会遵从幕主朱筠的教导,读书治学,创作诗文。前举洪亮吉、黄景仁入就朱筠幕府后,仿效朱筠以奇僻字入诗即是其例。洪、黄二人以奇僻字入诗,使诗歌表达变得较为晦涩,他们的诗歌风格因这种晦涩表达而也有较大的改变,与他们入就朱筠幕府之前的诗歌风格比较起来,几乎判若两人。阮元是清代汉学的殿军,一生致力于提倡学术,奖掖人才,“以文学裁成后进”。⑦(33)⑦王昶:《春融堂集》卷六〇,《续修四库全书》第1438册,第250、11429页。其官浙江学政、巡抚时,由于修书的需要,他逐渐建立起一个宾僚庞大的艺文幕府,对嘉道时期的中国学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以古学训迪年轻士子。阮元官浙江学政时,苏州曾发生这样一个现象,他在《定香亭笔谈》中予以记载:
苏州书贾云:“苏州许氏《说文》贩脱,皆向浙江去矣!”余谓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①(34)①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6页。
《说文解字》之所以在苏州脱销,全部销往浙江,这说明在阮元的倡导下,浙江的士子纷纷趋于经学的学习与研究了,故《说文解字》需求量大。阮元幕府中年轻的幕游士人,多浙江人,如朱为弼、陈文述、端木国瑚、徐熊飞、冯登府、张鉴、严元照、陈鸿寿等。学术与文学相表里,阮元倡导骈文,亦重视经学。他的这种文学祁向与学术取径,自然影响到其幕府中这些年轻的幕游士人的学术与文学选择,使他们的文学书写及其风格发生相应的变化。前举陈文述的诗歌创作由“好为侧艳之体”,到“乃一变旧习,归于醇雅”,他认为这是“自奉教于仪真阮伯元先生”②(35)②陈文述:《颐道堂文钞》卷一《王小村江亭论诗图叙》,《续修四库全书》1505册,第557页。的结果。陈文述的诗歌创作风格自入就阮元幕府后发生这样的嬗变,不过是阮元幕府众多年轻幕游士人文学书写及其风格发生转变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
总之,幕游能够促成士人的文学书写及其风格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不同幕游士人的文学书写活动中有不同的体现,只是程度有大小之别罢了。
四、作品传播方式的多元化
士人幕游,由于周旋于幕主、同僚以及幕游地当地名流之间,幕府中文宴集会的频繁举行,能极大地激发自己的诗文创作热情,幕游士人的许多作品是在幕府的文宴集会中诞生的。而幕游士人这些在幕府的文宴集会中产生的作品,并不为其个人所私密,而是在幕主或同僚中公开。换一句话说,即幕游士人创作的这些篇什在幕主与同僚或当地名流之间传播了。从幕游士人诗文创作的传播情形来看,他们的作品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一、题壁。幕游士人将自己创作的诗歌篇什以题壁的形式进行传播,主要发生于羁旅行役中或游览时。如陶元藻幕游燕赵时,宿于良乡旅舍,怆然有感,以诗题壁,云:
满地榆钱莫疗贫,垂杨难系转蓬身。离怀未饮常如醉,客邸无花不算春。欲语性情思骨肉,偶谈山水悔风尘。谋生销尽轮蹄铁,输与成都卖卜人。③(36)③陶元藻:《泊鸥山房集》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441册,第647页。
对于陶元藻的这首《题良乡旅舍》,同年北游的袁枚读到了,并作和诗《和良乡题壁诗,诗末有‘篁村’二字》:“天涯鸿爪认前因,壁上题诗马上身。我为浮名来日下,君缘何事走风尘?黄鹂语妙非求友,白雪声高易感春。手叠花笺书稿去,江湖沿路访斯人。”④(37)④袁枚著,周本淳点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1404-1405页。又作《篁村题壁记》,叙述陶元藻此诗的后话:“壬申,余北游,见良乡题壁诗风格清美,末署‘篁村’二字,心钦迟之,不知何许人,和韵墨其后。忽忽十馀年,两诗俱忘。丙戌秋,扬州太守劳公来,诵壁间句,琅琅然,曰:宗发宰大兴,时供张良乡,见店家翁方塓馆,篁村原倡与子诗将次就圬。宗发爱之,苦禁之。店翁诡谢曰:公命勿圬是也。第少顷制府过,见之保无嗔否?宗发窃意制府方公,故诗人,盍抄呈之探其意?制府果喜,曰:好诗也,勿塓。今宗发离北路又四年,两诗之存亡未可知。予感劳公意,稽首祝延之。不意方公以尊官大府,而爱才若是。”⑤(38)⑤袁枚著,周本淳点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1404-1405页。陶元藻的这首《题良乡旅舍》不仅因题壁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传播,而且俘获了不少知音,袁枚在《篁村题壁记》中所述的劳宗发、方观承等,只不过是其中官位较为显赫的知名者罢了。幕游士人在羁旅行役中题诗于壁,这是司空见惯的。如乐钧幕游京师五年后,自北京返回江西临川,在行役途中,作有《戏题旅舍壁》(《青芝山馆诗集》卷五)一首;胡天游《石笥山房诗集》卷七有《将赴幕府抒怀题旅壁》,等等,似此之类,不一而足。
二、唱酬。这里所说的唱酬指私人之间的文学交往。唱酬不仅是幕府文学重要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幕府文学很重要的传播方式。幕游士人在幕府中,不仅彼此之间免不了唱酬,而且与所服务的对象幕主也有较多的唱酬。如彭兆荪在曾燠幕府中,多次与乐钧、刘嗣绾等私下唱酬。彭兆荪《小谟觞馆诗集》卷八《移寓题襟馆示莲裳、芙初二首》《读莲裳、芙初见和之作,再答二首,即送其入都》等,即是他与乐钧、刘嗣绾唱酬之作。他的这些诗作自然被乐钧、刘嗣绾读到,所以乐、刘二人有见和之作。而乐、刘二人的见和之作,又被彭兆荪读到,彭氏又作再答二首。彭兆荪与乐钧、刘嗣绾之间的唱酬过程,其实是他们的诗歌篇什的传播过程。而且,彭兆荪与幕主曾燠也有过唱酬。其《小谟觞馆诗集》卷八《邗上即事,柬曾宾谷都转燠二首》,即是他与曾燠的唱酬之作。在此组诗之二末句“可许飞霞乞佩无”有小字注:“予初至邗上,以病懒未曾修谒,而吴白庵广文照、乐莲裳孝廉钧数道公延竚之雅,予滋愧也。”①(39)①彭兆荪:《小谟觞馆诗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第604页。彭兆荪将他的这两首诗柬于曾燠,固然有向曾燠致歉之意,但这也是将自己的诗歌篇什进行传播。唱酬的重要形式之一是赠别。如胡天游离开直隶总督方观承幕府时,作有赠别诗《保定幕府抒怀,呈别少仪,并示王、许二记曹》(《石笥山房诗集·续补遗下》),尽管此诗受者为闵鹗元(案:闵氏字少仪),但是,他又将此诗出示给同僚王、许两人,同一首诗,他向三人进行了传播。胡氏《送陈黄中还吴,即入闽赴王中丞,并寄座主虞山侍御一百韵》(出处同上)亦是一首幕府赠别诗,送同僚陈黄中归返苏州,但是,他又将此诗邮寄给自己的座主,一诗二用,将此诗向二人进行了传播。幕游士人在游幕期间的这种诗歌创作现象是极为寻常的。幕游士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幕主、幕游地的当地名流进行唱酬,形式多样,有赠答、次韵、叠韵、赠别、寄酬等多种形式。唱酬形式的不同,意味着幕游士人传播他们作品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幕游士人的这些唱酬活动,使自己的诗文篇什在结集刊刻之前,已拥有了不少读者,得到了一定范围的传播。
三、集会。这里所说的集会并非三两私人之间的小聚会,而是群体性的活动。乾嘉时期的幕府极为繁多,而以艺文幕府尤为著称于世。艺文幕府多由倡导风雅者主持,如卢见曾、朱筠、毕沅、王昶、曾燠、阮元等。作为艺文幕府,与非艺文幕府的最大区别是举行集会的频度高。艺文幕府最常见的集会是以消寒、祀苏轼生日、修禊、令节、赏玩花木名胜等作为主题的。如毕沅幕府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后,几乎每年要举行祀苏轼生日集会。在集会中,凡参与者都赋有诗作。毕沅幕府乾隆四十七年(1782)举行首次祀苏轼生日集会,据毕沅所述,与会者共“十有四人,操觚而竞赋”,而且是“预斯集者,诗无不成”②(40)②毕沅著,杨焄点校:《毕沅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36页。,每个人都参与了赋诗。这些与会者,主要是毕沅幕府中的宾僚,如洪亮吉、孙星衍、王复等。在洪亮吉、孙星衍、王复的诗文集中,我们还能找到他们这次祀苏轼生日集会中创作的诗歌篇什,如洪亮吉《卷施阁诗》卷四《消寒四集。十二月十九日,为东坡先生生日,同人集终南仙馆设祀,并题陈洪绶所画笠屐像后》、孙星衍《芳茂山人诗集》卷八《苏文忠公寿宴诗,在西安毕督部沅署中作》、王复《晚晴轩稿》卷五《十二月十九日苏文忠公生日,中丞毕弇山夫子设祀终南仙馆,各赋长句》等。洪、孙、王三人祀苏轼生日的诗作虽然题目不同,但均是此次集会中的作品。他们的这些诗歌篇什并不是私密的,而是供与会者品评赏鉴的,公开于与会的众人中。换言之,洪、孙、王三人祀苏轼生日的诗作在此次与会者中实现了传播。在上述六大艺文幕府中,以曾燠幕府与阮元幕府举行的这类集会最多。这类集会越多,幕游士人创作的诗文篇什传播的范围就越广,因而影响也就越大,毕竟,不是所有的这类集会都是封闭的,仅限于本幕府中人,也会有幕府外的名流参与。如卢见曾的红桥修禊集会,参与者达63人之多。③(41)③王昶:《湖海诗传》卷一八,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48页。这63位与会者中,确为卢氏幕府中宾僚的,顶多占三分之一,馀者或为当地名流,或为道经当地的过往名流。尽管卢见曾事后将参与此次红桥修禊与会者的诗作汇集刊刻了,但幕游士人在此次与会过程中已传播了自己的诗歌作品,虽然传播的范围不算大,但也是相当可观的。乾嘉时期幕游士人参与的这类集会,隔三差五地在不同的地点举行。据陆继辂《郡斋公宴图记》所述,庐州知府钱有序幕府,文宴之会一般一月举行两次:
嘉兴钱公治庐州之五年,岁稔而民安,案无奇袤斗很之牍,于江北八郡最称上理。得以从容多暇,与僚属为文酒之会,月一再举,行以为常。①(42)①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一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5页。
由钱有序幕府举行的文宴的频率,可以推知艺文幕府集会的大致情形。幕游士人参与这样的集会,并创作诗文作品,从而扩大了自己的诗文作品的传播范围。
四、题图。幕游士人聚集在幕府中,有较多闲暇时间。在这闲暇的时间里,他们纷纷从事艺文创作,诗文之外,最多的是进行绘画创作,赋予某种寄托。而他们创作的绘画作品,彼此之间观赏、品评。在这观赏、品评过程中,他们会表述自己关于绘画的意见。他们的这些绘画意见,大多是用题图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幕游士人诗文集中的题图诗,多为这种情形的产物。如彭兆荪入就曾燠幕府后,仅《小谟觞馆诗集》卷八就有题图诗《题襟馆分咏先贤画像,予得二首》《钱献之州倅坫归渔图》《题涧薲焦山拓鼎图即送其之山左》《簳山草堂图为华亭何氏作》《题莲裳青芝山馆图五首即次其自题韵》《频伽来邗上,过予寓斋。酒间赋赠五首,即题其灵氛馆图》《题频伽病起怀人册子二首》《仇十洲崆峒访道图》《抱琴图》等;乐钧《青芝山馆诗集》卷十二有题图诗《宾谷都转惠题访琴图次韵奉答》《题歙县鲍肯园棠樾村图二十六韵》《题宾谷都转赏雨茅屋图》《题仇实父桓伊吹笛图》《题单竹轩运判山水知音图》《题青芝山下卜邻图次宾谷都转韵二首并引》(都转与余及万廉山明府有卜居姑苏木渎之约,故为此图,廉山笔也)②(43)②乐钧:《青芝山馆集》诗集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90册,第532页。、《敬题王文成公画像二十四韵》《杭州沈秋湖赞府出其内子畹君夫人手画蝴蝶草虫册子,索诗,各题二绝,即以易画。夫人山阴朱氏,名怀兰,画品精妙,香墨欲飞,洵可宝也》(此诗为乐钧自扬州归江西临川,途经杭州所作)等。彭兆荪、乐钧这些题图诗所题之图虽然不全是出自幕游士人的手笔,但他们的题图诗却借助所题之图(有些题图诗确实是题于图上)或题图诗的书写现场而得以传播。幕游士人创作的题图诗虽然多寡有异,但题图是他们的诗歌作品得以广为传播的重要方式,因为观赏画作的人是远远多于画作的拥有者及题图诗的书写者的。
幕游士人诗文作品的传播当然不限于上述四种形式,但上述四种形式无疑是幕游士人诗文作品的重要传播方式,他们的许多诗文作品在刊刻之前,即因这些传播形式而拥有了更多的接受者。士人因幕游而朋友广泛,而这广泛的友朋均是他们诗文作品的传播对象。与僻居故乡、拘于乡土的士人比较起来,幕游士人的诗文作品传播的范围自然更为广泛一些,传播方式也更为多元化。
五、馀论
上述四个方面,是幕游对于士人的文学意义。此外,幕游对士人而言的文学意义还在于扩充自己的社会或学术的视野,近距离地接触社会现实,丰富与拓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如沈起凤在小说《谐铎》中对当时社会中的黑暗现实进行有力鞭挞与犀利批判,大多源于他多年幕游过程中对社会的深刻认识。而幕游对于士人的文学意义,曾幕游多年的凌廷堪在《大梁与牛次原书》中有过深刻的揭示:“仆少生海澨,长游水乡,未睹中原之雄阔与夫高山大川之形势,譬鸡栖于埘,燕巢于屋,比因饥寒所驱,获此壮观,携史而访苟晞之屯,载酒而问侯嬴之里,其方寸之盘纡,陈编所触发,盖不仅如前所云云也。”③(44)③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三,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0页。凌廷堪在这里表达的是:游幕能够增长自己的阅历,扩充视野。他虽然不曾直接语及幕游对于士人的文学意义,但是将其所论稍作演绎,至少指陈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士人因幕游而增长、扩充了自己的阅历与经验。而增长、扩充的这些阅历与经验,其中大多会转化为自己的文学表达。游幕士人在幕游期间的文学书写,大多是自己增长、扩充的阅历与经验的表达,只要翻开幕游士人的诗文集,我们一定能获得这一认识。
幕游士人在幕游过程中的文学表达,由于有深入的现实体验,因而较之流连光景、交际应酬的文学表达,更为深切感人,也更具有社会意义。如同是性灵诗人,大半生优游在随园的袁枚年寿高,名气大,其诗大多以巧思、灵趣取胜,却缺乏深邃的思致与深切的感染力,以及深广的社会意义;与之相反的是,有过多年幕游经历的黄景仁虽然年寿不及袁枚之半,但他的诗大多是抒写自己在社会中苦苦挣扎的生活感受,真切感人,赢得了不同阶层士人心灵上的共鸣。正因为如此,张维屏在《听松庐文钞》中称黄景仁为“天才”“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馀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①(45)①张维屏:《听松庐文钞》,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7407页。认为黄景仁是清代自王士禛以后最为杰出的诗人。黄景仁在诗歌创作上杰出成就的取得,固然与他的努力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其抒发自己多年幕游生活的独特感受所致。可见,幕游在某种意义上关系着文学成就的大小。
嘉道时期的姚椿在《史赤霞遗集序》中的一段话,尤能揭示出幕游对于士人文学创作的意义:“古之人才聚于幕府者为多,而于诗人为尤盛,盖其见闻繁富,阅历广博,凡欣愉忧愤之情,身世家国之故,其于人己晋接,皆足以徵性情而抒才藻,自风雅以来,其诗作于行旅者多矣。而唐宋以降,幕府征辟之士,班班著见载籍者,大抵其客游之作居多也。”②(46)②姚椿:《通艺阁文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22册,第319页。从创作角度,姚椿指出了幕游对于士人的文学意义。因此,清代士人的幕游,无论是对自己的文学书写,还是对整个清代文学生态而言,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