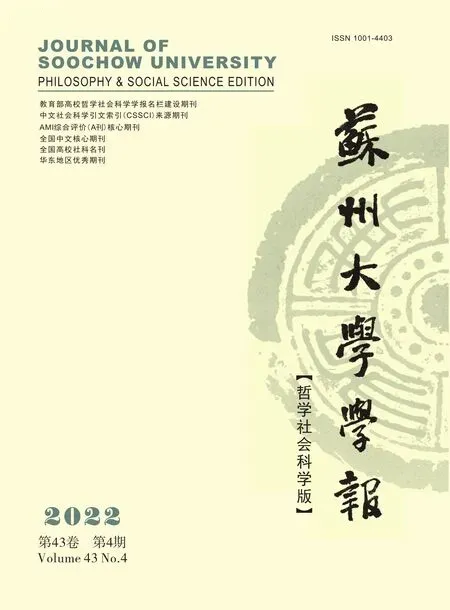论奈保尔殖民地社会空间的他者建构
2022-12-06张弛
张 弛
(南京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加勒比地区又被称为西印度群岛,地域范围包括加勒比海上诸岛,中美洲的伯利兹,南美洲东北部的法属圭亚那、圭亚那和苏里南。1932年,印裔英国作家V.S.奈保尔(V.S.Naipaul,1932—2018)出生于此。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当西印度群岛的文学热潮趋于平缓并有衰退趋势时,奈保尔开始重塑文化身份。虽然欧洲白人对接纳有色人种表现得极为严格、挑剔,但他仍然执意“要将自己的西印度身份变成英国的”,并在录制BBC节目时强调自己18岁便离开特立尼达,早已“摆脱对这些殖民地的政治关怀”(1)Patrick French.The World Is What It Is: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S.Naipaul.London:Picador,2008,pp.208-209.。
出生地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极为重要,对创作者尤其如此。他们的创作动机和性格受其影响,作品中表现的空间与之关联,因此有学者指出出生地对于“认识帝国时代和当代世界的地理极为重要……不论是失去的家还是回归的家”(2)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作为奈保尔的出生地,加勒比地区不仅承载了作家丰富的文学想象和复杂心态,还是欧洲殖民者假借发展之名进行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之地。表面上看,奈保尔在非虚构作品中回溯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历史时,创作视角一度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裹挟,采用投影式的辨识法将对肤色的恐惧和受禁锢的欲望投射到地理和社会空间中,以歧视色彩浓郁的种族区分,将加勒比殖民地建构成一个等级分明的异托邦。在西方文明的凝视下,地处殖民版图边缘的加勒比异托邦中充斥着主体对他者的规训和监视,有色人种和自然环境始终处于被扭曲、被苛责的困境中,导致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的蔓延。
显然作家对加勒比社会空间的真实呈现和犀利批判是对殖民主义暴行的高度还原,那些看似具有“辩护”色彩的描述,旨在促使人们不再以猎奇的目光审视前殖民地,而以辩证的方式反思异托邦内部的权力交锋与他者的生存困境。可以说,奈保尔对第三世界的刻画虽“难免带有西方思想烙印”和“政治参与色彩”,但其文本潜藏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体现了对第三世界社会不公的愤怒,这种愤怒恰恰“表明了作者的关切之所在”。(3)方杰:《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虚构与纪实:V.S.奈保尔作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页。
一、异托邦内的流散者:渴望逃离的无根人
奈保尔在游历印度时曾谈及自己的出身,以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印度人后裔自居。虽然特立尼达人种各异,但印度裔生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里,遵从特定的饮食习惯,拥有特别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尽管这些印度后裔“无法摒弃特立尼达……生活在一个充满社会差异和种族问题的社会中……[他们]却一直显得非常纯真……以传统的印度式等级制度区分其他族群”(4)V.S.Naipaul.An Area of Darknes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7,p.31、p.36.。19世纪中期,为缓解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劳工短缺的压力,殖民者开始从印度向特立尼达输送契约劳工。加勒比地区其他岛屿输入的人员构成单一,通常只有白人殖民者和黑人奴隶,但特立尼达输入人员却繁复驳杂。除了殖民者与黑奴之外,还有美国被解放的奴隶,南美来的流浪者,华人海员和劳工,印度契约劳工,以及极小一部分印第安人后裔。印度契约劳工中婆罗门只有不到六分之一,其余大多是来自印度北方的低种姓穷人。他们栖身于乡下的种植园,与当地的宗教文化和生活圈子格格不入,“对身处陌生社会感到惶恐,对人数占优的黑人感到恐惧”(5)Patrick French.The World Is What It Is: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S.Naipaul.London:Picador,2008,p.5.。由于语言不通,受教育程度低,印度人在岛上饱受歧视,生活环境也相对封闭。
作为极少数婆罗门移民中的一员,奈保尔的祖父为其家庭保留了非常纯正、浓郁的印度文化底蕴。他在特立尼达修建的房屋丝毫没有殖民地建筑元素,沿袭了印度北方邦厚重的平房特色。对祖父而言,这是特立尼达中央的印度北方村落;对奈保尔而言,这是他对印度构建现实与虚幻交错想象的发源地。尽管初访印度时遭遇的社会黑暗现状一度让他心态失衡,试图把自己从印度后裔这一族裔身份中剥离出来,但踏足印度之前,他对印度极为神往,印度文化飞地的存在成为他心中的一种“奇迹”(6)V.S.Naipaul.An Area of Darknes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7,p.31、p.36.。相比之下,特立尼达虽是奈保尔的实际出生地,也见证了他赴英求学前长达18年的人生历程,但第一次重返前,以特立尼达为代表的西印度群岛只是一个让他心生恐惧的符号。当博巴迪拉号客轮抵达西印度群岛时,他因担心离开轮船后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而拒绝下船。整座城市保留了熟悉的风格,现代化进程虽有瑕疵,却也让城市得到发展:街上安装了更多的霓虹灯,汽车数量也翻了倍,整座城市在钢鼓乐队的鼓点中充满勃勃生机。但在奈保尔看来,这些积极的城市发展元素只让他感到厌恶和失望。
对幼年奈保尔而言,印度是其祖辈流散的原点,是存在于想象中的虚构乌托邦,而特立尼达是其出生地和少年时期的实际居住地,是他曾经的家。通常,“家”是人类躲避外界伤害、得到庇护的空间,“回家”往往与温暖、舒适的感受相关联。但返家的奈保尔非但没有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安全感,反而满是烦躁和厌恶。可以说,特立尼达的印度社区成为乌托邦幻象在现实世界的投射,是一种被扭曲、被异化的异托邦。1967年3月,福柯在(Michel Foucault)在法国建筑研究会上以《另类空间》(“Des Espaces Autres”)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异托邦是一种在现实场景实现的乌托邦,混合了虚构和现实特质,即同时具备在场性与不在场性。福柯强调,异托邦具有普遍性,“世界上可能不存在一个不构成异托邦的文化”。(7)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王喆法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第54页。奈保尔发现,似乎外界的每一件事物都变异了。他上学时经常感到别人对印度文化传统的歧视和侵犯。每到此时,他都选择退缩,也无法和他人正常交往。上小学时,奈保尔在课本扉页上写下誓言,发誓要在五年内离开特立尼达,六年后他得以兑现承诺离开了加勒比。幼年时写下的逃离誓言印证了奈保尔的流散者特质。根据萨福兰(William Safran)的定义,流散者具备以下特征:他们或他们的祖先从某个特定的原点被驱散至多个边缘地域,但是他们依然对原始家园的历史、位置和文化成就保留集体记忆和神话般的想象;同时,他们无法融入迁居地的文化圈子,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疏离与隔绝,只能通过与故国的间接或直接联系表明自身的种群意识。(8)William Safran.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Myth of Homeland and Return,Diaspora,No.1,1991,pp.83-84.这种特质致使奈保尔无法与加勒比地区其他族群获得情感联系,处于边缘地位,也无法获得认同感。
同时,逃离誓言也揭示了奈保尔对于特立尼达的矛盾感情。一方面,他无法选择自己的移民身份,被迫在青少年时期受制于特立尼达社会和文化环境,继而产生拒斥心理,极度渴望逃离;另一方面,特立尼达的文化氛围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逃离途中,他觉得怅然若失,“加勒比海在阳光下闪耀,像是丁尼生在诗篇中描写的那样,这个我在其中渡过全部时光的世界缓缓离我而去,仿若一个我从来未曾接触的世界”。(9)V.S Naipaul.The Enigma of Arrival:A Novel in Five Sections.London:Penguin Books,1987,p.98.赛义德(Edward Said)将这种矛盾心理定义为“中间状态”(median state),即从未与新环境融合,也未曾与旧环境切割,处于半融入、半脱离的状态中,一方面被乡愁和感伤困扰,另一方面却扮演熟练的模仿者或是秘密的流放者。(10)Edward Said.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New York:Vintage Books,1996,p.49.也正是这种对特立尼达若即若离的复杂情感,让奈保尔对加勒比地区的态度在流散过程中发生转变。从少年时作为印度流散者的抵触排斥,到初次重返时作为帝国代言人的讽刺批判,最终以一种沉着冷静的宽容态度挖掘加勒比地区殖民活动的历史真相。刚接到出版社约稿要求时,他坦言“特立尼达几乎没有历史,奴隶制影响了其他岛屿,但它没有对特立尼达产生任何大的影响”。但当他真正实地造访后,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加勒比地区有“一段可怕的历史”,因此他尝试记录下人类的故事,“使一切活起来”。(11)法·德洪迪:《奈保尔访谈录》,邹海仑译,《世界文学》2002年第1期,第125页。
二、流动的异托邦:中途航道上的愚人船
在游记《中途航道》(TheMiddlePassage,1962)中,奈保尔乘坐西班牙移民船博巴迪拉号开始重返故土的旅程。作为连接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交通工具,轮船是一种移动的异托邦,是“空间的漂浮的一块,一个没有地点的地点,它自给自足,自我关闭,投入到茫茫的大海之中,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段航程到另一段航程,从关闭的房屋到关闭的房屋,一直到殖民地”(12)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王喆法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第57页。。轮船是白人殖民者建构殖民地秩序的必要前提。借助轮船这一载具,欧洲向新大陆海运去无数的士兵、传教士、牲畜、作物、奴隶和劳工,随同带去的还有致命的病菌,实现了欧洲地域的延伸。对于欧洲以外的种族、物种和地域而言,轮船是致其沦为殖民他者的罪魁祸首之一。殖民扩张时期,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被乘船而来的欧洲航海家们所征服。欧洲人带来的动植物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彻底改变了殖民地原有的生态系统;致命疾病在美洲扮演的角色甚至比枪炮更重要,对欧洲疾病毫无抵抗力的原住民屡遭灭顶之灾。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被迫离开家乡,沦为白人的奴隶。此外,欧洲人在殖民地大肆掠夺,大到矿产资源,小到各类生活必需品都经由海运拉回欧洲。换言之,轮船是具有强烈殖民空间隐喻的双重异托邦,一方面,轮船连接宗主国和殖民地,在航线上始终处于位移之中,是流动的空间;另一方面,轮船又是静止和封闭的,乘客们无法接触外界的空间场域。在等级分明的空间内,欧洲人的主体性得到强化,而被迫进入这一空间的移民和奴隶受到控制和规训,成为空间的他者。
博巴迪拉号就是这样一个等级森严、规训意味极强的异托邦。轮船的名字隐含了殖民与被殖民的权力关系: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Francisco Bobadilla)是西班牙派驻加勒比地区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殖民地法官,负责调查西班牙政府对哥伦布兄弟的指控,并于1500年将哥伦布兄弟收监,同年押送回西班牙。作为西班牙政府官员,博巴迪拉通过排他手段剥夺了以哥伦布为代表的意大利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殖民统治,生产并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殖民空间,强化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所有权意识,把抽象的主体性塑造过程付诸殖民活动实践之中。
奈保尔对船上成员明确划分等级:旅客和移民。旅客属于第一层级,只包括住在头等舱的人。他们确立了一种极具压迫性的边界,将船上其他西印度移民限制在规训范围内,将其建构为被驯服的种族他者。第二层级包括所有住在经济舱的乘客。尽管奈保尔将他们统一划分为移民,实际这一群体内部依然存在不同阶级:受过英国教育、举止优雅的移民首领、人数众多的西印度移民和最底层的黑人。空间等级是权力秩序的表现,空间主体通过分隔空间实现对空间他者的规训。作为主体的旅客和作为他者的移民之间有着严格的空间区分。头等舱的旅客拥有自己的单间,可以自由出入头等舱和经济舱;经济舱和头等舱之间有人为竖起的隔离栏,移民们不允许进入头等舱区域活动。旅客和移民之间的空间隔离体现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隔离状态,旅客们通过在空间中的自由位移彰显自己的主体权威,而移民们只能在轮船边缘位置的甲板下活动。偶尔天气好转,移民们才被允许走上甲板。权力秩序压迫着空间他者,空间主体“确保在一定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利润,也力图抓住时间的每一个片断而不至于让它白白浪费”(13)汪民安:《福柯的界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
移民们被丑化、物化成空间内的权力他者。靠救济金度日的屠夫被打上贫穷的标签,在头等舱甲板这一文明的区域内来回奔跑,暗示其野蛮的未开化状态。殖民地男孩被住在头等舱的葡萄牙人科雷亚(Correia)称为“战俘”(captive)。此处,“战俘”一词蕴含浓重的殖民色彩。中途航道原指运奴船从非洲向美洲输送黑奴的航线,奈保尔借这一词汇在连接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新“中途航线”上再现了帝国时期的殖民隐喻。同时,头等舱旅客将殖民地男孩视为“俘虏”的物化过程体现了殖民主体对工具理性的滥用,将殖民地的自然、动物和居民都视为工具性“他者”,使其“要么作为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被随意消耗,要么作为无尽的资源永久服务于人类”(14)Graham Huggan and Helen Tiffin.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New York:Routledge,2010,p.4.。
自从被科雷亚“俘虏”后,殖民地男孩除了吃饭和睡觉回到经济舱,其他时间一直待在头等舱。头等舱是欧洲人主导的权力空间,这里一个黑人也没有:葡萄牙人科雷亚来自英属圭亚那,特立尼达人菲利普(Philip)可能是白人或者犹太人,有色人种麦凯先生(Mr.Mackay)以欧洲人自居,他的五官和肤色看起来也更像白人。奈保尔则自视为英国公民。头等舱旅客将殖民地男孩留在他们主导的权力空间,象征对男孩生存空间的侵占与剥夺。作为空间他者,男孩被头等舱旅客包围,在受监视的过程中感受同化。赛义德指出,欧洲人通过对殖民地人的监护,按照种族和宗教对他们进行划分,让他们变得“依赖于欧洲的存在,或许是一个殖民地农场,或许是一个主流话语结构,他们均可被归属其中并发挥效用”(15)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7页。。
高大的黑人是个精神病患者,手捧《十诫》(TheTenCommandments)一言不发,隐喻被理性排斥的疯癫状态。这里,疯癫的黑人和游轮与福柯的“愚人船”意象不谋而合。“愚人船”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想象中,精神错乱的乘客被原先的城镇驱逐,搭乘帆船踏上流浪之路,前往其他城镇。对已知的出发地而言,他们是容易招惹麻烦、和理性截然相悖的他者,因此被社会排斥、驱逐;对未知的目的地而言,他们焕然一新,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载有疯人的航船既是囚禁疯人的放逐载具,又是给他们净化心灵的场所。福柯指出,“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透过真实和虚幻交织的地理位移确定疯人的边缘身份。(16)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殖民地黑人在宗主国患上精神病,受到欧洲理性和主体他者的排斥,被遣送回国。游轮既是他的囚室,也是他的流放之地,让他在航行中始终处于边缘地带,始终提醒着黑人的他者身份。《十诫》则是理性的象征,黑人在放逐中依然携带基督教圣典契合了被隔离的麻风病人向基督爬行的场景。虽然被欧洲主体放逐,但黑人依然试图在放逐中得到主体的宽恕和拯救。借此,奈保尔既对殖民地居民对白人主体性身份的趋炎附势和盲目追求表达了不齿和无奈,也暗讽了欧洲主体将排他行为神圣化的伪善做法。正如福柯所言:“遗弃就是对他的拯救,排斥给了他另一种圣餐。”(17)②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113页。
黑人总是独来独往,沉默地走来走去,读着《十诫》。沉默意味着主体性和话语权的丧失。《十诫》既是基督教圣典,也是知识载体,隐喻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即把“精神当做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权力主体通过知识话语对弱势者进行监视和规训,旨在控制黑人的精神并强化其他者身份,以巩固主体在空间内的权威。登上游轮后,黑人的沉默失语意味着权力主体阉割了精神病人的言语功能,剥夺了他的话语权,使其始终处于被言说的位置。这种无语—剥夺—疯癫相互印证,如福柯所言:“不管是被排斥或是被秘密地赋予理性,疯人的言语是不存在的,人们正是通过其言辞而确认了他的疯狂,其言辞是区别理性和疯狂的场所。”(18)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语言与翻译的政治》,袁伟、许宝强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黑人在反抗隔离时语无伦次的怒吼和尖叫也成了强化其疯人身份的证据。甲板上的隔离栏不仅在物理空间上将头等舱和经济舱进行区域划分,也在精神层面分隔出理性和疯癫。栅栏另一侧的船员和乘务员则扮演了病患监护角色,成为维护空间的稳定秩序和静态结构的规训手段,他们通过冷漠目光和规训话语让疯癫的黑人感受到微观权力的压迫性存在。
疯癫的黑人在规训中变得驯顺,船员们给他打了镇定剂后将他安置在医务室。麦凯先生感叹道:“太糟糕了,这么俊朗的畜生被逮住了。”(19)V.S.Naipaul.The Middle Passage.London:Andre Deutch,1974,p.35.作为头等舱的一员,麦凯先生自然也是理性主体的象征,他使用言语对黑人进行污蔑,称其为“畜生”(beast)。在菲利普眼中,黑人反抗空间隔离的行为是对西班牙长官的严重“侮辱”(insult),是罪恶的,应该受到谴责。而黑人被打了镇定剂,语言功能进一步遭到剥夺,无法给自己辩护。不具备理性的疯人成为动物性的野兽,回归到未开化的原始状态,彻底沦为受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侵害的双重他者。医务室的门敞开着,来往乘客可以看到蜷缩在角落的黑人。医务室传统的治愈功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监狱的监视与惩罚机制,其存在目的并非为疯癫者提供治疗服务,而是以禁闭作为手段将疯癫的他者排斥出轮船的社会空间,以维护船上的空间秩序与权力主体的实际利益。同时,医务室也是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异托邦,黑人可以进入这一物理空间,但他与医务室为其他乘客们提供的常规治疗空间是相互绝缘的。对于作为空间内权力他者的黑人而言,医务室既是真实的空间又是非真实的空间,既是休息的场所,也是遭受权力压迫和暴力侵害的囚笼。
三、权力主体与空间他者:传教站和监狱里的规训与监视
福柯认为,异托邦可以开辟幻象空间,即在原有的空间之外创造出另外一个貌似真实的空间,它既是原始空间的镜像,又对原始空间起到补充作用。这类异托邦的代表是英国人在美洲创立的清教徒社会,“基督的符号如实地到处再现,基督徒是这样用他的基本符号来标出美洲世界的空间和地理的”。(20)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王喆法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第57页。换言之,欧洲人以上帝之名在殖民地兴建基督教场所不仅成功分割了殖民地的物理空间,还让宗主国政体得以异域重现,使之成为凌驾于殖民地社会空间之上的霸权所在,为殖民统治和空间扩张提供了政治基础。
帕瑞玛(Paruima)的传教站便是具有类似功用的异托邦。传教站具有浓重的种族主义气息,是按照殖民者意愿建立的宗教符号。传教士的殖民教化,为殖民者的空间扩张披上合法外衣。牧师一家是空间内的特权阶级,通过时间安排对周围居民的生活节奏进行间接规训。每到周六,站内每个人都要穿上礼拜服饰。晚上牧师的妹妹播放彩色幻灯片时,印第安观众们从临近的村子云集而来,山间的小路上和传教站的庭院里都挤满了人。奈保尔强调了牧师一家的种族特性,他们是金发碧眼的美国白人。在加勒比地区,人们“把牧师看做上帝的使者,认为他们和政府部门的高级公务员一样都应该是白人”(21)V.S.Naipaul.The Middle Passage.London:Andre Deutch,1974,p.157.。换言之,在殖民地空间内,权力主体和他者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对立关系在空间规训作用下逐渐变成文化认同关系,他者对殖民文化的抵触心态被内在自觉取代,殖民过程从物理空间向心理和文化空间渗透。
“白人—印第安人”和“人类—非人类”的话语霸权导致传教站周围的非人类元素也处于被操控、被言说的状态。传教站是一圈新修的木头房子,建在河岸边的山坡上。新粉刷过的屋子里弥漫着刚被砍伐的热带松木的新鲜辛辣味道,屋外的空地上残留着一些尖利的树桩。有几个树根遭到焚烧,浓厚的白烟到处都是。露丝莉(Cheryl Lousley)指出,“空地”意象不仅象征着殖民统治对传统文化和政治团体的抹杀,还代表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设定,即自然必须为人类社会服务。(22)Cheryl Lousley.Hosanna Da,Our Home on Natives’ Land: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Democracy in Thomas King’s Green Grass,Running Water,Essays on Canadian Writing,No.81,2004,p.22.这里,牧师不仅在传教中借当地人的愚昧凸显自身的文明主体身份,还借砍伐林地、焚烧树木实现了对自然的剥削和控制。传教站里有条健壮的狗,它既怕黑又怕虫子,还很容易被突然的动作所惊扰,一直活在恐惧之中。奈保尔试图用感官体验传教站周围的自然环境。他闻到了松木新鲜的味道、看到了河岸巨石上承载的壮阔历史,但被砍伐的残桩和被焚烧的树根体现了人类对非人类物种的效用性和工具性挪用。传教站的狗不仅没有在驯化过程中获得理性,反而发生了物种退化,变得胆小怯懦,丧失了动物本该拥有的野性。狗被剥夺了作为动物存在的主体性,从而坐实了空间内的他者地位。正如哈根(Graham Huggan)和蒂芬(Helen Tiffin)所言:“无论是环境种族主义,还是由来已久的物种主义,都受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文化驱使,长期以来为利用非人类他者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辩护,而这一切都与霸权中心主义脱不了干系。”(23)Graham Huggan and Helen Tiffin.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New York:Routledge,2010,p.5.
在某种意义上,传教站既是欧洲人开展殖民活动、主导文化入侵的政治工具,也是他们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对当地人进行规训和洗脑的无形空间。相比之下,监狱则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进行监禁和惩罚的有形空间。奈保尔在《黄金国的失落》(TheLossofElDorado,1969)中详细描述了19世纪初期特立尼达西班牙港的监狱。作为公共设施,西班牙港监狱代表法律和权威,但支撑它运营的实际出资人却是当地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因而监狱里的囚犯大多是种植园里的黑人或街上的黑白混血儿。监狱最下层的地牢都是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房间里闷热难当,温度常年接近40摄氏度。犯人在这些被当地人称为“燃烧囚笼”的房间里待不了几天就精疲力竭。“燃烧囚笼”的居住环境很糟糕,五个从蒙塔朗贝尔男爵(Baron de Montalembert)的庄园里送来的投毒犯在里面待了好几周,“赤身裸体地在热气蒸腾的黑暗中挤作一团”,每个人双腿都被“捆在铁质刑具上难以动弹”,他们都经历了拷打,“有一个人看起来已经死了”。(24)V.S.Naipaul.The Loss of El Dorado.New York:Vintage Books,2003,p.221.第二层有几间较大的囚室,其中一间长宽均为20英尺的正方形牢房里关了五六十个黑人男女,他们赤裸着身体,腰部和颈部被铁链紧紧拴住。其中有十几个饿得奄奄一息,骨瘦如柴,状若鬼怪。
福柯认为,监狱和瘟疫收容所一样,是一种封闭、割裂的异托邦场所。“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2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21、221页。奈保尔笔下的西班牙港监狱也是如此,这里并没有采用全景敞视的现代监狱模式,而是延续了封闭、剥夺光线的原始牢狱风格。黑人囚犯被铁链“镶嵌”在牢房的刑具上。狱卒、警察和偶尔造访的殖民地官员可以随时出入空间审视囚犯,通过凝视对囚犯进行他者化的操控,进而巩固自己的主体身份,显示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正如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言,当主体进行注视时,客体的存在随着主体目光向主体靠拢,使主体获得存在性。而黑人囚犯“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漆黑的囚室剥夺了他们凝视的能力,被迫成为被探查的他者。
西班牙港的大多数黑人都是在种植园工作的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每个奴隶都被明码标价,是可以损耗的工具。殖民地总督皮克顿将军(General Picton)是奴隶制的坚定拥护者,认为黑人天生就是奴隶,应该受管制,监狱里的黑人囚犯应该受到拷问。18世纪末期,特立尼达两度出台《黑人法典》(NegroCode)对黑人进行规训和限制。1790年的法典规定,黑人来到特立尼达后的第一年里要接受天主教洗礼,日常饮食和衣着都必须符合规范,只能在种植园从事农业耕种,是种植园的不动产,不同种植园的黑人不能交流。黑人男性不能自主与女性交往,他们的婚配依赖种植园主购买黑人女性或将他们卖到其他种植园。种植园主有权监禁和鞭打自己的黑奴,如果黑奴打白人则会被割掉鼻子或身体其他部位。1800年的新法典进一步对黑人在殖民地空间的权益进行限制,比如黑人要随身携带证件,晚上9点后不得离开居住地。西班牙港有六名警察,他们最喜欢在宵禁后上街抓捕违规的黑人。殖民者是殖民地异托邦的空间主体,在他们看来,黑奴总是与偷窃、巫术、阴谋等贬义词产生关联,黑人的肤色代表了“低级感情、不良倾向、心灵的阴暗面、道德标准低下的原型”(26)李清云:《福克纳小说中“他者”的空间性解读》,博士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8年,第24页。。作为西方殖民主体的代言人,警察的存在目的在于维护殖民地异托邦的秩序。他们对黑奴的监视和规训标志着文明对野蛮、理性对非理性、主体对他者的权力压制。警察和总督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律法,从时间和空间上对黑人的活动进行规约,显示了社会权威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一种驯顺—功利的关系”(2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5页。,让整个特立尼达殖民地社会成为对黑人进行驯化约束空间,是监狱内部向外部社会的延展。统治阶级依靠社会空间进行持续性压迫,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受种植园主奴役,成为驯服工具。
监狱的第三层是阁楼,这里有几间面积很大、较为通透的牢房用来羁押白人囚犯。来自费城的苏格兰作家麦卡勒姆(P.F.McCallum)是西班牙港第一特派员弗拉顿上校(Colonel William Fullarton)的支持者,在弗拉顿与皮克顿将军的政治斗争中受到牵连,被羁押在此。尽管麦卡勒姆对居住条件很不满意,称牢房为特立尼达的巴士底狱,但他的房间却十分宽敞,有20英尺宽、10英尺长,他是房间里唯一的囚犯。楼下的黑牢里关了五六十个被铁链捆住的黑人,“啷啷作响的镣铐声和身体与排泄物臭烘烘的味道从楼板的裂缝中升上来”(28)V.S.Naipaul.The Loss of El Dorado.New York:Vintage Books,2003,p.235.。在监狱里白人占据的物理空间远远超过黑人,种族主体与种族他者的差异通过囚室的分配得以呈现,白人与黑人不仅在监狱外部的社会空间内构成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属关系,更是在监狱的内部空间形成隔离。
空间差异进一步影响了种族差异,加剧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像麦卡勒姆这样被单独羁押的白人囚犯很少遭受酷刑惩罚,而黑人和混血儿的境遇则悲惨得多。麦卡勒姆口渴时狱卒给他喝掺水的朗姆酒,饿时有仆人送来食物,仆人还送去纸笔以供他在狱中写日记。他只在监狱里待了四天,没有受到任何刑罚的折磨。而在这四天内,仅仅被他记录的黑人受刑事件就近十起。第二天,他记录下了狱卒瓦罗(Vallot)用“四柱”法鞭打四名黑人的过程,两男一女,还有一个小男孩。鞭子中间粗两头细,长约四英尺,每一鞭都能留下三到四英寸长的伤痕。接受完皮克顿的问话回到监狱时,麦卡勒姆看到瓦罗把两个黑人捆在树桩上鞭打。第三天早上,又有三个黑人被捆在树桩上鞭打。瓦罗没有任何监管者,他只对殖民地总督负责。相对于瓦罗而言,监狱内的其他人都是空间他者,生不出任何反抗念头,自觉处于空间的边缘位置。一旦他们违背了空间秩序,就会遭到权力主体不加节制的暴力惩戒。
瓦罗不仅是对囚犯身体进行规训和改造的实行者,还是监狱空间等级规则的制定者。福柯指出,人们无法自由进出监狱和军营这类异托邦场域,只有“经过一些许可”,或者完成一些规定的任务,外人才能进入这类场所的内部空间。(29)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王喆法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第56页。在西班牙港监狱,人们只有经过瓦罗许可才能进入监狱,就连第一专员弗拉顿上校也不例外,在瓦罗的带领下才能进行视察。瓦罗甚至还能决定监狱内犯人的去留。尽管弗拉顿认为按人头征收监禁费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做法,但瓦罗依然对监狱内的每个黑人囚犯按每天一先令收费。如果种植园主要求切掉犯人的耳朵,还得向瓦罗支付一笔额外的切耳费。付不起费用的有主黑奴被瓦罗视为监狱的负担。一贫如洗、身无他物的自由黑人囚犯则被他当成私有财产向外出售。
由此可见,作为监狱内部空间的绝对权力主体,狱卒瓦罗借助暴力强权和肉体惩罚,对一切扰乱空间秩序的僭越者滥加训诫。这样一来,监狱的规训机制逐渐体制化,进而成为一种非常严苛的纪律,而黑人囚犯们则不得不在肉体和意识形态上屈从于空间主体的暴力征服,最终被驯服成巩固殖民统治政权的工具。
四、结语
在奈保尔笔下,加勒比的社会空间呈现精神疏离、混乱、时空倒置等负面特质,是一种否定性的殖民地异托邦。同时多样化的殖民地异托邦具备破坏稳定的功能,这种消极空间的存在解释了社会空间固有的混乱和无序(30)Sara Upstone.Spatial Politics in the Postcolonial Novel.Farnham: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24.。可以说,奈保尔把加勒比地区塑造为充满压迫和对抗的负面空间,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被空间环境侵蚀,“他们的个性和意识都直接取决于他们所面对的空间状况,否定性空间生产了他们作为边缘人、流亡者和多余人的身份”(31)潘纯琳:《论V.S.奈保尔的空间书写》,博士论文,四川大学2006年,第92页。。在博巴迪拉号客轮、传教站和西班牙港监狱中,殖民者和统治阶级是空间内的特权阶级。他们利用空间主体的绝对话语制定了符合自身利益的社会规范和法制观念,并据此对空间进行种族主义色彩浓重的等级和区域划分,强迫有色人种和黑人成为被监视和被规训的对象,使其成为驯顺的空间他者。如此一来,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范式始终影响并蚕食着加勒比当地人的自我意识,使他们在敬畏西方文化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被动承受西方主体的扭曲想象和肆意言说,等待殖民主体的界定和承认,进而成为主体实现自我意志的工具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