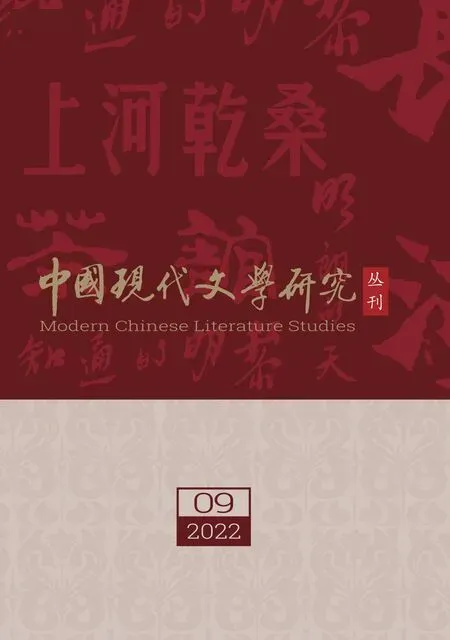诉苦·牲畜情结·劳动互助:马烽土改叙事独异性分析※
2022-12-06李致冯瑶
李 致 冯 瑶
内容提要:农民通过土改实现政治“翻身”后,农村社会生活变动首先延伸到生产关系和物质生活层面,牲畜情结、阶级觉悟和新型劳动关系(变工互助、合作生产)的龃龉与磨合成为马烽关注和思考的对象,而这恰恰被很多聚焦政治翻身的土改叙事小说所忽略。马烽创作于1948—1949年的《金宝娘》《解疙瘩》《村仇》借助斗争地主诉苦、牲畜情结和劳动互助等土改话语元素,将土改工作中流行的翻身解放、变工生产等话语具象化、文本化,在直面农村土改革命深层的同时,也形成了作家土改叙事的基本逻辑和叙事价值。
1947年春,马烽离开《人民时代》编委一职,前往崞县(今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参加土改工作。他先在大牛堡村担任下乡工作组领导,后调入工作团作随团记者,这是马烽下乡实际参与土改工作的开始,也为其后小说创作中的土改叙事奠定了基础。马烽土改题材小说数量不多却别具一格。学界对马烽创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马烽“山药蛋派”成员身份,将马烽置于“山药蛋派”背景下论述马烽及其代表作品的审美趋向、艺术特性、地域色彩,形成马烽研究的一种传统;而对马烽的土改题材小说关注不够。马烽创作于1948—1949年的《金宝娘》(原名《一个下贱的女人》)、《解疙瘩》、《村仇》正是对应于下乡参与土地改革后实际工作经验与见闻的生动表达,以土改为时代背景,凭借着对斗争地主、牲畜情结和劳动互助等文本元素的编织,将土改工作中流行的翻身解放、变工生产等话语具象化、文本化,在生成乡村基层土改“破—新”革命内在特质的同时,也形成土改工作的自我思考和呈现。马烽这一时期的土改小说,除了阶级斗争、社会秩序变动等宏大主题外,更通过文本细节展示了在农村基层政权变动深处的思想伦理变动及其对土改的思考。马烽土改题材小说在通过“斗争地主”“劳动互助”等昭示出农民群体翻身走向光明道路必然性的同时,更揭示出农村在建构崭新社会理想途中的困境及其出路。①陈慧荣:《土地制度与再分配的政治学》,《实证社会科学》(第2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一 《金宝娘》:“诉苦”与“劳动互助”的可能性建构
《金宝娘》是马烽参加土改工作后的发轫之作。这篇小说作于1948年11月,刊于1949年2月28日《晋绥日报》第四版,于1949年3月3日《晋绥日报》第四版全文刊载完毕。回溯这篇小说的文本内容,有助于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对广大农民的影响。
《金宝娘》讲述的是土改背景下贫苦妇女金宝娘(翠翠)艰难“翻身”的故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进程中,“翻身”一词的使用范围和历史语境主要体现在1946年到1947年老解放区土改时中共使用这一话语进行群众动员,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土改政治层面的代名词、农村革命的象征物,“明确提出‘翻身’就是‘土地改革’或‘革命’的同义词”②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在土改时期,“为了表达这一革命的社会的思想和状况,解放区的人民创造了不少新词。其中,几乎没有比‘翻身’这个词更能有力地表达革命过程的实质了”③[加]伊萨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冯明岩、朴莲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翻身”意味着贫苦农民打破地主剥削的枷锁,获得人身自由与解放,彻底摆脱封建地主阶级的奴役与摧残,“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价值被重新肯定。《金宝娘》中,“翻身”意味着金宝娘(翠翠)在贫下中农代表群体和下乡干部的支持下斗倒地主恶霸刘贵财,重获女性做人的尊严,进而获得在斗争会上控诉地主刘贵财的权利与资格,以此来展现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斗争激烈而又惊心动魄的全过程。也正是政治层面上作为个体“人”的重新挖掘,金宝娘完成了作为底层女性的权利再赋予与社会意义上从事劳动生产的合法性。由此可见,“翻身”不仅指向农民阶级追求光明的“反封建”行为实践,还指向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伦理与生产秩序的形成。
金宝娘借贫下中农代表会的集体意志和边区政权的合法存在实现了自我“翻身”,地主阶级刘守忠和刘贵财作为旧权威被彻底打倒。在小说的叙事链条中,除了代表大会和边区合法政权的力量支持,《金宝娘》还动用了“诉苦”的方式,形成以“斗争会”为载体的一套苦难言说与合法诉求相结合的情感宣泄机制。以金宝娘找到下乡干部“老马”争取开斗争会时倾诉受难经历为例:
在开斗争会时,金宝娘第一个控诉地主刘贵财的罪行,她讲到刘贵财怎样勾引她,怎样逼走她男人,怎样把她送到碉堡上……全场子人都在叹息,女人们偷偷地哭了。金宝娘起初是一面讲一面哭,随后一下气昏过去了。等人们拿冷水喷过来后,她忽然像疯了一样,跳了起来,头发散开了,她傻笑着,露出一口白牙齿,扑在地主刘贵财身上,用嘴乱咬。金宝也扑过去了,哭着,拿小拳头乱打,全场的人忿怒得大声叫:“打得好!”刘拴拴也挥着拳头大喊:“打得不亏!”
……代表主任田老大说:“刘贵财要交人民法庭审判,他的罪恶太多了,不光害了翠翠一家人;日本人在时当汉奸,阎锡山来了又当特务,害了多少人啊!”①马烽:《马烽小说选》,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金宝娘借以“诉苦”的方式回溯了自我(底层妇女群体)受苦难经历,“诉苦”也成为强化地主刘贵财与人民群众极端对立贲张的重要手段。围绕诉苦展开的,是地主刘贵财压榨农民群体的悲苦历史追忆,农民群体围聚下的现场倾诉,激起了彼此间强烈的情感共鸣,不仅构成了施展语言暴力的合法性基础,也在农民群体与地主势如水火的张力场中展现出土改工作的深层意义——“破旧立新,建立新秩序”,“通过成功的土改,才既能根除封建剥削的基础,又能打垮乡村原有的权威,树立新政权的威望”。①李巧宁:《建国初期山区土改中的群众动员——以陕南土改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在《金宝娘》中,“斗争会”和“诉苦”成为农民群体释放被压抑苦难情感的重要路径,也正是因为诉苦动员这一情感机制,农民群体的仇恨在强大的国家意志的疏导下转化为阶级意识的讯唤与觉醒,继而产生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上的共同体诉求,无疑,在《金宝娘》的故事框架中,“诉苦”成为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诉苦宣泄”不仅成为“斗争会”的仪式化存在,标志着旧社会的终结、新社会的开启,也成为受苦难农民谋求共同利益,实现集体翻身的有效途径。通过“诉苦”,农民的个体愤恨被整合为阶级仇恨,国家与政权意志也顺势进入这一情感机制中,“诉苦”后的农民群体在获得“站起来”所赋予的合法权利(政治翻身)后自然生发出谋求经济实利、改善自身境遇和生活条件的诉求(经济翻身)。在这里,“反封建”斗争实践确立的农民阶级主体性不仅成为进一步实现经济翻身(互助合作)的先决前提,而且蕴含着此后劳动互助的萌芽。下乡工作团干部老马了解金宝娘的悲怆经历后,“和代表们商议了一下,暂时借给了她(金宝娘——引者注)几斗粮”②马烽:《马烽小说选》,第12、13页。,作为战时紧缺物资的“粮食”在此成为吸纳被压迫农民走向我方阵营的向心力量,更富有意味的是,作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粮食出借也预示着翻身农民走上劳动互助合作道路的未来可能性,二者一道构成互助合作的有机部分,“借—还”这一乡村公序良俗促使翻身农民凭借自我劳动所得“偿还”此前集体名义下的粮食出借,在文本中,这体现为“翻身”后的金宝娘和丈夫李根元进城送给老马一双布鞋来表达感激之情,不可忽略的是,金宝娘一家获得物质资料生产的实现载体便是李根元口中的“甚也有了,分下房,分下地”③马烽:《马烽小说选》,第12、13页。,分归后的土地、房子等固定财产归农民个体(金宝娘一家)所有构成了此后农民阶级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物质基础。
实际上,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第六条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按照“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的原则“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④《中国土地法大纲》,渤海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4页。,为防止新的贫富两极分化与农村剥削阶级的再生,中共政权组织便有意识地引导农民群体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道路。因此,不同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接连出现,有时间上的临时互助组与常年互助组,发展程度不同的初、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互助的生产组织形式瓦解了地主阶级样态的租佃关系,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大众成为新型劳动群体。“变工组”(“互助组”“换工组”)既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革新,又是群众联合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但老户中农李二牛和翻身户刘大有互助合作闹生产在实现生产资料互有互补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和谐的人事纠纷。由此可见,“变工互助”并非完美无瑕,生产过程中非原则的纠纷给劳动主体带来矛盾的同时,也威胁着“互助组”政策执行的稳定性,这点在《解疙瘩》中尤为明显。
二 《解疙瘩》:牲畜情结与“劳动互助”的困境
在马烽1948—1949年的土改叙事中,《解疙瘩》作为反映初期合作化运动的“问题小说”,是颇具症结的文本。这不仅是因为《解疙瘩》的故事反映了农民翻身解放走向互助生产的集体化道路,还因为马烽借这篇小说叙述了“变工互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此问题的思考:“虽然发生的问题不大,而且是一些非原则的纠纷,但是如果不及时解决,也可能使互助组垮台。”①马烽:《〈解疙瘩〉写的是一个什么问题》,高捷等编:《马烽西戎研究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解疙瘩》作于1949年8月20日,在1949年8月28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星期文艺”专栏刊载。小说讲述了农民翻身解放后老户中农李二牛和新翻身户刘大有两家结成变工对象合力生产的故事,小说中“两个人土地亩数相差不多,劳动力一样,又是住在一个院里,平素相处得也不错”和农会主任李和和“你们两家闹变工,这是再合适也不能了”②《马烽文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0、41页。都突出了“变工生产”内含的“劳动美学”色彩。但正是这样一对看起来充满合作动机的互助对象,却也暗藏着互助破裂的传统乡村治理危机。老户中农李二牛突然终止与刘大有变工合作的直接原因便是“牲畜”,“球!变工,不变了。咱们以后各管各吧!”③《马烽文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0、41页。李二牛对农会主任李和和抱怨说:“他不心疼牲口!”④《马烽文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0、41页。牲畜作为乡村农业社会的重要生产资料与家庭固定财富,在农村劳动生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善待牲畜不仅显示了中国乡村文化传统中“朴”文化的价值内核,更是农民群体朴素真挚的生活经验的表达,农民群体爱“畜”如命的背后,并非出于国家意志赋予的政治使命与责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爱惜作为生产工具的牲畜的自然流露与表达。也正是因为小说对李二牛这种发自内心的对役畜(驴)之爱的叙述,与刘大有因缺乏饲畜经验而无法善待牲畜这一行为形成强烈反差,正反之间的张力酝酿转化为变工互助被迫终止的情感内因。这种突发的终止变工合作,恰恰衬托出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雏形阶段的变工组这一生产组织形式的不稳定性,“劳动互助”的政治美学和困境相叠加的历史尴尬境况可见一斑。此即《解疙瘩》文本价值所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未开展之前,传统农业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形成单一化的组织形式,到了根据地/边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号召打破传统生产方式,将个体纳入集体合作的范畴中来,李二牛和刘大有的“两情两愿”形成的“变工组”因是“自找对象闹变工”的结果,所以这种形态的互助办法属于临时性质的变工之计,它建基于农民群体翻身后个体生产资料互帮互助的基础上,目的便是互助对象之间实现生产资料公有互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将个体劳动价值转化为集体公共利益,这是农民群体实现政治翻身后继而在经济效益上寻求“翻身”的首要目标。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农民个体翻身后没有获得精神上的“翻身感”,或没有进一步实现“翻心”,这种不彻底性导致中国传统乡村伦理秩序在破裂后无法实现新的整合重组,那么,建构在此基础上的“变工组”就无法获得平稳运行的保障,这集中体现在新翻身户刘大有因缺乏饲养经验而无法赢得集体认同——作为两家共有生产资料的“驴”没有得到应有的珍视,换言之,翻身后的刘大有并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因此, 在这种文本语境下,劳动关系的变动与集体主义道德价值之间的错动便成为了《解疙瘩》潜在的弦外之音。
实际上,李二牛与刘大有对待牲畜所采取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已脱离小说呈现出来的动物伦理价值范畴,业已转换为互助合作中立场与情感范畴,农业合作化(“变工组”)进程中刘大有与李二牛政治上“落后/先进”、情感上“坏/好”,在对待牲畜(集体组织中的生产资料)这里获得了转喻与曲折表达,帮助“落后人物”实现集体主义情感认同的转换正是变工互助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对牲畜的情感态度成为检验合作化运动中政治标准的好坏与道德价值水平高低的试金石,这一点不仅在马烽《饲养员赵大叔》(1954)中“牲口迷”赵大叔的身上得以印证,而且在“十七年”时期小说诸如《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中得到更为深刻的体现。
三 《村仇》:“互助”的复杂性及伦理可能
如果说《解疙瘩》反映的是农民群体在业已实现“变工互助”后因对待牲畜的情感态度不同而出现的“非原则纠纷”,那么马烽创作于1949年9月的《村仇》则回望了农村社会抵达“互助合作”(在小说中即“修渠灌溉”实现公有化)道路的艰难与曲折。在这个意义上,马烽的两篇小说《解疙瘩》《村仇》形成了土改语境下“互助合作”这一完整叙事链条的两端。《村仇》延续了《解疙瘩》实现“互助合作”这一故事内核,不同在于,《解疙瘩》中的“互助合作”是结果,反映的是在此基础上出现的问题,而在《村仇》中是把“互助合作”作为目的加以呈现。这是因为,除了“劳动互助”实现后的困境需要解决外,抵达“互助合作”本身的艰难性也不应被忽视,马烽由此构建起一座连接“翻身”与“劳动互助”两者关系的桥梁。
在《村仇》中,赵拴拴和田铁柱两家的“反目成仇”(田铁柱在械斗中失手杀死侄儿狗娃,赵拴拴道路伏击田铁柱致其拐残)无疑是叙事焦点,而“反目成仇”背后裹挟的地主阶级内部两股势力的利益争夺与斗争,则是直接促使个体受损害的深层原因。以两村代表联席会议上赵有仁老汉及赵庄人民说理、陈述、道情为例:
赵有仁老汉接下去说∶“不过千中有头,万中有尾,我们村谁出的主意要霸水渠?……那是咱两村地主闹翻了脸,赵文魁才让霸的渠。你们想想,权柄在人家手里拿着,人家传下话来,一户一人上水渠,谁敢不去?!”
赵庄的人们这时都说开了,有的说∶“把田村家得罪下了,咱也没取上利。阉猪割耳朵——两头受罪!”①《马烽小说选》,第31页。
两村代表联席会议这样一种集体公开“断案”的方式,让错综复杂的矛盾置于明面,借以让地主阶级争权夺利的阴谋破产消亡,在集体言说与诉求的背后是赵庄与田村人民阶级意识的萌发与觉醒。换言之,在实现“劳动互助”的过程中,广大农民群众不应“只是被调动起来的群众演员”,而应成为“主角与指挥者”。①张丽军:《从经济翻身到精神翻身、人性解放——解放区文学中翻身农民的复杂心态、多元诉求与当代反思》,《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1946年《解放日报》的一则社论《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也强调,把群众发动起来“要看群众在争取这些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已经产生了主人翁的自觉”②《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1月9日第1版。,而是否产生“主人翁的自觉”,就是要迅速提高农民群体的政治觉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认清地主阶级是阻碍生产发展和阻止农民解放的根源,这也是土地改革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土改工作团工作员刘开明(赵拴拴和田铁柱的小舅子)口中的“农民本来都是一家,就是因为地主之间争权夺利,害得我们自家人结冤记仇”③《马烽小说选》,第32、20页。便是农民阶级觉悟的有力证明,也即只有在农民群体政治觉悟提高、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完成“互助合作”。
田村和赵庄两村合伙修建水渠引水灌溉这一行为本身已包蕴着互助合作的萌芽,但这种互助并非以集体利益为原则,而是旨在为地主阶级个人私利服务,田村和赵庄之所以因修渠分水而发生大规模械斗冲突,一方面是基于租佃关系维系下小农个体实利的得失,另一方面,由血缘关系和宗族姓氏联结而成的传统乡村伦理秩序的稳固性也成为地主阶级图谋利用的手段。以地主田得胜得知赵庄霸渠浇地后的“战前动员”为例:
田得胜叫村长打来七八斤酒,让大家喝,并且拍着胸脯说∶“姓田的大战场小战场也经见过,还怕了你个赵庄?!咱一家村,谁也不能退前缩后,谁敢胳膊肘向外弯,先打折他的腿!”说着看了田铁柱一眼。田二旦就趁势对田铁柱说∶“你是在赵庄长大的,可是你总是田村的人,如今也喝着田村的水,吃着田村的饭!虽说你舅舅家是赵庄,可是你死了总是往田家坟里埋,不是往赵家坟里埋!”④《马烽小说选》,第32、20页。
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拉拢”田铁柱及村民们参加“保卫”水渠斗争,是地主田得胜增胆壮势采取的策略,这就必然倒向了农村宗法血缘制度的另一个极端——宗族帮群势力在械斗冲突中发挥消极作用。由于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根深蒂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翻身运动很难第一时间获得农民的自觉支持,“由于地主在乡村财、权、势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很多农民对土改干部不理不睬,在诉苦教育中也闭口不言”①于昆:《变迁与重构: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心态研究(1949—195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0~71页。。所以,小说中工作员刘开明“向两村提议联合起来斗争地主”时,“又碰到两村群众都反对”的境况。因此,“互助合作”在成为一场全方位乡村社会变革运动的同时,不仅要实现集体主义生产的目标,农民群体的道义命理观念、人情道德观念,也要纳入“互助合作”的变革范畴当中,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无疑是一场极其复杂、深刻的乡村社会变革。它的实质是要求农民放弃几千年来世代因袭的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而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生产的道路,这必然涉及乡村发展方向的不同选择与道路斗争”②雷鸣:《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牲畜话语及其意义》,《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经由乡村秩序和乡村传统体制的重塑再建,农民群体“被赐予”的翻身方式③张丽军:《从经济翻身到精神翻身、人性解放——解放区文学中翻身农民的复杂心态、多元诉求与当代反思》,《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变为主动提高的阶级觉悟,工作员刘开明通过“发动两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启发诉苦运动,同时又和一些选出来的代表和积极分子们个别谈话”④《马烽小说选》,第29页。,召开了两村代表联席会议,不仅适时解开了“村仇”疙瘩,而且明确提出了“互助合作”下“修渠”和“扩大生产”在此后属于农民群体“利”之所在。
结 语
《金宝娘》《解疙瘩》《村仇》借翻身、牲畜情结、变工/互助合作等元素为土改工作勾勒塑形,构成了马烽土改题材小说叙事三部曲。当农民(贫雇农)群体成功实现“翻身”,农村社会生活转向生产物质层面时,牲畜情结、阶级觉悟与新型劳动关系(变工互助、合作生产)的龃龉磨合便成为马烽着重关注和书写的对象。这三篇小说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蕴含的斗争地主、翻身解放、牲畜情结和劳动互助等土改元素与在此基础上建构“问题—出路”的叙事逻辑,是马烽土改叙事三部曲得以顺利生成的深层机制,《金宝娘》在完成“翻身”叙事的同时,也揭示出农民群体未来走向互助合作的可能性,《解疙瘩》《村仇》完成了互助合作作为“目的—结果”叙事链条的两端,一面侧重于互助生产作为“目的”应当如何达到,另一面关注作为“结果”的互助合作所面临的困境难题,不仅表现出马烽小说独特的叙述特点与精巧的构思安排,也成为其创作生涯中别具特色的题材风貌。
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与合法存在正是依靠变工互助、合作生产、生产资料公有、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关系变更等步骤和进程得以确立起来,它们在颠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租佃关系、雇农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实现自主探索实践。在土改脉络的勾连下,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山乡巨变》《霜降前后》、柳青《创业史》、束为《老长工》、刘澎德《归家》等小说都将叙述重心置于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尖锐斗争的描写上,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疾风骤雨式的农村变革风情画。值得注意的是,与马烽同属于“山药蛋派”的赵树理,除将笔力置于土改中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描写外,打倒地主后的农民翻身、翻心等土改“弹性工作”的展开与发展成为赵树理着力书写所在,换言之,在赵树理笔下,“革命的第二天”①“革命的第二天”这一说法源自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他认为:“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见[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与“暴风雨”式的土地革命同样重要,因此,经由说理、诉苦、算账等方式确立起来的农民阶级主体性与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变化成为赵树理土改小说中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地板》(1945)、《福贵》(1946)、《小经理》(1947)、《刘二和与王继生》(1947)、《邪不压正》(1948)等一批小说对土改难题和中农路线的书写亦成为探讨土改工作中流行的翻身、翻心话语与解放区文艺生产机制关系的重要参考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赵树理在展现乡村生活伦理的重组更变与生产秩序的形成时,有意精简其复杂过程,而使其服膺于“问题小说”的叙事目的,一定程度上将历史真实与复杂性进行模糊与简化处理。
比较而言,马烽则采取了一种相对细腻与温和的书写方式,将目光聚焦在被压迫妇女(金宝娘)、贫农翻身户(刘大有)、中农(李二牛)和地主(《村仇》中的赵文魁、田得胜)等人物身上,逐层表现农民翻身、劳动互助、乡村传统伦理秩序重建的曲折过程:“翻身”农民在确立阶级主体性、获得个体财产(土地、房屋、地契)的同时,自然被纳入互助合作的轨道中;以“牲畜”为情感症结揭示“翻心”艰难及其带给劳动互助的困境;传统村落之间的械斗冲突同样折射出抵达互助合作的波折与颠簸,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在矛盾斗争中提升农民思想与政治觉悟,顺利实现“互助合作”,总体上呈现出真实化、复杂精细化的叙述特征。
总体而言,马烽在1948—1949年的创作土改叙事小说在创作生涯中具有独特性质与意味,既与其处女作《第一次侦察》展现出来的战争环境下战士“成长”经历不同,又和《停止办公》《我的第一个上级》等小说描写的侧重点相异,以《金宝娘》《解疙瘩》《村仇》为代表的土改题材小说显示了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与时代关注,以文学手段形塑土改的政治必然性和合法性。另外,也在方法论层面对围绕如何“互助”和“翻身”等命题进行了思考,聚焦于土改运动中的诉苦翻身、牲畜情结、乡村伦理秩序等核心议题,显示了土改叙事作品中少有的理性与深刻。特别是在当时创作语境下,这几部小说就显示出其特有的认知价值,为读者和研究者认识土改时期历史变革、农民思想风貌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