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亿《汉武》诗的重新审视
2022-12-04钟锦
钟锦
刘攽《中山诗话》里记载了当时的一个恶作剧:“祥符、天禧中,杨大年(忆)、钱文僖(惟演)、晏元献(殊)、刘子仪(筠)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敝,告人曰:‘我为诸馆职挦撦(扯)至此。闻者欢笑。”不过看起来发生时的气氛还是蛮轻松的,在赐宴那样休闲的场合,参与者也一定互相挺熟悉,优人搞了个不失善意的玩笑,所以闻者欢笑,没有觉得尴尬。但这个记载影响很大,《古今诗话》《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诗林广记》《宋诗纪事》等书纷纷转载,于是演变成对西昆体最尖刻的一则讽刺。我们对西昆体的第一个坏印象,一定由此开始。
然而西昆体并不背离宋代及其后诗歌发展的主流,严羽所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因为颇有特殊性,暂且丢开“以議论为诗”),“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沧浪诗话·诗辨》)。钱锺书先生注意到,主流跟西昆体有着同样的弊病:“西昆体是把李商隐‘挦扯得‘衣服败敝的,江西派是讲‘拆东补西裳作带的;明代有个笑话说,有人看见李梦阳的一首律诗,忽然‘攒眉不乐,旁人问他是何道理,他回答说:‘你看老杜却被献吉辈挦剥殆尽!‘挦扯‘拆补‘挦剥不是一件事儿么?”(《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钱先生还引了对明代“复古”派的挖苦:“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买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西昆体的人物也曾从事编辑类书《册府元龟》,是否也是一件事?可就算从弊病讲,西昆体显得能力和势力都远远不够,似乎像个做坏事都做不大的瘪三,被置于鄙视链的最底层。
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平心静气地审查宋代诗史,西昆体可谓有意识探索宋诗新路的最早尝试,即使其成就有限,求索之功也不该被忽略。中国的文言从口语脱离,逐步形成自身的法则,并以法则的秩序性建构出封闭的审美程式。这些法则来自对审美范型的熟练模仿,而那些范型无不出于古典,从而保持了与日常世俗的疏离。这些法则一旦成为历史性的审美规范,美感就在族类意识的积淀中具有了特别的品质,即“古雅”。王国维敏锐地发现“古雅”的两种价值。其一,“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一切美术品之公性也,优美与宏壮然,古雅亦然。而以吾人之玩其物也,无关于利用故,遂使吾人超出乎利害之范围外,而惝恍于缥缈宁静之域”。这是说“古雅”的美学价值。其二,“至论其实践之方面,则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虽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创造优美及宏壮之物者,亦得由修养而有古雅之创造力”(《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这是说“古雅”的实践价值。其具体的方法,就是所谓的“窥陈编以盗窃”(韩愈《进学解》)。齐梁以来直到初唐,因为骈文的盛行,其强调用事的特点加速了这方法的确立,当时类书编撰的盛行可以看作旁证。诗歌到了宋代,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这个方法,并将之进行理论归纳以便模拟。在宋代之后,更是被变本加厉地予以贯彻,成为旧诗写作的“共法”。西昆体就是这方法走向理论过程的第一步,揭示了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东西:“杨文公(亿)尝戒其门人,为文宜避俗语。”(欧阳修《归田录》)自江西派后,方法演变繁复,不过基本的东西始终没有变过,“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都是对此的反复强调。

艺术有了法则,本身就是双刃剑,一面方便了模拟,一面又走向僵化。上面钱先生提到的那些弊病,就是旧诗法则僵化后的必然产物。而西昆体那么简单的方法,更是很容易以最快的方式僵化掉。虽然西昆体很快没落,其方法或许还没来得及归纳完备,以致我们根本不清楚其细节。但其方法无疑极具有效性,也恰好为新兴的词体所需要,竟然一直被贯彻在那里。我们发现姜夔一派的理论成熟后,和西昆体有着极其相似的表现。仅从“字面”就看得出来,如张炎说“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词源》),沈义父说“要求字面,当看温飞卿、李长吉、李商隐及唐人诸家诗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采摘用之”(《乐府指迷》),如果不是填词而是作诗,不就是西昆体吗?只是词的体式在布局上更讲究,如张炎说:“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既了,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结,方始选韵,而后述曲。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词源》)由此发展出更为多样的方法。但词体给西昆体的方法留了空间,让其僵化的样态得以被窥见,也许更容易让我们了解它很快被驱逐的原因。这是沈义父的一段话:
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咏书,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筯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往往浅学俗流,多不晓此妙用,指为不分晓,乃欲直捷说破,却是赚人与耍曲矣。(《乐府指迷》)
这样的琐碎、呆滞,让人惊讶,也让人好笑,但西昆体的方法应该也不过如此,这从其作品里看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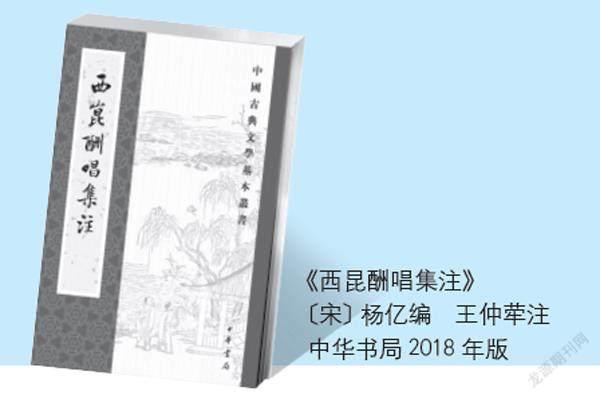
《汉武》是杨亿的一首名作,被刘攽赞许为“义山不能过也”(《中山诗话》):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汉武》之题在《西昆酬唱集》中同作者七人,全部写于真宗景德三年(1006)。这个题目受到一定的关注,从表面上看自然是讽刺汉武帝求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射并不很明确。王仲荦注释以为是想进谏真宗并止其东封泰山,两年后大中祥符元年(1008),杨亿代草有事于泰山的诏书里,也有“不求神仙,不为奢侈”的话。这个推测也许可以考虑。
前四句写汉武帝求仙的辛苦,意思很明白,但全由古典进行表达,让人感到没有“说破”。蓬莱山,是齐宣王、齐威王、燕昭王以来就入海寻访的三座神山之一,另外两座是方丈、瀛洲,记载在《史记·封禅书》里,非常出名。据说“黄金银为宫阙”,可是“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蓬莱银阙浪漫漫”,就是说蓬莱山的虚幻缥缈。“弱水”,《十洲记》云:“凤麟洲在西海之中央,‘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楚辞·九章》:“悲回风之摇蕙兮。”“回风”,指回旋的风,如果在海上,大概就是台风吧。四字写尽风浪的险恶。可见欲到实难,但汉武帝一次次派人寻找,不肯放弃。再写他自己也配合得很辛苦。《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在甘泉宫祭祀神仙:“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据《三辅黄图》:“竹宫,甘泉祠宫也,以竹为宫,天子居中。”借此典故用以写夜之劳。《汉书》注引《三辅故事》:“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把天上的露水用仙人承露盘接来,再和玉屑饮之以求长生,这是汉武帝求仙的著名故事,用以写昼之费。两句其实是互文,把汉武帝昼夜劳费的辛苦写得很典丽,甚至到了雕琢的地步。
如此辛苦求仙,无非为了长久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力通青海求龙种”,写汉武帝为了得到龙媒天马,不惜穷兵黩武,这是帝王奢侈的特别罪恶。《北史·吐谷浑》载:“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我们知道汉武帝所得大宛的天马,有“天马徕,龙之媒”(《汉书·礼乐志》)的美誉,却并不是青海的龙种。这里只是借用典故的字面,大概杨亿认为“龙种”更能突出马的神骏,或者仅仅是和下一句的“马肝”更容易对仗,原本不须指实。下面对仗的一句突然反跌,虽以帝王之尊无所不能,但面对求仙终究只有无奈,一次次的失败,不得不尴尬地以谎言进行掩饰。《史记·孝武本纪》说汉武帝拜齐人少翁为文成将军,因求仙不成杀之。后来汉武帝又希望栾大替他求仙,栾大说:“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汉武帝只好扯谎:“文成食马肝死耳。”这里也是借用字面,讽刺汉武帝用谎言来掩饰。
最后两句是极强的讽刺。“待诏先生”,指东方朔,传说中他也是和神仙极有关系的人物。《汉武故事》:“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说的正是他。《列仙传》里,也有“疑其岁星精也”的说法。但历史上东方朔却是经常以滑稽的方式向汉武帝进行有益的讽谏,比少翁、栾大之辈远该让汉武帝重视,可是汉武帝只以俳优视之。杨亿这里用了《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说他“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如此相貌堂堂,却混得不如侏儒,于是要求汉武帝:“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实际上,汉武帝重视少翁、栾大,轻视东方朔,无非只图穷奢极欲,对国计民生并不太关心。不过王仲荦根据沈括《梦溪笔谈》这个记载:“旧翰林学士地势清切,皆不兼他务。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杨大年久为学士,家贫请外,表辞千余言,其间两联曰:‘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认为是以东方朔自況,不满真宗的待遇。但这样解释,和上文缺乏衔接,也显得不够大气,似不宜从。
一般认为《西昆酬唱集》的作者们,多写空虚无聊的文学侍从生活,没有现实意义,故而连其艺术价值也都没有了。可姜夔的词也多写清客的生活,实在没有强到哪里去,但却以艺术性被视为宗匠。可见,文学重要的在写法不在内容。这首《汉武》的内容虽说极为正面,但写法已见僵化,过分地规避俗语,极力以古典修饰字面,使得表达显得滞涩。看了沈义父那段不许说破的论述,也许更能够明白这种僵化。有个故事可以见出杨亿僵化的程度。刘攽《中山诗话》说:“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对于字面的执着,到了嫌杜甫诗“村”的地步,这不是走火入魔吗?难怪梅尧臣要用“平淡”来矫正。只是梅尧臣矫枉过正,往往不是平淡而是简陋,也造不成大的影响。直到欧阳修从“以文为诗”中悟出“犯”字诀,再结合西昆体的古典字面运用,就有了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宋诗才真正开辟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即使在这条道路上也始终没有摆脱西昆体的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