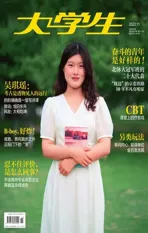不该再持专业决定主义
2022-12-01王洲淼中国人民大学
文/王洲淼(中国人民大学)
辛辛在大一的时候,就感觉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不适合自己。她是一位在某高考大省突破重围的理科生,如今进入了人大的一个双一流文科专业,但她“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专业课上“文科思维”的讲课方式让她困惑,专业实践又让她的恐惧症频频发作。一旦开始看专业书,很容易就困倦,她也不愿意参与任何竞选和面试。辛辛将这一切都归结于“选专业的失败”,可问她理想专业是什么,她又回答不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新生导师”活动
实际上,像辛辛一样经历千辛万苦来到大学,却惊恐地发现自己选错了专业,并为之纠结、痛苦的焦虑者,并不是少数。
从高中到大学的断层
辛辛如今的专业是她自己选择的,她将这个文科专业放在了自己的第一志愿,并没有被调剂。当初填志愿时她想着只要能不再学数学就行了,但“哪有人这么选专业的呢”?
其实有很多同学像辛辛一样,都是这么选专业的。小满如今在人大的某社科专业就读。她提到自己的专业选择时,也感到很草率:“我感觉自己对历史和政治挺感兴趣的,但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专业在学什么……”就读于西南某省的小城市,她的人生一直以高考能考出好成绩、进入到好大学为最终目标,然而真的面临填志愿时,她却有些慌乱:她需要在5天内做出决定,要去哪所大学、去学什么专业。
很多高中毕业生,对于自己兴趣的认知,通常依赖于高中的学科体验。“作文写得不错,我就觉得我可能适合中文系。”小满想起高中时似乎有过一些人生规划类的课程,但是都被占用来写作业了。
同样,就读于中科大生物专业的李元,在大一下学期的无机实验课中状况百出。他感到十分气馁,“我可能更适合理论类的工作,而不是处理瓶瓶罐罐。”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专家认为,这些专业焦虑者大多数可以被视为“专业认同缺乏”。大学生的专业认同需要经历从了解到接受,再到付出行动这一社会化的过程。而有些同学在“了解到接受”的环节就已经被卡住了,他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对于这个专业的不适。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最后成为一种固执的相信。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中心咨询师刘鹏,接触过不少专业焦虑者。他认为:“坚持自我探索,综合自己的人格特质、兴趣爱好去寻找自己匹配的专业和职业,应该是每个同学的必修课。”
鄙视链思维
李元认为自己不适合生物专业,决定向计算机转专业。原因很简单,并不是自己多么适合,而是因为计算机专业在目前是一个风口专业,处于专业鄙视链的顶端。“说白了,就是收入更高,”李元补充道,“我们的助教在博士毕业后都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生化环材在科研中也是底端,算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让李元坚定地要转专业,以换取退路和安全感。
热门的专业与顶尖的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兼顾,不少学生在填志愿时都会选择相对冷门的专业来换取更好学校的入场券。大成就是人大提前批某小语种的在读学生,大二的时候,他开始焦虑。“通过跟师兄、师姐交流或者看各种公众号,你就会慢慢发现可能没有什么前途。”大成也曾试图修一个双学位,但是学起来好像也不适合,中途还是放弃了。
小满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清晰地感觉到学校内部的鄙视链,不管是不同学院基础设施上的巨大差距,还是在社交中根据专业划分的“等级观念”,都让她觉得自己低人一头,“可你也没有办法,因为确实入学的成绩就比人家低。”
刘鹏认为这种现象还是应该追溯到高中时期的价值观塑造,很多同学把专业和个人前途做了过于紧密的挂钩,这种思维延伸到大学里,就成了“专业决定论”。
而即便是最开始“不听劝”,硬要追求情怀的一些同学,也在现实面前产生了不适、焦虑的情绪。熏熏是人大考古学专业的同学,最初她是遵从内心进入历史学院的。但是现在面对他人“你学了这个以后要做什么啊”的问题,她本能反感,而且听多了也会带来某种不好的心理暗示。“别人问我你为什么学考古,以后要做什么,这是一件很令人不适的事情,好像自己的专业低人一等一样。”
在天津大学就读的小木,曾经怀抱着去教育学院的梦想,而现在她是一名建筑专业的大二学生,说起她的专业选择,她说“兴趣是一点点发现的”。在经过了天津大学一年的大类培养之后,她权衡良久选了一条自认为合适的道路,慢慢地看清了自己的兴趣。
提前的毕业焦虑症:信息超负荷
嘉嘉如今已经进入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她本科读的是国际关系学院的一门小语种专业。回想起当时的本科生活,她惊讶于现在的学生似乎越来越提早焦虑了,“我感觉我整个学习过程还是挺快乐的”。
但是在人大学习小语种的马硕则不那么乐观,即使他还刚上大一。他有翻看知乎的习惯,知乎上铺天盖地都在说“小语种是天坑,各种劝退”,加上师兄师姐、甚至有些老师也在劝说他们要再多学一门其他学科,成为“复合型人才”,这让马硕觉得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我总是想一些最坏的打算,不想那么拼,却又不得不努力,很被动。”
从嘉嘉到马硕,中间经历的是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信息时代,日新月异的信息潮水般涌进每个人的手机终端,不断强化着大家对于某一信息的印象。以知乎为例,2019年,知乎的用户就已经超过了2亿,而学生用户比例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知乎近几年还开拓了高考之后“帮考生选学校选专业”的项目,众多师兄师姐、业内人士每天数以千计的劝退帖就是从这里发出。同时,豆瓣等社交平台也出现了“某某专业劝退小组”。“他们都是非常真诚地在劝退我,拿自己的个人经历,摆事实讲道理,让我真的感觉到了危机感。”
小满也说,当时她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获取志愿信息的时候,就曾经求助过知乎,结果“越看越纠结,越看越心凉,越心凉还越看,最后我直接把知乎卸载了”。开学第一天,她便悲观地认为,在这个专业得到的知识,很可能是没用的。
刘鹏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这个信息爆炸平台,想要保持清醒是非常困难的。“负面评价看得多了,肯定会对这些专业产生不好的印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曾研究过“校园信息过载”的问题,她认为校方应该主动培养学生面对信息过载的能力,甚至将互联网信息资源的使用作为一门课程来教授。
刘鹏也提到,为了弥补这种信息差,学校应该搭建平台引入优质的信息来源,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LEAD计划”,请各行各业的校友来做在校生的职业发展导师;还有新生导师项目,校内几乎所有老师都可以直接陪伴新生成长;还有一些学院搭建了学生和校友的一对一咨询平台……刘鹏建议同学们一定要学会充分利用这些优质的信息来源,万万不要迷失在信息的海洋里。
突围:夺回选择权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效能感”,它指的是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自己和环境。刘鹏认为,深陷专业焦虑的同学,往往都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自我效能感不足”。小满对此很认同,“上了大学之后,发现专业的事情不由你做主,以后的人生道路方向也不由你,即便是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内心也会惶惶不安。”
在天津大学就读的小木,曾经怀抱着去教育学院的梦想,而现在她是一名建筑专业的大二学生,说起她的专业选择,她说“兴趣是一点点发现的”。在经过了天津大学一年的大类培养之后,她权衡良久选了一条自认为合适的道路,慢慢地看清了自己的兴趣。小木说:“我从不觉得专业和专业之间的比较就能预测出谁的未来会更好。”她有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在她看来前途也会一片灿烂。“只要他真正喜欢自己的专业,就会自然而然地往那条路上走。”
与小木的选择不同,嘉嘉在小语种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了人大的教育学院,“其实现在也不太清楚未来能干什么,但是可能就是自己成长了吧,心态更稳定了一些。”提到未来,嘉嘉充满了使命感,她想,如果能有所成就,也许自己可以努力让下一代的孩子们少些焦虑。
大成则打算出国攻读博士,转换成研究机器翻译方向,现在的他“跑程序、跑代码,感觉学的东西很技术性,不那么焦虑了”。他想对师弟师妹们说:“我觉得现在社会分工其实是很细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了解的话,总有一些职位是既有前途又符合你自己的兴趣的。”
暑假期间,深陷焦虑情绪的辛辛接受了心理医生的咨询,她状态好了许多。新学期开始,她打算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