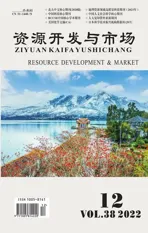民族旅游场域中文旅融合的逻辑分析
——基于旅游本质的再思考
2022-12-01张冠群阿荣娜宋河有
张冠群,阿荣娜,宋河有
(内蒙古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0 引言
文旅融合发展是“文化强国”战略的具体部署之一。2020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标志着我国文化和旅游业进入了高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从需求端看,旅游不仅是一种修身养性之道,还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未来五年,人们的旅游需求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缺不缺”转向“精不精”,对旅游产品多样化、特色化和品质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1]。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考虑的不再是产品或服务自身的价值,更多的诉求在于旅游过程中的情感需要[2]。不同于普通消费,旅游体验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接收到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刺激”后产生出来的一种情感体验,这对于民族旅游产品设计的内涵和深度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民族旅游场域中的文旅融合如果只停留在表层,或直接将一个个的“符号化”结果呈现给旅游者,并不能给游客创造深刻的旅游体验。旅游体验必须是在旅游过程中通过游客的融入与参与而积累形成的一种情感体验。在民族旅游场域中,文旅融合是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和精神世界进一步追求的迫切需要。同时,文旅融合有着切实的可行性,二者在逻辑上是紧密关联的。文化和旅游在效用与价值追求上具有一致性,在生产与消费模式上具有同质性,在产业组织形态上具有共生性,在微观经济性质上具有相似性[3]。在民族旅游场域中,文化就是“那一民族的生活样”[4]。据迈克·费瑟斯[5]对于文化的理解,一种是基于人类学意义上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另一种是作为艺术的文化,它是文化产品和体验的精神升华。显然,民族旅游场域中的文化,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其文化的基调,艺术精华是其文化的亮点,这些文化即构成了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文化和旅游作为人类两种基本文化生活方式,在“山脚下”(社会经济结构)分开,在“山顶上”(文化身份认同)相聚[6],二者有着天然耦合关系。
文化不仅是民族旅游得以开展的核心吸引力,也是旅游活动所承载的主要内容。现实中,民族旅游场域内的文旅融合效果往往不佳,原因在于人们对文旅融合的理解停留在表层,只在宏观层面上提供一些技术和方法上的设想,并没有直击民族旅游场域中文旅融合的本质,所以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那么,文旅融合的切入点到底是什么?只有搞清楚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才能抓住文旅融合的要害,使旅游场域中的文旅融合形神皆具。在民族旅游场域中,文旅融合最终是以文化旅游的形式呈现,其本质上是一种旅游形式,故探究文旅融合的深层问题,仍然要从旅游的本质入手进行探讨。本文试图从文旅融合的底层逻辑出发,对民族旅游场域中的文旅融合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1 旅游本质的再梳理
旅游的本质不仅关乎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也影响着旅游规划和旅游业的实践方向及实践效果。本文对目前学界比较流行的两种认识——“体验说”和“诗意地栖居说”进行分析,通过理论思辨,试图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析。
1.1 旅游的本质是体验
客户体验一直是娱乐业和服务业的焦点[7]。Pine等[8]认为体验不仅仅是服务的传递,而是创造一个值得纪念的独特事件,这一观点在服务业引起了广泛关注,包括旅游业[9-11]。Cohen[12]在《旅游体验现象学》一文中使用了“旅游体验”(Tourist experience)一词,将旅游体验定义为个体与各种“中心”之间的关系,体验的意义源自个人的世界观,对个体来说代表着终极的意义。国内学者谢彦君[13]明确了旅游的本质为体验,指出寻求愉悦体验是旅游的根本目的,而余暇和异地将这种体验和其他体验分离出来;曹诗图等[14]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认为旅游的根本目的是追求身心自由体验,是逃逸(来自自我补偿的动力,如消遣等)与追求(实现审美、求知、认同、自我实现的需求等)的统一,是一种主要以获得身心补偿、精神自由、心理愉悦为目的的审美过程和自娱过程,是一种精神生活和高层次的休闲生活方式,因此异地身心自由体验理应是旅游的本质;陈道山[15]将旅游的本质描述为一种出于愉悦需要的满足而暂时到异地进行现场审美体验的特殊生活方式;刘锋[16]将旅游的本质看作是一次经历、一次阅历、一次体验,也就是旅游者离开家门到达旅游目的地,然后再回去的这样一次差异化体验,是一种异地的生活方式的体验。
对体验说进行梳理和总结后,会发现持这一观点的人都将“体验”作为旅游本质解释里的关键词,并且一致强调异地性。但究其内部,也存在一些区别,具体体现在旅游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如有学者所持观点为追求身心愉悦,有学者指出是一种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相应地,对于旅游本质的解释有的是将体验视为旅游活动相伴而生的过程,有的则将体验的获取视为旅游活动的终极目的。这个区别看似微乎其微,实质上影响着对“旅游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终理解。“旅游是过程中身心愉悦的体验”和“旅游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最终形成体验”不能完全等同,出现了过程与结果的差异。前者将体验视为旅游活动的规定性和过程产物;后者将体验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即体验只是这种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情感结果或记录。
虽然各学科对于体验有不同定义,但是其共同之处在于指出体验是一种“实践”和“领会”,是对世界的认识而产生的情感感受,强调心理感知和认知过程[17]。体验,是一种经历,而且是能给予主体较长时间的深刻印象的经历[18],旅游活动无疑会给人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本文认为,旅游体验有两层含义:一是游客在旅游场域内受到任何感官“刺激”后所产生的即时感受,即瞬时体验(五官);二是游客经历了无数的瞬时体验后,在旅游活动结束后所产生的终极情感体验,即延时体验(回味)。前者指向过程,后者指向结果,体验的形成既关乎过程又关乎结果,这恰恰是学术界对旅游体验本质理解的不一致之处。将旅游视为一种异地的体验本身并无不妥,因为旅游过程之中和之后就能够产生旅游体验。
当然,体验也有好差之分,好的体验即沉浸式体验,能给人带来“心流”(Flow)体验,即个体将精力全部心流般地投注在某种活动当中,无视外界的存在,以达到忘我的状态[19]。“心流”与“沉浸”密切相关,其目的都是使人专注于当下的情境之中,完全投入到某项活动并乐在其中[20]。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在这件事完成之后会觉得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21]。差的体验即行动主体感觉糟糕或者平常,并没有形成特别的、积极的情感体验。可见,高质量体验的形成需要行动主体投入身心,专注于事情当中,并能够从该项活动中获得满足。可以说,行动主体对于某件事的投入与专注程度决定了他最终所获得的体验程度。当主体未全身心投入时,就无法获得满意的体验感。那么,旅游体验到底是我们应该追逐的“因”?还是“果”?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是怎么获得的呢?
1.2 旅游的本质是“诗意地栖居”
“诗意地栖居”源于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诗《人,诗意地栖居》,后经过海德格尔的哲学阐释,成为人们心目中共同向往的一种境地。“诗意地栖居”描绘了一种生活状态,即人类在与自然、自我的和谐一致中可以享受星空明月、青山绿水,使得生命的本真得以展现。诗意地栖居更多指的是人类所想构建的精神家园。曹诗图等[22]指出“诗意地栖居”是旅游的理想追求,其实质是人对生命自由和谐的追求,而旅游的本质则是人对生命自由和谐的追求或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这一分析既提到了旅游的本质是人对生命自由和谐的追求,又补充了旅游作为异地的体验。同时,作者也在文中说明天人合一的、生命自由和谐的“诗意栖居”要么是一种纯粹的理想,要么只能通过旅游或休闲这种生活方式获得体验[22]。这种试图将体验与“诗意地栖居”合为一体的解释,一方面突出旅游的愉悦属性,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旅游是既有生活品质提升的一种方式[12]。但遗憾的是,二者的关系并未得到厘清。罗良伟[23]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背景下指出现当代大众旅游的本质是旅游地的一种生存活动,是一种试图逃避沉沦和异化的生存活动。虽然他并未明确地提出诗意地栖居,但文中所反映的思想便是人们为了逃离现实的“烦”而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正如Crouch[24]所说,人们旅游是为了逃离现实,逃离是为了“回家”(理想的家园)而逃离,而不仅仅是逃离现在的家。杨振之[17]梳理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胡塞尔、康德、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及他们对本质的认识,在评价国内外对旅游本质认识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旅游的本质是人诗意地栖居,明确旅游是人存在于世界上的一种方式,旅游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人在旅游中,通过体验激发自我、认识到本我,感悟到天、地、神、人归于一体,通过忘记世俗生活获得本我的回归,使人们真正体悟到“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25]。
将旅游视为“诗意地栖居”,虽然表述略显文艺,但其核心思想彰显了旅游是人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人回归自我、发现自我,获得心灵自由的一种方式。按照杨振之等的解释,“诗意地”可以理解为“人真实的存在于世界中”,即人在旅游中寻找到自我,回归自我,达到天、地、神、人高度统一的自由和谐状态[17];文章虽然没有对“诗意地”及“天、地、神、人”四方归于一体的状态进行详细阐释,但是很明显将“诗意地栖居”更多的理解为一种精神境界。
旅游是人的主观和主动行为,所以人的主观意图无疑是理解旅游本质的关键。人类文明的积累与其相关的实践均建立在人类对自我的探索和对幸福的追求之上,科学研究中一次次的飞跃,都将人的认知和生活带到新的高度,彰显出人作为生命体的终极理想和追求。将旅游视为“诗意地栖居”,无疑遵循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将旅游的本质从哲学层面追溯到了“人性”和“人的追求与理想”之上,即通过旅游给人类所要追求的肉体和精神世界寻找一个栖息之所。从人性的角度看,旅游的初衷也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和谐的探索。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体现在对欲望的满足。黄力[26]将生命世界的运行规律归纳为三重欲望,指出生命就是严格按照对三重欲望不断满足的轨迹运行的,即生存欲望、官感欲望(在生存欲望满足的基础上追求舒适性)和精神欲望(超越其他人)。旅游在人类生命世界的进程中正是扮演着满足人类官感欲望和精神欲望的角色。将旅游视为“诗意地栖居”,其实质是构建出了旅游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二重性,指明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存在鸿沟,旅游世界是不同于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崭新世界[27],这也许是人们出门旅游的根本驱动力之一。那么,旅游世界的“诗意”究竟该如何呈现?民族旅游场域中的“诗意”又是何种状态呢?
2 对旅游本质的再思
对于旅游本质的这两种认识,看似不同,其实有着很强的内在关联和统一性。无论将旅游视为“体验”还是“诗意地栖居”,二者都是出于“旅游者主体视角”,即“以人为本”,从旅游者的角度考虑旅游本质问题。二者的区别在于它们分别指出了人们受到旅游地各种事物刺激后产生的“情感结果”和“旅游行为的根本驱动力”,也就是旅游“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体验是游客受到旅游地事物刺激后从感官到内心所形成的感受,是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并可以描述的情绪结果,所以旅游活动直观上对应着“旅游体验”。而“诗意地栖居”是从人的需求出发,对旅游做出价值判断,揭示出“旅游为了什么”这一终极命题,即指出旅游是人们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美好生活而意欲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的情感诉求。“诗意地栖居”从根源上解释体验是如何形成的,即当旅游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生命真谛的追求这一目标,旅游过程的所见所感皆能体现“诗意”,便能形成良好的和深刻的旅游体验。可见,体验最终可以成为“诗意地栖居”后的内心秩序结果,所以二者并不矛盾,且有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将“体验”和“诗意地栖居”理论联系起来思考和解决旅游问题,无疑会豁然开朗。
事实上,对于旅游本质问题的探寻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不同的认识及思考方式对旅游实践及旅游业的发展方向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们认识旅游一系列问题到底应该发端于旅游“是什么”还是“为什么”?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旅游是人的主观和主动行动,其出游的动机是理解旅游本质问题的关键,而对旅游不同的理解将会直接引发对如何进行旅游规划和旅游业如何发展等实践问题的追问与实施。西蒙·斯涅克[27]提出的“黄金圈法则”将人类思考问题的顺序由内向外依次构建为3 个圈层:为什么、怎么做和做什么,解释了思考问题从“为什么”开始,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其中,“为什么”即行动的原因,是人们做事的本质驱动力,也就是人们所持的信念,它指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当清楚了“为什么”问题后,就要考虑用什么方式落实,即“怎么做”问题。表层“做什么”的问题便会以结果的形式呈现出来。
旅游体验既是一种旅游行为过程的情感伴生物,也是一种参与旅游活动后所产生的结果性感受,它相对直观可感,所以最先进入人们的认知结构中。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在围绕用户体验进行设计,旅游产品也不例外。然而,旅游地到底应该给游客营造什么样的体验呢?如果是沉浸式体验,它又是如何实现的呢?现实中,当围绕用户体验进行文旅融合,在实践中就容易造成供给方并不了解或关心旅游者的真实需求,也就不了解用户的“痛点”,旅游产品的设计浮于表面。这样不仅会使体验设计无可依托,成为空中楼阁,也会造成旅游产品无差异性,同质化严重。虽然将旅游视为体验无可厚非,但是在指导实践过程中却常常无计可施,不能直达根本。
按照这样的逻辑,从人的旅游需求切入考虑问题,从根本上满足人们对于旅游的需求,即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烦忙”和对“理想家园”的追求,才能真正给游客创造出体验和价值,最终让他们产生认知、审美及意义的体验与收获。同时,因为各地所构建起的“理想家园”都依托于当地的生活方式,有着不同的地脉、文脉,所以各地都不相同,给游客形成的体验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基于“诗意地栖居”进行旅游产品设计和旅游业的供给,是保证实现旅游者体验差异化的根本。在旅游的过程中,游客通过融入旅游场域的生活方式,暂时远离了在家的“烦忙”,收获了对自己和幸福的理解,这才是旅游业高质量、差异化发展的正确思路。
3 民族旅游场域文旅融合的主要问题
在民族旅游场域中,文旅融合往往存在融合不深、不自然、游客获得的文化体验感弱等问题。一方面,表现在游客在特定民族旅游场域中感受到的文化地方性和独特性不强;另一方面,从旅游产品供给角度来说,产品同质化或商业化现象较为严重,影响着游客的文化体验。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①文旅产品设计脱离市场需求。在民族旅游场域的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规划者往往从旅游供给者的角度出发,对场域中的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产品策略,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真实诉求,或者对于旅游市场的真实需求的理解是不充分的。也就是说,在进行旅游产品的设计之初,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旅游地有什么资源和文化,有什么条件,怎样让旅游地出名或取得成功,却并没有完全站在旅游者的视角理解现代人通过到民族地区旅游究竟想要获得什么?他们有哪些情感方面的需求?旅游地要给他们创造怎样的体验或收获?因为脱离了市场的主体视角,往往造成民族旅游场域的产品设计“符号化”,流于形式,而难以真正让游客动心动情。②旅游体验设计缺乏灵魂。在民族旅游场域中,往往还存在为了给游客营造特别的旅游体验和感受而特意为之的情况。游客被放置在了一个虚拟的现实场景之中,在这个场景中,他们的所观所感虽然与在现实世界中存在极大不同,但因为场域中的文化都是以一种表演或者夸大的形式呈现,文化被进行了重新刻意的编排,并非场域中文化的真实流露。这种情境下的文旅融合无疑会浮于表面,缺乏灵魂,其结果便是游客的体验停留在表面。游客虽然在感官上受到了不同文化符号的冲击,但内心并未感受到民族文化的真实魅力,内心情感也未被真正触动,难以形成深刻的文化体验。
上述问题反映了民族旅游场域中文旅融合的“空心化”问题,即文旅融合浮于表面,缺乏核心的指引。这样的文旅融合并非是文化和旅游真实的互相渗透,而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形成的“假融合”,不能为游客营造深刻且富有诗意的旅游体验。
4 民族旅游场域文旅融合的逻辑
文旅融合的关键不在于形式或方法,而是要从本质上找到二者融合的切入点,才能实现文旅的真正融合。众多学者指出文旅融合的关键是为游客创造深刻的文化体验。如:McKercher[28]认为深度体验和游客参与是文化旅游至关重要的部分;傅才武等[6]通过建立基于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的框架,将文旅融合的内在逻辑描述为“体现为一种物质和符号空间结构的文化旅游装置,以文化旅游消费行为作为中介发挥‘通道价值’,让旅游者产生凝视和沉浸等文化体验”。可见,为游客创造良好的、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对于文旅融合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文化旅游要追求及达到的最终目标,也是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之一,更有甚者,将为游客创造深刻的文化体验视为文旅融合的出发点[29]。现实中,当我们聚焦于为游客营造深刻的文化体验时,也就是将焦点放在了“结果”上,往往不能获得文旅融合的良好效果。给游客创造深刻的文化体验既是文旅融合要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文化旅游形式,民族旅游地文旅融合的底层逻辑应追溯到旅游本质问题的思考上来,即处理“体验”和“诗意地栖居”的关系。
民族旅游场域中的文化,宏观上是一种世俗化、生活化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民族的生活日常之中。在微观上,民族旅游场域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艺术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节庆、仪式或者物质文化形态。本文认为,从宏观层面思考民族旅游场域的文旅融合及旅游供给时,一方面,可以将“诗意地栖居”作为始,将深刻的文化体验作为“终”,以始为终,即从“诗意地栖居”进去思考文旅融合和旅游产品供给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从“深刻的体验”出来检验文旅融合和旅游供给的效果。而从微观层面思考游客体验的文旅融合和旅游需求时,以终为始,从为游客创造深刻的五感体验为始,以人们在旅游地感受到强烈的“诗意”为终。而文旅的融合作为中间的重要渠道,在文化旅游过程中扮演着沟通“诗意地栖居”与“文化体验”的角色。

图1 文旅融合的逻辑圈层Figure 1 The logical circle of culture- tourism integration
4.1 以始为终
民族旅游场域作为一个特定的现实文化空间,文旅融合的切入点是要给游客构建起“诗意地栖居之所”,让游客真正地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与生活氛围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是从人对旅游的本质诉求入手,将旅游行为视为一种人类所追求的美好生活方式,将民族文化贯穿到游客在“旅游世界”的日常之中,注重游客在旅游场域中的融入与参与度,从而为其构建起在旅游地进行的理想的“栖居生活”。旅游地依托自己的文化地方性,将自己特有的文化渗透到旅游活动的各个要素和环节之中,融入到旅游地的生活方式当中,如饮食、作息、居住习惯、生活日常等,让游客真正地融入到旅游地的真实生活情境之中。也就是说,通过为游客构建理想和诗意的异地生活,让游客在旅游场域中真正的动心动情,沉浸其中,感悟旅游世界中不同的生命状态与幸福。以“诗意地栖居”为切入点,将文化融入旅游地的生活,让游客感受到“理想家园”的魅力,忘却烦忙,忘却时间,可为游客营造出了沉浸其中的深刻情感体验,即心流体验。
同时,在民族旅游场域中,深刻的文化体验是文旅高质量融合的外在表现,也是文旅融合效果的检验剂。旅游体验是人们在异地追寻幸福生活所获得的体会与感受,也是在旅游过程中激发本我、回归本我的体验过程。这种体验可以帮助人们丰富自我,满足认知与审美需求,帮助人们找到真实的自我并获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也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对幸福和快乐的追寻,获得对生命、生活真谛的启示。然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们融入旅游地生活之中才能获得。可以说,旅游体验是人们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体验“理想世界”后形成的情感结果。此逻辑下的文旅融合,不仅要求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将场域内的世俗文化自然融入到游客的旅游生活中,而非给游客构建一个虚拟的现实场域,还指出游客必须融入到旅游地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才能获得真实的、深刻的文化体验。
4.2 以终为始
从微观角度来说,民族旅游场域内存在众多艺术文化,这些文化是当地文化高度浓缩的精华,也是为游客创造强烈文化体验的素材。对于民族旅游场域中艺术类的文化形式,则可以从“游客体验”切入,从“诗意地栖居”出来。在这种逻辑下,旅游地为了给游客在特定时空内营造深刻而强烈的文化体验,可以通过精妙的设计和编排,应用高科技手段,给游客打造视、听、嗅、味、触觉全方位的五感体验,让游客沉浸其中并获得忘我、快乐等深刻体验感受,从而帮助游客在旅游场域中形成“诗意”的体验。对于旅游活动中涉及到的一些特别的旅游项目,如演出、仪式、娱乐活动、互动式参与项目等皆适用于这一逻辑。

表1 民族旅游场域中文旅融合的逻辑及适用范围Table 1 Logic and application of culture- tourism integration in ethnic tourism field
综上,在民族旅游场域中,文化体现在这一民族日常的生活生产中,文旅融合的不同逻辑可以指导该场域中旅游产品的设计。依托民族旅游场域中东道主真实的生活情境和生活方式,将“诗意地栖居”为出发点,将深刻的文化体验作为旅游最终获得的结果,以始为终,真正实现尊重人、理解人、以人为本,才能实现文旅的真融合与深融合;才能实现人们从自己现实的家走向理想的家,体验别样的、诗意的生活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中探索自我和寻找幸福。而对于民族场域内的一些艺术文化,则可以将为游客打造深刻的文化体验作为出发点,强调即时体验的营造,在有限的时空内将艺术文化浓缩成一个强烈的体验场。这个体验场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通过调动游客的感官体验,让其对旅游地的文化形成快速而深刻的情绪感受。这对游客在旅游地形成延时体验起到深化和强化的作用,其目的仍然是让游客感受到旅游世界的美好与诗意。
5 文旅融合情境下“诗意”的呈现
如果以“诗意地栖居”作为思考民族旅游场域内文旅融合的出发点,那如何理解“诗意”就显得格外重要。海德格尔引用诗人荷尔德林诗中的“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提出了其伟大的哲学思想——“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海德格尔[22]“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表述中,“诗意”的实质就是人对生命自由和谐的体悟,尽管作为人类生活理想图景的“诗意地栖居”并非现实存在,但并不妨碍人们将其作为追寻目标,人们需要追寻并“学会栖居”。海德格尔[24]用“天、地、神、人‘四方’归于一体”进一步解释了“诗意”的状态,即当天、地、神、人四重性融合互现时,人才能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若要剖析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四方归于一体”这种和谐自由状态的状态,“天”“地”指代环境或自然之物;“神”指的是人、物之精神、神性或人的心神,也可以理解为万物被赋予的“意义”;“人”可以理解为物质上的身体。四方归于一体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高度统一的自由和谐状态。栖居之为诗意地栖居始终只能实现于栖居者对栖居之自由的重新学习、重新找回和重新见证探寻的路上,诗意地栖居始终“不会穷尽、硬化在任何一种历史的栖居方式上”[30],这揭示了诗意地栖居与旅游具有互通性,二者相互对应。不难看出,“诗意”的核心在于以人生的完整、灵魂的完善来抵制现代技术发展带来的人的个性泯灭和碎片化,摆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态,找回人的精神家园,实现心灵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这是人类生存的至高境界[31],也应该是人类生存的不懈追求。而民族旅游场域中的“诗意”需要旅游地真实文化的融入才能实现。文化体现的是社会历史生活中人的现实性的实践活动,文化的本质是人化[32]。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客观指向是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33]。可见,文化体现在人的生活中,民族旅游场域内的文旅融合必须基于旅游地真实的生活情境,才能实现旅游的诗意,保证文化、旅游的真融合和深融合。
“诗意地栖居”完整地表达了旅游的现象及内涵:栖居体现了旅游的异地性、暂时性,“诗意”表征着旅游的动机与出游需求。将旅游视为人追求“诗意地栖居”的一种现实路径,文旅融合是实现“诗意”的必要保障,这是深刻理解人、旅游及文化相互联系的关键。那“诗意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本文认为,“诗意”包含两重意思:一是人的自我“诗意”状态,即人作为生命体。一方面要排除日常的“烦忙”,克服成为“空洞的人”,避免“空心化”,所以要主动地重新找寻自我;另一方面在旅游过程中,激发对真实自我的探索,即寻找存在的真实,通过旅游来激发生命中的潜在状态及发现自我[34]。民族旅游场域正是提供了异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让游客感受到不同地方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方式,让他们能够短暂的忘却世俗的“烦忙”,沉浸其中,理解他人,凝视他人,与他人交流互动,进而思考自己的人生,获得对生命、对自我的认识和体悟。二是生活的“诗意”状态。旅游是人离开现在的、世俗的“家”,追求理想的、美好的“家”的一种生存方式。人们在旅游中看美景、吃美食、住酒店民宿,体验着不同文化对于幸福及快乐的理解和实践,本质上体现了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不懈追求。总体上看,旅游给人带来的意义可概括为“自我的成长”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要实现“诗意地栖居”状态,民族旅游场域必须要符合“诗意”布局,也就是民族旅游场域空间和旅游产品的打造要富有“诗意”,人的“诗意”状态首先需要场域的“诗意”才能激发。旅游场域是体现着时间、空间及内在关系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其诗意性就体现在它既是真实的生活空间,也体现着空间内的人对于幸福生活的诠释,“诗意”需要将民族文化要素融入到旅游世界的生活才能体现。诗意地栖居地能够激发游客沉浸其中,实现“心流”体验。可以说,“诗意”是民族旅游场域内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己达到高度统一的状态。只有民族旅游场域首先达到的“诗意”的布局,人的“诗意”状态才能通过旅游活动被激发出来,从而形成沉浸式的旅游体验。
基于“诗意地栖居”理念,文旅融合更能助推民族旅游场域形成不同的“诗意空间”,彰显出各地的特色。因为各地的地脉与文脉不同,将民族旅游场域打造成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将各地的文化元素融入旅游活动的各个要素环节之中,让游客融入真实的生活情境之中,能给游客带来深度的体验,实现文旅融合下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6 结论
旅游的本质问题关乎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对旅游实践工作的指导,也是理解文旅融合的“根”。旅游体验是人们在旅游进程中形成的内心情感结果,并不是人们出游的根本动机。将旅游视为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一种生存状态,其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充分理解人、尊重人作为生命体的本质需求,从哲学的角度将人们的出游行为追溯到人类对于生命存在状态的追求上,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旅游。但“体验”和“诗意地栖居”两种理解并不矛盾,而是互为一体的。诗意地栖居是人们产生出游行为的原因,也是民族旅游场域实现文旅融合的切入点。旅游体验是人在旅游地栖居的过程中产生情感结果,反映文旅融合之效果。文旅融合是保证旅游地富有“诗意”及游客产生深刻体验的中间环节。在民族旅游场域中,文化蕴藏在这一民族的生活中,文旅融合应以始为终,从“诗意地栖居”进去思考旅游供给,从“体验”出来检验供给的效果。而对于作为民族艺术的文化,则可以遵循“以终为始”的思路,从为游客营造深刻的体验入手,利用高科技,设计精妙活动细节和五感体验,让游客获得快乐的体验感受。
总体上,以“诗意地栖居”作为旅游地文旅融合的切入点,不仅指出文旅的真融合、深融合需要游客融入到旅游地真实的生活场景,还揭示了旅游地实现差异化、避免同质化的根本原因。围绕旅游体验进行的旅游产品供给时,在指导文旅融合及旅游产品供给过程中往往会成为无源之水,且容易造成产品同质化,这说明尚未触及旅游的本质性。以“诗意地栖居”作为出发点指导旅游场域内的文旅融合,凸显出各地的地脉和文脉,彰显各地的地方性,为游客营造一种“诗意地”栖居地,让游客沉浸于真实的生活场景之中,那时深刻的体验便自然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