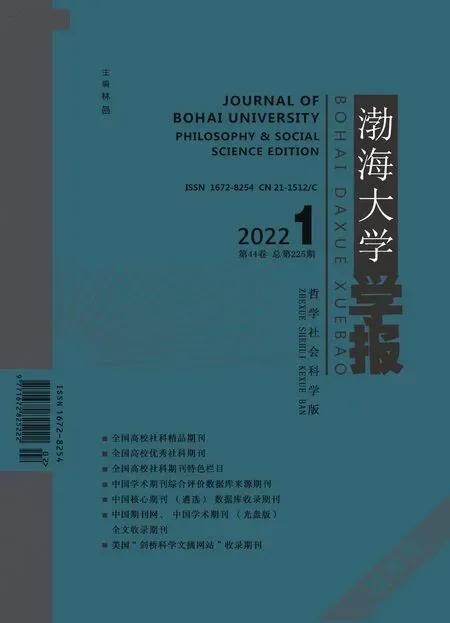张天翼20世纪20年代小说创作风格论
2022-11-30董卉川刘凤霞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董卉川 刘凤霞(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张天翼①在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以讽刺小说享誉文坛,鲁迅、瞿秋白、胡风等人都对张天翼的讽刺小说给予极大的肯定。张天翼讽刺小说风格的形成,经历了轻巧油滑到庄重批判的发展阶段,最终形成了“愤激冷峭”[1]、泼辣深刻的气质。张天翼讽刺小说的笔触对准农村与城镇纷杂的现实人生和社会世相,揭露社会与政治的丑恶与黑暗,从而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讽刺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学界在高度关注张天翼讽刺小说艺术成就的同时,却忽视了他早期小说——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实绩。例如,胡风就错误地把《三天半的梦》当作张天翼的处女作[2],事实上张天翼早在1922年就以短篇小说《新诗》[3]登上文坛。张天翼在讽刺小说方面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早在文学生涯伊始就已初露锋芒,进行了此方面的写作实践。除了尝试撰写讽刺小说外,张天翼还写作了通俗侦探小说——“徐常云新探案”系列。在风格上则呈现出多元并包的特质,或现实书写、或浪漫感伤、或感性抒发与哲理深思并置。20世纪20年代多元风格的小说试验,尽管在思想和艺术手法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早期小说既是张天翼自我风格探索的轨迹,同时也为他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达到创作高峰夯实了基础,在不断的选择中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
一、讽刺与探案的现实书写
张天翼以讽刺小说开启了文学之路,这样的审美趣味与他的家庭环境与教育经历有关。他自陈父亲和“第二个姊姊影响我是很大的”[4],他们都喜欢幽默和讽刺故事,这也影响了张天翼的审美选择。此外,在早期文学启蒙上,张天翼自称:“我在通俗图书馆看了许多林琴南译的东西,还有许多侦探小说。最拿手的故事是所谓《撒克逊劫后英雄略》(W.Scott:Ivanhoe),《滑稽外史》(C.Dickens:Nicola)等等,还有些什么《福尔摩斯》,《亚森罗苹》之类的侦探故事”[4](65)。“因为爱看小说之故,和几位同学写起来。都是些在林琴南和《礼拜六》之类的影响之下的”,“写了些滑稽小说”[4](66)。不难看出,张天翼早年的精神资源主要是通俗文学作品,包括侦探小说、林译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这些作品,尤其是狄更斯的讽刺小说,已经潜移默化地对他产生持久影响。
张天翼早期的讽刺小说有《新诗》《流星》《怪癖》。《新诗》和《流星》显然是林纾《荆生》《妖梦》的仿制品。虽然张天翼针对新文化运动冷嘲热讽,思想守旧,立场保守,却已表现出现实主义苗头,以及讽刺的天分。《新诗》讽刺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自命不凡实则滥竽充数的白话诗人。“斯莱”是一位热衷于写作新体诗的“诗人”,她将刚刚创作完成的一首不通文墨的诗作向夫君“黄遵妻”炫耀,“遵妻”听完这首毫无诗意、一窍不通的“诗”后,向妻子提出了一些疑问,尤其是诗歌的核心问题“韵”——“韵何在”[3](38)。自命为诗人的“斯莱”竟不知何谓韵,“吾乃未之前闻”[3](38),令人捧腹。“遵妻”向妻子解释诗歌的平仄、韵律等问题时,“斯莱”因不解其意,怕丈夫嘲笑,只能以下午外出购物为借口,匆匆结束谈话。值得玩味的是,小说全篇以文言谱就,而“斯莱”所做的两首新体诗“他底儿女”和“北风”,则以白话写成,这是张天翼故意为之,通过语言形式的巧妙布局,形成了高雅—低劣、深邃—肤浅的对立碰撞,由此激发出一种强烈的讽刺张力。张天翼以精巧的布局,借“斯莱”可笑无知的言行,揶揄批判了新文化运动中某些白话新诗人实乃沽名钓誉、言文不通之辈。
《流星》同样讽刺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某些社会世相。主人公“方苟丕”自命为“新文化健将”[5],这是典型的反讽。他追求“非孝”“平等”,称父亲为“仁兄”,父亲病重也不返乡探望,美其名曰要脱离旧家庭;而当生活费不足时,又无耻地向父亲道歉以讨要钱财。“苟丕”擅作新诗,三天能作三百多首,在一众新人物的鼓吹下,被誉为著名白话诗人,四处演说,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他的妻子“尤昌”更是一位思想开放的新女性,主动追求“苟丕”,目的是成为文化名人、著名诗人的妻子,从而与丈夫一道出版新诗,继而四处演说,追名逐利。她更是“自由”“平等”的倡导者,与“苟丕”离婚后,相继嫁给了无数个男人,践行男女平等、恋爱婚姻自由的人生理念,最后生了一身杨梅大疮。不学无术的“苟丕”与“尤昌”离婚后,被“尤昌”排挤得身败名裂,最终沦为乞丐。“苟丕”“尤昌”分别音同“狗屁”“犹娼”,再配以反讽的技法、夸张戏谑的情节,嘲弄批判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某些言必称自由平等的“新文化健将”们的丑态和无耻嘴脸。在小说结尾,张天翼以反讽的语气再次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我道方苟丕先生自命为新文化中的明星。后来流落了。所以叫做‘流星’”[5](35)。
《怪癖》描写了罗家二小姐的种种生活怪癖,如专用茶杯被打碎之后,竟不喝水,还要上吊明志,这只不过是她无理取闹和博取家人眼球的一种策略罢了,“二小姐这种上吊法子就是吊到明年,也是吊不死的咧”[6]。小说借罗家二小姐的怪癖讽刺暗喻了权势阶层中的贵妇人、娇小姐们的无病呻吟、扭捏作态。
除了讽刺小说外,张天翼还创作了多部侦探小说——“徐常云新探案”系列,包括《少年书记》《人耶鬼耶》《空室》《遗嘱》《玉壶》《铁锚印》《斧》《X》等作品。侦探小说由于情节紧张离奇、故事幽默风趣,因而在清末民初形成了翻译和创作热潮,翻译的侦探小说占了文坛译著的一半之多,程小青的《霍桑探案》、赵苕狂的《胡闲探案》等都是其中代表作,张天翼亦不例外。他的侦探小说引起了当红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注意,“新进作家中是当推张无诤先生所作之《徐常云侦探案》为首。虽情节略嫌草率,然彼年未满念稔,能为此不被人情之侦探作品,已是令人咋舌而钦佩不止矣”[7]。案件由“常云”侦破,“仁之”协助参与其中,并记录各个案件,“只有五天前的一椿钻石窃案。倒还离奇。但是这案破了之后。我和常云二人被多人仇视。又不便将他记在笔记上。这是我自己知道对于读者诸君很抱歉的。但也并不是我龚仁之的不是啊”[8]。“我很望无诤先生做侦探小说时也顾到这一方面”[9],这种元叙述的视角在早期的新文学创作中较为新颖。仁之一方面注重记录呈现常云那超凡严密的推理天赋,另一方面则借助不同类型的案件描摹社会世相,揭示社会弊病,在对人性的勘探上,已然显露出其敏锐的洞见。譬如《玉壶》中的罪犯陶冈,贼喊捉贼,陷害信任自己的好友子俊,“居心很恶”[10],人性的丑恶跃然纸上。他在作品中批判麻木愚昧的看客群体,“门外站了许多人。都颠了足尖,伸长颈子看里面。还有许多人在那里议论”[11]。这些小说,虽然并未摆脱西方侦探小说的套路,但在社会现实的细腻记录和忠实描写上,彰显出深厚的功力,同时体现出初步的批判色彩。
张天翼早期的讽刺小说和探案小说,显示出文学新人的不俗实力,初露了他对于讽刺手法的偏爱和执着,同时也体现了现实主义和启蒙立场的萌发,不仅为他日后讽刺小说中戏剧性的张力和简约的笔锋奠定了基础,也为他走向深沉的现实主义书写开辟了新的可能。讽刺小说的深刻泼辣以及侦探小说的严密细节,都开启了张天翼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转向。
二、浪漫感伤的心灵探秘
张天翼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在现实书写的同时,也显露出了新文学早期所流行的浪漫感伤气质。“五四”落潮后,学人们的内心郁积着彷徨、迷茫、忧郁的情绪,张天翼亦未能免俗。《苦衷》《月下》《走向新的路》等作,探秘描摹了个人悲苦彷徨、忧郁迷茫的精神世界,呈现出鲜明的浪漫感伤风格。
《苦衷》揭秘了主人公“我”苦痛的人生和悲苦脆弱的心灵,“你看,不是比劳工还苦吗……比做学生时代的书记还苦呢……我这么辛辛苦苦还要挨骂……不觉暗暗掉下泪来……不知我的苦衷……我几乎放声大哭起来……总有一个人吃这苦头……只得再去做那烦恼的生活……无论什么学校里的书记先生都有我这同样的苦衷”[12]。该篇是“我”个人感伤情绪的外泄与悲苦心灵的展露,心灵的脆弱悲苦看似是旁人的欺压、工作的繁重、肉体的不适,以及家庭的重担,实则与外部的环境无关,被“我”归咎于命运的作祟,“我的命运上似乎定着我是做书记的”[13]。神秘的宿命论进一步增强了作品浪漫感伤的气质,不幸的命运令“我”的心灵更加脆弱悲苦。张天翼深入“我”悲苦脆弱的精神世界之中,窥探、剖析、描绘“我”的心理状态,继而向读者倾诉呈现自我的烦恼彷徨、脆弱悲苦。在《苦衷》中,依然有一定的情节和少量的对话,但情节仅为情绪服务,对话则因情绪而消散,这是浪漫感伤风格小说的典型特质,以情绪结构文本。
《月下》展现了主人公“他”痛苦悔恨的精神世界,作品以“他”的感伤情绪建构文本,由“他”的心理活动、人生回忆、个人幻想所构成。“他”的心理状态为悔恨痛苦,源于自己的“非孝”观,这导致了母亲在临死前都未能见到自己,“他心想,我为什么要提创非孝?我当初激烈的说父母生我们,是偶然的。他们养我们,实抱着一种希望心,并非出于真心。他宣布这种话的态度还记得很牢。他又道,唉,我当初说这些话时,为什么不记起父亲临死的样儿啊。”[13](2)大段对母亲的回忆涌上心头:父亲早逝,母亲艰难抚养并悉心照料自己,生活的困苦、对丈夫/父亲的思念,令母子二人终日沉浸在苦痛的情绪之中,“哭泣”是母子二人的生活常态,“泪珠和潮水般的淌下来……他见他母亲无故的哭了,他也哭了……他哭了,伊也哭了”[13](3)。对自己“非孝”的极度悔恨、对慈爱无私的母亲的极度思念,令“他”产生了幻觉,进入了浪漫的梦境之中,梦中的“他”看到母亲在月下向自己走来,对自己没有丝毫的责备,而是依旧充满疼爱与关怀,这更加令“他”无地自容、怅恨无比,哭喊着扑向母亲,乞求伊的原谅,“却扑了个空”[13](4)。结尾短短几字将浪漫感伤的情绪推向了高潮,留下了无尽的苦痛哀怨,令人唏嘘。
《走向新的路》展现了主人公“她”矛盾、彷徨、痛苦、战栗的精神世界。“她”原本追求理想的爱情,不料现实的命运总是折磨、欺侮、玩弄“她”。因此,“她”渴望同“可怕的爱人”[14]私奔到“梦想的黑的国”[14]中,从而结束现实的苦痛。但当“可怕的爱人”——“黑的怪物”[15]真的出现时,“她”又对“她希望着的人,理想的爱情”[15]感到无比的恐惧和排斥,尖叫、身子颤抖、让“黑的怪物”快走、呼喊母亲,一系列的外在举动与内心诉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矛盾。而这“黑的怪物”只有“她”本人才能看到,“她”的父母、医生都看不到,大家认为“她”患了癔症。“她”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这是一个由自我的幻想建构而成的精神世界,幻想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矛盾。“黑的怪物”从“她”的幻想世界离开后,“她”便回到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适宜的温度,温和的空气”[16]令她感到舒适,再次印证了“她”外在举动与内心诉求的矛盾。但现实世界无法令“她”获得真正的快乐,“她”又感到了恐怖与痛苦,这意味着自己依然要“走向新的路”——与“可怕的爱人”私奔到“梦想的黑的国”。“黑的国”“黑的怪物”等意象暗喻了充满荆棘与苦难的人生新路,揭示了走向这条新路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与代价。作者在结尾设置了开放式结局,并没有揭示人物的最终走向,进一步凸显“她”的矛盾与彷徨,更平添了感伤的情绪。全篇在心灵探秘的同时,以幽婉含蓄的表述和暗示性意象的应用,增强了文本浪漫感伤的气质,意境悠远、韵味无穷。
在《苦衷》《月下》《走向新的路》中,心理描写表现了主人公感伤悲哀的情绪和痛苦矛盾的心灵。这种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彰显出张天翼精细的观察力,也体现了他对人心与人性探索的深度,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中也十分常见。《陆宝田》《宿命论与算命论》《请客》等小说,无不显示出张天翼出色的心理描写才华。
三、现代主义风格的初步尝试
《恶梦》《黑的微笑》《三天半的梦》几篇作品,透露着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对于痛苦、死亡、颓废、黑暗表现出别样的偏爱,通过对现代人情感模式、感受方式、想象能力的勘探,力图构建一种现代美学。作者自称这些作品“能在女人的头发里看出半个地球来”“想躲到象牙做的宝塔里玩玩神秘劲儿”,是趋附时髦之作,“这种东西是不要内容的”[17]。显然,这种说法有意气的成分,尽管这几篇现代主义的作品并不成熟,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写作手法和美学倾向融化到张天翼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中,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深度的表现空间。
《恶梦》描写了“我”的梦境,在梦境中,“我”抒发了亡国之痛,以及对侵略国的仇恨,“明月方当空也。此时寂寞若死。余仿佛已清醒而身已在廓然之中。”[18]开头的环境描写虽然只有寥寥数笔,但用语惊警,比喻新奇,充满了现代色彩。在激愤的情感抒发的同时,“我”在梦境中对国民性进行了批判。面对侵略国,青年知识分子带头抵制该国商品,然而他们很快使这场爱国运动成了“五分钟热度”[18](7)。而“我”从梦中悲愤醒来,一时间竟产生了“梦蝶”之惑,“眼眶之中犹有泪痕,唬哭之声隐隐在耳,不禁竦然。”[18](8)“我”在恍惚中混淆了梦境与现实的界限,而张天翼又在结尾处加了“叙述圈套”,“遂披衣起告之。无诤谓此可作小说也。”[18](8)这样的叙事实验,足见张天翼的精心营构。
《黑的微笑》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气质,浸染着现代主义的色彩。小说名与安特略夫的象征主义名篇《红笑》有相似之处。小说以日记体写来,揭示死亡的神秘与恐怖诱惑,表现出对生命本质的沉思与探寻。“这是怎样黑的空气,这是怎样恐怖的空气!”[19]开篇就奠定了全篇的阴郁、诡异、压抑的死亡气息。“看罢,夜是如此之高,如此之大,他伸着双臂拥抱着一切。他装着鬼脸叫所有的生物噤声,叫所有的生物灭亡了。大地上还有什么呢:什么都是黑的帝国的领土了,黑的势力伸张到天边,使人找不到地的轮廓。窗外也蓦人了寂静,死似的寂静,那棵枯树犹是矗立在空际,衬在暗蓝的天色上,变成黑色的枯骨了。可是他噤声着,即使拂过微风,也不敢摇他的手臂。此外呢,此外一天麻点似的星星在闪耀着。”[19](1)张天翼以象征、暗示、拟人等手段,刻画出具有颓废色彩的意象,“鬼脸”“黑的帝国”“黑色的枯骨”充满死亡气息,与人物躁郁的情绪联动应和,暗黑的色彩烘托出神秘氛围。而通感与联觉的调用,更是揭示出人物不安的精神世界。“黑夜多么可怕!他是死的羽翼。灯熄了,黑色便流进来,它一起一伏地翻着黑的波浪。……它在房中太骚扰了:它微笑,它跳舞,它来拂着我的头。象征式的话平素不爱说,可是这次确乎听到类似翅膀的声音”[19](5)。对于荒诞世界的一种情绪反应,……这些充满了颓废气息的象征,渲染出死亡的神秘残酷,以及“我”对死亡的恐惧,“没有想到的现实在神秘地跳舞”[19](5)。这里,张天翼通过象征主义手法极大拓展了小说的表现领域,死亡的探寻,生命本质的展现、人生真谛的揭示,都达到了此前创作未企及的高度。
《三天半的梦》以书信体的形式,细腻而忧伤地探索苦闷、彷徨、厌倦等现代心理感受。全文笼罩着忧伤的基调与迷梦似的氛围,以细腻之笔揭发现代青年的精神困境。“我”对一切充满了矛盾厌倦之感,“人所以为万物之灵,只是因为人类是一种矛盾的动物。人身上,一定还有生理学家所未发见的一种神经,叫矛盾神经。如今的人的对所谓家庭的态度,全是矛盾神经的作用吧。”[20]故乡杭州显得无聊可憎,年迈的父母可怜可厌,而自己同样可悲可叹。在父母建造的“感情的监狱”[20](1801)中,“我”立意反抗,出于怜悯又要敷衍他们。在这种矛盾和撕扯中,“我”感到寂寞和悲哀。张天翼对于中国式亲子困境的观照,其实也是对人存在本质的探寻。
《恶梦》《黑的微笑》《三天半的梦》比之张天翼20世纪20年代的其他作品,更显晦涩与深邃,作品借助现代主义风格,以日记、书信等形式,在晦涩的意象、迷离的梦境、精神的分析中渗透作者对生命、时代、人性等方面的玄思。张天翼20世纪20年代小说的现代主义的手法还略显稚嫩,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中则已十分圆熟,并且与作品的现实主义基调完美融合,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表现空间,也拓展了人物精神、心理、意识的探索深度。《梦》中则对卢俊义的梦境进行了细腻的刻画,烘托了人物迟疑、后悔、矛盾、充满疑虑不安的内心世界。《成业恒》就是将融合了象征主义手法与意识流的特质,细致描写出成业恒被捕入狱后精神陷入崩溃的境地。《蜜味的夜》则以讽刺的笔调,绘制出一群自称Modernist 的上海摩登人物的丑态,其中不乏对现代主义意象的纯熟运用。这些都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探索有密切关联。
结 语
张天翼20世纪20年代小说的创作风格多元并包,既有现实的犀利讽刺,也有曲折紧张的侦探推理;既有充满感伤的个人抒唱,也有智性的反思探索。早期的小说写作,虽然稚嫩,但其中鲜明的个人特色已经悄然成型,包括讽刺风格的初步尝试,对国民性的深入探查,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捕捉,对于生命存在的哲理探索……这些多元的尝试,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中有所显现,同时也为张天翼后期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通过早期的写作探索,张天翼锻炼了个人笔锋,确立了个人的特色,逐步转向20世纪30年代独特的现实讽刺风格。随着外部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的急遽变化,张天翼本人的思想倾向也产生了剧烈的震动,“从牛骨头之塔走出,想学习写写现实世界里的真正的事”[17](14),“从空虚到充实”,实现了文化立场、创作风格、审美趣味、思想内蕴等方面的全面转轨。张天翼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就其创作史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过渡意义;而张天翼由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转型,也是时代变动中的文化轨迹的具体彰显。
①张天翼(1906—1985),1906年9月26日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湖南湘乡,1912年之后随家人定居杭州。原名张元定,号一之,除笔名张天翼外,还有笔名张无诤、无诤、铁池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