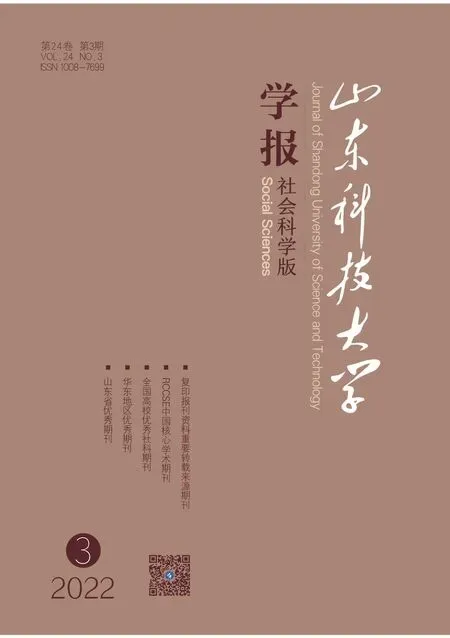《马丁·伊登》的电影改编策略
2022-11-29李方木李晓玮
李方木,李晓玮
(山东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是美国文坛的一位高产作家,书写风格粗粝原始,深受文学市场的青睐。作为伦敦后期的一部文学佳作,《马丁·伊登》(MartinEden, 1909)有其早年经历的投射与缩影。该书讲述了藉藉无名的年轻人马丁·伊登在爱情的鞭策下奋发图强,终成为名噪一时的作家,然而却在名利双收之际,因文学之梦的破灭而万念俱灰,最终选择跳海自戕。社会不公摧毁了一个有志青年的理想,也昭示着美国梦的幻灭。
20世纪美国电影业的崛起,促成了杰克·伦敦文学作品的多部头、多层次改编。受碍于当时技术的落后以及作品本身的复杂性,数次电影改编均差强人意,甚至不伦不类,无法凸显原著背后蕴藏的旨意。近年来,影视行业的技术革新与大幅提高为再现杰克·伦敦作品的恢宏磅礴提供了可能。意大利青年导演皮耶特罗·马切罗(Pietro Marcello)执导的《马丁·伊登》在2019年威尼斯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男主角也因在马丁·伊登角色上的出色表现,一举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国内外对这部小说已有较为详尽的研究。B. 贝科夫(B. Bekov)认为该作以逼真的生活场景与高度的艺术成就见长[1];萨姆·巴斯克特(Sam Baskett)则指出,伊登的梦想足以与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相提并论,两者皆宏伟有余,俨然一幅理想化的爱人形象。[2]作为一部典型的“成功小说”和“成长小说”,[3]这部小说的主题也很鲜明,尽管与其他古老话题一样普通。正如导演马切罗在接受新浪娱乐采访时所言,虽然小说再现的是已然过去经年之事,某种意义上说却是“永远不会过时”。这位新锐导演在充分研读、揣摩原著的基础上,实现了异常成功的跨媒介改编与意大利本土化重构。本文以马切罗《马丁·伊登》的电影改编策略为聚焦点,从外层叙事形式、内在叙事结构和主题意蕴三个角度进行跨媒介分析,探究电影改编者既不违原著的意指,又能充分餍足当下大众审美需求的个中策略,以期为同类名著改编的研究提供镜鉴。
一、外层叙事形式的改变
影版《马丁·伊登》的特色之一是对原著背景的悄然置换与文化符码的潜在解构。斯图亚特·麦克道格拉(Stuart McDougal)认为,每一种艺术形式都会因承载媒介的不同而独具特性,电影制作者将故事改编为电影之前,必须认清每一种媒介的独特性。[4]小说因其固有的虚构性,允许模糊化概念的存在,给予读者想象的留白空间。电影则需要营造一个明确的叙事空间,让观众在脑海里生成特定的场景效应,观影过程中才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二者的本质悬殊是电影改编者无法回避的难题,而且这一难题对于跨文化、跨国界的改编者则更为棘手。正如达德利·安德鲁(Dudley Andrew)所称,原作的独特性会被保留到一定程度,直到改编作品有意不予以吸纳。[5]因此,对原著进行本土化改编不宜照本宣科,而是要通过多样化的改编策略进行替换与舍弃,使电影逻辑更加合理,同时保留原著的精神主旨。
一般来说,时空变换是电影本土化改编的一个常见策略。杰克·伦敦原著的时代背景置于20世纪初,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中产阶级迅速崛起。与此同时,贫困人口大量涌现,社会矛盾难以调和。小说多次描写到马丁被资本家盘剥,日常生活基本被“折磨精神、摧残肉体的活计”[6]195占满。这从旁印证当时底层人民恶劣的生存状况,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影版《马丁·伊登》则将背景设置在一个年代不详的意大利小城那不勒斯。这一改动暗藏玄机,并非随意之举。影片没有透露确切的年代,一方面可赋予观众足够的想象空间,使其根据片中蛛丝马迹形成各自的观点,又在暗示该故事具有超越历史时间的普遍性。此外,故事地点的选择也彰显了改编者的独有考量。据希腊神话记载,女妖塞壬生活的区域就位于现在的那不勒斯附近。当奥德修斯的船队经过时,塞壬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跳入大海为爱而亡。这一凄婉的传说恰好与杰克·伦敦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投海自尽的结局遥相呼应,他在生命的尽头遵从冥冥之中的召唤奔赴大海,召唤本身也许正是海妖魅惑的歌声,亦或是如海妖般令其肝肠寸断的爱情。
改编电影对原著的文化符号改头换面,成功与意大利本土文化接轨,避免形式上的参差。影版《马丁·伊登》除了主角及其挚友布雷斯顿(Brissenden)的名讳未变之外,其余人物都被换上了意式传统浓郁的姓名:伊登爱慕的罗丝(Ruth)成为伊琳娜·奥西尼(Elena Orsini),姐姐则更名为朱利亚(Giulian),然而改编中沿用原名的做法也是别有用意。不论是电影还是小说之中,伊登和布雷斯顿始终恪守对美与艺术的不懈追求,不向金钱世俗妥协。如此操守令其与时代、与社会格格不入,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电影未对二者的名字作出改动,可视为对“异类”的接受,也是对原著的认可与接受。
此外,影版《马丁·伊登》淡化了小说鲜明的时代政治印记。小说中的美国与电影里的意大利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小说家所描绘的特定时期的美国社会以及大谈特谈的政治立场,无法在另一种文化里全盘复刻。当然,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仍具有相似性的基础,如生存的困苦与窘况,以及资本的丑恶与无情。改编电影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将三教九流之徒、附庸风雅之辈和蝇营狗苟之事刻画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当代社会大环境之下人生的芜杂与不易,这与小说中折射的时代特征不谋而合。这种地域与时间上的改变不仅顺应了本土语境的需要,也将观众带入感性认同的叙事背景中。无论变换时空,还是消解国别特性,这样的改编并未撼动原文本的深层结构,停留于表层的微调。这并不意味着表层元素的无足轻重,外部形式的恰当改动既能调动观者的心理认同,也可达至锦上添花的效果。
闪回(Flashback)是这部改编电影反常规叙事的另一重特色。莫林·特里姆(Maureen Turim)认为,经典的闪回往往出现于影像从当下叙事转入过去经历之时,可理解为人物的故事叙述或主观回忆方式。[11]内容可涉及人物的回忆、梦境或想象,透过丰富、暗示性影像制造悬念,阐释人物动机,表现人物情感。原著对人物细腻准确的心理描写是杰克·伦敦的鲜明特色,彰显了作家深厚的语言功底,在电影改编者那里却成为一个难题。电影人物无法像戏剧舞台上的人物那样,旁若无人般畅所欲言心中所想,往往只能通过面部表情或肢体动作来表现复杂、隐秘的心理活动。不过,此类常规性手法的弊端也是有目共睹,即观者无法知晓人物的心理全貌,不得不依赖演员对人物形象的揣摩程度与表演效果。对此,马切罗在处理原著俯拾皆是的心理或情感描写时,巧妙采取闪回策略,以极具张力的形式直观再现人物情感与心理波动,避免了纯粹流于形式的外在演绎。影片别具一格采用伪纪录片式的闪回镜头,这种影像外化了伊登的情感波动和精神顿悟,满足叙事要求之余,又赋予情景内容以厚重的历史感。
伊登与女友初次会面之后,一路雀跃着走过海滨大道,穿过逼仄的小巷与热闹的人群。在此过程中,女友柔美的面庞不断出现,同时又插入一个怀抱娃娃的小男孩,羞涩地看一眼镜头便转身跑回窄巷。这一段镜头的混剪令人困惑,事实上,女友的反复显现表明伊登对她的倾心,而怀抱娃娃的小男孩则可能是男主人公的回忆抑或想象。这便暴露了他的心理轨迹:伊登像对待童年美好记忆一样,将女友珍藏心底。此外,伊登因缺乏常识,被面试官建议先读两年小学时,镜头中插入一段黑白闪回的影像:一位衣着邋遢、满脸沧桑的中年人在黑板上歪歪扭扭写下自己的名字,下面一群孩子起哄嘲笑。这一片段究竟是伊登的真实回忆,还是窘迫幻想,观众不得而知,但闪回方式呈现的影像外化了人物彼时复杂的心理波动,增加了影片解读的多维可能性,制造了观影的难度与乐趣。值得一提的是,伊登创作的小说有时也以闪回方式再现,他一边在打字机上笨拙地敲入字码,塑造出的小说世界也透过几个闪烁的镜头片段徐徐展开:独腿的孩子,含泪送别丈夫的妻子,寥寥数个画面的穿插堆叠留给观者一览伊登文学世界的机会。
二、内在叙事结构的创新
与文字叙事不同,改编影片运用镜头语言与声光电设备,营造出别样形态的内在叙事结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指出,小说之中存在着“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7]事实上,电影也有“复调”。动态影像、音乐特效、演员动作与话语等叙事元素可以理解为“电影复调”,在电影叙事艺术与技巧指导下,重建起逻辑自洽的内在叙事结构,“引导观众深切感知电影”。[8]30受时长和呈现方式等因素的限制,改编电影往往会与原著保持一定距离,在差异基础上创新内在叙事结构,最大程度保留菁华是改编成功的关键。
E. M. 福斯特(E. M. 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AspectsoftheNovel,1927)中将故事定义为,“依时间顺序对事件的叙述”。[9]这种“叙述”会在文中埋藏伏笔,制造悬念,而电影改编则会巧妙运用小说叙事的时间性,重置故事的叙事进程,以更为契合电影媒介。原著采用常规的线性叙事模式,其中穿插着伊登对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使得整个故事架构明了简洁,逻辑清晰。而在改编电影中,除了常规的线性叙事之外,增加了环形叙事结构(Cyclical Narrative Structure)。所谓环形叙事结构是指故事的开头与结尾交相辉映,审美魅力不仅在于它“全新的形式陌生化”,并且取消了电影叙事中“绝对”和“停止”这两种概念,因果相对、首尾相连,时空因之成为心灵周而复始、轮回运转的载体。[10]改编版开端于功成名就的伊登口述写作的场景,他目光空洞,神情悲凉,俨然一个堕落浪子形象。接着,镜头切入一段古老的纪实影像,一辆满载旅客的火车从远方驶来,消失于漆黑的隧道之后,电影叙事正式开始。将这段看似与原著毫无关联的情节放置在电影开局的确令人匪夷所思,纵览电影之后才会猛然领悟:该情节在形式与内容上的设置精思密想,蕴涵深邃。从形式上看,开头的伊登即是结尾处的伊登,显得暮气沉沉、颓丧厌世,电影中间部分主要呈现他沦落至此的心路历程。这种首尾呼应的叙事结构使整部影片构成一个完满的闭环,让观众不禁为主人公命运的戏谑无常而悲嗟。从内容上看,片头的火车意象是对小说结尾的预设。小说描述伊登的意识消失之前:“[火车]在他的脑子里,它发出明亮而闪烁的白光。它的闪烁越来越快。他听到一阵长时间的轰隆声,似乎他正顺着一段深不见底的楼梯摔了下去。落到楼梯底下时,他陷入黑暗之中”。[6]482影片开头的火车同样轰鸣着进入隧道,镜头转向微弱晃动的外部白光,随着镜头逐渐拉长,白光愈来愈弱,黑暗从四周涌过来。这里的火车不妨视作伊登的象征物,火车从光明进入黑暗,象征着主人公由生到死的瞬间。这一开篇镜头实际是导演利用艺术性手法暗示伊登溺海死亡的最终命运,从而在宏观层面与影片结尾构成回环结构,增添了影片的神秘性与审美价值。
电影改编“反对依样画葫芦的虚假忠实,即图解原著式的改编方法,强调电影改编的创造性”,[12]事实上,电影可视作小说原著的二次创作。电影的时长限制意味着它不可能对各种细节面面俱到,一板一眼地涵盖小说全部内容,必须有所侧重与扬弃,以挖掘小说主题的新阐释,凸显不同人物特点或通过影片道出书中存疑之处。这里,小说与电影虽然都以伊登由生向死的主线娓娓道来,两种叙事情节则出入颇多。首先,影片有意淡化小说的爱情主线,反而落脚于伊登的个性成长。小说中许多次要人物的戏份在影片中遭到删减。例如,原著几乎每一章都涉及伊登对罗丝的爱慕,用较多篇幅对她的心理波动进行细致刻画:初见伊登时不可名状的“冲动”与“渴望”,[6]94对其不切实际的创作理想心怀不满,以及权衡利弊之后绝决抛弃昔日爱人等等。这种不吝笔墨的情感描写到了改编影片中大多只是寥寥几个镜头,没有大费周章地铺开叙述,更多的是作为旁支来辅助叙事进程。其他次要人物的镜头更是少得可怜,整个叙事框架仅围绕伊登的成长展开,着重于他对人生的开悟,而次要人物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影片有意借伊登所见所感来揭露底层民众的苦楚与上层阶级的虚伪,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处要属伊登与女友看完戏剧后的对谈。原作中伊登认为罗丝口中的艺术之美不过是矫揉造作的粉饰虚假,绝非真正的艺术,而罗丝出于出身偏见对此不屑一顾:“罗丝再次凭借外在的因素,根据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衡量着他的思想”。[6]257两人争论过后,伊登写出名为《幻想的哲学》的论文。改编电影之中,两个人物的争论超越审美理解,上升至阶级认知的高度:女友认为艺术应展现美好与期望,伊登则相信丑陋冷峻的现实才是最有力的呐喊。他将女友的鄙夷归咎为她从未目睹过真正底层生活的卑贱残酷,无法理解作品的内在价值,于是强拉着她穿街过巷,逼迫她一睹底层生活的凄凉。此时,晃动的镜头营造出焦灼的紧张气氛,浓妆艳抹的妓女、酒气熏天的醉汉、烈日下的采石者以及街头一掠而过的卖唱女,形形色色的人群浓缩了生活的各种苦难。然而,女友对此并未流露出悲悯,反而恳求回家,恐惧、反感与厌恶暴露无疑。这一处情节的增加不但暗示二人不可弥合的意见鸿沟,也反映出女友代表的上层阶级的冷漠与顽固。
小说开篇有个细节尤其需要关注,伊登在女友家中看到英国诗人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的一本诗集,到了电影中则改换成为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书。意大利毗邻法国,空间上的便利性促使两国之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异常密切,改用法国诗人的作品显得合情合理。更为重要的是,波德莱尔与杰克·伦敦在文风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摒弃传统,另辟蹊径,揭下生活隐晦虚伪的面纱,将现实的丑恶一一呈现。因而,两人的作品都曾遭受过排斥、打压和查禁,后来经过时间的检验,才成为不朽的经典。改编电影选择波德莱尔的书,因而也可是对原作者的影射与致敬。这一独具匠心的细节设计使得改编电影在原著之外更加耐人寻味,也体现了改编者的良苦用心。
此外,电影结尾增加了伊登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场景,这可视作全片的高潮,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面对社会名流与各路记者,他情绪激动地说:“我写的东西从前没人青睐,如今却风靡一时,它们从未变过……那些曾对它不屑一顾的人,如今对我趋之若鹜。”电影借主人公之口控诉着社会的荒诞不公,鞭挞了自诩为上流人士的虚伪与肤浅。既然理想之火已灭,伊登的满腔愤懑与无尽绝望则无处安放,只能选择最后的自戕。可见,改编影片独特的叙事手法以及对原著的增删与重置,并未给整部电影叙事框架造成突兀或累赘之感,反而既保留了原著的核心精神与审美价值,又传达出改编者独特的美学阐释。
改编电影以帆船意象影射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加深观众在对情感幻灭体悟上的视觉冲击。帆船意象在电影中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伊登在女友的劝说下决定重拾荒废学业的那一刻,镜头转向一艘海面上漂浮着的帆船,在微风中轻轻摇摆。接下来,马丁以画外音口述信件,把告别女友之后的个人经历娓娓道来:他找到了新工作,一刻不停地朝着知识王国进发,还在学习诗歌创作,从中萌生了对未来生活的大胆构想——成为作家。整个画面搭配欢快的音乐,传达出昂扬乐观的情绪,预示着马丁为了追逐理想而扬帆远航。帆船意象的第二次出现是在主人公爱情、友情双双受挫之时,伊登在寂静的旷野中无助地哭泣。此刻镜头切换至海面上的帆船,它在伊登啜泣的背景音中突然急遽下沉,加之紧张局促的钢琴伴奏,帆船很快就消失在海面之下,帆船的沉没意味着伊登个人理想的幻灭。正是从那之后,他的性情大变,先前的务实开朗全然被颓废沧桑所取代,周身散发出悲观厌世的疏离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帆船沉没于大海的画面预示了伊登跳海的悲剧结局,在此构筑了一个精妙的伏笔。再者,帆船与大海也十分契合伊登早年的水手经历,一浮一沉的帆船航迹也在指涉主人公生命斗志的大起大落,隐喻性呈现了伊登幻灭的人生旅程,从而加深了主题意蕴。
三、电影叙事的主题挖掘
杰克·伦敦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叙述了马丁·伊登的人生低谷、高潮与绝境,以人物的生活遭际来涵括许多引人深思的主题:个人主义、阶级跨越、爱情与事业的权衡。这既是小说的菁华,还暗含着作家自身的人生态度。改编者若将如此驳杂的主题逐一呈示,影片内容难免冗长累赘、主次难分。正如桑普·马克斯(Sample Marx)所言,电影改编不必遵从原文本,而应该照顾到观影人的视听感受。[13]霍顿·福特(Horton Foote)也认为,改编作品应该具有自己的“节奏和生命”。[14]因此,马切罗的改编电影基于原著,巧妙运用改编技巧与镜头语言,集中展现了幻灭的主题。幻灭是贯穿全片的主线,亲情、爱情、友情、理想则含蓄地点缀其旁,逐渐凋零陨灭。影片中伊登的幻灭之旅,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沦为沮丧“觉悟者”的转变过程。相较于小说的多视角叙事与多重主题,电影叙事更为明晰单一,观者跟随马丁·伊登的视角,一步步看到他的成长、觉悟与沉沦毁灭。
改编影片从两个方面来渐次深化幻灭主题。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幻灭是马丁·伊登对外部世界的绝望。姐姐的不解与姐夫的嘲笑奚落让他与家人日益疏离,爱人的决然抛弃也令其心灰意冷,屡屡被拒的稿件打击得他迷惘无奈,最终对生活的热情憧憬沦为无尽的失望与失意。好友布雷斯顿的突然离世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接二连三的变故之后,他认清了生活的痛苦本质,继而产生厌世的幻灭感。到了影片的后半部分,幻灭表现为主人公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消亡,突出表现于伊登对爱人与文学的弃绝。女友因某些世俗考虑离开伊登后,幸运之神突然降临后者身上:伊登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学新星,名望水涨船高,跻身梦寐以求的上流阶级。而昔日爱人在目睹他的声名鹊起之后,重新登门乞求复合,这种低微姿态与谄媚言语令伊登始料未及。那一瞬间,他猛然认清了女友的本质——她与那些矫揉造作、趋炎附势之流并无二致,对她仅存的过往幻想顷刻间烟消云散。爱情于伊登而言是纯粹高尚的,然而当他醒悟到原本苦苦维系的感情也无法免于世俗之染时,便对“神圣的爱情起了疑心”,[6]462精神世界不可避免地走向幻灭。另一方面,对文字丧失热情也是伊登精神幻灭的标志。影片前半部分中他醉心于文学创作,彼时的他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即便屡遭退稿,也从不气馁。对每一篇文章,马丁都倾注心血,精雕细琢,绝不敷衍了事,文字于他是神圣的,是情感的宣泄,是精神的支撑。好友布雷斯顿的逝世与突然的时来运转令其猝不及防,身心俱疲,以前被拒的稿件纷纷成为众人拜求的佳作,甚至情急之下草草写就的文章也备受吹捧。伊登看清了巨大文学市场的暗箱操作,文字不再是纯粹的符号,而是沾染了铜臭与恶俗,成为他人牟利与炫耀的工具。伊登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轰然坍圮,如同影片中沉没海底的帆船,杳无踪迹。
改编电影中的伊登自始至终都是孑然一身。他曾是站在世界外部的旁观者,单枪匹马拼命跻身于远非自己的天地,进入围城并受众人簇拥之时,他依然感到生命的寂寥荒芜,从未有人相伴左右。成长路上,他感受过亲情,得到过爱情,获得过友情,坠过谷底也攀过顶峰,然而当他回望之际,所有过往的情感与经历缥缈得令他无从琢磨。他的心灵丧失了原本的意义,丢弃了存活的意义,生命的尽头有如荒原般充满着幻灭与绝望。这也是贯穿整部电影的主题。雅各布·卢特(Jakob Lothe)认为,文学作品也和电影一样,开头和结尾均极为重要:开头部分能够引起读者/观众的兴趣,而结尾之处则令作者在读者/观众心目中的美学营造效果达到顶峰。[8]63影片最后,满脸沧桑的伊登跌跌撞撞地奔向洒满落日余晖的大海,这颇具悲壮色彩的唯美画面宣告了他肉体的消亡。事实上,精神幻灭后的伊登早已形同走肉行尸,死亡也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
四、结语
作为文学的二次创作,小说的影视改编并非简单将原著生搬硬套、改头换面,而须依据电影意欲凸显的主题对之撷取精华,弃去不宜,套用原著外壳,重构内容意蕴。马切罗对《马丁·伊登》的电影改编无疑是个范例,帧帧显细节,处处埋暗线,时空背景的重置、文明符号的解码、纪实影片的混剪、独具匠心的叙事,这些无一例外地彰显出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张力美学,弥补小说叙事媒介的隐漏。不论叙事形式的改变,抑或内在结构的创新,归根结底是在为改编影片的幻灭主题服务。如果说原著是一部纪实小说,那么电影更像一则醒世寓言,它超越时空与地域,正告世人:即便有钢铁般的意志,人一旦被幻灭侵袭,会在顷刻间变得不堪一击。电影中的马丁·伊登已然幻化为一个象征符号,一个人格缩影,折射出因信念丧失而陷入幻灭泥淖的普罗大众。当人们在为主人公伊登的悲惨遭际扼腕叹息之余,又不禁陷入沉思,在世界各个未知的角落里,还有多少位马丁·伊登悄无声息地重复上演这样一出人生悲剧。这部电影正是通过马切罗出色的改编技巧,将一个意义更为广泛的人物形象再现于世人眼前,带着杰克·伦敦的深邃气息,又缩影着形形色色普通人的际遇,马丁·伊登就是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