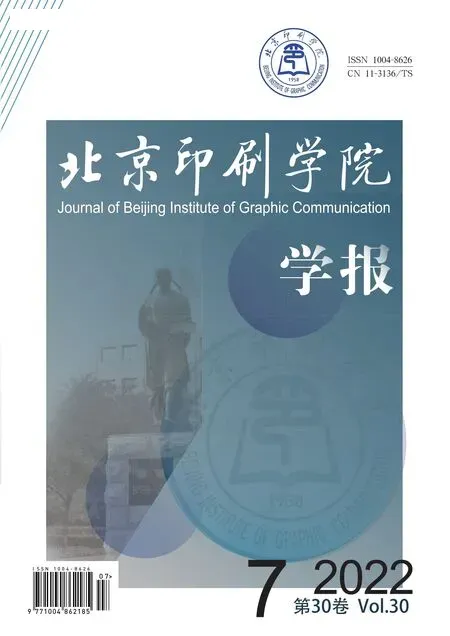论清代王琦《李太白集注》对宋代杨齐贤注释的借鉴与吸收
2022-11-27张佩
张 佩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北京 102600)
王琦,字载韩,号琢崖,緈庵(载庵),晚号胥山老人,浙江钱塘人,大概生活在清康熙、乾隆年间。他在文学史上以注释李白、李贺诗文而著名。 他辑注的《李太白集注》(《李太白全集》)三十六卷和《李长吉歌诗汇解》五卷影响深远。 该书卷末赵信序称赞此书 “一注可以敌千家” 。 王琦在重注李集的过程中,大量借鉴吸收了《分类补注李太白诗》[1]中杨齐贤集注、萧士赟补注,且下苦功做了不少校勘、考辨的工作,虽有不足,却极大提高了杨、萧注的利用率及参考价值,使其得以继续流传下去。 兹特就王琦《李太白集注》对杨齐贤注的借鉴与吸收予以分析。
一
《四库全书》对王琦注本没有严苛的批评,也没有太高的赞誉,仅称其: “……足以资考证。 是固物少见珍之义也。”[2]这是对王琦本价值的严重低估,从其对杨、萧注的吸收上就能看得出来。《李太白全集·跋五则·其三》云:
流传于世者,惟萧氏注本为多。 其本拔古赋八篇列于前为一卷,次以歌诗二十四卷,凡二十五卷而止。 明嘉靖间吴中郭氏取而重刊之,以其注之泛且复也,删节约半,于古风五十九首,增入徐昌谷评语,又取杂文五卷,另为编次附其后,共成三十卷。嗣后有依郭氏增删之本而刊者,为霏玉堂本。 有依旧注原本而刊者,为玉几山人本,为长洲许元佑本。有全去其注且分析其体为五七言古律绝句者,为刘世教本。 刘书虽缺训诂,然校订同异,改正讹舛,殊见苦心。 ……兹本(王本)自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萧本,杂文四卷略依郭本,而以缪本参订其间。 郭本杂文五卷,今依缪本合序文二卷为一卷,别采萧本所逸而缪本有者,得诗九首,及他书所录集外诸作,汇为拾遗一卷,以合三十卷之数。[3]
在这里,王琦对萧本的流传情况作了梳理,可以看出,他是见过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的,否则无法对郭云鹏本、霏玉斋本系统,玉几山人本、许自昌本系统及刘世教本做出准确的评定。 那么,王氏所言 “略依萧本” ,不仅指元版,当包括两大删节本系统,并与归属太白集另一版本系统的缪曰芑本互相参看,进行校勘订误。 故,王琦本所采用的杨、萧注与元版大为不同,或是取自删节本系统,或是自己进行裁汰筛选。 也就是说王琦对杨、萧注的吸收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并非全盘接纳或是轻率否定。 而杨、萧注在王注中也起到各种各样的作用,或是作为接受的对象;或是成为深入探研诗意的基础;或被立为箭靶,成为立论之前的反驳对象;或是为富有争议的诗篇提供重要的观点……以往研究比较粗糙,常将王本对杨、萧注的吸收混合起来讨论。 笔者在这里重点讨论王琦注对杨齐贤注的吸收,且不采用宽泛论述的方式,而是针对注释节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展示王琦注对旧注的吸收成果。
据笔者统计,王琦本选用杨齐贤注共有58 条。与元版相比,其中仅有18 条在位置和字句上没有作任何改动,以训释简单明了的词语为主。 形容词有 “澹荡” “蜂攅” ,动词有 “羽驾” “飙车” “吸景” 。名词最多,普通名词有 “海色” “胡孙藤” “浮人” “青岁” “奕世” “青牛” ;地理方位名词则包括 “河南” “白帝城” “吴京” “荆门” 。 此外,还有着重交代历史沿革及创作背景的,如历阳郡治,散花楼兴建,《赠汪伦》诗的创作背景,《三五七言》的诗体创立。 王注在选用这部分杨注时,全盘接纳,不再另行注释或是附上他人言语。 剩下的40 条,均与元版有出入,王琦或多或少做了一些改动。
二
第一,王氏调整了杨齐贤注的字句、行文顺序,使注释准确清晰。 如注释《古风五十九首·其一》,王本所引杨注与元版及删节本系统各本均不相同,但却参考了各本的修改方法。 删削旁枝末节,保持主干文路清晰明了。 在元版中:
齐贤曰:《诗·大雅》:凡三十六篇。 《诗序》云: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大雅》不作,则斯文衰矣。 平王东迁,《黍离》降于《国风》,终春秋之世,不能复振。 战国迭兴,王道榛塞。 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龙。 风俗薄,人心侥,中正之声,日远日微。 一变而为《离骚》。 刘勰辨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蔚起,其《离骚》哉! 故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词家之前。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滛,《小雅》怨悱而不乱。 若《离骚》,可谓兼之。 屈平之后,司马相如、扬雄激扬其颓波,疏导其下流,使遂闳肆,注乎无穷。 而世降愈下,宪章乖离。 建安诸子夸尚绮靡,擒章绣句,竞为新奇,而雄健之气,由此萎尔。 至于唐,八代极矣。 扫魏、晋之陋,起骚人之废,太白盖以自认矣。 览其著述,笔力翩翩,如行云流水,出乎自然,非思索而得,岂欺我哉?
在王琦本中:
杨齐贤曰:《诗·大雅》:凡三十六篇。 《诗序》云: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大雅》不作,则斯文衰矣。 平王东迁,《黍离》降于《国风》,终春秋之世,不能复振。 战国迭兴,王道榛塞。 干戈相侵,以迄于秦。 中正之声,日远日微。 一变而为《离骚》,轩翥诗人之末,奋飞词家之前。 司马、扬雄激扬其颓波,疏导其下流,使遂闳肆,注乎无穷。 而世降愈下,宪章乖离。 建安诸子夸尚绮靡,擒章绣句,竞为新奇,雄健之气由此萎尔。 至于唐,八代极矣。 扫魏、晋之陋,起骚人之废,太白盖以自任乎? 览其著述,笔力翩翩,如行云流水,出乎自然,非由思索而得,岂欺我哉?
首先,元版中杨氏指明刘勰语,但删节本系统均将 “刘勰” 名删去,王本沿袭了这种精简方式。其次,郭本、霏玉斋本无端加入 “《史记》曰” ,王本则一仍元版之旧。 第三,玉本删去了 “屈平之后,司马相如、扬雄激扬其颓波,……非思索而得,岂欺我哉” 这部分内容,仅止于 “若《离骚》,可谓兼之” 。王本没有用玉本的删减方案,却采纳了玉本调整杨注字句顺序的理念,力求使杨注文从字顺,更加清晰明了。 经过王琦修改后的杨注,将王政兴废,斯文更迭的过程展现得甚为流畅:
(一)王琦删减简化了一些冗繁的词汇
将 “祖龙” 换成 “秦” ,由秦始皇个人转而为有秦一代;删去 “风俗薄,人心侥” ,突出造成 “中正之声,日远日微” 的核心原因—— “斯文衰矣” 。
(二)王琦对冗长引文进行撮引
杨齐贤引用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之话,王琦概括为 “一变而为《离骚》,轩翥诗人之末,奋飞词家之前。” 关于 “风雅寝声” ,杨注在 “刘勰辨云” 之前已经交待清楚了。 《辨骚》中淮南作传所言 “若《离骚》,可谓兼之” ,这仍旧是对前文的重复与加强,结合注文前后语境,删去此处亦毫不影响文意,反倒使行文更加清楚流畅。
(三)王琦调整了杨注的语气
“太白盖以自认矣” ,杨齐贤确认太白以 “扫魏、晋之陋,起骚人之废” 自认,王琦修改为 “太白盖以自任乎?” 将肯定调整为设问,下文 “览其著述,笔力翩翩,如行云流水,出乎自然,非由思索而得,岂欺我哉?” 这样就形成杨注自问自答的格局,只代表他个人的见解。 而 “自认” “自任” 与否,王琦认为还需细细解读,不应草率下结论。 现在,不少学者在评述李白诗文创作宗旨时,喜以《古风五十九首·其一》为证,认定李白有一种变革时弊的自任精神,或是从杨注中得到启发。 但解读原诗,再结合李白实际创作,这种 “扫魏、晋之陋,起骚人之废” 并非其特别设定的任务或是目标,仅是达到的效果之一罢了。 不轻易下结论,对其他注家的言论持保留意见,这是王琦注的风格之一,从其删减简化注文的工作可窥见一斑。
第二,对杨注中地理名物予以进一步考证。 如《沙丘城下寄杜甫》,王琦《李太白集注》卷十三: “杨齐贤曰:‘赵有沙丘宫,在巨鹿。 此沙丘当在鲁。’按在巨鹿者乃沙丘台,赵于其地作宫,故有沙丘宫,非沙丘城也。 《太平寰宇记》:‘莱州掖县有沙丘城,殷纣所筑,始皇崩处。’夫纣所筑,始皇崩处,古今皆指在巨鹿者是,不云在莱州。 乐史所证亦误。 据此诗而约其地,当与汶水相近。” 此诗宋蜀本题下注明 “齐鲁” ,则沙丘城大体位置基本能确定。 比较有争议的是 “沙丘台” 、 “沙丘宫” 与 “沙丘城” 的称谓与所指。
沙丘台由纣王所筑,《三传折诸·左传折诸》卷二十七 “夏卫灵公卒” 条: “《一统志》:‘在平乡东北二十里纣筑沙丘台,卫灵公葬于沙丘宫。 穿冢得石椁,有铭云:不凭其子,灵公夺我里。 子韦曰:‘灵公之为灵也久矣’。” 这是说卫灵公卒,卜葬在沙丘,沙丘宫当因此而造。 “赵于其地做宫” 的说法并不准确,事实是赵武灵王在沙丘之乱中饿死于此。 《史记》卷四十三: “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4]《集解》: “应邵曰:武灵王葬代郡灵丘县。” 《史记正义》卷四十三 “饿死沙丘宫” 句,注云: “《括地志》云:‘赵武灵王墓在蔚州灵丘县东三十里。’应说是也。” 明董说着《七国考》卷四 “沙丘宫” 条: “《史记》:‘主父饿死沙丘宫。’正义曰:‘在邢州平乡县东北二十里。’” 应劭所注武灵王墓葬具体位置得到张守节、董说的认可。 这里牵扯沙丘宫称谓的演变,名字得来是因卫灵公卒葬于此,但灵丘县的名字却因赵武灵王葬于沙丘宫而得。
王琦认为 “乐史所证亦误” ,主要依据是 “古今皆言在巨鹿者是” 。 然而,李贤、彭时等奉敕修撰《明一统志》卷二十五曰: “古迹沙丘城,在掖县界内,世传商纣所筑,即秦始皇崩处。 唐李白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元代于钦《齐乘》卷四: “沙丘城,莱州北。 相传商纣所筑,始皇崩处。 按《史》、《汉》皆云沙丘在巨鹿县,此后人附会。” 《山东通志》卷九: “沙邱城,在县(掖县)东北,相传商王纣所筑。” 沙丘城在莱州的说法也得到支持,王琦对乐史的否定显然草率,但他根据李白诗意推测 “当与汶水相近” ,却非常合理,与《明一统志》对李白所写沙丘城的理解并不冲突。 他对杨齐贤注的纠谬并不完美,但却指明了应当仔细区分的地理名称。
又如《金陵白下亭留别》: “驿亭三杨树,正当白下门。” 齐贤曰: “唐武德九年,更金陵县曰白下县。 白下,吴之故都。” 诸本均置此注于诗句之下,所释词语均为 “白下” ,非白下亭。 王本于题下注释 “白下亭” ,引文也与原注不同,曰: “杨齐贤曰:白下亭,在今建康东门外。” 此注从他处借来,《金陵酒肆留别》: “风吹(一作白门)柳花满(一作酒)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 杨齐贤释 “白门” ,注曰: “白下亭,在今建康东门外。” 此外,李诗还有多处出现 “白下亭” “白门” ,如 “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 (《留别金陵诸公》), “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 (《献从叔当涂宰阳冰》), “春光白门柳,霞色赤城天” (《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因前以有注,故点到为止曰 “金陵有白下门” 。
按: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置金陵县,筑城于白石山下的白下村(在今南京金川门外)。 武德九年(626),更金陵县为白下县。 这时的 “白下” ,不仅指白下县所在的白下村,而且包括白下县地域。贞观七年(633),移白下县于青溪上的白下桥(今白下区大中桥)畔,白石山下的故城遂废。 此时, “白下” 之名系指整个南京地区。 白下亭的位置历史上变化不大,一直在白下桥附近,地处交通要道。南宋《景定建康志》卷十六云: “白下桥,一名上春桥,在城东门外,其侧有白下亭。”[5]此条下《重建桥记》云: “金陵为六朝故都,风土遗迹历历可考。自上元县治东行里许有桥,曰白下。 白下之义,访诸故老,无传焉。 宋元徽间,征北将军张永屯白下。唐武德中迁金陵县于白下村,其地盖在东晋白石垒之下也。 国朝自六飞南驻,以是邦为陪都。 白下一桥当江浙诸郡往来之冲,不惟士夫民牧所必经行而道也。” 至宋,江宁府上元县驿站东西各有一亭,均可称为白下亭。 《江南通志》卷三十: “白下亭,在上元县驿亭也。 唐李白诗‘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宋王安石诗‘门前秋水可扬舲,有意西寻白下亭’,是亭在府西也。 安石诗又有‘东门白下亭,摧甓蔓寒葩’之句,似又在府东,意驿亭饯送东西各有亭耳。” 李白所写之白下亭在府西,在府东者盖为宋新建。
第三,将杨齐贤对诗句的注释摘选出来作为题下注。 《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 “送君登黄山,长啸倚天梯。” 杨齐贤注明李白写此诗的地点及黄山的方位。 王琦注曰: “杨齐贤曰:太白自注:‘时在当涂。’即今之太平也。 黄山在城北,凌歊台在其上。” 他对注文未作任何字面上的改动,只是将其转为题下注。 类似的还有:《五松山送殷淑》《至阳陵登天柱石,詶韩侍御见招隐黄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詶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所注词汇分别为 “五松山” “阳陵山” “黄鹤楼” “五云裘” 。 这些均为杨齐贤阐释具体诗句时所注,且全部在诗题中出现过。
古人诗作的题目通常很讲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王琦这个改动有助于观者更快地掌握重要线索,从而对诗歌的创作背景有所了解。 可称得上是将杨注的功能提升了一个层次。 除此之外,王琦还做出更大范围的调整,实行不同作品间注释互借的方式。 比如《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 “祖席留丹景。” 王琦注: “杨齐贤曰:丹景,日也。” 但此诗句下并无此条注文,笔者初以为是版本问题,经过查找,发现是从他处借来。 前文所考对 “白下” “白下亭” 的注释也是如此。
第四,对杨注进行校勘,指瑕纠谬。 《江夏送友人》: “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 杨齐贤曰: “黄鹤楼,在鄂州。 图经云:费文伟得仙,驾黄鹤憩此。” 王琦将 “费文伟” 改正为 “费文祎” 。
除纠正明显错误,王琦还对杨注的注释方式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见解。 例如《寻雍尊师隐居》: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王琦注: “杨齐贤曰:青牛,花叶上青虫也。 有两角,如蜗牛,故云。 琦按:‘青牛’‘白鹤’,不过用道家事耳,不必作别创解。” 注家多博学,有时会对某些比较 “偏” 的知识不忍弃置,甚至津津乐道。 结合诗歌文本来看,起句 “群峭碧摩天” 视野开阔, “拨云寻古道” 表现出山中云气缭绕,结句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描写时间推移,光线变得更加黯淡, “云气” 变成 “暮气” 。 在这样始终云雾缭绕的环境下, “花暖青牛卧” 与 “松高白鹤眠” 一样,都是大致看到的景象。或者是像王琦所说,仅是以道家事烘托尊师隐居的特殊环境,不存在一个近距离观察花叶上青虫的特写。 此与苏轼所见王安石残句 “黄犬卧花心” 不同, “花心” 很明确定位了 “黄犬” 的位置,可解释为虫子。 “花暖” 是一种移觉,花本无温度,却能在一片盛开景象中,以其灿烂的色泽、纷繁的姿态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此条杨注算不上硬伤,仅是注释方式太过质实,无形中挫磨了原诗空灵飘逸的气质,也缩小了观者的想象空间。 并非杨注如此,这也是注家易犯的毛病。 王琦能及时指出,也可从侧面看出他对他人注释的裁汰标准,对自己作注的严格要求。
第五,对 “首创权” 的认定保持谨慎的态度。《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一》: “西入长安到日边。” 王琦注: “日边,杨、萧二注皆引晋明帝‘不闻人从日边来’之语,以为后人称帝都为日边因此。琦按:《晋书·陆云传》已有‘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之对,似不始于东晋。 盖日为君象,故邦畿之地有‘日边’‘日下之名耳’。”
按,《晋书·天文志》云:
日为太阳之精,主生恩德,人君之象也。 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 故日月行有道之国则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宁。 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日五色无主。 日变色,有军,军破;无军,丧侯王。 其君无德,其臣乱国,则日赤无光。 日失色,所临之国不昌。 日昼昏,行人无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不聊生,不去一年有大水。 日昼昏,乌鸟群鸣,国失政。 日中乌见,主不明,为政乱,国有白衣会,将军出,旌旗举。 日中有黑子、黑气、黑云,乍三乍五,臣废其主。 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6]
开篇即云日为人君之象,随即以日的各种变化比附人事,列出 “人君有瑕” “人君吉昌” “其君无德” “主不明” “臣废其主” 等情况。 这种认识由来已久,《周易》中离卦便体现出这种对应关系,宋鲍云龙撰《天原发微》卷二下: “愚曰:《易》崇阳抑阴之书也。 日为君象,故尊之崇之。 上经三十卦而终于离,离在天为日,则苍生无不仰照。 下经三十四卦而终于既未济,离皆在其中。 民无此则不生活,所以济生民之日用也。”[7]清代陈法撰《易笺》卷二笺释离卦,曰: “日为君象,故以大人言之。 大抵开创之君多天亶之圣,继之者为难觐光扬烈,善继善述则比德重华矣。”[8]这种对应也被后世接受,用来阐明事理,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四十二: “元和七年八月京师地震,上谓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树皆动摇,何祥也?’宰相李绛曰:‘……盖地载万物,日为君象,政有感伤,天地变异……’”[9]《辞源》高度概括为: “封建社会以帝王比日,因以皇帝所在之地为日下。”[10]
再看 “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 之对。 “云间” “日下” ,分别为陆机、荀隐二人的家乡, “士龙” “鸣鹤” 分别是二人的表字,构成了天然的对偶。陆云是松江华亭(今上海)人,松江古称 “云间” 。荀隐是洛阳人,洛阳是西晋都城。 故荀隐自称 “日下荀鸣鹤” 。 云从龙,日照鹤,更有自高身价之意。以 “云间” 对 “日下” ,成为诗家常用的骈语。 清李渔《笠翁对韵》: “名动帝畿,西蜀三苏来日下;壮游京洛,东吴二陆起云间。”[11]
杨齐贤在注里大段引用《晋书·明帝纪》来解释 “日边” 这个词从何而来。 王琦则扩展开来讨论类似词汇的由来问题,且以 “日为君象” 做出阐释。而像《三五七言》,杨齐贤曰: “古无此曲,自太白始。” 王琦不改一字,直接引用,是能肯定李白的首创权。
第六,将杨注中串讲的诗句和部分文献资料删去。 例如《长相思》: “赵瑟初停凤凰柱。” 齐贤曰: “江文通《别赋》曰:‘横玉柱而沾轼。’凤凰柱,刻柱为凤凰形。” 王琦仅吸收 “凤凰柱,刻柱为凤凰形” 一句。 《文选·江淹别赋》: “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 李善注: “琴有柱,以玉为之。”[12]在这里,杨齐贤以江淹诗歌来解释 “柱” ,这是将 “柱” 的范围定位在 “琴柱” ,然后再顺承阐释 “凤凰柱” 。
又如《赠裴十四》: “黄河落天走东海。” 齐贤曰: “黄河,出昆仑山,在吐蕃中,极西为最高,流入中国,势犹从天而落也。 《禹贡》:同为逆河,入于海。” 首先,王琦删去了《禹贡》引文。 所谓 “逆河” ,指黄河入海处的一段河流,以迎受海潮而得名。《尚书·禹贡》: “(禹导河)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孔传: “同合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 蔡沈集传: “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13]宋曾巩《本朝政要策·黄河》: “当禹之行水,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酾为二,至大陆又播为九,然后为逆河,以与海属,非屡散裂而顺导之,莫能为功。”[14]杨注引用《禹贡》,明确何谓 “走东海” ,在这里极有必要。 李白被视为浪漫主义诗人,给人造成的错觉就是,写诗歌所用词汇夸饰成分较多。 实际上李白行走天下,见识广博,对地理名物非常了解,他本人也喜欢在诗歌中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浪漫主义情怀,如《峨眉山月歌》连续运用地名,且仔细观察过月亮的变化[15]。杨注清楚地解释 “黄河” 与 “东海” 的关系,能够从侧面体现李白这一创作特点。
其次,王琦补充了 “在唐吐蕃中,隶大羊同国” 一句。 清胡渭《禹贡锥指》卷十: “自唐以前,未有言昆仑在羌中者,何可深信西域之昆仑?”[16]那么杨注援引《唐书·吐蕃传》来释 “黄河” ,以唐解唐,本无可厚非,但应当注明断代。 因为 “言昆仑在羌中” ,是唐首创,时代特色很鲜明,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唐人对黄河的理解。
王琦这种做法多是效仿删节本系统,虽能精简篇幅,但却忽略了集部注释应当尽可能体现出文学性的特质。
第七,在解释诗意时,以杨注作为驳论对象,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见解与观点。 如《秋浦歌十七首·其十四》: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后人对这首作品的注释与解读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难点在于无法确定审美客体的准确指代,而最终指引后人找到正解的恰是其中洋溢着的阳刚之美。 王琦注曰:
炉火,杨注以为炼丹之火,萧注以为渔人之火,二火俱不能照及天地,其说固非。 胡注谓‘山川藏丹处,每夜必发火光,所在有之。 《舆地纪胜》:宣州有朱砂山,石窍中每发红色,其大如月。 又,赤溪,神龙初,有赤气冲天,诏凿之,溪水尽赤。 第难定其所咏何处。’此解亦未是。 琦考《唐书·地理志》,秋浦固产银、产铜之区,所谓‘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者’正是开矿处,冶铸之火,乃足当之。郎,亦即指冶夫而言,于用力作劳之时,歌声远播,响动寒川,令我闻之不觉愧赧。 盖其所歌之曲,适有与心相感者,故耳‘赧’字当属已而言。 旧注谓‘赧郎’为吴音歌者助语之词,或谓是土语呼其所欢之词,俱属强解。
他认为杨齐贤理解的 “炼丹之火” 与萧士赟认为的 “渔人之火” 都不足以达到照及天地的壮大效果,而胡震亨注引《舆地纪胜》关于朱砂山的记载也很牵强。 杨齐贤理解为炼丹之火,并无任何可靠依据,放在全诗小环境中,无法解释后三句;参看其他十六首作品,也找不到炼丹修炼的痕迹。 萧士赟理解为 “渔人之火” ,首先是考虑到秋浦的自然环境,其次当是认定 “赧郎” 为吴音语助词或是渔人喜唱的赧郎歌,最后参考诗末 “歌曲动寒川” 一句,更是确信李白所写为渔舟唱晚的场景。 胡震亨注将 “炉火” 视为静态,是山川藏丹,朱砂映红的特殊现象,与人类的活动没有关系。 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是:矿藏发出的红光不足以达到炉火蒸腾,紫烟缭乱的强烈效果;诗歌后两句所描写的人类活动与前两句脱节,没有必然联系。 王琦既对三者的不足看得通透,又从中汲取了一些有用信息。 胡注提供了 “矿藏” 这个重要线索,王琦顺此思路考察出秋浦盛产银、铜,那么近水燃炉以冶炼矿藏着实合情合理。 杨注认为 “赧,……犹言愧汝明月之夜,歌曲之声振动寒川也” ,王琦吸收了 “愧” 这层含义,更点名 “惭愧” 的主体是李白,而羞愧的原因竟然是李白听见冶夫用力作劳时的歌声而 “闻之不觉愧赧” 。 大概是觉得这个解释不很妥当,王琦又补充道,是因为歌曲内容与李白当时心境或有相通,而触其情绪。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秋浦,有银有铜’,见《新唐书·地理志》。 ‘赧郎明月夜’与‘歌曲动寒川’为对句。 ‘赧郎’,旧时注家不得其解,其实就是银矿或铜矿的冶炼工人。 在炉火中脸被焮红了,故称之为 “赧郎” ,这是李白独创的词汇。 “明月夜” 的 “明” 字当作动词解,是说红色工人的脸面使 “月夜” 增加了光辉。 工人们一面冶炼,一面唱歌。歌声使附近的贵池水卷起了波澜。”[17]直言诸位注家不得要领,且将诗意串讲为是冶炼工人热火朝天劳动的场面。 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此言采矿冶炼火光直照天地,红焰与紫焰交映。 冶炼工人的脸色被火光映红,而其歌声则震动秋浦山川。”[18]对郭沫若的解释表示认可。 相比较而言,这个解释是最为清晰明确,合情合理的。 这首诗前三句写了所见,最后一句写了所闻。 从 “赧郎明月夜” 一句可以看出,李白离冶炼场地当是中远距离,视角为俯视。 这样他才能够从天地宏大背景中,顺着红星紫烟看到火光源头,再注意到红色炉火照亮冶炼工人的脸庞。 那种人影火光交相辉映热火朝天的场面,配合上冶夫的歌声,使得山川有被点燃与撼动的感觉。 为什么声光效果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最后才写声音? 这是因为月夜背景下,人类大场面活动对视觉更有冲击力。 整首诗中 “歌曲” 这个听觉所感并非重点,最后一句还是复归视觉。 他的构思是顺着视角推移:自然——人——自然,可以说浪漫主义的诗歌意境纯然出之以写实主义笔法。
注家不得要领之处在于:首先,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不够;其次,泥于个别字句的传统解释,对整首诗的意境体会不足;第三,阐释得过于质实生硬。郭沫若称 “赧郎” 是李白独创,清康熙五十九年敕撰《御定韵府拾遗》卷二十二上: “赧郎,李白诗‘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19]将此词的原创权归于李白名下。 但对 “赧郎” 的运用,后人多以其为渔歌,如明杨慎《长江万里图》: “笼筒津鼓惊浮客,欸乃渔歌属赧郎。”[20]明王世贞《江皋曲》: “赧郎轻舴艋,不敢向江皋。” (《弇州四部稿》卷七)[21]又《毗陵月夜张子歌》: “贪听赧郎歌宛转,任教风露湿衣裳。”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22]清黄之隽撰《香屑集》卷十六: “自扫一床间,双扉常自关。 赧郎明月夜,别宅宠妖娴。” 注曰: “自扫,贾岛《宿慈恩寺郁公房》;双扉,姚合《药堂》;赧郎,李白《秋浦歌》;别宅,元稹《台中鞫狱忆开元观旧事》。”[23]黄之隽没有用渔歌之意,转而用其字面,意为 “羞涩的郎君” 。 名清人对 “赧郎” 的理解与杨齐贤、萧士赟注差不多,王琦在这种整体趋向的语言环境下对旧注进行考证纠谬,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