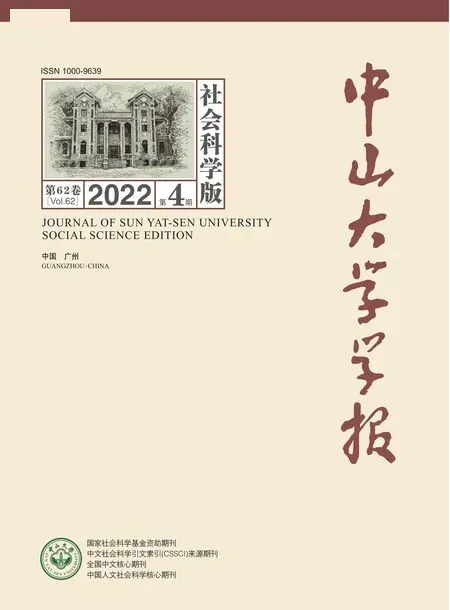朱熹“祝告先圣”及其诠释学意蕴*
2022-11-27张清江
张清江
引言
儒家传统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学界讨论和争议较多的话题,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直聚讼不已。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包含着多种面向,在历史和经典意涵的解释上都存在差异极大的表现;二是“宗教”概念及宗教学学科本身的边界仍不太清晰,这两者都可能导致学者在讨论时陷入自说自话。事实上,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去判定儒家传统是否属于意义并不明确的“宗教”,而在于利用宗教学的学科视角和方法能给理解儒家传统带来什么,或者说,它能否丰富和拓展现有对于儒家传统的理解,进而推进儒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将“儒家宗教问题”作为一个研究论域,而非将“儒家是否是宗教”作为论题,可能更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因而,选择以宗教学视角切入儒学研究,并非意味着要首先承认儒家是一种宗教,也不是要去证明儒家是否是宗教,而是因为相信,儒家传统中包含着与神圣相关联的向度,其独特性只有通过宗教学的特殊视角才能更好地揭示,并由此拓展和深化对儒家传统的整体性认知。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宗教学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宗教是人类历史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借由对这一现象的独特呈现,可以丰富和加深对人类文化的整体理解。而宗教现象的独特性,源于信仰者“遭遇”其所信仰的神圣对象时所产生的经验,它体现在活生生的人类行为、经验和情感中。因而,宗教学研究首先关注的并非不同宗教的教义差别,而是宗教信徒在面对神圣时所获得的经验①对这一看法较为清晰的阐述,可参黎志添:《宗教研究与诠释学——宗教学建立的思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年。。对朱熹“祝告先圣”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视角的启发下,试图将儒者的礼仪实践纳入讨论范围,分析儒者在具体礼仪行为的展演中所获得的意识经验,从而将礼仪、信仰与生活的交织互动,在具体时空下展现出来。因而,本文对朱熹“祝告先圣”的分析,尝试采用宗教学和诠释学的视角,说明这一行为实践可以为今天理解传统儒家的精神世界带来何种启示。
一、仪式行为及经验
“祝”是祭祀礼仪中的一个环节,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特定言辞(“祝文”)通达神明,“祝告先圣”即是在祭祀孔子的仪式上宣读祝文,表达祭祀者的愿望和诉求,从广义上说属于“祈祷”。因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本质上是一种仪式行为。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最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仪式向来是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尤其是对原始族群仪式的研究,已经产生非常多的重要成果,也形成了解读和分析的不同“范式”。比如,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强调仪式的社会功能属性,关心的是仪式如何推动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运转,经由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的阐发和精彩运用,这一研究范式业已成为学界看待和分析中国社会礼仪传统的基本视角。相比之下,格尔茨等人倡导的文化人类学更关心“体现于象征模式中的意义符号”,强调要通过文化象征体系中意义系统的“深描”,揭示文化象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①对人类学家仪式研究的不同范式,学界已有许多评介和反思。对于仪式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路梳理,参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第五章“象征与仪式的文化理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32 页以下。。这些视角虽有差别,但在强调仪式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方面则是一致的。研究仪式的著名学者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认为,这些视角的最大缺点,是从结构主义的静态立场将仪式视为一个整体和系统,过度强调仪式及其象征系统对行为者的单向度影响,把仪式活动看作对文化法则的接受和展演,结果忽略了仪式实践者的实践过程及其能动性。按贝尔及其称赞的“实践—表演”学派对仪式研究的看法,理解仪式的关键,是把握其“仪式化”(ritualization)的过程,关注特定时空里的身体运动和个人意识,如何界定和感受文化象征的意义和价值,如何与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相结合,仪式的核心是变化,它不单是价值观、等级和权威的体现,同时也是对这些观念的构建和修订②Catherine Bell,Ritual: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89,尤其是第81—83 页。实践—表演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克多·特纳,他强调仪式参与者的积极而非消极作用,重视分析参与者对文化象征的个人理解、解释和修订,从而把文化看作是不确定、戏剧性或过程性的,而非封闭性和已完成的。。
这里当然无意对人类学的仪式研究进行系统评述,但上述理论视角为讨论人类社会的仪式实践提供了基本框架,也构成了本文必须面对的学术史脉络,因而需要稍加说明。首先,文化人类学所关注的象征符号和意义系统,是仪式分析的基本对象,因为,“每一类仪式都可以看作象征符号的布局,一种‘乐谱’,而象征符号则是它的音符”③[英]维克多·特纳著,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象征之林:恩布登人仪式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7页。,这些象征符号承载着文化所特有的“思想、态度、判断、渴望或信仰”④[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97页。,在一种可感知形式中表达着信仰的理解。因而,研究和理解仪式行为,不能脱离特定文化的象征符号及其意义表征,因为这构成了仪式空间意义建构的基本前提,也构成了理解和诠释仪式经验的“客观性”依据。其次,贝尔等人的批评告诉我们,对于仪式空间中象征意义的理解,行动者并非单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可以实施积极的建构和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对象征符号的意义阐释,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传统赋予符号的一般性意涵,更要关注行动者对这些符号意义的特别理解,因为正是行动者对符号的这种信念,与仪式中的器物、动作、氛围一起,构建起具有神圣意义的价值空间。就此而言,一方面仪式要借由行动者对象征符号的特定信念,建立起一种具有开放性和转化性的意义世界,另一方面,这一仪式实践又会使行动者在其中获得一种特殊的意义经验,使其可以更好地重新进入世俗生活,这正是许多仪式具有“过渡性”的根本原因,面对神圣对象的宗教仪式尤其如此①[法]范热内普著,张举文译:《过渡礼仪》,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亦参[美]伊利亚德著,杨儒宾译:《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第27—30页。。行动者与仪式这个看似具有循环之嫌的双向互动,构成了仪式实践最具根本性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仪式的最关键之处。换言之,仪式研究的核心,是要诠释一个意义世界,既包括仪式如何借由特定时空和行动者的信念建构起这样一个意义世界,也包括行动者在其中所能获得的意义经验以及这种经验对行动者生活的影响。
对仪式的这一理解视角,是本文讨论朱熹“祝告先圣”的基本出发点。作为一种仪式,祭孔礼仪与人类社会的其他仪式一样,包含了由一系列象征符号组成的行为过程:祭祀中器物的象征意涵,行为举止的价值意义,对祭祀对象的信仰方式以及对祭祀本身的理解,等等。对于朱熹来说,这一行动的进行,以其对仪式的整体理解和精神信念为前提,并由此在行动的展开过程中获得特定的经验和影响,因而,围绕着祭孔礼仪所展开的,是朱熹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交织,行为、信念和意义均构成了理解这双重世界的基本维度,经验则是贯穿其中的核心范畴。就此而言,对这一礼仪实践的分析,需要放在思想与行动的交织互动中加以呈现,揭示出礼仪空间的意义建构和实践者在其中所获得的意义经验,以呈现“文本”所具有的诠释学意义和精神价值。
相较之下,传统礼学研究对儒家礼仪的关注,更多偏重礼经、礼制、礼义等向度,将讨论限定于思想文化层面,着重讨论儒者的礼学思想、制度安排及其塑造社会秩序的功能作用②仅就朱熹礼学的研究而言,近期的部分研究成果包括:叶纯芳、乔秀岩:《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殷慧:《礼理双彰:朱熹礼学思想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有关《朱子家礼》的相关研究文献更多,不再一一列举。近年来,随着经学研究的复兴,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角度对礼学文本和礼制的讨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沿此进路较为系统的思考,见吴飞:《当前的礼学研究与未来预期》,《中国哲学年鉴》2015年卷。对中国礼学研究的回顾,可参杨英:《改革开放四十年礼学与礼制研究》,《孔学堂》2018 年第3 期;杨华:《中国礼学研究概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对于儒者具体生活中的礼仪实践及其意义,并无太多关注。尤其从功能主义视角对礼仪社会作用的分析,虽然对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非常重要,但也可能会化约行为实践中蕴含的本真意义,因为它属于在研究对象“后”(对其产生结果)的研究,而儒者在礼仪实践中获得的意识经验,才真正与个体生活的深层精神密切相关。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既有礼学和社会学等研究视角的意义,本文也并非要在这些框架中展开讨论,而是希望在既往讨论的基础上,从另一视角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对传统社会礼仪的认知,尤其试图深入发掘儒家礼仪落实于儒者生活实践中所产生的意义体验,从人与“神圣”关联的结构性分析中展现这类经验的精神性意涵,以此加深对人类深层精神经验的理解和体认。在这个意义上,朱熹“祝告先圣”的礼仪实践,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本”范例,透过对这一“文本”的理解和诠释,可以很好地揭示儒者的生命深度与神圣经验。因而重要的是,如何进入对这一“文本”的诠释。
二、面对“文本”
“文本”是解释学的对象,它通常指作者留下的文字材料,供读者从文字和句法表达中解读其意义。将朱熹“祝告先圣”这一行为实践当作文本,是就其扩展意义而言。不过,这种扩展并非无据可依,解释学大师保罗·利科即阐发了“有意义行为”作为诠释“文本”的正当性与可能性③[法]保罗·利科著,孔明安等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语言、行为、解释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6—126、159—183页。。从诠释学的角度来说,今天的我们(诠释者)将朱熹“祝告先圣”看作“文本”,即意味着承认朱熹在这一礼仪实践中的态度及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经典”,并仍能够为我们理解人类生命本身提供重要启发。因而,将行为或事件视为一个需要理解和诠释的“文本”,目的是通过揭示其结构要素,凸显其诠释学意义。
“文本”的主体内容,是一种类型化的行为,即朱熹生活中对先圣孔子的祭祀实践。作为这一实践的重要组成,“祝告”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仪式中与祭祀对象直接交流的环节。保留下来的“先圣祝文”为理解朱熹这一行为提供了基本依据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6,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032—4051页。,这些祝文告诉我们,朱熹对孔子的祭祀,并非单纯出于传统礼俗的要求,而是首先出于真实信仰,因为在一些礼俗并无要求的情境下,如开除学生和刊刻经书等场合,朱熹也要从信仰的角度主动进行祭告,诚如陈荣捷所说,“朱子与孔子之关系,不止在道统之传,而亦在情感之厚。其祭礼禀告先圣,非徒公事例行或树立传统,而实自少对孔子早已向往,发生感情上之关系。故一生功业大事,必告先圣”②[美]陈荣捷:《朱子之宗教实践》,《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第184页。。陈先生从信仰和情感认同的角度看待朱熹的祭孔行为,确实独具慧眼,只是对于这种情感内核及其经验结构,需要通过更细致的“文本”诠释加以呈现。要理解这个出于信仰而外显于行动的礼仪实践及其意义,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研究所处的“双重诠释”的境地:朱熹对于先圣及祝告先圣的理解和诠释是第一重,我们对这种诠释的再诠释是第二重。因而,在这种境况中必须首先保持自觉,不仅需要历史地呈现儒家传统对于祭祀等文化意涵的累积观点,更重要的是朱熹本人对这些要素的理解和认知。我们面对的是朱熹眼中的先圣和仪式,而非近现代学者阐发出来的孔子和儒家形象。具体到“祝告先圣”这一礼仪行为,至少需要厘清朱熹的三个基础性信念:祭祀、祈祷与先圣。
首先是祭祀。祭祀的基本对象,是传统意义上的鬼神,但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精神演变,鬼神是否真实存在,成为儒家存而不论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儒者对祭祀之礼的重要性,多从人道和政教的角度来解释,将之作为“报本反始”之情的外在表达,并作为培养君子尊君、孝亲等品格的基本教化途径③《礼记·祭义》:“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参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329、1353—1354页。。换言之,“神道设教”是这种理解的基本表达,祭祀是圣人“教令”和“制作”的结果④孔颖达这样解释:“人之死,其神与形体分散各别,圣人以生存之时神形和合,今虽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圣人设教兴致之,令其如此也。”参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47,第1325页。。《论语》“祭如在”等说法,为这一理解提供了来自经典的重要支撑。不过,朱熹明确反对这种理解,尤其对“设教”之说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不诚”的表现⑤见朱熹答郑可学、欧阳谦之等人的书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79、2959—2960页。。朱熹当然不会否认祭祀礼仪中包含的人道情感和教化意义,但他一定要强调,祭祀之“诚”,来自对“鬼神之实理”的真切认知,是对“幽明一致”的深刻洞见。祭祀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目的虚设的礼仪规范,更非“心知其不然而姑为是言以设教”⑥朱熹:《答郑子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6,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79页。。在理气论架构下,鬼神的实在性与祭祀时鬼神的“临在”,获得了来自超越天理的本体保证。朱熹对此有着细密解释,在此无法详细展开⑦参赵金刚:《朱子思想中的鬼神与祭祀》,《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6期;亦参张清江:《祭祀的“理”与“教”:从朱熹晚年两封论学书信谈起》,《安徽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这里只需指出的是,朱熹真诚地相信,祭祀时可以引得鬼神之气“流动充满”,实现与祭祀对象的“共在”和“感通”。
与此相关联的,是祭祀中的祈祷。在一般意义上,祷的意涵是“告事求福”(《说文解字》),是信仰者对神明庇佑的祈求。在相信鬼神存在且有超自然能力的前提下,这种行为的正当性自不待言;但如果鬼神存在与否尚不可知,向鬼神的祈祷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依据,更不用说儒家会激烈反对谄媚鬼神以求“一己之福”。在这种背景下,祭祀时要不要祈祷就成了问题①明显的证据是,《礼记》中同时保留了两种不同的说法。《礼器》说,“君子曰,祭祀不祈”,《郊特牲》则云“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虽然后世儒者努力通过不同情境去弥合两种说法之间的冲突,但其仍可很好地反映出当时儒家对这一行为的纠结。。因此《论语·述而》所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路的做法受到汉唐儒者的一致批评。朱熹从理气论角度确立了鬼神的实在性,对祈祷合法性的疑问自然不复存在,“祷是正礼”成为他的基本主张②朱熹:《答陈安卿》,《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7,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19页。,但对于祈祷的目的和方式,他仍遵循儒家传统的一贯态度,将之与个人的世俗福祉相分离。在朱熹看来,子路的做法不应受到批评,因为这一行为是子路表达自身“不能自已之情”的“至诚”之举,安顿这种“慊然不足”的情感正是祈祷的根本意义③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04页。。在这里,朱熹强调的是祈祷对个体信仰者面对生命不同状态时的精神价值,延续宋儒“悔过迁善”的界定,祈祷成为生命转化的真实行动,与个体的切己情境密切关联。这一信念对于理解朱熹面对孔子时的“祝告”行为至关重要,因为祝告正是仪式中的祈祷环节,是真实面对祭祀对象并借以回顾和反思自身生命状态的当下时刻。
作为祭祀和祈祷的对象,“先圣”也是理解朱熹这一行为实践的基础信念,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信念,正是它使这一行为区别于其他祭祀行为。在朱熹确立的“圣圣相承”的道统谱系中,孔子处于非常特殊的位置。在上古圣人中,尧舜“德位兼备”,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典范,相比之下,孔子却“有德无位”,虽然《孟子》有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的评判,但在汉唐时人的观念中,这不过是基于假设性推论的溢美之词④参见赵岐之说:“以孔子但为圣,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当尧舜之处,贤之远矣。”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7页。,并非历史真实。然而对朱熹来说,《孟子》这一断语是确切无疑的历史判断,原因在于,孔子“收拾累代圣人之典章、礼乐、制度、义理”⑤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36,第959页。,“推其道以垂教万世”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6页。,功业远非尧舜所及。更重要的是,对于孔子以后的儒者来说,上古圣人“内圣外王合二为一”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世界延续“道”的传承,就要接续孔子开创的“道学”事业,用力于道德生命的提升和转化。就此而言,孔子不仅是“往圣”典章制度的继承者,更是“来学”的开创者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第14—15页。,是后世儒者必须效法的神圣“原型”⑧这里的“原型”概念,取自宗教史家伊利亚德。按他的说法,古人只有不断重复宇宙创生神话的范例,世俗生活才能“圣化”并获得意义和力量。这个被模仿的原初行为,即是“原型”(archetype)。参[美]伊利亚德著,杨儒宾译:《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第1—39、87—88页。。在朱熹的诠释下,孔子的出现作为一个事件,已不仅仅具有历史性,更具备了“原初性”的意义:规范和引导后世儒者行为的,不是“继天立极”的“上古圣神”,而是“继往圣、开来学”的先圣孔子。这一意义上的“先圣”,始终处于追求成圣的理学生活的核心,因为成圣之路就是要通过效法先圣,不断去体认“圣人之心”和“圣人之道”。“道—圣—经”是“三而一”的,并无序列上的高低,这与心学对圣人和经典的理解有很大不同。在这种信念下,与先圣的“对话”成为具有神圣意涵的精神性事件。朱熹的“祝告先圣”,必须放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去理解。
祭祀礼仪的空间,既不是与祭祀者无关的纯粹外在环境,也不是单纯由祭祀者主观想象出来的虚幻世界,而是一个通过祭祀者身体、信念与空间整体氛围的互动和交织,共同建构起来的“神圣空间”。因而,对于祭祀、祈祷和先圣的这些基本信念,共同支撑和建构着“文本”开显出来的意义空间,也是理解朱熹从中所获礼仪经验的基本前提。在这些信念的支配下,“祝告先圣”成为朱熹重要的生命经验,因为它是与朱熹最“敬畏”的圣人孔子直接“遭遇”的时刻。在祭祀的神圣时空中,祭祀者的身体经验向整个情境开放,通过斋戒所达致的洁净身体“体气”与“诚敬之心”,去感知与自身有关联的鬼神之气,就能像朱熹所相信的那样“致得鬼神来格”①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3,第39页。,实现与鬼神之灵的“感通”,祭祀空间由此成为祭祀者与祭祀对象融摄交感的真实场域。那么,对朱熹来说,这一场域的“感通”会带来怎样的意义经验?
三、礼仪、神圣与生活
如前所述,对“先圣”的理解构成了朱熹“祝告先圣”礼仪经验最重要的基础信念,因为先圣具有不同于其他祭祀对象的独特地位。简单来说,先圣不仅仅是历史人物,更是儒家神圣价值“道”的象征,它规范和引导着后世儒者的“在世生存模式”,与这样一个神圣对象的遭遇和感通,在意向结构和经验感受上与祭祀祖先或其他历史先贤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先来简要说明朱熹“祝告先圣”的意义经验及其对生活的影响。
在祭祀礼仪的展演过程中,“祝告”是核心环节,在这之前是请神、降神、迎神的一系列步骤,“祝告”则是神灵临在后的交流与祈求,基本内容即宣读事先写好的“祝文”。因而,这种意义经验的获得,首先是从书写“祝文”开始的。写作祝文并非随意的事情,虽然这种应用文体在长久历史演变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和格式。对朱熹来说,祭祀先圣具有特定处境,祝文写作要依据当下境况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祈求,绝非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这在朱熹留下的“先圣祝文”中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与同时代很多儒者的同类祝文相比较而言。书写的过程,本质上需要在对于先圣之神圣品格的信仰和“直面先圣”的“在场感”中,把自己要表达的内容序列化、书面化。在这一“书写”过程中,朱熹需要重新思索如何将自己呈现在先圣面前,如何将自身处境和状态呈现给自己所敬畏并追求达致的“神圣原型”。这个反思、排序与组合的书写过程,实际上是从身处其中的平面生活状态抽身出来,从更高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过去,从生命目标的向度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过程首先包含着对自家生命的反省、观照和审视,而由于“圣人可学而至”的信念,这一审视也同时包含着追求成圣的目标定向和意义确证。因此,对真正的祝文写作来说,书写是具有深刻精神性意涵的行为。也正因如此,相比同时代其他儒者所写的类似文字,朱熹“先圣祝文”的最大特质,是充满着对自身生命状态和道德境况的剖析和“告白”,以及充满强烈负疚和焦虑意识的言辞②例如《漳州谒先圣文》有“熹总发闻道,白首无成”“永念平生,怛然内疚”等说法,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6,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45页。。这表明朱熹在先圣面前真诚敞开了自己的生命,这是面对一个高于自己生命的理想典范对象的自然反应,这种敞开会自然走向对自身生命不足的反思与超越。
仪式中的“祝告”环节,是这一生命提升转化活动的直接时机与实践场域。如前所述,“祝告”发生在神灵降临之后,是与祭祀对象的直接遭遇与交流,向之“告白”或表达自身的诉求。这里需要特别留意的是,“祝文”的写作者虽然是朱熹,但仪式中的宣读者“祝官”并非主祭者本人。在这一环节的仪式安排中,作为祝文作者和主祭者的朱熹,是站在先圣神位前“聆听”祝官读出自己所写的祝文。这一聆听与日常语言交流中的聆听不同,因为这种情境下的说者不过是朱熹自己想法的代言人,因此朱熹的“聆听”并不带有对说者主观意义进行诠释的要求,他事先已经清楚并正确知道要读出的话语及其意义。在朱熹对于祭祀感格的信念中,“先圣”作为“道之象征”的“他者”,在仪式中以“神之灵气”的形式降临,与祭祀者实现“一气”的共在与感通。因而,主祭者“听”而不是“读”这一安排的意义在于,保证主祭者能够全身心进入到与“先圣之灵”的感通之中。在祭祀的神圣氛围中,在先圣之灵的“在场感”中,借由声音和对声音的感受,朱熹内心对自我不足的认知与负疚感,会获得一种真实体认,并在气类相感的遭遇中获得改变自身的真实力量。表达在祝文中对“先圣”之神圣性与完美性的向往、敬畏,对自身道德境况的谦卑与对生命不足的懊悔,都彰显出朱熹在面对神圣对象时的切身感受和精神经验。
这种感通经验是一种“对话的生命”,在结构上包含两个向度:一是信仰上的生存关联所带来的对先圣之神圣品格的确认,由此回溯自我所产生的负疚和焦虑感受,以及对于自我走向“创造性转换”所持的开放态度①“创造性转换”是杜维明先生发掘儒家“为己之学”所蕴含伦理宗教意义时使用的说法。参见[美]杜维明著,曹幼华、单丁译:《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二是在真实的“相遇”和对话中获得对自身生命的新认识,并在神圣的“在场”中产生真实的转化经验②有基督教研究学者将信徒与上帝之间的对话分解为“离”与“合”两个阶段,这与朱熹祭祀孔子的精神经验在形式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但由于先圣与上帝在本质属性上的不同,两者在信仰经验上存在根本差异。参温伟耀:《生命的转化与超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305—311页。。因而,在朱熹那里,“祝告”仪式中的遭遇先圣,是一个精神反省和超越的真实过程,这个行为具有宗教性意涵,是因为“先圣”代表着儒家神圣价值的超越向度,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生存意义上的“创造性转换”。这些价值规定着儒者整个生活的“基本模式”,而非只是影响某一部分。对朱熹来说,与先圣“感通”带有神圣临在的体验,这种体验的外向性使其能够超越本己的“自我中心性”,在遭遇和面对的体验中感受生命的不同向度。不同于独自透过反省而获得的自我认识,这种外向性的经验,首先是与“他者”感通所带来的包含实质内容的期望,它指向对自身整体生命品格的提升,并借由对先圣的敬畏情感而带来真实的精神转化经验。因而,对朱熹来说,这里包含着朝向一个“超越”向度的精神运动,先圣作为“道”的象征,成为“神圣”介入其生活的基本方式。
这种仪式空间中的“感通”虽然短暂,但其通过人心唤起的超越性的情感经验,必定会落实于生活实践中,对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对朱熹来说,生活的基本样式在于,要追随先圣的道路,通过修身工夫实践不断纯化道德,尽心知性知天,最终“参赞天地之化育”。这种修身信念来自天道的超越性召唤,它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是生存论上的必然行为。在这一“道学”事业的实践中,朱熹有过迷茫和困惑,也有对于相关信念和经典不同于其他同道的见解,在克服这些认同危机以实现价值定向方面,与先圣相遇的真切经验,无疑会产生根本影响。例如,绍熙元年(1190)朱熹刻印“四经”,专门为文以告先圣,留下了《刊四经成告先圣文》。文中将自己对“四经”文本的独特编次和相对于汉唐经学传统的独特理解,专门向先圣做了解释,比如要将《尚书》“序文”删去,恢复古经原貌,原因是他认为汉儒“穿凿”和“伪托”带来了对经典的混乱理解③朱熹:《刊四经成告先圣文》《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46、3888—3889页。。这种修订要改变的绝非篇目上的混乱,而是汉儒对“六经”的整个解释方式。对朱熹来说,这种做法当然是维护经典神圣性的行动表达,但这一信念的落实却必须获得来自神圣的超越性肯定,才能在终极意义上安顿内心。这是他在刻印这一版本的“四经”时一定要祭告先圣的重要原因,以求得到先圣的指引和肯认。这并非仅仅出于“郑重”的考虑,也正可说明与先圣相遇的经验对朱熹生活的真实影响。类似的影响方式,我们在朱熹对于道统、工夫等关乎道学事业根本问题的处理上也可以找到诸多证据。
由此可见,礼仪经验的获得,与朱熹对于先圣及儒学的价值信念密切相关,这种经验又会强化信念的真实性,进而对生活产生根本影响。在朱熹这里,与先圣的遭遇,是与儒家神圣价值的真正遭遇,其中蕴含着关于意义和真理的观念,也塑造着儒者在世的生命态度与价值意向。仪式中的遭遇先圣,不仅出于纪念和尊重,也不只为了功能性的“神道设教”,而是有着转化生命的精神性意涵,礼仪与信念的相互交织和促进,构成了这一遭遇经验中的真切内容,“神圣”在其中以特别的方式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因而,信仰、礼仪与生活的复杂关联,在朱熹祭祀孔子的礼仪实践中得到了很好呈现,对这一生活经验与其中所含神圣因素的阐释和反思,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儒者生活的精神性意涵及其展开方式。相反,如果忽略这种与神圣相关的价值面向,将其单纯化约为伦理道德感受,则会窄化儒者生命的深度和丰富面向,无益于对儒学传统深层精神价值的发掘。
结语:“文本”价值
对朱熹来说,祭祀孔子是具有生存论意义的重要事件,与生命具有内在关联性,他也在仪式中倾注了更多对自家生命状态的关注。朱熹相信,祭祀是与祭祀对象的真实“感通”,祈祷是安顿自身情感并“悔过迁善”的精神活动,先圣则是道学事业的神圣“原型”。“祝告先圣”是真实遭遇“先圣之灵”的当下时刻,在此时刻,面对先圣这样的完美人格,朱熹会深刻体认到自身生命的缺失与不足,这从他祝文中对自己生命境况的认识即可看出,而在面对神圣引发的向往感、谦卑感、懊悔感中,朱熹也会真实地开启自身生命的转化和超越之途。朱熹“先圣祝文”中充满敬畏、谦卑和懊悔的语词,正是这种精神活动的外化表达,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因而,对朱熹来说,先圣作为“道”的象征,成为“神圣”介入生活的基本方式。
对朱熹“祝告先圣”这一行动的理解和诠释,关涉着思想信念落实在生活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其根本指向,则要揭示朱熹基于特定信念在仪式的神圣空间中获得的意义经验。如本文开头所说,儒家是否为“宗教”是争议颇大的问题,但儒学传统中包含着神圣与超越的面向,并在历史与社会生活中对儒者产生了真实影响,是确凿无疑的。从朱熹的个案可以看出,对儒者生活实践中所蕴含的神圣经验的阐发,包含着重要的文化意蕴和思想深度,必须放在儒家传统和文明史脉络中加以理解,而缺少了宗教学视域的观照,这一向度的丰富内涵会大打折扣。对于当代儒学研究来说,面对古典世界不仅是面对思想和概念,更要面对古典的生活世界,从根本上说,思想的形成首先来源于思想家的生活经验,一个人所处的“生活形式”,构成了其思考与言说的“深层语法”。就此而言,古人生活实践所获得的精神经验值得更加重视,它蕴含着人类精神的深刻意义,可以为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祝告先圣”这个“文本”,具备了诠释学上的普遍意义和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