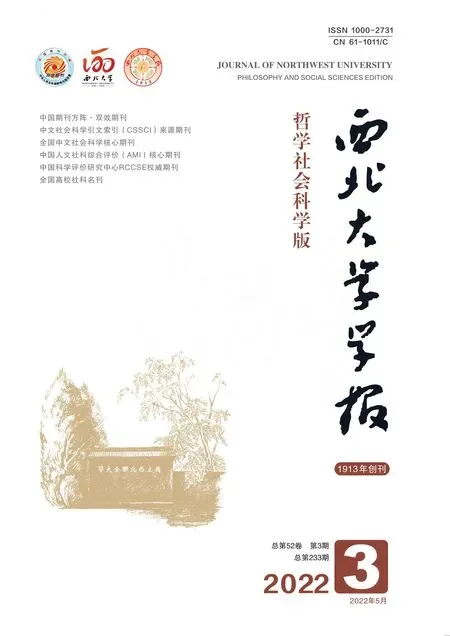“审美”研究方法论:在经验-先验论与审美历史主义之间
2022-11-27刘旭光
刘旭光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审美”?这个问题是否能给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回答?
这关系到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根本难题:我们的经验世界丰富多彩,且具有各种差异,我们的观念则是从这些经验中概括提取而出的,但经验世界一直在变化,而观念一旦被提取出来,便具有了一种相对确定的形态和内涵,其中的难题在于:当经验世界变化之后,那些从经验世界中概括而来的观念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有,那就意味着观念有一种超越经验的一般性;如果没有,那就意味着新的经验应该用新的观念才能够解释,那就要不断地进行观念更新。
对于这个难题,人文学科做出了两种反应。一种态度认为在一切经验现象后都有一种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可以用某种方式进行还原,还原到一个可完全确信的不可怀疑的事实或命题。比如说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当笛卡尔试图对世界进行认识的时候,他对认知进行了还原,还原到一个对他而言不可怀疑的事实——“我在思考”。这种思维方式叫作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这种还原主义要么还原出一个不可怀疑的本质,要么还原出一个不可怀疑的起点,这个本质或者起点在还原论者看来是普遍的,并且认为一个理论如果把握住了经验事实背后这种规律的不可怀疑的确定性和普遍性,那么这个理论便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形成了本质主义。第二种态度叫做历史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认为经验世界丰富复杂,以至于无法被一个普遍的确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观念所概括。这种态度认为事物的存在有其时间性,会不断在历史中变化,而与经验相关的观念也必然在跟着变化,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导出一个唯一普遍的观念,那么所有的观念应该是并置的。如此就形成了历史多元主义。
还原——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冲突,在对“审美”这个人文现象的研究中,尤其强烈:极端的历史主义放弃了对审美是什么,美是什么的追问与确信,放弃了定义,以反本质主义的姿态成为历史意识过于强烈的虚无主义或者是多元论者;极端的还原论者必然成为一个本质主义者,坚信美和审美有其普遍本质,成为一元论者,最终会成为一种“话语霸权”式的独断论。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是历史主义的多元论者,但还原论者并不甘心。二者在审美领域各有其长短,其功用需要具体分析,但关键之处或许在于,如何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在这两种方法上取长补短,达到理论更高的有效性?
一、审美中的经验-先验论:海边荒野中的康德
审美研究中的还原主义,体现为把审美经验还原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先验主体条件或者主体的认知能力上,以这种认知能力为审美经验的前提。这种方法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康德美学,从近二百年的美学史的发展来看,这一方法有普遍性。
审美活动是一个感性的具体的经验活动,通过对审美活动的反思而获得的诸种美学理论,总是具有以下两种经验性质:一是对那些被称之为“审美”的人类行为的普遍特征的概括与描述,以特征来回答什么是审美,这是一种应用性经验主义的态度,是以经验效果和经验到的特征为着眼点的,比如18世纪以“非功利性愉悦”这一特征来定义审美,或者温克尔曼以“单纯与静穆”两种心理感受来概括希腊艺术,再如荷加斯的“美在蛇形线”这一命题,以及博克说美的就是柔弱、娇小、艳丽的,这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观念。这种经验主义在美学研究中饱受质疑,因为通过这种经验总结而得出的命题,有教条化的嫌疑,教条化意味着具体的审美经验比这些命题所涵盖的要丰富得多!问题是审美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审美经验,它的任何结论都应当建立在具体经验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可以通过反思康德与黑格尔的美学的来源而得到证明。
康德的主要美学思想实际上来自于他的这样两种经验:
“花,自由的素描,无意图地互相缠绕、名为卷叶饰的线条,它们没有任何含义,不依赖于任何确定的概念,但却令人喜欢。”[1]42
“谁会愿意把那些不成形的、乱七八糟堆积在一起的山峦和它们那些冰峰,或是那阴森汹涌的大海等等称之为崇高的呢?但人感到在他自己的评判中被提高了,如果他这时在对它们的观赏中不考虑它们的形式而委身于想象力,并委身于一种哪怕处于完全没有确定的目的而与它们的联结中、只是扩展着那个想象力的理性,却又发现想象力的全部威力都还不适合于理性的理念的话。”[1]95
以上两段话描述的应当是他的日常经验:每天清晨他走出自己的宅第走向哥尼斯堡的海边,他首先看到的是建筑墙面上的卷叶饰,而后是一路之上不断出现在路边的诸种花朵,当他最终走到海边,近看海边的荒野,远看堆积在一起的山峦和它们那些冰峰,远望那阴森汹涌的大海……。他在前者中,分析出无概念而令人愉悦的;在后者中分析出与想象力和理性的自由游戏相关联的内心的情调,并且意识到崇高只在判断者心中。在他的经验和他的理论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通过对日常审美经验的反思,追问被经验对象的一般特征,比如说在对花的欣赏中,确定其中的非概念性,而后,反思非概念性的直观和对象存在的非概念性会引发出什么样的愉悦?——建立在惠爱基础上的自由愉悦(1)这个结论的深入讨论,见刘旭光:《作为“惠爱”的审美》,载《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2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愉悦?——诸表象力的自由游戏,或者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与知性的合规律性的和谐(2)对自由游戏这一命题的深入阐释,见刘旭光:《自由游戏与自由愉悦:审美自律性的一种方案》,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在他的经验和他的理论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通过对经验的反思,探寻经验的普遍性的可能,然后将这一可能归给主体的先天的经验能力,让这一经验能力成为经验,也就是经验的先验前提。我们可以把康德的这一作法,称之为经验-先验论。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的每一个审美相关观念的提出,都是按这个原则提出的,比如崇高、审美理念、美是德性的象征、天才、艺术的特征等等。从具体的审美经验出发,通过对经验的反思与演绎而获得美学的一般性命题,这是康德的根本方法。这或许也是审美研究的基本方法。
这种方法的根基在于康德对知识的认识,他认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从经验中发源的。”[2]1按这个原则,对审美的认识也当然是从经验开始,然后反思这种经验的发源。但经验不具有普遍性,鉴赏判断要成为先天综合判断,除了从经验开始外,必然有其先天认识条件作为其先验前提,也就是鉴赏判断需要有康德所说的“纯粹的知识”,即纯粹鉴赏判断,这才是康德意欲探讨的。那么经验意味着什么?康德在第一版《纯粹理性批判》导言中说:“经验毫无疑问是我们的知性在加工感官感觉的原始素材所得到的最初的产品。……经验提供最初的教诲,但同样使我们的知性受限。……正因此它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真正的普遍性,而对知识的这种方式如此渴望的理性,则更多地是被经验所刺激的,而不是被经验所满足的。”[2]4在确立了经验这一起点之后,康德转向强调“理性”力量,而他的先验论也是“建构了理性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即理性概念是先天给定的,它超越于经验之上,并以先天的范畴规定着经验的意义。”[3]47
按这个思路,康德对于审美,对于鉴赏判断的研究,形态上是经验主义的,因为他总是从描述具体经验开始,无论是美还是崇高,他都描述了对象给予我们的经验;但在理论结论上,是先验论的,他要给出对自然美和自然崇高的欣赏,以及艺术鉴赏这些行为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他并不是像博克一样寻找经验特征的普遍性,而是寻求获得这种经验的先天能力上的普遍性,并将这种普遍性作为审美的普遍性,或者美感经验之普遍性的根据。因而,他对审美的研究,是基于经验论的先验研究,或者说是通过经验而激起的先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按康德本人的说明,是把对审美的经验性的心理学,提升到先验哲学的高度[1]106。
以经验心理学为起点,通过对具体经验还原式的反思,最终以先验哲学为终点,以这种方法展开的审美研究,尊重了审美的经验性质,也在先验层面上体现了对普遍性的追求,因此是一种可为借鉴的研究方法。但麻烦的是,后世的美学者们在接受康德美学时,主要着眼于他的先验性的理论结论,而没有关注康德的出发点,因此,几乎没有人说康德美学是经验美学,而是直接把它定位于先验认识论美学,并且把他所探寻出的经验的先验基础定位给人类学,视为人的先天能力所具有的普遍性。这种接受康德的方式弱化了康德理论的经验性质,以及研究审美经验的意义,造成的结果是,康德研究美学的方式是经验反思式的,而不是观念演绎式的,但人们更愿意接受后者。观念演绎式的研究对于美学而言,往往无助于对具体审美经验的理解,而成为纯粹的审美知识论,且也与具体审美经验的获得与审美敏感的获得无关。这使得人们可以在不关涉具体审美经验的情况下抽象地讨论关于美与审美的所谓本质问题。
关于这种审美研究的经验-先验论模式,当代哲学家德勒兹有所体认,他认为康德哲学总体上是先验经验论(Empirisme transcendantal),也就是说,他承认了康德研究方法的经验性质。但他和康德不同,他认为:“我总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来自怀特海所规定的经验主义的两个特征:其一,抽象的东西不能解释什么,其本身就需要被解释;其二,目的不在于重新发现什么外在的或普遍的东西,而是探究任何新的东西可以据此产生的条件。”[4]基于这样一种经验观,德勒兹探究新经验得以产生的条件,德勒兹承认经验是被激发的,是被构成的[5],他强调经验的生成与激发,这是他与康德不同的地方:康德欲使知识摆脱变换不息的经验,寻求其中普遍的东西,落实到审美研究中,他要探寻审美愉悦是不是具有普遍性,鉴赏判断是不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但德勒兹认为日常诸多的经验并不能被某种固定的法则所统一,并认为康德的先验论是对经验的直接超越[3]48,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知识的稳定性”还抛弃了思想的自由与情感的丰富。康德确实忽视了审美中情感的丰富与审美上思想的自由,但不能因此否定康德的经验-先验论,毕竟,德勒兹关心的是经验的生成问题,是先验的经验能力如何成为具有无限差异的诸种经验的可能,他在强调生成与差异;而康德关注的是经验的普遍性问题,是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有相通的审美经验,是探寻审美经验的普遍性。
审美研究要探寻什么?如果是强调人类审美经验的生成过程与差异性,那么德勒兹所说的先验经验论是可资借鉴的;如果是为了探寻经验的普遍性与相通性,探寻人类的审美经验上的交流何以可能,那么应当是经验-先验论。审美研究,应当是经验-先验论,因为审美经验的个体差异是自明的,无需强调,而美学研究的初衷,是审美是不是可以走出趣味无争辩的困境,是研究美感是不是可以成为人类的共通感问题——寻求普遍性,在个人化的感性愉悦的领地反思出可理解的,可交流的普遍感受和普遍原则,将人类的审美行为上升到先天综合判断,这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根本趣旨,因此,经验-先验论作为寻求审美经验之普遍性的方法,应当是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尽管它不是唯一方法。
经验-先验论的经典案例除了康德对自然美与自然之崇高的经典分析之外,还可以在一些艺术创作者的美学研究中看到,比如英国18世纪美学家贺加斯。贺加斯在进行人体素描与速写时,发现人体身上的每个部分几乎都是由这种弯曲的线条所构成的。如人的小腿和大腿,其肌肉纤维就如同蛇形线 般缠绕、附着在骨骼上,由此产生了一股股互相交织、连绵不断的波浪线条。当我们用肉眼观察人体时,我们只能看到人的皮肤。在这层脂肪的覆盖之下,人体的肌肉线条就少了一份尖锐突兀,多了一份柔和自然。这是个体经验,根据这个经验,贺加斯得出一个结论,画面中人的形体如果“无变化的轮廓线和结构,没有任何波状线,这使得这个形体像是木制的”[6]117,而生动的美的人体,一定是由蛇形线构成的,进而,他提出美在蛇形线。这是一个简明的案例,说明个体经验如何上升到审美先验原则。
经验-先验论的当下意义在于,在审美领域,不断地有新的感性经验被纳入审美中来,这些经验为什么能够成为审美的,这些经验为什么具有普遍性,这都是需要美学进行应答的问题。比如当代人看3D电影的经验,欣赏沉浸式数字媒体艺术的经验,看《忒修斯之船》之类的小说的经验,听重金属音乐的经验,这些新的经验发生了,这些经验是审美的吗?这些经验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愉悦?有何价值?这不是心理学问题,而是审美经验现象学问题,也是经验-先验论可以施展自己的统摄力与反思能力的地方。
经验-先验论作为方法,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理论模式:通过对具体的经验的反思、统摄与综合,探寻个别经验背后的一般性,或者说把丰富的现实经验还原到一个先验原则上,它表现为主观合目的性的反思判断。这听起来是主观主义的,是从“我的经验”上升到主体间的普遍性,但个体经验不正是审美的现实形态吗?当我们能够反思出个体经验中的包含着的一般性时,这个一般性才能保证不是外在于经验的,一切从外部颁布给经验的一般性,都不能尊重经验的差异性,而审美总是从富于差异性的经验开始的,因为审美判断是单称判断:“这一朵花”美,这是审美判断;“花儿”很美,这不是审美,是倾向性表达。由此,我们可以把从个体经验中寻求普遍性的思路,概括为经验-先验论模式。这个模式从美学史角度来看,具有方法上的普遍性。
从鲍姆嘉通的《美学》一书来看,他总通过审查艺术作品的实例和我们对它的反应,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就是他如此细致地叙述莱辛,以及他在美学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论述出现在评论莪相和莎士比亚的文章中的原因——以经验开始,以定义结束。从康德之后的美学史的演进来看,黑格尔的美学实际上是关于审美经验的辩证演绎,黑格尔对每一种具体艺术的研究,都遵循着经验与理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虽然他不导向一种认识论的先验机制,但导向一种观念论的辩证统一,仍然遵循着经验-先验论在经验中寻求一般性的思路。之后,叔本华对于诸种美的形态的研究,尼采对瓦格纳的批评,卡西尔对于艺术美的概括以及“审美从反思差异开始”的观点,都包含着经验-先验论的向度。狄尔泰关于“体验结晶”的思想,海德格尔关于艺术真理性的思考,都体现着从个体的感性经验到经验的一般性的追问。而杜夫海纳和英加登的现象学美学,可以看作经验-先验论在美学领域中的深化。
首先要有真切的经验,而后反思这个经验,还原经验的原因与经验的一般性,这应当是审美研究的基本的方法——经验-先验论。
二、审美历史主义的方法
审美研究最困难的地方在于,人们的审美经验太过丰富了,审美经验是历史性的,民族、文化和时尚都会影响人们的具体审美经验,这种差异性被现代文化体制强化了——在博物馆中,当我们一天之内按时代和地域观看了所展出的艺术作品之后,必然会产生视觉经验的多元感受;在艺术史著作中,艺术作品的历史演进必然会带来观念与功能的多元认识。这意味着“审美”有其历史性。不仅仅是观念上的历史性,本质上是行为上的历史性。简单地说,中世纪人的审美行为和现代人的审美行为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行为和西方人的审美行为是不一样的。这个观念或许需要一部“审美史”来进行证明,但前提是,承认审美本身有其历史性,也就是承认“审美历史主义”。
审美历史主义是20世纪的文艺理论家奥尔巴赫的观点,见其194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维柯与审美历史主义》(Vico and aesthetic historism)。他说:“普遍的审美历史主义是人类思维的珍贵的收获……我们审美视野的扩展是建立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上历史视角扩展的结果,比如承认每一个文明和时代都有其完善的可能性。不同的人,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以及他们的生活形式,应该被理解成不同的个体条件的产物,是要通过他们自身的发展来判断而不是通过绝对的美丑标准。”(3)Auerbach, Erich. 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of Erich Auerbach. Ed. James I. Porter. Trans.Jane O. New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P.36.这是一种审美相对主义的观点,其相对性源于历史的多样性,而历史的多样性源于个体存在的差异性,这就把个人主义和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建立在二者之上的历史主义方法:“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个人的作品是他的存在的产物,一个曾经在这里和现在的存在;因此,一个人所发现的关于他的生活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用来解释这个作品——这一点不能仅仅因为由于没有足够的内部经验所造成的天真和学者对它的过度运用,就忽视这一点。”(4)Auerbach, Erich. 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of Erich Auerbach. Ed. James I. Porter. Trans. Jane O. New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P.6.
奥尔巴赫没有明确的界定“审美历史主义”这个词,但我们仍然能够分析出这样一种思路:关注每一个时代的人的具体经验,承认这种经验的独立性,不进行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上升或概括,也就是承认审美在历史长河中所呈现出的差异性,具体作品具体分析。用他的话说:“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及之前所产生的法则,现在已经过时了。没有人会因为哥特式教堂或中国寺庙不符合这些法则而认为它们是丑陋的。谁也不会认为《罗兰之歌》野蛮粗糙就不值得和伏尔泰精致完美的《昂利亚德》相提并论……我们以乐于去理解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欣赏不同时代的音乐、诗和艺术。”(5)Auerbach,“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of Erich Auerbach.”P.6.这就是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会创造出不同的美。这可以看作是审美历史主义的核心观念,那么它在美学研究的体现,就是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这些不同的美,发现其中特殊的形式,特殊的理念,与可能的“完美”。
审美历史主义承认审美的丰富与复杂,以至于无法被一个普遍的确定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观念所概括。这种态度认为审美行为和审美观念有其时间性,会不断在历史中变化,而与经验相关的观念也必然在跟着变化,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导出一个唯一普遍的观念,那么所有的观念应该是并置的。如此就形成了审美领域中的历史多元主义。
奥氏的这个思想是欧洲历史主义传统的总结,是通过研究维柯与赫尔德确立起来的。维柯宣称他所研究的是“人类思想史、人类习俗史、又是人类事迹史”[7]154,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是维柯之所以在思想史上有崇高地位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历史意识思想背后,是一种人文主义情怀:“在沉沉的黑夜之中,闪烁着永恒的,确定的真理之光:文明社会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它的原则就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心灵变化中被发现,……既然是人创造了它,人是能够了解它的。”[7]134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人能够理解它,对历史的研究,最终就转化为对人的创造的研究。这种历史意识最终在维柯这里上升为这样一个人文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凡是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它们在某种时代以某种方式发生出来的过程。”[7]378这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应从事物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来研究,这或许是“历史主义”这个词的核心内涵。这个内涵很快被赫尔德转化为一种多元论。
在讨论莎士比亚时赫尔德就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之间的差异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在希腊,非如在北方。因此,在北方,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希腊的样子。情节的简单,行为的朴素,恒久的、具有高尚品质的措辞,音乐,舞台,以及地点和时间的一致,——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如此自然地作为希腊悲剧的起源,而非任何艺术或者魔力——悲剧只有在所有这些特征的升华中才能产生。”(6)Herder, “Shakespeare,” trans. Joyce P. Crick in German Aesthetic and Literary Criticism: Winckelmann, Lessing, Hamann, Herder, Schiller, Goethe. Ed. H. B. Nisbet. Cambridge UP, 1985,P. 162-3.他以此来反对把原古希腊戏剧的三一律强加给北方戏剧,他认为莎士比亚的“世界没有提供作为单一整体的历史、传统、家庭、政治和宗教条件,当然这种单一整体也就不会呈现在他的作品中了”。相反,他将创造出他的“戏剧,这戏剧来自于(他的世界的)自己的历史,它的时代精神,习俗,观点,语言,民族态度,传统和消遣方式。”(7)Herder, “Shakespeare,”P. 167.
莎士比亚有莎士比亚的世界,索福克勒斯有索福克勒斯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他所在的世界的结果,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相对性。根据这种历史相对主义,赫尔德反对从先验的角度研究审美:“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塑造我们的鉴赏,学会了解自然的规律和类比,学会不要把美的艺术或科学用于夸夸其谈的游戏或偶像崇拜,而应怀着喜悦的、严肃的心情把它们用于培养[教化]人类,不应有任何先验的鉴赏,因为先验的原则只存在于人类绝对无意识的超感官基础中。”[8]511这是针对康德的自由游戏与自由愉悦的,赫尔德反对美学的先验方法,并反对任何将审美经验还原为一种先验形式而不是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对于真理的认识的理论。在他看来,先验原则无法被认识到,对于具体的实践也是没有意义的。
显然,赫尔德更相信对人类经验的历史描述,而反对个体经验的先验分析。二者的差异下文再述,问题是,历史主义者是不是停留在历史的多样性上,而不去寻求其中的普遍性?首先要回答的是,历史之中有普遍性吗?
历史主义研究本身是反对本质主义的,也是反对笛卡尔与康德式的还原论的。这体现在审美研究中,就是反对给美一个本质性的定义,然后拿这个定义把审美转化为以这个定义为目的的合目的性判断;还原论体现在,把审美还原为一种先天能力或者先验原则,以这种能力或原则作为无限丰富的审美活动的前提。这两种方法对于历史主义来说都是需要反对的,审美活动的历史性决定它不可能有唯一本质,或许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有其本质,但不同时代的审美是有差异的。但历史主义仍然在寻求某种相对的普遍性,比如同一个时代或者同一个民族在审美上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因而,历史主义最终会确立起一种有限的多元论,也就是承认审美有多种形态,美有多重内涵。但是历史主义者仍然会对历史进行逻辑演绎,去寻求历史本身的内在统一性。比如说赫尔德,他并不是简单的历史相对主义者,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之间又有统一性:“莎士比亚与索福克勒斯如同兄弟,在他们看起来如此不同的地方,就其内在而言,他们却是完全相像的。他整个戏剧的想象是通过这种真实性,真理和历史创造性获得的。”(8)Herder, “Shakespeare,” P.172.正是因为索福克勒斯的艺术和莎士比亚的艺术都遵循着同样的基本原则——真实与创造,所以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可以欣赏它们。“因此对于每一种艺术、每一门科学和一般意义上的好的品位而言,都有一种美的理想,它将在(不同的)民族、时代、学科和作品中被发现——尽管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容易被发现。”[8]395这似乎是说,最好的艺术总是揭示了有关它的世界的真理,以及在人类对于这些真理的情感反应中,存在着深层次的共性。在每个时代,伟大的艺术家都想要传达他们世界的真理以及他们对这种真理的情感,而每个时代的观众都想要理解这些无论是关乎他们自己的世界还是其他世界的表达。这样就把历史主义造成的相对性,演绎为历史内在的普遍性。
这个做法在黑格尔的美学研究中尤其明显,他一方面是一位历史主义者,强调“不管一件艺术作品是从哪个时代取材,它总带有一些特点,使它不同于另一个民族和另一个世纪的”[9]336。但同时又强调,“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当然是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所能共赏的,但是要其他民族和时代能彻底了解这种作品,也还要借助于渊博的地理、历史乃至于哲学的注疏、知识和判断。”[9]337历史主义的真正目的,似乎是借助历史知识与历史还原,发现伟大艺术的共性,并欣赏这种共性,因此黑格尔说了这样一个短语——“艺术作品所必有的反历史主义”![9]353
黑格尔的出发点是历史主义的,但最后的终点是反历史主义。通过这样一种辩证统一,历史主义既可以实现多元论之间的对话与理解,也可以在历史经验之中进行历史演绎,探寻其中普遍而永恒的部分,但问题是,要让真正的历史主义者相信历史中包含着普遍而永恒的东西,这实际上是矛盾的,因此,历史主义往往是人文学者处理观念的多样性的基本方法与态度,但这并不影响成熟的理性在其中寻求普遍的东西,只不过,这种普遍的东西并不被上升为“本质”,从而成为排它的理由,历史主义者最终都是多元的综合论者。
这意味着,当我们在面对美学史上关于审美的多种观念,面对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审美精神时,放弃本质主义的一元论,而采取一种综合的方法,是现实的。因而,审美历史主义给审美研究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尽可能广泛地探寻历史经验,寻求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在审美活动上的特征与特性,另一个是把这些尽可能多的特征与特性进行综合,并且在综合中探寻普遍性。前者是美学史、审美意识史的任务,而后者则是审美理论的任务。应当说,审美历史主义和审美的反历史主义之间的辩证统一,是当下美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
三、在经验-先验论与审美历史主义之间……
这两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经验-先验论必须把经验上升到先验层面上才能找到普遍性,实际上这很难,经常会陷入主观主义的经验论,甚至会求助于心理学或者科学的认知学说,比如脑科学与神经认知学说;审美历史主义必须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反历史主义,才能避免彻底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经验-先验论和审美历史主义是两条道路,对审美的研究应当走哪条路?两条道路的差异,实际上是两种思维的差异:
审美历史主义希望通过还原“审美”曾经是什么样子,以及它的发展历史,为理解今天的审美提供一个比较的维度,甚至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事物是如何成为今天这样的。我们今天的审美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个状态的?审美历史主义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种阐释性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研究“审美”这种在人类历史中不断流变的人类行为,具有切适性,正如维柯所说,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它们在某种时代以某种方式发生出来的过程,用历史主义的方式研究审美,把审美视为历史流传物,既能保证从多元论的角度对审美持开放性的态度,从而在诸种不同的审美理论中形成对话与理解的可能。
经验-先验论可以为理解现实经验提供前提,它本质上是分析性的,它相信事必有据,当下发生的必有其根据。经验-先验论使得我们必须直面现实经验,通过对现实经验的分析,创造与现实相匹配的理论,并且在鲜活的经验领域中分析出某种普遍性,并以这种普遍性作为理解经验的出发点。
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可能被极端化的局限性。
审美历史主义会导向关于审美的虚无主义。历史主义实际上放弃了对普遍性与本质性追问,从而陷入“坏无限”,比如当代美学家艾柯的名著《美的历史》。在这本著作中,艾柯采取了一种激进的历史相对主义态度,他说:“本书可能招来相对主义之讥,仿佛我们认为美随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而转移。我们正是此意。……美的观念千汇万状,在这些变化之上,可能有某种施诸百世万族而皆准的规则。本书并不期望不计代价地搜寻这些规则。我们不作此意图,而只期凸显差异。至于是否在差异底下寻找万流归宗的统一,请读者自便。”[10]12
在这种观念里有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在书中他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和商业、时尚的产品审美价值是同等的,这就取消了艺术与商品之间的差异,他对历史的多样性采取一种综观而不统摄的态度,只陈列历史事实,不进行理论化与体系化:拒绝从一个理论立场来看待历史的多样性,拒绝把美的历史梳理成一个逻辑链条与逻辑结构——他实际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历史拒绝被逻辑统一。
由于拒绝进行统一,因此艾柯不可能拿出一个美的普遍定义,因此他的经典表达是“某某某之美”,但问题在于,如果不敢定义美,凭什么说某某东西是美的?美在这本书中是个模糊的能指,但是我们统观这本书所举的诸种例子,可以帮他概括出一个他不愿意概括的“美”——艾柯在审美领域中显然是个经验主义者,他所说的某某之美,比如人物、怪物、废墟、消费,以及诸种时代性的艺术的主题,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人感到好看或感到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作为时代的审美对象的特征,被视为美的。这种激进的历史相对主义,最后呈现为一种泛化了的经验主义,他把所有他认为有趣的,带给人们愉悦的,或者体现着特殊愉悦的,都纳入“美”。
艾柯的美学观呈现出了极端的审美历史主义方法,他所给出的实际上不是美学史或者美学理论,而是审美文化的历史陈列,他实际上取消了“美”或者说泛化了审美,只承认某种愉悦的发生;他也取消了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只承认时间排序。理论研究不应当只是开设文物陈列馆,艾柯当然可以秉持审美历史主义,并且拒绝任何反历史主义,但他连多元的综合都不肯。这种极端的历史主义最终会取消审美的相对独立性,不承认艺术中有普遍而永恒的东西。因此,审美历史主义的无限多样性必须被限制,即便不是走向反历史主义,也必须保持在一个有限多元论的限度内。
经验-先验论方法的问题在于,它无需历史感和历史背景作为个案分析的前提,当个体的鲜活经验作为个案被进行先验分析时,这里有两个问题:个体经验是不是普遍经验?先验分析的结果是不是有客观性或者说普遍性?
经验-先验论最大的问题是对经验的分析很难达到先验的层面,从而落为个体感受的描述,散文家们对于艺术的观感多有此病,而批评家们则善于发现其中经验的一般性,但不能上升到先验层面。先验分析需要以认识论层面的审美认知分析为前提,需要康德美学和现象学美学的修养。经验的先验分析作为一种审美研究的方法,意味着需要对审美的先验认识论原则与先天机制有深入的研究,然后,把一种具体的经验置入其中,反思这种经验是不是具有审美性,或者从审美的先验认识论原则来说,它在什么意义上是审美的,什么意义上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审美的经验-先验论研究,实际上是康德美学在经验领域的延伸,至少是像康德一样,从先验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审美经验。后来的现象学美学,特别是盖格尔和杜夫海纳的审美研究,对审美经验进行了先验反思,可以看作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延伸。经验-先验论研究实际上是认识论思维在审美研究中的具体化,而不是个体审美感受的描述。在描述作品给人的审美感受这一点上,艺术评论家们,特别是文人出身的艺术评论家,如狄德罗、波德莱尔、本雅明、格林伯格等人,都有杰出的成就,并且被当代的批评家所继承,但经验的先验分析不是批评与观感表达,而是认识论研究。对于认识论研究而言,个体经验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经验从认知的角度来说是怎么获得的,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认知机制——比如直观、体验、想象、反思、感悟、判断等等能力及其相互关系——得以获得的?对于这个问题,就对具体的审美经验的认知机制的分析而言,不同的审美观会有不同的回答,但对于同类经验会有普遍性,经验的普遍性保证着这种研究之结论的普遍性。
阐释性的审美历史主义和分析性的经验-先验论之间,是不是相互反对的?是的,这正是赫尔德批判康德,康德指责鲍姆嘉通,黑格尔批判康德的根本原因,也是经验论反对理念论的原因。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审美历史主义所导出的多元论与先验论的纯粹认知机制之间的冲突,是审美在历史长河中的“生成性”与先验层面上的“确定性”二者间的冲突。历史意识曾经在19世纪后半期差点摧毁了先验哲学,并且干掉了“先天”这个词,历史意识相信一切现实的与观念性的因素都是在时间之流变中生成的。“普遍性”和“确定性”这样的词在历史意识中是需要被打破的,彻底的历史意识必然会放弃“普遍性”,但这样一来“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就会因为没有共同的支点而得不出肯定的回答。现在我们既要寻求普遍性,又要尊重时间性,那就需要在二者间寻求平衡。
现代解释学为这个矛盾的解决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本书希望以这种方式增强那种在我们这个倏忽即逝的时代受到被忽视的威胁的见解。变化着的东西远比一成不变的东西更能迫使人们注意它们。这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条普遍准则。因此,从历史演变经验出发的观点始终具有着成为歪曲东西的危险,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稳定事物的隐蔽性。我认为,我们生活在我们历史意识的一种经常的过度兴奋之中。”[11]导言20承认在历史的流变中有隐蔽的稳定事物——就是这个原则,构成了加达默尔,或者说现代解释学的一套方案,在这套方案里,承认“审美”这样的人类行为有其生成性,是在历史中经历着时代性的变化的,但另一方面,这个生成有其方向,同时,这个生成之中有一种隐蔽的稳定性——虽然有诸多差异,但总是能够被归入“审美”这个概念之下。
根据现代解释学的这套方案,可以作这样一个演绎:对审美的研究应当在审美历史主义和反历史主义之间进行辩证统一,寻求历史的生成性之中的某种统一性。同时,在经验-先验论和审美历史主义之间进行统一,寻求当下经验和历史经验之间的某种统一性。
“审美”这种人类行为的构成与机制,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不断生成演变的,但无论怎么变,我们都还承认它们是“审美”,这本身说明,这个行为之中有某种隐蔽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究竟是预设一个概念出来,然后看这个概念怎么在历史中逐步深化完善,还是通过对历史演进的整体进行反思与统摄而获得?前者是黑格尔的方法,他在处理艺术的历史演进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艺术表现的普遍性并不是由外因决定的,而是由它本身按照它的概念来决定的,因此正是这个概念才自发展或自分化为一个整体中的各种特殊的艺术表现方式。”[12]3这个观念实际上在说:有一个在先的艺术的概念,而各个历史时期艺术类的不同形式,都是这个概念自分化的结果。如果把这句话中的“艺术”,改为“审美”,似乎也可以成为一种解决“审美”的内在统一性的一种方案,这个方案或许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反历史主义”。在这个方案里,总有一个概念左右着我们对某个时代的人类鉴赏活动是不是“审美”的判断,而经验又是无限丰富的,这个方案也需要用一个观念来统摄经验的丰富性,从而实现对对象的整体性认识。黑格尔的具体作法是先确立起“真理性内容”作为审美的对象,真理性内容是有历史性的,而“真理性内容”作为一个理念却是普遍的,这就完成了历史主义和理念论的统一:理念论保证了命题的普遍性,而历史主义保证了对一切艺术经验的开放性。在黑格尔那里,“一切艺术经验所包含的真理内容都以一种出色的方式被承认,并同时被一种历史意识去传导。美学由此就成为一种在艺术之镜里反映出来的世界观的历史,即真理的历史。这样,正如我们所表述的,在艺术经验本身中为真理的认识进行辩护这一任务就在原则上得到了承认”[11]125-126。
但这个方案仍然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因为这样做会把历史变成对一个概念的证明,或者变成对一个概念之内涵的逻辑生成的时间性说明,这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因此,可行的是第二条路,对历史演进的整体进行反思与统摄,从我们当下的“审美观”回顾与反思“审美”的历程,并且为未来的审美经验留下将其纳入的可能。那么怎么判断一种行为是不是“审美”?这就需要回到经验-先验论,从认识论角度先提炼这个行为的认知范式,看这个范式如何在历史的长河里被具体化,被深化,被补充,被突破,或者被置入新的因素。承认审美的先验机制的在先性,并以这个先验机制作为判断某种行为是不是审美的出发点,进而在历史演进中,根据新的经验对审美的机制在先验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
第二条道路实际上是要求用经验-先验论为审美历史主义奠基,也就是说,把审美历史主义所要处理的每一种感性经验,先进行先验论意义上的还原,寻求其可以被纳入“审美”的先验根据,这个先验根据保证着这种经验可以算作是审美经验,并保证着这种经验所包含的普遍性,然后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审美的多样性进行演绎。这种方法论的选择是基于“审美”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它是一个历史现象,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审美观,有不同形态的审美活动;它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认知行为,这个行为具有先天基础,有其经验中形成的一般性;它是一个构成性的复合体,人类的许多认知能力介入其中,并在不同的审美观中体现出某种倾向性;它既像是感觉,又像是判断。这些特殊性使得任何一个审美经验都是特殊的,在研究审美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审美活动的这些特殊性,但仍然要探寻其中的普遍性。这意味着必须要进行一个方法论与视角上的综合,这个综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审美历史主义和经验-先验论之间交融。
以经验-先验论为审美历史主义奠基,并形成二者间的综合,这种方法论选择还有一个原因:历史主义总是期待用过去来解释当下,这必然包含着某种保守性,它只能用旧经验来解释新经验,因此历史主义者是开放的,却无法及时的切入当下;这一点在审美研究中需要警惕,因为审美领域,是一个新经验不断发生的领地,这个领地之内有这样一种倾向:以摆脱历史传统、以求新求奇为乐。这或许是另一种反历史主义,审美领域之中所产生的变化,总是以反对之前的历史状态为出发点的,这个倾向使得用历史传统来解释当下经验会受到抵触,这是历史主义的尴尬之处。经验-先验论则可以直接面对新经验,对新经验进行先验分析,因而,经验-先验论总能保持一种理论的前沿性和当下性,它欢迎一切新经验的发生,并且不惮于在新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新理论,但它的尴尬在于,必须要能够意识到什么是“新的”,而新旧判断当然需要把历史经验当作比较的背景。审美研究既要面对新经验,并对新经验做出积极的理论反应,又要尊重历史传统,并且充分利用历史所提供的多种审美模式,从而对当下正在发生着的审美,给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选择性的推动新经验的发展,以期把积淀在历史中的普遍性提炼出来,又能够吸纳特殊事实。
“审美”的历程体现着人类精神的集体业绩,它必须把开放包容与继承、理解结合起来,研究“审美”的目的既是一种自我理解,也是一种自我否定。在自我理解中,需要寻求普遍性和统一性,而在自我否定中,又需要放弃已有的普遍性而肯定新事物。审美让我们沉浸在由历史传统构成的文化的世界里,也让我们陶醉于刹那间涌出的陌生的宇宙。必须在我们自身存在的连续性中肯定体验的非连续性和瞬间性。因此对于审美,必须有历史主义的统摄,和经验-先验论的分析,二者的结合,应当是审美研究的合理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在导向普遍性,审美历史主义从对具体的历史经验的统摄中寻求普遍性,而经验-先验论则是从具体的审美经验中寻求普遍性,被统摄的历史经验越多,被反思的现实经验越多,人类的审美精神所达到的领域就越广大,越深远,人类感觉的丰富与敏锐,人类情感的丰沛与深邃,以及人类精神的雄伟与宏阔,就越可以得到体现。在审美历史主义与经验-先验论的结合中,再来审视康德的这段话:
每个人也都期待和要求着每个人对普遍传达加以考虑, 仿佛是来自一个由人类自己所颁定的原始规约一样; 所以一开始当然只是魅力, 在社会中具有着重要性并结合着很大的兴趣, 如用来纹身的颜色(如加勒比人的橙黄色颜料和易洛魁人的朱红色颜料), 或是花卉、 贝壳, 颜色美丽的羽毛,随着时间的进展,还有那些根本不带有什么快乐即享受的愉悦的美丽形式(如在独木舟、 衣服等等上): 直到最后, 那达到最高点的文明进程从中几乎产生出了文雅化的爱好的主要作品, 而各种感觉只有当它们能普遍传达时才被看作有价值的; 于是, 在这里每个人在这种对象上所感到的愉快尽管只是微不足道的和单独看来并没有显著的兴趣的, 但关于这愉快的普遍可传达的理念却几乎是无限地扩大着它的价值[1]139-140。
这段话中所说的在单一而微不足道的愉悦经验中,无限地扩大这愉悦的普遍可传达的理念,让人类的审美愉悦成为由历史的长河汇聚成的海洋,成为由每一个个体的独特体验所凝聚成的交响乐,这种汇聚与凝结,才是美学史研究和审美理论研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