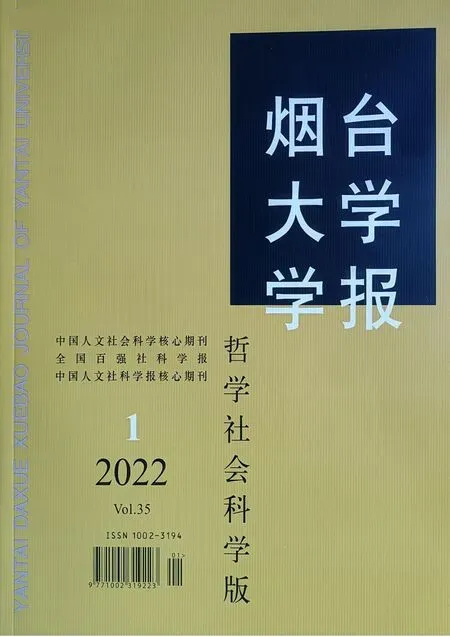光宣诗坛情感论的复古与新变
2022-11-26孙银霞
孙银霞
(烟台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光宣诗坛是中国诗歌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其诗派林立,理论丰富。光宣诗人论诗追溯汉魏,融通晋宋,兼采唐宋,师法百家,古典诗歌在此间迎来一次回光返照式的“繁荣”。光宣诗坛又处在社会发生变革的过渡时期,西学的扑面而来、传统思想的土崩瓦解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新诗在传统与革新的洗练中冲破成规得见曙光。光宣诗人在新旧时代的纠缠中彷徨,他们用诗的方式找寻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同光体诗人谈性情、说苦楚;中晚唐派诗人力主真性情;吴下西昆派诗人“楚雨含情皆有托”;湖湘派诗人提倡诗为己作、自发情性;诗界革命派诗人在情感上对传统诗学依恋又在理智上对其反叛。总之,光宣诗人内心的萧索与孤寂历经复古与革新的纠缠,在复古中创新、在创新中修正,共同推动中国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
一、古今“治情”传统的诗学回归
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悠久的“治情”传统:“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陈子展:《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在诗乐舞一体的形式下,“情”是诗歌创作内在的源泉和动力。不论是“发愤抒情”“缘情绮靡”,亦或是“摇荡性情”“本于情性”,情感永远都是萦绕诗人心中的主旋律,也是诗家论诗要旨。在光宣诗坛上,湖湘诗人复古汉魏六朝诗,追溯传统文学自觉的源头,对个体情感的审视与关注更加深邃,不掩悲情,强调“中和”之情的自然流露。表面“热闹”的光宣诗坛溺于浮世,关注情感的缘发与表达是湖湘诗人论诗的一大特征。王闿运认为“自发情性,与人无干”,(2)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2325页。肯定创作主体的直觉体悟,重视人的“自觉”。高心夔以情论诗,评邓辅纶诗近楚地之风,在《白香亭诗集序》中说:“夫啸歌为娱者,肥遁之业。寤叹不缀者,贞荩之义。故苞稂离黍,风士抒其概。杜衡芳芷,骚客纫其怀。情之所蓄,声之所宣,山水滋华,月露沦艳。含镛簴于法尺,贯坟典若佩珠。”(3)高心夔:《白香亭诗集序》,见邓辅纶:《白香亭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页。邓绎论情,配以日月天地,尚中和之美,在《藻川堂谭艺》中道:“汉、唐、宋人论文,其最高者皆本于气,而以孟氏为之渊源,推而上之即至圣‘辞达’之说也。黄梨洲集《明文案》,独以至情为主,其说本于《诗序》,亦孔门之微言。辞辑辞怿,非主情而言者欤?气本刚而用柔,情本中而达和,其大原出于天地,而配之以日月。”(4)邓绎:《藻川堂谭艺》,见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66页。湖湘诗人尚“情”,豁然可知。
湖湘诗人对“情”的理解十分深刻。首先,湖湘诗人拓宽论“情”的范畴。王闿运善言“情”,认为善、恶皆情:“情自是血气中生发,无血气自无情。无情何处见性?宋人意以为性善情恶,彼不知善恶皆是情。道亦是情,血气乃是性。食色是情,故鱼见嫱、施而深潜,嫱、施见鱼而欲网钓,各用情也。”(5)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2357页。他否定性善情恶论,以兼容的姿态包容善与恶,论“情”的范畴、气度和境界更加开阔。其次,湖湘诗人邓绎论“情”贵真:“诗为乐心,文宣乐旨,其抑扬抗坠,高下疾徐,上通于天籁,旁达于八音者,实缘人心之至乐而生。知人心之至乐,结响含情有出于玉振金声、条理始终之外者,而天地无声之乐可以神遇独得之于千载而下矣。”(6)邓绎:《藻川堂谭艺》,见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6122页。感物而发,实缘人心,结响含情,出于自然。邓绎论“情”贵真,与王闿运“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所感则无诗,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7)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2328页。大抵相同。最后,湖湘诗人所彰显的“情”多以“悲情”为主。湘楚文化笼罩下的文学自然流露着浓郁的感伤情调,王闿运的《独行谣》、邓绎的《感怀诗》寄予的悲情悲感,是时代的直观写照。
湖湘诗人论诗不仅注重内容上的“缘情”,也十分追求形式上的“绮靡”。“近代儒生深讳绮靡,乃区分奇偶,轻诋六朝。不解缘情之言,疑为淫哇之语,其原出于毛、郑,其后成于里巷。故风雅之道息焉。”(8)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544页。以“绮靡”之貌传达情感之妙,是形式与内容的兼顾,是外象与内在的融通。王闿运论诗,“缘情”与“绮靡”皆重。在湖湘诗人中,邓绎也十分注重“心”与“辞”的关系。其曰:“心犹光也,辞犹景也,光圆则景明,心慧则辞炳。故达于心,乃所以达于辞也。”(9)邓绎:《藻川堂谭艺》,见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6135页。由此可见,湖湘诗人论诗不仅主“情”而且尚“辞”。在实际创作中,湖湘诗人注重平衡“情”与“辞”的关系,主张“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10)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544页。
如何把握“情”与“辞”的尺度,湖湘诗人将“情”“辞”与“兴”联系在一起。邓绎认为“六艺之学造端于《诗》”。他说:“文章之妙必有待于所感,所感而悲则悲,乐则乐,清浊、高下、疾徐必与之肖。其动于外者天也,其根于内者亦天也。知本者明,得源者清,学道而后文章者,与之终身而不厌焉。默然无营而待物之至者,其感也神。道之至者不可以书言喻也,而其喻者已至矣,则亦有至焉者矣,斯之谓文化。”(11)邓绎:《藻川堂谭艺》,见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6115页。文章的悲喜、清浊、高下、疾徐皆有赖于情感。“《诗》之有《风》、《雅》、《颂》、赋、比、兴也,人心自然之礼乐与天地中和之气相应而为节宣。”(12)邓绎:《藻川堂谭艺》,见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6118页。诗人有感即发,不论悲欢,无须抑制,情感是诗人内心的自然倾注,更是文章玄妙的关键所在。可见,邓绎论诗追求自然状态下的诗合道心,其实质亦契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论诗传统。王闿运指出:“诗有六义,其四为兴。兴者,因事发端,托物寓意,随时成咏。始于虞廷‘喜’‘起’及《琴操》诸篇,四五七言无定,而不分篇章,异于《风》《雅》,亦以自发情性,与人无干。虽足以讽上化下,而非为人作,或亦写情赋景,要取自适,与《风》《雅》绝异,与《骚》、赋同名。”(13)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2325页。他说:“五绝、七绝乃真兴体,五言法门皆从权舆,既成五言一体,法门乃出。要之,只苏、李两派:苏诗宽和,枚乘、曹植、陆机宗之;李诗清劲,刘桢、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则李之别派。潘岳、颜延之,苏之支流。陶、谢俱出自阮,陶诗真率,谢诗超艳,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雕绘,未若宫体,故自宋后,散为有句无章之作,虽似极靡而实兴体,是古之式也。”(14)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2326页。王闿运提倡“兴”与他论诗尚“情”密不可分。怎样做到“言不可肆”与“情有所止”,他提倡“掩情”:“诗,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风上化下,使感于无形,动于自然。故贵以词掩意,托物起兴,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闻者激昂而思赴。其所不及设施,而可见施行,幽窈旷朗、抗心远俗之致,亦于是达焉。”(15)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544页。诗人的情感自然地通过“托物寄兴”的方式表达出来。湖湘诗人在中国古典诗歌日渐萧条下回归传统,执着地振兴古诗,向往重回文学自觉的时代。
二、新旧思潮下重“我”的情感觉醒
时局动荡,光宣诗人内心遭受了极大苦痛,却依旧无力挽回颓败残局。《史记》有言:“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6)《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10册,第4006页。诗人的痛苦与愤懑无处宣泄,纷纷寄情于诗,成就了古典诗歌最后的短暂辉煌。光宣诗坛表面的“繁荣”历经沉淀,透射出诗人在情感上的觉醒。
同光体诗人郑孝胥在《偶占视石遗同年》中曾言:“诗要字字作,裕之辞甚坚。年来如有得,意兴任当先。”(17)郑孝胥:《海藏楼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4页。“意兴”正是诗人在观照物象时所引发的一种不可言喻甚至转瞬即逝的情感,郑孝胥论诗极重个人性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曾记:
苏堪少日,尝书韦诗后云:“为己为人之歧趣,其微盖本于性情矣。性情之不似,虽貌其貌,神犹离也。夫性情受之于天,胡可强为似者?苟能自得其性情,则吾貌吾神,未尝不可以不似似之,则为己之学也。世之学者,慕之斯貌之。貌似矣,曰异在神;神似矣,曰异在性情。嗟乎!虽性情毕似,其失己不益大欤?吾终恶其为侫而已矣。韦诗清丽而伤隽,亚于柳;多存古人举止,则高于王。遗王而录韦,与其不苟随时,然亦不可与入古。柳之五言,可与入古矣,以其渊然而有渟也。柳之论文也,曰得之为难。韦之为韦,亦曰得之而已矣。弗能自得其性情,而希得古人之得,尽为人者也。”苏堪论入古处,尚有古之见存;其论性情神貌,则固渊明问答之旨,濠梁鱼我之机也。(18)陈衍:《石遗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郑孝胥通古今之变,得古人意而不被古人意所束,更不强似古人之貌。在《答樊云门冬雨剧谈之作》诗中,他曾言:“何须填难字,苦作酸生活。会心可忘言,即此意已达。”(19)郑孝胥:《海藏楼诗集》,第228页。沈其光在《瓶粟斋诗话》中谈及郑孝胥和陈三立诗风时说:“然苏戡胸中先有意,以意赴诗,故不求工而自工;散原胸中先有诗,以诗就意,故刻意求工而或有不工。”(20)沈其光:《瓶粟斋诗话》,见张彭寅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71页。以意赴诗,意念首当其冲,以诗为体,诗则精警自醒;以诗就意,刻意为诗,诗则生奥僻涩。因此,同光体内部诗风有着显著差异。诗歌要想达到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境,意兴所引发出的情感是绝不可缺的。郑孝胥重情,曾说:“尝谓伦类之相恃,二者而已,一曰义,二曰情。义疏而情密,义长而情短,圣人使之互相恃,而后人类各安,而相弃相背之风可鲜矣。又论恒人之好尚未定也,大概有三:质也,情也,习也。质者所赋也,情者所溺也,习者所从也,三者常相胜,而终于习胜矣。”(21)郑孝胥:《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6页。从海藏楼诗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他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怀念与留恋。
同光体诗人陈衍论诗重情、重变。他说:“夫学问之事惟在至与不至耳。至则有变化之能事焉,不至则声音笑貌之为尔耳。”(22)陈衍:《石遗室诗话》,第810页。一方面重视性情、学问与作诗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能关注情感的变化:“天地间之至文,云与水耳。云遇风万其变态,水则声容俱变。”(23)陈衍:《石遗室诗话》,第811页。陈衍将作诗看作是“寂者之事”,其实质也是对情感的肯定与关注。他在《何心与诗序》中说: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为,为之而可尝;喧者反是。故吾常谓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之贤者也。既而知其不尽然。犹是诗也,一人而不为,虽为而不常;其为之也,惟恐不悦于人,其悦之也,惟恐不竞于人,其需人也众矣。内摇心气,外集诟病,此何为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觉者,己独觉之,人如是观,彼不如是观也,人犹是言,彼不犹是言也,则喧寂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己所自得;求助于人者得之乎?余奔走四方,三十余年,日与人接,而不能与己离,不能与己离,虽接于人,犹未接也,焉往而不困?若是者,无所循于其诗也。持此以相当世之诗,若是者,百不一二,其一二者,固无往而不困也……柳州、东野、长江、武功、宛陵、后山以至于四灵,其诗世所谓寂,其境世所谓困也。然吾以为,有诗焉,固已不寂,有为诗之我焉,固已不困,愿与心与勿寂与困之畏也!(24)陈衍:《石遗室诗话》“前言”,第16页。
陈衍认为作诗是寂者之事,无当乎利禄,不必以此取悦于人,不必凭此胜于他人,不必借此求于他人,作诗当是觉人之所未觉,观人之所未观,言人之所未言。作诗要寻求与人不同之处,创作属于自己的艺术。在宗宋情结的笼罩下,陈衍重视学问根柢的力量,号召“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他在诗学天地中所坚守的那份“孤寂”,是对那个时代的执着留恋,恰是这份“孤寂”的深深埋藏,为情感的自觉蓄积了深厚坚实的力量。
湖湘诗人王闿运论诗主张“自发情性,与人无干”,在诗歌创作“为人”作还是“为己”作的本质问题上,他主张诗“为己”作。在《论诗法答唐凤廷问》中他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情。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余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25)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2328页。关于“情”,他在《湘绮楼说诗》中又说:“诗贵有情乎?序《诗》者曰发乎情而贵有所止,则情不贵。人贵有情乎?论人者曰多情不如寡欲,则情不贵。不贵而人胡以诗?诗者,文生情。人之为诗,情生文。文情者,治情也。孔子曰:礼之以,和为贵。有子论之曰:和不可行。和不可行而和贵,然则情不贵而情乃贵,知此者足以论诗矣。”(26)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2290页。王闿运论诗尚“情”,作诗主“情”,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力求达到中和的状态。这不仅取决于他对汉魏六朝诗的追捧,也透露出当时诗人对个性与自我情感的关注。王闿运论诗主张“自发情性,与人无干”,作诗坚守诗“为己”作,重视诗歌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的《泰山诗孟冬朔日登山作》《秋兴十九首》等诗作,在某种程度上散发出“通经致用”的观念,既有对创作个体情感的关注,又有对末世的深切关怀。
末世的感伤,引发诗人内心深厚的艺术情思。光宣诗人论情的重“我”构成了情感论的艺术内核。在近代诗派中,除同光体、中晚唐派、湖湘诗派、诗界革命派之外,还有吴下西昆派。西昆派诗人取玉溪体“楚雨含情皆有托”的方法,通过大量的咏史、咏物诗来表达绵邈的情思和无限的伤感。曹元忠的《失题》诗和汪荣宝的善化典故,都传递出内心的苦楚与悲凉。吴下西昆派诗人善于化情,孙景贤仿义山之作,“主动地从诗作意蕴、诗情等方面追求出新,同时把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寄寓诗作”。(27)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7页。不论是时代寄寓诗人孤独的悲情,还是诗人内心保持的真性情,都为光宣诗坛情感论谱写下精彩篇章。
三、中西合流后的情感自觉
光宣诗坛的情感论既有客观、冷静的执着,又有任性、恣肆的洒脱,还有理性、包容的开放,为中国古典诗歌情感论注入新时代血液,加速中国诗歌走向自觉。中晚唐派诗人易顺鼎以特立独行、洒脱不羁的个性备受后人瞩目,张之洞称其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采飞腾”。(28)易顺鼎:《琴志楼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19页。易顺鼎的诗歌集伤感、真挚与善变为一体。程淯在《琴志楼编年诗集序》中说:“尔时所作诗,一字一泪,蔼然仁人之言,不知者乃以名士目先生,妄已!”(29)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498页。易顺鼎诗歌中的伤感是真实地、不加掩饰地直抒胸臆,正如他所说:“我诗皆我之面目,我诗皆我之歌哭。我不能学他人日戴假面如牵猴,又不能学他人佯歌伪哭如俳优。又不能学他人欲歌不敢歌、欲哭不敢哭,若有一物塞其喉。”(30)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283页。这与王闿运论诗“自发情性,与人无干”的论调相似,他们都关注和彰显个体情感的力量。倘若“雅”是王闿运诗歌的美学追求,那“哭”则成为易顺鼎诗歌的基本格调。
易顺鼎在丧母后以“哭盦”为号,丧母是其人生的一大转折。此后,在易顺鼎的诗歌中,充满许多“哭”的意象,如《叠前韵四首寄夢湘伯棠》中有“痛哭年华销贾傅,穷愁仕宦赚虞卿”,(31)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603页。《立秋夕淮舟即事》一诗中有“对此茫茫翻忍泪,怕疑阮籍哭穷途”,(32)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630页。《五月八日悦城龙母祠歌》中有“五月五日楚人哭,汨罗江边花踯躅”。(33)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091页。易顺鼎以“哭”入诗,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的诗哭出了对人生的无奈、对现实的感慨,哭出了对时代的失望、对新人的召唤。他的“哭”不再只为亲人,而填满了他整个跌宕起伏的一生。
“哭”是易顺鼎个人情感的外现,也为他的诗歌奠定了极浓郁的悲伤基调。易顺鼎一生仕途坎坷,诗体屡变。《哭盦传》中有言:“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处,其师与友谑之称为‘神龙’。其操行无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为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34)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435页。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评易顺鼎诗,称其屡变面目,不免为世所訾。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当中称其“早负诗名,足迹几遍天下,所至成集,随地署名,合编为琴志楼集。诗体屡变,中以庐山诗为最胜”。(35)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527页。以“樊易”相称的樊山诗能自始至终,保持一格,而易顺鼎与之迥异。易顺鼎三岁能读《三字经》,五岁便能作对子,十四岁就入县学,初应试,交卷第一,十六岁就补廪生,十八岁应试中举。他的一生集名士、经生、学人、贵官、隐士于一身,极具变化的人生阅历幻化为无形的“财富”,遭受了千般坎坷,亦铸就了诗歌的不朽。张之洞称其“作者才思学力,无不沛然有余。紧要诀义,惟在割爱二字”。(36)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519页。樊增祥在《书广州诗后》中赞“石甫既负盛名,率其坚僻自是之性,聘其纵横万里之才,意在凌驾古人,于艺苑中别树毫纛”。(37)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496页。易顺鼎的诗有意炫才,樊增祥又道:“庐山以后之诗,大抵才过其情,藻丰于意,而古人之格律、之意境、之神味,举不屑于规步而绳趋而名亦因是而减。文襄深惜之,又力诫之,君方自谓竿头日进,弗能改也。”(38)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496页。过分地逞才降低了易顺鼎的诗名,即便如此,易顺鼎狂妄的个性和洒脱的人生态度并不因此让步,他依然不惧人嘲人骂,不畏天变和人言。
在易顺鼎的人生观中,三副热泪各有落脚点:一是自身对国家和百姓的关心,二是自己文章是否被赏识,三是个人情感是否有佳人寄托。每一点都是易顺鼎至情至性的真实流露。庚子国变后,易顺鼎在戏剧中找到了精神寄托的避难所,他的创作更加恣肆,不再合于古人法度,更不在意师友们的劝诫。他热衷对名伶的追捧,创作了大量的捧伶诗,这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轰动,但易顺鼎却依然保持他特立独行的狂傲个性。在《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中,他毫不掩饰地说:“请君勿谈开国伟人之勋位,吾恐建设璀璨庄严之新国者,不在彼类在此类。请君勿谈先朝遗老之国粹,吾恐保存清淑灵秀之留遗者,不在彼社会、在此社会。”(39)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277页。他大胆地提出“尧舜汤武皆伪儒”“桀纣幽厉为俊物”之言,与传统诗学背道而驰,在当时招致不少诟病。又作《读樊山后数斗血歌作后歌》进行反驳,“歌又恐被谤,哭又恐招尤”,是诗界之诗囚。对诗坛上出现的诗分唐、宋表示不满,他直言“真唐真宋复何用”。面对世人的评论,易顺鼎毫不避讳地说:“嗟我作诗未下笔以前胸中本有无数古人之精魂,及其下笔时无数古人早为我所吞。此时胸中已无一二之古人,此时胸中岂复尚有一二之今人?他人下笔动作千秋想,我下笔时早视千秋万岁如埃尘。他人下笔皆欲人赞好,我下笔时早拚人嘲人骂、不畏天变兼人言。”(40)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284页。
易顺鼎真性情的诗学观以古人为我所用,不图虚名,不惧恶言。“不畏天变兼人言”是何等狂妄不羁,又是何等洒脱恣肆。王代功在《湘绮府君年谱》中记载王闿运与诸生谈“恒”,认为“恒”即不易业、不求名、不好名、不求达、不违心,易顺鼎的创作心态已然达到了“恒”的境界。在他伤感的艺术基调下,人生、诗歌和境遇统统被糅进了丰富的诗情中。易顺鼎之所以“哭”,是对现实的不满、对情感的宣泄、对怀才不遇的无奈;之所以“变”,是因为天赋异禀却屡经坎坷;之所以“真”,是因为他洒脱任性、无所畏惧。不论是湖湘诗人王闿运的“自发情性,与人无干”,还是中晚唐派诗人易顺鼎“我诗皆我之面目,我诗皆我之歌哭”,都不同程度地对传统诗学开始发出警示,这预示着在古典诗的国度里,即将迎来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新文化运动荡涤了封建的旧文化,诗界革命派诗人梁启超按捺不住内心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开始徘徊和反思。他善于运用理论再现诗歌的特征和本质,对传统文化“理智上反叛、情感上依恋”的态度是过渡时代中西学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这种被称为“爱国主义的精神分裂”态度既保守又开放,既进步又落后,充分体现了那一时代诗人内心的矛盾。梁启超晚年诗学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对传统诗学的审视和反思,其间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情感”的关注。他从情感论出发挖掘古典诗歌的本质和特征,在《情圣杜甫》《屈原研究》《陶渊明》《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都有较为集中的论述。传统诗人论诗向来重情,与其他诗派不同的是,梁启超的“情感”论更富时代特质。他理性、全面地再现了古典诗歌的唯美,同时又极大丰富了中西文化交叉合流后的精神体验。梁启超论诗重视情感,他说:“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4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2页。
在梁启超的理论中,“情感”和“理智”都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人们往往关注“理智”却忽略“情感”,梁启超极为重视“情感”,将“情感”比作生活的原动力。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说:“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门,别无他路。所以情感是宇宙间一种大秘密。”(4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921页。人类情感的内在潜力超乎人类的想象,它一方面能够突破极限,引导人们进入超本能的境界,另一方面又能穿越时空,使人进入超现在的境界。情感的力量能够透过表象直达超时空境界,梁启超的情感理论将人的生命、生活、众生和宇宙串联在一起,通过创作主体、个体经验、读者经验和超现在的宇宙融为一体,这在当时是传统诗人无法企及的。
不仅如此,同湖湘派诗人主张“善恶皆情”一样,梁启超指出情感的本质不都是善的。“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他的本质不能说他都是善的都是美;他也有很恶的方面,他也有很丑的方面。他是盲目的,到处乱碰乱迸,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也坏得可怕。”(4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922页。人类情感是多面的、立体的、深刻的。尽管“情感”有善恶、美丑之分,但在艺术的视角下仍然追求的是真性情:“大抵情感之文,若写的不是那一刹那间的实感,任凭多大作家,也写不好。”(4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929页。梁启超重视情感的力量,他提倡真实的、丰富的、深刻的艺术情感,只有号召将这种情感倾注到作品中,最终才能成就文学的价值。不论是在《情圣杜甫》《陶渊明》里还是在《屈原研究》中,梁启超都是从情感论出发,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评价和研究人物,真正地将情感论融入文学研究与创作中。
梁启超以客观、冷静、理性的科学态度对“情感”进行剖析,他的“情感论”是中西合流的结果。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说:“我们有极优美的文学美术作品。我们应该认识他的价值,而且将赏鉴的方法传授给多数人,令国民成为‘美化’。”(4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4068页。受康德理论的影响,梁启超的思想闪烁着西方理性的光芒,他指出情感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孔子之人格》一文当中说:“近世心理学家说,人性分智(理智)、情(情感)、意(意志)三方面。伦理学家说,人类的良心,不外由这三方面发动。但各人各有所偏,三者调和极难。我说,孔子是把这三件调和得非常圆满,而且他的调和方法,确是可模可范。”(4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152页。西方人极难调和理智、情感和意志,梁启超认为孔子是当之无愧的调和模范,在中西伦理学与心理学的比较过程中,他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此外,梁启超认为“情感”在某些领域已经完全超越了“科学”的层面,体悟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科学精神”。(4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4006页。在人生中关于理智的方面必须要用科学方法去解决,而关于情感的方面是超科学的。尽管在具有唯物史观的理论工作者看来,这种脱离科学而言情感的说法缺少科学性,但“情感”本就妙不可言,在文学的领域里单纯用科学去界定它的存在似乎无章可循,他由此指出:“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4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978页。由此可见,相比传统诗人的“治情”传统和重“我”的真性情,梁启超的“情感”论既充满西方的理性色彩,又符合古典诗歌“缘情”的历史传统,是中西学理论在过渡时代调和的产物。
过渡时期西学自由、平等、开放的思想不断发酵,诗界革命派诗人随之关注到了女性的情感世界。在《专论女性文学和女性情感》中,梁启超阐发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文学观。他毫不掩饰地赞美“情感”的力量:“用情感来激发人,如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49)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921页。他除了对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女性文学家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之外,对描写女性形象、表达女性情感、刻画女性意志的作品也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之际,一些传统文人仍以“发乎情止乎礼”来约束内心的情感世界,但梁启超的“情感”论已尝试转型,一方面融入西方理论,另一方面又不机械定义“情感”。他的情感论既发扬了古典诗歌“缘情”的艺术传统,又突破性别的歧视。梁启超晚年的情感论诗学既打破传统又回归传统,同其他诗界革命派诗人一起引领和推动着新诗的发展。
在中西文化交融碰撞过程中,中晚唐派诗人樊增祥对捧伶诗虽用“拉杂鄙俚”冠之,但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也给予了很多关注。他的长篇叙事诗《彩云曲》用艳诗的形式塑造了乱世之际的赛金花形象,他的《十忆》诗突破传统道德对女性的束缚,表现出对女性美好的肯定与关注,用一种近乎“游戏”的心态真实地流露内心的情感。易顺鼎在《崇效寺牡丹下戏作短歌》中言:“人生不过一生耳,若不行乐真堪哀。人生不过一死耳,若尚畏死真庸才。”(50)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281页。他的诗如同他的人一般有声有色。他在《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读樊山后数斗血歌作后歌》中,颂扬名伶是一群可爱可敬之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5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5327页。光宣诗人对女性情感与形象的突破和肯定,为他们饱经沧桑的心灵寻找到一个精神慰藉的“避难所”,尽管在当时被世人诟病,但足以为新诗吹响前进的号角。
四、结 语
光宣诗坛流派纷呈,情感理论丰富。传统诗人检视历史,溯源回归,追慕向往文学自觉;具有觉醒意识的诗人能顺应时势,在古与今、进与退之间搭建桥梁,他们情感的觉醒,迎合时代发展所需;革命诗人主动求索,自觉突破,推动时代进步,使自由思想得以在诗学中发酵,促使中国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光宣诗坛的情感论在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的对抗、融合、修正中,为中国诗歌开辟出一条新“诗”路。在风云跌宕的没落年代,光宣诗人已然感知到古典诗歌的消退是一种历史必然,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在诗歌的天地中呐喊、突破,使新诗与古典诗相互成就。光宣诗人在文化情感上的“执念”和“向往”刺激着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与新时代的发展。“当我们走到19、20世纪相交的那个年代,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型的这一历史时期,晚清遗民们痛苦、彷徨、挣扎,又何尝不是在为即已衰落的旧文化呐喊、哭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多种形态,所采取的多种生存策略又何尝不是在为那种旧文化做种种挽回的努力?”(52)傅道彬、王秀臣:《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北方论丛》2002年第1期。光宣诗人内心交织的复杂情感,在彷徨中复古,在革命中披荆斩棘,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最后的辉煌。中国古典诗歌和西诗在经历相互“破坏”和相互“汲取”之后,共同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