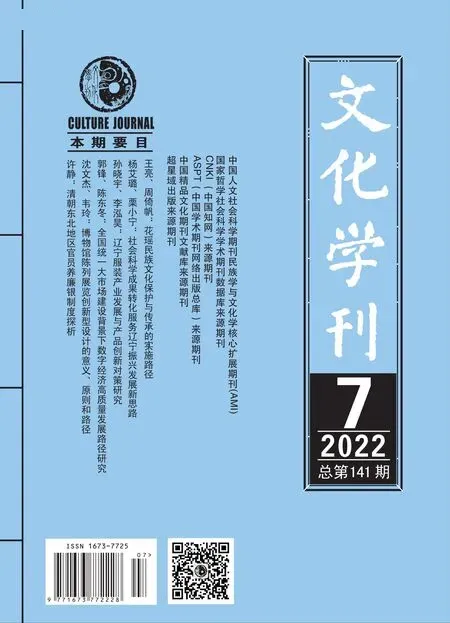汉代“八能之士”略考
2022-11-25李泉呈
李泉呈
一、“八能之士”身份查探
(一)儒士身份
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至此儒学兴起,大批儒士受到重用。此时的儒学,已经不再是前朝时纯粹的儒学,它已经融合了“阴阳五行说”与“天人感应”等,出现了经学化的倾向。至东汉,儒学继续延续发展,光武帝曾利用符瑞图谶起兵,登位之后,便开始尊崇谶纬之说,并且“宣布图谶于天下”[1]84。之后,儒学思想中的谶纬学说逐渐成为了东汉时期的统治思想,也发展为帝王即位时所必须举行的仪式,以验证其合理性。谶纬的思想不仅体现在用人施政方面,甚至各种祭祀都有谶纬仪式的参与。
有关“八能之士”,早在《礼记·月令》就出现了“夏至,人主与群臣从八能之士,作乐五日”[2]505的记载。后在《易通卦验》中又有“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调黄钟,或调六律,或调五声,或调五行,……或调阴阳,政德所行,八能以备。人主乃纵八能之士,击黄钟之钟,人敬称善言以相之”、《乐纬》“冬至,人主与八能之士作乐五日”、《乐协图》“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阴乐以成天文,作阳乐以成地理”的记载。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整理,有关“八能之士”的记载大部分存在于《易通卦验》《乐纬》《乐协图》等纬书中,纬书是属谶纬的范畴。除此,《后汉书》礼仪志与律历志中都有对“八能之士”进行详细描述。虽然“八能之士”多作乐,调五声等,但历代记载却都没有将其置于“乐志”的分类中,而是记载在纬书或正史律历志之中。另外,“八能之士”以“士”为称,“士”被认为是“以才智用者”在谶纬之学盛行的背景下,阴阳五行已经成为“士”进入贵族阶层必备技能。加之儒学盛行,通经之士日渐其多, 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学之士, 经学渐成为儒士入仕之阶,所以“八能之士”应是精通音律并懂阴阳历法以及天文谶纬之学的儒士。
(二)人众选拔
东汉时期,所谓“八能之士”并不是一人全能,而是八人各司其职,见《后汉书·礼仪志》:“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间竽;或撞黄钟之钟;或度晷景”[1]3126。每位八能之士都有自己精通的一个方面,八人之间相互配合,合称“八能之士”。
对于“八能之士”的选拔并不随意,首先,自身专业性上的要求较高,《礼记正义·卷十六》载:“从八能之士,谓选于天下人众之中,取其习晓者而使之。”可以看出其选拔是于“天下人众”之中,取“习晓者”而用之,说明已经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其次,八能之士的选拔并不是在小范围内以位高者推荐为主,而是公开选拔,择优选用。
(三)分工明确
“八能之士”并不是由八人同时进行,而是需要八人相互配合,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分工,几人按照顺序,各执其职,共同协作来完成对当时政治系统的测调。
其中有调黄钟者,“调黄钟者,县黄钟于子,其以大小之差展其声”[2]506;有调六律者,“调六律者,六律管,阳也。又有六吕为之合,管有长短,吹之以调乐器之声”[3];有调五音者,“调五音者,金为钟,革为鼓,石为磬,竹为管,丝为弦,皆有声变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调者,声少变,故不调”;有调五声者,“调五声者,宫、商、角、徵、羽,声弘杀缓急。凡黄钟六律之声,五音之动,与神灵之气通,人君听之,可以察已之得失,而知群臣贤否”;有调五行者,“调五行者,五行谓五英。”;有调律历者,“调律历者,律历谓六茎也”;有调阴阳者,“调阴阳者,谓《云门》《咸池》”;有调正德所行者,“调正德所行者,谓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通过对这八个方面的测调,使之阴阳相合,从而实现政治上的稳定。
政治是否平和体现在“钟音”“鼓音”“管音”“磬音”“竽音”“琴音”的测调结果。若钟音调,则君道得,君道得,则黄钟、蕤宾之律应。君道不得,则钟音不调,钟音不调,则黄钟、蕤宾之律不应。而将黄钟比附君主的原因,是由于黄钟主一,一生万物。故君子铄金为钟,四时九乳,是以撞钟以知君,钟音调则君道得。鼓音调,则臣道得,臣道得,则太簇之律应。管音调,则律历正,律历正,则夷则之律应。磬音调,则民道得,民道得,则林钟之律应。因为钟磬之音,能动千里。竽音调,则法度得,法度得,则无射之律应。琴音调,则四海合,岁气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则姑洗之律应。五乐皆得,则应钟之律应,天地以和气至,则和气应,和气不至,则天地和气不应。
二、“八能之士”功能职责
(一)听乐知政
所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王朝更迭,每位统治者获取政权之后,都会重做礼乐,彰显自己的统治地位,除了以显文治武功,更重要的是以求国泰民安。这便是“听政、观得失”。最熟为人知的就是春秋时期“季札观乐”,季札通过听乐、观舞,不仅能判断“诗乐”来自何方,更能分析出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差异,从而推测国家走向,这正是“听乐知政”的最好例证。
统治者将八音乐器作为省察社会政治功效的工具,以“八能之士”作为实际操作者。《后汉书·礼仪志》载“夫圣人之作乐,不可以自娱也,所以观得失之效者也。故圣人不取备于一人,必从八能之士。故撞钟者当知钟,击鼓者当知鼓,吹管者当知管,吹竽者当知竽,击磬者当知磬,鼓琴者当知琴。故八士或调阴阳,或调律历,或调五音。故撞钟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击磬者以知民事”[4],可以看出两汉时期作乐同样是以“观得失之效者”为目的,不用于自娱。相较季札观乐,两汉时期“听乐知政”的方法并不相同,相较前代更加系统且完善,并且出现专门从事这一仪式的人员“八能之士”。统治者通过取备于“八能之士”,由其调律历、调阴阳、调五音等,以求“与天地神明合德者,则七始八终,各得其宜也”。七始,也就是所谓的四方、天、地、人,是政治与天地调和的体现。
人主与八能之士联合组建了一套将乐器与政治连结的音乐行政体系,如用钟代表君、用鼓代表臣、用磬代表百姓、用琴代表德行等等,产生了与五声相仿的归附模式,宫与君对、商与臣对、角与民对、徵与事对、羽与物对,再对五音进行调整,以求达到音谐政和。
(二)观察预测
《易象正》中有记载,八能之士,登台以书云物。“书”作动词,描绘、记写之意。“云物”,《左传》中有注,云物代表气色灾变也,即天象云色变化。也就是说“八能之士”登台观云,据云色变化来预测吉凶。在我国古代,一直就有观云色测吉凶的传统,如“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分别以青、白、赤、黑、黄五种颜色来代表虫、丧、兵荒、水、丰,通过观测预知并作准备。
在汉代,八能之士也通过观察天象,以晷长短来判断政治是非,如若“其晷之如度者,则岁美,人民和顺。晷不如度者,则其岁恶,人民为讹言,政令焉之不平。晷进则水,晷退则旱,进尺二寸则月食,退尺则日食,月食籴贵,臣下不忠,日食则害王命,道倾侧,故月食则正臣下之行,日食则正人主之道。晷不如度数,则阴阳不和,举措不得,发号出令,置官立吏,使民不得其时,则晷为之进退,风雨寒暑为之不时。”
在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下,统治者通过“八能之士”对音律的协和、日晷长短的观测,来判断政治的优劣,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察知现在之政,二是预知未来之政。
三、“八能之士”仪式流程
(一)时间
仪式一般在每年二至二分的“二至”时进行,“二至二分”就是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时间节点,“二至”就是夏至和冬至。因为夏至、冬至分别是每年日照时间最长和最短的时候,所谓“阴阳晷景长短之极,微气之所生也”。《汉书·天文志》载:夏至晷长“尺五寸八分”,冬至晷长“丈三尺一寸四分”,夏至日阳气最盛,冬至日阴气最盛,这两个时间节点阴阳极为不平衡,急需通过八能之士来进行调测,以达到阴阳平衡。所以在汉代,八能之士的仪式时间就确定为夏至日和冬至日。《汉书》记载:“夏至人主与群臣从八能之士,作乐五日”“冬至人主与群臣从八能之士,作乐五日”,可知仪式一般要持续五天。在这五天时间内,先王与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来“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阴乐以成天文,作阳乐以成地理”,阳乐就是黄钟律,阴乐就是蕤宾律,也就是君调,达到天地相和。
(二)乐器
按《乐纬》的记载,仪式所用乐器以金、石、丝、竹、土、木、匏、革八类为八音,与之对应的钟、磬、弦、管、埙、概圄、笙、鼓为八器,这些乐器发出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根据乐器音调的不同,其背后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乐器开始与民情政道、时令以及音律相匹配。此时乐器已经不单单以乐器本身而论,而是与音律、时令、政治等相配。以磬为例,磬之声于音调上属于十二律中的夷则,而对应于十二月,夷则又象征着七月,属于阴气初起凌阳之势,因此在节气上又属于立秋。立秋万物始结实,又对应了象万物之成。这样的相互对应使得乐器本身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
在汉代八能之士仪式过程中,针对使用乐器、乐器材质、乐器形制也都有细致规定,且夏至日与冬至日所用乐器规格也不相同。
冬至时,击黄钟之鼓,所用鼓的材质为马革,鼓直径为八尺一寸,鼓黄钟之瑟,所用瑟使用槐木,槐木属阴,瑟长八尺一寸。吹黄钟之律,间音以竽补,竽长四尺二寸,竽的长度是根据五行中火、水两数得之,冬至火数七,水数六,六七四十二,就得出竽之长。
夏至时,鼓用黄牛皮,因为夏至离气,离为黄牛,鼓直径五尺七寸为蕤宾之律也。瑟用桑木,柳槐条取其垂象,炁下也,瑟长五尺七寸。间音以箫,箫亦以管,形似鸟翼,鸟为火禽,火数七也,数又有二七四,因此萧长尺四寸。
除此,汉代八能之士仪式中所用乐器皆有各自在政治中的体现,钟,知君、显功罪;磬,知民;管,知律;鼓,和臣;琴,知德;芋,知法度。
(三)仪式
每至冬至、夏至,八能之士开始做事,冬至时,人主不得出宫,商贾人众不能出行,持续五日,这五日中,人主在八能之士作乐的地方观看,五日之后,开始迎接日至大礼。仪式进行中,分别在先气五刻、三刻、二刻、一刻时进行不同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先气五刻:“待到先气至五刻,太史令与八能之士即坐于端门左塾。大予具乐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钟为端。守宫设席于器南,北面东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仪东北。”接着三刻:“中黄门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门,就位”。二刻:“侍中、尚书、御史、谒者皆陛。”一刻:“乘舆亲御临轩,安体静居以听之”。待到准备工作完成后,八能之士开始行事:“太史令前,当轩溜北面跪。举手曰:‘八能之事以备,请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诺’。起立少退,顾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诺’。皆旋复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间音以竽。’八能曰‘诺’。五音各三十为阕。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并作,二十五阕,皆音以竽。讫,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书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钟之音调,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则召太史令各板书,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书,施当轩,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书授侍中常侍迎受,报闻。以小黄门幡麾节度。太史令前白礼毕。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诺’。太史命八能士诣太官受赐。陛者以次罢”。至此,整个仪式结束,夏至时仪式亦如之。
待仪式结束后,八能之士便把几个方面的预测结果反馈给先王,先王通过五音的协和程度对接下来的政治决策进行考量。其中就有祭祀用乐问题,如冬夏至于圆丘祭祀是否用乐就决定于此次的仪式结果,一般来说,在音谐政和的情况下,先王都会决定使用乐。
由汉代出现的“八能之士”,实质上其背后体现出的是天、地、人的音乐思想,在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之下,统治者认为乐是调和阴阳与天地的,因此制乐须法天地,“八能之士”仪式便体现出了统治者听乐知政的思想,充分地体现了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学说进入汉代后对乐带来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