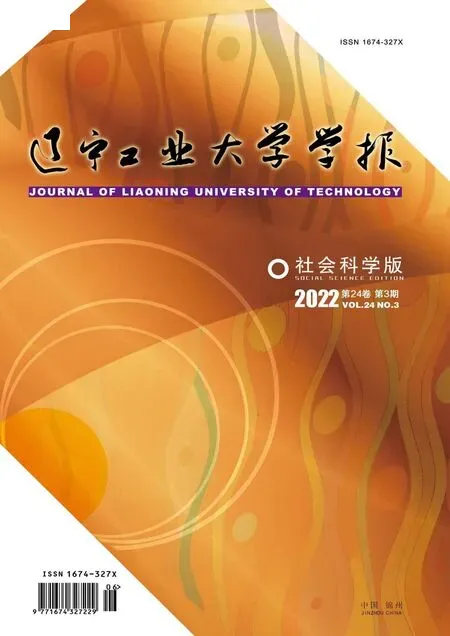宋代昼寝诗的内涵拓展与诗境构建
2022-11-25艾迪
艾 迪
宋代昼寝诗的内涵拓展与诗境构建
艾 迪
(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昼寝”题材是古代诗歌中的一道独特风景,自中唐起昼寝诗数量开始增多,宋代蔚然成风。昼寝诗歌经宋代诗人之手呈现出了不同于前代的审美内涵,展现了作者对心灵自由层次的追求。凭借对昼寝诗的施行主体、时间、空间等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见宋代诗人将笔触逐步从闺阁扩大到室外,此时期的昼寝题材成为古代诗歌对凡俗生活的艺术化反映和对诗境的立体化构建的重要途径。
昼寝诗;审美内涵;诗境
昼寝,亦可称“昼眠”,即白天眠寝的行为,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唐朝以前对昼寝行为的描写多集中在闺中,士人昼寝诗自中唐兴起,宋代渐成风尚。聚焦于昼寝诗在唐宋时期的盛行特点和审美心理,这是已有研究的核心观点。昼寝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之相关的“记梦诗”的叙事性也逐渐受到关注,但论者也往往止步于此,并未关注到宋代昼寝诗具有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和立体的诗境构筑方式。
一、宋前昼寝诗的发展
宋代昼寝诗包含着对前代的继承,《论语·公冶长》中便记载了一个关于宰予昼寝的故事:“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1]从孔子的愤怒态度可以看出,昼寝行为在当时是不被提倡的。中唐前,诗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将士人白日寝居于内视为不符合礼法规范的行为,故昼寝诗创作并不多,即使有也多将书写对象局限于女性。闺闱成为了诗人们在这一题材中环境描写的重点,意象也无非是女子闺房陈列的熏笼、玉枕等物品。如萧纲便有一首《咏内人昼眠》:“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2]便是对女子体貌和闺阁内外环境的环绕式描写。《乐府诗集》中也有“寒闺昼寝罗幌垂”之句[3]。享受田间恬淡生活的陶渊明曾代表隐士群体发声:“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4]由此可观,此前诗中昼寝行为的施行主体很少愿意承认是“我”,多指他人。将其细分,还可窥见因描写对象的性别与身份的不同,带来的差距是非常鲜明的,女性和所谓的出世者往往能得到更多的宽容。当昼寝施行主体为女性时,昼寝于内闱的女性更像是作为一个意象或一个观赏对象出现,与帷帐、琵琶等物品共同承担起对昼寝环境的空间构建,诗境里往往隐含着一个“观赏者”在其中,而这个隐含的观赏者更偏向于以男性的视角审视整个诗境。吟咏女性昼寝的作品,昼寝空间多处于内室,对窗外的环境描写较少,描写重心集中在女性的音容笑貌上,绮丽雍容。
自唐起,昼寝题材一方面继承了前代对女子眠寝体貌描述的偏好,如杨衡的《春梦》、韩偓的《深院》。另一方面开始渐渐撇开士大夫昼寝乃废学懒惰的内涵,此类以白居易为代表。白居易宣扬其昼寝的闲适,专咏昼寝的作品便有《春眠》《隐几》《昼寝》《昼卧》等,忙里偷闲成了这个时期的士人可以标榜的生活趣味。其《晏起》一诗便声明了作者不为财名所累的境界:“鸟鸣庭树上,日照屋檐时。老去慵转极,寒来起尤迟。”[5]白居易还将自己与“霜满衣”之人进行对比,表达了自己对官场浮沉的不屑。除白居易外,韦应物的《夏日》和张令问的《与杜光庭》都表达了类似的情感态度,大胆承认了对自然平和心境的接近和对朝堂俗务的疏离。
二、宋代昼寝诗内涵的拓展
到了宋代,日益繁盛的昼寝诗进入黄金期,并且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增添了新的内涵。首先,从数量上看,历代昼寝诗当以宋朝为最。随意翻检《全宋诗》,单就“昼寝”或“昼眠”为题的,就有郭印《昼眠》、晁冲之《昼寝》、刘兼《昼寝》、梅尧臣《昼寝》、邵雍《昼寝房》、宋祁《昼寝》、张耒《和晁十七昼眠》、王安石《昼寝》等等。由此可见,将昼寝诗作为表现作者的情绪与心态的工具,是宋代文人有意识的主动选择。
宋代昼寝诗的大量创作,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宋代文官制度发达,对文官待遇的提高为士人的生活活动也提供了众多的选择,社会风气向闲适意趣、吏隐风尚转型,大大促进了昼寝题材的发展。第二,宋代取消了宵禁,享乐之风盛行,夜晚生活的丰富使士人不必日落而息。第三,与近古期文学逐渐日常化趋势相关,诗人们便尽可能从平庸卑琐中最大程度地挖掘生活美学。其实,对现实生活进行广泛的描写,本就是中国诗学历来的传统与特色。自《诗经》起,创作者便开始以现实为摹本,以日常活动为素材来进行个人或群体情感的抒发。近古诗歌对于生活的插入更是无孔不入,饮茶、看花、濯足、静坐、乘凉、吃饭、睡眠皆能为诗。宋代诗人在诗歌日常化和私人化书写上更是进行了有意识的努力,市民走卒、春睡小寐,无有不可入诗者。宋代诗歌对生活的艺术化处理像是石子砸入静湖,每一片掀起的涟漪都对周边的景物进行了映照,从不同的方向对真实的生活进行单个侧面的反映。这些涟漪共同构成的映像是诗人对于真实人生的观照和艺术化的剪裁。昼寝诗作为宋代诗人对大千世界观照的一个方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宋代昼寝诗内涵,一方面照例有继承前代对闺阁女儿的关注和对士大夫闲适生活的镜像描写,另有一部分,却是抒发了文人对不满意的真实生活的反抗。前者如蔡襄的《阁下昼眠》、陆游《竹窗昼眠》。后者以苏轼为典型,他在唐人基础上进一步将昼寝诗提纯,通过日常化的书写、诗歌意境的烘托,让人直观地感受到作者对自由心灵的追求与面对困境毫不妥协的精神。他曾作《春日》一首:“鸣鸠乳燕寂无声,日射西窗泼眼明。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6]1331“鸣鸠乳燕”本给人一种活泼鲜活的感觉,却说它们寂静无声,窗外阳光耀眼,却依旧不扰睡眠,足见诗人的安眠闲适。此时的西窗,将诗人与窗外的鸣鸠与日照隔阂开来,睡与醒的界限便在一窗之间,不论外界如何与室内进行沟通与连结,作者都能守住心灵的平静。苏轼多在失意时作旷达之语,如《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其四》:“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6]478浅浅的品一茗茶,清风徐来,落花随着起起伏伏的呼吸悄然落下,一场好睡足以弥补此刻心中的遗憾。苏轼亦有《纵笔》一首,纪昀评:“此诗无所讥讽,竟亦贾祸。盖失意之人作旷达语,正是极牢骚耳。”[7]苏诗体现的闲适旷达,在政敌看来,便更像是无言的宣战。此时的昼寝题材通过苏黄一代宋人的努力,其内涵加入了对生活黑暗面的抗议,更能借睡梦之杯酒,浇抒怀之块垒,无论是怀亲倦游之念、江湖落拓之感皆可暗藏其中,承担起弥补作者情感需求的功能。宋代文人借安眠好睡展现对外物得失的坦然,此时的昼寝诗早已摆脱了废学的内涵,代表了心灵的自由。
三、宋代昼寝诗时空的铺展与诗境的立体构建
昼寝者、昼寝的时间与空间,根据这些因素,便可以让我们在诗境的构建过程中试图体悟诗歌的内涵。
诗歌中的昼寝行为出现的空间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固定且相对封闭的室内或庭院之中,一是在行动的交通工具里。
较为封闭的室内或庭院是昼寝行为的理想场所,一些作品虽未提到具体的昼寝地点,但诗中的一些意象可以作为我们推断的依据,比如前文提到的《春日》一诗,虽没有明确指出昼寝环境,但“西窗”一词便暗暗提示了读者,实际上有一个居室的存在。作者昼寝于室内,并与窗外的景色进行了交流,这种交流的范围可分为虚实两种。交流途径运用视觉器官,描绘外界实际看到的风物,是实景。运用听觉器官,对外界存在进行合理的推测与想象,便是虚景。虚实相生,诗人通过运用几个视野范围内可清晰感知的意象“鸣鸠”“乳燕”“西窗”共同筑起了一道不与外界世界交叉的诗墙。诗人不干涉外界空间而转自关怀自己的内心情感,既是自我意识的凸显,在情绪上也体现了作者面对俗务时仍然保持的平静淡然。又如苏东坡在儋州所作的一首昼眠诗《独觉》,其中有几句云:“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8]后两句本是苏轼在他的词作《定风波》中的语句,暗接在这里变成了作者半梦半醒间思想活动的暗喻,更是可供作者描写,进行对“外”交流的一类虚景。仅仅四句,便将自己多年面对朝政、人生风雨的坦然不惊和通透自适表达了出来。人生的风波,朝读者汹涌而来,虚景如实景般供阅读者在脑海中尽情塑造。睡与醒之间的连结,既有此刻的鼾声,又有往事的回忆。宋代昼寝诗将个人的真实情感与理想赋予在昼寝题材中,诗境便通过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进行延伸,立体框架便搭建了起来。
在行动中的交通工具内昼寝,如杨万里《过水车铺二首其一》:“轿里看书得昼眠,梦中惊浪撼渔船。”[9]26302形象描写出了出行时的轿辇颠簸。宋代制造业发达,水路交通发展迅速,故坐船成了士人出行的交通选择之一,宋代大诗人苏轼诗中便常常出现“舶趠风”等航行者行业语。随着宦游的增多,昼寝于舟船之内也变得寻常起来,如陈与义《过孔雀滩赠周静之》中有:“高眠过滩浪,已寄百年身。”[9]19548又如杨万里《舟中雨望二首其一》:“雨里船中只好眠,不堪景物妒人闲。”[9]26239小小扁舟,承载着诗人不同的“诗情”。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于,作者昼寝的地点如室内、庭院、舟船,都较为封闭,但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却往往放在所处空间之外——居于室内的昼寝者更倾向于描写窗外景物或自己脑海中的人生回忆。也许正是与关注对象保持了一定的审美距离,才能将自己的所思所感更为真切地投射到景物之中。
昼寝行为的时间往往发生在一天中的上午及午后,诗人或因醉酒,或因午后小憩,将本应清醒应对俗务的白天作为自己的眠寝时间并写诗记录。宋代的文人昼寝诗借助昼眠时睡与醒之间的关系强烈表达了对于理想生活的追寻,可称之为是短时间内对于世俗事务的超越性情怀。
一年之中,昼寝是四季皆宜的事,诗作中对昼寝行为的记述却多集中在春季,夏季次之。春日昼寝诗如刘兼《昼寝》、张玉孃《昼寝》、张耒《和晁十七昼眠》、张嵲《春词二首》、苏舜钦《春睡》,皆是对春日美景下安眠的闲适描写。蔡襄《阁下昼眠》、陆游《初夏昼眠》等夏季昼眠诗多是对雨后暑热褪去昼眠行为的记述。
昼寝行为的发生时间,无论是一天时间中的上午及午后,还是四季中的春夏两季,都处在一段时间轴的前半段。“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便说明了中国古代对一个时间段起始的重视。对特定时间与季节的选择,令昼寝诗境的铺展体现出独具特色的审美趣味,同时也说明此时期士人的昼寝行为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
四、结语
因为昼寝题材的发展,众多与昼寝相关联的意象使用的频率也大大增加了,例如:“日高眠”“高卧”“卧看”等。这些词汇的大量运用丰富了宋诗的表达范围,为诗境的构建提供了“建筑材料”。
宋代昼寝诗的书写带入了宋代的“吏隐”风尚,加入了追求心灵自由的特点,构建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诗境,为后代诗歌提供了范本。金代“苏学盛于北”,诗人们在融合全真道思想下,使得昼寝题材中对睡与醒关系的思考经久不衰。元明清文学受唐宋文学影响也出现了很多关于昼寝的作品。
昼寝诗本身就是诗人选择性活动的产物,作者昼寝行为动机与诗歌内涵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对于昼寝诗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在探究诗人的内心情感世界。昼寝诗对理想与现实的调和,对睡与醒、隐与仕等关系的处理,不但展现了宋代诗歌对现实生活描写的一个重要的侧面,也体现着古代诗歌生活化方面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1]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高流水, 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77-178.
[2]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下册[M].逯钦立, 辑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940-1941.
[3] 郭茂倩. 乐府诗集: 第三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807.
[4] 陶渊明. 陶渊明集[M]. 逯钦立, 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88.
[5] 曹寅, 彭定求. 全唐诗[M].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765.
[6] 苏轼. 苏轼诗集[M]. 王文诰, 辑注. 孔凡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7] 苏轼. 苏文忠公诗集: 卷四〇[M]. 纪昀, 评. 韫玉山房刻本. 1869(清同治八年).
[8] 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 苏轼全集校注: 诗集[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4945.
[9]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0.15916/j.issn1674-327x.2022.03.018
I207
A
1674-327X (2022)03-0076-03
2021-10-10
艾迪(1996-),女,河北唐山人,硕士生。
(责任编辑:叶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