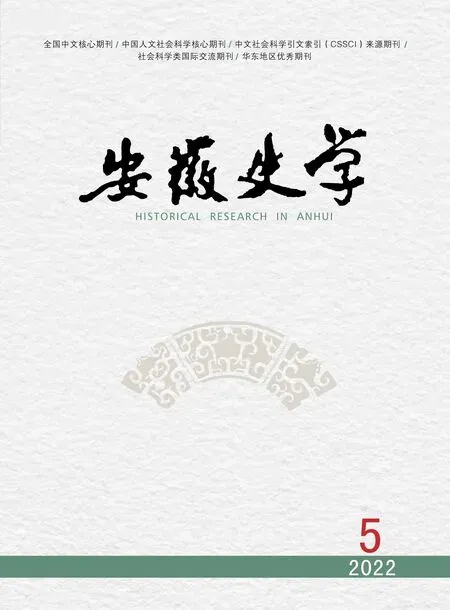“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2022-11-24周伟义李琳琦
周伟义 李琳琦
(1.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2.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明清时期的士商关系向为学界探讨的热点。研究者多认为,传统的士商关系在明清时期发生了一定的变动,具体表现为商业实践在价值观上被重新定义、士商界限渐渐模糊、商人地位在士商互动中的提高。(1)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后来的学者与余氏有着相同的研究理路,可参见夏咸淳:《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的关系》,《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郑利华:《士商关系嬗变:明代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高建立:《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精神的塑造》,《江汉论坛》2000年第1期;黄开军:《明清时期商贾墓志铭的书写与士商关系》,《学术研究》2019年第11期,等。已有研究多将商人视为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研究视角多为商人阶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但研究的史料基础,多为对商人心理变化的记载与士人对商人的肯定之语——这些材料几乎都是出自士人之手。并且,这些材料多为墓志铭、行状、寿序等,由于文体限制,其真实性自然也需要进一步深究。因此,本文拟转换视角,从士人出发,对明清时期的士商关系进行另一角度的思考,以期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贾名儒行”:商人自信的来源
徽商程季曾说过:“藉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2)汪道昆:《太函集》卷52《明故明威将军新安卫指挥佥事衡山程季公墓志铭》,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102页。这句话可以视为对明清商人自信心理的一种概括,具有类似内涵的言论在徽商有关文献中并不少见,徽州的《汪氏统宗谱》上亦有这样的记载:“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岩鱼盐中,良弼师保寓焉。贾何后于士哉!世远制殊,不特士贾分也,然士而贾其行,士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贾之不为士也。”(3)《汪氏统宗谱》卷168,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39页。“空同子曰:‘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于缝章而后为士也。”(4)《汪氏统宗谱》卷116,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0页。“空同子”是为李梦阳,“士商异术而同志”一语,则是李梦阳对商人之语的转述。其语出自李氏所撰的《明故王文显墓志铭》:“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5)李梦阳:《空同集》卷46《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根据文章所述,传主王文显系山西蒲州商人。可见,晋商与徽商在与士人比较这一方面,具有相同的自信心理。在明清士人为商人撰写的文章中,这种表达商人自信心理的语句并不鲜见。余英时便以此认为:“‘良贾何负闳儒’‘贾何后于士’这样傲慢的话是以前的商人不敢想的,这些话充分地流露出商和士相竞争的强烈心理。”(6)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第459页。需要说明的是,“良贾何负闳儒”一语是汪道昆所发的议论,但该论述与上引商人话语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核。诚然,这些商人的言语话锋显露,直接表达着“欲与士人试比高”的意味。但我们不得不思考,商人这种自信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核心便是,商人们所要与士人竞争的内容是什么?换言之,商人的自信究竟源于何处?
对于这个问题,多数研究者延续了余英时的思路,理所当然地认为商人欲与士人竞争的是社会地位,因为商人已将自己与士人平等视之。(7)参见张明富:《论明清商人商业观的二重性》,《史学集刊》1999年第3期,等。然而,研究者们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商人”是人在社会实践中所拥有的多重身份之一,这种角色由职业所赋予,而职业,不过只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是构成人的本质要素之一,并非人的本质。因此,如果我们要讨论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问题,只有基于其职业所限定的商业实践维度才具有意义。那么,明清社会的商人对于单纯的商业实践又是否具有自信呢?
弃儒就贾的凌珊“恒自恨不卒为儒”;(8)凌应秋:《沙溪集略》卷4《文行》,《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73页。洪庭梅以经商发家后,虽“今庶几惟所欲为,奚仆仆风尘坐以商贾自秽”。(9)婺源《燉煌洪氏通宗谱》卷58《清华雪斋公传》,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84页。商人吴烈夫晚年则叹道:“商贾末业,君子所耻,耆耄贪得,先圣所戒。”(10)民国《丰南志》卷6《艺文志下·存节公状》,《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7册,第373页。亦有商人对后代教导道“毋效贾竖子为也。”(11)汪道昆:《太函集》卷67《明赠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司署员外郎事主事江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第1386页。可见,商业实践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转换为商人自信的资本,他们对自己商业实践者的角色仍旧自感卑微。这样的自卑,其实与上文所引商人自信言论在本质上如出一辙。正如已有研究所揭示的,这些商人在士商比较中所赖以立论的根据“仍然是儒家的理念,他们对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还依然是以传统的‘士’‘农’为其参照系。”(12)李琳琦:《传统文化与徽商心理变迁》,《学术月刊》1999年第10期。商人得以与士人进行比较,离不开对“士君子之行”“高明之行”等儒家理念的修持。“大凡取得商业成功的徽商几乎都以诚信为本……大凡以利以义制,非义之财不取为圭臬者,都往往取得商业的成功”(13)叶显恩:《论徽商文化》,《江淮论坛》2016年第1期。,实践证明,这些所谓“士君子之行”中所蕴含的道德要素,并不为士人们所独占,亦是商业成功的条件。但从上文所引可见,在明清商人的认识里,这些能够赋予商人自信的道德要素并不存在于商业实践之中。也即是说,这些自信的商人并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可见,商人在与士人竞争中,真正自信的是“儒行”——对儒家伦理等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贾名”。也正因此,“士君子之行”“高明之行”是商人与士人进行比较所不可或缺的前提。
洪亮吉《更生斋集》中有一则关于士商交往的记载,经常被研究者用以讨论商人的自信心理:
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中愤极,从石狻猊下,潜往拍商人项。商人大惊回顾,中大声曰:“汝识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识。”曰:“识向之趋揖者乎?”商人曰:“亦不识也。”即告之曰:“我为汪先生,趋揖者为某先生,汝后识之乎?”曰:“识之矣。”中曰:“汝识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惊,然度不能奈何,丧气以去。(14)洪亮吉:《更生斋集·文甲集》卷4《又书三友人遗事》,《续修四库全书》第14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余英时将此记载中肄业生的态度作为捐纳制度使商人在地方上成为有势力绅商的证据,以此说明明清时期士商关系所发生的新变化。(15)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第464页。一些研究者对此也有相同的解读,如范金民认为:“商人高傲,贱视劣生,于此可见。”(16)范金民:《科第冠海内 人文甲天下:明清江南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页。唐力行认为:“商人用金钱买得了官职,也就买得了受尊敬的社会地位和声誉。”(17)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页高建立认为:“富有商人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18)高建立:《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精神的塑造》,《江汉论坛》2000年第1期。但是,以上分析均到“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为止,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从整段材料来看,士人在与商人的交往中,其实出现了两种态度——肄业生的谄媚阿附与汪中的冷面鄙夷,商人也对应出现了倨傲与丧气。肄业生对商人的恭谨显然并非是震慑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否则便无法解释汪中的公然鄙夷。此事发生的时间为乾隆三十九年,汪中并未承担任何行政职务。商人虽然并不知晓汪中身份,但从其表现来看,也并不认为汪中身居官职,只是将其当作与肄业生一般的普通士人。面对普通士人的直言呵斥,“三品章服”的商人尚觉得“无可奈何”,可见,面对真正的士人,捐纳来的官衔所赋予的另一种身份,并没有为这位商人带来社会地位上的自信。就此而言,商人先前的倨傲态度自然并非自身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底气,而是对士人谄媚态度的回应。因此,这则材料并不能有力地证明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怎样的提高,但却能够充分地说明,商人与士人的交往模式是动态的,在这种交往模式中,士人才是主动因素,商人所做的其实只是被动的回应。换言之,士人才是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不过是因变量。商人的倨傲态度真正揭示的,其实是部分士人在与商人的交往中已经“降尊纡贵”,斯文尽失。
士人在实践中的“斯文尽失”,自然为商人践行士人之道的自信提供了前提。因此,商人借以比较的士人,并非理想中士人之道的真正践行者。上文提及的王文显,对比的是“名以清修”的士人。“名以清修”并非褒义,因为早有商人意识到“儒者直孳孳为名高,名亦利也”(19)汪道昆:《太函集》卷54《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第1143页。,所指的是那些在熙攘世间追逐利益的士人。徽商汪弘也常自语:“虽终日营营,于公私有济,岂不犹愈于虚舟悠荡,蜉蝣楚羽者哉!”(20)《汪氏统宗谱》卷116,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0页。将那些“纵情山水,无所事事的儒士”(21)李琳琦:《传统文化与徽商心理变迁》,《学术月刊》1999年第10期。作为自比对象。
正因为士人才是士商交往中的自变量,明清时期商人以“贾名儒行”所展现的自信心理并不基于对商业实践的价值重赋,而是基于对士人之道的实践成效。因此,这并不能够表示商人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动,但其潜台词——“士人对士人之道的实践未必做的有商人好”,却足以说明,明清士人的社会实践,已经使商人开始对士人进行“德不配位”的质疑。
二、自我祛魅:士人对商人的肯定
明清士人在为商人撰文时,也多有对商人的赞扬之辞、关于士商平等的阐述,这些多被作为讨论明清士商关系的重要论据。但是,受限于文体特性,这些文字大多不能表达作者的真实思想,自然也不能如实反映士商关系的真实面貌。
清人沈垚曾作《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对商人进行赞颂,谓:“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22)沈壵:《落帆楼文集》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民国吴兴丛书本。认为商人值得被称颂的原因之一即是商人已经摒弃了“纤啬”的品质。这番论述经常被研究者引用,但此论述并非作者思想的真实表述。他在给友人丁子香的信中曾言道:“治生者,既非如商贾之纤啬,亦非如土豪之武断。”(23)沈壵:《落帆楼文集》卷10《与丁子香》。认为“纤啬”恰好是商人所具有的特质。寿序多为溢美之词,信件更能反映作者的真实思想。就此而言,沈垚对商人所谓“转敦古谊”的肯定之语不过是虚言逢迎,并非出自真心。对于具有“纤啬”特质的商人,其内心仍旧鄙夷。
上文所述的李梦阳亦复如是,虽然他曾为商人撰文谀墓,但仍在道德上鄙视商人。甚至曾撰《贾道》一文,专论商人是“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24)李梦阳:《空同集》卷59《贾论》,第538页。之辈,对商业实践直接做了道德上的否定。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文章开头,李梦阳直言:“语人曰:‘贾之术恶’,人必以为谬。”但这只是李梦阳为抒发议论所假设的场景,并未亲身实践,也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与李梦阳同时期的唐寅便曾以诗言志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兴来只写江山卖,免受人间作业钱。”(25)唐寅著,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伯虎全集》补辑卷第4《题画(一百一十三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唐寅出身于商贾家庭,也以卖文鬻画的形式进行了商业实践。尽管在客观上,唐寅已经成为了商业的实践者,但他在主观上,却依旧选择与商人划清界限,认为商人经商是“作业钱”的一个来路,作为士人的卖画行为比商人的商业实践更具备道德上的完满性。这种“孔乙己”式的骄傲,更能反映出士人对单纯商业实践的轻蔑。因此,我们并不能依据李梦阳所预设的语境,认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对商业实践具有与其不同的道德价值判断。
由于对商人多有肯定之语,又出身于商人家庭,汪道昆一向被学界视为“徽商的代言人”,他的言论,则未必是违心的谀颂之辞。在一篇为商人所撰的墓志铭中,他曾言道:“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26)汪道昆:《太函集》卷55《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第1146页。,以表达对商人的赞颂。但是,这种赞颂同样脱离商业实践。梁仁志认为,“良贾何负闳儒”是“表达商人在躬行‘儒行’方面做得不一定比士人差之意”。(27)梁仁志:《“良贾何负闳儒”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新论》,《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因此,这种赞颂其实与商人的自信基于同样的逻辑,乃是对商人践行士人之道的肯定。因此,汪氏曾以“司马氏”为名言道:“儒者以诗书为本业,视货殖辄卑之。藉令服贾而仁义存焉,贾何负也!”(28)汪道昆:《太函集》卷29《范长君传》,第638页。认为商业实践在先天上便缺失了“仁”“义”等道德因素。更直言“彼行贾,贱业耳”(29)汪道昆:《太函集》卷28《汪处士传》,第604页。,对商业实践直接表示鄙夷。
汪道昆曾有一个经典的命题——“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30)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第1099页。在汪氏为商人所撰的文章中,“名高”一词也几乎成为“儒”的代名词。“贾为厚利”是理所当然,由于汪氏鄙视商业实践,自然并非褒扬之辞。同理,“儒为名高”也并非士人分所应当。汪氏曾言道:“世之命儒者二,其一道德,其一文辞。当世并訾之,訾其户说长而躬行短也。”(31)汪道昆:《太函集》卷16《鄣语》,第330页。可见,他认为儒家士人的使命应为道德的修养与文辞的琢磨,所谓的“儒为名高”实际上是士人在实践中“不务正业”,即所谓“躬行短也”。因此,在汪氏的思想中,“儒为名高”实为对士人的贬抑之辞。他更曾直接批判道:“当世所取重者,非讲学则建言,抑或藉为名高,本实蠧矣!”(32)汪道昆:《太函集》卷36《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陆季公传》,第781页。认为追求“名高”其实是士人实践的蠹蚀之行。由此而言,汪氏对商人的肯定语境,实际建立在士人对士人之道短于躬行的前提之上。恰好与上文所论商人自信心理的前提如出一辙。
汪道昆并非第一个真心认为士商平等的人,学界一般将士商平等的思想源头追溯至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中的论述,即所谓“新四民论”,兹引如下: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33)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3册卷25外集7《节庵方公墓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86页。
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段材料对商人价值的肯定是一个新的命题。(34)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第456页。但这种认识其实值得商榷,因为历代“抑商思想的倡导者,对商业的社会功能都有清醒的认识”(35)阎守诚:《重农抑商试析》,《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阳明所肯定的“商以通货”,并不为前代士人否定。士人们所否定的,其实是商业实践过程中,因为追求营利所导致的道德缺失。对于营利,王阳明曾言:“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36)王阳明撰、[日]佐藤一斋注评、黎业明点校:《传习录》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45页。尽管诸多研究者都将此论述作为王阳明对商人进行新的价值审视的证据,但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此论述中,营利一事仍是以圣贤之道对立面的形象出现。而商业的本质,即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此,作为“生人之道”——单纯以通货为目的的商业,在实践上根本不可能存在。(37)在明清时期的很多史料中,士人们对商业所发表的肯定言论都与之有着相同的逻辑,所肯定的并非是现实中的商业实践,而是一种脱离实践只存在于概念中的“商业”。这样的言论不应看作是对商业实践的重新认识,而应视为对商业实践的理论构想。并且,这种理论构想是否能称之为“商业”也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由于这种言论多出现于墓志铭、行状等功能性文体中,其真实性也值得进一步推敲。因此,即使在理论上,可以“四民异业而同道”“满街都是圣人”,但若落之实践,王阳明显然并不认为实践中的商人真的与士人同道,能够真正成为圣人。因此,这一段对“旧四民论”的理论反思,并不代表王阳明对商业实践的价值重赋。但是,如果转换视角,我们却可以发现从“旧四民论”到“新四民论”中所蕴含的对士人阶层的重新认识。
“新四民论”之所以认为四民平等,是因为四民之业同为“生人之道”。在“新四民论”之前,士人的修治工夫是以明明德为修持目标的“大学之道”。(38)王国轩译注:《大学 中庸》,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页。当“修治”从“大学之道”沦为“生人之道”,士人之道的神圣性与道德性在理论上被消解,士人在理论维度被祛魅;另一方面,“新四民论”又为“旧四民论”的士人加之了“王道熄而学术乖”“射时罔利”的道德批判,实现了对士人在道统与道德维度的否定。由此可见,“新四民论”所谓的四民平等背后,其实是士人阶层的自我祛魅与自我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研究者们多以“新四民论”作为明清士商关系变动的一大表现,但“新四民论”本身并不具备讨论明清社会士商关系的功能,因为该理论并未在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与理解——否则无需详尽阐释。若以此来讨论士商关系,则会难免以点概面,忽略对社会整体的感知。
在墓志铭等文体之外,并不乏士人对商业实践的肯定,但这些肯定往往与对士人的批判相伴而生。黄宗羲便曾以“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39)黄宗羲撰、李伟译注:《明夷待访录·财记三》,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202页。来论述“工商皆本”,将工商与农相提并重,对“世儒”进行批判,但并未将士与其他三民等同。陈龙正曾言:“农工商贾,各有所为。既自食其力,亦有造于世。惟士不为劳力之事,以其劳心耳。今若悠悠泄泄、饮食嬉戏,与鸟兽何异?士本贵于四民之上,而不知所用心,则反贱于四民之下。其自喜贵于民者,形骸也,隐然实贱于民者,行事也。心事也愧哉!”(40)陈龙正:《几亭外书》卷2《士反自贱于民》,《续修四库全书》第1133册,第277页。此处以肯定其他三民的“各有所为”批判士人的“不知用心”,显然仍承认理论上士在四民之首的地位。可见,这些对于商业实践的肯定,无意于构建四民平等的新秩序,真正的目的是对士人阶层进行自我批判。
由于“士人赞扬的并不是商人这一群体,而是亡者身上所具备的某些高尚特质”(41)谷梦月、梁仁志:《明清士商关系嬗变新论——兼论商人墓志铭的史料价值》,《黄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他们对商业实践或商人的肯定便不足以表示传统的四民观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虽然士人有关商人的论述无法揭示出商人社会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动,但却足以证明,士人阶层在此时已经开始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三、“士风日下”:对士人的质疑
商人对士人的质疑并非空穴而来,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42)孟轲撰、金良年译注:《孟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在理论上,士人比普通民众具备更高的道德修养,只有士人能在金钱与个人意志的矛盾中保持个人意志的完整,在道德上建构了士人阶层相对超然的地位。明清理学则对士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但此时士商交往的实况显示这种道德沦为了一纸空谈,成为了商人质疑的实践来源。除了上文所引部分士人的躬身结交,明代开始,文学创作商品化已非常普遍(43)张世敏:《论明代文学商品化与碑传风格的融合》,《华中学术》2015年第2期。,这正是士商交往愈加密切的一大表现。“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44)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续笔》卷6《文字润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6页。润笔作文,前代既有,但这种行为一向受到非议。一代大儒韩愈,即因生前替人广作墓志文而得“谀墓”之名,为后世诟病。(45)宋佳霖:《唐代“润笔”盛行的社会原因》,《乾陵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为商人大量写碑传、寿序,则是明代出现的新现象。(46)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士与中国文化》,第535页。尽管明清士人时有对商人的赞颂,但并非出于真心。唐顺之即曾对友人王慎中感叹:“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47)唐顺之著,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上册卷6《答王遵岩》,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唐氏以“屠沽细人”称之商人,可见对其轻视,然而,其文集中却不乏为商人所撰的应酬文章。可见,他的赞颂之语不过是在利益驱使下的违心行为。事实上,正如陆容所言:“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亦必夤缘所交,投贽求挽。受其贽者,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48)陆容撰、佚之点校:《菽园杂记》卷1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9页。士人为商人撰文,不过是单纯的金钱交易,有些执笔者甚至直接将其称为“利市”。(49)李诩:《文士润笔》,倪进选注:《元明笔记选注》上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51页。可见,在润笔费的主导下,士人文章已经失去了先贤所谓“文以载道”的功能,沦为了可以违心曲笔借以谋利的工具。
在润笔费面前,明清社会已是“文士无不重财者”。(50)李诩:《文士润笔》,倪进选注:《元明笔记选注》上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51页。那么,士人的违心曲笔,又是所为何求?财富的意义来源于其一般等价物的属性,因此,若要究其缘由,则需要从钱财的去向中去寻找。士人卖文所得的润笔费,大多流向了奢侈性的消费。李开先曾说:“崆峒(即李梦阳)虽四次下吏,而晚景富贵骄奢,以其据纷华之地,而多卖文之钱耳。传据素闻,或不得其真。”(51)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中麓闲居集》之十《李崆峒传》,《李开先全集》(修订本)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31页。可见,润笔作文已成为李梦阳骄奢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但讽刺的是,生活骄奢恰恰是其抨击“贾之术恶”的理由之一。(52)李梦阳:《空同集》卷59《贾论》,第538页。虽然李梦阳以卖文供给奢侈生活之事无法以传闻判断真假,但润笔费流向奢侈消费在社会实践中并不鲜见。纵情诗酒、追求享乐的屠隆亦是“卖文为活”。(53)《明史》卷288《文苑传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8页。
润笔费不过是士人取财方式之一,从其流向来看,士人与商人交往的一大动因便是为了满足自身奢侈享乐的欲望。《两淮盐法录要序》云:“乾隆盛时,扬州盐商供巡典、办年贡而外,名园巨第络绎至于平山,歌童舞女、图画金石、衣服肴馔,日所费以巨万计。……在京之缙绅,往来之名士,无不结纳。”(54)盛旻:《意园文略》卷1《两淮盐法录要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页。“为了迎合文人名士的品性,徽商又往往招徕歌妓戏班,陪酒吟唱,极尽放荡豪侈。”(55)李琳琦:《徽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心理探析》,《历史档案》1995年第4期。除直接的金钱交易外,奢侈享乐也是士商交往过程中难以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明清时期,通婚也是士人与商人之间的重要桥梁(56)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士与中国文化》,第534页。,但正如徐阶所云:“欲观士大夫名节,但不联姻富室,不接袵山人,便是端庄之士。”(57)徐树丕:《识小录》,江畲经编辑:《历代小说笔记选·明》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页。这个重要桥梁的构造过程在士人看来,也是与名节逐渐背离的进程。无论是在商人“恒产”面前的违心润笔还是躬身交结,都是财富对士人的一种异化,商人作为这种异化的始作俑者,亲眼见证了士人在“无恒产”状态下失去“恒心”。同时,商人“恒产者”的身份,又足以让他们保持“恒心”,这自然使得商人开始产生对践行士人之道的自信,从而进一步开始质疑士人是否真的“德以配位”。
财富的异化功能不仅体现在士人与商人的交往中,同时也体现在士人的“正业”中。因此,这种异化不仅为商人所体味,也为士人所捕捉。王阳明便谓:“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58)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册卷4《与黄诚甫》,第174页。徐有贞亦有言:“古之士为道德,不为功名,不为富贵,今则或惟富贵之为而已。为乎道德而功名在其中,为乎功名而富贵在其中,为乎富贵则出乎道德功名之外矣。”(59)徐有贞著、孙宝点校:《徐有贞集》下册附录《常熟县学兴修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687—688页。可见,士人所必由的科举之路以及所追求的道德修行也被认为已经异化为财富的附庸。王廷相曾言:“由今观之,岂直民间四维丧失?为之士大夫者,刻忍而不仁,淫荡而蔑德,贪利而忘义,骄横而犯礼,鄙陋之风,肆行于上,机巧剽劫,尤甚于民,恬然安之,不以为异。”(60)王廷相:《雅述》上篇,李敖主编:《陈献章集 王阳明集 王廷相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95页。将财富对人的异化视为与“义”的背离,并且认为,这种背离不会孤立存在,只不过是“四维丧失”的表征之一。而士人对此的“不以为异”,则更说明士人“异化”的普遍性。正所谓“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61)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1册,台北里仁书局2017年版,第1页。在时人的经验中,追求财富的最终导向是对欲望享乐的举手投降。这显然与理学阐释的士人之道——“存天理,灭人欲”,背道而驰,自然将得到正统士人的批判。
在正统士人的眼中,士人对于财富与享乐的追求,完全可以“士风日下”一言概之。明代的余珊即曾向嘉靖皇帝上疏痛陈时弊,他认为由于刘瑾等奸佞当道,从正德年间开始,“风俗波荡,无复士气矣”。(62)余珊:《陈言时政十渐疏》,汪少泉辑:《皇明奏疏类钞》卷5,《四库禁毁书丛刊》第20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其实早在弘治五年,蔡清便在奏疏中提到“数十年来,上下玩安忽危,纪纲日以废弛,纪纲日废,则士风日弊。”(63)蔡清著,张吉昌、廖渊泉点校:《蔡文庄公集》卷1《管见上堂尊》,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8页。二者的论述都指向了一个历史事实——即明代士大夫精神的堕落。(64)陈宝良:《从士风变迁看明代士大夫精神史的内在转向》,《故宫学刊》2013年第1期。这种堕落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挽回,类似“今日之士气日衰、士风日下”(65)曹禾:《重修江阴县督学察院记》,卢文弨:《常郡八邑艺文志》卷4上,清光绪十六年刻本。,“士趋日卑,士风日坏”(66)李颙:《二曲集》卷34《泰伯篇》,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64页。的论述在清代文献中依然多见。梳理文献发现,具有和“士风日下”类似含义的批判,早在南宋时期便已出现。(67)以“士风”或“士气”为关键词,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进行检索,具有“士风日下”含义的最早论述来自南宋蔡戡的《定斋集》。由于数据库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简单断言这种论述自南宋开始,但并不难推定,南宋之后这种论述出现的频率大于前代。这种现象颇堪玩味,有待进一步研究。批判者们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士风日下”的开始阶段。“士风日下”类论述的实质,是对多数士人违背士人之道的批判。因此,这些批判足以很好地说明,违背“士人之道”的士人实践并非自明代而起。
正如上文所述,“士风日下”是商人对于自己践行士人之道自信的基础之一,因此,商人“贾不负儒”自信或许也并非始于明代。由于资料的缺乏,尚不能对此做出明确的判断,但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在明清时期,商人对于士人的质疑已经是一种可以公开表达的心理。宋仪望曾言:“今为儒学者必诎商,为商者亦多訾儒,固其所见者异耳。”(68)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9《南山居士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84页。商人已可以公开对士人进行质疑与訾毁,并能够得到士人的理解与同情。显然,明清时期,对士人原有道德超越性的信仰已遭遇很大程度的消解。
这种消解一方面来源于王阳明一脉学说对士人的祛魅;另一方面,则来自被批判的“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69)张瀚:《松窗梦语》卷7《风俗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的社会环境。正如上文所述,明清“士风日下”的社会环境遭到了正统士人的强烈批判,但单纯的“士风日下”并不足以导致士人道德超越性的消解,因为这些士人或许在实践上是士人之道的切实笃行者,他们完全可以以自身的实践作为道德标杆,建立起士人道德超越性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在明清时期,这道防线业已崩溃——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士人的道德标准具有在实践上实现的可能。
部分被批判为“士风日下”的士人为欲望进行了重新赋值,对欲望享乐在理论上的合理性进行了阐释,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纵欲思潮,“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来对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规范”。(70)成淑君、张献忠:《晚明纵欲主义社会思潮的历史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但是,这些士人在后期,往往走向了自己思想的反面——多进行了禁欲的尝试。这些尝试常常以失败告终,又促使他们开始对传统伦理进行现实性的反思。禁欲失败的屠隆便曾言:“即圣人不能离欲,亦淡之而已。”(71)屠隆:《白榆集》文集卷9《与李观察》,《屠隆案》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394页。认为即便是圣人也不能消灭欲望。宋楙澄亦曾言:“人若未死,惟病可以寡欲”(72)宋楙澄:《与陈二》,谭邦和主编:《历代小品尺牍》,崇文书局1987年版,第387页。,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无法通过主观意志的克制而实现。这种从实践角度出发对欲望的认识与判断,自然将使人们进一步质疑:站在道德高地的正统士人是否真的能够言行如一?
颜元便曾谓:“口言圣贤之言,身冒圣贤之行,而屋漏或有放肆之心,对妻孥或有淫僻之态者,真人妖也。”(73)钟錂编:《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刁过之第十九》,颜元:《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2页。屋漏之事难证其实,但其仍然认为这些正统士人未必不是言行不一的“人妖”行径,可见,明清社会对士人不仅不“听其言而信其行”,也不去“听其言而观其行”。王源曾批判道:“天下无事不伪,而理学尤甚,今所号为儒者类,皆言伪行污,不足起人意。”(74)王源:《居业堂文集》卷7《与李中孚先生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4册,第63页。可见,士人群体已经被建构为一种“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虚伪形象。也正因此,“假道学”成为了攻讦士人的常用武器。张履祥便曾言:“虽穷乡妇女、三尺童竖,熟于口,惯于耳,见夫人一言一行稍异流俗也,遂以假道学为诮诋。一人始之,众人相与和之,咸指而名以假云假云。曾不问其人之躬行操履,与夫存心学术之果何如。概将推而内之假之之中,于是朝廷之上、乡曲之间,尽以是为攻正人之矛帜,而空善类之坑阱矣。”(75)张履祥:《假道学说》,张天杰等选注:《张履祥诗文选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即便士人真的独善其身,言行如一,也难免得到“假”的攻讦。更曾有人言道:“彼耗心力于举业者,其于人世嗜欲,以何分别而独得美名也乎?”(76)谭元春著、陈杏珍点校:《谭元春集》下册卷23《金正希文稿序》,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493页。认为士人的“正业”与其所批判的行为并无二致,其内核都是对于欲望的竞逐。就此而言,士人的寒窗苦读,自然也不再能够超然其他三民。由此可见,明清士人的行为与道德的关联开始松绑,至少在道德维度,士人已经降格。
结 语
由于没有对于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明清商人“士商异术而同志”“贾何负于儒”的自信,并不能解读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明清商人与士人的比较,并不是以社会地位为内容,而是以对士人之道的实践为标的。这种逻辑表明,商人们已经开始对士人践行伦理道德的实效进行质疑。
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之语,大多并非出自真心,而是在利益之下的违心谀辞,这些言论因此不能直接用以讨论士商关系。即便是士人对于商人的真心肯定,也应加以逻辑与实践层面的分析。“新四民论”虽然将四民同等待之,却不能说明士人对商业实践进行了重新赋值,因为该理论所肯定的商业实践功能,并不为前代轻视商人的士人所否定,他们所肯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是否能称之为“商业”也有待探讨。由于尚需阐释,“新四民论”在先天上便存在讨论明清社会士商关系的缺陷。但明清社会对商人的肯定多以与士人的比较为手段,其中所蕴含的底层逻辑,则是对士人阶层本身的反思与批判。
这种反思与批判源于财富对士人的异化,财富的异化离不开与欲望的绑定,自然得到正统士人的批判。但由于纵欲的士人多有禁欲失败的经验,人们开始质疑士人之道是否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在这种质疑下,士人之道的现实性已经在观念中破产,无论士人是否言行如一,都将得到“假道学”的评价,新的道德标杆因此无法树立起来。这表明,明清时期士人在道德维度上已经降格,其道德超越性业已消解,这也成为商人得以质疑士人的前提之一。由于士人对自身阶层的批判与商人的质疑具有同样的实践来源,在社会实践中,士人才是明清社会士商交往中的自变量。因此,对士人阶层变动的分析才应是探讨明清士商关系的首要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