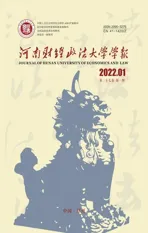处理具体打击错误的新路径
2022-11-24康子豪
康子豪
(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打击错误案件都是极具争议的问题(1)打击错误包括了具体的打击错误与抽象的打击错误。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具体的打击错误。因此,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称的“打击错误”均是指具体的打击错误。。甚至可以认为,刑法中的事实错误论就是围绕着如何处理打击错误问题展开的[1]。我国司法实务通说采取了法定符合说,但也不乏采纳具体符合说的判决。譬如,在乔某伤害案中,乔某与陈某等人发生冲突,在争执过程中,误伤了朋友董某,致其轻伤。法院认为,乔某发生了打击错误,对于造成董某轻伤仅具有过失(2)参见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法院( 2016) 皖1003 刑初58 号刑事判决书。。实务中的争议案件也引起了学界的兴趣。譬如,围绕着吴某杀妻案(3)在得知妻子徐某又与黄某进行不正当男女关系后,吴某携带匕首找黄某理论。双方发生争执,吴某愤怒之下即拔出匕首威胁黄某“戳死你”,并用力戳向黄某,徐某见状上前意欲阻止吴某,结果吴某手中的匕首刺进徐某左胸部,导致其死亡。在本案中,法院倾向于采取具体符合说的观点。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 2003 年第1 辑)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年版,第18-23 页。,学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4)采取法定符合说的意见,参见倪培兴《对象错误条件下犯罪既遂的认定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 年第4 期,第103-111 页。采取具体符合说的见解,参见陈洪兵《刑法错误论的实质》,《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4 期,第18 页。。
当前学界主流意见认为,解决打击错误问题的关键是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实际情况在规范意义上是否相符,即符合说[2]。根据对符合程度的要求不同,理论上存在着法定符合说与具体符合说的对立[3]。近来,受德国理论观点的影响,有见解批判主流意见仅止于效果的比对,未能真正揭示打击错误的本质问题。考察打击错误的发生机理,解决打击错误问题的关键是判断行为人最初创设的危险是否发生了实质偏离,即危险实质偏离说[4]。然而,前述观点均存在不足之处。危险实质偏离说存在着以客观归责代替主观归责的嫌疑,而符合说则可能在个案中得出不合理的结论。
基于此,本文将在评析传统路径的基础上,探寻合理解决打击错误案件的新方案。
二、对传统路径的检视之一:危险实质偏离说的缺陷
在危险实质偏离说下,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诠释路径。
( 一) 故意危险理论
故意危险理论主张,故意危险与过失危险之间具有质的差别。就如何区分故意危险与过失危险,理论上又存在着客观说与主观说两种不同的见解。
1.客观说。客观说认为,过失危险实质上就是不被容许的危险。与之相对,只有根据实践理性某一行为是客观上能够有效地引起结果的方法,该行为才具有故意危险。如果按照理性一般人的标准,行为人是有意识地创设故意危险,并且该危险在结果中实现,就可以将该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故意。具体到打击错误的场合,由于行为人往往采取的是根据实践理性能够有效地引起结果的方法,并且他对此也有认识,故解决打击错误问题的关键就是,判断行为人所创设的故意危险是否在结果中实现。如果结果中实现的是故意危险,则打击错误不排除故意归责;反之,打击错误阻却故意归责[5]。该见解存在如下问题。一方面,客观说存在混淆客观归责与主观归责的嫌疑[6]。结果中实现了故意危险,仅意
味着可以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而不意味着行为人是故意地引起该结果。譬如,甲曾受过特技驾驶训练,对自己的车技深信不疑,为向朋友炫耀,违反渡口的规定,不经跳板直接从岸边“飞车上船”时造成渡船倾覆。在这一场合,根据客观说,结果中实现的是行为人有意识地创设的危险,甲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导致轮船倾覆的危险,甲对于轮船倾覆具有故意;但是,甲只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轻信可以避免结果,其对于结果仅具有过于自信的过失。另一方面,客观说在本质上属于概然性说,在个案中会遇到与概然性说一样的困境[7]。其一,在个案中如何查明概然性存在问题。譬如,客观说主张,如果因打击错误击中的是一个站得比较远的人,结果中实现的就不是故意危险,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死亡不具有故意[8]。但是,被害人究竟站得多远才能说缺少被击中的概然性并不明确。其二,当行为人认识到结果发生的概率达到多大时,才能说他具有故意,也并不明确。该理论希望借助理性一般人的判断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理性一般人的判断也一定是以概率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因此,其仍没有为故意的判断提供明确的标准。
2.主观说。主观说认为,故意行为是具有目的性思维的活动,对危险流的发展具有目的性指引,所以危险流的发展具有方向性。相反,过失行为具有任意性,这导致危险流的发展具有盲目性。因此,在甲原本想杀A,因打击错误杀B 的场合,甲实施的杀人行为中就蕴含着故意杀害A 的危险和过失致人死亡的危险。B 的死亡不是故意杀害A 的危险的实现,而是过失致人死亡的危险的实现[9]。尽管相比于客观说,主观说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判断标准,但该见解也并非没有问题。首先,如果认为,在打击错误的场合,甲的杀害行为中本身就包括了故意危险和过失危险,B 的死亡是过失危险的实现,那么甲所创设的过失危险就并未发生实质偏离地在结果中实现。这显然不符合该观点对打击错误问题的本质的理解。其次,主观说不过是对已知的处理结论的重复说明。只有当我们已经认定甲对A 的死亡是故意的,对B 的死亡是过失的,才能说甲对A 创设的危险的实现具有目的性指引,对B 创设的危险的实现具有盲目性。但是,在打击错误的场合,我们事前并不知晓是否能够在规范意义上认定甲对B 的死亡具有故意,需要判断的也正是B 的死亡可否被看作是甲所创设的危险的目的性实现。最后,主观说也存在着混淆客观归责与主观归责的危险,因为主观说建立在不区分客观归责与主观归责的见解之上[10]。这就使得对打击错误是否阻却故意归责的判断与能否进行客观归责的判断混杂在一起,极容易出现以客观归责取代主观归责的问题。
( 二) 预见可能性理论
预见可能性理论主张区分故意认定与故意归责。在打击错误的场合,行为人对于意图侵害的对象具有故意。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能否将实际发生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业已成立的故意。对此,该理论所提出的标准是,行为人是否能够认识到结果会发生在实际侵害的对象上。如果能够预见,则打击错误不排除故意归责;反之,则排除故意归责[11]。有学者通过区分主观恣意与实践认知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判断标准。譬如,在甲于50 米外向正与丙聊天的乙开枪,造成丙死亡的场合,甲对乙的特定化就属于主观恣意,不影响故意归责;相反,甲对“乙和丙靠得很近”和“远距离射击”的认识属于实践认知。如果甲的实践认知足以说明他可以预见到自己对丙的生命创设了不被容许的危险,就可以将丙的死亡归责于甲的犯罪故意。
预见可能性理论所面临的最大的批判是,该理论使故意归责的判断取决于一个过失犯的判断要素( 预见可能性) ,有混淆故意与过失的嫌疑。针对这一批判,持该观点的学者做了如下回应: 第一,故意与过失之间存在位阶关系,预见可能性是故意与过失共同的要素;第二,在打击错误的场合,为了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有必要将行为人能够预见的结果归责于他的犯罪故意;第三,打击错误与纯粹的过失犯在构造上存在差异;第四,预见可能性理论没有加重行为人的罪责[12];第五,故意与过失的作用仅在于说明遵法动机的强弱,从而区分行为人不法内涵的高低,并不会影响能否进行主观归责。
然而,这些回应均不具有说服力。第一,预见可能性是故意与过失共同的要素,恰恰说明如果行为人对某一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他可能仅是过失地引起该结果,不能仅仅因行为人对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就认定他成立故意犯罪既遂。第二,在打击错误的场合,实现一般预防的最佳方式是,不论行为人是否能够预见到结果发生,只要行为人故意地实施了犯罪行为,就以犯罪既遂论处。第三,诚然与纯粹过失犯的情形相比,在打击错误的场合,行为人对意图侵害的对象具有故意,但是当他对该对象成立故意犯罪未遂后,其犯罪故意已经被“耗尽”,不可能再将实际发生的结果归责于这一故意。第四,持预见可能性理论的学者一边认为风险关联标准加重了行为人的罪责[13],另一边却又通过与风险关联标准进行比较得出自己的没有加重行为人的罪责的观点,缺乏说服力。第五,不法的判断仅涉及行为人的行为能力,罪责判断才会涉及行为人的动机能力[14]。而遵法动机要求行为人遵守规范,自觉形成对犯罪的反对动机,在本质上属于动机能力的范畴。因此,如果认为故意和过失的意义仅在于标示遵法动机,那么它们仅是罪责要素。但是,这与该学者对故意、过失的体系定位相矛盾。
此外,该理论在理论体系的融贯性方面也存在不足。一方面,该理论容易导致以客观归责代替主观归责的问题。无论是根据客观归责理论,还是折中的相当性因果关系说,只有因果流程的偏离并非不可预见,才能将实际发生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也才存在能否进行故意归责的问题。因此,如果将预见可能性作为能否故意归责的标准,由于这一判断并没有超出客观归责的一般要求[15],则只要能够进行客观归责,就可以认定行为人对实际发生的结果具有故意,导致故意归责的判断被虚化。另一方面,该理论无法合理解决正当化事由中的打击错误。譬如,在甲对乙实施正当防卫,误伤丙的场合,按该理论的论证逻辑,很容易得出甲对丙成立正当防卫的结论[16]。然而,甲对丙的“防卫行为”不会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或法秩序的维护产生任何积极作用,将之认定为正当防卫,并不合适。
三、对传统路径的检视之二:符合说的问题
在符合说内部,根据对符合程度的要求不同,存在着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下文将在确定两者实质争议的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 一) 法定符合说与具体符合说的实质争议
当前多数见解认为,法定符合说与具体符合说的实质争议在于如何理解刑法中的故意,即刑法中的故意究竟应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17]。其中,法定符合说主张抽象地和规范化地理解犯罪故意,而具体符合说则主张具体地和事实化地理解犯罪故意。但是,真正使得两者对犯罪故意产生不同理解的原因是,个案中它们对于客观构成要件的理解存在差异。
法定符合说主张:行为对象个别性与客观构成要件实现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以故意杀人罪为例,法律并没有将被杀害的对象限定为某一具体的人,而是包括了任何人。故意杀人罪的行为对象不会因具体案件而发生改变。相应地,只要行为人实际造成他人死亡,就实现了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构成要件[18]。由于故意是对构成要件的认识与意欲,故根据法定符合说,故意成立也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构成要件意义上的“人”,其所理解的犯罪故意必然是抽象的。
与之不同,具体符合说主张:所谓构成要件的行为对象不会随具体案件发生改变,是就记述在法律规定中的构成要件而言的,而不是说个案中的行为对象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刑法规范都是抽象的,要想将这些抽象的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必然要对规范做具体化理解。以故意杀人罪为例,故意杀人罪的规定是“杀了人”,但在实际适用该罪的构成要件时,却不是“凡是杀了人”这样抽象的形式,而是针对某个具体的被害人[19]。譬如,如果A 想射杀B,而C 劝说A 杀D,A 射杀了D。此时,C 无疑由于教唆他人实施了一个新的故意杀人行为而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倘若这里针对的是具体的被害人,那么在打击错误时,也理应如此[20]。因此,按照具体符合说,在判断客观构成要件是否实现时,必须要区分不同的行为对象分别进行判断。相应地,其所理解的故意也与具体的行为对象相联系,行为对象个别性对于故意归责的判断具有重要影响。
( 二) 法定符合说的缺陷
法定符合说对构成要件做抽象化理解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如果抽象地理解构成要件,将无法在并发案件中得出合理的结论。其中,一故意犯说面临着故意分配的难题[21]。为了避免出现不合理的结论,该说不得不自相矛盾地一边认为客观构成要件都是等价的,一边去寻找行为人意图实现的客观构成要件[22]。数故意犯说则存在着违反责任主义的嫌疑[23]。在行为人仅具有一个故意的情况下,该说认为行为人具有数个故意,不当地扩大了故意犯的成立范围[24]。正因如此,我国司法实务在并发案件中也并未采取法定符合说的见解。譬如,在余某使用铁锤击打谭某头部致其轻伤,同时击中李某致其重伤的场合,法院就认为,余某对李某的重伤结果不具有故意,仅成立过失致人重伤罪(5)参见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常刑一终字第34 号刑事判决书。。
其次,在个案中,犯罪行为总是指向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对象[25]。在打击错误的场合,从特定的时空条件看,行为人所欲侵害与实际侵害的“人”,并不是同一个“人”。此时,如果认定行为人属于故意犯罪既遂,难免给人一种“张冠李戴”的感觉。我国司法工作人员就正确地指出:“站在一般民众的立场来看,不论理论多么抽象和深奥,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行为人没有实现其预期的犯罪结果,而是出现其并不希望发生的危害结果,无论如何很难以故意的心态去评价。”[26]这一问题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时表现得更为明显(6)本文所指的特殊关系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紧密的邻里关系以及冲突中的本方成员。。正因如此,在乔某伤害案和吴某杀妻案中,法院才没有采取法定符合说的见解。不仅如此,即使是认定行为人构成故意犯罪既遂的案件,也很难说法官采纳了法定符合说的观点。一方面,在很多案件中,法官是通过认定行为人对实际造成的结果具有间接故意的方式,来论证行为人成立故意犯罪既遂(7)参见陕西省汉阴县人民法院( 2019) 陕0921 刑初20 号刑事判决书。。但是,当其认定行为人对实际发生的结果具有间接故意时,他就已经承认实际发生的结果是附随结果而非主要结果[27],不是行为人所追求的结果(8)当然,这种论证本身也存在问题。存在打击错误的前提是行为人对实际造成的结果不具有间接故意,否则,根本不存在打击错误的问题。。换言之,实际实现与意图实现的构成要件不是等价的。另一方面,有时法院认定行为人构成故意犯罪既遂不过是权宜之计。在这些案件中,行为人仅造成了轻伤结果,我国刑法不处罚过失轻伤的行为,为了满足被害人的处罚要求,法院不得不认定行为人成立故意伤害既遂。
最后,考虑打击错误案件的量刑情况,也应当承认行为对象个别性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从刑罚适用的角度讲,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时,法官对行为人的量刑明显更轻。在笔者收集到的55 份判决中(9)截至2021 年4 月30 日,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通过检索“打击错误”共获得判决76 份,排除其中重复和无关的判决,获得有效判决52 份,另外,通过查阅《人民法院案例选》和“中国法院网”获得判决3 份,共计55 份。,有20 份判决涉及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案件。在这些判决中,有10份判决对行为人适用了缓刑,占此类判决总数的50%;有2 份判决对行为人判处了管制,占此类判决总数的10%;有3 份判决对行为人免予刑事处罚,占此类判决总数的15%;有5 份判决对行为人判处了有期徒刑,并且未适用缓刑,占此类案件总数的25%。不过,在这些案件中,行为人均造成了死亡结果,并且法院最大限度地给予了行为人刑罚上的宽免。譬如,在吴振江误杀其父案中,法院尽管认定其构成故意杀人罪,但仅对其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 1992-1999 合订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年版,第360页。。与之相对,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特殊关系的案件中,缓刑的适用率仅为25.71%。另一方面,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法院对于与被害人存在特殊关系的行为人的量刑也明显更轻。譬如,在殷某误伤同伴龚某( 一级轻伤) 的场合,尽管法院认定殷某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对其免予刑事处罚(11)参见甘肃省敦煌市人民法院( 2020) 甘0982 刑初4 号刑事判决书。。与之相对,在李某误伤郭某( 一级轻伤) 的场合,法院对李某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12)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2019) 新0104 刑初452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 三) 具体符合说的问题
对客观构成要件做具体化理解的具体符合说也面临着以下两个问题。
1.构成要件具体化的程度。对具体符合说的重要批判是该说并未为构成要件具体化的程度提供明确的标准[28]。不过,在本文看来这并不能真正地被作为批判意见,其只是提出了具体符合说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构成要件具体化的标准,存在着以行为对象个别性为基础和以法益主体个别性为基础的见解[29]。但是,以行为对象个别性为基础的学说明显存在问题,不能将之作为构成要件具体化的基准。
一方面,不存在脱离法益主体个别性的行为对象个别性。以故意毁坏财物罪为例,其保护的不是对属于某一法益主体的个别财产的侵害,而是对该法益主体的财产的个别侵害[30]。在甲本欲毁坏乙的电脑,结果毁坏了乙手机的场合,在乙的手机被毁时,已经实现了对“乙财产”的个别侵害,应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既遂。而且,刑法所要规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对于财物的保护,最终还是为了保护权利人自主决定地对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益。因此,故意毁坏财物罪所要保护的财物,必然都是属于特定法益主体的财物。如果某一财物不属于任何法益主体,它就不是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例如,毁坏无主物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
另一方面,以行为对象个别性为基础的观点无法与罪数理论保持协调。在接续犯以及狭义的包括一罪的场合,即使行为人实际毁坏了数个财物,一般也只认定为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罪。譬如,甲以毁坏的故意,先后毁坏了乙的电脑和手机,属于接续犯的,仅认定为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罪。再如,甲以毁坏的故意,同时毁坏了乙的电脑和手机,属于狭义的包括一罪的,仅认定为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罪。如果财产( 行为对象) 本身的个别性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在上述情况下,甲就应当分别针对乙的电脑和手机成立两个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是,在上述场合,持行为对象说的学者也认为甲仅成立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罪[31]。
因此,具体符合说并不存在构成要件具体化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在个案中应当以法益主体个别性具体化地理解构成要件。
2.构成要件具体化的适用范围。具体符合说真正存在的问题是构成要件具体化适用的范围。因为,只要对具体的犯罪认定过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并非在任何案件中都需要对构成要件做具体化理解。易言之,不是在所有的犯罪中法益主体个别性都会影响客观构成要件的实现。譬如,因纠纷李某欲开车撞伤冯某,因冯某躲闪,李某撞上了黄某,致其重伤(13)杨夏怡:《李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载中国法院网2015 年9 月18 日,https: //www.chinacour t.org/article/detail/2015/09/id/1709195.shtml。。在本案中,李某对法益主体进行的个别化选择就并不重要。事实上,即使在采取具体符合说的德国,其通说也不得不承认,并非在任何犯罪中法益主体个别性都会影响客观构成要件的实现(14)Vgl.NJW 1956,1448.。
( 四) 修正的具体符合说的问题
针对具体符合说在构成要件具体化适用范围方面的问题,存在着多种修正观点。
1.实质等价理论。实质等价理论主张,法益主体个别性是否影响客观构成要件的实现,取决于该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法益。详言之,如果构成要件保护的是高度人身性法益,则法益主体个别性影响客观构成要件的实现;反之,如果构成要件保护的是非高度人身性法益,则法益主体个别性不影响客观构成要件的实现。因为,高度人身性法益与其法益主体之间具有高度依赖关系。在高度人身性法益中,法益本身就包含着高度的人格特征,法益与其法益主体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如果构成要件保护的是高度人身性法益,就不能在不考虑个体价值的情况下,判断客观构成要件是否实现。相反,在非高度人身性法益中,不存在这样的依赖关系,不法内涵的实现不以侵害特定的法益主体为条件[32]。因此,如果构成要件保护的是高度人身性法益,打击错误阻却故意归责;相反,如果构成要件保护的是非高度人身性法益,打击错误不排除故意归责[33]。
实质等价理论正确地认识到了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法益对法益主体个别性重要与否的影响。但是,其对法益所做的分类本身却存在问题[34]。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并非维持特定行为客体的客观状态,而是保护权利人对该客体的支配,确保权利人可以自主决定地对之加以利用,以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35]。因此,就财产法益而言,权利人对于相应行为客体进行支配的意志自由也是法益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这种意志自由也与法益主体之间具有高度的依赖关系,能够体现出法益主体的个体价值。所以,不能在个人法益下再区分所谓高度人身性法益和非高度人身性法益,并将财产法益归入非高度人身性法益。
2.行为计划理论。行为计划理论主张,行为对象个别性是否影响构成要件实现,取决于行为人的行为计划是否依赖于行为对象的个别性。当行为人的行为计划依赖于行为对象个别性时,行为对象个别性对构成要件是否实现具有重要影响;相反,如果行为人的行为计划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个别性,则构成要件是否实现与行为对象个别性无关。相应地,如果行为人的行为计划依赖于行为对象个别性,打击错误阻却故意归责;反之,打击错误不排除故意归责[36]。
这种观点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行为计划是行为人事前的主观想象,而故意则是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尽管行为计划通常会转化为犯罪故意,但这种转化关系却并非是绝对的。在甲因看到仇人B,放弃杀害A 的场合,甲事前的计划是杀害A,但行为时却仅具有杀害B 的故意。另一方面,行为计划理论未能提出明确的判断标准。譬如,在甲想下毒致A 丧失生育能力,仅造成A 双目失明的场合,该理论认为行为计划依赖于对象个别性(15)需要注意的是,行为计划理论以行为对象为基础对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化,故正文中的两个案例存在打击错误能否阻却故意归责的问题。如果以法益主体为基础对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化,则前述案例中的“打击错误”不影响故意归责,甚至可以认为根本不存在打击错误的问题。;相反,在甲想打伤B 左眼,实际打伤B 右眼的场合,该理论认为行为计划不依赖于对象个别性。但是,从构成要件的角度看,这两种情况在行为方式、行为客体以及结果等方面,都没有任何差别,根据该理论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不禁让人怀疑,行为计划理论不过是包裹着行为计划外衣的、持该观点学者本人的法感觉。
四、新路径之展开:新实质等价理论
在本文看来,尽管法益主体个别性对于客观构成要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故意毕竟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对它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想法。如果在个案中行为人仅具有针对特定种类法益主体的类型化的故意,而不具有针对特定法益主体的个别化的故意,那么,行为人就不可能针对特定主体去实施犯罪。所以,抽象地主张法益主体个别性影响构成要件的实现就是毫无意义的。相应地,解决打击错误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个别化的故意,即是否具有侵害特定法益主体的故意。故意包含了认识要素与意志要素。因此,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个别化故意,需要在个案中分别确定法益主体个别性对于故意的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是否具有重要意义。
( 一) 法益主体个别性与认识要素
本文认为,法益主体个别性对于行为人的认识是否具有重要意义,取决于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法益。在此,需要区分人身法益和财产法益。
1.侵害财产法益的犯罪。财产法益的特点决定了,实施财产犯罪的行为人行为时通常无法认识到自己实际侵害的法益主体。首先,从规范层面讲,在财产法益中,法益主体通过占有或所有等法律关系支配其法益客体。这种占有和所有法律关系具有规范性。为了认识规范性内容,人们不仅需要通过感觉器官获取事物的外在现象,还需要运用抽象思维对这些外在现象进行概括和整理,而这一认识过程很难在行为时完成。原因在于,“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只有“社会实践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才会“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进而人们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37]。在财产犯罪案件中,尽管行为人可能分别认识到了法益主体与客体的存在,但是,这仅是对事物现象方面的认识,是通过感觉器官获取的感性认识,仅此尚无法认识法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规范支配关系。为了把握这一规范关系,行为人需要将自己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但是,这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行为人在行为时无法完成这一飞跃。刑法通过保护法益客体的完整存续,来保障法益主体可以自主决定地支配法益客体,以实现其自身的利益诉求[38]。与之相应,犯罪行为也是首先侵害法益客体的完整存续,进而实现对法益主体自主决定权的否定。因此,在犯罪中,行为人首先认识的是法益客体,并通过把握法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支配关系,实现对特定法益主体的认识。在财产犯罪中,行为人行为时通常无法把握法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支配关系,也就无法认识到自己行为所侵害的究竟是哪一特定法益主体,更没有办法形成针对该主体的个别化的故意。因此,法益主体个别性通常不影响故意归责的判断,打击错误不排除故意归责。
其次,从事实层面讲,在财产法益中,法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一方面,可能存在两个法益主体同时占有或所有某一法益客体的情况。譬如,在遗产分割前,继承人A 和B 共同所有某一古董花瓶。另一方面,还可能存在法益客体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况。譬如,在遗产分割后,A 和B 仍然对花瓶的所有权存在争议。这些复杂权属关系的存在,使得行为人行为时无法正确地把握主客体之间的规范关系,无法形成个别化的故意。不仅如此,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如果甲想通过打碎这个花瓶报复A,但因实际毁坏了花瓶旁B 的手机,能否认定甲意图毁坏与实际毁坏的财产属于同一法益主体也存在困难。而且,在财产权属存在争议的场合,如果要求在故意的判断中考虑行为人对法益主体的认识,那么法院事后关于财产权属的判决就可能对行为时故意的判断产生影响。例如,如果法院将花瓶的所有权判给A,则甲行为时毁坏的就不是同一法益主体的财产,打击错误阻却故意归责;反之,如果判给B,则甲毁坏的就是同一法益主体的财产,打击错误不排除故意归责。但是,故意是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其不应受到法院事后做出的判决的影响。因此,从事实层面讲,也应当认为,在财产犯罪案件中,法益主体个别性通常不影响故意归责的判断,打击错误不排除故意归责。
当然,如果行为人对于法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支配关系存在特别认知,能够针对特定法益主体形成个别化的故意,打击错误阻却故意归责。譬如,甲明确知晓面前的两个花瓶分别属于A 和B,其原本想打碎A 的花瓶,实际打碎了B 的花瓶。此时,甲就具有针对A 财产的个别化的故意,打击错误阻却故意归责。原因在于,本文之所以认为实施财产犯罪的行为人行为时不具有个别化的故意,是因为在财产犯罪中,仅依靠行为时的感性认识行为人无法形成对法益主体和客体之间规范支配关系的认识。但是,如果行为人行为时确实正确地把握了两者间复杂的规范关系,并形成了个别化的故意,就不应当予以否认。
综上所述,在财产犯罪中,除行为人存在特殊认知的情况外,通常应当认定其行为时不具有个别化的故意,打击错误不排除故意归责。
2.侵害人身法益的犯罪。参考以上论证,在侵害人身法益案件中,判断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认识是否依赖于法益主体个别性的关键就是,其是否能够仅凭行为时的感性认识,就把握法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支配关系,并认识到特定的法益主体。如果行为人借助行为时的感性认识就可以把握两者间的关系,则其行为时的主观认识依赖于法益主体个别性;反之,就不依赖于法益主体个别性。考虑人身法益的特点,本文对此持肯定态度。首先,在人身法益中,法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具有事实性和可感知性。这就意味着,人身法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支配关系,本身就属于可以通过感觉器官认识的事物现象,行为人行为时运用感性认识就可以把握这一关系。其次,人身法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高度的依赖关系。以身体为例,通常情况下,人体的部分一旦与人的身体分离,均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物,原主体仅对其享有所有权[39],对其的侵害不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因此,即使在法益客体脱离其主体独立存在时,也不会出现难以认定两者关系的情况。最后,在人身法益中,也不会出现法益客体“权属”不明的情况。同样以身体为例,人体的部分一旦植入他人的身体,原法益主体就不再对之享有任何人身权利,不会出现“权属”争议,针对该人体部分的侵害,仅成立针对新的法益主体的故意伤害。因此,在侵犯人身法益的场合,行为人具有针对特定法益主体的个别化的认识,如果其同时具有个别化的意志因素,则具有个别化的故意,打击错误排除故意归责。
3.侵害复合法益的犯罪。值得研究的是,如果构成要件保护的是复合法益,应当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个别化的故意。持实质等价理论的学者认为,应当根据构成要件的内容,判断构成要件优先保护的法益,并将之作为侵害优先保护法益的犯罪,适用相应的规则。以抢劫罪为例,由于该罪属于财产犯罪,财产法益处于被优先保护的位置,就应当对其适用处理财产犯罪案件时所采取的规则[40]。但是,这样抽象地判断构成要件优先保护的法益,并不能真正为实际案件的解决提供帮助。譬如,甲原本想通过重伤A 的方式抢劫A,由于A 躲闪造成B 重伤。在这一场合,如果将之作为财产犯罪处理,就会将B 的重伤结果也归责于甲的故意。但是,根据实质等价理论,在甲原本想重伤A 因打击错误造成B重伤的场合,不能将B 的重伤结果归责于甲的故意。在这两种情形中,甲的不法行为内涵以及故意的内容没有任何区别,但按照这种观点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并不合理。
在本文看来,对于构成要件优先保护的法益的判断也必须是立足于行为时的判断。在个案中,构成要件优先保护的法益就是行为人发生打击错误的法益。譬如,在甲原本想抢劫A 的手机,因打击错误抢劫了B 的手机的场合,甲的打击错误发生在财产法益上,处于优先保护地位的就是财产法益,就应当将之作为财产犯罪处理。亦即,除行为人具有特别认识的外,打击错误不排除故意归责,甲仍构成抢劫罪。反之,如果打击错误发生在人身法益上,则处于优先保护地位的就是人身法益,就应当将之作为侵害人身法益的犯罪,如果行为人具有个别化的意志因素,打击错误排除故意归责。比如,在前述由于A 躲闪而造成B 重伤的场合,行为人对B 的重伤结果就仅具有过失。
4.质疑与回应。对本文见解可能的质疑意见是,故意归责的一般原则应当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法益[41],不能仅仅因为构成要件所保护法益的性质不同,就对在性质上几乎相同的错误行为采取不同的处理原则[42]。不过,这一质疑意见并没有说服力。因为,在构成要件保护的是个人法益的场合,之所以法益主体个别性影响故意归责,是因为行为人行为时能够认识到其所侵害的是特定法益主体的法益,法益主体个别性会对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产生影响,行为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针对该特定的法益主体实施犯罪行为。与之不同,在构成要件保护的是财产法益的场合,行为人在行为时通常无法正确认识其所侵害的特定的法益主体,法益主体个别性不会影响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法益主体个别性自然无法影响故意归责的判断。而且,本文并非一概否定在财产犯罪中打击错误可以阻却故意归责,而是主张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处理。在个案中,如果行为人行为时确实认识到了其所侵害的是特定法益主体的法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侵害某特定法益主体的犯罪行为,那么,打击错误仍然可以阻却故意归责。总而言之,本文的观点并未违反故意归责的一般原则,相反,考虑了不同性质的犯罪各自的特点以及行为人的特别认知情况,可以更好地贯彻故意归责的一般原则。
( 二) 法益主体个别性与意志要素
尽管行为人行为时能够认识到特定的法益主体,但是,如果其不具有仅侵害该特定法益主体的主观意欲,仍然不能认为其具有个别化的故意。就个别化意志因素的判断,存在着感知说与手段说的对立。不过,这两种观点均存在缺陷。
1.感知说的缺陷。感知说尊重行为人对法益主体的个别化选择。按照这种观点,只要行为人感知到特定的法益主体,并决意对其实施犯罪行为,就可以认为行为人具有个别化的意志因素,存在个别化的故意。根据对感知程度的要求不同,又可以划分为心理感知说和感官感知说。前者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心理上感知到特定的法益主体,并针对该主体实施犯罪行为,就可以认为其具有个别化的意志因素[43]。与之相对,后者认为,仅有心理上的感知还不够,只有当行为人通过感觉器官实际感知到特定的法益主体时,才能够说其具有个别化的意志因素(16)BGH NStZ 1998,294 f.。在本文看来,感知说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之处。
首先,对个别化的意志因素的判断不能仅靠主观感知。一方面,脱离具体行为手段的单纯主观认知,只是行为人的主观计划,对于个别化的意志因素的判断没有任何意义。譬如,为了报复刘某,姜某趁刘某和其丈夫范某熟睡之机,从窗户向刘某投掷炸弹(17)参见辽宁省调兵山市人民法院( 2016) 辽1281 刑初51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在这一场合,尽管姜某已经感知到了刘某,并决意对其实施犯罪行为,但是,其所采取的手段在客观上具有导致多人伤亡的可能性。因而,不能认为姜某仅具有侵害刘某的犯罪故意,而没有侵害范某的故意。另一方面,在个别化的意志因素的判断中,如果过度强调行为人的自主选择,就会使得故意归责的判断完全取决于行为人的恣意,最终使得故意等同于行为人事前的行为计划。而且,法官事后很难通过客观的方法查明行为人行为时是否实际感知到了特定的法益主体,这就难免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无疑增加了刑讯逼供的风险。
其次,在隔离犯的场合,根据感知说会得出不合理的结论。一方面,在该场合,由于时空阻隔,行为人行为时根本无法通过感觉器官实际感知到具体的法益主体。因而,根据感官感知说,就只能认为其没有个别化的意志因素,对实际发生的结果也具有故意。这显然与感知说尊重行为人自主选择的初衷相悖[44]。另一方面,由于时空间隔变大,在隔离犯的场合,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也更加困难。如果采取心理感知说,很容易仅凭主观想象随意认定因果联系,不当扩大个别化故意的成立范围[45]。譬如,在甲原本想在A 的汽车上安装炸弹,但误将炸弹安在B 的汽车上,导致B 死亡的场合,持心理感知说的学者就认为,甲仅具有杀害A 的故意[46]。但是,这种情形与甲误以为坐在车里的B 是A,而向B 扔炸弹致其死亡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根据心理感知说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难以令人赞同[47]。
2.手段说的缺陷。手段说认为,只有当行为人通过“程序上的设定”[48],将自己行为的影响限定于特定的法益主体时,他才具有个别化的故意[49]。对该说最大的批判是,其未能说清楚“程序上的设定”包含了哪些内容。譬如,甲在A 的汽车上安装炸弹,A 将汽车借给B 使用,导致B 死亡,此时能否将B的死亡归责于甲的犯罪故意。如果A 是十分偶然地将汽车借给B,是否仍然能够将B 的死亡归责于甲的犯罪故意[50]?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持手段说的学者不得不求助于概率的判断。譬如,有学者主张,应当根据行为引起结果的可能性,将具体案件划分为通常的情况、极不寻常的情况和不太寻常的情况。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将B 的死亡归责于甲的故意;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甲对B 的死亡没有故意;在不太寻常的情况下,则需要根据生活常识具体地判断甲是否具有杀害B 的故意[51]。然而,究竟达到多大的概率才能说该情况属于通常、极不寻常以及不太寻常的情况并不清楚。而且,在现实案件中,受到行为时各种因素的影响,行为究竟有多大的概率会引起结果也总是难以查清楚的。总之,手段说无法为行为人是否存在个别化的意志因素的判断提供明确的标准。
3.本文的观点。只有当行为人在规范上能够信赖自己所创设的危险会向着侵害特定法益主体的方向发展,他才具有个别化的意志因素。行为人的这种规范信赖必须来源于对社会分工的信赖。譬如,根据社会分工,快递员有义务将包裹送到指定的位置,制作炸弹的人应当保证炸弹的有效性。如果甲能够信赖快递员会将炸弹送给其指定的人以及炸弹会按时爆炸,并通过邮寄炸弹的方式杀害乙,甲就具有针对乙的个别化的杀害故意。之所以行为人可以信赖这样的社会分工,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都需要在不同程度上依靠他人,社会分工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分工“使社会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总之,只有社会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52]。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快递员也经常会送错快递,炸弹的合格率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不过,这只是从事实层面讲的,并不会影响根据社会分工的要求,快递员和制作炸弹的人在规范上所负有的保证义务。而且,也恰恰是在事实层面,快递员的妥投率和炸弹的合格率达不到百分之百,才会出现打击错误的问题。因此,如果行为人根据社会分工可以信赖自己支配着风险现实化的过程,那么他就对于自己所选定的法益主体具有个别化的故意。
在非隔离犯的场合,由于危险现实化的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因此,根据社会分工,行为人是否可以信赖自己支配着危险现实化的过程的判断也比较容易。譬如,在甲本欲射杀A,导致碰巧路过的B 死亡的场合,甲可以信赖使用枪支瞄准A 并向他开枪,是使自己创设的导致他人死亡的危险仅实现于A的有效方式,因此,甲具有针对A 的个别化的杀害故意。相反,在甲向A 投掷炸弹,导致碰巧路过的B死亡的场合,尽管甲可以信赖炸弹有效爆炸,但是,爆炸的范围并不完全受制作炸弹的人以及甲的掌控,甲无法信赖炸弹仅炸死A,而不会炸死B,因此,甲的杀害故意并非仅针对A。
在隔离犯的场合,由于时空的阻隔,行为人必须要借助他人的“帮助”或者一定的客观事实,才能实现对特定法益主体的侵害。因此,行为人创设的危险现实化的过程比较复杂。相应地,根据社会分工,行为人是否可以信赖自己支配着危险现实化的过程的判断也比较烦琐。下文将通过对经常被讨论的案例的分析,明确如何运用本文的观点解决这类案件。
第一个案例是汽车爆炸案,即甲欲杀死A,在A 的汽车上安装了炸弹,结果炸死了B。如前所述,根据社会分工,尽管甲可以信赖炸弹会爆炸,但却因无法控制炸弹的爆炸范围和爆炸的时间,不能信赖炸弹一定会炸死自己选定的A,缺少对A 的个别化的杀害故意。因此,无论被炸死的是盗窃汽车的小偷,还是借用汽车的朋友,抑或是A 的妻子,都可以将死亡结果归责于甲的杀害故意。不过,如果甲知晓A根据社会分工,必须要在每天早上7 点使用该汽车,并且设置了一个在早上7 点爆炸的定时炸弹,那么,甲就具有对A 的个别化的故意。甲对于7 点前触发炸弹的小偷B,或者7 点时借用汽车的朋友B的死亡,均不具有故意。因为,根据社会分工,甲可以信赖A 在早上7 点使用汽车,并且炸弹会在7 点爆炸,甲可以信赖自己支配着危险现实化的过程,并使之实现在A 的身上。
第二个案例是“邮寄毒药案”,即甲欲杀害A,给A 邮寄有毒的蛋糕,导致B 死亡。在此类案件中,需要区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甲邮寄有毒的蛋糕到快递员将蛋糕交给收件人。根据社会分工,快递员有义务将快递送到正确的地点。因此,在这一阶段,甲可以信赖自己支配着危险现实化的进程。如果快递员将有毒的蛋糕误送给了B,导致B 死亡,甲对B 的死亡不具有故意。第二阶段是收件人收到蛋糕之后。在这一阶段,根据社会分工,甲无法信赖一定是A 接收了快递并食用蛋糕,甲并未支配危险现实化的进程。因此,无论是A 的朋友B,还是他的妻子B 因食用蛋糕而中毒身亡,都可以被归责于甲的杀害故意。
五、结论
解决打击错误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个别化的故意。在具体认定时,需要考察法益主体个别性对于行为人主观认识和意欲的影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在财产犯罪中,除具有特别认知的情况外,行为人行为时通常无法认识到具体的法益主体,无法形成针对该主体的个别化的故意,打击错误不排除故意归责。在侵犯人身法益的犯罪中,尽管行为人行为时能够认识到具体的法益主体,但是,只有当行为人根据社会分工能够信赖自己支配了危险现实化的进程时,他才具有个别化的故意,打击错误阻却故意归责。在侵害复合法益的犯罪中,需要具体判断发生打击错误的法益,并将之作为侵犯该法益的犯罪处理。根据本文见解所得出的结论与实质等价理论具有相似性,故可以将之称为新实质等价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