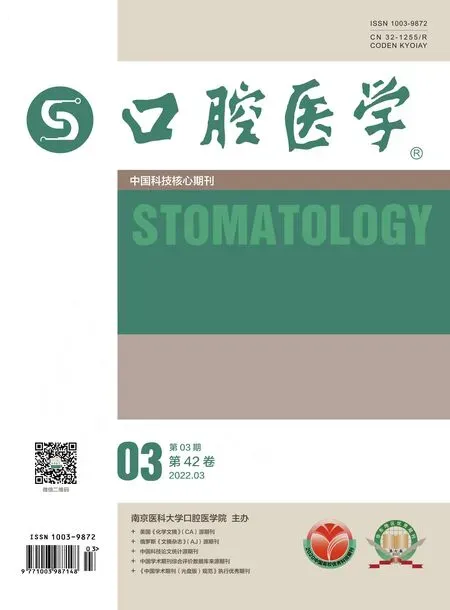人β防御素2与口腔扁平苔藓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2022-11-24黄辛兆钟良军
黄辛兆,钟良军
1 人β防御素2(human β defensin-2,hBD-2)的简介
防御素是一类广泛存在于昆虫、植物及哺乳动物的内源性抗菌肽,根据结构的不同可分为α-防御素、β-防御素及富含特定氨基酸的多肽[1]。1997年,Harder等[2]推测在银屑病这种非感染性疾病中可能存在抗菌肽,并从银屑病患者的皮肤鳞屑中分离纯化得到一种约4.3 ku的多肽,氨基酸序列分析表明其属于人β防御素成员,被命名为hBD-2。
hBD-2是天然免疫的第一道防线皮肤和黏膜中的一种重要介质,是一种有41个氨基酸的阳离子小分子内源性抗菌肽,其相对分子量为4 328.3 u,电离常数为9 130,含有6个半胱氨酸残基及3个稳定其构型的二硫键。hBD-2的基因包含两个外显子(第1个外显子编码信号肽,第2个外显子编码很短的前导肽和成熟的hBD-2基因)和一个1 610 bp的内含子,含有TATA盒(CTTTAATAAGGTGGAA)和多个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元件[1]。
2 hBD-2的生物学活性
hBD-2基因及蛋白的表达主要通过激活基因转录因子NF-κB实现,有丝分裂激活蛋白激酶通路以及Src-依赖的Raf-MEK1/2ERK信号通路也参与其中。其主要的生物学活性如下。
2.1 抗菌作用
hBD-2能杀灭多种病原微生物,主要包括大多数带负电荷的G+菌、G-菌、真菌、支原体及螺旋体。大部分研究认为其抗菌作用主要与破坏质膜双分子层有关,带正电荷的hBD-2通过静电吸引与带负电荷细菌的细菌膜脂层结合,在膜脂上聚集形成稳定的孔隙或通道,使胞外的离子、多肽等流入胞内,并使胞内重要的盐类、大分子等泄漏到胞外,从而导致不可逆性的菌体死亡[3]。hBD-2的杀菌作用有剂量依赖性,且由于带正电荷的离子可与其竞争结合位点,故其活性与盐浓度、离子种类也有一定的关系[4]。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除了破坏膜结构,防御素还可通过其他途径起到抗菌作用[5]。
hBD-2呈可诱导表达,在健康的皮肤中可检测到hBD-2的mRNA,但不能分离出具有抗菌活性的hBD-2。当皮肤和黏膜被细菌感染时,hBD-2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增高[1]。
2.2 免疫活性
hBD-2在对病原体的免疫防御、自身抗原或肿瘤抗原的免疫监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hBD-2与趋化因子受体6(chemokine c-c motif receptor 6,CCR6)的配体巨噬细胞炎性蛋白3α的三级结构相似,能竞争结合树突状细胞和T淋巴细胞表面特异性的CCR6,从而激活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6],使其聚集于局部皮肤或黏膜,发挥获得性免疫反应作用,提高机体抵抗感染的获得性免疫水平。
hBD-2可作为Toll样受体4(toll like receptor 4,TLR4)的内源性配体与之结合,在白细胞介素-1相关蛋白激酶和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6等信号传导分子的协同作用下,与TLR4结合后触发级联反应信号,导致NF-κB激活并迁移至细胞核内,激活细胞因子基因转录,介导协同刺激分子的表达上调和树突状细胞的成熟,进而活化T细胞,触发特异性免疫应答[7]。
2.3 其他作用
hBD-2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类型相关[8],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的过度甲基化可导致hBD-2表达降低,hBD-2可能是OSCC的抑癌基因[9-10]。hBD-2对肿瘤细胞有细胞毒性,能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的形成,可通过调控细胞周期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hBD-2可能与OSCC的分化和淋巴结转移相关[11]。
此外,hBD-2拥有广泛的抗病毒谱[12],在细胞的激活与分化,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产生,激素的调节,血管的新生,炎症、创伤及神经损伤的修复等方面均起作用[9]。
3 hBD-2与口腔扁平苔藓(oral lichen planus,OLP)的关系
3.1 hBD-2在口腔中的表达
hBD-2广泛表达于口腔组织,健康口腔黏膜组织有少量hBD-2的表达,OLP患者病损组织中hBD-2表达较健康口腔黏膜组织明显增强。在过角化的OLP中,角化层及颗粒层均有明显的hBD-2表达,且在棘细胞层中有强阳性表达[13-14]。
有研究表明白细胞介素-1、肿瘤坏死因子-α、白念珠菌感染等刺激因素可诱导hBD-2基因表达上调[13-14],但hBD-2在OLP中的高表达现象在其他有炎症浸润的上皮病变(如严重炎症所致的牙龈增生或根尖囊肿)中并未发现,可能与OLP相关的特异性炎症或免疫发病机理相关[13]。
OLP组织中朗格汉斯细胞(Langerhans cell,LC)的数量较正常上皮多,hBD-2在OLP的LC中高表达可能是诱导性表达增强的结果,与LC的分布无相关性,但其在OLP中的定位可能与LC的分布有关[13]。
3.2 hBD-2与OLP感染
OLP可能与细菌、念珠菌和病毒感染相关[15],有研究显示玛氏普雷沃氏菌、艾肯菌属、直肠弯曲菌、二氧化碳嗜纤维菌等多种菌属在OLP的唾液和组织中富集[16-18]。在人体其他组织中的研究表明hBD-2对与OLP密切相关的HPV有抑制作用[19]。OLP相关炎症因子可能特异性地诱导hBD-2在病变区域的高表达。
白念珠菌感染与OLP关系密切,OLP患者较健康人群更易伴发白念珠菌的感染[13-14]。有研究表明白念珠菌在不同类型的OLP中均有阳性表达,且随着病情加重其阳性率增加,而hBD-2的表达随着白念珠菌感染及炎症程度增加而增强[20]。糖皮质激素是治疗OLP的一线用药[20],而糖皮质激素是公认的口腔念珠菌病诱发因素之一[21]。有研究显示,30%的白念珠菌检测为阳性的OLP患者,在开始局部类固醇治疗后会发展为口腔念珠菌病[22]。hBD-2有抗真菌活性,当白念珠菌接触口腔黏膜上皮的角质形成细胞后,细胞壁中的甘露聚糖可被TLR2识别,介导hBD-2的产生,并激活核转录因子NF-κB,调控hBD-2的基因转录,从而增强hBD-2 mRNA的表达[23]。
角化作用有助于上皮中hBD-2的保留,但在OLP的角化层表层常检测到hBD-2染色暗淡或呈阴性[13],可能是由于临床上OLP患者的白念珠菌感染多表现为浅表感染或仅为带菌者[17]。
3.3 hBD-2与OLP免疫
OLP是一种T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性疾病,免疫失衡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OLP患者同时存在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的异常,以细胞免疫功能降低、体液免疫功能亢进为主[24-25]。
OLP的主要病理改变是基底细胞液化变性及上皮下淋巴细胞浸润[26]。其发病机理可能是:外来抗原或与外来抗原结合的自身抗原使口腔黏膜上皮细胞发生改变,引起T淋巴细胞对上皮的自身免疫性攻击并激活固有层淋巴细胞增殖[27],造成基底层细胞和基底膜损伤,破坏的上皮细胞可产生白细胞介素等活性因子,募集淋巴细胞到病变部位,形成恶性循环[28]。
hBD-2在OLP中更强、更广泛的表达可能是由特异性T细胞主导的炎症所致,与OLP有关的炎症可强烈诱导hBD-2的表达以增强局部皮肤的免疫防御功能。hBD-2可通过与CCR6结合,趋化树突状细胞和记忆T细胞,活化T、B细胞,调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参与机体的获得性免疫反应,使OLP长期处于宿主防御和微生物入侵的动态平衡之中。hBD-2的表达水平可能会影响OLP患者抵抗微生物入侵的能力及OLP的预后。
3.4 hBD-2与OLP恶变
目前认为OLP是一种潜在恶性病变,是否可能癌变尚无确切说法,大多数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OLP癌变率在1%左右[29-30]。OLP的癌变可能是由于长期的炎症刺激导致上皮细胞的增殖和凋亡失衡,使某些基因或信号通路出现异常,最终诱使疾病向OSCC发展[31]。hBD-2的抗炎、抗菌及免疫激活作用在防止OLP恶变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白念珠菌在OLP向OSCC转变过程中具有促进作用,白念珠菌可在乙醇氧化和葡萄糖酵解过程中产生乙醛,乙醛能促进上皮异常增生和口腔癌发生[32],导致OLP恶变。体外研究发现的hBD-2可能通过抑制粘附上皮细胞、上调对菌丝生长的反应等灭活白念珠菌[33],可能在抑制白念珠菌促OLP的癌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 hBD-2与OLP的治疗展望
hBD-2的生物学特性体现了其在调动机体的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中的作用,通过破坏病原微生物的生物膜结构或病毒外壳蛋白产生抗菌、抗病毒作用且不产生抗性,同时还具有抗肿瘤、激素调节等作用。这些特性使其在物种生存、抵御侵害以及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应用前景。
hBD-2与OLP关系复杂,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完善。作为内源性抗菌肽,hBD-2在机体正常组织中表达水平很低,能够通过分离、提纯获取天然的具有生物学活性hBD-2的量极其有限。hBD-2含有3对二硫键,化学合成的hBD-2较难保证正确的配对,且前酶易快速降解,合成的hBD-2具有一定细胞毒性[34]。而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获得hBD-2时,会由于其抗菌活性引起工程菌“自杀”。如何建立持续、稳定且高效表达系统生产具有生物学活性的hBD-2尚处于研究阶段。虽然有基础研究通过氨基酸残基替换改良hBD-2,可降低其细胞毒性,增强其抗菌作用及耐盐性[35],但鲜有其在临床中的应用方式、效应剂量或不良反应的相关报道。
尽管如此,研制安全无毒的免疫制剂以诱导hBD-2在局部黏膜高表达,或直接在口腔黏膜中应用具有较高生物学活性的hBD-2可能会给OLP的防治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