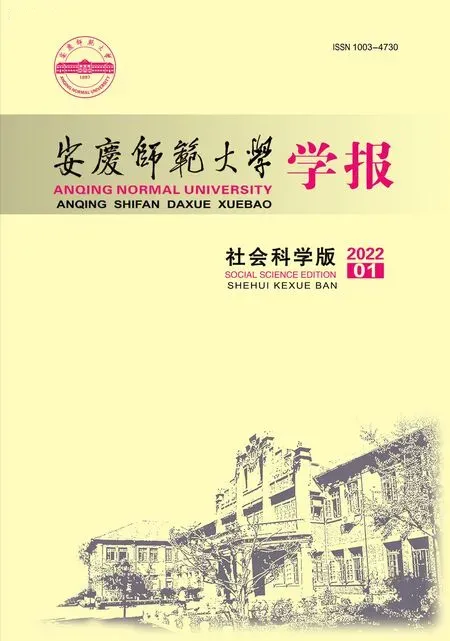方东树游幕与骈文创作及其思想面相
2022-11-23汪孔丰郑晨晨
汪孔丰,郑晨晨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士人游幕是清代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特别是从康熙中期到嘉庆末年,这一百多年里,士人游幕呈现出极为兴盛的局面[1]。在如过江之鲫的游幕者中,不乏桐城士人奔波南北的羁旅身影,方东树(1772—1851)就是其中之一。方东树“自二十后,多客四方”[2],颠沛流离,谋食求存,或主讲书院,或游幕授经。他先后客游胡克家、阮元、邓廷桢等地方督抚的幕府,历经十数载。长期的幕府生涯,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和精神世界,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他的诗文集中,就存有大量作于游幕时期的作品。其中的诗歌、散文,往往为学界所关注,而骈文则鲜有问津。
就方东树现存的骈文作品而言,绝大多数都是作于游幕时期①方东树的骈文收录于《考槃集文录》卷十二,共计18篇。按,方东树文集共有两种刊本:一是《考槃集文录》12卷,收文239篇;一是《仪卫轩文集》12卷,外集骈体文1卷,收文103篇。前者系方东树生前自订,未及刊刻,直到光绪四年(1778)的《方植之全集》刊印;后者系方宗诚据前者选录,并予以更名,且在同治七年(1868)先行刊出。参见严云绶《〈方东树集〉整理说明》(写于2008年5月20日),《方东树集》,方东树著,严云绶点校,《桐城派名家文集》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154页;陈晓红《方东树诗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42页。。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自撰,如《跋彭甘亭小谟觞馆文集》《谢邓中丞启》等,其中还包括《孔雀赋》《汉晋名誉考》等拟作;二是代撰,如《陶云汀宫保六十寿序》《拟进安徽通志表》等。从文类来看,这些骈文涉及跋、赋、寿序、表、启、铭等,以应酬公文居多。它们辑成一卷,存于文集,不仅反映了方东树辗转多方、佐理翰墨的游幕生活,同时也呈现出方东树游幕期间丰富多元的思想面相。
一、游胡克家幕府与骈文思想的阐示
嘉庆十七年(1812)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方东树客于安徽巡抚胡克家幕府。这五年,是他人生中游幕时间最长的一段。他在胡幕期间的诗文创作,留存不多②这可能与方东树有意焚弃有关。他在《半字集序录》中说:“丙子遭忧,灰心文字,兼悔少作,遂尽取而焚焉。自后酬应感寄间有谣咏,多不满意,辄弃去,故篋中留稿十不能一二。”(《方东树集》,第486页)“丙子”即嘉庆二十一年(1816),是年闰六月四日,方绩去世。方东树遭父忧期间,焚弃大量旧作,其中可能包含着他在胡克家幕府期间所作诗文。。就骈文来说,《跋彭甘亭小谟觞馆文集》应当是此时创作。这是方东树文集中现存最早的一篇骈文作品。
对于这篇跋文,学界虽有一些关注,但也有未察之处。诸多学人,要么征引跋文开篇一段直接反映方东树骈文观念的文字,以说明嘉道时期桐城派兼容骈散的新动向;要么援引方东树赞称彭兆荪骈文之语,以说明彭兆荪骈文成就之高。实际上,围绕这篇跋文,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比如方东树与彭兆荪的关系如何,他所见文集是何版本,跋文受到文集影响几何,等等。倘若我们能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遥体人情,悬想势事,解释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全面、深入地理解这篇骈体跋文,还可以知晓方东树骈文观念的产生背景。
方东树为《小谟觞馆文集》作跋,与结识幕府内的彭兆荪有关。彭兆荪(1769—1821),字甘亭,又字湘涵,江苏镇洋(今太仓)人。“少随父宦山西,神隽有声。年十五,应顺天乡试,诸公卿争欲招致,然竟十余年无所遇。”[3](姚椿《彭甘亭墓志铭》)年二十余,因家遭变故,衣食驱遣,不得不作客四方,授经游幕。嘉庆十二年(1807)冬,入江苏巡抚胡克家幕,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因胡氏病殁而离去。彭兆荪居幕十年,深得幕主胡克家器重,是“客胡果泉中丞幕最久最密”[4]之人。这期间,彭兆荪应当结识晚来且居幕五年的方东树。方东树的这篇跋文末尾云“高文载觌,倾伫如何?堂下鬷明,未能默息。岂谓一共商榷,解读郊居,类彼汝南,论兹月旦也哉”①按,此处出自萧纲《与湘东王书》:“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辩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萧纲与湘东王萧绎为兄弟,其中“类彼汝南”征引了许劭及其从兄许靖“月旦评”之典。再考虑方、彭二人年纪相近,因此,方东树所云,不应是客套的礼节用语,而是他们密切关系的真实表露。,即从侧面佐证了双方之间有着亲似兄弟的密切关系。更何况,如果双方无交游往来,方东树的跋文应当很难刻印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小谟觞馆文集》。
方东树所见《小谟觞馆文集》为何版本,这个问题鲜有关注。彭兆荪的文集,最早刊印于嘉庆十一年(1806)韩江寓舍。是年,彭兆荪正客于扬州曾燠幕府,宾主情谊深厚。曾燠不仅让他佐辑《国朝骈体正宗》,还帮他选定和刻印《小谟觞馆诗文初集》,并撰序赞称“观其所作,顿惊痴俗,始叹灵奇”[5](《小谟觞馆诗文集序》)。此外,彭兆荪在幕府中结识的王芑孙也为此集撰写了序文。此集中,有古今体诗8卷、诗余1卷、赋序书记碑铭杂文4卷。其后,嘉庆二十二年(1817),彭兆荪诗文又有娄东城南草堂续刻本,而方东树所撰跋文已录于《小谟觞馆文集》卷末。由此推之,方东树所见彭兆荪的文集,应当是嘉庆十一年(1806)刻本。此本卷首有嘉庆十一年(1806)长至前十日长洲王芑孙序,卷一赋,卷二序,卷三书,卷四记碑铭杂文。方东树在《跋彭甘亭小谟觞馆文集》中赞称彭文“鸿序兼于众体,谥议美于碎金。诔掩安仁,书休曹植;论屈灵运,铭夺士衡”[6]468,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他所阅文集版本的相关内容。
方东树撰写跋文前,应当阅览过文集卷首的序文,而序文作者王芑孙亦与桐城文学有较深的渊源。王芑孙(1755—1817)早岁尝从方苞弟子钟励暇处习闻桐城义法之说,由此被刘声木收于《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二“师事及私淑方苞诸人”中[7]。王氏在中年时,又钦慕姚鼐其人其文,虽终身未曾面晤,但双方书札往来频仍[8]。不过,他是否为方东树所熟知,或与方东树有所往来,受资料限制,尚难考定。王芑孙研治古文,用力甚勤,其文被姚鼐赞称“殆非今世所有”,得归有光之真传[9];然亦不废骈文,吴锡麟赞其骈文沉博绝丽,凌轹古今,气盛声宏,趣高词雅,“此真能由六朝而晋而魏,以仰窥东京之盛者”[10]893(《渊雅堂文外集序》)。
然而,王芑孙的《小谟觞馆文集序》,并非以骈体写之,而是以散体为主,兼带骈语,体现出“寓复于单”的特点[11]。这个特点体现在他发表骈散关系见解的文字上:“夫文何有奇偶哉!‘九州四隩’见于《书》,‘断壶剥枣’咏于《诗》,其文奇欤、偶欤,莫得而离判之也。班、扬极其盛于汉,韩,柳起其衰于唐,其文奇胜欤、偶胜欤,莫得而轻重左右之也。盖奇偶之用不齐,而一真孤露,吹万毕发,氤氲于意象之先,消息于单微之际。上者载道,下者载心。其要,固一术尔。”[10]539(《小谟觞馆文集序》)显然,王芑孙认为文无必要分奇偶,且举儒家经典《诗经》《尚书》为例,强调其文中之奇偶难以分判;又举班固、扬雄、韩愈、柳宗元之文为例,强调其文中之奇偶孰轻孰重难以衡量。基于此,他又指出彭兆荪“不自知其文之为偶为奇”,而读者“亦且忘乎其为排偶之文焉”[10]539(《小谟觞馆文集序》)。可以推想:对于王芑孙序中“文何有奇偶”的思想,方东树在阅读文集时,多少会产生一些思想的触动,要么引为同调,要么视为谬见。
实际上,方东树在跋文中的骈文主张,与王芑孙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跋彭甘亭小谟觞馆文集》开篇即云:“骈体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椎轮既远,源派益歧。悼先秦之不复,则弊罪齐梁;陋骈格之无章,则首功萧李。自是而降,殊用异施;判若淄渑,辨同泾渭。”[6]468方东树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他从“运意遣词”层面,指出骈文与古文本来就有相同之处,它们皆宜乎意明词达①按,虽然方东树没有言明骈文与古文“不异”之处究竟何在,但我们可寻绎于梅曾亮的《马韦伯骈体文叙》,从侧面窥知一二。梅曾亮云:“昔会课钟山书院中,每论文,讼议纷然,忘所事事。异之色独庄,盛言古文。余曰:‘文贵者辞达耳,苟叙事明,述意畅,则单行与排偶一也。’异之不复难,曰:‘君行自悟之。’时韦伯在坐,亦右余言。”(《柏枧山房文集》卷五,110页)另据方东树《寄梅伯言》:“宗儒得韩徒,斯文所寄存。与君侍经幄,异受实同闻。不有知十敏,那觉回非邻。竝时管幼安,清德更莫群。惭彼原与歆,头尾附一身。复有侯马俦,如泉共醴源。会文必齐等,出游常连肩。……四主吾一客,传食以为常。”(《方东树集》,第536页)以及梅曾亮《放歌行示植之异之韦伯彦勤弟》《立春日送植之酒》《和方植之来诗感念姬传先生殁已逾年》等诗,知方东树在钟山书院期间,与梅曾亮、管同、马韦伯、梅彦勤有交游。“论文”之事,恐在所难免。由此推之,此时梅曾亮强调“苟叙事明,述意畅,则单行与排偶一也”,当在方东树那里有所共鸣和认同。;其二,他从“源派益歧”层面,指出骈散分途后,两者各有所用,差异分明。由此来看,方东树不满骈散“辨同泾渭”的现象。
随之而来的,是方东树为骈体正名的一番议论:“嗟夫,临颍剑器,曲舞公孙;河阳猪肉,案参荆国。不有子美、子瞻,孰辨其波澜之莫二、妙谛之无上哉!高文典册,汉用相如;韩碑柳雅,集言鸿苑。咸能镂介邱之泥,镵燕然之石。亦可知自命作家,奄有百䙫,必无有专执;记序小文,阴何杂响,以惩羹吹齑,是丹非素者矣。唐人号称熟精《选》理,崇贤之业,冠时独出;珠囊金镜,哲匠挺生。驱染烟墨,摇襞纸札。虽复文章浅言,不拘糟粕,而当其卓然合作,犹足书之万本,入人肝脾。又况颖达序经,房乔论史,贞元之诏,会昌之集,鸿笔巨制,包羸越刘者乎?”[6]468这段话往往不为人所深究,其实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兹特拈出两点:
其一,他指出具有超卓才能的作家与骈体写作的关系。文章骈格本身无弊陋,所致者在于作家。有卓绝才能的作家,自然能充分展示其波澜莫二、无上妙谛。正因为杜甫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苏轼作《跋王氏华严经解》,世人才知公孙大娘剑舞之绝妙、河阳猪肉之鲜美;同理,司马相如、韩愈、柳宗元也因擅文而卓荦不凡,青史留名。
其二,他肯定唐代的崇尚骈文之风。唐人熟精《选》理,而崇贤馆直学士李善所注《文选》,“敷析渊洽”,传业甚众,“号‘文选学’”[12],冠绝一时。加之朝廷优待文士,哲匠挺出,他们用骈体书写浅言小品,也能入人肝脾;更何况孔颖达的序经之作、房玄龄的论史之作、贞元时期的诏令、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皆可谓鸿篇巨制,超越秦汉。方东树的这份评价,意在表明骈体具有强大、灵活、多元的表意功能。
方东树的骈文见解,与彭兆荪相近。彭氏虽然在《小谟觞馆文集》中没有直接表述其骈文思想,但其创作已体现出了“不自知其文之为偶为奇”的意识。不仅如此,《小谟觞馆文续集》中《荆石山房文序》亦说:“文章骈格……有唐一代,斯体尤崇,颖达以之序经,房乔用之论史。其于散著,途异原同。昧者不察,自为卑滥,是盖末流之放矢,以致伪体之滋繁。”[13]这段论述,与方东树跋文论唐代骈文的部分文字相似,亦体现出彭兆荪论骈散持其同源异途的主张。
概言之,方东树的这篇跋文在桐城派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跋作于嘉庆年间,方东树在文中提出“椎轮既远,源派益歧”,强调骈散同源,虽接踵于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提出的“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14]的主张②按,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作于何时,确切时间,有待考论。“王子卿太守”,即王泽(1761—1842),字子卿,一字润生,号观斋,安徽芜湖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嘉庆十二年任徐州知府,不满一年即离任。(《同治徐州府志》卷六,《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由此推知,此序所作,不迟于嘉庆十二年。,但要早于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所强调的骈散之源“则其所出者一也”[15]的主张③按,钟涛,彭蕾《李兆洛〈骈体文钞〉成书和版本考述》认为“《骈体文钞》编定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底,付梓于道光元年(1821)年底”,参见《励耘学刊(文学卷)》,第1辑(总第21辑),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257页。。这说明,姚门弟子对骈散关系的认知,因时而变,已与“桐城派三祖”异趣,有了新的理论取向和审美追求。
二、入阮元幕府与宋儒义理的维护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月,方东树受两广总督阮元之邀,赴广州入幕,修纂《广东通志》,逾年离开幕府,到粤东廉州主讲海门书院;道光四年(1824)和五年,又入阮幕授经,次年因阮元调任云贵总督,而离粤归里。两次入居阮幕,方东树写下了不少诗文作品。就骈文而言,有《学海堂铭并序》《孔雀赋》《汉晋名誉考》。这三篇作品,均作于方东树第二次入居阮幕期间,或隐或显地表露出他在汉学风气浓厚的阮幕内维护宋儒义理的思想心态。
《学海堂铭并序》的创作,与新建学海堂有关。道光四年(1824)九月,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粤秀山择址,创建学海堂,“十二月,学海堂落成”[16]。当时,为纪念这一盛事,粤地士人对此堂各有所述,作品多达一百余卷。其佳者,有赵均《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吴岳《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谭莹《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樊封《新建粤秀山学海堂题名记》《粤秀山新建学海堂铭并序》、居溥《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诗序》、谢念功《新建粤秀山学海堂序》、崔弼《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谭莹《新建粤秀山学海堂上梁文》、吴兰修《学海堂种梅记》、徐荣《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诗》、郑棻《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诗》,等等。方东树之所以创作此文,可能受到了粤地士人集体创作风气的影响。
《学海堂铭并序》中的序文,是一篇结构严谨、气势宏大的长序。序文大致可分为四部分:首先叙述粤地古今学风之递嬗;其次颂扬阮元政事、学术、文教之功绩;再次描述学海堂的建设以及方位情况;最后叙写阮元与士人“济济一堂”的和美景象,并阐释“学海”的寓意。
《学海堂铭并序》的第一部分尤为特殊,颇能反映方东树复杂的学术心态。序文起笔高远,从上古尧舜写起,“圣化所被,文明大启。南土之宾,自此始也”;接着写秦、南越、西汉政权治理粤地情形,尤其是西汉任延、锡光两位太守教化之绩,“故史称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紧接着大加称颂杨孚、黄颍、董正三位儒士以及陆贾、虞翻两位名贤。随之写此后岭南人文之盛:“是以斯文未替,并有所承。辙岐派别,专门亦兴。越羸傃刘,洎吴徂晋,更兴迭盛,以迄于今。研经者昧道德之华滋,测理者分窔奥之荧烛。发藻者搴兰芷之芬馨,采韵者激丝磬之宫徵。天钟其瑞,地毓其灵。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野馗风动,都庄云兴。家自以为郑孔,人自以为坚云。莫不枝附叶著,猋飞景从。含精吐茫,霅煜流光者,盖不可胜记。”[6]472这段话语对岭南学风自汉晋以后“更兴迭盛”的情形,写得比较含糊、笼统,不及前文那样明确、具体。其实,在广东历史上,三国时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代研治《左氏春秋》,声动九州;唐代,张九龄为一代贤相,主盟开元文坛;慧能为禅宗六祖,开创南宗一脉;逮至明代,陈献章创江门学派,开启一代心学新风;湛若水创甘泉学派,启迪阳明心学。然而,对于这些文化成就,方东树均未提及,似乎有意避之。后面写岭南士风、学风之流弊时,也是这样:“然而士有常习,俗有旧风。运有隆替,化有浇淳。时有升降,气有浊清。精粗殊会,通蔽相徵。千载不作,渊源莫瀓。浚明爽曙,祖构雷同。学者蔽暗,师道又缺。虚张流宕,优劣非一。亦不可同年而语矣。”[6]472方东树为什么要这样书写呢?这要从阮元创建学海堂的动机说起。
阮元创建学海堂,其目的在于改变广东学术风气,倡导经解之学,返崇儒道。他自己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17](《揅经集自序》)。自嘉庆二十二年(1817),他莅任两广总督以来,重视当地文教事业,对粤地学风颇有不满,认为“粤东自前明以来,多传白沙、甘泉之学,固甚高妙,但有束书不睹,不立文字之弊”[18]。为扭转粤地空疏学风,阮元引江浙学术入粤,在广州西城外文澜书院附设学海堂,仿抚浙时所立诂经精舍之例,课士古学[19]。此外,樊封在《新建粤秀山学海堂题名记》中也曾交代创建背景——学者昧于经训:“夫圣贤垂训示人,开通明畅,本为易知,虽中材皆可训行,后之释经者,务高以诩奇,务新以矜异。经训于是晦。汉人去古未远,犹能得孔门之传授,故许郑诂经不过因文立训,求其章句详明而已。六代以后,始尚名理,蹈虚索漠,取古圣谆谆教人之旨,与老庄同揆,学者乃更畏经训之难而不敢学。”[20]作为局中人,樊封之语,也从侧面验证了学海堂新建的初衷。
然而,学海堂所倡导的经训稽古之学,于方东树而言,却别有一番滋味。他论学尊崇程朱,笃守宋儒义理之学。他在道光四年(1824)曾经上书阮元,称赞国朝汉学“超越前古,至矣盛矣,蔑以加矣”,接着话锋一转,真意显露,认为“今日之汉学,亦稍过中也”(《上阮芸台宫保书》)[6]351。他在《汉学商兑》中,对自己的学术旨趣毫不掩饰,认为汉唐诸儒于小学经义尚未洞明,不可“谓之汉儒训诂、名物、制度,尽得圣道之传也”,断言“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21]125。他指出今世有为汉学训诂者,“必欲寻汉人纷歧异说,复汨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21]1(《序例》)。
显然,方东树在序文中有意模糊或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不能在集体纪念盛事之际,公开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不过,他那种有意淡化、模糊的书写方式,又何尝不是一种维护宋儒义理之学的隐晦策略呢?
十余年后,方东树终于在《重至学海堂》诗中,无所顾忌,一吐心声。诗云:“南纪向文明,朱鸟当离位。人物首曲江,如羽在旌旞。近世陈湛徒,儒术自轩轾。未暇泾渭别,劣得洙泗比。六籍暴秦来,文字未终弃。道丧辞又枝,祸甚焚坑崇。维昔何邵公,学海占相谓。观其解《公羊》,大义颇颠踬。谬种晚流宕,异学煽风气。国朝乾嘉中,儒林若羹沸。谈理仇真儒,逃难覔碎义。鬼方欲覃及,何论中国奰。末也本则亡,王熄霸全炽。率阔具予圣,侈张不知忌。胡思畏圣言,个欲立新帜。卫道仰大贤,宣风仗连帅。所以创此堂,根源古学记。”[6]534-535此诗创作于道光十七年(1837),方东树因总督邓廷桢之邀又一次来到广州,重游学海堂,有感而发,详细叙述了学海堂创建的起因和背景。与《学海堂铭并序》相比,方东树重本卫道、反对谬种异学之意,昭然可见。
《汉晋名誉考》系拟学海堂课,收入《学海堂集》。此文围绕汉晋士人名、实问题,展开考论。首先,考论汉晋以前之士人,认为三代之人才未尝立名,“所可得而名者,惟循其实而加之以名而已矣”,如舜、周太王、周文王、周武王等人,就是如此;而其后的孔孟之贤,亦是“实先而名后,实至而名归”。在方东树那里,“名”指名誉,“实”指道德修养,三代之人才、孔孟之贤皆是有名有实,名实相符。开篇如此立论,意在为后面考量汉晋士人树立标准。接下来,重点考论东汉以至六朝之人,“春秋列国卿大夫及于汉兴将相名臣”,大抵争于名利,名不符实;东汉前中期,文士皆喜立名,其中“良有不可得而磨灭者”,“名体虽殊,风轨足尚”[6]475;逮至末造,文士竞得虚誉,钓采华名,实之不副。三分之际,虽不尚名誉,然魏吴之士肇开两晋名士之习,“隆玄学而尚清谈,疏礼法而践名教”[6]475。自是以逮梁陈,江南人物声华赫赫,名动天下。逮及李唐,名望犹存。由此,方东树展开进一步论述,认为:“远自汉魏三分,逮于隋唐一统,……独是古今以来,闇契姱修者寡,暴智燿世者众。但慕其华,不寻其实。”[6]475也就是说,他认为汉晋士人好虚名,不求实,不修身,不务本。最后,他不仅假设:“使汉晋之士矫易去就,则三代何远焉。”还戛然收束全篇:“故邹鲁之统,千四百年至宋而始续。”[6]478此处推崇宋儒之意,点出即止,简练斩截,然韵味深长。
《孔雀赋》在方东树文章中较为特殊,它是仅有的一篇赋作,而且还是拟作。《孔雀赋》最早由曹植所作(今已佚),杨修在《孔雀赋并序》中揭示其内容主旨:世人初见孔雀,视为奇伟,久则习以为常,视若无睹,故临淄侯曹植“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兴志而作赋”[22]。据陈元龙《历代赋汇》,在曹植之后,魏之钟会、西晋之左芬、南宋之林希逸、明之周靖履等人皆有同题之作,其旨意大抵不出曹植赋之囿。方东树所拟《孔雀赋》,殆有深意,不能以游戏之作视之。本赋拟杨修《孔雀赋》,体物铺陈,巧借杨修之口,抒发心中愤懑,写出了孔雀陷入牢笼后进退失据、忍辱委命的境况与心态:“唯饰表以招累,懵潜身而远辱。仰天路而靡救,虽百悔其焉赎。盖患莫大于有身,而咎恒生于失足。”[6]471这种境况与心态,又颇似方东树入居阮元幕府时的遭际心态。方东树论学论文之宗旨,与阮元异趣,也与幕府内江藩、曾钊、吴兰修等汉学家异趣,在幕府内并不见重。因而,这篇《孔雀赋》也隐晦地反映了汉宋之争背景下方东树的特殊心态。
综上,方东树为谋生计,两度游居阮元幕府,不得不忍受着幕府内浓厚的汉学风气。在学海堂内,他与汉学家们一道参与公共活动,赋诗课文。推崇宋学的他,难免会有屈己从人之处,但尊奉程朱义理之学的初心未改。这三篇骈文,不仅隐晦地反映了他维护宋学的初心,也曲折地反映出他在幕府内复杂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
三、入邓廷桢幕府与音韵学思想的展露
道光六年(1826),方东树自粤返里后,有过客居安徽巡抚邓廷桢幕府的短暂经历。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复赴粤东,再客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三年后归里。方东树与邓廷桢先后师从姚鼐,有同门之谊。这层关系的存在,拉近了宾主之间的心理距离和情感距离。双方相处融洽,屡有雅集酬和,论艺谈文。方东树有诗《嶰筠中丞以双研斋诗集命为作序因题其卷》云:“开府匡时切,论文暇日亲。”[6]518还谦称“受恩愧已宏,十年蒙暍荫”[6]518。他在邓廷桢幕府期间,写下了不少诗文,其中一些是代撰之作,如《安徽通志序》《粤海关志序》《七经纪闻序》等。就骈文作品而言,有《谢邓中丞启》《拟进安徽通志表》(代撰)①按,《拟进安徽通志表》是代撰之作,其中蕴含的方志学思想,难以辨清是否完全归属于方东树,故此处不予讨论和阐析。。
《谢邓中丞启》是方东树文集中仅有的一篇骈体启文。“邓中丞”即邓廷桢,时任安徽巡抚。他审阅了方东树之父方绩的《屈子正音》,并且有意代刊,这让方东树十分感激。由于启这一文体“明慎之旨,侔书为有余”[23],方东树遂用以致谢。
方东树呈请邓廷桢审阅《屈子正音》,固然有假以自重之意,但主因在于邓廷桢精通古音,深研双声和叠韵。邓廷桢后来总督两广时撰写的《诗双声叠韵谱》《说文双声叠韵谱》,即可觇其音学造诣之高。可以说,邓廷桢在方东树的交际关系网络中,确实是校对《屈子正音》的合适人选。
《屈子正音》分三卷,卷上《离骚》《九歌》;卷中《天问》《九章》;卷下《远游》《卜居》《渔父》《招魂》。每篇作品韵脚处,方绩均予以注音。其实,《楚辞》注音,由来已久。隋代释道骞《楚辞音》影响较大,及宋之时,此书亡佚,但影响犹在,朱熹《楚辞章句》“也习用其法于不知不觉之中,而常以叶韵直音之类出之,再证以《广韵》”[24]。据方绩《自叙》,此书正音以《广韵》为主,其《广韵》之谬者,以古音正之,同时于吴棫《韵补》之误者亦悉正之[25]117。由此来看,方绩的正音工作,并未曾参考明清以来的音学研究成果②《方东树集》卷三《刻屈子正音序》:“顾先生此书作于乾隆壬寅,其时顾氏书虽行,而江氏、戴氏之书犹未盛出,段氏、孔氏抑又后矣,故其分部审音如鱼、侯、萧、尤之类,不能无小失。继起者易周,而作始者难密,斯固古今之通趣与?”(第268页),此序系方东树代邓廷桢所作。。这可能与他长期僻居乡里、闻见局限有关,方东树即自谓“先人空山隐雾,幽谷潜姿”[6]479。《屈子正音》中存在舛漏之处,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本书到了邓廷桢手中后,他不仅“摆落常调手笔,子细详论,究其巢穴”[6]478,还让方东树“率据胸臆见知,逐条申答,以求至是,不必回隐”[6]478。道光七年,在邓廷桢的帮助下,经过一番精心校订的《屈子正音》,终于在南京刊印面世。
方东树在《谢邓中丞启》中,除了表示谢意外,还着重表露了他的音韵学思想。首先,他谈音学的起源:“树闻音学之起,实本声气之原。击辕拊缶,应风雅而感和;破斧登天,构鬼神而写韵。天籁地籁,累吹万之殊声;笙均磬均,象奋雷而为豫。轻清重浊,变出自然;喉舌齿唇,递而相及。于是联之以双声,纽之以叠韵。参差窈窕,标万古兴物之风流;灿烂锦衾,播千载怀人之雅韵。是知中天帝陛,已传喜起之歌;何必蛮府参军,始办娵隅之句。”[6]479-480他认为音学之起,本原于自然之声气。因为自然界的声响,引发了人类的注意和拟仿。音之轻、清、重、浊,即“变出自然”。至于喉、舌、齿、唇、牙之五音,则是人的呼吸器官、鼻腔、口腔、声带等发音器官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实,当代研究也表明:“汉语中有许多词的语音形式,其来源就是对自然和人类的声音即自然之音的模仿或搬用。”[26]由此来看,方东树对音学起源的认识还比较到位。
其次,阐论清代以前音韵之学演变的情况。方东树说:“夫圣不虚作,六书固曰审音;而袐未全宣,两汉惟传读若。设法以取之,立度以均之。反切由是而兴焉,韵书因之以起矣。然而孙刘释音,虽精于耳学;或者马班作赋,仍病于聱牙。周沈以来,四声斯显。平上去入,固神解之创获;天子圣哲,弥常语所易知。由是而吕忱、孙愐,则源流祖构;李涪、沈重,或臆说滋讹。颜之推讥江南学士,自为凡例;魏华父诮魏晋俗师,强立两音。”[6]479-480他认为,圣人造字,并不虚作,必有依据,有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之别,每字皆有形、声、义,如欲识字,必先辨析字形,审音辨义。两汉时人即以“读若”注音,许慎《说文解字》堪称代表,然“秘未全宣”,比如对无同音之字或生僻的同音之字,则难以注音。后来,反切之法出现,韵书也因之以起,至六朝时,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问世,“四声斯显”。这对字音依韵分类产生重要影响。其实,早在西晋吕静《韵集》中,就已有韵部之分,至隋陆法言《切韵》,酌古鉴今,兼顾南北,一总前代韵书。至唐,孙愐以之为基础加以增订,名为《唐韵》。当然,在音韵之学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古今音的认识问题,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观念和做法。如北周沈重提出“协句”说;唐李涪刊误《切韵》,别白上去,改吴音以归本音,等等。然而,这些观念和做法都难免存在问题,造成“臆说滋讹”,引起了颜之推、魏了翁等人的批评。
直到吴棫的出现,古音问题才有了新的认识。故而,方东树接着说:“疑今韵,求古韵,大辂椎轮,蓝缕筚路。平心而论,吴棫之功,实维称首。特四声互用,犹昧于不烦改字之言;即两界相通,终未达古音缓读之故。夫古今敛侈有异读,然后有协句叶韵之求;省转假借有本音,然后有字母等韵之法。要之双声叠韵在前,字母等韵在后。有叠韵,而后人因有二百六部;有双声,而后人因有三十六母。四声昉于六朝,不可谓古人不知叠韵;字母起于唐季,不可谓古人不识双声。祥符以还,韵书倂省,日趋陋妄;守温而后,华梵争辨,益属歧旁。”[6]480南宋吴棫一反唐代陆德明的“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提出古韵通转之说,著《诗补音》《韵补》,说明古今音之别。此外,宋人在唐季守温创造三十字母基础上提出三十六字母,发展出等韵之学。这些都为后人研究古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看来,方东树知晓音韵学的发展历程,且能洞察其中的业绩与不足。
再次,方东树称赞本朝音学的成就:“爰及近代,通儒崛起。陈第、顾绛始溯源而精骛;江永、戴震继沿波而讨论。本证旁证,《易》音《诗》音,并驱六经之中,独立千载之后。其余撰述,各足专家。莫不辨晰磝碻,读通雌霓。盖臻真境,自发天藏。不比狂蕐,徒生客慧。”[6]480他的这段评价,比较符合清前中期古音学研究的实际情况。自明代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吹响“清代古音学的前奏”[27];其后,顾炎武又著《音学五书》,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奠一代音学之基。至乾嘉时期,江永著《古韵标准》分古韵为平上去声十三部、入声八部;戴震受江永、段玉裁影响,著《声韵考》《声类表》,分古韵为七类二十部。“其余撰述”如孔广森《诗声类》、王念孙《诗经群经楚辞韵谱》、江有诰《音学十书》等,对上古音的认识益加邃密精深,蔚为大观。清代古音学成就之高,让方东树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赞不绝口。他为邓廷桢代撰《屈子正音序》时称:“国初至今日,音学大明。江氏、戴氏、段氏、孔氏承陈、顾之后,覃精硏思,博辨广证,举魏晋六朝唐宋以来一切讹音谬读一复于古焉。”[6]268他为朋友李元祺《佩文广韵汇编》作序时又称:“我朝文运昌明,超轶前古,凡诸经疏传注莫不仰秉圣裁,聿埀制作,而音韵小学经诸儒讲订,亦复参微造极。同文之盛,薄海风行,洵非陆法言等之智所能囿也。”[6]267(《佩文广韵汇编序》)当然,方东树的赞赏并不为过。后来的王国维评价清学,亦称“经学、史学皆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而小学之中,“训故、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28](《周代金石文韵读序》)。
最后,方东树赞称邓廷桢的音学业绩:“凡兹发守而钩沉,悉足匡缪而正俗。昔陆法言之定《切韵》,商榷者八人;许祭酒之作《说文》,覃精者二纪。未有政余之下,旬日之间,手挥目治,丹墨纷下,倂部分部,了无遯形;从字从声,具达神旨。足使李登失色,吕静叹嗟。”[6]480鉴于邓廷桢的高官身份,方东树的这份过誉评价,符合情理。当然,邓廷桢在古音学上的确有造诣。《屈子正音》中“今按”,系邓氏所作,其中指出了方绩的一些疏误之处。如方绩谓《离骚》中“忍尤而攘诟”,“‘诟’,古音‘古’”;“固前圣之所厚”,“‘厚’,古音‘户’”。邓廷桢曰:“今按:‘诟’,古音‘古’;‘厚’,音‘户’,乃改‘侯’就‘虞’也。亭林颇持此论,然考之《诗》,多窒碍,应读如字。《天保》首章‘厚’字不入韵,《巧言》五章与‘树’‘数’口韵,‘树’古读若‘豆’,‘数’古音‘薮’。《卷阿》三章与主韵,主古音朱陬反。《广韵》入四十五‘厚’,不误。即依《韵补》之说,亦当入‘麌’,不当入‘语’矣。”[25]119
方东树在《屈子正音》中也留下了大量按语,这是他治古音学的心得体会。不仅如此,他还研读过邵长蘅的《古今韵略》,知其弊病,认为此书“以今韵本求古音,坿载纷然,止标汉魏、杜、韩诗为准。既不能如陈、顾诸君力求古经,以订周、沈四声之失;又不能著明《广韵》二百六部之旧,使学者晓然知唐宋人所用之韵之祖本”(《佩文广韵汇编序》)[6]267。后来,他赴广东,在邓廷桢幕府内,与邓氏“相依之久,时时窃闻绪论”,在古音学上认知愈深。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他为好友曾钊《二十一部古韵》作序,序文用对话体,表露了他对古韵分部的看法;同年冬十一月,受邓廷桢之命作《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序文两篇(其中一篇代邓廷桢撰),也表露了他对双声、叠韵的认识。
总而言之,《谢邓中丞启》较早表露出方东树的音韵学思想。他的音学知识,除了家学传承外,也与个人钻研有关。他在《汉学商兑》中尝言“宋儒义理,原未歧训诂为二而废之”[24]126,表明他钻研训诂,其目的在于通达古人义理,并非像汉学家那样舍义理而空言训诂。方东树虽未留下专门的音韵学著述,但其有关音韵学的诸多见解,在嘉道时期桐城地区文人的学术谱系中并不多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桐城学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四、结 语
清代是骈文创作复兴的时代,尤其是嘉道年间,骈散并行的观念在文坛已呈流行之势。以古文起家的桐城派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在这个文人集群中,桐城刘开、上元梅曾亮等人兼擅骈散,蜚声文坛,堪称典型。与刘、梅二人交善的方东树,亦操觚骈文。尽管它们现存数量不多,艺术成就也逊于刘、梅,但仍有独特的思想价值。
方东树的骈文大多作于游幕期间,不仅反映了他在不同幕府的生活经历,还呈现出其不同面相的思想世界。在文学思想上,他主张骈散同源,运意遣词相同。这反映出嘉道时期桐城派在骈散之争问题上出现了新动向。在学术思想上,他尊崇宋儒理学,并极力维护之;他也不是一味地反对汉学,相反他在古音学上也有一些钻研和心得。可以说,方东树骈文中的这些思想面相,于散文和诗歌中所蕴含的文学、学术思想而言,或能弥补其不足,或可相得益彰,是建构方东树思想世界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