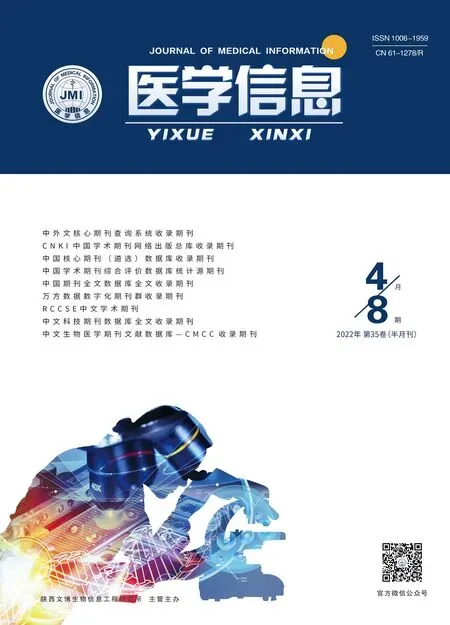抗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中成药研究进展
2022-11-23帅苍南张玉亭耿嘉蔚
帅苍南,张玉亭,刘 敏,耿嘉蔚
(1.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2.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及肝病科,云南 昆明 650000)
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是我国流行最广泛,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也是导致肝纤维化(liver fibrosis,LF)的主要原因。LF 是由于肝脏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的弥漫性过度沉积与异常分布所导致的,随着病程的发展可能进展为肝硬化及肝癌[1]。目前大量研究表明[2,3],如果在LF的早期进行临床干预,部分患者可能实现LF的逆转,从而改善预后。有研究表明[4],中医药在抗LF 治疗中具有明显优势。本文旨在综述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医药治疗CHB 伴LF(包括肝硬化)的研究进展,并基于中医辨证论治理论,探讨复方鳖甲软肝片、安络化纤丸和扶正化瘀胶囊等常用的抗LF 中成药在临床上的应用指征、治疗效果及药物不良反应。
1 中西医对LF的认识
西医学认为[5],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HSC)的活化是形成LF的关键过程。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诱导的机体免疫应答可导致肝实质细胞损伤、炎症及凋亡,促使邻近的Kupffer 细胞、窦内皮细胞和血小板等通过旁分泌作用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激活HSC。而活化的HSC 增生后可分泌大量的ECM,导致LF的形成。因此,抗病毒、抗炎、保肝、抗脂质过氧化是抗LF 研究的重要内容[6-8]。
中医学本无LF 病名记载。历代医家对LF的中医病因病机认识各不相同,但多数医家认为,湿热疫毒是本病的主要病因,也可同时兼有正虚和血瘀。清·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提出“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入络”,指出LF的病机是湿热毒邪外袭,使肝失调达,疏泄不利,肝郁气滞,而日久则气滞血瘀,瘀热互结,阻塞脉络,最终形成LF。现代中医根据LF 和肝硬化的病理变化和临床表现,归纳在“积聚”“胁痛”等疾病范畴。关幼波[9]认为,本病之本为气虚血瘀,而湿热疫毒留伏血分为标。叶放等[10]研究将LF的总病机高度概括为湿热瘀毒。王灵台等[11]研究提出,LF 病机主要是肾精肾气亏损,或命门之火不足,兼夹湿热,肾虚是本病关键。
2 关于CHB 和LF的中医证型相关研究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疗疾病的特色与优势。2018 年中医临床诊疗指南[12]将CHB 中医证型分为肝胆湿热证、肝郁脾虚证、肝肾阴虚证、瘀血阻络证、脾肾阳虚证5 型。2019 年中西医LF 指南[13]则认为CHB 相关LF的基本证型为瘀血阻络证,同时可兼夹肝胆湿热证、肝郁脾虚证及肝肾阴虚证。有研究显示[14],CHB 患者临床最常见证候为肝郁脾虚证。
目前,中医学界对中医证型的诊断标准和分类具有很大主观性。中医证型的客观化实验室指标和新型生物标志物研究正成为学术前沿和热点。高风琴等[15]对48 例CHB 患者的肝组织病理和中医辨证分型之间进行探讨,发现肝胆湿热证患者的肝组织炎症程度较重,纤维化程度较轻;而肝郁脾虚证患者纤维化程度较重,炎症程度较轻(P<0.05);在肝硬化阶段,瘀血阻络证则较为明显。杨婵娟等[16]探讨CHB 患者中肝郁脾虚证与脾胃湿热证之间基因表达差异,发现以 LOC340508、HIST2H2BE、MPL、FLJ22536、TUBA8、NT5M、EG-FL7、PTPRF、TSPAN33 等9 个基因差异最显著,提示CHB 患者中医证型分类具有基因组学依据。Liu X 等[17]发现,肾阳虚证CHB 患者与HLA-DRB1/DQB1 基因多态性、高HBV-DNA 病毒载量(≥2000 IU/ml)相关。Shi MJ 等[18]发现在早期LF的CHB 患者中,相较于肝郁脾虚血瘀证,气虚血瘀证的患者肝组织中miR-654-3p及其靶基因PTEN、ATM的表达明显上调。Liu Y 等[19]发现血浆蛋白组中免疫球蛋白J 链(immunoglobulin J-chains,IGJ)在不同中医证型间表达差异显著(P<0.05)。Xie HP等[20]发现289 例CHB 患者中,5 种不同中医证型间血清HBsAg 定量水平差异显著(P<0.05),脾肾虚证(4.48 log10IU/ml)最高,而肝肾虚证(3.60 log10IU/ml)和瘀血阻络证(3.81 log10IU/ml)最低。
3 中成药抗LF的研究进展
目前,西医学尚缺乏有效的抗LF的药物及治疗方法,中医药则在防治CHB 和LF 方面优势明显。由于中成药具有性质稳定,疗效确切,服用、携带、贮藏保管方便等优点,因此在国内临床广泛应用。已批准上市的抗LF 中成药多达数十种。其中,复方鳖甲软肝片、安络化纤丸、扶正化瘀胶囊三者在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中均已显示一定的抗LF 作用,临床应用较为广泛。
复方鳖甲软肝片是由鳖甲、赤芍、冬虫夏草、三七、紫河车、连翘、当归、莪术、党参、黄芪、板蓝根11味中药组成,其中最为重要的中药配伍是鳖甲、赤芍和冬虫夏草。鳖甲抗LF 机制[21]与其有效肽类物质抑制促炎细胞因子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s,TIMPs)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平衡,下调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AM)表达,从而调控ECM 增殖以及调控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TGF-β1/Smads、TIMPs/MMPs 信号通路等多种途径有关。赤芍总苷[22]能阻断放射性LF 大鼠的TGF-β1/Smad 信号传导通路,抗LF 作用显著。有研究表明[23-25],冬虫夏草多糖具有增强Kupffer 细胞功能和降低HSC 活化;作用TGF-β1,血小板衍生生长因 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TNF-α,IL 等炎症细胞因子,降低炎症反应;增加胶原酶mRNA的表达,促进胶原降解;提高肝脏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的活性,减少脂质过氧化物的产生等作用,进而抗LF。周光德等[26]报道,复方鳖甲软肝片能抑制HSC 活化,并促进活化HSC 凋亡。袁强等[27]报道,复方鳖甲软肝片抗LF 机制与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有关。赵景民等[28]认为,复方鳖甲软肝片能抑制大鼠肝组织内TIMP-1 和TIMP-2表达,促进MMPs 和膜型MMPs及其mRNA 表达,同时抑制TGF-β1及其mRNA。此外,据Rong G 等[29]报道,在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中,在基线和治疗72 周后分别行肝穿的复方鳖甲软肝片联合恩替卡韦(entecavir,ETV)治疗CHB 相关LF 患者358 例LF 逆转率(即Ishak 纤维化评分下降≥1 分)显著高于单用ETV的对照组347 例(40%vs31.8%,P=0.0069),而在388 例基线水平为肝硬化(即Ishak 纤维化评分≥5)患者中,联合治疗组肝硬化逆转率(即Ishak 纤维化评分≤4)显著高于对照组(41.5%vs30.7%,P=0.010)。
安络化纤丸由地黄、三七、水蛭、僵蚕、地龙、白术、郁金、牛黄、瓦楞子、牡丹皮、大黄、生麦芽、鸡内金、水牛角浓缩粉等14 味中药组成,其中最主要配伍是三七、水蛭和牛黄。三七总皂苷抗LF 主要机制[30]是通过多途径抑制TGF-β1表达,降低肝组织羟脯氨酸(hydroxyproline,Hyp)含量,进而抑制肝组织中胶原纤维和HSC 细胞的活化。水蛭素抗LF 机制[31,32]主要是通过抑制HSC 胞浆游离钙升高,阻断或抑制HSC的AngⅡ信号转导通路,下调Smad4 mRNA的表达,进而抑制HSC 活化与增殖等。牛黄的主要抗LF 药理活性成分为熊去氧胆酸,其机制[33]与减少TGF-β1合成,抑制HSC 细胞活化,抑制ECM 合成有关。据报道[34,35],安络化纤丸能通过改善肝功能,增强MMP-13的表达,抑制MMP-2 和TIMP-1/2的表达,并抑制TGF-β1合成,抑制HSC 激活等作用机制,延缓LF。有研究[36]纳入在基线和治疗78 周后分别行肝穿的219 例CHB 患者,安络化纤丸联合ETV治疗78 周患者LF 改善率为36.53%,LF 进展率为23.29%。此外,研究还发现,LF 改善与基线水平纤维化分级(t=-6.868,P<0.001)、LSM 值(t=-2.040,P=0.044)和应用联合治疗(t=-2.035,P=0.045)有关,进一步分层分析发现,基线轻度纤维化(F<3)联合治疗后LF的改善率显著高于单用ETV 对照组(54.74%vs33.33%,P=0.016),联合治疗组LF 进展率低于对照组(13.68%vs18.75%,P=0.466),而在基线F<3的患者中,联合治疗组LF 改善和稳定的患者比例高于对照组(68.08%vs51.72%),但联合治疗组较对照组在病毒学应答、生物化学应答、HBeAg病毒学转换率和炎症改善率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扶正化瘀胶囊由丹参、虫草菌粉、桃仁、绞股蓝、松花粉和五味子6 味中药组成,主要抗LF 药物为丹参。丹参酮ⅡA 能显著抑制AngⅡ诱导的HSC 中TGF-β1,Smad2 和Smad4的mRNA及蛋白表达,增强Smad6,Smad7 蛋白的表达,并通过在TGF-β1/Smads 信号通路上多点调节,抑制HSC的活化并促进其凋亡[37,38]。有研究表明[39],扶正化瘀胶囊抗LF 主要机制包括下调TGF-β1/Smads 信号通路,抑制HSC 活化、炎症反应、减少ECM 沉积、保护肝细胞、抑制Kupffer 细胞活化、抑制肝窦毛细血管化和血管生成、促进肝再生等多靶点的综合作用。研究报道[40],纳入基线水平为乙肝未治且Ishak 纤维化评分≥3 分的22 例扶正化瘀胶囊联合ETV 治疗的CHB患者和单用ETV 对照组24 例,在治疗48 周后再次行肝穿检查,联合组患者LF 逆转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82%vs54%,P<0.05),联合组的坏死性炎症改善率高于对照组(59%vs25%,P<0.05),在双光子显微镜下分析的80 多个胶原参数中,与对照组相比,联合组有5 个指标明显下降(P<0.05)。此外,48 周治疗结束后,两组之间的生化、病毒学或血清学应答率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 抗LF 中成药的不同中医证型间比较
与西医不同,中医治疗学基于“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两大理论。中医理论将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分为不同证型,每种证型均对应一种特定的治疗方案。因此,不同中医证型的CHB 伴LF 患者应采用不同的中成药治疗。
复方鳖甲软肝片具有软坚散结、化瘀解毒和益气养血的功效,适用于以胁肋隐痛或肋下痞块,面色晦黯,脘腹胀满,纳差便溏,神疲乏力,口干口苦,赤缕红丝等为主要临床表现,气血两虚、瘀血阻络证的CHB 伴LF 患者。安络化纤丸具有健脾养肝、凉血活血、软坚散结的功效,较适用于肝脾两虚、瘀热互结证。而扶正化瘀胶囊具有扶助正气、活血祛瘀和益精养肝的功效,临床上适用于胁肋隐痛,遇劳加重,腰膝酸软,两目干涩,口燥咽干,失眠多梦,或五心烦热;舌红或有裂纹,少苔或无苔,脉细数之肝肾阴虚证。
值得注意的是,LF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中医证型变化,需要根据中医辨证使用不同适应症的抗LF 中成药治疗,以达到最佳疗效。
5 中草药导致的DILI 与抗LF 中成药临床合理应用
近年来,中草药,尤其是含有多味中药、药理活性成分复杂、作用机制不明,药物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的中药复方和中成药在临床上的安全应用越来越受到关注[41]。目前,全世界还没有关于中草药相关肝损伤(herb-induced liver injury,HILI)发病率的权威数据,各研究中心报道的HILI的发病率差别很大,HILI的真实发病率仍然未知[42]。此外,对因中医辨证失误导致的HILI 不良事件发生率也缺乏相关研究和报道[42]。HILI 相关危险因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草药本身含有有毒成分(如何首乌、菊三七、雷公藤等),这类肝损伤程度与用药剂量呈正比,潜伏期短,可以检测和预防;另一类是由于临床使用不合理,不遵循中医理论,辨证分型错误导致肝损伤。对于既往有基础肝病,在服用中成药治疗的过程中发现肝损伤的患者,由于尚缺乏诊断HILI的特异性方法和客观特异实验室标志物,很难鉴别是CHB 肝炎活动还是HILI 药物不良反应。如在中医药和日本汉方医学(Japanese Kampo)中用于抗LF 和预防肝细胞癌的中成药小柴胡汤(Sho-saiko-to,TJ-9),因为违背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长期不合理大量服用,导致慢性肝病(包括CHB 和慢性丙型肝炎)基础患者出现急性肝损伤和胆汁淤积症[43-45];而在停用小柴胡汤后的4~8 周内,患者肝损伤能迅速缓解且预后良好。此外,小柴胡汤和干扰素联合治疗CHB 患者还会导致肺纤维化和间质性肺炎[46],其他更为罕见的不良反应还有自身免疫性肝炎[47,48]和急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49]。
目前,减少临床上HILI 事件发生应以预防为主。首先要重视中草药的肝毒性,对固有型或剂量依赖型肝毒性的中草药要慎重选用,严格限制剂量与疗程。此外,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提高对HILI的认识。同时提高中医医师的中医辨证论治能力和医学水平,对开中成药的西医医师进行中医辨证论治的相关培训,以避免因中医辨证诊断失误导致的HILI。对于既往有慢性肝病基础并长期服用中草药的患者,应加强肝功能监测。由于许多中成药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目前暂不推荐抗LF 中成药在西医院内大规模推广应用,也不推荐婴幼儿、老年人、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服用。国家及相关主管部门也应加强对中草药制品和中成药上市销售后的药物不良反应事件的监测,实行药物警戒制度。
6 总结与展望
LF 是一个涉及多个环节与因素的主动进展与动态变化的复杂病理过程。因此,应该结合患者自身病情的发展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LF 进行有效治疗。基于辨证论治理论的中医药治疗LF 有其独特疗效优势,但目前中成药在临床的应用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临床上开具中成药的多为西医,难以根据患者辨证开具合适的中成药;且目前对CHB 导致的LF的中医证型及辨证基本规律及肝组织病理学本质仍缺乏规范化研究,辨证标准尚未统一。其次,基于人群的大样本的临床研究仍然较少,且目前仍缺乏基于肝脏组织病理改变评估疗效的试验。中医药抗LF的药理机制仍不明确,不同组成、配伍和功效的中成药临床适应证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中药安全问题,尤其是中草药导致的HILI 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临床医生应在医疗实践中对于这些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努力改进,必将有益于中医药抗LF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并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