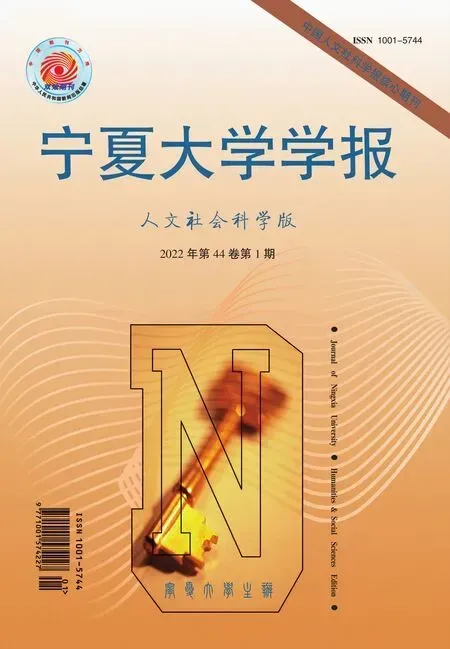元代士人与国家的互动
——基于藏书的考量
2022-11-23侯赛华张金铣
侯赛华,张金铣
(山西传媒学院 思政部,山西 晋中 030000)
探究国家藏书,无法割裂士人藏书活动对其的辐射作用。每当新朝初立,国家除接手前朝“遗书”之外,亦向民间“征书”用于丰富国库,且士人主动献书国家的事例亦不少。当国家稳定发展、经济繁荣阶段,国家又出台相应政策促进士人藏书的发展。总体而言,国家从统治阶级层面促进了士人藏书活动,士人也以其藏书、著书等补充着国家藏书,二者存在着一个互动关系。本文探究元代士人以藏书活动与国家的互动。
一 元初士人与南北藏书交流
元初(包括金元、宋元)由于政治问题导致在文化上呈现南北对峙局面,时南北藏书交流受阻,直待以赵复、姚枢等儒士的助力,才使得儒学逐渐北传,南北文化事业建设缓慢走向正轨。
(一)元初南北藏书不互状态
“金、元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1]。宋、元时,南宋政权偏安江南一隅,而当时“二程”、张载、朱熹等均为江南地区理学大家,但他们的学说主要传播于南宋地区,北方士人则知之甚少,相应书籍在北方的传承十分有限。
元初北人不得南人藏书、南人不知北人藏书的事迹众多,如南宋郑樵所著《通志》200 卷,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部通史巨帙,元时刊印于三山(福州)郡庠,藏之于秘阁。吴绎《通志疏》中记载,该书“虽经呈进,而北方学者概不多见”[2],因而北方士人很难传阅学习。吴绎任福州路总管期间,在广泛征求同僚意见的基础上,捐己俸刊印五十部“散之江北诸郡,嘉惠后学,熟而复之”[3],并在至治二年(1322年)作《通志序》。许有壬《雪斋书院记》记载,“金源氏之有中土,虽以科举取士,名尚儒治,不过场屋文字,而道之大者盖漠如也。天相斯文,新安朱夫子出,性理之学,遂集大成。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学者不知有所谓四书也”[4]。虞集《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载,“干戈未宁,《六经》板本,中原绝少,学者皆自抄写以成书。其后朱子《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传至北方,学者传授,版本至者尚寡,犹不能无事手录”[5]。然直至至元十年(1273年),世祖在元大都始设秘书监,国家层面的藏书工作才正式启动。
(二)士人对元初南北藏书交流的助力
南北学术交流发展史上重要士人有赵复、姚枢、许衡等。“元兵南下江、汉,得赵复,朱子之书始传于北。姚枢、许衡、窦默、刘因辈翕然从之”[6]。
赵复是将程朱理学系统性传到北方的第一人。朱右《元朝文颖序》记载:“方南北未通,江汉赵氏,默记朱子《四书集注》及各经传,身载以北”[7]。杨宏道《送赵仁甫序》记载:“旃蒙协洽,君始北徙,羁穷于燕。已而燕之士大夫闻其议论证据,翕然尊师之,执经北面者二毛半焉。乃撰其所闻为书,刻之,目曰《伊洛发挥》,印数百本,载之南游,达其道于赵、魏、东平,遂达于四方”[8]。以上史料均论及赵复对理学传播作出的重要贡献。后杨惟中和姚枢建议建太极书院,选取理学书籍八千余卷,请赵复讲学其中,“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9]。
姚枢在蒙军破许州时投靠杨惟中于燕京(今北京)。1235年,姚枢从窝阔台南征,过德安得江汉赵复,赵复尽出程、朱二子著书于姚枢。姚枢“始得程颐、朱熹之书”[10],当时南北书籍交流受阻,赵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11]。姚枢得之“躬行实践,发明授徒”[12],时江汉到燕京从赵复学经者众多,至此北方经学开始复出。后姚枢在隐居卫辉县期间“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并请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13]。此外,因当时《小学》流传未广,姚枢教弟子杨古为沈括活字印刷术,将《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等书散布四方。在姚枢隐居卫辉期间许衡造访苏门(河南省辉县西北),“相依以居,卒为大儒”,尽录姚枢藏书[14]。世祖在潜邸时遣赵璧征姚枢进京,时姚枢见忽必烈“可大有为”,于是尽平生所学“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次及救时之弊,为三十条,疏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15]。世祖授命姚枢教授太子经学,后受命征大理、定礼乐、议大举等事宜,元初政策多受其影响。至元十三年(1276年)姚枢去世于京师,在1347年为纪念姚枢建立雪斋书院,时雪斋书院是北方经学的重要传播基地。
当姚枢居苏门以传道为己任,传伊洛之学于赵复处时,“鲁斋先生”许衡迁居辉州苏门,得“《易》程氏传、《春秋》胡氏传、《书》蔡氏传、《诗》朱氏传,与《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小学之书”[16],以上皆手抄而归。当时“国家兴隆之初,南北未一”[17],许衡得朱子之书与边境,“读之,起敬起畏,乃帅学者尽弃旧学而学焉。既相世庙,遂以其学推行天下,迄今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者”[18],“而儒者之道不废”[19]皆源于许衡之力。
从藏书史论及,元初南北对峙,程朱理学时多传于南方,然“长期的分裂割据,虽使南北思想文化的发展有了较大差异,但是,汉族儒家思想文化的传统,是南北士人的基本思想内涵”[20]。后蒙元统治初期,北方地区得以流传朱子之学则得益于宋儒传播,并将其最终发展到独尊地位。
二 士人藏书对国家藏书的补充
国家藏书来源是多样的,一般情况下首先是通过接收前朝遗书补充国藏。其次,除以国家层面致力于藏书活动外,士人献书也不断充实着国家藏书,国家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
(一)国家征书与士人藏书
在国家藏书来源上除接手前代遗书外,元政府也组织士人编纂图书,其规模最宏大者当属对前朝正史的编纂。在至正三年(1343年)开始撰修宋、辽、金三史前,顺帝就曾下诏购求士人藏书,其中以袁桷为主的士人对史馆购书作出了重要贡献。袁桷在史馆工作历二十年之久,至正三年任职于翰林国史院时仍兼史职,对三史求书编撰颇有心得,载:“卑职生长南方,辽、金旧事,鲜所知闻。中原诸老,家有其书,必能搜罗会粹,以成信史”[21],“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久湮落,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22],主张到南方求书。袁桷《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将当时修史所缺书籍分为19 部分,如:“宋太祖实录”“杜太后金縢之事”“天圣三朝正史”等[23]。
在此次修史征书活动中,国子助教危素任征书官。为此危素在至正中著《史馆购书目录》,虽然目录现已散佚,但所撰《史馆购书目录序》中对此有简要论述[24]。时危素好友邓子明也曾向政府编修史书贡献藏书,时所献藏书为其祖父邓剡著书。修三史时,危素“衔朝命来江西,至庐陵,求礼部(邓剡)所为书”,邓子明“不隳世学,抱其先祖所著,上进史馆,以成前代之书”[25]。邓剡为宋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官任礼部侍郎等职,为文天祥门友。宋亡邓剡投海,为元兵所救,与文天祥囚禁于建康,得释后张弘范以客礼谒请为子张珪教授讲学。邓剡晚年隐居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著书立说,以所见所闻辑录为野史若干卷,秘不示人。《宋史》记载“方秀夫海上时,记二王事为一书甚悉,以授礼部侍郞邓光荐”[26],崖山之战后邓剡将陆秀夫日记带回庐陵。邓剡所著《填海录》就是在陆秀夫日记的基础上向下延伸记载至卫王、陆秀夫及张世杰之死。在邓子明献书后危素曾回信以表感谢之情。
(二)士人献书与国家藏书
在国家修史活动中除以国家名义向士人征书外,也有士人主动献书助力于史书修撰。在修三史购书活动中,江南藏书家多献自家藏书。“元至正初,史馆遣属官驰驿求书,东南异书颇出。时有蜀帅纽鄰之孙,尽出其家资,遍游江南。四五年间,得书三十万卷,溯峡归蜀,可谓富矣”[27]。在宋禧《代刘同知送危检讨还京师序》中记载,“宋氏之事,窃纪于江南草野间者甚博,实採摭者之所资焉”[28],因此至正四年危素至四明宋氏处购书七千余卷。另外,在至正六年时,危素曾到江南藏书家庄肃家求书,《正德(松江府志)》记载:“至正间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铭简讨危素购书于其家,得五百卷”[29]。庐陵曹毅(字士弘)生前为文数百篇,逝世后由子曹友仁板行于世,为《曹先生文稿》,其多涉宋朝礼乐、文物、名臣、硕儒等史实。至正三年(1343年)诏修三史时,馆丞论辑网罗旧闻,曹毅子曹汝舟将父亲遗书进献朝堂供编史之用,危素《夏小正经传考序》记载:“素以使事求史馆遗书,过句章,得是书于君之子塾孙”[30]。当时史馆所得季敷甫《夏小正经传》来自于其子献书。
元代士人除在国家藏书活动中献书以助力著书活动外,也有一部分士人直接献书作为国家藏书的组成部分。例如郭守敬在任太史令时,将其所著书上进殿前,有“《时候笺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测验书有《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舍杂座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31],后来这些书均藏之官。危素《浸铜要略序》记载,至正十二年德兴张理(字伯雅)任福建宣慰司期满,调官京师,时值国家更钱币之法,因而献其先世《浸铜要略》于朝。宰相以其书之有益经费,为复置兴利场[32]。王天与(字立大,号梅浦)在传承朱熹学说的基础上,辅之以真德秀《西山先生读书记》《大学衍义》等内容,本二家遗意,“有未当,则引诸家说评之。有未备,则引诸家说足之。说俱通者,并存之。间或以臆见按之”[33],“息意科举之学,研精覃思,博采详说”[34],撰《尚书纂传》46 卷,并请友人彭应龙“增广校定”。彭应龙认为“与其藏诸家塾之私,孰若广而流布,与四方同志之士切磋之,以无忘往训”[35]。大德三年王天与被授予临江路儒学教授,得因于宪使臧梦解将是书进献朝廷。江浙儒学提举陈德永《李五峰行状》中记载,至正三年(1343年)时,顺帝征召海内遗逸士入朝为官,时永嘉李孝光被征召入京,授著作郎。在至正七年时,李孝光进《太极图说》,升秘书监丞[36]。
此外,《秘书监志》卷五亦曾记载士人献书秘书库事件,在延祐三年五月仁宗所下圣旨中要求“赵子昂每写来的千字文手卷一十七卷,教秘书监裹裱褙了,好生收拾者。合用的裱褙物料与省家文书应付着”[37]。在延祐六年九月时,“斡赤丞相上奏:‘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曾巽申小名的秀才将他自做大驾卤簿图二轴、书十册,上位根底呈献过’。奉圣旨:‘教续院使将去,与秘书监谭秘卿将往秘书监裹好生收拾者,后头用著去有’”[38]。
值得一提的是士人有关礼乐方面的献书。元初政权甫定,直到中统、至元年间礼乐渐兴,“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来”[39],时有若庐陵曾巽初著《卤簿图》5 卷、《郊祀礼乐图》5 卷,进上江西行省,后太常礼仪使田忠良等将其书上进中央,曾巽初得对玉德殿,后是书藏之秘府。英宗时,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秘书所藏曾巽初图书,而“卤簿大兴”。曾任仕佐郎、淮安路推官等职的周之翰(字子宣),“独在侍仪,明习礼文之事,尝述《朝仪备录》五卷、《朝仪纪原》三卷以进,蒙赐币帛,命以其书藏史馆”[40]。
此外,士人献书助力国藏方面亦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士人献书活动。世祖皇帝在位初期南北混一政权未定,时遗老在位建言献策,使得国家建设初具规模,民族融合始入佳境。在此阶段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部分士人群体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也读书为文、撰写著书,期间有的士人也将其藏书进献官府。畏吾儿人鲁明善(铁柱)在延祐元年任安丰路达鲁花赤时撰《农桑衣食撮要》2 卷,因思食之本,将其献之学宫刊行。察罕以《皇极经世》为准“悉取诸家纪载而集正之”,撰《历代帝王纪年纂要》,欲上进朝廷请程钜夫作序[41]。
元代士人不论为官与否都在以己之力通过献书将著书立说传承下去,但是士人献书国家活动中还有并未成功的案例也值得关注。例如,虞集在《忠史序》中记载,番昜杨玄曾为纪念祖父在宋咸淳末战亡事迹专著《忠史》一书,列夏商以来至宋忠义之士800 余人,“泰定初元,以其书来京师,国史与学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闻,凡三年,不遇而归。且行,来求一言以为识”[42]。
(三)地方官文教与国家藏书
所涉士人对国家藏书助力时,不得不探讨士人在地方上的兴文教政绩,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书籍的补充。例如,吕衍所撰《濮州庙学记》记载到中统以来濮州官员兴学、兴教化情况,初度礼班(朵鲁班)脱脱出弟兄治州期间就开始注重治教与藏书的问题,郡守更迭次达数二十年之久,庙学开始完备。迨至元二十五年前后,哈 又为学宫,时“有师生而经籍弗具,学者无所业于其间”,因此与尹皇甫焱、同守郭钦、判官哈累“表书万八千卷,皮而藏之,日集诸生讲求经义,讨论古今,虽寒暑不废”[43]。大德四年刘敏中撰《柏乡县新修夫子庙记》记载,邑人湖广行中书省检校官贾庭瑞,“以书千余卷施于学(柏乡县新修夫子庙)”[44],藏之庙学书楼,以施惠于家乡。柏乡县旧有孔子庙,但毁于靖康之乱,直至元初教官范天祥、县尹刘世英旷地、修庙才得以复兴。
三 国家政策导向下的士人著书以藏
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伊始,在保留草原游牧特色的同时,吸收传统儒家文化,推行“汉法”。而推行汉法的措施之一就是沿袭儒家传统政权因政府之需而发展相应的国家藏书。与藏书所涉的相关事迹如科举、文教出版、为官途径等政策对士人藏书具有一定的导向性。首先,士人藏书活动还得益于国家藏书对其助力之效,所涉统治者以国家名义赏赐士人书籍以藏,其得益者主要是为官士人。在政权演进中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蒙古帝王还命大臣将儒家经典翻译成国语,赏赐于士人,而这些士人则主要是少数民族群体。另外,士人在著书过程中,其史料来源有的也得益于国藏,如架阁库所藏档案文献。此外,统治阶层还以国家名义刊印士人著书以传,以上种种均涉国家对士人藏书的助力之效。其次,士人为科举、为吏等需要也著藏相应图书,而国家层面的禁书政策也影响到了士人藏书。
(一)士人藏书与国家文献抄录、阅读
图书最原始、最直接的保存与流转方式就是抄录。“古人之读书,凡其有会于心者,则笔而记之,志有得,示无忘也”[45]。而抄录活动中不乏国家藏书的身影,士人得机亦能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这为其著书、藏书提供了便利。
例如,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国朝文类》等传世典籍,就得益于国家藏书。李穑曾指出“苏公在太平全盛之世,四方文学之交游,累朝典则之谙练,又有精敏之才,非独笔札之富也”[46]。而苏天爵丰富的笔札是其能著书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历履丰富为其在藏书、著书活动中摘录国家文献提供了极大便利。赵汸在《治世龟鉴序》载:“参政赵郡苏公早岁居馆阁,尝即经史百氏书,采其切于治道政要者,通为一编,名曰《治世龟鉴》。至简而不遗,甚深而非激,疏通练达而公平之规著,亲切确苦而正大之体存,信为谋王断国者之元龟宝鉴也”[47]。
此外,王鹗、齐履谦等士人著书以藏也得益于国家藏书。至元二年(1265年)王磐、徐世隆、王鹗等摭采《金世宗实录》180 余件成《大定治绩》,“以备乙夜之览,其于圣天子稽古之方,不无万分之一助”[48]。齐履谦在太史院任职时,会朝廷将所收宋三馆图籍置太史院,其得以“昼夜诵读,精思深究,故其学博洽而精通”[49]。齐履谦将其所学阐释于著书之中,专著《易本说》4 卷、《系辞旨畧》2 卷、《蔡氏书传详说》1 卷、《春秋诸国统纪》6 卷等等。
国家除出藏书助力于士人著书、藏书活动外,其所藏档案文献也是士人著书的史源之一。这就涉及国家对所藏档案文献架阁库的管理问题。元朝在承袭宋金档案管理规制的基础上在中央和地方均设架阁库以管理档案文献。国子博士、承德郎张以宁在至正二十年所撰《中书省架阁库题名记》论及中书省架阁库沿革。在中书省署官西侧设库名曰架阁,“凡天下之图书、版籍,计金穀钱帛出纳之文牍,尊闳庋藏,以待夫考徵之用者,咸在焉”,设官管勾二人、吏书写十人,“分厘其事务”,次者十五人,“分周藏史、汉掌故遗制”[50]。
至正九年(1349年)冬,札剌尔为资政院使,任职伊始,首询官府沿革情况,以及所涉政务本末次第,但“前徽政院纪源之书部帙汗漫,而序述弗详”[51]。对于资政院变迁,在东宫时则名詹事院,在东朝则名徽政院,后又曾改建储庆使司及储政院,由于其“更易靡常,新旧交承,文案填委,舛错隐漏,猝难穷竟,故于户口之登耗,财计之盈亏,人材之升黜,工役之作辍,皆无从周知”,时札剌尔认为“古之君子,居其官则思其职。苟非有旧典之可稽,则虽欲举其职,不可得也”[52]。因此令架阁库出所藏故牍,与经历司官与提控掾史等人,精加考核,著3 卷《资正备览》,凡资政院所涉诸司官属之员数品级、系籍人户、拨赐土田、方物贡输、岁赋徵纳、铨选格法、营造规程,彪分胪列均详细刊载。
徐泰亨著书亦利用到了地方架阁库档案。徐泰亨,字和甫,其在任平阳州提控案牍期间“考漕法利病,下至占候探测”,著7 卷《海运纪原》;后任福建帅幕田令史期间,采列郡图籍著若干卷《福建总目》[53]。徐泰亨“读书务以致用,不屑屑于章句”,曾著《端本书》《忠报录》《自警录》《可可抄书》《历仕集》等藏于家,而家谱诗集并藏于家,《海运纪原》《福建总目》则列于官书。
(二)帝王赐书、译书与士人藏书
在帝王赐书、译书方面,元朝以国家层面专设机构负责这类事宜。如《元史·百官志》载艺文监“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者俾兼治之”[54]。在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卷一经类下设译语类,著录汉文译成蒙古文的典籍包括:《尚书节文》(翰林院学士元明善等译进),《蒙古字孝经》(大德十一年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译进),《大学衍义节文》(延祐四年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译),《忠经》《贞观政要》(天历中中书平章政事察罕译),《帝范》四卷,《皇图大训》(天历中翰林奎章阁臣译),鲍完泽朵目《贯通集》《聊珠集》《选玉集》(皆蒙古言语),《达达字母》一册,《蒙古字母百家姓》,《蒙古字训》一册。元朝将部分儒家经典译成国语,供蒙古贵族学习,且建立专门的机构从事此事,是普及汉文化的表现之一,对于多元民族文化融合与建设不无益处,与金、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元代对翻译儒家经典的认识显然更进一步。此外,元设奎章阁除负责藏书活动外,还涉及编辑、翻译、出版图书等任务。文宗皇帝开奎章阁搜集藏书,延经讲学,“以奎章天历之宝,颁赐讲官”[55],赏赐给大臣“以扩大训示百僚,始及朝著之有闻者,而加用二玺焉”[56]。例如,仇济任户部郎中时所藏霑赐本就来自于奎章阁文章赏赐。而奎章阁赏赐给大臣的藏书均印有“天历之宝”,或加用“奎章阁宝”。天历二年,奎章阁学士同翰林国史院官编著《经世大典》等。
元朝诸帝王中尚文治的首推文宗皇帝,“以天纵之圣,历试诸难,既践帝位,海内思治,乃稽典礼,述文章,躬祠郊庙,增建官仪,黼黻治化,咏歌太平”[57]。赵汸《邵庵先生虞公行状》载,“上方好用文学,开奎章阁,置学士员,立艺文监以治书籍,设艺林等库任摹印,将大修圣贤经传之说以为成书,知名之士多见进用。自中朝至于方外,金石之锡,承诏撰作,几无虚日”[58]。奎章阁下属的藏书管理机构所涉书籍均为“皇朝祖宗圣训及番译御史箴、大元通制等书”[59]。
元朝历代帝王赐书、译书最为积极者当属仁宗皇帝。大德十一年(1307年),武宗继位诏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时为皇太子的仁宗“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60]。当时有人进献真德秀《大学衍义》,仁宗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认为“治天下,此一书足矣”[61]。同时下令将《图象孝经》《列女传》并行刊印,颁布赐臣下。据《滋溪文稿》记载:“上(文宗皇帝)雅爱尚文学,敕印真德秀《大学衍义》分赐侍臣,俾知忠君爱民之说”[62]。仁宗继位后览《贞观政要》时,指示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63]延祐二年,仁宗以《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李监“择其切要者译写以进”[64]。“天历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阁,延问道德,以熙圣学,又创艺文监,表章儒术,取其书之关系于治教者,以次摹印而传之”[65]元统三年(1335年)孛术鲁翀《序韵会举要书考》中论及,文宗皇帝时奎章阁得昭武黄公绍所撰葛元鼎写本《韵会举要》,后至顺二年春,翰林应奉余谦承帝命校正,次年完工上进。余谦在校勘《韵会举要》过程中,“念惟韵版文字乖误颇繁,兹既考徵就易”,辑校勘成果著《古今韵会举要》,“获与学书者咸被于天下同文之休”[66]。虞集《饮膳正要序应制》曾记载文宗皇帝赐臣下书籍事件。图帖睦尔“天纵圣明,文思深远,御延阁,阅图书,旦暮有恒,则尊养德性,以酬酢万几,得内圣外王之道焉”,于是孛兰奚,以膳医忽思慧所撰《饮膳正要》上进[67]。中宫命留守金界奴,庀工刻梓,摹印以赐臣下。
此外,《元史》载:泰定帝元年“敕译《列圣制诏》及《大元通制》,刊本赐百官”[68]。危素《君臣政要序》中记载到顺帝赐书、译书事件。至正元年(1341年)九月顺帝出东宣文阁所藏3 卷本《君臣政要》,召翰林学士承旨 、学士朵 直班、崇文少监老老,传敕翰林侍读学士锁南、直学士拔实、崇文太监别里不花、少监老老、宣文阁鉴书画博士王沂、授经郎不答实理、周伯琦等人翻译,书成又敕留守司都事宝哥以突厥字书之[69]。许师敬著《皇图大训》,阿璘帖木儿、忽都鲁迷失曾将其润译成国语。
综合而论,能有机会得到帝王赐书、译书这部分士人多为为官颇有政绩者,对普通士人而言有此丰富藏书实则机会渺茫。
(三)国家对士人藏书刊印的助力
国家除在赐书、译书、档案文书抄录等方面为士人藏书提供一定便利外,也在诸路设局刊印士人著书以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藏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便利之径。
元代刻书事业与宋代相较更为繁荣。宋元“一起代表了中国雕板印刷史上的古典时代,为其鼎盛时期;代表了活字印刷的古典时代,为其奠基时期,承先启后,直接开启了后来活字印刷的先河”[70]。其中在中央层面由太医院的广惠局、医学提举司,兴文署,艺文监的广成局,太史院的印历局;地方上则有各路儒学、各地书院刊板印刷书籍。加之元代雕版印刷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套印技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其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国家层面助力士人藏书刊印的例子,如:“国子祭酒宋公(宋本)既卒,制赠翰林直学士、范阳郡侯,谥正献。其弟翰林修撰褧,次辑遗文为四十卷,将版行之。家贫不克,御史共以为请,遂命江陵佥宪刊诸学宫”[71]。在至正四年(1344年)御史台刻《曹文贞文集》于诸路府学,以“褒崇元老,劝励来者,而使有矜式”[72]。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年)下诏刊印书籍:
皇帝圣旨里:集庆路达鲁花赤总管府来申张学正牒,尝谓书分八法,要刊陋俗之讹;学擅一家,实得补遗之妙,必锓诸梓,庶益于时。切见乡贡进士东原吕宗杰纂辑《书经补遗》一部,计五卷,如蒙刊行,以广其传,庶为便益。今将《书经补遗》一部,计三十八面,请施行。准此申乞施行,得此总府合下仰照验施行。至正十四年九月日[73]。
此外,士人在刻书方面还得到官方资金的帮助,元政府规定“诸路儒生著述,辄由本路官呈进,下翰林看详。可传者,命各行省,檄所在儒学及书院,以系官钱刊行”[74]。以诸路名义出版的士人著述,虽然数量上较少,但以国家之资刊印的书籍使得士人藏书不至于快速遭枣梨之灾。而国家经费的资助也保证了刻书的质量。
(四)科举、为政等导向与士人藏书
在皇庆二年十一月元仁宗所颁发《行科举取士诏》,明确规定考试程式,规定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中心。元仁宗重开科举一举对士人藏书读书产生了重要影响,士人科举用书重新成为坊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程度远超宋代[75]。例如,时任稼轩书院山长的程端礼“本朱、真二先生教法,详为工程,以教今之应举者”[76],专著《读书分年日程》,“使家有是书,笃信而践习如规”[77]。而在钱大昕所集纂的《元史·艺文志》中,第四部分下专列“科举类”一目,著录与科考有关书目。
元代在藏书著书方面,因为政之需还专著专藏为官方面的书籍。其中,“由吏入仕”方面的藏书著述就是重要组成部分。元时吏的地位仅次于官,且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来源。《经世大典》对吏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予以了较高评价,“惟习于刀笔者为适用于当时,故自宰相百执事皆由此起,而一时号称人才者,亦出于其间,而政治系之矣”[78]。元政府充分利用“儒通吏事”作为官吏选拔的重要依据,“儒不习吏,谓之拘儒;吏不业儒,谓之俗吏”[79],“儒”“吏”二者相契,以藏书为桥梁将二者完美结合起来。有关因“由吏入仕”而所藏所著的儒家著述如徐元瑞《吏学指南》、张养浩《牧民忠告》等。
《吏学指南》,全称《习吏幼学指南》,为吏学启蒙性读物。徐元瑞在《习吏幼学指南序》中明确指出其著书意图,“善为政者必先于治,欲治必明乎法,明法然后审刑,刑明而清,民自服矣。所以居官必任吏,否则政乖”[80]。此外徐元瑞认为“读律则法理通,知书则字义现,致君泽民之学,莫大乎此”[81]。此书不仅是当时为吏者学习的典范,对于今者而言也是研究政治、经济、风俗、法律等各个方面的重要史源。
张养浩将其任县尹、监察御史、参议中书、陕西行台中丞期间的为官经验撰写成4 卷本《三事忠告》(《为政忠告》),包括《风宪忠告》《庙堂忠告》《牧民忠告》。明代张纶《林泉随笔》称:“张文忠公《三事忠告》,诚有位者之良规。观其在守令则有守令之式,居台宪则有台宪之箴,为宰相则有宰相之谟。醇深明粹,真有德者之言也。考其为人,能竭忠徇国,正大光明,无一行不践其言”[82]。
元时任大都路总管府推官李威卿“少习城旦书,以儒术饰吏事”,为官期间集“取经史子集,下逮百家之说,凡关于刑宪者,撮其机要,纂而从类。先之以历代法令轻重沿革,著明其体;继之以听断节目之详,彰施其用”[83],共分三十二门,总名《嘉善录》,并恳请王恽撰《嘉善录序》。以上因政策变迁而影响士人藏书著书的例子不在少数。
(五)国家藏书活动中的禁书现象
历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控制时有禁书运动,虽然元代并未出现明清时代的“文字狱”活动,但也曾出台相应政策管控士人言行。至元三年(1266年)十一月,颁布《禁收天文图书》:“道与中书省,据随路军民人匠,不以是何投下诸色人等,应有天文图书及《太一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圣旨到日,限一百日赴本处官司呈纳。候限满日,收拾前项禁书,如法封记,申解赴部呈省。若限外收藏禁书并私习天文之人,或因事发露,及有人告首到官,追问得实,并行断罪”[84]。至元十年(1273年),“禁鹰坊扰民及阴阳图谶等书”[85]。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86]。泰定二年(1325年),“申禁图谶,私藏不献者罪之”[87]。此外,《元史·刑法志》记载,大恶:“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88];禁令:“诸阴阳家天文图谶应禁之书,敢私藏者罪之。诸阴阳家伪造图谶,释老家私撰经文,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寺观者,罪及主守,居外者,所在有司察之”[89]。《岳铉第二行状》记载,大德三年(1299年),“有告山西某家私藏谶纬图书者”,成宗命岳铉辩考,时岳铉认为“山野愚民岂知谶纬法象之典,第恐怨家诬罔”,后推验果真如此[90]。从以上件事也可窥测元代禁书现象。
此外,元政府所采取的禁书活动也影响到了士人藏书,曾任宋秘书小史庄肃家藏书万卷,其藏书被毁与政府禁书不无关系。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至正六年,朝廷开局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有以书献者,予一官。江南藏书多者止三家,庄其一也。继命危学士朴特来选取。其家虑恐兵遁图谶干犯禁条,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烬余。存者又无几矣。其孙群玉悉载入京,觊领恩泽,宿留日久,仍布衣而归。书之不幸如此”[91]。
总而言之,官府藏书作为藏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层面将中央和地方文化建设通过藏书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作为共有财产而存在的官府藏书由于其公有性也决定了典籍的流通性和利用率显然低于私人藏书。尽管在元朝之前官府藏书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士人更多将己之力投入典籍的编辑、收藏、校勘、编目等文献活动之中,且在这些活动之中通过交友使藏书得以流动起来,不至于迅速淹没于历史长河。最终,士人与国家基于藏书上的互动使得中华文明不因朝代更迭而消逝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