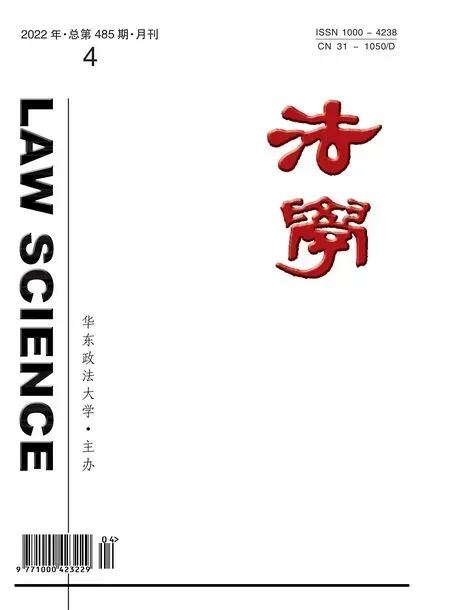企业“吹哨人”举报行为的刑法评价
——以法域协调为视角
2022-11-23朱奇伟
●朱奇伟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学者将“将发现的违法违规、危险或不正确的信息或者行为向组织内或组织外进行披露从而拉响警报的人”〔1〕彭成义:《国外吹哨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载《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44页。称为“吹哨人”(whistleblower)或举报人。2019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出要“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保护”。之后,各省份相继推出了对吹哨人的保护或奖励的规范性文件,〔2〕类似的规范性文件在最近两年比较多,比如《江苏省保护和奖励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人的若干规定》,苏环办〔2021〕293号,2021年10月22日发布;再如《安徽省药品质量安全吹哨人举报处置工作制度(试行)》,皖药监械生〔2021〕38号,2021年12月13日发布。意图保护吹哨人。但是,在现实实践中,面临的困局是,由于吹哨人举报的事实与相关企业或者经营者的商业秘密存在密切关系,在行政法被鼓励的吹哨人的举报行为,在刑法上很容易被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3〕也有部分案件以侵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进行定罪处罚,如“张文奇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参见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8刑终316号刑事判决书。因此,如何平衡对吹哨人和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是建构吹哨人制度必须妥当解决的前提。
对该问题,实务界与学界的取向截然相反。实务部门在很多案件的处理中,将利益衡量的天平向企业倾斜。例如,在“唐明芳侵犯商业秘密案”中,唐明芳将公司人力招募、加班数量等公司文件,发送给一名微信好友,该内容后被以“亚马逊非法用工,强迫实习生加班”为题加以报道。衡阳富士康认为此举侵害了公司的商业秘密,最终唐明芳被衡阳市蒸湘区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4〕参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20)湘0408刑初151号刑事判决书。类似的处理方式,还可以参见“张文奇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但后者因为行为人并非企业员工,因而被认定为侵害商业信誉、商品信誉罪。与之相反,不少学者倾向于强化对吹哨人的保护,其于教义学层面的理由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如果没有侵害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即使造成了损害结果,也不应构成本罪。〔5〕参见王志远:《侵犯商业秘密罪保护法益的秩序化界定及其教义学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6期,第50页。
总之,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将争议的核心聚焦于“商业秘密”的认定。这种处理方式存在两个特点。一方面,将对吹哨人行为的评价限制在构成要件层面;另一方面,尽管两者对“商业秘密”的内涵有不同界定,但两种立场都认为只要吹哨人行为侵害了“商业秘密”就构成相应犯罪,这实质上意味着在评价逻辑上,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仍然优先于对吹哨人利益及其体现的公共利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对于“吹哨人”行为的评价,应当突破构成要件评价的限制,通过将违法阻却事由适用拓展到经济犯罪领域的方式,妥当平衡吹哨人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利益。
二、立场反思:对司法实践入罪立场的反思
对于吹哨人举报行为的刑法评价,司法实践采取的入罪立场,无论是在教义学层面,还是在法政策层面,都不允当。此外,此种评价模式也不利于促进企业或者其他市场主体的合规经营。
(一)司法实践的入罪立场忽视了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要求
首先,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是法律适用应当坚持的基本要求。“所谓法秩序的统一性,是指由宪法、刑法、民法等多个法领域构成的法秩序之间不矛盾。”〔6〕[日]松宫孝明:《日本刑法总论讲义》,钱叶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法秩序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现实的法秩序,往往由不同时期、不同的立法主体,基于不同的政策考量或者立足于不同的利益衡量立场制定。因此,就现实的法秩序常态而言,其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协调乃至矛盾的情形。前述情形只是法秩序的实然状态,而非法秩序的应然状态。就法秩序的应然状态而言,法秩序应当具有统一性。一方面,立法主体应当科学立法,尽量避免制定存在冲突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法律适用者也应当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法律解释或者法律续造等法律方法,消除法秩序的矛盾状态。否则,不但会导致立法者通过法规范所拟实现的规整目标落空,同样也会导致国民面对相互冲突的法规范时不知所措。〔7〕Vgl. Karl Engisch, Die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Carl Winters, 1935, S. 8.
其次,对吹哨人举报行为入罪的立场将导致法秩序冲突。具体到对吹哨人举报行为的刑法评价,如果采取轻易入罪的立场,必然会导致刑法秩序和行政法秩序的冲突。吹哨人的举报行为在客观上可能造成企业经营者的商业信息或者秘密的泄露,因而存在触犯刑法相关规定的可能性。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吹哨人制度同样是由现实有效的法秩序所确立的制度。因此,直接将该类行为入罪,显然忽视了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要求。
最后,入罪的立场不能通过“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规则正当化。或许会有学者认为,即使将吹哨人的举报行为入罪也并不必然抵触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要求。因为,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是由刑法规定的,而吹哨人制度是由相关行政法规或者相关的规章制定的。由于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的效力,即使将吹哨人的举报行为犯罪化,也可以被解释为在法律适用立场上坚持了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冲突化解规则。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是化解法秩序冲突的基本规则之一。〔8〕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由于法秩序的统一性在“目的—手段关系协调”这一目的论层面的统一性,〔9〕参见于改之:《法域协调视角下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之重构》,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217页。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形式化的规则并不当然有效。特别是,在整体法秩序中刑法处于担保法的地位,而民法和行政法等属于前置法。原则上,在前置法上被认为是合法的行为,在刑法评价上也应当被评价为合法行为。〔10〕参见王昭武:《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182页。既然如此,由相关行政法律规范所肯定的吹哨人制度,在刑法评价层面,也应当被认为能够提供行为正当化的根据。
(二)司法实践入罪的立场在法政策层面欠缺妥当性
司法实践采取的入罪立场,将导致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确定的举报人制度的法政策诉求大打折扣。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2008年在中华儿科杂志发表矮身材儿童诊治指南,是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指导性文件[1]。该文强调,矮身材是指在相似生活环境下,同种族、同性别和年龄的个体身高低于正常人群平均身高2个标准差者(-2SDS),或低于第3百分位数(-1.88SDS)者,而绝对不是只低于正常值或正常偏矮。即使符合上述标准者,还有部分属正常生理变异。
首先,入罪的立场将导致保护吹哨人的法政策诉求难以实现。我国相关行政法律规范建立吹哨人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保护吹哨人。在现实社会中,吹哨人因举报而遭到报复的报道并不少见。〔11〕参见徐日丹:《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调动群众举报积极性》,载《检察日报》2016 年4月9日,第002版。正因如此,很早就有观点指出,更好地构建举报人保护制度“除了尽快出台举报人保护条例之外,还应建立健全举报人紧急保护制度、举报人身份重置制度,必要时,国家可以为举报人或亲属迁居、易容、重新安排工作,甚至实施终身保护”。〔12〕徐伟:《应尽快出台举报人保护条例》,载《法制日报》2011年3 月15 日,第 006 版。事实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也指出“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保护”。由上可见,在法政策取向上,相关行政法规关于举报人制度的规定,侧重于“奖励和严格保护举报人”。这一点也体现在各省份制定的相关规章中。如果将吹哨人的举报行为入罪,显然违背了保护吹哨人的法政策诉求。
其次,入罪的立场将影响吹哨人制度和举报人制度所拟实现的社会监督效果。吹哨人制度和举报人制度有利于鼓励及时发现企业的经营者的违法违规行为并防范相关的风险隐患。但是,该社会监督效果的实现建立在相关人员积极举报的基础上。法规范是行为规范,“对规范的对象(行为能力者)是告知/提示的行为标准”。〔13〕[日]井田良:《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秦一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4页。法规范的意义在于其通过肯定或者否定某种行为的方式引导国民的行动。然而,这种引导功能建立在法规范能够提供明确的行动基准的前提上。在行政法规范提供的行动基准和刑法规范提供的行动基准有冲突的情形下,如果赞同司法实践的做法,对于举报人的举报行为采取入罪的立场,意味着刑法规范提供的行动基准优先于行政法规范提供的行动基准。其后果将是,国民因畏惧刑事制裁而不敢担当吹哨人或者举报人。由此导致,寄希望于吹哨人制度和举报人制度实现的社会监督效果不再具有现实性。
最后,入罪的立场不利于企业自身进行合规建设。时至今日,刑法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参与社会治理的工具。将刑法视为实现社会治理的工具,并不意味着只要出现相应的不法行为,刑法就积极切入,而是强调通过刑法的介入能够实现积极的社会治理效果。对于吹哨人的举报行为,如果采取积极入罪的立场,不利于实现积极的社会治理效果。其一,对吹哨人行为入罪的立场,将导致企业获利。将吹哨人的行为入罪,意味着企业即使违法,其利益也将获得保护。这样一来,不但导致企业因违法行为而获利,也会导致一般公众在客观上不得不容忍企业的违法行为。这有违一般公众的正义观念。其二,对吹哨人行为入罪的立场,不利于企业进行合规建设。吹哨人或者举报人制度是企业合规建设的重要环节。“为了使举报人不畏惧报复并敢于对涉嫌参与犯罪的法人组织及其内部雇员予以及时举报,使得合规计划整体上具备真实发挥犯罪预防效果的可能性,赢得潜在举报人对于合规计划的信任是重要前提之一。”〔14〕宋颐阳:《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与举报人保护制度之构建》,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第91页。对于吹哨人或者举报人,如果采取入罪立场,必然使吹哨人或举报人丧失这种信任,导致企业很容易怠于从事或者完善企业合规计划。
三、路径确立:经济犯罪中违法阻却事由的法定主义优先性
司法实践认为吹哨或者举报行为侵害了企业的“商业秘密”,并进而将之入罪的作法并不妥当,但这并不同时意味着学界主张的通过对“商业秘密”进行实质解释,进而限制入罪的立场具有妥当性。因为,吹哨人或者举报人的举报行为所拟实现的利益与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属于对立的利益。两者的冲突表面上看是法秩序统一性的协调问题,实质上则是如何进行利益衡量评价,或者说赋予何种利益以优先性的问题。在犯罪评价体系中,“商业秘密”的认定属于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的问题。鉴于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不具有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的机能,因此,即使通过限制“商业秘密”范围,也不足以妥当处理吹哨人或举报人举报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
(一)对“商业秘密”进行实质解释的出罪立场的缺陷
司法实践通过肯定吹哨人或者举报人透露的“信息”属于“商业秘密”的方式,肯定吹哨人或者举报人的行为构成了相应的犯罪。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一些判决,确实会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商业秘密”的内涵或者外延有被形式化解读的弊端。例如,在“唐明芳侵犯商业秘密案”中,“被告人唐某泄露的信息是衡阳富士康公司未采取保密措施的违法用工的信息”,但司法鉴定意见将之认定为“商业秘密”,而法院也接受了这种见解。然而,赋予相应主体掌控信息以“商业秘密”属性,是通过激励相应主体,“从而能够可持续地增加社会总的知识产品存量,更大程度地发挥知识产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终使社会总效益达到最优状态”。〔15〕刘秀:《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经济学根据及制度安排》,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6期,第71-72页。因此,“商业秘密”属于值得通过法律保护的信息,其应当具有正向价值。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只有将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作为商业秘密刑事制裁体系的着力点,才能充分发挥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和社会治理效能。”〔16〕王志远:《侵犯商业秘密罪保护法益的秩序化界定及其教义学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6期,第50页。换言之,从实质解释的角度进一步合理限制刑法保护的“商业秘密”的范围,确实具有必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通过对“商业秘密”概念进行实质解释就能有效化解行政法规范和刑法规范之间的冲突。
首先,实质解释论的立场,并不能有效解决侵害到实质“商业秘密”的举报行为的评价问题。在犯罪评价上,实质解释的运用逻辑是,在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时,以法益为指导“将字面上符合构成要件、实质上不具有可罚性的行为排除于构成要件之外”。〔17〕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第50页。根据实质解释的立场,由于“商业秘密”必须是与“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竞争”密切相关的信息,因此,对于前文提及的“唐明芳侵犯商业秘密案”,很容易通过实质解释的方式,对吹哨人或者举报人的行为予以出罪。考虑到吹哨人或者举报人的举报行为必然涉及企业经营者的生产或者经营信息,在现实实践中,确实存在举报行为泄露了企业经营者控制的与“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竞争”密切相关的信息的情形。对于该类情形,我们显然很难仅通过对“商业秘密”概念进行实质解释的方式出罪。
最后,基于实质解释限制处罚范围的路径,在犯罪评价体系上也不妥当。犯罪是该当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行为。一个行为如果不符合相应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没有进行后续评价的必要性。再者,在评价内容上,不同于违法性评价和责任评价,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涉及定罪的积极要件。因此,构成要件评价在犯罪认定中具有关键意义。或许正因如此,针对吹哨人举报行为的评价,无论是出罪的立场还是入罪的立场,都将评价重心置于构成要件该当性层面。正如德国学者罗克辛指出的那样,犯罪评价体系必须“从一开就用它们的刑事政策之机能的视角加以观察、加以展开、加以体系化”。〔18〕[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在这一观察视角下,“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构成要件的刑事政策基础”。〔19〕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86页。换言之,为了担保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的实现,在构成要件该当性层面,原则上不能进行利益衡量的判断,或者说,涉及法域关系协调这一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实现,与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无关。由于吹哨人或者举报人的刑法评价涉及的是冲突利益之间优先性的衡量,因此,原则上不宜从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的阶层加以讨论。或许会有学者认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也可以作为实践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范畴。例如,对于民法上的不法原因给付财物的刑法评价或者权利行使行为的刑法评价,就是通过否定财产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方式,实现法秩序的统一性。然而,在前述财产犯罪的领域,之所以可以通过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消弭法秩序的冲突,是建立在前述冲突涉及的是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问题的基础上的。而本文涉及的吹哨人和举报人的利益冲突,本质上并不涉及相关犯罪的保护法益的确定问题。因此,立足于构成要件该当性的维度限制对吹哨人或者举报人举报行为入罪的立场,并不妥当。
(二)经济犯罪违法阻却事由立场的提倡
其一,立足于违法性评价的解决路径,更契合违法性评价的刑事政策功能。涉及利益冲突的优先性评价时,除非该利益冲突的协调可能涉及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法益之确定,原则上应当通过违法性评价的范畴加以解决。区分前述不同的处理方式,是由违法性评价范畴所欲践行的刑事政策所决定的,“在违法性层面,人们探讨的是相对抗的个体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需求之间产生冲突时,应该如何进行社会纠纷的处理。”〔20〕[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2版),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但是,2019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要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一些省市也相继推出了对吹哨人的保护或奖励的规范性文件。由于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的举报或者吹哨行为,通常涉及企业的一些经营性活动,因此,吹哨人或内部举报人等制度不可避免地会与保护商业秘密的刑法规定产生冲突。此时就面临着行政法规范与刑事法规范之间存在法秩序冲突的问题。因此,立足于违法性评价的解决路径,不但符合吹哨人举报行为刑法评价所涉问题的实质,更契合违法性评价的刑事政策功能。
其二,基于违法性评价的解决路径能够提供一般化的解释原理。吹哨人或者举报人的行为,有时不仅仅涉及企业或者相关市场主体的“商业秘密”问题,还可能涉及其他问题。比如在张某甲破坏生产经营案中,张某甲认为“兰陵县盛和石子厂”的生产经营造成了村内房屋、道路损害,产了大量粉尘、噪声污染,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带人围堵工厂,阻止车辆通行,张某甲被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21〕参见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2016)鲁1324刑初365号刑事判决书、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702刑初804号刑事判决书。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说,张某甲的行为确实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可见,基于否定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解释路径,只能着眼于各个具体的犯罪的构成要件,提供个案解决方案,并不能提供一套一般化的解释原理。即便通过讨论吹哨人或者举报人的行为所涉及的构成要件能够进行适当的出罪判断,也不得不强调“体系性是一个法治国刑法不可放弃的因素”,〔22〕[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王世洲译,载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刑法学(尤其是犯罪论)的最大特色就是追求体系的完整性和首尾一贯性”。〔23〕黎宏:《日本刑法精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而立足于违法性评价的解决路径,则可以为该类问题的解决提供统一的教义学原则。
(三)适用紧急避险的可能性
虽然我们确立了吹哨人的举报行为引发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违法性评价的方式予以化解,但成为问题的是,应当如何在违法性层面进行利益权衡。违法阻却事由有法定违法阻却事由与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之分。有学者认为,经济犯罪中的法定出罪事由无法适用,因此,需要更多地依赖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24〕参见孙国祥:《经济犯罪适用中的超规范出罪事由研究》,载《南大法学》2020年第1期,第119页。甚至有观点认为,应当取消从属于构成要件的违法性,因为不可能存在不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法定主义。〔25〕Vgl. Jochen Späth, Rechtfertigungsgründe im Wirtschaftsstrafrecht, Duncker & Humblot, 2016, S. 42.但更有力的观点则认为,社会变化中的相关因素会融入犯罪论体系的违法阻却事由中。前述观点都是主张,应当积极发现或者归纳新的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用以处理前述由吹哨人举报行为引发的利益冲突的评价问题。对此,笔者持相反立场。
首先,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具有优先适用性。不法的要素是法定的,不法的排除事由要尽可能地维持法定性。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自产生以来,其核心观点从未发生变化,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尽管在新时代,法定犯的大量出现,存在诸多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但存在空白罪状并不等于否定不法要素的法定性。古典犯罪论体系想要法官不用解释法律,而只需要机械地适用法律,因此想在构成要件阶层作纯粹客观的判断,但最终折戟沉沙。其被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官无法机械地适用法律,这就意味着法的规定不明确,从而认为不法的要素并不都是法定的。实际上,法定主义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法官面对法律没有规定的问题无法处理恰恰说明了不法的要素应当是由法律事先规定的。即便是面对空白罪状,也应当遵守法定主义,在此基础上对空白罪状进行解释和适用进行构成要件化。〔26〕参见于冲:《行政违法、刑事违法的二元划分与一元认定——基于空白罪状要素构成要件化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第103页。需要注意的是,不法要素是法定的并不等于不法要素是明确的,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是说不法的要素是由刑法规定的,而后者则是说法定的不法要素是否足以让法官无疑问地进行解释适用。前者是立法原则,而不法要素是否明确,这是立法技术问题,不可混为一谈。而过度扩张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导致的法的不确定性是刑法难以承受之重。〔27〕Vgl.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1, Grundlagen, Der Aufbau der Verbrechenslehre, 4. Auflage, Beck, 2006, §14 Rn. 38ff.因为类似的理解在不断提高容许性原则的适应性,来确保其与通说的契合度。但是只要违法阻却事由的构成要件没有自己独立的形式,法的确定性都应当是立法者和司法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即考察尚未被认可的规则能否把握、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住那些需要被判断的事实。经常自由地创设不法排除事由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其次,可以通过对紧急避险制度作出相应扩张解释的方式,合理解决由吹哨人举报行为引发的利益冲突的评价问题。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两种违法阻却事由,即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两种违法阻却事由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冲突的利益评价中,前者具有正对不正的属性,而后者具有正对正的属性。前述由吹哨人举报行为引发的利益冲突,具有正对正的属性。因为,不具有正当属性的利益,一开始就不属于刑法构成要件所保护的范围。既然如此,这部分情形一开始就被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所过滤。例如,在前文提及的“唐明芳侵犯商业秘密案”中,由于违法用工信息不能被评价为“商业秘密”,因此,至少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而言,并不存在吹哨人的举报行为所欲实现的利益与企业拥有的商业秘密的冲突。但是,在该案中,可能涉及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利益被侵害的问题。如果对此采取肯定的态度,则可以认为存在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利益与吹哨人的举报行为所欲实现的保护劳动者的人身健康或者正当薪酬利益的冲突。由于由吹哨人举报行为引发的利益冲突,具有正对正的属性,所以其在涉及的利益冲突的构造上与紧急避险所涉及的利益冲突具有类似性。
再次,在比较法上,很多涉及正对正的利益冲突经常通过适用紧急避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处理。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66条第1款规定了截留为员工缴纳保险金的犯罪行为。供货商甲(同时作为某区域银行的监事会成员)发现生产商非常有可能会变得没有支付能力,因此其向董事会建议,暂停发放乙公司的重要贷款,而该贷款本是要为乙公司员工缴纳保险的。〔28〕Jochen Späth (Fn. 25), S. 299.甲的行为很显然是符合《德国刑法典》第266条第1款的犯罪构成的,但是因此入罪也不合理,德国学者主张以紧急避险对其进行出罪。再如,对于属于义务冲突的事例,在日本等一些国家也通过类推紧急避险的方式加以处理。我国也存在一些类似的案件,本来应该作为紧急避险处理,反而被认定为犯罪。比如前述“张某甲破坏生产经营案”,张某甲认为石子厂的生产经营造成了村内房屋、道路等财产损失,产生的粉尘、噪声污染还会影响村民的身体健康,于是带人围堵工厂,阻止车辆通行的行为。〔29〕参见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2016)鲁1324刑初365号刑事判决书。张某甲的行为确实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张某甲的行为应当入罪,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普通群众的生命法益或健康法益需要向有经济效益的污染企业让步,容忍企业污染对自己身体造成损害?但如果非要从构成要件层面进行实质解释,认为围堵工厂的行为不是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则又有曲意维护之嫌。因此,在我国刑法不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的前提下,被告人只有通过紧急避险才能实现出罪的有效辩护。
最后,在现实实践中,很多吹哨人举报的事件也能被评价为现实存在的急迫危险。传统刑法学之所以未考虑紧急避险在经济犯罪中的作用,关键就在于传统观点认为发生在企业内部的危险不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但传统观点对现实性和紧迫性的理解都有失偏颇。紧急避险所涉及的现实危险包括两种,一种是即刻性危险,这是传统刑法学类型化的典型危险形式,而另一种则是持续性危险。〔30〕参见隗佳:《责任阻却性紧急避险的厘清与适用——以受虐妇女杀夫案为视角》,载《法学家》2020年第1期,第133页。对于持续性危险的存续状态期间内,损害一定会发生,而且会反复发生。危险的现实性表现为持续性在传统的自然犯中早就得到了证明,比如德国刑法中的“平底锅案”与“赫辛格案”,〔31〕同上注。在经济犯罪尤其是数额犯或情节犯中,危险的现实性更是表现出了持续性的特点。比如“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行贿案”,虽然行贿罪本身是行为犯,但是企业在经营期间,为了销售利益,行贿的风险都是存在的,损害结果一定会发生,如果不及时制止法益侵害行为,那法益造成的损害结果便无法挽回。危险如果是持续的,那危险发生的紧迫性就随时存在。“癖马案”裁判理由为规范责任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如果考虑“癖马案”危险结果发生之前其危险的紧迫性,那任何一次驾驶行为,其本身都是危险持续存在,并在随后的每一次驾驶行为中都有危险发生的紧迫性。
以上的说明只是揭示了,吹哨人举报行为引发的利益冲突,在构造上与紧急避险具有相似性。进一步的问题是,其能否被评价紧急避险。这涉及两个更根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吹哨人举报行为所欲实现的利益在法益位阶上是否优先于企业的商业利益;第二个问题是,吹哨人通过举报行为实现其正当利益的行为,是否满足紧急避险的补充性要件的要求。
四、成立紧急避险法益均衡要件:商业秘密在利益衡量上的低位阶
(一)企业的商业秘密并不具有绝对优先性
对商业秘密保护的优先性,学界有不同的观点:首先,根据严格举报义务说,当根据《刑法》第310条窝藏、包庇罪的规定,行为人有告发义务时,也需要将保护秘密的举止要求以有利于企业的解释作为前提,此种观点认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优先级最高;〔32〕德国有类似观点,即企业存在犯罪计划,而员工知道该计划但并没有检举揭发的,构成《德国刑法典》第138条“对犯罪的计划知情不举罪”,但员工告发企业犯罪计划的行为是否需要作最有利于企业的解释,存在不同观点。Vgl. Uwe Hellmann/Katharina Beckemper, Wirtschaftstrafrecht, 4.Aufl., Stuttgart: Kohlhammer, 2013, Rn. 515.其次,广义检举权说认为,对吹哨人举报的合法性依据应当作广义理解,认为吹哨人可以取得进行检举的一揽子权利,相对来说,商业秘密保护的优先级就最低;〔33〕类似观点萨茨格在论述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8条属于违法阻却事由时有过论证,认为检举揭发只是维护刑事追诉利益的第一步,因此,应当赋予其更广泛的权利,使更多的犯罪行为浮出水面。Vgl. Helmut Satzger, Der Staat als „Hehler“?-Zur Strafbarkeit des Ankaufs rechtwidrig erlangter Bankdaten durch deutsche Behörden, in: Hellmann, Uwe/Schröder, Christian(Hrsg.),Festschrift für Hans Achenbach, Köln 2011, S.451f.最后,折中说认为,如果行为人是为了反抗企业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或刑事侵害行为,就可以公开企业的犯罪或违法行为,因此折中说中,商业秘密的优先级也是最低位阶。〔34〕Vgl. Roland Hefendehl, in: Spindler/Stilz(Hrsg.) Kommentar zum Aktiengesetz, 2.Aufl., C.H.Beck, § 404, Rn. 53.
首先,将企业商业秘密置于绝对优先地位的严格举报义务存在缺陷。因为根据该观点,企业的商业秘密更值得刑法的保护,甚至大于国家刑事追诉的利益,这有损国家司法的权威。因此,有德国学者认为,高效率的刑事追诉利益是作为超个人法益的紧急状态,而需要进行高效率的刑事追诉的犯罪行为,并不局限于《德国刑法典》第138条所列之犯罪目录,作为基本原则的紧急避险应当赋予企业员工“帮助查明案件的权利”这一优待。〔35〕Vgl. Armin Engländer/Till Zimmermann, Whistleblowing als strafbarer Verrat von Geschäfts- und Betriebsgeheimnissen? Zur Bedeutung des juristisch- ökonomischen Vermögensbegriffs für den Schutz illegaler Geheimnisse, NZWiSt 2012, S.328-330.而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无论是《刑事诉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劳动法》都确认,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有权进行举报,〔36〕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进行报案或者举报;即便是尚未构成犯罪的,也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6条,对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监督检查部门进行举报;《劳动法》虽未直接规定举报权,但是第101条也明确表示,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并未因举报对象是否为企业而有所区别。这一方面意味着国家的刑事追诉利益不能被限缩于特定的犯罪圈之内;另一方面则表明,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并无特权,企业的利益不会大于国家利益,甚至不会大于个人利益。
当然,在目前缺乏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此一结论,只能通过学理进行推导。如《德国刑法典》第203条规定了侵害他人隐私罪,即当行为人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时,可以基于紧急避险的考量而不进行刑事追诉。在德国,侵犯个人隐私的避险要求比经济犯罪的避险要求要更严格一些,〔37〕Vgl. Bernd Schünemann, LK-StGB, 12. Aufl., 2012, § 203, Rn.32.因为隐私作为被侵害的法益,其基础是一般性的个人权利,这被规定在德国《宪法》第1条第1款和第2条第1款中。特定秘密的所有人和保密者之间也存在着特殊关系,〔38〕《德国刑法典》第203条规定,医师、心理学家、律师等具有特殊职业资格的人,因特殊身份知悉他人秘密,应当负有保密义务。这种特殊关系因为刑法法条而上升为一种特殊关系。但是与此相比,企业员工作为吹哨人,并不需要面对如此严格的规定,因为吹哨人举报的信息只涉及与财产有关的商业秘密,既不存在宪法规定的基本的个人权利,也不涉及需要特殊保护的信任关系,此时,对企业秘密保护无法获得比个人隐私更优的保护等级。
同理,我国刑法虽没有规定如《德国刑法典》第203条所规定的侵害他人隐私罪,但类似的规定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即涉及个人隐私的是绝对不公开审理,而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是经申请可以不公开审理。这证明在我国刑法中,商业秘密不能获得比个人隐私更高等级的保护。没有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提出更高要求的,也就不能要求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提出更高要求。“唐明芳案”中的核心并不是唐明芳与富士康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而是公司违法行为的范围及其可能威胁的法益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允许一个企业员工告发企业的违法行为,那么这甚至剥夺了他作为一般群众的举报资格。〔39〕2018年财政部与原安全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规定了对安全生产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的奖励制度。在2020年9月24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就《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举报处理规定》答记者问时,有关负责人指出,该奖励办法未区分一般群众和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举报,从而没有对奖励标准进行区分。依此而论,一般群众也有举报生产经营单位违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权利,生产经营单位内部员工举报更应当予以保护。安全生产本身也是可能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比如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很可能会被要求停业整顿。
其次,严格举报义务说过度保护了企业利益,而广义检举权说则放纵了个人的检举权利,但折中说也并非没有问题。因为,如果行为人只能基于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或刑事追诉才能进行检举揭发,那此时适用的条款就不是紧急避险,而应当是正当防卫。因此,折中说还应当作广义理解,或者说,不需要对《刑法》第21条做限缩解释,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或者是他人的人身财产权利的,也可以适用举报制度。除此之外,折中说的观点是比较妥当的,原因在于折中说强调了举报行为的预防作用。〔40〕对行为人公开权的评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主要争议是主张告发行为的作用是什么,究竟是预防作用,还是仅仅只是限制作用。对此,有学者提出,在面对特别重大的犯罪行为时,不论涉及企业多大利益的秘密,行为人都要履行告发义务,比如窝藏、包庇罪,立法者消除了有资格的告发行为(预防作用)与秘密保护的法条之间的冲突。但是此类评价不能只被限制在法定的冲突情况下,公开企业秘密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发挥法的预防作用。立法者是鼓励人们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不实施告发行为才是非法的行为。〔41〕Roland Hefendel (Fn. 34), Rn. 53.因此,可以说企业的商业秘密在利益的衡量中,其保护位阶是最低的。
最后,广义举报义务强调的举报人利益优先性的观点,原则上值得赞同,但需要作出一定的修正。广义检举权说存在的弊端是,如果吹哨人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举报,势必造成权利的滥用,无法平衡企业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例如,“魏宏让、韩杰等与江门市威登迈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原告魏宏让诉称作为公司股东的第三人李冲曙和柯冬云,为拖垮被告,谎报被告公司有经济犯罪嫌疑,举报公司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和财物的收付凭证不齐全,滥用举报权,导致公安机关的经侦人员多次找财务人员进行调查、询问,致使公司业绩下降。〔42〕公安机关并未对被吹哨人进行立案侦查,可见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而且对于原告的控诉,第三人并未予以正面回应,只是辩称对公司进行控告是为了公司更好地经营,可以看出,第三人确实属于滥用举报权利。原告控诉及第三人的答辩可以参见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4836号民事判决书。因此,无论是“唐明芳案”还是“魏宏让案”,吹哨人进行举报的基础必须是企业的违法抑或犯罪行为。只有吹哨人担心会有更大范围、更具威胁性的法益侵害行为时才能够举报,否则,过度放纵个人的检举权不利于企业的稳步发展。然而,广义举报义务虽然可能导致举报人滥用举报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利益在法益位阶上必然优越于举报行为所欲实现的利益。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即使像广义举报义务说那样,认为举报人所欲实现的利益在法益位阶上优先于企业的利益,也并不必然导致举报权的滥用。因为,紧急避险行为的正当化,除了满足法益均衡性要件外,还要满足避险行为补充性要件。为了避免举报行为的滥用,完全可以通过严格认定避险行为补充性要件的方式实现。
(二)附随性损害不属于需要进行利益衡量的利益范围
在前文提及的“唐明芳侵犯商业秘密案”中,衡阳市蒸湘区法院认定公司调薪等支出的140余万元属于公司损失,并将其设定为刑罚发动的要素。对此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将之视为由吹哨人举报行为引起的财产损失,那么,是否可以将之作为独立于“商业秘密”,但也需要被纳入利益衡量范围的企业利益。对此,原则上应当采否定态度。因为,这部分损失是避险行为的附随结果,不是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不能认为唐明芳所造成的损害超过了其所避免的损害。不考虑违法阻却的性质,避险所造成的结果应当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但无论基于哪种理解,唐明芳的举报行为与企业撤换领导层、调整薪资之间都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财产损失是财产利益遭受侵害后产生的法益侵害后果,〔43〕参见蒋太珂:《除斥期间的刑法评价》,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3期,第147页。因此,确定是否存在财产损失是判断是否存在法益侵害,进而判断避险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的核心因素。对于损失的认定,应当首先明确商业秘密的价值。对于商业秘密的价值如何计算,我国司法解释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只在2007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了“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根据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确定”。学界也多是从研发成本、利润实际损失情况、商业秘密的竞争程度、前景预测等作为参考因素来认定损失。〔44〕参见王文静:《论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的认定原则》,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6期,第162页。因为衡阳富士康违法用工并不存在判断投入开发成本、可得收益等因素的必要,而利润的实际损失则是在调整薪资上的支出,但这只是企业公关的行为,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是纠正违法用工行为而对员工做的补偿,所以不能作为企业的损失;而开除厂长刘某以及人资主管肖某造成的赔偿也只是企业内部追责的行为,与企业的利润也没有关系。
综上,通过紧急避险阻却吹哨行为的违法性看上去是可行的,即如果保守的企业秘密涉及违法行为时,员工便可以举报企业的违法行为;而如果保守的企业秘密涉及刑事犯罪时,即便是消极的刑事追诉利益也应当具有绝对优势地位。〔45〕Vgl. Theodor Lenckner/Jörg Eisele: Schönke/Schrö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8.Aufl., C.H.Beck, 2010, Vor § 13 Rn. 51.此外,从立法者的角度来讲,立法者是反对对商业秘密有过高评价的,这一点从《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商业秘密只是申请不公开,因而不能提出比保护个人隐私更高要求中就可以看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员工虽然可以举报企业违法行为,但是不能扩张其“举报的权利”。〔46〕Vgl. Alexander Schemmel/Felix Ruhmannseder/Thomas Witzigmann, Hinweisgebersysteme- Implementierung in Unternehmen,Müller, 2012, Rn. 43.
五、紧急避险的补充性:企业内部合规的意义
企业员工在何种限度内能够向有关部门、企业内设机构或者直接向公众揭露违规违法行为,从目前的刑法规定来说并不明确,〔47〕Vgl. Nicolai Warneke, Die Garantenstellung von Compliance-Beauftragten, NStZ 2010, S. 312.在此,企业合规体现了其必要性。员工举报的权限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而是应当取决于合规官的权限范围,因此,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合规官的权限范围。尽管企业合规概念被发明出来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其出发点甚至被形容成是一种“尽可能地使企业法务和董事会成员免遭牢狱之灾的艺术”〔48〕Christoph Hauschka, Von Compliance zu Best Practice, ZRP 2006, S. 258.,但企业合规计划的意义不应被限制在为证明企业在自身活动中表现了应有的注意,更应表现出企业在法令遵守方面的组织体文化,举报制度不应当只是作为合规监督功能的权宜之计,企业应当存在针对发生违法行为的应对方法与报告程序,〔49〕参见[日]川崎友巳:《合规管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李世阳译,载李本灿等编译:《合规与刑法——全球视野的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24页。否则就不应当限制举报的范围。
(一)合规官限制举报行为的权力基础
其一,合规官的权力基础来自企业内部授权。普通部门的企业员工以其职责范围承担法律风险,但合规官不同,合规官负责企业内部的监管工作,是受企业委托的独立监察人,〔50〕参见[日]川崎友巳:《合规管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李世阳译,载李本灿等编译:《合规与刑法——全球视野的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其权力基础首先是从企业内部组织规定中间接派生出来的。现有观点认为,合规官的权力包括监管权、惩戒权、建议权以及向法律执行机关报告的权力。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合规官之所以能获得权力,或者说能获得多大的权力,是来自企业管理层的授权。〔51〕根据《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第5条的规定,董事会负责合规管理负责人的任免,并能够决定合规管理牵头部门的设置和职能。受合规委托,需要为之答责的合规人员才被授权从事公司治理、损害预防、危险控制以及保护和监管的职能,而并不是说,合规人员从自身的角度来讲天然获得指示和监管的权力。〔52〕Jürgen Bürkle, Compliance-Beauftragte, in: Christoph Hauschka(Hrsg.) Corporate Compliance, Handbuch der Haftungsvermeidung im Unternehmen, 2.Aufl., C.H. Beck S. 136.合规部门既然有损害预防和危险控制等职能,其在企业内部就能够形成一个双向的保护罩,一来保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企业内部的非法侵害,二来则限制员工向外举报的权利,以保护企业经营的利益。
其二,合规官的权力基础来自保证人义务。就目前来说,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合规官的权力范围,因此,合规官为了履行其保证人义务可以获得哪些权力也是不明确的。德国联邦法院曾表达过:“被委托人会经常遇到《刑法》第13条第1款不作为犯罪所规定的保证人义务,其有权阻止企业其他员工实施的基于企业行为所产生的犯罪行为。这是相对于企业经营所涉及的义务、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所必需的。”〔53〕BGHSt 54, 44, 49f.根据该判决所体现的基本原则,合规官可能基于故意,甚至可能是基于过失而为企业其他雇员的行为承担责任。那么合规官的风险就来自不力的监管,或者干脆就不作为,因而合规官为企业其他雇员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依据就是不作为的帮助犯。〔54〕Vgl. Anderas Ranisiek, Zur strafrechtlichen Verantwortung des Compliance Officers, AG 2010, S. 147.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也能得出类似结论,如我国《公司法》第170条规定:“公司应当向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拒绝、隐匿、谎报。”该条款规定了公司的财务、会计需要履行的强制性义务,违反该义务就要承担相应责任,而合规官因其具有保证人义务,在财务、会计不履行相应义务时也要承担保证人责任。基于该保证人义务,合规官也可能双向承担责任,比如企业发生了安全生产的事故,那合规官可能因为企业的经营行为侵害了员工的生命法益而作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共犯;再就是其不作为,而企业员工向外举报造成公司利益受损,〔55〕前提是企业员工向合规官反映个人权益受损,而合规部门并未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戒和改进。而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共犯而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两点,合规官是有限制举报行为的权力基础的。但是合规官也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即如果其没有对相关人员的惩戒权,甚至没有启动企业内部调查的权力,那么不但合规官本人随时可能因为他人的行为而面临可罚性风险,而且由于企业的合规规则也丧失了有效的合规性,〔56〕参见[德]弗兰克·萨力格尔:《刑事合规的基本问题》,马寅翔译,载李本灿等编译:《合规与刑法——全球视野的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4页。因此,也就无法限制他人的举报权了。
(二)合规官的权力范围与举报的行为边界
想要通过合规计划来限定吹哨人的举报权,那么合规计划必须是完整的,否则吹哨人的举报权就不应受到限制。有学者认为,一个完整的合规计划应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由独立的合规组织接收并评估风险;其次,由合规组织主导上传下达的信息流;最后,对违规行为进行制裁并改进。〔57〕参见李本灿:《企业视角下的合规计划建构方法》,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7期,第81页。这体现了合规官三个方面的权限,即独立组织、信息主导和有惩戒权限。
首先,如果想限制吹哨人的举报权,就必须存在一个能够越过企业经营的独立的合规部门。合规部门只对企业董事会负责,必要情况下可以只对董事长负责。〔58〕同上注,第80页。合规部门的独立是为了保持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有独立性才能确保合规部门在面对可能有损于企业经营的举报行为时,做出不受企业经营影响的合规决策;而权威性则使合规部门能够对涉及企业经营的行为展开内部调查,并且能够允许合规官在权限框架内能够直接向监事会或股东(大)会反馈举报信息。在特定案件中,相对于企业经营,合规官能获得多少调查的权限,取决于吹哨人所涉紧急避险中的利益衡量,但只要合规部门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企业内部的报告手段就会被认为是最合适的手段。此时基于劳动法上的忠诚义务,如果吹哨人选择对外举报,那么基于《刑法》第21条的必要性要求,吹哨人都不再能够成立紧急避险。但在面临企业重大犯罪时,员工的对外举报权就不能被类型化地排除。〔59〕Vgl.Meinrad Dreher, Unternehmensbeauftragte und Gesellschaftsrecht, in: Martens, Klaus-Peter (Hrsg.), Festschrift für Carsten Peter Claussen zum 70. Geburtstag, Köln, 1997, S. 69.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国家的利益要高于个人劳动利益,因此,如果行为人的举报行为不是向国内媒体进行的,那无论如何也不能阻却其违法性。
其次,限制吹哨人的举报权,必须建立上传下达的信息流。合规部门要有独立信息流,除此之外的其他要求都是多余的。〔60〕参见李本灿:《刑事合规的制度边界》,载《法学论坛》2020年第4期,第140页。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合规部门向上反馈合规信息,既包括向董事会、监事会或者是合规委员会进行反馈的信息流,也包括例外情形直接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反馈,甚至包括在劳动问题上向劳动部门进行反馈的独立信息流;另一方面则是企业内部员工向合规部门进行反馈企业违法信息的信息流,这也是员工在非企业重大犯罪情况下企业内部的最后报告途径。
最后,限制吹哨人的举报权,合规部门必须具有惩戒权。从目前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合规官的企业管理职能是董事会或企业运营所赋予的,因此,合规官的义务也只是告知风险,或者是作为合规问题的顾问。〔61〕Jürgen Bürkle (Fn. 52), S. 136.所以现实情况中,合规官不得不面临两难的局面,即一方面不得不履行义务来调查和预防企业内部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企业经营的相关指示又违背刑法上的义务。但是,企业的利益不是快速处理企业的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因为很多违法犯罪行为是有利于企业经营的,比如贿赂犯罪,通过贿赂行为企业能够获得合同上的利益。〔62〕Vgl. BGHSt 52, 323 ff.正如前文所述,企业的经营利益不具有优先性,更不可能大于国家的刑事追诉。因此,合规官的权力还应当予以扩张,即便董事会默许企业犯罪的违法行为,也应当赋予合规官以独立的惩戒权,因为合规官是不能从合规计划中免责的。〔63〕Jürgen Bürkle (Fn. 52), S. 138.
六、结语
我国在宪法中也规定了对吹哨人的保护条款,即《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的“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但面向非国家机关的举报、揭发非国家机关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就容易符合刑法的犯罪构成而被入罪。为了实现实体正义,司法机关往往过度依赖对构成要件进行所谓的实质解释。但是,在公诉机关能够证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情况下,对行为人的出罪更应当回归体系性思考,亦即吹哨人的举报行为并非不符合刑法的犯罪构成,而是应当通过违法阻却事由来排除不法。在此基础上,应当优先适用违法阻却事由的法定性,以维持法的安定性。而相较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构造更为灵活,能更好地实现阻却违法的目的。对吹哨人的举报权限制不能过于严苛,但也应当鼓励信息的内部披露,着力增加组织内控的合规官权力,其实质是对吹哨人举报权的合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