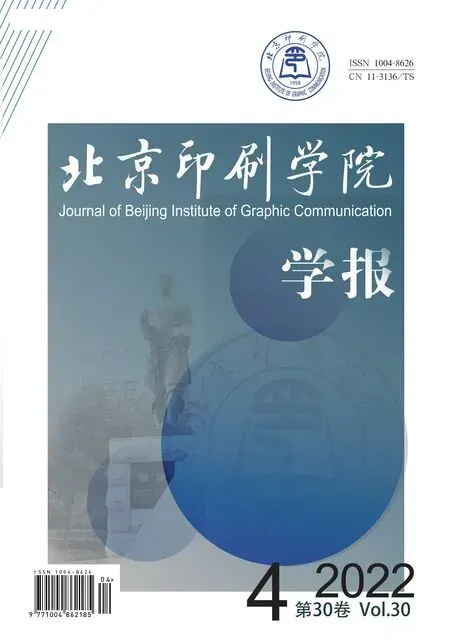回顾与展望:直播与出版传播生态的变迁研究
2022-11-23胡文学
胡文学,刘 欠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传播生态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的发展,技术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其发展和变革改变了传受关系、传播情景、传播主体以及传播需求。出版传播生态既包括出版业内部各主体的传播状态也包括出版业与外部大环境的互动关系,这些内外部的互动状态和关系随着技术的更新显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在出版业整个产业链中,营销阶段是与技术联系最为密切的,不同的营销手段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出版传播生态。直播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它与出版业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的结合使得出版传播生态出现了三次变迁。
一、直播与出版传播生态的三次变迁
(一)辅助直播阶段:线下活动的补充手段
直播的出现是技术对受众多元化需求的满足,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的创新。2016年直播大热,艾媒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在线直播行业专题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接近200家,其中网络直播的市场规模约为90亿,因此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直播从技术上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将电视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在互联网上进行实时播放;二是在活动现场设立独立的信号采集器,将内容导入到播放端,用户通过网上的所发布的直播地址就可以实时观看直播。当下所说的直播更加倾向于第二种。从受众的需求来看,直播平台的兴起起初更多是为了满足娱乐需求,例如“斗鱼”“熊猫”是游戏直播的平台,“六号房间”是秀场直播的平台,“映客”和“花椒”是移动直播平台。
在直播发展的初期阶段,出版业并没有与其进行密切的结合,只是将其作为助力传播活动的一种辅助手段。这种辅助手段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线下活动的实时直播,突破线下活动的空间局限,使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扩大线下活动的影响力;另一种方式是开展固定的直播栏目,参照电视直播栏目,选择特定的时间和话题以直播的形式与受众进行实时交流,在此过程中推荐出版社相关的产品。
但早期的直播辅助手段有明显的缺点,线上和线下活动的结合只能带来短时的宣传效果并不能带来可观的知识变现,因为线上直播活动的变现依然是依赖于固定的粉丝群,短时间的直播活动难以将用户转化为消费者,宣传效果也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消失。
(二)弱直播阶段:依赖直播带货模式
喻国明教授提出,“直播以人性化的逻辑构建了兼具临场感和便利性的消费场景。”[1]这个消费场景所具有的优势使其迅速成为了新的营销阵地,2019年“直播电商”异军突起,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是为直播电商的发展按下了加速键,越来越多的网民接受了这一购物方式。出版行业为了应对“居家隔离”的大环境和受众消费场景的转换,也试图探索“直播+出版”的营销模式,将场景化融入其营销过程之中。
出版业的直播营销已经成为了当下直播带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0淘宝直播新经济报告》数据,图书音像在淘宝直播成交额增速中位列第三。[10]但这一阶段仍处于弱直播的传播生态,大多数成功的案例都是依赖于固有的直播电商模式,通过头部带货主播的推荐进行销售,3万册的《人生海海》在5秒内售罄、65000册的《薛兆丰经济学讲义》在较短的时间内售罄都是在头部直播间实现的,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销售量,但都依赖于直播平台和带货主播固有流量,直播间的受众也并不是专门为了购买图书而来,出版行业缺乏主动性和掌控力,难以再复制。
(三)强直播阶段:打造独立平台
“直播热”过后,出版业更应考虑的是如何从与直播结合到与出版融合的转变,摆脱对直播带货的依赖成为了当下发展的重点。在各出版机构的积极探索下,直播与出版传播生态也迎来了第三次变迁:出版业打造独立平台,建立独特的直播模式。这一方面能够使技术的运用更加贴合出版产品的本质,使技术与内容得到最大程度的兼容;另一方面,独立化的运作有利于出版业掌控发展模式,成为稳定的发展路径。
强直播阶段的代表模式主要有两种:直播栏目和直播运作模式的建立。在此阶段的直播栏目不同于辅助直播阶段,不再依靠于媒体平台而是完全由出版行业自身打造。2020年京东图书打造的行业首档直播栏目《高能出版社》正式亮相,出版社社长+作家的组合在直播间为读者推荐权威书单。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成为首期栏目嘉宾,直播当天,中华书局在京东平台的成交额同比增长达到407%,直播间点赞量近百万。出版行业和营销平台相互合作,打造成了流量闭环的模式。
与此同时,直播运作机制的建立意味着出版行业逐渐脱离对直播带货的依赖,创建出了自身的一套直播流程。以“掌阅”为例,其旗下的“都靓读书”账号主播都靓就依靠着内容输出完成了从品牌经理到读书主播的转变,在“快手”的直播首秀中销售额突破了30万,成为该平台头部图书类主播。
二、当前出版直播生态存在的问题
(一)私域流量获取艰难
在出版直播传播生态中,私域流量成为了出版机构争夺的重要资本之一,是否有足够的流量决定着能否在此场域中找到容身之地。传统的出版传播生态更多的是强调文化资本,出版社机构不与受众进行直接的接触,对流量资本所需较少,所以传播生态的改变导致当前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只集中在头部出版机构。直播营销模式对流量产生了极大的依赖,这就意味着流量将会是此场域中重点争夺的资本。
与其他的直播传播生态直接争夺流量不同,在出版直播传播生态中,出版机构利用文化资本这种隐性的社会资本,与直播平台、网红主播KOL之间进行着较为频繁的资本置换。当前出版业与KOL合作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找“头部主播”营销图书,从而提高书籍的销售量;二是以出版机构的名义与其合作直播,以期获得更多的私域流量。但这两种模式都有很强的依赖性,出版业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独立发展的流量资本。因此,如何脱离对外部的依赖,打造私域流量池是当前出版直播传播生态面临的一大问题。
(二)运营模式难以适应
虽然出版业打造了独立的直播平台,但并没有成熟的运营模式。首先是主播的缺乏,虽然有些出版机构已培养了自己的主播,但整个出版业内部优秀主播的欠缺仍然是一大问题。不同于直播电商模式中产品的可试用性,图书无法在短时间给受众最为直观的体验,这就对图书主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图书的内容进行梳理又能唤起受众的消费热情,这就意味着其他商品的带货方式是不适用于出版直播生态的。其次是出版业缺少用户思维,传统出版业的营销发行是不直接接触读者的,一般会借助第三方进行营销,而直播模式的引入实现了出版业的“前台化”,需要直接面对用户,过去以“低价促销”作为卖点的模式不仅无法进行用户沉淀也无法打造“生态化”的盈利链。
(三)平台属性无法平衡
伊尼斯曾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8]每次媒介技术的变革都会创造出新的媒介,而新的媒介又会产生新的文明。当下出版业的主要直播平台是电商(淘宝、京东)和短视频(抖音、快手),在这些平台上进行直播就必须符合平台自身属性,而短视频平台的娱乐属性无意中将书籍的严肃内容娱乐化,将系统内容碎片化,从而形成“文化异化”的风险。此外,直播平台“随进随出”的特性也会对“出版+直播”的传播生态造成影响。在直播平台上,受众可以随时选择任意想进入的直播间,但由于图书内容的解说具有系统性的特点,中途突然进入的受众往往很难跟上直播间的节奏,造成直播间无法留住受众。
三、直播与出版传播生态结合的未来发展
(一)精细化的深度运营
就出版机构而言,未来要想具有竞争优势就必须打造用户所认可的符号品牌,突显出自身的价值。对于具有高知名度的出版机构来说,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彰显在新场域的符号价值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例如结合直播在场性的特征用直播的方式全面展现出版社内部,满足了受众好奇心的同时也打造了出版社亲和的品牌形象。而对于知名度较低的出版机构,首先要明确自身的定位,针对目标受众的需求介绍优质图书,在凸显自身的专业度的基础上增强受众黏性。同时,直播平台的垂直化运营也是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通过内容分类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
(二)完善化的营销链条
目前短视频平台已成为了出版社直播的重要阵地,平台和业界也在进行积极的探索,2020年“快手”和中国出版协会合作的“快手读书·创作者学院”正式成立,进一步助推了出版业在线上的开拓。出版业在充分利用好平台所给资源的同时也要完善自身的营销链条,使其符合短视频的用户“进入模式”,打造闭环营销链。直播营销的有效转化不能仅仅局限于直播本身,还必须与短视频内容相结合,做到“浅深相融”,使受众既能够通过直播深度了解单本书的内容,又能够通过短视频对出版社有一个整体把握。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图书的销售量还有助于进行用户沉淀,打造私域流量池。
(三)情感化的双向互动
在直播营销的模式中,传播双方之间的交流不再仅仅是营销的内容,还包括围绕图书内容的交流以及彼此的感受与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达成了相同的意义空间,从而为表面化的文本交流赋予了触动情感的空间意义。直播营销场域脉络的情感性不仅仅可以驱使消费的转化而且可以构建“情感启动效应”。因此,未来“直播+出版”传播生态要注重与受众情感化的互动,利用直播场景的相对封闭性和媒介本身的社交性,构建出版社与用户之间的情感互动。
四、结语
直播与出版传播生态的变迁既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出版机构发展模式的更迭,当下虽然强直播阶段成为了出版业可借鉴的稳定发展模式,但直播与出版传播生态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只是对当前直播与出版传播生态的变迁进行了总结,“未来”的变迁也是值得探讨的视角,5G技术的全连接性对直播与出版传播生态的再一次更新也许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