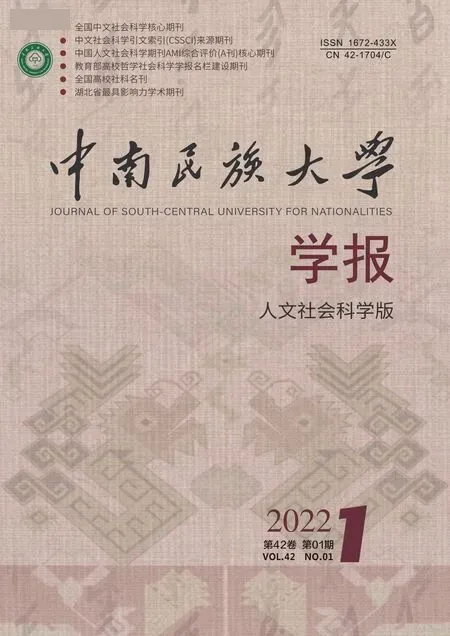妨害安全驾驶罪结果与行为的实质标准及危险犯类型
——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照
2022-11-23夏朗
夏 朗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对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实施暴力或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案件并非新近有之,但真正使公众直观感受到此类行为的危险性,进而发出加强公交司机安全防护、严惩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呼声的,是“10·28重庆公交坠江事故”[1]12。为回应社会关切与民众诉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出台,其后,《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对于本罪,司法适用及刑法理论层面存在如下问题或争议。
(一)司法适用层面:如何界分妨害安全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之前,司法实践中对相关行为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据统计,在2007-2019年间的262起妨害安全驾驶类型的案(事)件中,41.6%的被告人被判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高居所有罪名第一位[2]。这背后的成因可能是:一方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构成要件的规定缺乏明确性,进而,“将一个案件认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于检察官与法官而言,都是一件轻松的事情”[3]。另一方面,民众对重刑化、严罚化的诉求会藉由司法机关反映于司法解释与裁判实务之中[4]。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较重,正好满足了这一“体感安全”诉求。这两方面共同“推波助澜”,使司法实践格外偏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正如张明楷教授所指出的,“越是不明确的法条越容易被司法机关滥用”[3],实务在没有分别仔细地判断是否符合“其他危险方法”与“危害公共安全”的基础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做法并不妥当[5]。考虑到《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定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属于重罪,对其适用应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在可以认定为其他犯罪的情况下,尽量不要认定为本罪”[6]891。就妨害安全驾驶罪而言,该罪法定最高刑仅为一年有期徒刑,属于轻罪。如果将仅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行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既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然而,如何将妨害安全驾驶罪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口袋”中剥离,却是司法适用中的难点问题,因为,妨害安全驾驶罪构成要件用语与以危险方法妨害公共安全罪高度契合。从两罪构成要件的对应关系来看,妨害安全驾驶罪罪状中的“危及公共安全”是对结果危险的限定,对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状中的“危害公共安全”;妨害安全驾驶罪罪状中的“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是对“暴力”、“抢控”等行为手段的内蕴行为危险的限定,对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状中的“其他危险方法”。而将仅有一字之差的“危及公共安全”等同于“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将“暴力”、“抢控”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至少在文义上不存在太大障碍。因此,只有在厘清这些对应概念之间的实质区别后,才能较为清晰地界分两罪,此为本文的问题意识之一。
(二)刑法理论层面:妨害安全驾驶罪属于何种危险犯
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罪属于何种危险犯的问题,存在“具体危险犯说”与“抽象危险犯说”的分歧。同时,即使对此问题持相同见解的学者,对于“危及公共安全”是否须由司法在个案中进行具体判定以及“危及公共安全”的意涵等问题,亦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周光权教授及邓永定博士均认为妨害安全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但就“危及公共安全”是否须由司法在个案中进行具体判定的问题,前者持肯定观点[7]226,后者则持否定观点[8]。又如,张明楷、劳东燕、陈兴良以及刘宪权教授均认为妨害安全驾驶罪是具体危险犯,但就“危及公共安全”的意涵问题,张明楷教授明确指出“危及公共安全”所要求的危险程度低于《刑法》第二章中的其他具体危险犯的要求[6]934,而劳东燕[1]12-13、陈兴良[9]以及刘宪权[10]则似乎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上述现象既是因为对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界定不同,也源于对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的理解有别。
如果认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分野在于前者的危险是需要司法具体判定的危险,后者的危险已由立法事先推定[11],那么主张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是需由司法进行个案判定的危险的学者就会认为本罪是具体危险犯;反之,认为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已由立法推定的学者则会主张本罪是抽象危险犯。而如果认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分野在于前者是高度的危险,后者是缓和的危险[12],并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作为“具体危险”的标准,那么主张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等同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学者就会认为本罪是具体危险犯;反之,认为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对危险程度的要求轻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学者,则既可能得出本罪是具体危险犯的结论,如张明楷教授[6]934,也可能得出本罪是抽象危险犯的结论,如梅传强教授[13]。这里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具体危险是否存在程度之别?如果不存在程度之别,意味着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只有一种程度,未达到这一程度要求的危险就不属于“具体危险”,进而,“危及公共安全”轻于“危害公共安全”就意味着其不是“具体危险”;而如果存在程度之别,那么“危及公共安全”轻于“危害公共安全”不必然就意味着其不是“具体危险”,而完全可能是危险程度较低的“具体危险”。
由此可以看出,明确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危险犯形态,既取决于如何界分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也涉及到如何理解“危及公共安全”的意涵。本文将以此为问题意识之二,在澄清妨害安全驾驶罪中“危及公共安全”的意涵以及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界分标准后,明确本罪的危险犯形态。
二、“危及公共安全”与“危害公共安全”
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仅有一字之差,不仅学者鲜少探究“危及公共安全”与“危害公共安全”之间的区别,司法解释与司法裁判也存在混同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情况,应予辨析。
(一)危及公共安全应有别于危害公共安全
首先,既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时,没有使用“危害公共安全”而使用了“危及公共安全”的表述,就应当认为这是刑事立法的有意为之。对此,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教授在接受专访时提到,此次修正案对妨害安全驾驶罪采用“危及公共安全”的表述确是为区别于《刑法》第114条中的“危害公共安全”[14],也明确了这一点。
其次,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之前,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司法实践,都倾向于将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而《刑法修正案(十一)》特意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显然是为了建立一个层次性更完备的规制架构,使危险驾驶罪、妨害安全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形成一个从抽象公共危险、“危及公共安全”再到“危害公共安全”进而刑罚逐渐加重的梯度。如果认为“危及公共安全”与“危害公共安全”无异,在实践中则可能出现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一概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从而都成立《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况,使妨害安全驾驶罪没有适用空间[7]225-226,这显然不相容于这种梯度性建构的设想。
再次,《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远高于妨害安全驾驶罪的一年有期徒刑。如果认为“危及公共安全”与“危害公共安全”描述的是同一种危险,难以解释两罪法定刑差距为何如此巨大。
总之,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应有别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而二者之间有何不同则取决于如何具体理解二者的内涵。
(二)危及公共安全意指“一般公共危险”
多数学者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理解为是一种危险程度极高的状态,这并非仅仅因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体危险犯,所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成立标准高,而是考虑到罪刑均衡以及体系关联、法条关系等方面,才将“危害公共安全”限定为一种与实害结果之间仅有一线之隔的危险状态。即,一方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定刑较重,因此构成要件结果应是较为严重的结果;另一方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刑法》第114条的兜底条款,需要与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在构成要件结果上相协调。可以认为,这些犯罪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例示,限定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范围,即“危害公共安全”应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类型造成的危险特点一致:一旦发生就无法立即控制结果,行为终了后结果范围还会扩大[6]891。而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法定刑较轻,且紧邻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规定于《刑法》第133条之一,妨害安全驾驶罪规定于《刑法》第133条之二)。既然危险驾驶行为所造成的危险通常达不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那么从体系关联与协调的角度来看,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也毋需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程度。
据此,“危及公共安全”虽然与“危害公共安全”都是构成要件危险结果,但二者在危险程度上有所差别,妨害安全驾驶罪中“危及公共安全”所要求的危险程度低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程度要求[6]934。本文认为,“危及公共安全”可谓是一种“一般公共危险”,对于“一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1.危险的紧迫、可控程度。通常认为,“危害公共安全”是指危险在因果进程中完全脱离行为人、被害人或第三人的掌控,实害结果的出现具有高度盖然性,实害结果不出现反而具有偶然性的状态。而对于“危及公共安全”,或可将其理解为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前阶段[15]172-174,是一种公共性的结果危险最终停止于公共性实害之前的原因,并不要求出于偶然,因果链条中的情势发展尚处于可控状态的较为和缓的危险状态。例如,在“胡某某案”(1)2018年12月9日,胡某某从婺源县中云镇龙山村乘坐客车前往县城,客车途径华逸大酒店斜对面公厕路段时,因胡某某等乘客要求下车而临时停车,但胡某某不肯下车,司机欧某见胡某某不下车就继续向前行驶,行驶没多久胡某某突然上前抓抢方向盘,导致客车方向向右偏,偏离了正常行驶路径,乘车的武警王某立即上前将胡某某拉开,欧某及时将客车停住。事后查明,事发时车辆处于刚起步的阶段,车速不快。参见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2019)赣1130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中,由于车辆刚起步且车速较慢,即使实施抢夺方向盘的行为,司机也完全有时间和机会制动车辆而不至于造成严重事故。同时,考虑到事发时周边人流、车流较小,难以认为达到了“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程度。但胡某某抢夺方向盘的行为确使客车行驶轨迹发生偏移,具有导致车内、外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一般可能性,属于“危及公共安全”。
2.危险现实化的内容。从危险现实化后可能造成的损害来看,《刑法》第114条中的“危害公共安全”所指向的是第115条中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实害结果,换言之,“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现实化的内容必须是严重的人身及财产损害等物质性结果。仅可能导致少数人轻伤或轻伤以下的轻微物质性结果的危险,或仅引起公众恐慌的非物质性结果的危险,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3]。而“危及公共安全”这种危险现实化后的内容,则通常是一种非(重)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物质性结果,或是仅足以引起或已经引起心理恐慌的非物质性结果。例如,在“朱某案”(2)2017年8月18日15时50分左右,周某驾驶101路长株潭公交车行驶至107国道比华利山附近的栗山村站台时询问是否有乘客(不足10人)下车,确定无乘客下车后,周某继续驾驶公交车行驶。当公交车往北驶离栗山站300米左右时(时速约37km/h),朱某要求下车未果,便冲到公交车驾驶室朝周某脸部打了一拳,周某旋即将公交车停住。事后查明,事发时车辆载客少,事发路段车辆和行人较少。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刑终924号刑事判决书。中,虽然朱某实施了妨害安全驾驶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但考虑到即使该危险现实化,也不足以造成多数人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因此认定为“危及公共安全”更为合适。
总之,在妨害安全驾驶类型的案件中,对作为结果危险的公共危险的判断,应结合车速、载客量、路况、人流、车流密集程度以及事发时间点等内、外部情状进行综合判定。要评价为“危害公共安全”,通常应是发生在主干道、要道或路口等人员、车辆密集区域,或者在桥梁、隧道、高架、陡坡、急弯、高速公路等危险路段,或者车速较快,或者事发时处于雨天、雾天、雪天等恶劣天气条件下,又或是处于上、下班高峰时段等等。而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则通常是一种较为和缓、尚且可控且危险现实化的内容较为轻微的“一般公共危险”。
三、“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与“其他危险方法”
一般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须与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行为危险性相当、同质、等价。从性质上来说,“其他危险方法”应在客观上具有导致不特定多数人重伤或死亡的内在行为危险性;从程度上而言,“其他危险方法”应具备导致不特定多数人重伤或死亡的直接性、迅速蔓延性与高度盖然性[16]。进而,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要认定为属于“其他危险方法”,应是足以使车辆完全失控的行为。
而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行为则毋需与“其他危险方法”相当。因为,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原本就具有风险,这种风险在正常驾驶的情况下是被允许的,但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以不被允许的方式进一步升高了驾驶行为本身所内蕴的风险。至于行为将风险升高至何种程度足以达到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所要求的行为危险程度,则取决于“危及公共安全”所意指的危险程度。如前所述,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结果危险是一种较为和缓、尚且可控且危险现实化的内容较为轻微的“一般公共危险”。既然如此,“由于只要行为足以使公共交通工具的车速异变(非正常加速或非正常制动)或车体行驶轨迹异动,就会合乎规律地、高度盖然性地造成‘一般公共危险’,或者说,达到了这一危险性标准的行为就适足于‘危及公共安全’,因此,本罪行为危险的标准应是‘干扰适足性’,即足以使公共交通工具(短暂)脱离原本的正常行驶状态已足,而毋需达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所要求的足以使车辆失控的危险性程度”[17],这也对应于本罪罪状中对构成要件行为属性的界定——“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
例如,在“朱某某案”(3)2019年9月17日,朱某某伸手拉扯行驶中的搭载16名乘客的客车的方向盘,时间在一秒左右,司机吴某将其手推开,引起客车轻微晃动,最终朱某某被售票员陈某及时拉开。参见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2刑初394号刑事判决书。中,一方面,朱某某短暂、轻微且被及时拉开后就停止了的拉扯方向盘的行为,显然不足以使车辆完全失控,不与“其他危险方法”相当;另一方面,虽然朱某某仅是短暂、轻微拉扯方向盘,但由于方向盘本身的转动会直接导致车辆方向的变化与车身晃动,使得原本正常行驶的车辆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移进而(短暂)脱离原本的正常行驶轨迹,因此,可以评价为达到了“干扰适足性”这一行为危险的程度要求。又如,在“吴某甲案”(4)2019年6月3日,吴某甲因上、下车纠纷与公交班车司机韩某某发生争执,在公交车经过七里公交站后,吴某甲突然上前抢拨换挡杆,将档位拨至空档并阻止司机韩某某抓换挡杆,韩某某随即用左手控制方向盘并减速靠边停车。参见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9)苏1012刑初660号刑事判决书。中,一般情况下将档位调至空档会使车辆失去动力,但对刹车及方向系统本身不会直接造成较大影响,因此,该案中吴某甲的行为难以评价为“其他危险方法”。同时,在“高档低速”或“低档高速”时,档位对车速能够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而空档会使这种限制机能丧失,因此可以认为该案吴某甲的行为异常地改变了公共交通工具原本的行驶状态,达到了“干扰适足性”这一行为危险的程度要求。还如“吴某乙案”中吴某乙拍打公交车司机握着方向盘的右手的行为(5)参见广东省珠江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3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书。以及“张某某案”中张某某打了正在驾驶客运车的司机左脸一巴掌的行为(6)参见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2020)辽0681刑初73号刑事判决书。等等,均难以评价为是具有使车辆失控危险性的、与“其他危险方法”相当的行为,而是“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妨害驾驶行为。
简言之,妨害安全驾驶罪罪状中的“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是对本罪行为手段的属性(行为危险性程度)的限定,其实质意涵是“干扰适足性”,即足以使公共交通工具(短暂)脱离原本的正常行驶状态,而毋需达到“其他危险方法”所要求的足以使车辆完全失控的程度。
四、妨害安全驾驶罪是具体危险犯
上文已述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是指“一般公共安全”,其危险程度低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在明确了这一点后,要厘清妨害安全驾驶罪属于何种危险犯形态,就需要进一步明晰不同危险犯形态之间的界分标准。
(一)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分野标准
周延且有实际意义的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分野标准应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所划分出的集合能够囊括、穷尽危险犯的所有类型;第二,危险犯类型之间能够得到清晰界分。据此,以危险程度或危险是否紧迫来区分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认为“前者的危险程度轻于后者,前者的危险较为和缓,后者的危险较为紧迫”的标准并不可取。因为,有些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未必就是轻度的、和缓的危险,例如,我国《刑法》第144条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通常被认为是抽象危险犯,但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造成的往往是紧迫的危险[18]215;又如,《日本刑法典》第108条针对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被公认为是抽象危险犯,但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危险却是紧迫而非和缓的[19]。因此,这种标准并不周延。而以立法是否已事先推定危险来区分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认为“危险由立法推定的犯罪是抽象危险犯,危险需司法具体判定的危险是具体危险犯”的标准,也存在疑问。即使承认这种推定允许被反证,其“似乎只是用来诠释在实证刑法中既存的抽象危险犯类型,但我们却不能在危险推定说中发现转换证明负担的实质理由何在,这无疑已违背了宪法层次的罪疑惟轻原则”[20]。
本文认为,应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来共同界分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
1.形式标准:条文是否明文规定了构成要件危险结果。条文明文规定了构成要件危险结果的是具体危险犯,条文未明文规定构成要件危险结果的是抽象危险犯。之所以强调“明文规定”,是因为有学者认为,即使构成要件结果危险并未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呈现在罪状中,其也完全可能以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形式存在。即“虽然危险的发生不是明示的构成要件的标志,但是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应当通过解释将危险的存在视为暗含的构成要件标志”[21]。进而,抽象危险犯也具有构成要件危险结果,需要司法具体个案判定。这种“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说”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将抽象危险构成要件化可能导致抽象危险与具体危险没有质的差别,进而使得抽象危险犯变为具体危险犯的翻版[22];另一方面,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的添加,需要具备充足、必要的理由。如果考虑到“立法者已将这种典型行为纳入可罚范畴,即表明他对其可能的危险性的排除已有所体认,但仍不愿放弃刑罚”[23],那么,这种将抽象危险构成要件化的做法可能就是对立法意图的不尊重。
2.实质标准:处罚依据是结果危险还是行为危险。着眼于上述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在形式上的差异,其实质是,具体危险犯处罚的是结果危险,而抽象危险犯处罚的是行为危险。刑法中的危险可分为行为危险与结果危险,前者是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导致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也可称为行为的属性;后者是指行为所造成的对法益的威胁状态[18]213。刑法通常的处罚依据是结果危险,但在有强烈的目标价值导引,为了实现对法益前置化、扩展性保护这一目标价值时,也会处罚仅有行为危险的情况。这其中明显存在立法者在社会风险量化评估后,代表强化社会利益保护的立法动机与对非防堵不可的典型危险的提前控制的政策考量[24]。对此,与其说是对国民自由的限缩,毋宁说是立法者在风险社会之下,对“社会民众安全诉求”[25]的回应,以及基于“行政处罚不力现状”[26]的不得已却又必要之举。
简言之,如果罪状中没有明文规定构成要件危险结果,就意味着,成立犯罪不需要结果危险,此即抽象危险犯。反之,如果罪状中已明文规定了构成要件危险结果,就是具体危险犯,对于这种结果危险需要在司法中进行具体的个案判定。
(二)应将妨害安全驾驶罪归为具体危险犯而非抽象危险犯
从形式标准来看,妨害安全驾驶罪不符合抽象危险犯的构造特点而应属于具体危险犯。上文已述,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中不应存在对结果意义上的危险之规定而仅规定构成要件行为即可。显然,“危及公共安全”是对构成要件结果的规定。从反面说,如果立法欲使妨害安全驾驶罪成为抽象危险犯,完全不需要也不应当规定“危及公共安全”。既然明文规定了这一条件,就说明“危及公共安全”是需要在司法中被证明存在的要素,而非无实意的“注意性要素”,但也有不同观点[27]。
从实质标准来看,妨害安全驾驶罪也应属于具体危险犯。对此,关键在于澄清,“危及公共安全”是对行为危险的征表还是对结果危险的征表。本文认为,一方面,“危及公共安全”显然是指一种与行为属性相区别的外部状态[28],征表的是一种结果危险。另一方面,上文已述,“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才是对本罪行为手段的属性(行为危险性)的描述,如果认为“危及公共安全”征表的是行为危险,则无疑成了“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同义反复,这是没有意义的。
一言以蔽之,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是被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危险结果,本罪的成立需要存在结果危险。因此,妨害安全驾驶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在司法实务中需要对是否“危及公共安全”进行具体的个案判定。
(三)妨害安全驾驶罪不是“准抽象危险犯”或“准具体危险犯”
对“具体危险犯说”可能的质疑是,既然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程度低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而后罪又是公认的具体危险犯,那怎么还可以说妨害安全驾驶罪也是具体危险犯呢?进而,就会认为妨害安全驾驶罪应属于“准具体危险犯”或“准抽象危险犯”。但本文认为,妨害安全驾驶罪不是“准抽象危险犯”,也没有必要称其为“准具体危险犯”。
1.妨害安全驾驶罪不是“准抽象危险犯”。“准抽象危险犯”的特点是:一方面,其危险是一种内蕴于行为的属性,是作为行为意义上的危险性,进而区别于以结果意义上的危险为构成要件与不法本质的具体危险犯;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危险性的有无又需要司法进行个案判定,从而区别于(狭义)抽象危险犯[29]87-89。
首先,“准抽象危险犯”这个概念本身是否成立,值得商榷。一方面,“准抽象危险犯”这个概念的提出原本是为了解决对于某些被认为是抽象危险犯的犯罪,如果行为当时完全不可能造成任何法益侵害,连“抽象危险”都没有,就不应当处罚,但按照通常对抽象危险犯的理解,抽象危险不由司法个案判定,进而也就不允许反证,那么就无法对这些事实上完全没有任何危险的行为出罪处理的问题。所以,主张应将这些犯罪归为“准抽象危险犯”,是需要对“抽象危险”进行具体判定的危险犯。然而,如果承认抽象危险犯允许反证,则不需要创设“准抽象危险犯”这个概念。另一方面,对行为的认定本就应实质判断,没有法益危险的行为原本就不具有相应的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符合性。既然如此,如果认为“准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判断只需要考虑行为本身的因素,就与对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符合性的认定采实质判断一致。而如果认为“准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判断还要考虑行为的时空环境甚至前后的所有事实,那么与具体危险犯中对危险的判断又似乎没有区别。因此,“准抽象危险犯”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存疑的。
其次,即使承认“准抽象危险犯”的存在,妨害安全驾驶罪也不属于这种形态。第一,“准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一种行为危险性,其成立毋需结果危险的存在。而妨害安全驾驶罪罪状中的“危及公共安全”这一表述显然是指结果意义而非行为意义上的危险,或者说,“危及公共安全”并非直接修饰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本身,而是额外要求达到的一种外部危险结果状态。因此,本罪的罪状不符合“准抽象危险犯”的特点。第二,虽然妨害安全驾驶罪罪状中除了“危及公共安全”外,尚有“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这一对行为属性(行为危险性)的描述,但这并不能成为本罪是“准抽象危险犯”的依据。当法条或司法实践对某个行为造成的危险进行了划分,对其中的一部分危险赋予抽象意义,对其中的另一部分危险赋予具体意义,而划分为具体危险的那部分比划分为抽象危险的那部分更重要时,说明对危险判断标准的依赖,已超越了(准)抽象危险犯所能容纳的限度[23]。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罪而言,法条以“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赋予了行为层面上的危险性意涵,即行为本身应属于一种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具有“干扰适足性”的行为。同时,又以“危及公共安全”赋予了结果层面的危险以具体内涵,即必须现实性地存在公共性的结果危险。从重要性来看,真正充足本罪不法的应是“危及公共安全”这一结果危险而非“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这一行为属性,因此,本罪已超越(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涵射范围。
2.毋需将妨害安全驾驶罪称为“准具体危险犯”。“准具体危险犯”是指,在刑法条文中有明确的对结果危险的要求,但其所谓的“危险”并不是针对刑法保护法益现实上的“具体危险”,而是伴随着保护对象的一般化,在具体危险阶段之前所认定的危险状态[30]。例如,在Binding所举的“溃坝案”中,行为人炸堤的行为本身是有危险性的,但从水库的水到达下游数百里外的村庄,这期间,应该存在一个由行为危险性所引起的,从较为和缓的现实危险状态,再到紧迫危险状态的危险程度逐渐升高的过程。在“溃坝案”中,很显然存在两种危险强度不同的情状,可以把前者理解为后者的前期阶段,立法者也完全可以以这种前期阶段为依据设定犯罪类型。在德国,这种犯罪类型被Zieschang称为“以引发具体的危险状态为前提的犯罪”,其认为,结果危险可进一步分为紧迫的具体危险和不紧迫的一般危险,对于“以引发具体的危险状态为前提的犯罪”,行为造成外部一般危险状态是其构成要件要素,也需要法官具体考察[29]。在日本,山口厚教授称之为“准具体危险犯”,其认为,“具体危险”指的是现实所存在的对法益的迫切危险,在此之前阶段的危险状态,则称为“准具体危险”。在保护对象是多数或不特定法益的情形下,在具体危险发生之前的前阶段仍有刑法加以介入之必要性与合理性[15]172-174。
显然,“准具体危险犯”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有些犯罪造成的危险程度较为和缓、轻微,似乎难以归为具体危险犯。同时,这种危险本身又确是一种结果危险而非行为危险,似乎也难以归为(准)抽象危险犯。为了给这类犯罪在危险犯范畴中寻求合适定位,就创设了“准具体危险犯”这个概念。
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将妨害安全驾驶罪称为“准具体危险犯”。诚然,“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程度确实低于“危害公共安全”,且是一种结果危险,似乎符合“准具体危险犯”的构造特点。但是,具体危险犯中的“具体危险”原本就包括不同程度的危险,对于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准具体危险犯”的犯罪,例如妨害安全驾驶罪,将其仍归为具体危险犯,同时明确其结果危险的程度要求较低足矣。
具体而言,一方面,既然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中的“具体”与“抽象”的意思并非“高度危险、紧迫危险”与“低度危险、和缓危险”,而是指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危险结果与没有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危险结果,那么即便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程度低于“危害公共安全”,也不影响将其归为具体危险犯。另一方面,即使认为具体危险的危险程度高于抽象危险,那也是就同一种犯罪而言的,某种危险犯的危险低于另一种具体危险犯的危险程度,并不必然就意味着它是抽象危险犯而不可能是具体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中的不同“具体危险”的轻重缓急可能差异甚大,例如有学者根据具体危险的程度不同,将具体危险犯进一步划分为紧迫型具体危险犯、中间型具体危险犯以及轻缓型具体危险犯[31]。因此,承认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所意指的“一般公共危险”轻于“危害公共安全”所意指的“具体公共危险”,并不影响将前罪归入具体危险犯的范畴。简言之,具体危险犯中的“具体危险”可以包括“一般危险”在内,因而无需创设“准具体危险犯”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