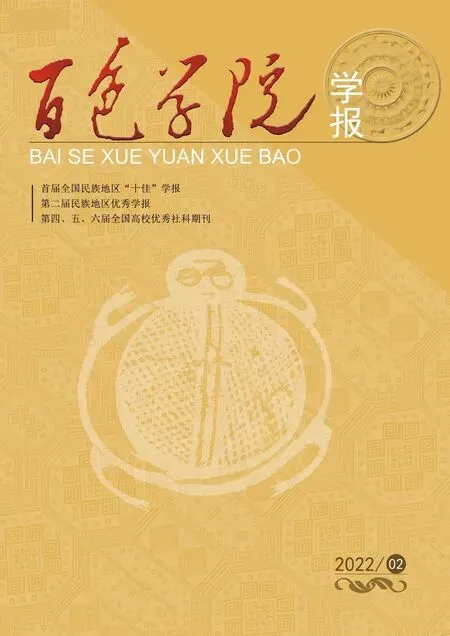傣族的“史诗歌手”章哈:师承、演述与发展
2022-11-23屈永仙
屈永仙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在文字和书写广为流通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知识记忆和传播手段之前,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记忆及传播主要靠口耳相传。”[1]在这个“前文字”时代中,歌手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佛教传入傣族地区后傣族先民创造并开始使用文字,但是绝大部分历史文化仍靠口头传承。口头诗歌是文字流通之前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傣族民众记忆、传播知识和历史文化的主要手段。“章哈”(也称为“赞哈”)正是名副其实的“故事歌手”,他们走村串寨,将优美的诗歌传到广大民众之中。他们是傣族历史上重要的知识传播者和传承者,对傣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史诗歌手,也称“故事歌手”“说唱艺人”,都是借助合辙押韵朗朗上口的韵体诗歌作为记忆的法门来叙述、演述故事的人。正如藏族有《格萨尔》的说唱艺人“仲巴”(或“仲肯”),蒙古族有《江格尔》的故事歌手“江格尔奇”,柯尔克孜族有《玛纳斯》的史诗歌手“玛纳斯奇”,傣族则有“章哈”,意思是歌唱的能者、艺人、师傅。他们都是史诗的演述者、传播者和创作者。一个合格的章哈应该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够完全脱稿地口头演述长篇诗歌;二是能够根据现场情况即兴创作;三是能够独立表演,灵活应对受众的反馈并与之互动。简言之,“他们是在不借助写的前提下传播和创作诗歌的人。”[2]章哈的演述有独唱、对唱和合唱三种方式,但是在仪式中演述长诗时以对唱形式居多,时间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通宵达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德宏、孟连、临沧、保山等其他傣族地区皆有史诗、长篇叙事诗流传,也有称呼不尽相同的佛经演述人和歌手,但是基于前人资料和实地调查来看,只有傣泐支系才有“章哈”,他们属于口头诗学意义上的“史诗歌手”。目前在傣泐支系以外并未发现有能够完全脱稿口头演述史诗、叙事长诗的歌手。可以说,“章哈”是傣泐支系的文化符号之一,随着傣泐南迁到东南亚地区,章哈文化也传到了各地。在老挝北部和泰国北部也有不少泰泐歌手,他们称之为“哈泐”(Khap Lue),即“泐人的歌手”。
下文根据笔者在西双版纳以及缅、泰、老三国的北部地区所做的一些田野考察,探讨章哈的学艺过程和师承模式,他们在演述过程中的即兴创作与互动能力,国内外章哈的发展趋势。
一、章哈的习得与师承
傣族章哈有男有女,他们通常会同台对唱,一问一答共同演述一部完整的史诗。在传统的傣族社会中,男童有入佛为僧的习俗,他们因此在佛寺中学得傣文和其他知识;而傣族女性则没有入寺学习的机会。在章哈的成长之路上,打好傣文基础然后通过背诵诗歌文本掌握越来越多的篇目是普遍方式。尽管章哈必须是脱稿演述,但歌本是他们习得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拐杖”。诸多案例表明,男章哈和女章哈具有不一样的社会资源和文化基础,其习得之路往往是“男易女难”。
西双版纳在历史上与中原长期隔绝,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聚居于此的傣族大多数没有姓氏。男子名一般称为“岩XX”,女子名则称为“玉XX”,这好比汉语中的“XX 君”和“XX 姬”,“岩”和“玉”绝非姓氏。笔者采访过许多章哈,他们的名字有较高的重复度。基于此,本文将如实记录其姓名,但会舍去其他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一)男章哈的习得——以岩拉为例
岩拉是能够演述创世史诗《捧尚罗》的男章哈之一。他生于1963 年,家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镇。岩拉所在的村子居民并非世代居住于此,而是从玉溪迁下来的傣雅支系,由于和周边的傣泐支系长期共处,彼此通婚往来紧密,久而久之就融入了傣泐支系,喜欢听章哈唱歌,并且有不少人也成了章哈。
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章哈呢?岩拉回答说“是为了赚钱”。在西双版纳,民间歌手早已经发展成一种职业,章哈们以演唱获得主要的经济收入。岩拉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学过新傣文,也读过几年小学,认识一些汉字。22 岁时他才开始学习章哈演唱,最初是跟邻村的一位名叫岩才达留的老章哈学,后来又跟他的大姐夫岩拉罗学习。成为合格的章哈后,岩拉边学边唱,在实践中成长很快。他曾经到过勐罕、勐阿、勐宋等地与其他章哈对唱,有的还成了良师益友,其中一位就是勐罕的老章哈岩罕罗。如今,岩拉已是一位资深的中年章哈,他有着20 多年的演唱经验。至今依然受民众欢迎,经常被附近的村民邀请去在一些仪式上演唱,包括升和尚、贺新房、婚礼等活动。他最远曾去过缅甸的勐勇、勐哏、勐养等地演唱,听众主要是那些跨境而居的傣泐人。
岩拉代表了大多数章哈的水平,虽不是顶尖的“章哈勐”,但他所掌握的篇目足够应付日常仪式所需。在婚礼上唱与姻缘、人类起源相关的《布桑该》;上新房仪式上唱与房屋起源相关的《帕雅桑木底》《贺新房歌》;在祭祀寨神、勐神时唱《捧尚罗》(神创世)以及地方历史传说。此外,他比较熟悉的篇目有《维先达腊》和《西塔》(悉达多)、《嘎迫》(白乌鸦)等佛经故事,这些都是仪式演述中的热门篇目。岩拉较少演述《兰嘎西贺》《召树屯》《相勐》等这些史诗,他解释说一方面它们与日常仪式没太多联系;另一方面,这几部史诗内容宏大,一般的章哈不能驾驭。此外,有老章哈解释,《兰嘎西贺》具有某种神秘力量,村民不能随意将它拿回家中诵读,传说这将会招致火灾。总之,与仪式关联不大的诗篇被演述的概率很低,这些冷门的篇目需要专门的演唱培训。如今,西双版纳州文化馆不定期组织章哈培训,演唱曲目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召树屯与喃木诺娜》等。
在章哈们的心目中,创世史诗《捧尚罗》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涉及开天辟地、诸神诞生、人类与万物起源等许多神话。一方面,该史诗内容古老而丰富,深受老年受众的欢迎;另外一方面,该史诗含有许多历史文化知识,章哈们在赛唱过程中常提出相关的问题来考验对方的演述能力和知识储备。因此,资深的章哈几乎人手一本《捧尚罗》。岩拉手中也有《捧尚罗》手抄本,是从他姐夫岩拉罗那里誊抄来的。原来的版本是老傣文抄写,为了让更多的年轻章哈可以看懂,岩拉罗将老傣文转写成了新傣文。岩拉将抄本带回来后靠自学,逐段背诵直到全部记住。当他受邀去上新房仪式演述的时候,通常会唱到这部史诗,许多老年人会听得津津有味。岩拉回忆,1998 年他到曼勒莱唱《捧尚罗》,那时候与他对歌的是水平较高的女章哈玉轰。他们唱了一整夜,当时几乎全村的村民都来听,屋里坐满了人。
如今也有一些章哈来向岩拉拜师,其中两个男章哈就在本寨,两个来自勐遮镇,还有两个女章哈是勐混人。这几个徒弟年纪都已30 多岁,都能上场演唱,在当地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有时徒弟们应邀去演唱,岩拉会前往捧场,如果他们唱错了或者忘记歌词了,他会认真地指正。当他应邀到勐养、勐勇等地演唱时也会带上某个徒弟,有时候徒弟还可以唱若干片段。这不仅是徒弟见习的机会,也是他们积攒人气的过程。岩拉表示,章哈基本都是零门槛收徒,凡是想跟他学章哈的人都可以跟他拜师。如果学徒基础不好,那他会先教他们练习基本功,包括识傣文、背歌词和练习章哈调等。如果学徒已经是一位章哈,届时他会将自己手中的唱本分段抄写给他们自己去琢磨练习。
除了岩拉之外,笔者还访谈过勐腊、勐龙、勐海等地的章哈,如岩帕、岩三布歪、岩邦等等,他们学成章哈的经历与岩拉大同小异。受访的男章哈几乎都懂傣文,年长的懂老傣文居多。他们大多是在佛寺里学到了傣文,少数是在学校里学的。总体来说,男章哈有先天的优势。另外,男章哈更容易获得支持和理解,家人大多能包容他们在农忙时的缺席,妻子能体谅丈夫外出挣钱无法尽家庭责任的难处。
(二)女章哈的习得——以玉旺叫为例
西双版纳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佛教,但是女性不能入寺为尼。①德宏瑞丽、盈江有傣族尼姑,傣语称“朗浩”。因此,若她们要想成为一名女章哈,最好先跟家中男长辈学习傣文,有的跟师傅学,极少部分女章哈是文盲,全靠记忆力。如玉旺叫是知名度中等的章哈,是绝大部分女章哈的代表之一。她生于1970 年,家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镇。章哈是她一生的事业,她从小就爱唱歌,早在12 岁那年就开始跟随本寨的老章哈岩龙学习。结婚后因为丈夫的反对加上家务繁重,她就没有出去唱歌了。后来她离了婚,孩子也已长大成人,于是她再次一心扑在章哈演唱上。她说自2000 年时她就发现章哈人数越来越少,她希望能将章哈文化传承下去。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她还重新去拜了几个师傅,其中一个是勐海县的岩帕(省级传承人)。如今,她已在勐遮附近小有名气,也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
玉旺叫称自己拜过3 位师父。第一位是她的启蒙老师岩龙,他把歌词写在黑板上教她,让她识傣文,认识唱词的韵律和句式,学会章哈曲调。第二位师父她称之为罕燕大爹,那时她已经是一名合格的章哈了,她从他那里学过几首曲目。第三位是岩帕,他主要教玉旺叫如何用恰当的形容词润色出优美的诗句。她认为自己水平有限,多拜师傅就能多获得一些抄本,多学一些新歌曲。因此,玉旺叫也将岩拉视作自己的师傅,因为他抄给了她一份《捧尚罗》,这是她一直想学习的史诗。她以前常听老章哈们唱《捧尚罗》这部古老的歌,但凡祭寨神勐神,或者贺新房时老人们都爱听这个叙事。自从岩拉把唱本给了她一份后,她就废寝忘食在家里背诵、练习演唱。
与其他章哈一样,玉旺叫会唱的歌大多是仪式上常用的篇目。贺新房时她能唱《帕雅桑木底》,升和尚仪式上她能唱《维先达腊》《西塔》,如今她也能唱《捧尚罗》《布桑该》了。她每次受邀去演述的时候,村民们会自己抬着小凳子前来听歌,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如果她唱对了,听众们就纷纷表扬她,唱错则会引发低声议论或笑声,听众是章哈传统的检验者和监督者。玉旺叫说她几乎唱遍了勐遮镇附近的村寨,但她至今还没有收到徒弟。她希望能有人来跟她学章哈,她将会认真教学。可惜现在大部分傣族年轻人对章哈文化并不感兴趣,也听不懂内容。
除了玉旺叫,笔者也采访了若干女章哈,如勐遮的玉章、玉叫、玉燕等,她们的命运与玉旺叫有相似之处。她们年轻时具有唱歌的天分,心中对章哈充满向往和热爱,因此拜师学艺入了这行。等到成家后她们必须在歌唱事业和家庭之间权衡和选择,大部分人放弃了歌手职业,回归了平静的农妇生活。因此,女章哈比男章哈承受了更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能够坚持唱歌到中年的女章哈人数较少。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章哈的习得基本是这样的轨迹:在日常生活中聆听和了解章哈并热爱章哈文化,然后拜师学习打基础,包括学傣文、曲调和韵律,背诵和练习演唱短篇、中篇、长篇曲目。他们对章哈传统的耳濡目染和日积月累,量变引起质变最后可以独立演唱。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学傣文并非必要条件。历史上不乏文盲章哈,他们可凭强大的记忆力来演述史诗。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些女章哈双目失明,她们通过拜师求教,博闻强识成为远近闻名的歌手。如今,绝大部分人在初学阶段仍然是依赖文字和歌本的。拜师学习可以发生在任何阶段,有的从零基础时就拜了师傅,有的能独立演唱了才拜师。最重要的是夯实基本功,包括学会诗歌韵律和章哈曲调,学会聆听笛声②从伴奏乐器角度来分的话,章哈分为“哈赛苾”和“哈赛玎”,前者是笛子伴奏,后者是二弦伴奏。章哈演述史诗多半以笛子伴奏,笛师傣语称为“摩苾”。并与之配合。学习的过程中需要跟随师父见习,参与小范围内的片段式演述,并从中学习师傅处理突发情况、即兴创编以及和受众互动的技巧。当他(她)在公开的场合演唱并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后,邀请函也会纷至沓来,自然而然就成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章哈了。
如此看来,学习章哈是零门槛或者门槛极低,一部分人可以拜师学习,一部分人全靠自学掌握。一是因为章哈曲调简单易学,可以通过聆听和模仿来学得,同时有抄本作为辅助的工具;二是凭个人对章哈文化的热爱自愿学习。总之,坚持练习就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章哈,习得过程简单且可操作性强。
(三)章哈的师承模式
章哈有一定的拜师礼,傣语称“胆夯”。在拜师当天,徒弟准备一只鸡、几个鸡蛋、两斤肉、3 斤酒、帕阶囡(手工制作的绵手帕)、8 根腊条和人民币(近年一般为300 元)前往师傅家中奉礼。如果师傅收下,师徒关系就正式确立了。出师时也要举行结业仪式,傣语称为“波夯”。章哈一生中可拜多个师傅,他们既是师徒,也像是朋友。以岩拉为例,他在不同时期拜了3 个师傅(岩才达留、岩拉罗、岩罕罗),这是师承关系的上一层;岩拉还收有4 个徒弟(岩山囡、岩温罕、玉罕、玉应香),可以看作师承关系的下一层。绝大部分章哈的师承符合这种情况,他们既向多位师傅学习,又教授若干学徒。资深的章哈可以收几十位学徒,例如“从20 世纪80 年代起,景洪市两个著名的老章哈——勐罕镇曼岭村的波双和景哈乡景哈村的岩罕罗,主动承担起教授学生的义务,分别教了40 余名学生”[3]149。
在“非遗”之前,章哈行内有自己的评级制度。一个勐的行政首领叫“召勐”(土司),被封为“章哈勐”的人就算是全勐章哈的首领。勐腊县勐捧镇勐哈村的康朗屯(1939 年出生)就是一个“章哈勐”,在1961 年他就已经获得了这个称号,可谓远近闻名。除了西双版纳各地傣族,老挝北部的一些傣泐也纷纷来邀请他去演唱。笔者于2012 年8 月访谈了他(那时73 岁),他家传统的木楼廊上挂着许多绵纸抄本,大部分是歌本和佛经故事的“母本”,空闲时他常在阁楼上抄写副本,用来送给自己的徒弟或者出售给需要的人。那时他已收了30 多个徒弟,男女均有,大部分徒弟是已经可以独立演唱的章哈。徒弟们来到他家里学习,他会将创作好的歌篇给他们带回去自学。有不会拿音、不懂意思的地方下次再来问他。逢年过节徒弟们会不约而同前来拜谢师傅,有的带一些礼品答谢,有的则将他们在演唱获得的酬金分给师傅。
傣族章哈在2006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此后一些资深的老章哈逐渐被认定为章哈传承人。目前国家级章哈传承人有康朗屯、玉光,省级传承人有岩帕、岩罕罗、波双、波旺优、依香、玉涛坎。[4]314-315其中,岩帕是勐海人,他生于1939 年,18 岁开始唱歌。到了1976 年,也就是他37 岁时开始收徒,截止笔者采访时他已经收了74 个徒弟了。这些徒弟来自西双版纳各个地方,年龄小的有8 岁,年长的有40 多岁。岩帕家门口挂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傣族章哈演唱传习所”牌子,堂屋内铺着几个简单的垫褥,家近的学徒可随时来找师傅学歌,家远的可小住几日专心学习。岩帕说那些有傣文基础的人学得比较快,有的从入门到出师仅需两个月。没有傣文基础的需要先教傣文,然后写一些简短的句子让他带回练习,等学好了再来师傅家里背诵和试唱。师傅听后发表一些指导意见,再抄一些合适的曲目给他带回去继续练,如此循序渐进。
在演唱实践中章哈能够迅速提高自己的能力。笔者访谈岩帕的时候,正遇到一个勐遮来的徒弟(当时39 岁),因他在赛唱中答不出对方的歌,于是当晚紧急跑来请教,第二天一早他拿着师傅给的两首曲子又赶回去了。岩帕的大多数徒弟每次来都会带着一些具体的要求和疑问,他了解具体情况后会给他们带回一些新歌稿,自己不断练习直至完全背诵。可见,这种师傅类似于研究生的“导师”。有时师傅和学徒就是赛唱中结识的对手,所谓“不打不相识”,败下阵的一方心甘情愿向对方拜师学习,最后形成了良师益友的关系。岩帕曾经去过许多地方演唱,除了西双版纳各勐,也到老挝孟新等傣泐的聚居区。游唱四方的章哈,一方面可以在旅途中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地方人文知识,吸收沿途的有趣叙事,这些内容都可以编入他的歌中;另一方面,章哈也需要在赛唱中寻觅知音,淬炼出优美的诗句,不断增长自己的唱功。
笔者试着构建章哈的师承模式。大多数曲艺的师承都是树状结构的,通常追求一脉相承和开枝散叶的宗旨。因此,不同的师承之间具有排他性,这是门派之间的自我保护。这种师承模式与中原文化的宗族观念相符合,体现了一种香火传承的理念。相对来看,傣族的章哈传承呈现出一种网状结构,某个节点代表一位章哈,他上面有多个线条链接到不同的点,这些点是他的师傅们;他的下面也可以分散出几条线链接到其他点,他们则是徒弟,同时徒弟也可能是同门,他们有共同的师傅。因此,章哈的师承模式是一种不规则的网状模式。如果将这种结构放大,很可能会得到一个类球体,历时性和共时性在这里都失去了意义。总之,章哈的师承关系不具有排他性,而含有强烈的内聚力。
这种师承模式与傣族的扁平化家庭网络结构是相符合的。首先,正如西双版纳傣族大多没有姓氏一样,民间社会是没有宗族观念的。傣泐人死后通常采取火葬,就连骨灰都不会拿回家摆放,家中也并没有祖先牌位。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会统一汇入祖先众神,逢年过节子女会到佛寺为已故父母滴水祈福,也有在房屋神柱①神柱,也叫女柱,傣语称“绍婻”,位于主人卧室内,是家神的寄居地,汇集了祖先的灵魂。此神柱是神圣的,人死后需停放在这里。外人不可随意进入主人的卧室,更不可触摸该神柱。那里供上一些食物。每人只需负责为父母祭祀,三四代后就不记得其祖先了。其次,傣泐人普遍有入赘婚俗,婚后男子到女方家居住一段时间,两三年后或自立门户或回到男方家。在这样的家庭制度和婚俗中,西双版纳傣族并没有形成汉文化中那样浓厚的宗族文化。此外,西双版纳是一种均质化的农耕社会,形成了封闭但却自洽的圆环结构,这样的社会具有较强的内部稳定性。
二、章哈在仪式中的演述
学界普遍认识章哈有两个基本含义,即傣族的民间歌手和曲艺形式。不过,我们不妨从章哈的视角来重新理解该词的含义。在对岩帕等几位章哈的访谈中,他们都解释道“章”指会者、能人、工匠,这没有异议。“哈”的傣语发音为khap 或xap,该字有多层意思。首先,“哈”是名词,是指有韵律的歌,“甘哈”[kam33xap55]一词意为诗歌。其次,“哈”是动词,是指创编诗歌的行为。例如,如果问对方“你是章哈吗?”是问他是不是一个歌手。如果问“你章哈吗?”则是问他能不能创编诗歌。此外,“哈”还有仪式词的意思。傣语中有“哈摩”[xap55mot35]和“哈疲”[xap55phi35]这两个词,前者是指驱邪词,后者是指撵鬼词。因此,“章”与“哈”组合在一起后,除了具有歌手、曲艺形式的解释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两个层面的含义,它们与史诗歌手在“仪式中的演述”及“演述中的创作”具有密切的关系。
(一)章哈口头演述的史诗文本
章哈有传统的文本可以参照,但是他们每次演述的时候并非固定不变,除了传统的内容外,章哈也会即兴创作加入一些新片段或者删除一些内容。每次演述所得的口述文本与章哈的个人能力有很大的关系。笔者曾承担“傣族创始史诗《捧尚罗》”的录制,②该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子课题,根据该项目的要求,要录制和提交3 部分内容:一部完整的史诗演述视频,一个与章哈演述相关的仪式完整录像,以及对章哈艺人的访谈视频。因为开门节后章哈才可以开始演述活动,所以才选择这段时间完成该课题。在2014 年的开门节期间跟踪拍摄了章哈的两场口头演述:一是10 月2 日傍晚至3 日凌晨,岩拉和玉旺叫两位章哈在勐遮镇曼么代村通宵演唱了《捧尚罗》;二是25 日至27 日他们参加勐龙镇的上新房仪式,贺新房演唱是其中重要一环。《捧尚罗》全称是《巴塔麻嘎捧尚罗》,“捧”泛指神仙,“尚罗”是开世界、造天地。
岩拉认为按篇幅长短可以将《捧尚罗》分为旧本和新本。《捧尚罗》的异文本广泛流传于西双版纳傣族等地,章哈们你传我我传你,你教我我教你,有的文本像滚雪球一样吸收其他文本的内容使得篇幅越来越长,叙事越来越丰富。有些章哈学唱的是新本,有的学的是旧本。岩拉认为自己手中的那个版本篇幅很长,属于旧本,需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唱完。《捧尚罗》在章哈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并非人人都能唱,也不能随时随地唱,一般是在祭祀寨神、勐神、祭寨心这类庄严神圣的仪式场合才能演述该史诗,大多由德高望重的老章哈承担此重任。村民普遍认为在这些仪式中演述《捧尚罗》可以使寨子平安,人畜兴旺。玉旺叫同样认为《捧尚罗》很重要,唱该史诗能使寨子“干净”。当寨子出现瘟疫,村民发生事故或有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届时就邀请章哈来唱《捧尚罗》可以祛邪。简单来说,演述这部史诗具有禳灾驱邪的仪式功能。
章哈的每一次口头演述都能产生不同的史诗文本。在2014 年10 月2 日,岩拉和玉旺叫从傍晚开始他们的演述一直通宵唱到了第二天凌晨3 点多。在各自笛师①岩拉的伴奏是岩温胆(男,1959 年生),玉旺叫的伴奏是岩温洪(男,1974 年生),他们都是勐遮人。的伴奏下,两位章哈轮流演述,中间短暂停息过两次。根据他们所唱的内容整理出标题如下:
第一段女唱“英叭神造天地”。
第二段男唱“神划分四大洲”。
第三段女唱“江河湖泊的形成”。
第四段男唱“众天神的诞生”。
第五段女唱“帝娃达神变绿蛇”。
第六段男唱“神果园——最初的人类诞生”。
第七段女唱“火烧地球和水淹大地”。
第八段男唱“地球复生形成四大洲五大洋”。
第九段男唱“布桑嘎西和雅桑嘎赛造万物”。
第十段女唱“布桑嘎西和雅桑嘎赛造人类”。
第十一段女唱“桑木底建房”。
第十二段男唱“桑木底教人类建房定居”。
这是岩拉和玉旺叫此次口头对唱的史诗文本,通过剪辑形成的演唱视频时长共计130 分钟。将他们所唱的歌词忠实记录成文本后有885 行傣文诗,共约2 万字(含傣文及其译文)。这个文本是无数个口头演述的史诗文本之一,换搭档或换场合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版本。“歌手是表演者,也是创作者……在歌手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文本、原创的文本或原型。每一次表演都是原创的。”[2]章哈演述史诗、长篇叙事诗时,基本都是按照一问一答的演述模式展开。由于每一个章哈师承不同,每个人掌握的史诗内容也就有差异。试想一个国家级章哈传承人与一位资历较浅的章哈对唱,前者必定只能降低水平来配合后者,减少演述的内容,才能以问答形式完成演述。这个道理正如“木桶定律”,即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木板,而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
(二)不同的演述语境
演述语境对口头诗歌的传承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村落仪式,章哈传统便不能生存和繁荣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任何民间的重大活动中,赞哈的演唱都是其中的重要项目,例如盖新房、升和尚、祭幡、请神送鬼、过年过节、结婚、庆丰收、孩子满月等等,都要请赞哈演唱。因此,他们与人民的生活有很密切的联系。赞哈所演唱的内容往往有一定的针对性,盖新房专有贺新房的唱词,送鬼神也有送鬼神的唱词,隆重的年节庆贺活动,则唱开天辟地的故事,或者长篇的历史故事。有时可以连唱几个夜晚”[5]30。附近村寨的群众都赶来听。上新房仪式上自然要唱房子的起源故事,中间会加入许多即兴的唱词,内容以赞美主人和宾客居多;在婚礼中唱婚姻的起源故事,新婚夫妇的成长和成就,祝福他们生活幸福美满;祭寨心、寨神、勐神仪式时要唱村寨的历史,当地的土司家族史、勐神的传说、民族英雄的传说;每年泼水节章哈们要唱泼水节的起源,放高升的起源等。总的来说章哈演述的内容有这几类:“(1)古代神话史诗;(2)历史故事(帝王将相、农民起义皆有);(3)宗教故事;(4)训世箴言、寓言教义;(5)文学唱本;(6)天文地理、历法算术、占ト和字母来历等的唱词;(7)祝词、贺词;(8)对领主头人的颂词。从赞哈们演唱的这些内容来看,几乎包括了傣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实可称为傣族社会的百科全书。”[6]85相对来说,一些与宗教仪式相关的篇目比较有市场,被演述的机会较多。每年傣历9 月15 日至12 月15 日之间的3 个月正是南传佛教的入夏安居期,按照传统傣族民间得停止一切娱乐性歌舞活动,章哈也进入修整期。待开门节后,各项庆典活动启动,章哈们就迎来了一年里的繁忙期,有的忙起来一个月都不能回家,村寨间也随处飘荡着章哈的歌声。
笔者曾经在2021 年10 月25 日至27 日到勐龙参加上新房仪式,目睹了章哈在一片欢庆中演唱的景象。第一天是东家宰牛宰猪准备待客的食材;第二天是邀请僧人来诵经做净化仪式,当天晚饭后章哈开始唱歌,在亲友的聚餐欢饮中一直唱到第二天凌晨;第三天是亲友们帮忙将家具家电搬入新居。实际上,章哈的出场时间并不严格,可以在第二天就来,也可以在第三天来,具体看章哈的档期。章哈坐在屋内演唱,院子里摆着酒席,宾客时不时传来“水水水”的欢呼声,章哈们坐在屋内用话筒演唱,用一个扩音器将他们的歌声播放到屋外。当晚章哈演述了很多叙事,其中就包含《帕雅桑木底》和《布桑该》的内容,凌晨还要唱驱邪词,还有许多赞美主人和宾客的祝福语。屋外的宾客听到高兴时就进屋里给章哈手里送上红包,以此表达赞赏。
(三)即兴创编与互动能力
根据现场情况来即兴创编是章哈的基本功,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开场白、赛唱中的应对以及和受众的互动。首先,在不同的仪式场合中,章哈会根据不一样的受众情况选择开场白,用歌声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例如,在泼水节活动中,可以先描述现场人山人海的境况,或者祈求风调雨顺,进而开始叙述泼水节的起源故事。如果是在婚礼中,要先赞美一番主人家和宾客,新婚夫妇的样貌人品等。见人夸人见物咏物,这种控场能力是国内外所有章哈都必须具备的能力。笔者在泰北清莱府美赛边镇果赛村考察时访谈到了一位女章哈,她小时候在西双版纳出生成长,并跟老章哈学习过。长大后她随父母移居到泰北清莱,成为当地的章哈。当她见到笔者时就即兴唱了一段,内容是欢迎来自祖国的客人,对我们一行远道而来考察泰北的傣泐文化表示非常感动。实际上,许多前辈学者在傣泐地区考察章哈的时候也会遇到相同的情况。
其次,章哈在赛唱中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其临场应对反映了他们的综合能力。要做到这一点,章哈必须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善于将所掌握的诗歌片段(程式)、典故(主题)和故事传说(故事范型)迅速组织好,然后用韵文形式输出。章哈的赛唱最为精彩,也最能吸引听众,双方所提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他们展开叙事的引言。例如,对方问“为什么人会死亡?”答方往往叙述“绿蛇引诱人类吃疾病果导致死亡”的神话。等他唱完,可能会反问对方“为什么男人喜欢抓女人胸部?”对方就要回答“布桑该雅桑该用泥巴造人”的神话。如果对方回答不准确或者缺少一些细节,就会加以反驳或者补充更详细的叙事。在这样考问式的对唱中就显出了孰高孰低。“赞哈在这种赛唱会上单纯能背诵多少现成诗句是完全不够的,还必须有创造性的才能。这种赛唱会对丰富和扩大赞哈演唱的内容、培养和锻炼赞哈演唱的才干、推动傣族诗歌的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不为人们重视的普通赞哈往往就在这种赛唱会上迸发出才华的火花,在艺术的创造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准,一跃而成为知名的赞哈。”[5]35
再次,章哈在演述过程中需要与受众互动,要能根据现场的突发情况即兴创编。在诸多仪式现场中,章哈一般是在舒适的屋内坐唱,院子设有许多宴席,宾客一边吃饭喝酒一边听歌,听到喜欢的地方就会走进屋来将50 元或100 元红包送入章哈握着话筒的手中。这是章哈获得额外赏金的传统途径,也是馈赠者彰显身份和经济能力的方式。旁边有专人将馈赠者的名字、金钱数额等信息简单记在一张纸条上然后送到章哈手中。章哈收到这些纸条后会不慌不乱继续他的演述,根据所得到的信息,他(她)在心中默默组织腹稿,然后找一个合适的空档唱出这段赞美歌以此为谢。这种赞歌内容主要是夸奖对方样貌出众、心地善良、出手阔绰,然后祝福其工作顺利、升官发财、出入平安云云。章哈也可以主动去逗引听众,夸某男子人帅钱又多,夸某女子美貌善良等。听到这些夸奖的人获得了心理满足,在众人的欢呼中自然就会送来一些奖励。除了和受众互动,章哈之间也互相夸赞以此活跃气氛。
“口头诗学的核心命题是‘表演中的创作(composition-in-performance)’,这是从活态的口头传统诗歌的现实中获得的。对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的共时性分析表明,创作和表演是同一过程中处于不同程度变化的两个方面。”[2]对傣族章哈来说,他们演述的那一刻就是创作本身,演述者即创作者,他们的即兴创作牢牢植根于对传统的把握,包括古老的神话故事、民族历史和传说以及民族传统节日的相关叙事。
三、章哈的兴衰趋势
章哈在历史上对傣族诗歌的发展、繁荣和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进入21 世纪以后,在“非遗”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章哈赢来了繁荣发展的历史机遇,当然也面临着一些内在的困境和挑战。
(一)我国傣族章哈的发展
章哈的人数变化可以反映章哈文化的兴衰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次调查统计中,“西双版纳州拥有半专业性的章哈1300 多人,其中被封建领主封为‘章哈勐’的有60 多人”。[7]170特殊十年中缺少具体的统计数据。自改革开放后,传统习俗得以恢复。20 世纪80 年代张公瑾先生在西双版纳长年考察傣族文化,他提到:“现在,在西双版纳有一千二百多赞哈。”[6]39可见当时的章哈人数基本恢复了。此后是社会巨变和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20 年,当时的云南省文化厅曾经开展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普查”,西双版纳州文化馆从1999 年起到2003 年对全州的章哈人数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西双版纳现共有登记在册的章哈280 人,其中,男性148 人,女性132 人。地区分布为:景洪市169 人,勐海县83 人,勐腊县 28 人;60 岁以上的 25 人,50~59 岁的 35 人,40~49 岁的 67 人,30~39 岁的 112 人,19~29岁的25 人,10~19 岁的13 人,10 岁以下的3 人。以上280 名章哈中,识傣文的有229 人。能进行创作演唱的有124 人。[3]14960 岁以上的章哈占比已达9%,可以说章哈人群正趋向“老龄化”。①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之后迎来了“非遗”文化保护运动时期,2001—2003 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起步阶段,2004—2006 年是启蒙阶段,2007—2011 年是推动和加速阶段,2012—2015 年是“后申遗时代”的起步年,又属于非遗保护的稳定期和反思期,申遗热潮逐渐淡去。[8]“傣族章哈”在2006 年被录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名录(编号V-44),不能不说这是章哈复兴的一个历史机遇。
傣泐村民深爱章哈文化,客观上来说章哈有着扎实的群众基础。2011 年笔者在西双版纳勐龙镇考察时,走在村寨巷道里见到一位正在晒太阳的老人,聊起来才发现他竟是一位老章哈。于是邀请他到我暂住的朋友家里进一步访谈,问他会唱哪些曲目,他没法回答具体篇名,却直接开口唱了一段,内容有“火烧天地”“布桑该雅桑该造人”等叙事。这次走在路上就能遇到章哈的经历让笔者感叹章哈文化的生命力。通过访谈村民得知,大家普遍乐观认为现在的章哈人数在不断增多,只不过优秀的章哈人数比较少。如今,章哈协会②1963 年,经云南省委宣传部批准,西双版纳州成立了“章哈协会”,这使得广大章哈歌手有了自己的组织。见杨昌一:《云南曲艺概论》,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171 页。每隔几年不定期组织培训和赛唱活动,通常在文化馆举办。参加培训的人可以领到一些材料,例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召树屯与喃木诺娜》③根据贝叶经《召树屯》改编,改编者岩帕,西双版纳州文化馆,2010 年8 月8 日。,有西双版纳州文化馆编的《章哈学习演唱传统唱词》。培训会规范章哈们的演唱内容和秩序等。此外还有政府牵头由文化馆承办的一些赛唱活动。例如,2005 年12 月16 日景洪市文化馆在勐罕镇曼法村委会曼岭村举办的“西双版纳州勐巴拉娜西章哈演唱会”。[9]305参加的章哈来自景洪、勐海、勐腊各村寨,演唱的内容丰富多彩,观众达1 万余人次。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文化馆的这些培训、赛唱会无疑是促进章哈发展的有效举措。
傣族章哈的兴衰背后是国家经济繁荣的大背景。章哈是一份职业,其兴衰反映了市场的需求。过去许多章哈通过唱歌养活家庭,现在的章哈更是赚到了足够的钱,住上了新式小楼房,出行坐的是小轿车。现如今章哈协会规定演唱一场的报酬不能超过3000 元,但是他们在演唱过程中可以收下听众的馈赠(赏金),这也是很多原本歇唱的女章哈纷纷出山重启唱歌事业的原因之一。
章哈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危机和挑战,其中两个是传承囧境和受众缺失。“章哈勐”康朗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几乎每村每寨都有章哈,人们最大的文化娱乐就是听章哈唱歌。如今章哈听众多为老年人,年轻人不想听、听不懂,也不愿学章哈。据他了解的情况,目前勐腊的章哈人数已经不多,因为勐腊的章哈学出来后没有多少演唱市场。勐腊的村民上新房时不一定请章哈来演唱,有的用光碟播放章哈歌曲便可。55 岁的岩温晃表示他希望有人跟他学章哈,传统上这个年纪的章哈可以收徒了,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对章哈文化并不感兴趣。岩坎溜生于1985 年,家里的新楼是在2008 年盖起来的,当年上新房也邀请了两个章哈和一个笛师来庆祝。他虽然学过傣文,而那些章哈演唱的大部分内容他仍然听不懂。绝大部分像他这样的“80 后”父母都将自己的孩子送入幼儿园,然后接受国家九年义务教育,不再像老一辈那样将男童送去佛寺里当小和尚了。
(二)东南亚Khap Lue 的发展
现在居住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区域的泐人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从中国云南西双版纳迁徙过去的,如今他们成为跨境民族。他们自称为“傣”,老挝、泰国官方将他们识别为“泰泐”(Tai Lue)或者泐人。他们将傣泐方言、地名、节日、饮食和服饰等一整套文化系统都带到了新家园,作为傣泐文化符号的章哈自然也传到当地。笔者2012—2016 年之间多次到泰国北部、老挝北部考察,每当问及哪里有“章哈”(Chang Khap),回答者会自动改成“哈泐”(Khap Lue)一词。可见在他们的认识中,“章哈”是专指泐人的歌手。
章哈文化的根部在西双版纳,东南亚各地的Khap Lue 则属于末枝,章哈是“族群内部的纵向文化传承和异地共生现象”。[10]然而,在不同的国家主流文化土壤中生存,章哈出现了不同的历史命运。章哈文化在我国受到了重视和保护,迎来了再次发展和繁荣的历史机遇。相反,在泰国、老挝的Khap Lue 人数逐年减少,最重要的是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功能逐渐消失。
泰北的清莱、清迈、南奔、南邦、楠、帕、帕腰都有许多傣泐村,仍然保存“哈泐”文化的则以清莱、清迈、难、帕腰四府为主。但是,在这些地方的“哈泐”只作为舞台表演或自娱自乐的一种音乐形式存在,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失去了西双版纳那样的演述语境。“如今,泰国北部Khap Lue 已失去了它本应该依附的表演语境,导致歌唱者与伴奏者的表演能力不断下滑,且大多歌手只能演唱‘情歌’‘故事’等通俗易懂的内容,从而使Khap Lue 所涉及的佛教仪式等相关传统内容也逐渐消失。”[10]
老挝的傣泐主要生活在北部的丰沙里、琅南塔、乌多姆赛、沙耶武里和琅勃拉邦等省,人口在11.9万人。[11]69笔者曾经与同事到达琅南塔省的孟新县考察,那里有曼那坎等许多傣泐村寨。通过访谈村民得知,在一两百年来他们依次从西双版纳迁徙下来到达这里。为了考察这里的章哈传统,笔者曾经到塔包村( Ban Thapao) 和端摆村( Ban Donpoy)访谈了一位章哈及其笛师,他们介绍了自己的习得过程、演述曲目等情况。①关于这两位老挝章哈的访谈,详见屈永仙:《傣/泰族群的史诗传承人:从布摩到章哈的发展》,《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 第 1 期 。他们说自己是章哈,但是与西双版纳的章哈不太一样,不能像他们那样演述整部史诗或长篇叙事诗了,本地的章哈人数也在急剧减少。在今天的老挝社会中,傣泐年轻人更倾向于流行歌曲和其他多媒体作品,对本民族的传统曲艺缺乏关注。
章哈演述作为一种口头艺术,其生命力存在于仪式演述之中,只有通过传播被大众接受和欣赏才会传承下去。总体而言,Khap Lue 的传承机制正趋向衰退,加上没有官方的经济支持和制度性的保护——尽管有一些民间机构会组织一些活动并制定计划致力保护和传承章哈文化,但是Khap Lue 的存续不容乐观。
(三)章哈的发展困境和原因
对于傣族章哈来说,如何传承是最重要的问题。后继无人,主要因为这几个原因:一是章哈演唱的内容虽然丰富但曲调显得单一,对年轻一代来说缺少吸引力。这原本是章哈这种曲艺形式的本性,其曲调虽然简单但却经典,作为一种口头叙事艺术,目的是将故事尽可能全面传达到受众耳中。相比较来说,德宏有40 多种曲调,可谓是丰富多彩,花样繁多,根据不同的仪式场合和仪式目的就要用不同的曲调来表达。花样太多反而缺少其经典性,难以专一地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至今德宏傣族民间歌手“摩哈”也没有完成其职业化。
二是因为章哈曲调演唱的内容与现代生活脱节。绝大部分年轻人包括一些中年人听不懂,章哈听众以老年人为主。加上现代化多媒体作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更少人去关注深奥难懂的传统民族曲艺。60 岁以上的老章哈最能体会这个变化过程,他们在访谈中都说40 岁以下的傣族年轻人基本听不懂章哈演唱了,50 岁以上的勉强可以听懂。这些老章哈纷纷表示,他们内心担忧章哈传统后继无人。
三是主流文化的传媒思想已深入广大的普通傣族村寨。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日益频繁,人们会对本民族传统文化逐渐淡漠,傣族章哈便是案例之一。“傣泐人的文化认同已经由过去封闭社会环境中的文化认同转型为一种开放社会中的形态,即融合了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地方文化认同、国家文化认同,以及对外文化的认同等多种因素的认同形态。在这种认同形态中,传统文化认同面临着弱化。”[12]
四是章哈演唱往往受到场景、时间和体力的局限。章哈演唱远不如一般大众传媒那样随意,它植根于传统习俗,与仪式生活息息相关,这无疑会影响到它的发展。章哈每年只能在开门节后密集演唱,而且每次演述都是通宵达旦,如此势必损耗身体。此外,听众群体在老龄化,演唱内容缺少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演述时间和场域受限制,以上种种都是章哈文化发展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四、余 论
综上所述,章哈是傣族的史诗歌手,他们能够通宵达旦演述史诗、长篇叙事诗,即使有文本,他们也必须延续传统进行脱稿口头演述。在传统的傣族社会,男性与女性有着不同的受教育机会和文化基础,因此男女章哈成长之路不尽相同。章哈的师承模式并非具有排他性的树状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网状结构。章哈的师承体现出一种务实性,章哈在一生中会拜多个师傅也会传承给许多徒弟。作为史诗歌手,章哈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村落仪式常需演述的传统曲目,还要具备即兴创作的能力。
章哈们基本都知道这则故事:古时候僧人都在佛寺里念诵佛经,要求人们都去听经。同时,佛寺外面有一个章哈在唱歌,所有人都跑去听歌而不到佛寺里听经。于是佛爷说“好吧,傣族的章哈还是不能丢掉,可以传下去,但是不能在佛教安居期内唱。”最终傣族的章哈才得以代代传承下来了。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了佛教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反映了书面传统挤占口头传统空间的历史过程。随着佛教的扎根,佛经典籍具有不可置疑的神圣地位,诵经是在传授佛祖的智慧;相对来说章哈的歌唱则是一种娱乐消遣,不能与文本化的经典并肩。最终傣族的史诗歌手章哈被隔绝在庙堂之外,被限定了演唱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并未从此销声匿迹,他们一直活跃在与书面佛经为权威的傣族社会中,他们依然是傣族民间文化生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章哈作为口头曲艺,必须依赖于演述语境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在科技全球化的当今社会中,傣族地区早与外界全方位联通,社区变得更加开放,章哈受到本国主流文化,乃至全世界其他文化的冲击。外部的“非遗”文化运动使它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没有源自内部的改革,我国傣族章哈仍然面临着与东南亚Khap Lue 消亡的同样命运。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傣族章哈文化将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