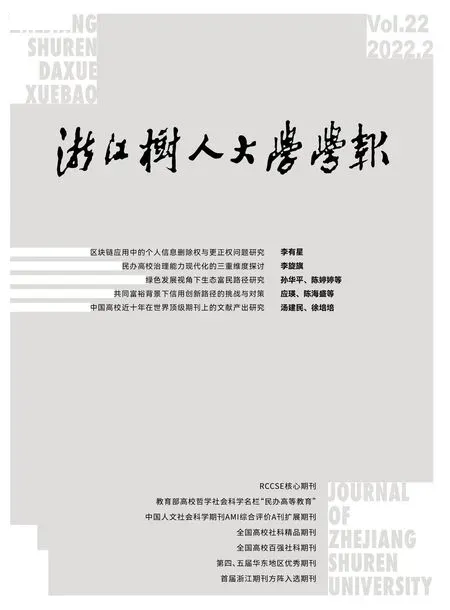绿色发展视角下生态富民路径研究
2022-11-23孙华平陈婷婷胡诗宇
孙华平 陈婷婷 胡诗宇
(1.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2.嘉兴学院 中国共同富裕研究院,浙江 嘉兴314001)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出口面临外需萎缩的窘境,2018年美国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战更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伴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社会经济系统复苏迫在眉睫,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从国内情况看,高储蓄、高投资的过度积累所导致的要素边际报酬加速递减,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减缓现象。同时,消费端不同维度的收入差距过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共同富裕的实现。从消费函数角度看,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阶层趋于减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有利于产业扩张及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由于人类经济活动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已成为全人类共识,开展绿色研发是发展低碳经济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通过设计良好的环境规制可以向企业施加一定的外部压力,进而克服组织惰性,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形成互补关系,并有效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生态富民可以实现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协同,也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转型。
共同富裕是指在消除贫困、缩小两极分化的前提下,由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维度发展水平的普遍提升(1)黄奇帆、厉以宁、刘世锦:《共同富裕》,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76-78页。。生态福利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生态福利的持续提升。亚当·斯密提出的普遍富裕是建立在分工导致的极大物质财富条件和政府实施的公平正义制度保证基础之上的,市场规模和绿色制度决定绿色分工水平,绿色分工水平又决定需求端的共同富裕程度(2)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4页。。古典经济学家配第认为,劳动创造经济财富的过程受到自然资源条件的约束(3)威廉·配第著,薛东阳译:《赋税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0页。。马尔萨斯分析了人口与土地、粮食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资源稀缺绝对论”(4)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著,郭大力译:《人口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59页。,并认为财富增长取决于要素间比例的协调性,有必要把生产能力与分配方式相结合来保证经济财富的持续增长。李嘉图以阶层利益对立为出发点,提出了“资源稀缺相对论”,并强调从调整分配关系层面研究经济“包容性普惠制”发展的制度动力基础(5)大卫·李嘉图著,郭大力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地阐明了生态自然思想,提出了消除生态环境危机的制度设计(6)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翻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9页。。美国生态经济学家Boulding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和地球环境容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模型(7)Boulding K E, Jarrett H, 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3-14.。随着“两山”理论的提出,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做大生态产业、推进绿色发展不仅是推进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革新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生态富民的重要路径。
一、 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
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是当前及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绿色发展内嵌于高质量发展之中,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推进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
(一)共同富裕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收入均等化会通过帕累托改进增加整个社会的集体福利(8)庇古著,金镝译:《福利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因此,征收累进税或转移财富等财政手段已成为各国促进共同富裕的普遍做法。劳动经济学理论认为,两极分化的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中等收入群体占最大多数比例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9)赫尔曼·E.戴利著,诸大建译:《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第42-45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率先在农村地区推进改革,激发农民创业活力,通过“农民赋权+市场化模式+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成功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在不损失城市系统福利的情况下顺利推进了农村系统改革,极大地增加了全社会的经济福利。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家又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协同的收入分配体系,有效激发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潜力与创业活力,不但提升了全社会的就业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全国社会福利。因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激发经济活力及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机制保障。
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首次提出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大方面的平衡问题,探究了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环境污染矛盾主体进行博弈的现象,并得出它们之间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关系的结论(10)蕾切尔·卡森著,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20世纪60年代,Boulding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学”概念,所提出的“生态经济协调理论”也开启了人类平衡生态与发展的大门(11)Boulding K E, Towards a New Economic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2, pp.12-13.。戴利分析了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并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动态过程,它既关注本代人的发展,又关注后代人的发展与福利问题(12)赫尔曼·E.戴利著,诸大建译:《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第42-45页。。他还提出目前生态经济学面临的三大问题是可持续规模、公平分配和资源高效配置,并且拓展了现有关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及理论框架。国内生态经济学理论起步较晚,不同学者的研究角度也很不一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生态经济学所具有的理论基础日益成熟且逐步深化。总体上看,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一种综合性多维式方法,强调用系统观来看待环境问题。
(二)共同富裕需要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最早系联合国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提出,强调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进步与增长方式,考虑世界各区域共同的环境责任和世代发展与资源配置均衡。2011年经合组织(OECD)发表的《走向绿色增长:进程监测》报告认为,绿色增长是指“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持自然资本的可持续服务”(13)OECD, Towards Green Growth: Monitoring Progress, 2011, pp.1-2.。广义的绿色发展包括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及可持续发展,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以生态失衡、环境破坏、资源耗竭为代价的“黑色增长”模式的一种革新。绿色发展有浅绿色发展及深绿色发展之分(14)赫尔曼·E.戴利著,诸大建译:《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浅绿色发展主要关注解决局部环境问题、强调对生产系统进行污染末端治理、认为环境与经济非此即彼、主张技术决定论;而深绿色发展坚持系统发展理念,强调源头控制及过程管理,主张环境与经济对立统一、生态文明制度决定增长模式(15)沈满洪:《绿色发展的中国经验及未来展望》,《治理研究》2020年第4期,第20-26页。。
Pearce等(1989)认为,绿色经济发展不会因为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破坏、资源耗竭和社会分裂,而是一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模式(16)Pearce D W, Markandya A, Barbier E,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Earthscan, 1989, pp.3-14.。Kaivo-Oja等(2001)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维度涵盖经济、生态和社会文化等方面(17)Kaivo-Oja J, Luukkanen J, Malaska P, Sustainability Evaluation Frameworks and Alternative Analytical Scenarios of National Economies,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001, No.2, pp.193-215.。Glemarec等(2012)认为,绿色发展不但关注增长与发展,还强调环境可持续性(18)Glemarec Y, Oliveira J A P D, The Role of the Visible Hand of Public Institutions in Creat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Public Administration & Development, 2012, No.3, pp.200-214.。Dinda(2014)提出,绿色增长追求经济增长、污染减少、废弃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的同步实现,且能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生物多样性(19)Dinda 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Green Grow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 Economics, 2014, No.2, pp.177-189.。Bouma等(2015)提出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模式,认为其要义在于平衡经济增长、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创新,特别重视长期与短期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环境服务价值之间的动态辩证关系(20)Bouma J, Berkhout 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PBL Publication, 2015, pp.18-19.。
杨雪星(2014)辨析了绿色经济与包容性发展的逻辑关系,提出包容性绿色经济增长的特征是效率、包容与可持续三方面的平衡,强调通过绿色技术和绿色投资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高价值的服务产业(21)杨雪星:《包容性绿色经济增长指数构建与实证研究——基于G20国家数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42-48页。。易信等(2018)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主要为潜在增长率降低所致,而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则是由于各种体制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长动力衰减,往往表现为经济结构的利益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22)易信、郭春丽:《未来30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变化趋势及2049年发展水平预测》,《经济学家》2018年第2期,第36-45页。。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及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资源配置会更加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也会逐步提升。孙华平(2021)提出,通过生态富民加快经济社会全面实现绿色转型,在此过程中,通过市场机制力促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是极为关键的抓手和要点(23)孙华平:《以生态富民力促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2021-10-21,https://m.gmw.cn/baijia/2021-10/21/35248210.html。。张学升等(2022)发现,财政分权对绿色发展产生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影响,并会通过外溢作用促进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而税收竞争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发挥财政分权对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24)张学升、张行:《财政分权、税收竞争与绿色发展》,《统计与决策》2022年第5期,第126-131页。。
上述对于绿色增长的阐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将绿色增长作为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绿色增长产生在以绿色产品、绿色企业和绿色产业为主导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即将绿色增长理解为经济体达到较高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结果。第二类理解则将绿色增长看作经济发展的手段,认为经济增长绿色化的核心要义是将环境因素等自然条件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性因素,而非传统经济理论所认为的制约性因素。总之,实现经济社会财富增长,应特别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利益关系的动态协调。为此,要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培育绿色生态文化、强化生态管理并促进绿色公正转型。从国际视角看,在双循环战略推进和实施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绿色低碳技术的国际合作,力促新能源产业跃迁式创新发展,同时有必要以国际绿色环境标准协同为抓手,加快构建与完善国际环境治理体系。
(三)生态福利与共同富裕是共同体
从生态学角度看,根据生态需求递增规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者生态需求呈递增趋势(25)沈满洪:《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共同富裕观》,《治理研究》2021年第5期,第5-13页。。因此,生态资本会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增加,在收入水平相同的情况下,生态环境质量会影响个人福利,生态福利也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从经济学角度看,生态资本的价值增值需要持续不断的运营:一是如何实现经济生态化,即经济增长不以生态破坏为代价;二是如何实现生态经济化,即将生态环境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和资本,并不断产生新的生态资本。经济生态化,要求使传统生产系统的污染负外部性内部化,纠正了生产者和消费者面临的生态福利扭曲;而生态经济化,则扭转了“生态资源无偿使用”“生态产品低价无市”等资源配置扭曲问题,在提升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同时,通过生态产品交易实现了城乡之间的财富转移,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26)周小亮:《包容性绿色发展:理论阐释与制度支撑体系》,《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第41-54页。。实现生态富民模式的关键在于,通过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找到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进而挖掘和发挥生态比较优势、形成生态增收与持续富民的良性循环(27)胡咏君、谷树忠:《安吉乡村生态富民的模式识别及演化特征》,《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年第8期,第1-8页。。
综合而言,生态福利属于共同富裕的天然内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种必然的诉求。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注重开发生态资产,推进生态资产运营,不断提升国民的生态福利。对于具有较好生态资源禀赋的区域,应鼓励开发生态旅游产品,不断加大营销力度,积极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当然,任何区域生态资源的开发也有限度,不能一味注重经济效益,还要通过横向与纵向生态补偿,把各区域发展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起来,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加国民生态福利,进而促进生态富民与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的互动与协同
在理论上,比较有名的关于环境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有“增长极限说”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假说(28)Stern D I, Progress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No.2, pp.173-196.。有研究者认为,环境绿色与经济增长难以兼而得之,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舍弃经济增长;反之,要想促进经济发展就不得不牺牲生态环境;也有研究者认为,绿色发展是否会带来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富裕并无定论;还有研究者持乐观的观点,认为绿色发展方式有助于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
(一)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富裕
如果EKC假说具有普适性,那么从长期来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环境质量改善的途径。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把“自然要素”作为生产函数中的变量,提出劳动、资本及自然资源是任何社会生产都必须具备的三种投入要素(29)转引自蒋自强、张旭昆、袁亚春等:《经济思想通史》(第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280页。。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学派主张各国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标准化制度,政府通过采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及技术创新补贴政策等绿色激励政策扶持绿色企业的成长,加速黑色经济的退出与淘汰,约束黑色消费,提高绿色发展的递增报酬(30)胡鞍钢:《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1页。。根据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以绿色制度与环境规制推动绿色分工演进和结构跃迁(包括绿色部门和绿色产业等结构演进),那么政府主导的分工演进会减少社会总交易成本,扩大绿色产品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分工演进向绿色方向深化,从而实现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张和交易效率的动态提升,通过绿色制度创新促使绿色产品的市场结构进一步专业化,不断跳转到一个更高的分工水平,实现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31)Sun H P, Edziah B K, Sun C H, et al., Institutional Quality, Green Innova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 Energy Policy, 2019, No.12, 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9.111002.。相反,污染产品的市场结构将会在与绿色产品的博弈中逐渐萎缩和消亡。向国成等(2018)提出,在政府、市场、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之间内生形成了一个“绿色分工演进—供给侧和需求侧—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程度—市场规模—绿色分工演进”的正循环链条(32)向国成、邝劲松、邝嫦娥:《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71-76页。。在这个理论框架中,绿色分工演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源泉。刘伟等(2019)认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挑战,在双循环战略下实现经济现代化并达到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33)刘伟、范欣:《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增长跨越》,《管理世界》2019年第1期,第13-23页。。刘志彪等(2020)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仅表现为产品数量的增加,还体现为产品质量水平的跃迁与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同时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及资源环境视角下的公正转型也是重要的考察维度(34)刘志彪、凌永辉:《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管理世界》2020年第7期,第15-28页。。沈满洪(2020)认为,生态要素参与财富分配,可以提高乡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或财富,基于生态要素使用的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的差异性,开展区域间生态产权交易,推进生态资本运营,必然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从而推进达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35)沈满洪:《绿色发展的中国经验及未来展望》,《治理研究》2020年第4期,第20-26页。。
(二)绿色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抑制共同富裕
在进入人均收入较高的阶段之后,随着环境治理投资的逐步增加,环境质量状况会逐渐改善,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达到环境拐点时所处的经济水平、耗时长度与污染产业区位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而根据EKC假说,达到环境拐点之前经济增长是与污染增加同步,因而此时推进绿色发展必然会减缓经济增速。依据新古典边际分析,绿色发展能够提升社会整体福利,但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效应。Meadows等(1972)认为,经济不可能无限扩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制于自然资源的约束;为实现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均衡,人类社会只有实行稳态经济发展模式(36)Meadows D H, Randers J, Meadows D L,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The MIT Press, 1972, pp.22-23.。陆旸(2012)以美国为例,发现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高度正相关,即增长持续性与环境质量难以同时兼容(37)陆旸:《从开放宏观的视角看环境污染问题:一个综述》,《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第146-158页。。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技术水平与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企业污染治理投入减少,会促使生产经营成本降低并推动企业利润提升,但同时环境污染的外部不经济会促使政府采取环境规制等绿色发展政策对该负效应加以抵消(38)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No.4, pp.1-44.。此外,绿色发展往往依赖于绿色投资,而绿色投资的回收期一般是很长的,这就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不足。而政府的绿色公共研发支出往往会挤出私营企业的创新投资,并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尚不完善,绿色技术研发所需要的投资往往具有动力不足的特征,这也导致了绿色经济发展慢,一定意义上也是多数区域还没迈过环境拐点的重要原因。
(三)绿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不确定论
周琛影等(2021)认为,绿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尚不确定,这是因为其综合效应高度依赖于政府与市场的互动(39)周琛影、田发、周腾:《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3页,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10513.1530.002.html。。何爱平等(2019)认为,从宏观上看,着眼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的环境规制一般是趋于严格和细致化,这会引致微观企业的绿色投资,并改变企业的环境行为(40)何爱平、安梦天:《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3期,第21-30页。。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不但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还会改变企业的预期利润,进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或削减工人工资,同时治理污染的投入也会对产出造成挤压,因此短期内会给企业利润及员工就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波特假说也指出,适宜的环境规制也能激励企业开展绿色研发活动,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并创造“绿色”就业。Pizer等(2002)认为,一方面,环境规制会推动环境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就业增加,政府出台的环境规制也提高了企业制度成本,改变了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弹性,因“需求效应”导致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投入要素下降;另一方面,资本密集型环境规制会鼓励企业生产绿色自动化和低碳化设备投资,资本替代劳动力引发“要素替换效应”,也对就业产生负面效应(41)Pizer W A, Shih J S, Morgenstern R D, Jobs Versus the Environment: An Industry-Leve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2, No.3, pp.412-436.。
然而有些产业类别属于劳动密集型绿色生产,比如乡村旅游,相比资本密集型生产反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这类产业的发展会提高对劳动力投入要素的需求,因此属于绿色就业增加型发展。绿色发展是否促进整体就业,目前学界对共同富裕的净效应并无定论,不能一概而论。政府出台的环境规制是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就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两者的关系随着不同产业的性质而发生逆转。同时,现实中空间极化是市场发展的一个规律,经济发展往往表现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规律。因此,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也要考虑产业集聚效应的作用机制。当前我国大力推行的城市群经济、新型城镇化、“美丽中国”及乡村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绿色发展模式及其实施政策是不谋而合的。
综上所述,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通常需要采取各种组合性的政策手段与治理模式。传统扩张型增长模式往往会带来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个阶段符合EKC前半部分的发展趋势,即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加重。但实质上环境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辩证统一的复杂关系,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在动态演化中可以有机融合起来。首先,作为新阶段的绿色发展是基于生态承载力和资源环境保护与建设为核心的创新型发展模式,强调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具备系统协调性和动态可持续性等特征,又要维持生态环境良性运转,从而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和社会共同富裕。绿色发展不但能推动分工结构的深化,还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保护和共同富裕三者的和谐共赢。其次,绿色发展虽然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但通常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效应,主要是因为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与消费者支出。经济社会建设会受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制约,对环境的保护也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约束,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即到达EKC拐点之后,环境污染的程度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在新时代,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两者无法分离,相辅相成。只有正确认识并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使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实现生态富民。
三、我国实现生态富民的路径选择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推进“四化”建设:产业组织市场化、收入分配合理化、社会保障普及化和生态环境价值化。“四化”建设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协同与支撑,在实践中缺一不可。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共同富裕的实现事关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需要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产业组织市场化是效率的保障,而收入分配合理化与社会保障普及化关系到每个人福利的提升。生态环境价值化则是当人们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自然而然的需求。没有高质量的环境作为基础,人民的生活不可能非常幸福。常用的幸福指数不仅涵盖经济福利,还包括精神福利、政治福利、文化福利以及生态价值福利。幸福指数的调查统计表明,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幸福指数不一定就高,但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地区幸福指数则基本上不高;人均收入和生态福利均很高的区域往往幸福指数较高(42)沈满洪:《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共同富裕观》,《治理研究》2021年第5期,第5-13页。。一些地区幸福指数之所以高,就是因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共同改善促进了综合效用水平上升。如果只是生态改善,但生态产品价值未成功转化;又或只有经济增长,但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经济增长的福利增加无法抵消环境质量下降的福利损失,则共同富裕都将无法实现。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大力发展清洁低碳能源并逐步替代传统能源、努力开发碳捕捉及碳汇产业,将成为区域低碳转型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在此过程中,碳汇产业的崛起与兴盛离不开具有良好生态禀赋的区域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而生态富民可以也应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生态富民这一新概念是在新时代中国国情下结合经济最新发展态势提出的。目前,国外尚未明确提出与之对应的概念。沈满洪(2016)将生态富民化看作一个渐进的转型过程,并强调环境容量的服务价值、生态保护的合理补偿及生态投资的资本收益等要体现在实现生态富民化的过程中(43)沈满洪:《生态经济学》,中国环境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很早就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特别是在提出“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这一重要论述后,“生态富民”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深入,生态富民、脱贫攻坚及共同富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衍生出了多种产业振兴与农民增收模式(44)黄祖辉、叶海键、胡伟斌:《推进共同富裕:重点、难题与破解》,《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6期,第2-11页。。关于实现生态富民的路径选择,唐任伍等(2022)认为,各级政府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尤其是需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及有爱社会的协同努力(45)唐任伍、李楚翘:《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基于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轮驱动”的考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49-58页。。各区域应充分利用自身具备的资源优势,积极主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利用其地理上独特的气候环境资源和区位优势,激发企业家资源创新活力,努力培育绿色金融家,通过创新创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产业发展是富民的关键,产业组织市场化是实现生态富民的核心机制。要想真正富民必须解放思想,转变发展观念,将生态文明建设提上日程。将生态与富民结合起来辩证思考,最主要的是用产业组织市场化激发生态资源价值,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主体作用,积极探索区域生态富民模式的适宜结构与独特模式。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实施绿色生态发展、产业振兴与创新驱动战略,需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与生态优势,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经济发达国家转型也经历了从“先污染、再治理”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跃迁过程。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可以为二氧化碳排放(如碳储存和再利用)提供可能的末端处理手段,还会带来新一轮产业变革并拉动绿色消费,持续提升能源效率,促进绿色就业的扩张。比如,日本的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跃迁式发展(46)Sun H P, Geng Y, Hu L X, et al., Measuring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Patents: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 Energy, 2018, No.12, pp.685-693.。目前,很多欧洲发达国家已经给出了未来燃油车退出的时间表。因此,在我国双碳目标的约束下,应鼓励企业加快绿色技术研发,积极推动全球绿色技术的合作,加快各经济体的绿色技术转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另外,要推动政府出台奖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农产品的生产与标准化认证,促进区域绿色产业规模化发展。
(二)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生态富民的实现离不开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金融的核心目的是利用金融工具来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金融是经济的血液,绿色生产方式的推行和绿色消费模式的推广都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持。尤其是应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绿色贷款奖补、贴息、担保等激励政策,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向实体企业投放绿色贷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因为,在现阶段生态资源价格体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绿色发展类项目收益率相对较低,项目回收期长、风险高,使得注重流动性、安全性的传统信贷不愿接手此类项目。而环保类绿色产业要想获取资金,离不开具有政策性特征的绿色信贷的强力支持。以美国为例,为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绿色金融法律体系,如1980 年的《环境补偿法案》提出银行在环境保护方面需承担连带责任;2007 年的《美国能源独立与安全法》规定了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诸多举措。另外,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包括持续不断的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开发等。尤为重要的是,开拓创新的绿色金融家精神的形成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绿色金融(47)Muganyi T, Yan L N, Sun H P, Green Finance, Fintec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technology, 2021, No.3, DOI:10.1016/j.ese.2021.100107.。比如,江苏盐城滩涂广阔,其沿海具有丰富的风、光资源,因此大力发展绿色新能源产业具有较好的资源禀赋。具备战略眼光和环保情怀的央企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在盐城东台投资30亿元建设太阳能电站,并按照集约、集中、集聚的发展理念,形成“上有风电利用、中有光伏发电、下有水产养殖”的“风光渔”三位一体开发模式,实现了沿海滩涂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最大化。后续带动了神华、中电投、中海油、华电、国网鲁能等一批央企投资落户,目前已建成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滩涂风光电产业基地,形成了“风光渔”互补、生态科普旅游、循环经济与高效养殖四大特色示范区。
(三)强化生态系统管理
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往往伴随着生态困境的逐步消除。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在高速经济增长“量”的扩张之后,及时转向“质”的提高。在“质”的提高过程中,必须消除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生态“赤字”。目前,我国多数区域在生态富民实践中遇到三大问题:发展理念跟不上生态发展要求、生态发展服务体系与结构不完善、农民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另外,城市生态功能退化以及生态建设机制不够完善,也是导致生态富民进程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城市生态环境脆性进一步加大,自我修复能力较为有限,生态保护建设投入明显滞后。因此,推进生态环境价值化、强化生态资源管理是实现生态富民的重要前提。自然资源与生态资产产权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开展生态资产运营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另外,绿色金融家的形成与不断涌现也有赖于健全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各区域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呈现出金融化、平台化和信息化趋势(48)张伟、张海峰:《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的三大趋势》,《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9日,第11版。。深化自然资源产权改革、明晰自然资源产权有助于环境保护的边际收益提升,从而激发生产者采取更为清洁和低碳的方式进行生产,进而降低环境保护增量的边际成本(49)陈建成:《推进绿色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国林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79-82页。。
(四)促进绿色公正转型
目前,生态富民要突破发展观困境、制度设计困境及价值观困境,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尤其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因为中西部地区居于我国很多河流的上游。收入分配合理化和社会保障普及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与保障,对于实现经济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动态平衡具有压舱石的作用。我国不同区域和城乡差异显著,从绿色转型公平正义的角度看,需要对中西部欠发达区域的低收入群体进行横向与纵向的生态补偿。但是,不少中西部区域在农村推进生态富民建设中,面临着农民主体参与度低、缺乏绿色先进理念等问题,而且对自然资源缺乏有效利用。因此,打造生态型政府是实践“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关键,但部分政府还未从经济增长型观念转向保护生态型观念,仍迷失在传统扶贫的老路中,需要将生态富民原则从社会、政府到民众层层渗透。从区域角度而言,地区越偏远就越贫穷,进而更加需要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优势摆脱贫穷,若在这些地区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生存环境必将遭到破坏。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将生态经济和富民思想结合起来这一模式,将会更适合社会发展,利用经济的生态补偿力争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并在产业发展中使得生态资产价值持续增值。另外,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环境整治还是美丽乡村建设的薄弱点,因此乡村生态富民模式应注重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持续构建区域生态环境优势,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主体作用,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及经营模式创新。生态富民应特别保障农民的增收能力,且使其增收具有内生动力,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生态资产增值的良性循环。
(五)培育绿色生态文化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趋势。浙江安吉绿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村的经济增长还保护了生态环境,并且实现了经济和生态互融共生,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长远的发展利益。宁波湾底村在实现农村工业化之后积极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并且因地制宜,利用地处都市近郊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通过旅游规划和资源整合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已建成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浙江农家乐特色示范村等。同时,湾底村还积极谋划周边地区一起富裕,持续支持安徽、江西等欠发达地区发展果桑种植,带动了4 000多户农民一起致富。江苏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试点省份,全省资源利用效率高于全国均值,在探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经验。比如,江苏新沂把桃产业作为生态富民新路径,用“绿色银行”带动农民就业持续增收。江苏连云港依靠当地资源优势,借助技术创新和交通发展推行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创造出一些新的发展契机和特色,直接嵌入市生态富民的新路径中。这些成功的案例都离不开区域绿色生态文化的培育。同样地,绿色金融家的形成与涌现也往往依托于平等开放、鼓励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家精神形成的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国有金融机构具有绝对性垄断优势,它们往往缺乏竞争压力、创新意识比较淡薄。同时,全社会针对金融家价值的市场评估体系也尚未形成。因此,应大力发展金融家人才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的金融家遴选与激励约束机制,不断培育绿色金融家群体。
四、结 语
生态富民不仅是乡村振兴的良好策略,也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依托。通过对国内外共同富裕和绿色发展研究进行整理和归纳,发现国外学界关于生态富民发展这方面研究的文献不太充分,但学者们对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得很早,相关研究成果可以为本文研究生态富民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参考。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发展目标均迫切需要加快对生态富民及生态运营等方向的深入研究。我国对于生态富民的整体研究还较为分散,未形成一个综合的、成熟的体系,多数研究集中于生态富民对产业的影响、实践价值和路径等方面的讨论,缺乏一个全面实现生态富民的系统框架,相关案例研究还不充分,理论性和分析深度均亟待加强。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未来碳排放所余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当前我国“煤炭型”能源结构尚未发生根本转变,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亟须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加快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共富和谐社会。绿色发展是促进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如何实现取决于选择何种分工模式并达到某种分工水平。因此,应促进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能组织的协同互动,注重对生态资源丰富区域的市场化开发,加强生态平台运营与组织建设(50)高帆:《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与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机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5-17页。。从实践角度看,应鼓励各区域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依托生态资源优势,让青山绿水焕发市场生机。对于具备生态资本比较优势的区域,绿色金融的开展要有的放矢,瞄准重点项目,同时要建立绿色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大力发展具有区域禀赋特色的绿色产业,通过多措并举、绿色运营实现生态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