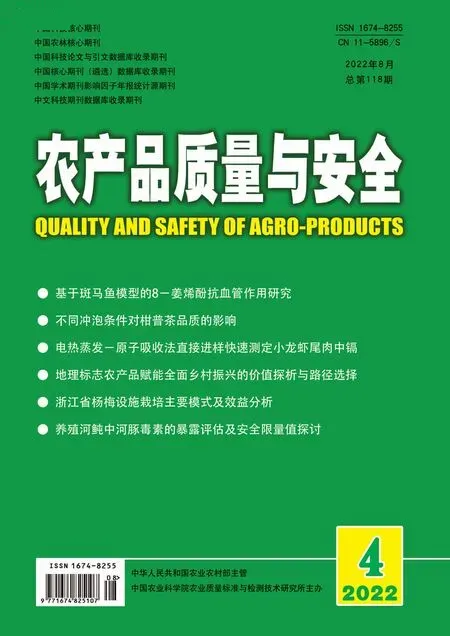基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限量转化谈我国农药残留限量的制定
2022-11-23朱光艳陈增龙贾春红刘艳萍
朱光艳 陈增龙 贾春红 刘艳萍 刘 帅
(1.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北京 100125;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3.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100097; 4.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640; 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术研究所, 广州 510640)
2021 年, 我国 GB 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发布实施, 规定了564 种农药的10 092 项最大残留限量[1]。 这些限量基本涵盖我国已批准使用的农药和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农产品, 不仅为我国人民的食品安全健康提供了相应的保证, 也超额完成了国务院批准的《加快完善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工作方案》 提出的1 万项农药残留标准目标, 标志着我国标准制定工作迈上了崭新的台阶[2]。 这1 万项限量不仅有利用我国残留试验数据制定的限量, 还包括禁限用农药的限量, 转化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我国香港规例的限量, 以及使用监测数据制定的再残留限量。 其中, 转化CAC 限量为我国限量标准提供了有益补充。
目前我国作为农药使用大国, 农药安全性评价数据尚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 经过40 余年残留试验数据的积累,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依然难以摆脱数量少、 未全面覆盖食品和农产品的瓶颈。 这给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造成了困难, 尤其是进口农产品和动物源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限量, 相对数量更加缺少。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 所有在我国销售的食品, 其农药残留量均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进口食品也在管理之列。 但由于缺少相关限量标准, 导致执法部门在抽检过程中无法有效判定, 难以保证我国消费者的膳食安全。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息, 2020 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2 468.3 亿美元, 同比增长8.0%。 其中, 出口 760.3 亿美元, 减少 3.2%; 进口 1 708.0亿美元, 增加 14.0%; 贸易逆差 947.7 亿美元, 增加32.9%[3]。 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已高于出口额, 对进口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进行监管已是我国政府亟需解决的民生问题。 针对我国自主生产的农产品尚无法满足每种农产品都制定限量, 对于进口农产品的限量制定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 转化CAC 已有的限量标准, 就成为解决困局的可行之路, 这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 协定》) 和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 协定》) 中 “当贸易中产生争端时, 优先使用国际标准” 的规定[4]。
2012 年我国开展CAC 限量转化工作, 按照第1 届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第6 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转化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建议》, 确定了相关转化原则, 一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 名单中的农药, 原则上直接采用CAC 标准; 二是我国禁限用的农药, 根据我国农药管理和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单独进行评估并制定限量; 三是我国已登记的农药, 可结合我国已取得的数据, 评估后进行转化; 当该农药在作物上尚未取得登记时, 可根据CAC 的相关评价资料和我国的监测数据, 评估后提交审议。 之后, 我国分批次开展了CAC 限量转化工作, 具体流程包括标准查询、 限量指标翻译、 作物分类修订或拆分、 市场监测、 文本撰写等, 其后文本草案则按照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一般程序经历公示、 送审、 报批等, 最后成为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经过近10 年的努力, 我国已转化了212 种农药在动植物源食品中的近4 000 个限量。 其中, 500 余项限量为动物源食品 (包括肉、 蛋、 奶、 动物内脏等) 中的限量, 其余均为植物源性食品中的限量; 87 种农药尚未在我国批准使用, 共涉及1 742 项限量[2]。CAC 限量转化有效解决了我国进口食品监管无标可判的问题, 占目前发布限量数量总和的39%,与其他来源的限量共同构筑起保护我国人民生命安全的长城。 本文从CAC 限量转化工作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角度入手, 总结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转化工作中的经验及做法, 并提出限量转化工作建议, 以期完善我国农药残留监管体系, 提高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科学性。
一、 转化工作方案的制定
CAC 限量转化的工作方案分为限量查询、 限量比较、 限量适用性监测和风险评估4 个部分。 在制定转化工作方案时, 查询到CAC 已制定了234种农药共计 3 338 项限量标准[5~7], 为了与我国农药登记使用及限量制定衔接, 针对不同情形对CAC 限量进行了分类。 按照农药分为3 种情形,即我国已登记, 但尚未制定限量的农药;我国已登记, 也已制定限量的农药;我国尚未登记的农药。按照食品来源则分为动物源食品和植物源食品, 其中植物源食品又包含食品和饲料两种。
由于农药登记情况复杂, 食品来源多种多样,在制定转化原则时, 采用分类制定, 以保证转化工作的顺利进行。 首先根据农药在我国登记使用、 限量制定情况和食品来源分类, 将CAC 限量与我国限量进行比较, 制定了不同转化工作原则, 主要包括5 个方面: 一是我国已经制定的或者我国已有数据的农药和作物组合, 不转化; 二是农药已在我国取得登记, 但在作物上尚未制定限量的, 进行转化; 三是农药尚未在我国登记, 或者已经撤销登记的, 其限量予以转化, 但不包括禁限用农药; 四是按照食品来源分类, 动物源性食品与植物源性食品的限量分别进行转化; 五是饲料类的限量, 基于我国现阶段饲料相关数据较少, 为避免对我国贸易产生较大影响, 先不予转化。
二、 转化工作的实施
转化工作方案制定后, 为避免工作中出现偏差, 需要解决相关技术性问题, 依据转化工作实施的流程, 依次涵盖作物及食品分类、 残留物定义、限量适用性的监测评定以及风险评估等方面。
(一) 协调不同作物分类作物分类对于限量标准的使用非常重要, 为规范我国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制定, 2010 年原农业部发布了 《用于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作物分类》(农业部第1490 号公告), 该公告中的作物分类与我国现行所使用的用于指导农药残留试验的作物分类不同, 为专门针对限量制定而划分的[8]。 我国后续随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3 更新版本的发布, 其中附录A 食品类别及测定部位 (以下简称附录A) 经过多个版本的细化, 作物分类更加系统和全面。 该作物分类不仅可指导标准使用者在进行市场监管时, 对食品的采样部位、 残留量计算方式进行规范操作, 如对于柑橘类水果, 应采全果进行检测并判定农药残留量是否超标; 还可用组限量的指标作为单个农产品限量是否超标的判定依据, 如苹果中粉唑醇残留量是否超标, 可使用粉唑醇在仁果类水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进行判定。
由于CAC 限量所涉及的作物分类与我国有较大差异, 根据 《关于转化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建议》, 需在转化时将所有农产品按照我国的农产品名称进行核实、 分类。 CAC 所制定的组限量, 也应按照我国制定最大残留限量的作物分类进行拆分。 例如, CAC 限量中的葫芦科果菜类蔬菜对应的是我国瓜类蔬菜和瓜果类水果; 果菜类蔬菜 (葫芦科除外) 对应的是我国茄果类蔬菜; 甜瓜 (西瓜除外) 对应的是我国甜瓜类水果; 树生坚果与坚果合并后则对应我国的坚果。 对于动物源性食品, 食品名称更加复杂, 拆分也应注意与我国食品及食用农产品的分类相协调, 如奶, 对应我国奶类标准, 其名称为生乳, 而附录A 中又将其细分为牛、 山羊、 绵羊、 马等生乳, 使其适应我国农产品的分类; 如禽肉等, 将其分为鸡、 鸭、 鹅肉等,这些食品的分类与细化, 更便于标准使用人员抽检时进行标准操作。
当在我国的作物和食品分类中缺少所需转化限量的农产品时, 应在标准中增加相应的食品名称,如我国限量标准中缺少的加工农产品、 调味料、 小宗作物以及动物源性食品等。
(二) 选择适合的残留物定义残留物定义是残留限量标准中的核心部分, 但由于我国农药评估工作起步较晚, 过去在农药登记评审过程中, 很少对代谢物进行评估, 企业也基本不提交农药代谢物的相关材料, 导致我国对于残留物定义的研究明显不足, 也因此产生CAC 限量的残留物定义与我国有较大差异的情况[9]。 转化CAC 限量时, 应考虑我国实际情况, 如将CAC 的残留物定义照搬, 将会导致两种限量不协调, 因此采取将两种来源食品的残留物定义相结合, 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残留物定义的做法。 为此, 相关转化原则细化为: 针对植物源性食品中的残留物定义, 如CAC 的监测定义与我国不同, 优先按照我国的残留物定义执行;而当我国的残留物定义中所含的代谢物多于CAC制定的残留物定义时, 可参考CAC 的残留物定义;针对动物源性食品中的残留物定义, 如我国尚未制定相关限量, 则直接采纳CAC 的残留物定义。
(三) 判断限量的适用性当确定需转化的限量后, 为保证该限量在我国的适用性, 需要进行市场上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 制定了转化原则: 当监测结果中农药残留量超标率大于5%时, 表明该限量不适用于我国, 暂不转化限量, 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判断是否需要制定其他限量。
为保证监测结果的代表性, 考虑我国食品农产品消费量、 产量以及残留风险, 选择消费量大、 产量高、 残留风险高的食品和农产品进行抽检。 对于植物源性食品, 选择谷物、 油料和油脂、 蔬菜、 水果、 饮料、 糖料、 药用植物等共31 种产品进行检测。 其中优先选择鲜食的蔬菜、 水果进行抽样监测, 尤其是甘蓝、 苹果等我国种植面积广且膳食消费量大的农产品。 对于动物源性食品, 也按照相同原则进行抽样监测, 如肉, 抽取猪肉样品; 生乳,抽取牛奶样品; 可食用内脏 (哺乳动物和禽类) 抽取猪肝和鸡肝样品; 脂肪类则仅需要抽取猪脂肪,对于非脂溶性农药, 可不抽取脂肪类产品。
不同农产品用不同方式采样, 我国生产的农产品尽量选择主产地的批发市场、 大型超市、 集贸市场等初级农产品集散地采集样品, 如植物源性食品中的谷物、 油料和油脂、 蔬菜、 水果等, 尽量选择主产区采样; 动物源性食品中的生乳, 选择内蒙古、 新疆、 宁夏等奶类生产量大的地区采样, 而猪肉则选择四川、 湖南、 河南、 山东、 河北等生猪饲养大省采样。 此外, 为保证农药残留风险的最大化, 蔬菜和水果样品尽量不采反季节产品, 如香蕉、 苹果、 柑橘等尽量在收获季采样。 我国不种植的农产品, 如蔓越莓等, 可选择进口产品。
另外, 采样品种应兼顾差异性及代表性, 如柑橘类水果, 应采集柑、 橘、 橙等样品, 尽量采集个体差异较大的品种。 还应考虑采样部位的准确性,如稻谷是带壳的谷粒, 糙米则为去壳后未经抛光的大米等。 生乳不能为市场销售的经过加工的液态乳制品, 应为尚未添加任何物质的奶, 一般在牧场直接采样。
最后是样品制备, 一般要求按照NY/T 788《农作物中农药残留试验准则》 和GB 2763 的附录A 进行制备, 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与准确性, 并保证尽量降低样品中农药残留量的损失。
(四) 选择检测方法对监测样品进行农药残留量检测时, 优先采用已经制定成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检测方法, 并应对检测方法进行确证。 当方法存在灵敏度及回收率问题, 或无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参照时, 由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检测方法的研发, 为保证方法的重复性, 应经3 家以上 (含3家) 试验单位验证。 方法的精密度、 正确度等应符合NY/T 788 的要求。 代谢物的测定应符合残留物定义的要求, 当选择的检测方法的范围中缺少代谢物时, 若检测母体的方法可检测代谢物, 则直接使该方法, 否则应研发新的检测方法, 并进行验证。
(五) 进行风险评估所有限量应按照我国居民膳食结构进行风险评估。 由于我国居民膳食结构数据为2002 年的数据[6], 分类较为笼统, 如蔬菜只分浅色蔬菜和深色蔬菜两类, 水果只有一类等,因此进行风险评估时存在采用一类食品的残留量替代一种食品的情况, 这将高估了相应残留风险水平。 此时, 可借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起的全球环境监测计划/食品污染监测与评估规划 (GEMS/FOOD)收集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膳食数据[9]进行风险评估, 这一地区膳食数据中包括我国卫生部门提交的膳食数据, 可作为我国风险评估的参考。
三、 限量转化工作的建议
CAC 限量充实了我国食品中农药限量标准体系, 提高了我国限量标准与CAC 限量的协调一致性, 对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同时, CAC 限量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值得人们在后续限量制定工作中予以关注。
(一) 限量的适用性由于农药使用的情况不同, 以及农作物种类及栽培差异, 导致有些限量转化后, 与我国的生产实际有较大出入。 例如, 我国制定的韭菜中腐霉利最大残留限量, 为参考CAC所制定的腐霉利在韭葱上的限量 (0.2 mg/kg) 而制定。 而根据我国的生产实际, 韭菜上腐霉利残留严重超标, 导致农药不能在韭菜上登记[10]。 为解决此问题, 相关部门组织了专项研究, 重新修订了该限量。 随着我国小宗作物登记增多, 这一矛盾会日益突出, 因此应对CAC 转化限量的适用性进行逐一评估, 当我国有残留数据后, 应优先修改CAC 转化限量, 以保证农药在我国及时登记。
(二) 限量标准的动态跟踪由于CAC 限量的制修订是动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限量会重新评估并更新, 因此我国转化CAC 限量之后, 还应继续关注CAC 限量的更新情况, 以保证与CAC 限量 的 匹 配 性[11~13]。 例 如 , 矮 壮 素 在 生 乳 上 0.5 mg/kg 的限量值是在2017 年第49 届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 (CCPR) 会议时通过的, 在2018年第50 届CCPR 会议时限量值更新为0.3 mg/kg,而我国并未进行相应修订。 目前, 我国与CAC 限量不一致的限量指标仅在动物源性食品上就有77项, 其中38 项限量指标限量值低于CAC 限量值,39 项限量指标限量值高于CAC 限量值, 应在后续工作中对这些限量进行重点梳理与修订。
(三) 检测方法的配套我国农药残留检测方法经过多年清理、 整合与新制定, 其适用性、 覆盖性已经大大提高。 目前, GB 2763 标准中推荐了194 个检测方法标准[14], 但仍未覆盖所有限量, 尤其是转化CAC 的我国尚未登记使用的农药, 以及动物源性食品中配套的检测方法标准更少, 导致标准使用者在进行市场监测时无法执行。
(四) 标准的协调性限量转化工作的分步开展也带来转化限量与我国已经制定限量间的不协调问题。 CAC 限量数据是根据一种农药在作物上的施药方式与作物种植模式制定的, 由此制定的食品、 饲料中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在指标上基本协调。 若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种农药在植物源性食品中的限量, 而动物源性食品的限量为CAC 限量转化而来, 极有可能造成限量的不协调。 因此, 也应对此类问题予以关注和协调。
(五) 饲料中农药残留限量的缺失农药在农作物上使用后, 会残留在植物的果实或茎、 叶、 根中, 其中作为人类食品的部位可以通过进行农药残留试验以及膳食风险评估而控制其风险, 但农药还可能通过动物饲料进入动物体内, 因此, 需要制定农药在动物饲料中的最大残留限量[15]。 而我国目前由于各种原因, 饲料中的限量指标是极度缺失的,且由于缺少动物负荷相关数据也无法进行风险评估, 导致动物饲料中最大残留限量暂无法制定, 转化也存在一定困难。
随着我国农药残留研究的深入, 农药残留基础数据将逐步充实, 这将有力提升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技术水平。 同时, 应在完善农药代谢、 细化膳食数据、 规范评估方式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 国外用了60~70 年建立起来的庞大体系, 我国要在短短20 年内达到先进水平是存在难度的, 但我国可以借鉴CAC 的评估模式及其相关经验, 争取早日建立起我国特色的、 全方位、 多层次的标准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