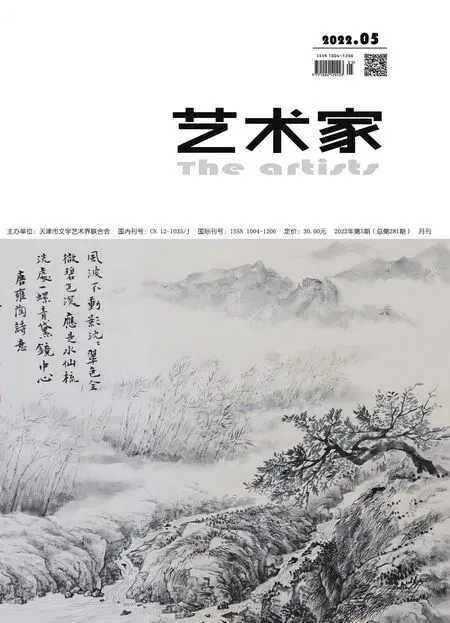从《美的滥用》看丹托对康德美学的回应
2022-11-22王慧婷
□王慧婷
(王慧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美的滥用》是丹托艺术哲学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与前两部相比,丹托的关注点从对艺术的哲学沉思重新回到了“艺术与美的关系”这一古老的话题上。本文将以《美的滥用》为切入点,探讨丹托对康德美学的回应,从中探寻丹托对“艺术与美的关系”的看法,并比较二人思想的差异与联系。
一、概念与解释:艺术作品的内核
丹托对康德美学的选择与评判基于其自身的美学诉求,正如他用“美的普遍性”与“理想美”来佐证自己的艺术定义一样。丹托认为,在现代艺术多元化的语境下,像康德那样对美或艺术作出内部阐释已经不合时宜了,若想为艺术找出一个普适的定义,必须从外部入手,即从关注“艺术是什么”转为关注“是什么构成了艺术品”。丹托对艺术的定义是从区分艺术与非艺术开始的。在他看来,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区别在于,艺术品有一层“光晕”(aura),而非艺术品没有,尽管它们在物理属性上毫无差别。艺术品通常有两种意义:所呈现之物和象征之物,即它的外观本身所展示的表层意义和由表层意义衍生的深层概念。
丹托在《寻常物的嬗变》中对这一定义进行了详尽阐释。而在2003 年发表的《美的滥用》中,丹托试图从康德身上为这一定义寻找哲学上的依据。首先,丹托从康德美学的第二契机,即“美是那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这一定义展开论证。康德指出,与鉴赏判断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带有基于客体之上的普遍性而对每个人有效的要求,就是说,与它结合在一起的必须是某种主观普遍性的要求”。既然美是普遍可传达的,鉴赏判断具有主观普遍性,那么在鉴赏判断中,对对象之评判必须先于愉快感。因为愉快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情感,不能保证普遍性,只有判断才能保证这一普遍性,并且“可以被普遍传达的不是别的,而只是知识和属于知识的表象”。丹托认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康德才将“鉴赏”定位成一种“判断力”,而非纯粹的趣味问题,同时也体现了康德自己杰出的“判断力”。丹托指出:“美也许的确是个主观的问题,但它就像康德所坚持的那样具有普遍性……它与人性中内在的某种东西息息相连。”但是,丹托不认同康德仅仅将鉴赏与美相连的做法,他认为鉴赏判断不仅要评判一个对象美不美,更重要的是剥离其中的思想内涵。“艺术可以、事实必须同时是理性和感性的方式”,关键在于如何将它的感性属性与理性内容联系在一起,即康德所谓的“由表象所激发起来的诸认识能力在这里自由地游戏”。审美之美可以通过感官辨别出来,而艺术之美需要眼力和批评智力。如果仅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事物,对艺术的评判只会是主观而非普遍的,正如康德不认为原始部落的文身是美的。所以丹托认为,我们在看艺术的时候应更多地运用认知判断力而非审美判断力,这样才能更尊重艺术的差异,让不同种类、风格、地域的艺术作品各放异彩。
丹托还在康德的“依附美”与“自由美”中得到灵感,提出了“内在美”与“外在美”概念。康德在论证鉴赏判断的四大契机后,又将美分为“自由美”和“依附美”。“自由美”是“不以任何有关对象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为前提”的美,而“依附美”是“以这样一个概念及按照这个概念的对象完善性为前提”的美。“自由美”符合康德之前对美的论述,而“依附美”则与概念联系在一起。矛盾的是,对康德来说,理想的美恰恰是与概念相连的“依附美”而非纯粹的“自由美”。他指出,理想美“必定不是什么流动的美,而是由一个有关客观和目的性的概念固定了的美,因而必定不属于一个完全纯粹的鉴赏判断的客体,而属于一个部分智性化了的鉴赏判断的客体”。对此,丹托首先指出:“康德有关内在美不单单是趣味问题的观点完全正确。”接着,他具体剖析了康德的理想美,明确理想与道德的联系:“康德自己急于强调,我们必须‘区分美的规范观念与理想美’,特别是就人类而言,它体现在道德性的表达上。‘这表明与标准一致的判断,绝对无法是纯粹美学的,但与理想一致的判断却不是纯粹的趣味判断。’所以,理想美可能涉及规范美与康德列举为‘心的良善、纯洁、力量平安等它们可以在身体显现中看到(正如其影响是内在的一样)’的表达之间的平衡。”但是,丹托认为康德对美的分类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当代的艺术实践。从“概念内在于作品并解释美”这一点出发,丹托提出了自己对美的划分,即“外在美”与“内在美”。所谓的“外在美”类似于康德的“自由美”,即只关乎感官,不涉及任何概念;而“内在美”类似于“依附美”,其中包含智性与概念的因素。与康德不同的是,丹托认为康德的理论缺乏“意义的概念”,所以在“内在美”的阐释中,他特别区分了不同对象的意义概念。在丹托的阐述中,首先,思想是艺术的内核,但不是思想支配艺术,而是艺术支配思想;其次,美是艺术表达的一种模式,情感在这种模式中与激发艺术品的思想联系起来,但除了美,艺术表达还有恶心、色情、崇高等多种模式,美并非唯一的选择;再次,只有当美与艺术思想并行不悖的时候,美才能成为艺术表达的模式,内在于作品的意义,使思想呈现出感受力;最后,美虽然是艺术模式之一,但它是唯一一种拥有价值观的艺术模式,这就解释了艺术为何对人类有重要性,以及为何必须在艺术的定义中给美找到一处空间。
二、道德与人性:艺术的普世追求
在《美的滥用》一书中,丹托还多次回应了“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命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对美和道德进行类比,并经常用一些道德评判标准来称呼美的对象,如将巴黎圣母院称为庄严雄伟的、将白色说成是纯洁的象征等。在中国文化中也有“比德”的说法,即用自然美好之物比喻美好的品德,正如梅之傲骨、兰之旷达、竹之谦逊、菊之高隐,“它们激起的那些感觉包含某种类似于由道德判断所引起的意识的东西。鉴赏仿佛使从感性魅力到习惯性的道德兴趣的过渡无须一个太猛烈的飞跃而成为可能,因为它把想象力即使在其自由中也表现为可以为了知性而作合目的性的规定的,甚至教人在感官对象上也无须感官魅力而感到自由的愉悦”。审美可以为我们架起一座从知性向理性过渡的桥梁,使感性的人通过对感性活动的思考,猜测不可认识的本体就是道德本体,认识到人是自由的。
丹托认同康德的这一决断,并将其应用到美的艺术的历史叙述中。丹托指出,此前的艺术对美青睐有加,而20 世纪后的前卫艺术却开始放逐美,这是因为艺术家秉持着“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观念。艺术创作并非单纯的感官再现,它需要也一定会表现艺术家的思想倾向、情感态度,而好的艺术作品需与世界前进的方向保持一致,其内核是善的。以达达主义为例,达达派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宗旨是通过废除传统的文化和美学形式发现真正的现实,以抵抗现实的虚伪与绝望,表达自身与统治阶级的决裂。他们“拒绝用艺术迎合那些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的人的美学情感——用胡说八道取代美,用愚蠢取代崇高,用一种惩罚性的小丑方式伤害美”。对达达派来说,将艺术画得美,意味着对残酷现实的美化与粉饰,意味着对当局的迎合与妥协,这种做法为他们所不齿。在那个充满不义战争的年代,如果要有艺术,它不应该是美的,因为这样的世界不配得到美。艺术真实必须相应地和人生一样粗糙、原始,被美过滤过的艺术起不到人类行为的“镜子”作用。而美化者则被看成是邪恶的合作者。
对丹托来说,美的滥用同样是“针对道德的一种象征性冒犯行为,因此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冒犯”。即便美只是道德的“象征”,二者之间仅为类比的关系,美的滥用不一定意味着一种根据事实的道德邪恶,但美毕竟长久以来都与善绑定在一起,成为一种约定俗成。所以,作为一种拥有价值倾向的艺术表达模式,美是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的。“如果一幅画的目标是激发欲望,那么,它画得美就是适合的。而如果目标是要激发憎恶,也许画得恶心更恰当。”既然美与作品的内容有着内在的联系,那么当艺术作品不合时宜地表现为美时,我们完全可以批评这样一件美的作品。
三、崇高:对美的强力一击
当后现代艺术摆脱美的束缚走向崇高时,艺术与美便彻底失去了必然联系。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纽曼激动地宣称:“崇高就在现在。”后现代艺术家从崇高中找到了“没有可能在美的美学中找寻的艺术公理”。纽曼指出,从古希腊至今,欧洲艺术家就一直在美的观念与崇高的欲望之间挣扎,一面是“有待于发现的完美形式的升华”,一面是“摧毁形式的欲望,形式可以没有形式”,最终,在后现代艺术这里,艺术彻底捣毁了美。利奥塔受到纽曼的启发,吸收博克、康德的理论对崇高展开了后现代的阐释,指出崇高就是“呈现不可呈现”,即对未定性的见证,因此崇高具有瞬时性。丹托对崇高的论述基于康德、博克、纽曼和利奥塔的理论。首先,他与利奥塔一样,都在康德对崇高的阐述中找到了超越感官的依据,认为崇高就是呈现不可呈现,而不可呈现的是一种观念,如宇宙、人性、善、此刻等。康德指出:“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对自然的美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我们之外的根据,对于崇高我们却只须在我们心中,在把崇高性带入自然的表象里去的那种思想境界中寻求根据。”崇高是心灵的特殊感受力,当想象力无法把握无限的对象时,它会在内心激起一种类似于道德情操的理性感悟。也就是说,想象力的有限性激起了理性的超越,于是产生了崇高。崇高只存在于心灵之中,因此,它与涉及对象形式的美不同,它呼应着无形式,这就使艺术超越了再现形象的诉求和对形式的依赖。正如纽曼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画面中往往只有色块、布局和材料本身,作品不指涉任何外在的形象,而只作自我指涉,绘画的意义在于其自身。丹托指出,崇高的这种未定性与瞬时性类似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在那里以及意识到在那里,也类似于纳博科夫的描绘:“犹如在虚空的夜晚时分,阳光普照大地,窗户突然‘啪’地打开”,与利奥塔对崇高的看法相近。
但是,利奥塔与丹托在对康德崇高的共通感阐释上出现了分歧。利奥塔认为,崇高就是对未定性的见证,而康德的共通感使得崇高最终指向一个确定的理念,即对道德或实践理性的指涉。在利奥塔看来,崇高艺术的价值只在于“呈现不可呈现”这一事实,而不是去模仿自然,或者再现、象征、指涉某种被设定了的“绝对理念”。所以在后现代艺术中,艺术家拒绝呈现那些能激起共通感的形象,而以“怪异”“无形式”的消解姿态出现。而丹托则赞同康德将崇高与共通感和道德律令相连的做法。他指出,在崇高中,我们重新发现了人类的尊严。早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康德就通过对比优美和崇高来提高崇高的美学地位,他说:“崇高必定总是伟大的,而优美却也可以是渺小的。崇高必定是纯朴的,而优美则可以是着意打扮和装饰的。”“在道德品质上,唯有真正的德行才是崇高的。”这就昭示了崇高与道德、人性的联系。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崇高能够把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其日常的中庸,并让我们心中的完全不同性质的抵抗能力显露出来,使我们有勇气能与自然界的这种表面的万能相较量。即便人在自然的强制力面前不得不屈服,我们的人格依旧没有被贬低。
崇高与美一样都基于人类的共通感。崇高深埋在人性之中,“在趋于对(实践的)理念的情感即道德情感的素质中有其根基”。归根结底,崇高是人性的集中体现,它使我们将日常所操心的东西(金钱、健康、生命)都看成是渺小的,在内心唤起超越自然的使命与尊严。从美到崇高,康德将审美与更高的人类理想也就是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试图在人类自身的尊严和意义之中寻找审美的根源,用审美的自由为德行的自由做准备。丹托延续了康德对崇高的道德指涉与对共通感的分析。他指出,美可以是无关紧要的,但崇高一定是受人尊敬的,崇高代表着对人的重新发现,象征着人的尊严和存在意义。“康德说:‘崇高是,仅仅由于能够思维它,证实了一个超越任何感官尺度的心意能力。’如果感觉像顽童似的话,我甚至会补充说:‘它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它在观看者的心中。’”艺术摆脱美走向崇高是向道德与人性跨越的一大步。通过展现崇高,艺术家重新发现了人类,也指明了世界前进的方向;通过崇高,艺术恢复了它的道德重要性。
四、艺术不一定是美的,但人生需要美
通过对美、善、艺术三者关系的辨析,对崇高的阐释以及对康德美学的回应,丹托最终要证明:美不是艺术的必选项,它“既不属于艺术的本质,也不属于艺术的定义”。首先,在传统美学中,艺术的定义通常离不开对美的执念,美学家往往将目光聚焦于艺术品本身特殊的属性带给人视网膜的反应或心灵的震荡。但丹托要证明,是解释构成了艺术品而不是美构成了艺术品。艺术的内核在其思想,而美仅仅是一个诱饵,是将思想呈现给感受力的模式之一。其次,好的艺术是善的,如果艺术作品不合时宜地表现出美,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道德的角度批判这件美的作品。再次,在艺术史的问题上,许多艺术批评家认为,艺术史的发展实际就是一场美的接受史,就像事物在被感觉为美之前,通常都会被感觉为是丑的。从模仿艺术到印象派、现代派、前卫艺术,人们的审美水平逐步提升,美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但是丹托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许多艺术作品是不美的,如马蒂斯的《蓝色裸体》、达明安·赫斯特的《生满蛆的牛头》,马蒂斯和赫斯特也不会因为观者把他们的作品看成是美的而感到高兴,因为最关键的是艺术品中观念的传达。因此,他建议“把美的概念限制在它的审美身份上,后者指各个感官,承认艺术终有些东西就其最高级实例而言属于思想”。当美从艺术的概念中消除之后,是否要使用美成为艺术家的重要选择。
丹托用语言学中的“屈折语”对艺术的定义和美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如果某物被屈折以引起观众对其内容的态度,那么,某物就是艺术品。迄今为止,美是屈折语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是,恶心是另一重要的屈折语,残暴蛮横则是第三个……我不会说屈折语的数目无限多,但迄今这些屈折语太多了。”屈折语解释了艺术存在的意义:为何人需要艺术,而哲学不能取代艺术?因为人不仅仅是知性的、理性的,人首先是情感的动物,通过情感,思想才能更深入触及人类的心灵世界,而美就是激发情感的一剂良药。在艺术作品中,美像恶心、色情一样,通过感官激起观者强烈的情感,而观者再通过情感深刻理解美蕴含的思想。但美并非唯一的屈折语,恶心、崇高、色情都是引发情感的屈折语,所以美不是艺术的必要选项。此外,美也仅仅是艺术的屈折语,是诱饵,是手段,而非艺术的内核与目的。“美并不是一道彩虹,等着我们去观看,作为不懈寻找的报酬。美学沉思从来都不是探讨艺术的唯一适当的方法。换句话说……无可争辩地出现在眼前的美(如宏伟的大教堂)也许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美仅仅是诱饵,如同美在两性关系中的作用一样。”
虽然美不是艺术的必选项,但美是人生的必需品,丹托反对的只是美对美学与艺术的全盘侵占,而非美的现实意义。他以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巴尔贝克的苹果树”举例:叙述者马塞尔本在为深爱的外祖母离世而感到悲痛,突然间,他看见了一片红彤彤的苹果树,这一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色使得他对外祖母的悲痛开始减小了。美是治愈心灵的良药,正如预言家以赛亚所写“赐予它们美,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艺术可以让美缺席,因为“如果消灭的是艺术美,我们也许损失不算很大,无论那意味着什么,因为艺术具有大量其他补偿价值,而且艺术美在世界上大多数艺术文化中,只是种偶然性特质”。但人生不能缺乏美的存在,“美与无数其他美学特征之间的差异是,唯有美拥有至高的价值,像真和善一样。倘若美被消灭了,留给我们的将是一个令人不堪忍受的世界,就像倘若善不存在了,一个完全人性的生活将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上看,丹托的艺术哲学与康德美学一样,有着深厚的人性论基底,无论抬高美还是放逐美,二者的出发点都是“人”,最终也做到了“人”的复归。
五、康德美学与丹托艺术哲学的差异与联系
虽然丹托对康德美学作出了诸多回应,但从根本上看,二人对美和艺术的理解还是有不少相悖之处。例如,基于模仿的艺术,康德认为好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美的艺术“必须看起来好像是自然,虽然人们意识到它是艺术”。自然美和艺术美是统一的,艺术也必须符合目的性,必须表现为想象力在自由中与知性的规律性的适合。丹托则认为,美只是艺术的一种模式,是艺术家的选择之一,艺术也可以是令人恶心的、恐惧的,重要的不是美,而是艺术中蕴藏的思想。艺术可以模仿自然,可以表达抽象情感,也可以运用现成品,只要它包含思想,能够解释。在艺术的定义上,康德认为美的艺术需包括想象力、知性、天才、鉴赏力这几大因素。丹托对艺术定义的思考角度则从“艺术是什么”变为“是什么使得艺术品成为艺术品”,即从康德式的内部阐释转变为外部阐释。丹托甚至说过,当他阅读那些经典的美学文献时,“无法看出来它们与我在纽约遇到的艺术有什么关系”,这其中必然包括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正是出于对传统美学的不满,丹托拒绝别人称他为“美学家”,而以“艺术哲学家”代之。
基于相差甚远的时代背景、哲学路径,面对相隔天堑的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康德与丹托对美与艺术作出了看似截然不同的阐释。但细细品之,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的思想有许多暗合之处。首先,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康德和丹托都在呼吁美学中的道德回归,他们都是人本主义的忠实拥趸,无论康德抬高美的地位还是丹托意图放逐美,都是出于人性论的考虑。对康德来说,美是贯通天人之际的桥梁,是他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佳解答,审美的目的性与审美理想最终都服务于“人”这个终极目的。对丹托来说,艺术代表了世界前进的方向,为艺术去除“美的污名”也是为了提高艺术的道德重要性,以此为饱受争议的艺术正名。此外,二人对形而上学有着相似的追求。康德自不必说,丹托则实现了多元化视野与本质主义立场的完美融合。彼得·基维曾指出,如果以狐狸和刺猬作比喻,丹托就是“一只有着大智慧的刺猬”。20 世纪风云巨变,万象更新,理论界更是思潮频现,众说纷纭。在本质主义备受诟病的时期,丹托依旧坚守立场,努力在纷杂中把握整体,试图在纷扰繁杂的艺术世界中建立一个清晰完整的观念体系。例如,他提出的“艺术界”理论虽然是一套完整的观念体系,但这一体系是不断生成变化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各有分别,意义即便来自语境,但语境是开放的。丹托对艺术的定义并没有将艺术禁锢在一个圆圈之中,而是赋予艺术更多的可能性,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一切新事物,为艺术的多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总而言之,无论是《美的滥用》中丹托对康德美学的回应,还是比较二人美学的内在诉求,我们都能看出两位思想家理论的暗合之处。丹托与康德看似南辕北辙,但究其根本,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二人都在呼吁道德的回归,且都对人性的尊严充满信心,这大概也是丹托回应康德美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