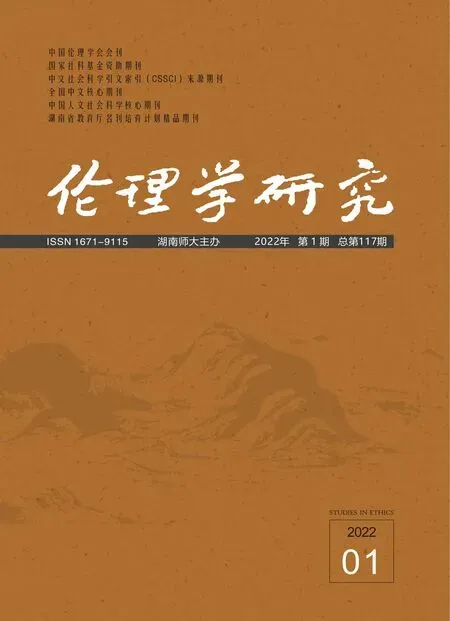明代大礼议的情礼分歧与论证方法
2022-11-22刘文
刘 文
“大礼之争”是明代围绕由藩王入继帝位的明世宗朱厚熜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尊号与主祀问题而产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学界关于明代大礼议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1)将大礼议与嘉靖政治革新相联系,视其为“嘉隆万改革”的序章[1];(2)从礼秩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2];(3)从明廷人事变局的角度进行研究[3];(4)从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斗争的理学史的角度进行研究[4]。这些观点各有侧重,而对至少如下三个问题的研究,仍有深化、补充的必要:第一,所议何事?第二,分歧何在?第三,如何议礼?第一个问题,议礼议的是朱祐杬的“尊号与主祀”,实质是一个正名与用名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5];第二个问题,议礼双方是情与礼的分歧,实质是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道德理性的分歧;第三个问题是议礼方法的问题,属道德实践层面。本文探讨后两个问题,求教于方家。
一、情礼分歧
1.宗法派的主张及其理论基础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议礼的诏书下达后,朝臣们主要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多数朝臣持第一种方案,主张继统必先继嗣:让朱厚熜改换父母,称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给朱祐杬夫妇议的尊号为“皇叔父兴献大王”“皇叔母兴献王妃”,皇帝在父母面前称“侄皇帝”[6](卷一,9-12)。杨廷和这一派理论以宗法礼制与宗法伦理为基础,故被称为宗法派,又称护礼派、多数派。
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是宗法社会[7](1)。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以大宗小宗为准则、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封建伦理体制”[8](54),这套宗法礼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而大宗、小宗是其最重要的准则。嫡长子一系世世为大宗,其余子孙为小宗。嫡长子对王位、侯位等名爵和土地、财物等具有优先继承权。有时嫡长子死了,则顺延一代,立嫡长孙为继承人,若再死了,则又顺延一代。若嫡长子一系没有继承人,则按年龄顺序立其他嫡子。这就是《春秋公羊传》所说的“立嫡以长,不以贤”。如果没有嫡子,则从庶子中选择继承人[9](110)。宗法制度在周朝时就得以确立和实施,随着时代变迁,制度时有存废和损益,但一些重要原则和观念一直影响到明清。朱厚熜以小宗入继君位,宗法派让他称孝宗为皇考,严格区分“所生”与“所后”的关系。针对朱厚熜想在其父的尊号中加“皇”字的要求,御史曹嘉上奏批评说:“陛下坚欲加称‘皇’字,所生、所后惟势重轻,大宗、小宗任情颠倒。”[6](卷七,9)嘉靖三年(1524)初朱祐杬的尊号议定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后,针对人情派要立庙大内进行祭祀的主张,时任礼部尚书汪俊等言:“陛下欲改称庙号,自尊本生,立庙大内,臣等窃念此举所系甚大。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犹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10](卷三十七,1-2)宗法派认为,“皇”字是大宗“正统”的专属用字,小宗不能使用,否则便会混乱大小宗的界限。根据宗法原则,小宗不得祭祀大宗,大宗也不能祭祀小宗。现在皇帝要“立庙大内”祭祀朱祐杬,这是不合礼的。
宗法派的理论基础可以归结为一个“礼”字。《礼记·曲礼》有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是社会运转的仪轨、君臣行事的道德规范,是确定差序、等级、亲疏的依据。邹守益称:“礼者所以正名定分,别嫌明微,以治政安君也。君失礼则入于乱,臣失礼则入于刑,不可不慎也。”[10](卷三十七,2-3)正是出于对礼的规范性、秩序性作用的强调和对失礼的担忧,宗法派提出了让皇帝入继大宗为后、不祭小宗、不妨碍大宗统系的议礼主张。
2.人情派的主张及其理论基础
少数几位中下层官员如观政进士张璁、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副都御史席书等持第二种方案,主张统、嗣二分:让朱厚熜只继承孝宗—武宗的君统,不继宗统,仍以自己的父母为父母,称孝宗、张皇后为伯父母[10](卷四,160)。张璁这一派理论以孝道亲情为基础,称为人情派,又称议礼派、少数派。
孝道是以“善事父母”为核心的道德规范,“是中国社会一切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精神基础和实践起点,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11](33)。西周之时,孝道已经是普遍的道德观念。而后孔子建立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体系,把对父母、兄弟的孝悌视为仁的基础与前提。成书于汉朝初年的《孝经》,已经把孝道的核心内容从“善事父母”发展到其引申意义“以孝治天下”了[12](77)。至此,孝道成为整个传统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张璁高度肯定朱厚熜的尊亲之举是大孝之举,他在议礼第一疏中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陛下嗣登大宝,即议追尊圣考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诚大孝也。”[10](卷四,162)除了抬出孝道的规范之外,人情派还将议论的重心转移到儿子对父母的天然的道德情感即孝心上来。如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朱厚熜在杨廷和等人拒绝在朱祐杬的尊号中加“皇”字并威胁辞职时诉说道:“卿等所言皆推大义,朕之所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为朕申明孝义,勉录皇号施行,庶安朕母子哀心。”[10](卷九,13)皇帝希望用“昊天至情”“母子哀心”来打动、说服宗法派同意他尊亲。
人情派基于孝道亲情而议礼,他们的理论基础可以归结为一个“情”字。他们不仅仅是停留在道德情感层面进行论证,而是从礼的起源上寻求理据,重释礼的精神。如张璁以《礼记》中礼是“人情而已”的记载为依据,强调顺应人情便是“先王制礼”的精神。熊浃亦上疏称:“夫礼者,因人情者也。”[6](卷六,15)席书则明确说:“礼本人情,皇上尊为天子,慈圣将临,设无尊称,于心不乐,于情难已。”[6](卷七,20)礼既然是缘情而制、因情而生,议礼自然不能违背人情。现在皇帝出于孝心而尊亲,如果不能实现上尊号的心愿,“于心不乐,于情难已”,这显然不符合先王制礼的精神。
3.情礼之辨
宗法派、人情派议礼主张的分歧可以归结为礼与情的冲突,也就是宗法派所谓“正统”与“私情”的冲突,即内在道德情感与外在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孔子曾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13](1400)在礼的起源上来说,礼是缘情而制,是社会运转所必需的规范,对情加以节制,使其行之有度。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时有损益、变革,这就是“礼,时为大”[13](719)的精神。而礼制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很可能与人情产生矛盾而不近人情。明代大礼议这一特殊而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好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情礼冲突的绝佳案例。
对于大礼议之争实际上是情礼之辨这一问题,议礼双方都有清醒的认识。吏部尚书乔宇等疏论大礼言:“今之为议者有二:礼官之议欲考孝宗,为隆正统,存所后者父子之名;(桂)萼等之议,欲考兴献帝,为厚私亲,存本生者父子之名。”[10](卷三十六,10-11)兵部主事霍韬称:“窃谓大礼之议,两端而已:曰崇正统之大义也,曰正天伦之大经也。徒崇正统,其弊至于利天下而弃父母;徒重天伦,其弊至于小加大而卑逾尊。”[10](卷四十二,3-5)议礼的分歧已经非常清楚,解决分歧的路径却势同水火。为了维护“正统”也就是宗法礼制,宗法派认为应该“抑情准礼”(蒋冕)[10](卷三十七,15),“制于礼而情有所屈”(汪俊),“以礼制情,以义正恩”(陈江、易瓒等)[6](卷七,10)。他们甚至直接批评皇帝“情衷过厚”,孝心太过。他们辩称,继嗣孝宗并不是要皇帝“忘情”,只是服从礼制的安排罢了[6](卷六,18-19)。人情派则认为“父子也,天性也”[6](卷三,12),岂能割舍?朱厚熜明确要求“以伸朕情”[6](卷十一,10),方献夫提出“缘情乃所以制礼”[6](卷十七,18)。他们反驳说:先王制礼,能质诸鬼神而无疑,俟之百世而不惑,现在宗法派竟然要“以伯为父,以父为叔”,这能“质鬼神、俟百世”吗?[6](卷三,16)两派各执一端,难以调和。
对于大礼议中礼与情的含义与关系,清人李祖陶有比较准确的评论:“礼者,人心之堤防也,稍或不谨,则决裂将无所不至;情者,又典礼之枢机也,稍或过执,则拘泥亦无以自行。”[14](卷六十二,23-24)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情是典礼内在的“枢机”。失去规范,“则决裂将无所不至”;而太过拘泥于情,“亦无以自行”。礼与情必须权衡至当才能实现畅通无阻的局面。
二、论证方法
大礼议爆发后,议礼双方围绕朱祐杬的尊号问题相互辩难,采取多种方法论证自己的主张,力图说服、驳倒对方。幸而相关文献保存较完备,我们得以进行“文本田野调查”,采取立足本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解释途径[15](19),考察大礼议发生时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和当事人的价值观念,探究议礼双方开展情礼之辨的具体方法。
1.考论史例
中国一向重视历史传统,传统知识精英做国事决策时往往会考察历史上发生过的类似情况(史例),在结合当下现实、综合权衡之后,再拿出解决方案。这种历史上的类似情况,可以是本朝的,也可以是前朝的。议礼开始后,毛纪去请示杨廷和,杨让他参考汉哀帝与宋英宗的史例。这两个史例,都是皇帝无子,择建支子预立为后,新皇登极后要求追尊亲生父母而引发争议的情况。宗法派完全照搬了宋代“濮议”中司马光、程颐的观点。毛纪称“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皇上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10](卷二,80)。杨廷和称“程颐濮议最得礼义之正断,宜称皇伯考兴献大王”[16](5037)。此外,宗法派还援引舜与东汉光武帝的史例,说舜受尧之禅让之后没有尊崇生父瞽叟,光武帝登极后也没有尊崇其父南顿君刘钦。他们称:“惟皇上取法二君,则圣德无累,圣孝有光。”[6](卷二,15)
针对宗法派援引的史例,人情派做出了反驳。张璁上《大礼疏》,称不能拘泥汉宋史例作为议礼依据,他敏锐指出汉宋史例与当下现实的不同之处:汉哀帝、宋英宗都是“预立为嗣”,迎养宫中,而朱厚熜的堂兄武宗并无立嗣之举,继位的直接法律依据《武宗遗诏》只提到入京继位,未提继嗣孝宗。他也引用两个史例:汉文帝继惠帝是以弟继兄;汉宣帝继昭帝则是以兄长的孙子继位,都没有建立父子之号[6](卷三,5-17)[10](卷四,160)。而舜与光武帝,没有追尊,也没有改称生父为叔伯父。霍韬上《大礼议》,称古代帝王制礼,“因诸人情,准诸天理”,现在廷议“顾区区汉宋故事之求沦胥世俗之陋”,而“舜受尧之天下,未闻不父瞽叟而父尧;禹受舜之天下,未闻不父鲧而父舜。舜不父尧,未闻废尧之祀;禹不父舜,未闻废舜之祀”[6](卷三,12-16)。要学尧舜禹的史例,而不是“区区汉宋故事”。
上述,都是援引史例进行议礼。有些史例中往往有权威人物的论断,被引用来作为论证各自主张的论据。双方都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史例,即使引用了同样的史例,也往往作有利于自己的解读。
2.诠释经典
宗法派的理论基础是宗法礼制与伦理,而充分体现宗法礼制与伦理的是《仪礼》《春秋公羊传》等儒家经典。于是,诠释这些经典中的相关内容所含的礼意便成为该派最重要的论证工作。正德十六年五月,毛澄在第一次集议之后上疏道:“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极矣。”[10](卷二,80)他同样主张入继之君改称所生父母为伯叔父母,称先君为父。宗法派另一干将何孟春在议礼疏中称:“《仪礼》传:‘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大宗不可以绝。”[10](卷四十一,9-20)这些话出自《仪礼·丧服》,可见,《丧服》篇所含的礼意成为宗法派立论的理论基础。《丧服》对“为人后者”如此解释:“为所后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17](555-556)为人后者“若子”,意即对所后者所服的丧服如亲生儿子。因之,程颐、毛澄提出“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也就理所当然了。这一思想在《春秋公羊传》中表达得更为明确:“为人后者,为之子也。”[18](396)
人情派的主张基于孝道与亲情,他们主要通过征引、诠释《孟子》《礼记》中的相关内容来论证自己的思想。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张璁在议礼疏中引用孟子的话:“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这几句话出自《孟子·万章上》,下文是“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他巧妙地将孟子所说的尊亲和奉养父母与给朱祐杬上尊号和迎养兴献后蒋氏的议题结合起来,用经典语录为其尊亲主张做支持。尊亲之外,张璁还重新解释了礼的精神。他引用《礼记》的话说:“《记》曰: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10](卷四,162)这几句话出自《礼记·问丧》:“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13](1537)前文已述,先王“缘情制礼”,“礼以饰情”,情本就是礼的一个来源,礼虽然具有规范、节制情的作用,但其精神实质却与情是相通的。张璁批评宗法派的主张不止违背孝道,还违背人情,自然也违背了礼。针对宗法派引用《公羊传》中“为人后者为之子”的做法,张璁驳斥道:“非圣人之言,汉儒之言也。况我皇上乃入继大统,非为人后者也。其说又焉可用哉?”[10](卷八,311)
中华文明拥有的经典数量众多,加上注疏解释系统,更是汗牛充栋。众多的经典固然能为生活实践提供尽可能详尽的指导,但不同经典的记录、人们对经典的理解往往也是千差万别,歧义纷呈。大礼议中议礼双方各执一端,难有定论,这或许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是“礼的困境”的表现[19]。
3.探究典章
除了考论史例、诠释经典外,议礼大臣还重视使用本朝甚至前代的典章制度来为自己的议礼主张进行论证。具体而言,主要有《皇明祖训》《孝慈录》《大明律》《武宗遗诏》以及《魏明帝诏书》五种。限于篇幅,本文只谈祖训与遗诏两种。
“祖制”顾名思义是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代所制定的典章制度,如《皇明祖训》《孝慈录》《大明律》《大诰》等,其中尤以《皇明祖训》(下文简称祖训)位序最崇高也最具权威。明代君臣标榜“奉天法祖”,祖训的大部分条款都能为后代所遵守。如果有皇帝未能遵守,大臣们往往进行谏诤,固然祖训不是挽回圣意的万灵丹,却是言事臣僚的护身符[20](27)。宗法派对典章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对祖训的严格遵循上。内阁起草的迎立朱厚熜的《武宗遗诏》的法律依据就是祖训的“兄终弟及”条文:“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21](179)正是因为“兄终弟及”必须是“嫡母所生”的亲兄弟,所以朱厚熜必须继嗣孝宗,以“如亲子”的身份视孝宗,与武宗成为宗法上的“亲兄弟”,才有资格入继大统。
遗诏是前朝皇帝临终时发布的诏书。因其发布于新老皇帝交替之际,故意义重大。遗诏的基本规制相对固定,大多含有回溯政绩、检讨过失、认定继位之君等八项内容[22](47)。确定皇位继承人是遗诏最重要的政治功能。与宗法派以祖训为论据不同,人情派搬出《武宗遗诏》为理论武器,因为迎立遗诏只说了“以陛下聪明仁孝、伦序当立,迎继大统……而未尝著为人后之义”[10](卷四,162),现在朱厚熜已经遵诏继位,宗法派却要求继嗣为孝宗后,显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对此,宗法派胡侍辩称:
璁等引遗诏云嗣皇帝位,初无为孝宗之子之说。臣按璁等尝倡议谓继乃帝王相传之次,嗣必父子一体之亲,继统者不必继嗣。夫使嗣必父子之亲,则遗诏不当言“嗣皇帝位”,使廷臣称嗣为不经,则遗诏称嗣,何以独为继统而非继嗣也?[10](卷四十,10-14)
胡侍认为,遗诏中明明是说“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6](卷一,1-2),这个“嗣”字,已经表明遗诏暗含了继嗣的意思。因之,张璁二分统、嗣,继统不继嗣的主张是错误的。可见,由于立论不同,即使是援引同样的典章,议礼双方都能作出截然不同的解读,双方的辩难已经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
4.借助灾异
灾是指灾害,异是指异常的自然现象,汉代以后的学者往往并用此二词,不做意义上的分别。灾异很早便与政治发生联系,《周易》中有“渐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的记载,因灾言事的灾异学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明代统治者比较敬畏灾异,国家意识形态中有天人感应理论的一席之地。朱元璋登极之初便要求各级官员“遇灾异具实奏闻”[23](1016),后来形成礼部定期分类上奏全国各地的灾异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弭灾修省”的制度。据《大明会典》记载:“凡各处地震、山川异常,礼部案候年终,类奏通行,在京大小衙门及南京礼部并各被灾地方一体修省,或有异常灾变不在类奏之例者,即行具题,一应祭告、宽恤、修省事宜,照灾轻重施行。”[23](1016)如有异常情况,皇帝往往要发布诏书,做出至少是礼节上的反省,“以回天意”。
嘉靖元年(1522)正月十一日,朱厚熜母亲蒋氏所居清宁宫后面的三座小宫殿发生火灾,几乎烧到清宁后殿。当时朱厚熜正筹划将父母尊号由兴献帝、后改为兴献皇帝、皇后(即所谓“争皇”),于是,以此为契机,宗法派大臣如钦天监少卿华湘、礼部尚书毛澄及科道言官纷纷上奏谏止,吏部尚书乔宇更以灾异自陈乞罢。兵科给事中邓继曾上疏言:
去年五月朔日精门灾,今年正月二日长安榜廊灾,今月郊日内宫小房灾。夫五行之德,火则主礼。五事惟火曰言,言生于名,礼兴于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不兴。今未期而灾者三,臣虽至愚,知其为废礼失言之效也。[10](卷十,10)
宗法派认为火灾与兴献帝、后的不当加称触怒天意有关。邓继曾根据五行学说,认为五行中火主礼,后宫起火为“废礼之应”。于是朱厚熜暂时不再坚持己见,继续称孝宗为皇考,称朱祐杬为“兴献帝”,不加“皇”字[24](740)。宗法派借助灾异取得这一回合的暂时胜利。
余论
当然,随着朱厚熜君位稳固,他屡屡以个人意志加于礼制之上,大礼议最终的结局即按皇帝旨意行事,一大批宗法派官员遭到了清算。大礼议之争以血腥收尾而沉寂,但其蕴含的情礼之辨的声音一直响彻在思想史上。
近年已有学者关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一系列的“辨”,对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论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运思方式和认知方式[25](6,209)。情礼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因为仁属于情感,礼为理的载体,故此论题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表述为仁礼关系、情理关系。总体而言,情礼关系可以视为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就礼的一个重要起源来说,礼本人情,情礼关系是以情为基础的,后来才逐渐发展出以礼抑情、重礼轻情的倾向。“就基本倾向而言,中国伦理思想史是重理抑情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尽管其中有不少思想家重视具体道德实践中情的作用。”[26](38)对于礼(理)的这种主导地位,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道德生活的实践层面,都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挑战。明代大礼议便是情礼之辨这一重要论题在政治实践层面的展开,是研究情礼关系的一个极佳的历史案例。通过梳理议礼双方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分歧、分析双方的论证方法,我们清楚地看到,明代政治精英如何处理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道德理性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及传统道德哲学的运思方式和认知方式是如何深入地影响明廷的政治和当时人的生活的。
只有理解传统,才能利用传统,将丰富的传统道德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为今人所用。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挖掘传统的道德规范乃至研究某些重要思想家的伦理思想的层面。古人云“道不远人”,深入研究古代道德实践的典型案例,检讨古人得失,弄清其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作用,或许是更好地利用传统道德文化资源的一种可能途径,也是新时期开展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