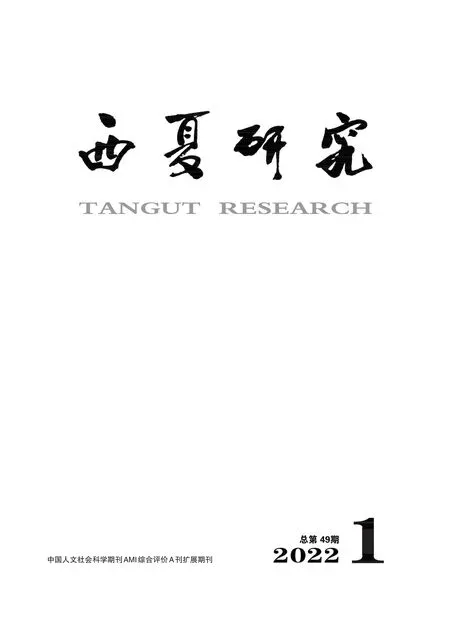契约文书所见清代石羊河流域的水权交易
——民间文书与明清以来甘肃社会经济研究之二
2022-11-21谢继忠毛雨辰
□谢继忠 罗 将 毛雨辰
清代石羊河流域主要包括甘肃古浪、武威、永昌、镇番(今甘肃民勤县)四县。在甘肃武威市档案馆和永昌县档案馆收藏的清代契约文书中,有11份土地水利契约,最早为康熙四十六年(1707)王家栋、王良栋、王朝栋立“绝卖庄田房屋永远契”,最晚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登魁“出典田地文契”,时间跨度近200年。这些契约文书对认识清代石羊河流域的水利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清代石羊河流域水利社会的研究中,王培华研究了清代黑河和石羊河流域的水利纷争与水资源制度[1],钱国权研究了清代河西走廊的水利制度和技术[2],李并成研究了清代河西地区“水案”史料[3],潘春辉研究了政府应对水利纠纷的措施[4],魏静研究了清代河西地区的水利碑刻及其社会功能[5],张景平、王忠静研究了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的国家与信仰[6]和河西走廊水资源管理中的政府角色演进[7],谢继忠研究了明清时期石羊河流域的水利开发与水利管理[8]。
在上述研究中,很少涉及水权问题。水权问题在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史研究中是一个核心问题。在以往的方志等史料中,对水权的记载很少。本文主要依据新发现的契约文书,对清代石羊河流域的水权交易进行探讨。
一、清代石羊河流域水权交易的类型
一般而言,在中国古代社会,水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而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归私人所有。清代石羊河流域的水权交易,就是指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的交易。清代石羊河流域的水权交易主要有水权买卖、水权出典与转典、水权归并、水权出租等类型。
(一)水权买卖
水权买卖,是指土地一次性买断的同时,水权也随之买断,交易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地,一买两清。在新发现的甘肃武威与永昌契约文书中,一般都是“绝卖”,在契约文书中通称“杜绝卖”、“绝卖”。所谓“绝卖”,就是把土地和水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一次性买断,买卖双方从此再无瓜葛。
例1 康熙四十六年(1707)王家栋、王良栋、王朝栋“绝卖庄田房屋永远契”
立杜绝卖庄田房屋永远契书人王家栋、(王)良(栋)、(王)朝(栋)因缺使用,今将自置中坝小庄壹处、田地贰分、水壹昼夜,其地东至周家地,南至本坝,西至陈家地,北至大北坝,四至分明,无力耕种,兄弟同商议,托中说合,情愿绝卖于本卫监生张生名下,永远长久为业,凭中言定,卖价系银共柒拾肆两叁钱整,当交无欠,除酒食画字银在外。自此之后,葛藤根断,再无不明等情,任凭买主修理为业,永不与王姓相干,若有房亲人等争论,良栋等一面承当。恐后无凭,立此绝卖契书存照。(画押)
王家栋 画字艮三钱(画押)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立绝卖庄田人
(王)良(栋) 画字艮三钱(画押)
(王)朝(栋) 画字艮三钱(画押)
同中人(略)
代书人 何新民 画字艮(银)三钱(画押)[9]
这份契约表明,王家栋、王良栋、王朝栋自置田地二分,“绝卖于本卫监生张生名下”,卖价银共七十四两三钱,水权“壹昼夜”,土地与水权同时卖断,属“绝卖”文契。
例2 康熙六十一年(1722)周文学、周文举“绝卖庄田房屋永远契”
立永远杜绝卖庄房田地书契人周文学、(周文)举因乏使用,今将自己祖置中坝所下周文玉田地一角,承纳官粮壹石贰合五抄并草,随地水叁个时辰,庄内房西南壹角土房贰间,上堂屋西南半间,门窗俱全,大圈壹个,随带门壹合,小圈壹个,前后道路通行,庄外涝池壹角,西南白杨树伍棵、坟园树壹棵在外。
兄弟商议,央中说合,情愿绝卖于张世俊名下,永远居住布种为业,同中得受卖价系银壹百两整。除酒食画字银在外,当交无欠,不少分文。其地上段南至本坝,北至下横沟,东至周文英地直垦(埂),西至王定国地。中段庄北面菜地壹块。下段南至本地斜沟,北至大北坝,东至周文英地直沟,西至王定国地,四至分明。自卖之后,葛藤根断,永无缠绕。此系文学兄弟自己情愿,并无准折逼勒等弊,日后若有房族人等争论者,文学兄弟一面承当。恐后无凭,立此永远杜绝卖文契存照。(画押)
周文学 画字银壹钱(画押)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十九日立永远杜绝卖契书人
(周文)举 画字银壹钱(画押)同中人(略)
中书人 柴映秀 画字银伍钱(画押)[10]
这份契约表明,周文学、周文举将祖置田地一角,“绝卖于张世俊名下”,卖价银一百两,水权“叁个时辰”,水权随土地一次性“绝卖”。其特点是“自卖之后,葛藤根断,永无缠绕”。
例3 乾隆五年(1740)陈朝相、陈朝英、陈朝俊等“绝卖庄房田地文契”
立杜绝卖庄房田地文契人陈朝相、(陈朝)英、(陈朝)俊侄怀德、月德等因为缺少使用,今□父置中坝周文玉田地壹角,承粮壹石弍合五勺并草,随地正水照粮分浇。房屋壹间半。无力耕种,情愿出卖与焦名下,永远布种为业、承粮应差,凭中言明,得受卖价系银玖拾柒(缺“两”)整,其银当交无欠,自卖之后凭意卖(应为“买”)主安茔立业筑打庄园,葛藤两断,永远为业,并不与陈姓丝毫相干。若有房族异姓亲䜹人争论,朝相等兄弟子侄五人一面承当。恐后无凭,立此杜绝卖庄房田地葛藤两断文契为照。(画押)
胡永福(画押)
中亲地邻人 傅好玉(画押)
周文英(画押)
陈月德(画押)
陈朝英(画押)
乾隆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立绝卖庄房田地文契人
陈朝相(画押)
陈朝俊(画押)
陈怀德(画押)
书契人 陈朝俊亲笔(画押)[11]
这份契约表明,陈朝相、陈朝英、陈朝俊与侄月德、怀德共同拥有的“田地壹角”,出卖与焦姓名下,其中虽然没有标明水权“几昼夜”或“几个时辰”,但却有笼统的水权表述,即“随地正水照粮分浇”。
例4 光绪十三年(1887)陈际雍“绝卖田地水利文契”
立永远绝卖田地水利文契人陈际雍因为耕种不便,今将祖遗应分上北山上坝庄科水田地壹块,约下种籽壹石贰斗;地下田地壹块,约下种籽肆斗。其地四置:东至东直沟为界,西至西直沟为界。下壹块,西至张姓和垦为界,南至王姓使水横沟为界,北至坝沿。又与烂七斗田地壹块,东至西直沟为界,西至沙缕直沟为界,南至陈姓使水横沟为界,北至坝沿,四置分明,前后沟渠道路通行,水随坝例浇灌,共地叁块,共约下种籽贰石叁斗,共承纳官粮肆斗,央中说合,情愿出绝卖与坝邻赵垾城名下,永远经理耕种为业,同中言明,照时估作得受卖价制钱陆拾玖千文整,当中交清,并不短欠,自卖之后,凡有官粮草束差务,有赵姓一面承当,不与陈姓相干,倘有房亲户族及异姓人等争论者,有陈姓一面承当,不与赵姓相涉。恐后无凭,立此绝卖文契为证。(画押)
说合人 何正兴(画押) 画字钱贰佰文
代书(人) 陈世俊(画押)
陈际虎(画押)
王经国(画押)
同中亲 雷凤鸣(画押) 画字钱五拾文
张伯卿(画押)
王修礼(画押)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 日立永远绝卖田地水利文契人 陈际雍(画押)
同胞叔 陈衡元(画押)画字钱 五百文
同堂兄 伯英 (画字钱)五百文[12]
这份契约表明,陈际雍将三块土地“绝卖与坝邻赵垾城名下,永远经理耕种为业”,其中关于水权交易的内容,则表述为“水随坝例浇灌”。
上述4份契约,前后延续了180年,说明清代石羊河流域的土地买卖以“绝卖”为主,即一次性买断,“葛藤两断,永远为业”;也未见多次“找价”等情形,这与安徽徽州等地土地买卖有很大的差异。
(二)水权出典与转典
水权出典,即是指随着土地的出典,水权同时出典。所谓“典”是指出典人保留土地和水权的所有权,仅“出典”土地和水利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承典人要向出典人缴纳一定的“典金”。土地和水权出典,必须立契约,一手交钱,一手交地,契约才能成立。立契后,双方不能反悔,因在契约上有中人画押并见证,这就保证了契约的信用。有学者认为,“典”是一种“活卖的形式”。杨国桢认为,“债务人直接以土地在一定期限内的经济收益抵算利息,交由债主掌管收租,谓之典”,“当,是在典的基础上,每年另加纳粮银若干”,“土地在出典、出当期间,典主、当主有使用权、处分权,可以自种或招佃收租,或原主耕作纳租,或转典于他人。这样,典当土地与活卖土地已经没有多大差别,实际上是活卖的一种形式”[13]27—28。
例5 乾隆二十四年(1759)陈桂芳、陈玉芳“立典庄房田地场圃文约”
立典庄房田地场圃文约人陈桂芳、(陈)玉(芳)因为缺乏使用,今将祖遗中坝十九牌陈所应田地壹角,约下种籽叁石捌斗,随地正水叁个时辰,承纳官粮柒斗壹升并草,其地南至本坝岸,西至本家伏德地界,东至焦姓地界,北至本庄,四至分明。庄北地贰段,约下种籽壹石伍斗;庄南地贰段,约下种籽壹石贰斗;顶坝岸地贰段,约下种籽壹石贰斗,内有垡地捌斗,其庄西南壹角坐西向东土房贰间,庄外窗壹个、场壹角,前后道路沟渠通行,兄弟议妥,央中说合,情愿出典于王名下为业,同中得受典价银肆拾两整,当交无欠。自典之后,任意典主修理耕种,渠坝差徭典主一面承当,并不与原主相干,日后有银赎取,无银不拘年限,如有修损验工、增迭地水、庄房,倘有不明,以及房亲族姓人等争论,桂(芳)、玉芳一面承当。恐后无凭,立此典约为照。(画押)
同中人 张应举(画押)张洁士(画押)王秉肃(画押)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 立典房屋田地场圃人约人 陈桂芳(画押)
陈玉芳(画押)
同堂祖 陈朝英(画押)
叔 陈合德(画押)陈伏德(画押)陈茂德(画押)[14]
这份契约表明,陈桂芳、陈玉芳祖遗的七石七斗土地(以下种籽计算)及其房屋等,出典与王姓名下,“典价银肆拾两整”,水权为“叁个时辰”,水权同时转移,承典人承担官粮草、渠坝差徭等义务,并约定“日后有银赎取,无银不拘年限”。可以赎取,正是这类典约的特点。
所下种籽数量与土地面积的换算,可以参考清代甘肃肃州的资料。据《屯田条例》载“雍正十一、二年,总督刘公与侍郎蒋公上议”:“所下籽种,因土地厚薄,每亩多寡不同。小麦则每亩一斗六、一斗四、一斗二以至八九升不等。青稞、豆照依小麦。糜子则每亩五、六、七升不等。粟谷则颗粒尤细,每亩一、二升不等。”[15]87若以小麦计,取中间数每亩种籽一斗二升,那么一石地的面积应在八亩二左右。由此推算,例5 七石七斗土地的面积应有五十八亩左右,每亩典价约0.69两。
例6 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登魁“出典田地文契”
立出典田地文约人王登魁,因为务(无)力耕种,金(今)将大渠碱滩沟西沟三畦应分祖遗科地二段,约下籽种一石三斗整,当中言明,其地四至:东至水沟,西至老垦,南至老愤(坟),北至老坟,四至分明,道路通行,用使本沟泉水二刻一厘,山水照地浇灌,承纳官粮九□八升五合,官草六束五分。央中说妥,请愿出典与谪议宝号、天裕生号下,典价纹银七十两整,当中得受,至典之后,所有差法门役挑河垒坝,典者□□,不与业主相干,有银赎去,无□□拘年限。恐后无凭,立典约为证,□□存照。(画押)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立此典约人王登魁(画押)
同中人 王春魁(画押) 顾永德(画押)[16]
出典或转典,不同于买卖契约之处,是出典人享有收回的权力,即“有钱赎回,无钱不拘年限”。杨国桢认为“清代各地广泛存在的‘转租’、‘转顶’、‘转典’、‘转佃’等地权转移形式,在多数情况下,都属于佃户之间‘私相授受’的行为。这些都是从永佃权向‘一田两主’过渡的中间形态”[13]83。
例7 乾隆二十八年(1763)吴贵卿“转典田地水利文约”
立转典田地水利文约人吴贵卿因为无力耕种,今将原典站家牌陈月、李进斈田地弍半分,约下种籽三石余,随地正水一昼夜,承纳官粮一石零五升并草,其地大小一十一段,各有四至,央中说合,情愿转典与张名下布种为业,得受典价系银一十二两整,当交无欠,自典之后,任凭张姓布种,不与吴姓干涉,渠坝差徭张姓一面承当,有银赎取,无银不拘年限。倘有房亲暨异姓人等争论,吴姓一面承当。欲后有凭,立此转典田地文约为照。(画押)
此地内并无冬水。
中人 陈献可(画押) 张立修(画押) 吴尚卿(画押)
同原主 陈封可(画押)
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立转典田地水利文约人吴贵卿(画押)[17]
这份典约名为“转典”,即吴贵卿的三石土地,转典与张姓耕种,“随地正水一昼夜,承纳官粮一石零五升并草”,一并转典至张姓名下,“有银赎取,无银不拘年限”。所谓“转典”,实际上出现了二次出典的情形,即这块土地及其水权是由站家牌陈月、李进斈典与吴贵卿,再由吴贵卿典与张姓,等于说倒手两次。这在当时的民间习惯法中是被认可的。
例8 雍正二年(1724)张毓奇“转典田地文约”
立转典田地文约人因缺使用,今将原典中坝陈朝相田地半角,特转典与王名下耕种为业,凭中言明得受典价系银壹拾柒两整,当交无欠,并不短少。其地南至本坝,北至大坝,西至王定国,东至本地,四至分明,道路通行,其地约下籽种贰石五升,承纳官粮五斗壹合五勺并草,渠坝差役照粮均当,其水亦照粮均浇,日后若有地水不明,毓奇一面承当。恐后无凭,立典约存照(画押)。
其地冬水五斗(画押)。
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立转典田地文约人张毓奇(画押)
中人 庞一统(画押) 陈朝相(画押) 周文玉(画押)
柴圣云(画押)
同叔 张世英(画押)[18]
这份典约表明,张毓奇的二石五升土地,典自陈朝相,又转典与王姓耕种,其水权随之转典出去,即“渠坝差役照粮均当,其水亦照粮均浇”。这种“转典”与江浙地区的“一田两主”性质相同。正如杨国桢所说,“从永佃权向‘一田两主’的转化,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其一般规律是:“即从‘私相授受’佃耕的土地开始,经过田主承认‘佃户’的田面权但不准自由转让的初级形态,到‘佃户’获得转让田面权的完全自由,并形成‘乡规’、‘俗例’,得到社会的公认。这也是明清时期地权分化的发展趋势。”[13]88
(三)水权归并
在石羊河流域,土地与水权交易的特点是“水随地走”,因此水权的归并与土地的归并也是“合二为一”的,虽名为归并,但实际上与“出典”无异。
例9 乾隆二十四年(1759)陈良策归并田地水利文约
立归并田地水利文约人陈良策因军需频繁,无力耕种,同子德耀、德枢商议妥确,今将站家牌祖遗应分李得朝田地半分,水半昼夜,承纳官粮六斗七升并草,央中说合,情愿归并与胞弟陈良术名下布种为业,凭中得受归并价银六十五两整,当交无欠。自归并之后,其地渠坝差徭官粮草束,胞兄一应完纳,不与良策干涉,同中言明,日后若有银两,许良策归赎,无银不拘年限。恐后无凭,立此归并文约存照。(画押)
同中亲人 张得本(画押) 张如龙(画押)王铭(画押) 张国琏(画押)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七日立归并文约人陈良策(画押)
子 陈德耀(画押) 陈德枢(画押)
同族祖 陈侯抒
同叔父 陈兆玖[19]
这份契约表明,陈良策及子德耀、德枢把半分田地归并与胞弟陈良术名下,“归并价银六十五两整”。归并之后,陈良术享有“水半昼夜”的水权,“承纳官粮六斗七升并草”及其地渠坝差徭。同时约定,“日后若有银两,许良策归赎,无银不拘年限”,故这份契约又具有“出典”的特点。
例10 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材年归并屯田地文契”
立永远归并屯田地文契人陈材年,今将自己应分怀二坥花寨畦冲子沟屯地庄子北墙地四摆,约下籽种玖斗五升,外承纳官粮捌斗弍升伍合,税草捌束弍分。其地四至:东至直沟,南至使水沟,西至顺年和垦,北至三坥南河沿,四至分明,道路通行,水列(例)随畦浇灌,差徭案(按)粮均当。情因无力耕种,父子商议妥确,情愿央中周念祖来往说合,归并与堂侄陈铠名下耕种为业。当中三面言定,每斗估作价银弍两伍钱,共银弍拾叁两柒钱伍分,外升酒食画字银壹两肆钱弍分伍厘,共三项银弍拾伍两一钱七分伍厘,当中交足,并不短分少厘丝毫。自归并之后,任凭置主栽培树株、筑打庄院、修立坟茔,亦不与失主丝毫相干,恐后无凭,立此归并文契为证,是实存照。
同子 金泉子(画押)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立永远归并文契人 陈材年(画押)
代书人 吴光耀(画押)
同中人沟邻户族人 陈锐(画押) 马得名(画押)
周念祖(画押) 陈顺年(画押)
陈均(画押)[20]
这份契约表明,陈材年将自己的九斗五升土地,“归并与堂侄陈铠名下耕种为业”。这里的“归并”,没有“赎回”的约定,故其性质同“买卖”,其价格是“银弍拾伍两一钱七分伍厘”。
(四)水权出租
土地与水权的出租也是“合二为一”的,出租不涉及土地与水权的所有权,它只是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出让,承租人是新地主,所有官粮草束和差徭等义务一并转移到新地主名下。
例11 道光二十八年(1848)杜长山承租庄房田地水利文约
立承租庄房田地水利文约人杜长山今租到焦伯选名下金龙坝石小庄田地一处,约下种籽三十余石,其地四至俱以典约为凭,同中言明,本年不出租资,自二十九年起每年出备租粮小麦四石,绝不短少。自承租后,凡有官粮草束渠坝差徭以及兵车,杜长山一应承当,约以六年为满。欲后有凭,立此文字存照。(画押)
(中缝)合同为证
同中人 谢博如(画押) 南崇之(画押) 杜毓兰(画押)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立承租田地水利文约人杜长山(画押)[21]
这份契约表明,杜长山租种焦伯选名下金龙坝石小庄三十余石田地,“不出租资”,从康熙二十九年起“出备租粮小麦四石”,这里的租金是以小麦作为等价物的,“官粮草束渠坝差徭以及兵车,杜长山一应承当”,租期为六年。从中可见,水权随着土地一并出租。
二、清代石羊河流域水权交易的特点
清代石羊河流域水权交易契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水随地走”,地水“合二为一”
由于石羊河流域气候干旱,降水稀少,昼夜温差大,武威(清代凉州)年降水量在60—610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1400—3010 毫米;永昌(今属甘肃金昌市)年均降水量173 毫米,年均蒸发量达2067毫米。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农作物的生长主要靠灌溉,如果没有石羊河的水利灌溉,就没有农业,土地也就失去了价值。嘉庆《永昌县志》“永尽水耕,非灌不殖”[22]就是最好的概括。因此在清代石羊河流域的土地交易契约中,内在地包含着水权交易的内容,如上述11 例契约中,都有水权交易的内容。在土地交易的四种类型中,土地买卖、土地出典与转典、土地归并、土地出租都伴随着水权买卖、水权出典与转典、水权归并、水权出租,二者是“合二为一”的,故可将这一特点归纳为“水随地走”,如例1的“水壹昼夜”、例2的“随地水叁个时辰”、例3的“随地正水照粮分浇”、例4的“水随坝例灌溉”、例5 的“随地正水叁个时辰”,这种情形在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流域、黑河流域、疏勒河流域极为普遍,从清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二)水权与赋税、渠坝差徭一体化
特定土地水权是农户享有的特殊权利,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有其承担的义务,权利—义务体系构成了水权的系统,可称之为水权与赋税、差徭一体化。如果只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会使水权失去意义。
在上述契例中,水权的表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时间水权的表述,如例1的“水壹昼夜”,例6的“用使本沟泉水二刻一厘,山水照地浇灌”,例7的“随地正水一昼夜”,例9的“水半昼夜”。另一种是对水权的概括表述,如例4 的“水随坝例浇灌”,例8“承纳官粮五斗壹合五勺并草,渠坝差役照粮均当,其水亦照粮均浇”,例10 的“水列(例)随畦浇灌”。例4、例10 没有确指时间水权“几个昼夜”“几个时辰”,是因为作为水权交易的当事人各方以及中人、族人、沟邻等见证者,都明白所交易土地的时间水权应是“几个昼夜”或“几个时辰”,并不因为契约中书写“水随坝例浇灌”而带来误解,或在具体灌溉过程中难以落实,可以说,这已经形成了“俗例”,并为各方所理解和接受。
同时,上述契例都明确表明,赋税完纳、渠道维护、差徭及其他义务,在办理完交收过割手续之后,原主不再承但。也就是说,随着土地、水权的转移,所有的义务都由买主、承典人、承租人等所承但。如例3陈朝相、陈朝英、陈朝俊等的一块土地,“承粮壹石弍合五勺并草”,“情愿出卖与焦名下,永远布种为业、承粮应差”;例4陈际雍的三块土地,“共约下种籽贰石叁斗,共承纳官粮肆斗”,“自卖之后,凡有官粮草束差务,有赵姓一面承当,不与陈姓相干”;例5陈桂芳、陈玉芳的一块土地,“承纳官粮柒斗壹升并草”,“自典之后,任意典主修理耕种,渠坝差徭典主一面承当,并不与原主相干”;例6王登魁的二段土地,“承纳官粮九□八升五合,官草六束五分”,“至典之后,所有差法门役挑河垒坝,典者□□,不与业主相干”;例7吴贵卿的半分土地,“承纳官粮一石零五升并草”,“自归并之后,其地渠坝差徭官粮草束,胞兄一应完纳,不与良策干涉”;等等。由此可见,水权交易已经形成了由权利—义务构成的水权体系。这也是我们理解清代石羊河流域水权交易的重点所在。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例11杜长山租种焦伯选名下金龙坝石小庄三十余石田地,应该包括水权。一方面是契约中有“官粮草束渠坝差徭以及兵车,杜长山一应承当”的约定,这本身就包含了使用水权而必须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没有在契约中表明水权“多少昼夜”或“多少时辰”,是因为出租人、承租人和中人等都清楚这块土地的灌溉水权,把灌溉水权省略,并不影响承租人享有水权的使用权,应当说这是当地的又一种习惯。
(三)遵循“亲邻优先”的原则
在清代至民国,河西走廊水权交易中一直遵循“亲邻优先”原则,即先问亲邻,如亲邻放弃优先权,才能同其他人交易。
清代,石羊河流域水权交易中享有“优先权”的,主要是坝邻和宗族内成员,如例4陈际雍的三块土地,“情愿出绝卖与坝邻赵垾城名下,永远经理耕种为业”;例9陈良策的半分土地,“情愿归并与胞弟陈良术名下佈种为业”;例10 陈材年的一块土地,“归并与堂侄陈铠名下耕种为业”。
(四)信用意识不断强化
从康熙四十六年(1707)王家栋、王良栋、王朝栋“杜绝卖庄田房屋永远契”,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登魁“出典田地文契”,时间跨度近200年。在两个世纪的时间内,石羊河流域的水权交易秩序保持稳定,一方面是因为普遍签订契约,且契约的订立本着“自愿”原则,这就有效约束了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契约签订过程中,“中人”发挥了见证作用,如果一旦有人违约,那么就会丧失“信誉”,他就无法在“熟人社会”中立足。与此同时,官府的介入也为契约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如例1、例2皆为“红契”,既是政府纳税的凭据,又是官方对契约认可的法律依据。如果一旦出现纠纷,这就是最可靠的法律依据,这都强化了人们的信用意识,也为契约的履行提供了有力保障。故大量水权交易契约的存在,表明石羊河流域人们信用意识在不断强化,这是清代河西走廊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结 语
综上所述,清代石羊河流域的水权交易主要有水权买卖、水权出典与转典、水权归并、水权出租等类型。水权交易的特点主要有:“水随地走”,地水“合二为一”;水权与赋税、渠坝差徭一体化;遵循“亲邻优先”的原则;信用意识不断强化。这些特点是西北内陆干旱区水利社会的基本特点。如果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特点对民国时期河西走廊水利社会秩序的运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至少一直延续到20 世纪40 年代末。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石羊河流域、黑河流域、疏勒河流域水利社会既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同时又出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型,对此还需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