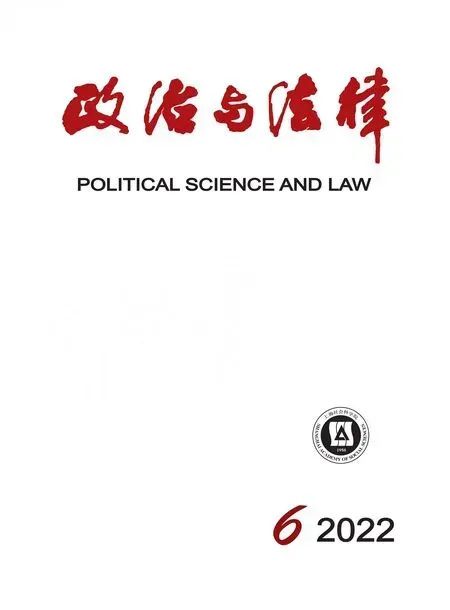准强奸罪的定性研究
2022-11-21陈兴良
陈兴良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强奸罪是各国刑法通常都规定的罪名。当然,各国刑法对强奸罪的规定存在某些差异。我国刑法设立了单一的强奸罪罪名,并且根据强奸手段不同而区分为暴力或者胁迫手段的强奸罪和其他手段的强奸罪。其中,暴力或者胁迫手段的强奸罪属于普通强奸罪,而其他手段的强奸罪属于准强奸罪。有些国家的刑法则对普通强奸罪和准强奸罪分别设置罪名。笔者拟对其他手段的准强奸罪的定性问题进行刑法教义学的研究。
一、准强奸罪的特征与分类
根据我国《刑法》第236 条的规定,强奸罪具有三种行为类型,即以暴力为手段的强奸罪、以胁迫为手段的强奸罪和其他手段的强奸罪。从刑法规定来看,前两种强奸罪的手段内容是明确的,这就是暴力和胁迫,第三种强奸罪的手段内容则具有概然性,这是因为立法机关采用了空白规定的立法方式。
在世界各国刑法中,强奸罪是妨害性自主的犯罪,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强奸罪修改为强制性交罪,主要目的是将强奸罪的主体由男性扩张到妇女,强奸罪的客体则由妇女扩张到男性。例如,日本在2017 年6 月23 日法律第72 号将强奸罪修正为强制性交罪。当然,在日本刑法中强制性交罪的主要案件类型还是强奸妇女。为表述方便,笔者于本文中对其他国家刑法中的强制性交罪仍然称为强奸罪。各国刑法关于强奸罪的罪名设置,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立法例。
第一种立法例是除了强奸罪的基本罪名之外,同时设立补充罪名。例如《日本刑法典》第177 条规定的普通强奸罪,是指以暴力或者胁迫手段奸淫13 岁以上女子的行为,这是强奸罪的基本罪名,其强奸手段限于暴力和胁迫。此外,《日本刑法典》第178 条第2 款又规定了准强奸罪,是指乘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或者使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而奸淫的行为。由此可见,普通强奸罪与准强奸罪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强奸手段的不同:普通强奸罪的手段是暴力或者胁迫,而准强奸罪的手段是乘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和使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这里的“乘”是指利用既存之状态,其造成心神丧失或不能抗拒状态的原因则非所问;“使”是指采用某种手段造成心神丧失或不能抗拒,至于何种手段则并无限制。由此可见,《日本刑法典》对准强奸罪的手段并未予以明确描述,而是对该种手段所造成的结果状态做了规定。这种手段模糊化而结果明晰化的规定方法,有利于对准强奸罪的行为方式进行实质判断。
第二种立法例是设立单一的强奸罪名,但在暴力或者胁迫手段以外,同时规定了其他手段的强奸罪。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13.1 条规定了强奸和相关犯罪,指出:“男性与不是其配偶的女性性交,存在下列情形时,构成强奸:(a)行为人以武力或者以即将造成的任何人死亡、严重身体伤害、极度痛苦或者实施绑架相威胁,致使该妇女屈从;或者(b)行为人在该女性不知晓的情况下,通过使用药物、致醉物或者令该女性不能抵抗的其他手段,实质减弱该女性对自己行为的理解或者控制能力;或者(c)该女性处于无意识状态;或者(d)该女性不满10 岁。”以上列举的强奸行为,属于强奸罪的基本情形。〔1〕参见刘仁文、王祎:《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2 页。在上述条文中,(a)规定的是暴力或者胁迫的普通强奸罪;(b)规定的是暴力或者胁迫以外的其他手段的准强奸罪。在(b)规定的准强奸罪中,除了列举使用药物、致醉物以外,还规定了令该女性不能抵抗的“其他手段”。我国学者指出:“这里所谓的其他手段,并非指上述类型尚未穷尽的某一具体强奸手段,而是指一种表述方式,即用‘其他’一词来概括没有被列举到的任何强奸手段。”〔2〕郑伟:《刑法个罪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01 页。也就是说,这里的其他手段不属于前面所列举的使用药物、致醉物手段之未穷尽的手段,而是指与之并列的其他强奸手段。尤其是在这里的其他手段之前加上“令该女性不能抵抗”这一限定词,对于正确界定其他手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上述两种强奸罪的立法例中,我国刑法显然是采用第二种立法例。对比两种强奸罪的立法例可以发现,第二种立法例中的强奸罪实际上包含了第一种立法例中的普通强奸罪和准强奸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将第二种立法例中其他手段构成的强奸罪称为准强奸罪。在上述两种立法例中可以看到,第一种立法方法对于两种强奸罪的手段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明确,可以为司法认定提供更为具体的操作规则;第二种强奸罪的立法方法在明文列举暴力或者胁迫后,对于其他手段并没有具体描述,而是采取了一种兜底条款的规定方法,不利于司法机关掌握这种准强奸罪的司法认定标准。
那么,如何界定强奸罪的其他手段呢?笔者认为,对于强奸罪的其他手段只有通过刑法的同类解释的方法才能予以明确。兜底条款是我国刑法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立法方法。我国学者指出:“兜底条款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在立法者无法穷尽法条需描述之情形时所采用的概括条款,通常用‘其他……’或者‘等’等表述方式。”〔3〕马东丽:《我国刑法中兜底条款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7 页。由此可见,兜底条款一般都是以概括规定的形式呈现的,由此将那些立法者无法穷尽的事项全部予以涵括。兜底条款使刑法规定具有一定的解释空间,实际上是立法机关将进一步明确某项法律规定内容的权限让渡给司法机关。在我国刑法中,兜底条款是以列举性规定为前置内容的,在这个意义上的兜底条款并不是完全的空白规定,而是具有框架立法的特征。框架立法是指原则性或者概然性的立法方法,相对于精细立法而言,框架立法当然是粗疏的,但它毕竟为兜底条款的解释提供了某种参照依据,因而兜底条款的内容并非完全无迹可寻。我国学者认为兜底条款具有对列举规定的附随性特征,指出,“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和立法者预见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立法者无法穷尽可能发生的一切事实并对其进行类型化的逐一列举。兜底条款的设置,是为了严密刑事法网,弥补列举性规定不周延的缺陷,防止将列举性规定以外的法益侵害行为遗漏于构成要件之外。兜底条款总是附随于列举性规定出现在构成要件中,这就决定了兜底条款具有附随性的特点,不可能脱离列举性规定而独立存在”。〔4〕张建军:《刑法中不明确概念类型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194 页。因此,对兜底条款的解释就必须以列举规定为依归,这就是同类解释的真谛之所在。
同类解释是指如果法律上列举了具体的人或物,然后将其归属于“一般性的类别”,那么,这个一般性的类别,就应当与具体列举的人或物属于同一类型。〔5〕参见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315 页。同类解释不是孤立地对某个法律词语做出语义解释,而是强调概念的体系化,尽可能避免概念含义的冲突。在同类解释中,将一定的法律概念置于特定的法律语境中,以明确的法律规定为根据对模糊的法律规定进行解释,使其获得明确的含义。因此,同类解释采用的是一种归类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同类解释是以一定的类型性思维为基础的。我国学者杜宇曾经提出合类型性解释的概念,认为对规范意义的探寻,必须回溯到“作为规范基础之类型”,对超出类型轮廓的行为,则应予以排除。〔6〕参见杜宇:《刑法解释的另一种路径:以“合类型性”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5 期。规范背后的类型是合类型性解释的根据。在兜底条款的情况下,刑法条文的规范内容分为两部分,这就是列举与其他。列举是已知部分,而其他是未知部分。例如我国刑法对强奸罪方法的规定是“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其中,“暴力、胁迫”的内容是确定的,“其他手段”的内容则是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脱离了暴力、胁迫,对其他手段的任何理解都是偏颇的。对这里的“其他手段”就应当采用同类解释的方法。同类解释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类比解释,类比解释是在两个事物(基准点与问题点)之间采用对比的方法,寻找相同点,以此为前提,将适用于基准点的法律规定及于问题点。因此,类比解释是解决具有类似关系的事项的法律适用问题。然而,在兜底条款的情况下,并不存在这种类似关系,而是存在确定规定与模糊规定之间的关系。从兜底条款中唯一获取的信息是:模糊规定应当具有与确定规定性质上的同一性。这种性质上的同一性是通过类比方法无法辨别的,只能采用合类型性的思维方法。根据这种合类型性的解释,首先应当探寻一定的规范类型,然后根据这一规范类型将模糊规定的内容清晰化。例如,在强奸罪兜底条款的解释中,不能直接从暴力、胁迫推导出其他手段,而是应当穿越法条的语言屏障,提炼出该语言背后的规范类型。暴力是一种物理强制,而胁迫则是一种精神强制,因而暴力和胁迫的本质就在于对妇女实行强制,利用这种强制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是违背妇女意志的。暴力、胁迫背后的规范类型就是违背妇女意志的手段。基于这一理解,刑法所规定的其他手段应当符合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质。也就是说,只有具有违背妇女意志性质的方法才能归属于强奸罪的其他手段。因此,暴力和胁迫只是事物的表象,事物的本质是违背妇女意志。违背妇女意志虽然不是刑法条文所规定的内容,但它是从我国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中推导出来的强奸罪的本质,也是强奸罪的规范类型的应有之义,它对于解释强奸罪的其他手段具有直接的制约性。我国学者张明楷在论及同类解释时,对刑法中的同类关系进行了分类,其中包括行为时的强制性的同类,这就是其他手段或者其他方法。张明楷指出:“根据同类解释规则,这里的其他方法仅限于与其前面列举的暴力、胁迫的强制方法作用相当的方法,而非泛指一切其他方法,否则必然扩大处罚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显然,按照同类解释规则进行的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类推解释存在本质区别。因为同类解释是对刑法所规定的‘其他’、‘等’内容的具体化,而不是将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以犯罪论处。”〔7〕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60 页。因此,通过同类解释获得的强奸罪暴力、胁迫以外的具体方法,具有与暴力、胁迫性质上的相同性,它属于刑法本来之意,而不是额外添加的法外之意。
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本质,它为界定强奸罪的其他手段提供了基准。违背妇女意志是刑法所没有明文规定的,因此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是否将违背妇女意志确定为强奸罪的本质是存在争议的,主要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否定说认为,强奸罪的客观要件是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性交。违背妇女意志不应作为强奸罪的要件,强奸罪的要件应严格执行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8〕参见谢慧:《违背妇女意志不应该作为强奸罪的构成要件》,载《政治与法律》2007 年第4 期。肯定说则认为,奸淫是强奸罪的结果(目的)行为,而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是其手段行为。由于强奸罪的保护法益是妇女的性的自己决定权(性自主权),而妇女是否同意性交,或者说性交行为是否违背妇女的意志,成为是否侵犯妇女的性的自己决定权的表征,因此,强奸罪的手段行为的意义在于表明奸淫(性交)行为是在违背妇女意志的情况下实施的。既然如此,违背妇女意志应为强奸罪的本质特征。〔9〕参见胡东飞、秦红:《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兼与谢慧教授商榷》,载《政治与法律》2008 年第3 期。上述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违背妇女意志与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之间的关系。否定说将违背妇女意志简单地理解为妇女是否愿意发生性关系,只要在妇女不愿意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实施性交行为,就认为是违背妇女意志的,而不考虑客观上是否存在强制手段,因而认为强奸罪不应当以违背妇女意志为构成要件,只要具有强制行为就能成立。肯定说则将违背妇女意志作为强制手段的后果,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因而必然得出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本质的结论。笔者赞同肯定说,违背妇女意志虽然不是刑法规定,但它是从刑法规定中抽象和提炼出来的,它与暴力和胁迫手段之间具有表里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为强奸罪其他手段的判断提供参照根据。
从文字表述来看,妇女意志是妇女对性行为的自主性,具有主观的属性。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违背妇女意志之存否完全取决于妇女的主观心理。因为是否构成强奸罪并不单纯取决于妇女的感受,而是应当重点分析妇女被迫发生性关系的客观原因。因此,违背妇女意志这一论断的主体是实施强奸行为的人,而被害妇女则是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性交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并非单方面取决于妇女的主观感受,而在于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暴力或者胁迫等强制手段。笔者认为,在不能将违背妇女意志归于妇女的主观心理状态的同时,也不能将违背妇女意志理解为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例如我国刑法学界存在将违背妇女意志归于主观要件的观点,指出:“当妇女不愿性交时,无论是谁,强行与之性交都是违背妇女意志的表现。因此,可以将强奸罪中的违背妇女意志表述为违背妇女对性交出于内心自愿的心理态度,即明知自己未获对方同意而强行与之性交的心态,故我们应当将违背妇女意志理解为主观要件,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性交未获对方同意,而与对方进行性交就是违背妇女意志,哪怕对方对性交内心是渴望的情况也不例外。”〔10〕梁健:《强奸犯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67 页。这种观点将违背妇女意志看作是行为人的主观要件,明显不妥当。违背妇女意志是采用强制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一种客观状态,这种客观状态真实地反映了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对于把握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按照这一思路理解刑法所规定的暴力和胁迫等强制手段与违背妇女意志之间的关系,强制手段是原因,违背妇女意志是结果。因此,通过强制手段之原因确定违背妇女意志之结果,可以说是一种从原因探求结果的分析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一种以不同意代替违背妇女意志的观点,认为应当在强奸罪的认定中引入同意制度,指出:“性自治权是性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因此,‘拒绝’或说‘不同意’也就成了性侵犯罪的本质特征。从概念表述上看,‘不同意’比‘违背妇女意志’这种说法更具准确性和规范性。‘违背意志’一说不符合法学用语的规范性,它更多地带有心理学上的内容。”〔11〕参见罗翔:《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从性侵犯罪谈起》,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40-41 页。笔者认为,“不同意”与“违背妇女意志”是两种含义不同的表述:“不同意”的主体是妇女,是否同意取决于妇女的意愿。而“违背妇女意志”的主体是实施强制手段的行为人,其完整表述是指使用强制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
在确定强奸罪的其他手段的时候,应当以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为基准进行衡量。对于强奸罪的其他手段,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曾经规定:其他手段是指犯罪分子用暴力、胁迫以外的手段,使被害妇女无法抗拒。例如,利用妇女患重病、熟睡之机,进行奸淫;以醉酒、药物麻醉,以及利用或者假冒治病等等方法对妇女进行奸淫。《解答》作为司法解释虽然已经失效,但其内容目前仍然被我国司法机关和刑法学界采用。《解答》的上述规定,并不是对强奸罪其他手段的完整列举,且《解答》的规定也存在不够准确之处。例如,《解答》将利用迷信进行欺骗归入胁迫的手段,这并不妥当。根据《解答》的规定,暴力是使妇女不能抗拒的手段,胁迫是使妇女忍辱屈从不敢抗拒的手段。这里涉及强奸罪与妇女抗拒(也称为反抗)之间的关系。应当指出,如果妇女对发生性关系进行了反抗,这表明性关系是违背妇女意志的。然而,不能由此得出妇女反抗是强奸罪构成的必备要件的结论;也就是说,不能认为只有妇女反抗才能证明性行为是违背妇女意志的,更不能将被害人无明显反抗行为或意思表示推定为被害人对性行为表示同意。例如,孟某等强奸案的裁判要旨指出:“对妇女是否同意不能以其有无反抗为标准。由于犯罪分子在实施强奸时的客观条件和采用的手段不同,对被害妇女的强制程度也相应的有所不同,因而被害妇女对强奸行为的反抗形式和其他表现形式也会各有所异,有的因害怕或精神受到强制而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不知反抗。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被害妇女当时有无反抗的意思表示,作为认定是否同意的唯一条件。”〔12〕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826 页。在此,裁判要旨提出了在妇女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考量违背妇女意志的三种标准,即不能抗拒、不敢抗拒和不知抗拒,这对于认定其他手段的准强奸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解答》所规定的不能抗拒和不敢抗拒都是以被害妇女没有反抗为前提的。行为人采用暴力手段实施强奸,该种暴力具有压制被害妇女的性质,例如对妇女进行捆绑,因而妇女处于不能抗拒的状态。行为人采取胁迫手段实施强奸,例如对妇女进行威胁或者恐吓,因而妇女处于不敢抗拒的状态。在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的情况下,例如利用封建迷信谎称发生性关系能够治病,由此妇女对事实发生错误认识,此时被害妇女并不是不敢抗拒而是不知抗拒。因此,不知抗拒是与暴力手段的不能抗拒、胁迫手段的不敢抗拒相并列的第三种情形。可以说,强奸罪的其他手段主要是在妇女不知抗拒的情况下与之发生性关系。
关于强奸罪的其他手段,我国相关指导案例对司法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出其他手段的具体表现,对于我国正确理解强奸罪的其他手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部门在唐胜海等强奸案的裁判要旨指出:“所谓其他手段,一般认为应当包括以下情形:(1)采用药物麻醉、醉酒等类似手段,使被害妇女不知抗拒或无法抗拒后,再予以奸淫的;(2)利用被害妇女自身处于醉酒、昏迷、熟睡、患重病等不知抗拒或无法抗拒的状态,乘机予以奸淫的;(3)利用被害妇女愚昧无知,采用假冒治病或以邪教组织、迷信等方法骗奸该妇女的等。”〔13〕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版,第784 页。在此,裁判要旨在《解答》的基础上概括、充实和明确了准强奸罪的以下三种情形:麻醉型准强奸罪、欺骗型准强奸罪、趁机型准强奸罪。以上三种准强奸罪的共同特征是因妇女不知抗拒、在个别情况下是不能抗拒,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因而具备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强奸罪的本质特征。
二、麻醉型准强奸罪的司法认定
麻醉型准强奸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采用麻醉方法致使妇女丧失知觉而与之发生性关系。因此,麻醉型准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可以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利用药物或者酒精进行麻醉,造成被害妇女丧失知觉的状态,这是手段行为;二是在被害妇女不知抗拒的状态下发生性关系,这是目的行为。
麻醉型准强奸罪与以暴力或者胁迫的强制手段构成的普通强奸罪的构成要件相比,其目的行为都是与妇女发生性关系,这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采用何种手段行为实现该目的。在此,应当考察麻醉手段与暴力和胁迫的强制手段之间是否具有性质上的相当性。暴力和胁迫作为强奸罪的手段,其本质特征在于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为手段的强奸罪之所以可以认定为违背妇女意志,就在于行为人对妇女采取了物理性的强制措施,被害妇女因而丧失了意志自由,处于不能抗拒的状态。而以胁迫为手段的强奸罪中,行为人采用以暴力相威胁或者其他心理挟制的方法,对妇女形成精神上的强制,被害妇女虽然没有完全丧失意志自由,但其心理受到外力的抑制,被害妇女处于不敢抗拒的状态。不能抗拒与不敢抗拒虽然存在程度上的区分,但其共同之处在于违背妇女意志。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直接使用暴力甚至会对妇女造成人身伤害等严重结果的强奸罪与采用胁迫手段只是造成精神上的损害而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强奸罪相比,前者显然要比后者在犯罪性质上更为严重。麻醉型准强奸罪是利用妇女丧失知觉而实施强奸行为,被害妇女处于不知抗拒的状态。在个别极端案例中,被害妇女苏醒以后甚至并没有发现自己遭受性侵,因而麻醉型准强奸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然而,仅就违背妇女意志而言,麻醉型准强奸罪与强制型普通强奸罪并无区别。如果说,普通强奸罪是明目张胆地在妇女不同意的情况下与之发生性关系,那么,麻醉型准强奸罪则是在被害妇女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由此剥夺了妇女的性同意权。
麻醉型准强奸罪的手段是麻醉。在医学上,麻醉是由药物或其他方法产生的一种中枢神经和(或)周围神经系统的可逆性功能抑制,这种抑制的特点主要是感觉特别是痛觉的丧失。麻醉的效果可以通过服用药物或者饮酒的方式达成。其中,药物麻醉是指使用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致使他人丧失知觉。麻醉药品是指对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使用、滥用或者不合理使用,易产生身体依赖性和精神依赖性,能成瘾癖的药品。在服用后能迅速催眠镇静,服用者将进入自然睡眠状态,且身体是麻醉无意识状态。这种药品就会被行为人用于强奸犯罪,在妇女被麻醉丧失知觉的情况下奸淫妇女。对于强奸罪的麻醉手段,我国学者指出:“所谓麻醉手段,系指使用药物、酒类饮料等,使被害人丧失知觉或无力反抗,从而达到奸淫的目的。如果说,暴力手段是使被害人不能反抗,胁迫手段是使被害人不敢反抗,那么麻醉手段,则是使被害人不知反抗。”〔14〕郑伟:《刑法个罪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298 页。根据麻醉的不同媒介,麻醉型准强奸罪的麻醉手段可以分为药物麻醉和酒精麻醉两种情形。
第一,药物麻醉型准强奸罪是指行为人使用能够使人丧失知觉的麻醉药物对妇女进行麻醉,然后利用妇女处于不知抗拒的状态实施奸淫。例如,在龚某某强奸案中〔15〕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 刑初5302 号刑事判决书。,2018 年至2019 年期间,被告人龚某某与方鸿晖(另案处理)在网上搭识,并先后加入交流黄色淫秽内容的QQ 聊天群。2020 年6 月间,被告人龚某某明知方鸿晖欲以药物迷昏妻子后邀请他人实施强奸行为,为了获取相关淫秽视频,仍在微信中转钱款给方鸿晖让方用于购买吸入式麻醉剂七氟烷,还于2020 年6 月28 日将6 粒含有三唑仑成分的固体药物交给方鸿晖。2020 年7 月间,方鸿晖与张启航(另案处理)在网上搭识,后两人预谋由方鸿晖以药物迷昏妻子唐某某后张启航至其家中与唐某某发生性关系。2020 年7 月23日22 时45 分许,方鸿晖将被告人龚某某提供的含有三唑仑成分的固体药物偷放入其妻子被害人唐某某所喝中药里,待被害人喝下中药并昏睡后,又使用七氟烷致被害人唐某某陷入昏迷。当晚23 时30 分,张启航携带情趣丝袜等物品至方鸿晖的暂住地,后张启航、方鸿晖先后与昏迷的被害人唐某某发生性关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龚某某帮助他人以欺骗他人吸毒致人昏迷的方法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为严肃国家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依照我国《刑法》第236 条第1 款、第25 条第1 款、第67 条第3 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龚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该案中,龚某某为他人实施强奸行为提供了麻醉药品,并且参与预谋,虽然本人未实施奸淫,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的共犯。该案可以说是一起十分典型的药物麻醉型的准强奸案,被告人欺骗被害妇女唐某某服用麻醉药物,使之丧失知觉,继而实施强奸犯罪。应当指出,采用药物麻醉的手段进行强奸,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妇女昏迷的情况下与之发生性关系,对妇女的人身并没有造成伤害结果,其实麻醉药物对人体健康存在损害,因而对被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具有较大的危害性。
第二,酒精麻醉型准强奸罪是指行为人对妇女进行灌酒,使其深度醉酒并丧失知觉,然后利用妇女处于不知抗拒的状态实施奸淫。酒精麻醉型准强奸罪,在形式上与药物麻醉型准强奸罪具有相似性,区别仅仅在于麻醉物品的不同:药物麻醉型准强奸罪是以具有麻醉功能的药品为媒介对被害妇女进行麻醉,而用酒精麻醉型准强奸罪是以酒为媒介对被害妇女进行麻醉。两种准强奸罪都是要使被害妇女丧失知觉,从而为奸淫妇女创造条件。醉酒是一种急性酒精中毒,过量饮酒会导致深度昏迷,因而丧失知觉。在用酒灌醉妇女实施奸淫的案件中,行为人对妇女以劝酒或者强制饮酒的方式,将妇女灌醉,然后利用妇女丧失知觉的状态与之发生性关系。例如,在万方平等强奸案中,〔16〕参见刘树德:《刑事裁判的指导规则与案例汇纂》,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327 页。2011 年1 月16 日晚,被告人万方平、邢正发、凌洲云在去响石广场步行街桂林风味馆吃饭的路上,被告人万方平提出其前女友被害人言某会过来玩,且以手势暗示趁言某酒醉之机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被告人邢正发、凌洲云表示同意。被告人万方平、邢正发与被害人言某见面后,邀请言某去吃宵夜,席间,万方平、邢正发轮流向言某敬酒,将言某灌醉。期间,万方平又打电话要在四通宾馆201 房间休息的被告人凌洲云来敬酒。凌洲云到达后,三被告人继续轮流向言某敬酒,致使言某酒醉不省人事。三被告人将言某带至四通宾馆201 房间,万方平趁言某不省人事之机与其发生性行为。邢正发接着也强行与言某发生性关系。此时,言某呕吐并逐渐酒醒。一直在旁观看的被告人凌洲云见状遂离开房间。言某酒醒知道自己被轮奸后,要求离开宾馆,被万方平、邢正发阻止。后言某趁万方平、邢正发睡熟之机,离开宾馆并报警,公安机关先后抓获三被告人。法院认为,被告人万方平、邢正发伙同被告人凌洲云以奸淫为目的,以醉酒的方法使妇女不知反抗、不能反抗,轮奸妇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遂依法判决如下:被告人万方平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邢正发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凌洲云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从该案可以看出,采用灌酒的手段的准强奸罪,在实施灌酒行为之前都有预谋,如果是二人以上共同作案,则数个行为人之间事先进行了共谋,并且是在被害妇女被灌醉后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因而属于不知抗拒的情形。
麻醉型准强奸,无论是使用麻醉药物还是采用灌酒方法,都是在致使妇女丧失知觉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因此,麻醉手段是强奸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的一部分,麻醉手段的着手就应当视为强奸罪构成要件行为的着手。
三、欺骗型准强奸罪的司法认定
欺骗型准强奸罪,亦称为骗奸,是指使用欺骗手段,利用被害妇女不知抗拒的状态实施奸淫的情形。在准强奸罪中,欺骗型准强奸罪是争议最大的一种强奸罪类型。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是违背妇女意志,因而在妇女同意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就可以排除强奸罪。然而,在某些情形中,妇女因被欺骗而同意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在真相明白以后妇女对性关系会产生后悔之意。也就是说,在骗局揭穿以后,妇女并不同意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对于此种情形,能否认定为违背妇女意志因而构成强奸罪?如果完全以发生性关系当时是否同意为标准,则所有的欺骗都不能成立强奸罪。反之,如果以事后是否同意为标准,那么所有欺骗都可以成为强奸罪的手段。因此,在发生性关系当时同意而事后不同意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当时同意的效力,直接关系到欺骗型准强奸罪的成立范围。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欺骗能否成为强奸罪的手段,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17〕参见李邦友、王德育等:《性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年版,第34 页。第一种是肯定说,认为欺骗手段属于强奸罪的其他手段之列。采用欺骗手段与妇女发生性行为的,构成强奸罪。因为欺骗是违背妇女意志的,性交时妇女虽表面上同意性交,但这是被欺骗的结果,不是妇女真实意思的反应。第二种是否定说,认为采用欺骗手段与妇女发生性交的,不构成强奸罪。因为采用欺骗手段是指行为人采用花言巧语,或虚构事实,或捏造事实,使被害妇女产生错觉,从而与行为人自愿地发生性交。在本质上,采用欺骗手段没有使被害妇女处于不敢反抗、不能反抗、不知反抗的地步,没有违背妇女意志。第三种是折中说,认为以欺骗手段奸淫妇女的情况是否构成强奸罪不能一概而论,欺骗手段是否能成为强奸罪的其他手段,关键在于欺骗手段是否达到使妇女无法抗拒(包括不能抗拒与不知抗拒)的地步。笔者认为,折中说较为妥当。肯定说将强奸罪的欺骗手段理解的过于宽泛,就会把那些明显不具有强奸性质的行为认定为强奸罪。反之,否定说完全否定欺骗可以构成强奸罪的其他手段,也会出现将个别情况下确实因欺骗而处于不知抗拒或者不能抗拒状态发生性关系的情形排除在强奸罪之外,并不合理。因此,对于欺骗手段能否成为准强奸罪的其他手段,应当区别对待。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对因欺骗而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进行甄别,由此提出作为认定以欺骗为手段的准强奸罪的判断标准。
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的骗色情形中,妇女确实因欺骗而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例如行为人以与妇女结婚为名,骗取妇女与之发生性关系,而实际上根本不想与妇女结婚。对此,肯定说认为,这种情形在形式上是妇女同意的,但这种同意是由于行为人欺骗的结果,因此,在实质上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应当认定为强奸罪。这种观点还以诈骗财物为例进行对比,〔18〕我国有学者认为,事实上,把性欺诈类比为财产欺诈并不恰当。与商业交易不同,即使存在欺诈,性行为本身也是男女双方都会感到愉悦的事情。在严重强制型和威胁型性侵犯中,强制之下性行为很难有快乐可言,这些行为对被害人造成了真实的损害,因此在这两类性侵犯中,可以把性与财产类比,而在性欺诈中,却不能做同样的类比。参见罗翔:《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从性侵犯罪谈起》,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146 页。论证因上述欺骗行为而发生的性交构成强奸罪,指出:“如果说,在妇女受蒙蔽和欺骗的情况下‘同意’发生性关系,把她看成是‘自愿’的话,那么,某甲诈骗财物,为什么还要定诈骗罪呢?我们之所以要对某甲定诈骗罪,就是因为某甲采取了欺骗手段,骗得受害人‘同意’才把财物交给某甲。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说,被害人交给某甲财物没有违背被害人的意志。所以,在上述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性交行为,欺骗属于其他手段。”〔19〕欧阳涛主编:《当代中外性犯罪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1 页。蒙蔽和欺骗的范围是较为宽泛的,例如以结婚或者其他名义与妇女交往并且发生性关系,如果从事后获知真相就不会同意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的意义上说,该性交行为确实具有因被欺骗而实施的性质。然而,在发生性关系的当时,并没有违背妇女意志。因此,此种情形不能认定为准强奸罪中的欺骗手段。这里应当指出,准强奸罪中的欺骗与诈骗罪中的欺骗,虽然在表现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相同性,但两者的性质不能完全等同。具体而言,诈骗罪中的欺骗范围较为宽泛,而准强奸罪中的欺骗只限于某些性质严重的情形,并不包括所有因欺骗而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因此,不能将欺骗手段构成的强奸罪与诈骗罪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在论证欺骗手段通常不能成为强奸罪的手段行为时,也与诈骗罪做对比,却得出与上述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指出:“尽管为多数刑法所认可的强奸手段中,有些也具有欺骗性质,例如假冒被害人丈夫和以婚约相诱等,但毕竟不能和一般的‘欺诈’相提并论。通常认为诈骗与其它侵犯财产罪的最大区别,在于被害人‘自愿’交出财物。可见欺诈手段具有不妨碍被害人意志自由的特点,然而强奸罪却是以违背妇女意志为先决条件的,两者本难相容却硬要牵扯在一起,自然为绝大多数国家刑法所不取。”〔20〕郑伟:《刑法个罪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297 页。这种观点认为,在欺骗的情况下,并没有违反被害人的意志,以此论证欺骗不应成为以违背妇女意志为特征的强奸罪的手段行为。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人的意志分为两部分,一是认知,二是意欲。如果把同意视为是符合意志自由的表达,那么,在被欺骗的情况下,被害人的认知受到蒙蔽,其同意并非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欺骗而所为应当认为是违背意志自由的行为。至于在被强制的情况下,被害人的意欲受到压制,其同意更非真实的意思表示,因强制而所为也是违背意志自由的行为。以财产犯罪而言,诈骗罪是典型的因欺骗而处分财物的行为,敲诈勒索罪则是因胁迫而处分财物的行为,两罪都是违背财产所有人或者保管人的意志而取得财物的犯罪。因此,不能认为在欺骗的情况下并没有违背被害人意志自由的问题。当然,财产犯罪是根据侵犯财产的方法设立罪名的,对财产权保护十分周延。人身犯罪则是根据人身权的种类设立罪名的,例如以保护生命权为内容的杀人罪,以保护健康权为内容的伤害罪等。其中,强奸罪的保护法益是被害人的性自主权。从各国刑法规定来看,一般都保护免受外力强制的性自主权,因而通常以暴力、胁迫为强奸罪的基本手段。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被欺骗而导致被害人不知抗拒才能例外地构成准强奸罪。在对准强奸罪单独设立罪名的情况下,强制手段的普通强奸罪与被欺骗或者其他手段的准强奸罪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但在对准强奸罪未单独设立罪名,而是将其附属于强奸罪的情况下,对于欺骗手段的准强奸罪的认定应当严格限制其范围。
在强奸罪中,以欺骗为手段的强奸与诱奸是不同的。所谓诱奸是指利用欺骗或者金钱财物等诱惑手段,使妇女与之发生性交的行为。我国有学者指出:对于诱奸来说,在行为人与妇女发生性交的当时,男女双方对性交行为的意思表示一致,不存在违反妇女意志问题,因此不能按照强奸罪论处。同时,诱奸又不能等同于采用欺骗手段而勾搭成奸的通奸行为。〔21〕参见欧阳涛主编:《当代中外性犯罪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278 页。诱奸虽然带有一定的欺诈色彩,但同时又具有利用精神或者利益引诱的性质,因而其性行为具有一定的利益交换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性关系,不符合违背妇女意志的特征。
在受到欺骗而发生性关系的案件中,妇女因被骗而对性关系产生认识错误,基于这种认识错误而同意发生性关系。在对这里的同意的效力进行考察的时候,在英美刑法通常采用事实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分析思路:如果被害人的认识错误属于事实错误,包括对性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和行为人身份的认识错误,那么被害人的同意无效,行为人构成强奸罪;如果被害人的认识错误属于动机错误,那么行为人的同意有效,行为人不构成强奸罪。〔22〕参见何洋:《强奸罪:解构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249 页。与之不同,德日刑法则采用法益关系错误的分析框架。例如,日本学者山口厚指出,因欺骗所导致的认识错误而作出同意的场合,同意是有瑕疵的。在以下两种情形下,不能肯定同意的效力:在对所产生的结果的法益侵害性陷入错误的场合;对于影响到法益的保护价值或影响到结果之法益侵害性的法律评价的事实陷入错误的场合。反之,如果不是上述两种对法益关系的认识错误,而是对同意的动机存在错误的场合,则应当认定同意是无效的。〔23〕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3 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68 页。其实,这里的法益关系错误说中的两种否定同意效力的情形,就是英美刑法中的行为性质错误和动机错误。我国学者对法益关系认识错误与动机认识错误进行了举例说明:医生欺骗作为被害人的女性患者,如果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话,就可以免收其治疗费用,但事毕之后医生却不将其许诺兑现的场合,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被害人的承诺是被欺骗的无效承诺,由此而认定医生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因为,强奸罪的保护法益是妇女的性自由权,被害人对于自愿和医生发生性行为这一点上有认识的,并没有产生错误,只是对发生性行为的原因或者说动机没有正确认识,因此,这是动机错误而不是法益错误,强奸罪不能成立。相反,如果医生欺骗女患者说,要治好病患,除了与其发生性关系之外,别无他法。被害人信以为真,与医生发生了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奸淫行为构成强奸罪。因为,在这种场合由于医生的欺骗行为,使被害人错误地理解了奸淫行为的性质,误以为该奸淫行为是治疗行为,而没有意识到该行为是侵犯其性自由权的行为,且被害人同意的是治疗行为,而不是侵害自己性自由权的奸淫行为。因此,此种认识错误是法益错误。〔24〕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410 页。应该指出,妇女被欺骗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因为在发生性关系之时,妇女是同意的,并没有违背意志。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此种被欺骗而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不能构成强奸罪。妇女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对于性行为亦是如此。只有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以欺骗手段发生的性关系才能构成准强奸罪。并且,欺骗手段较为隐蔽,不像暴力、胁迫或者麻醉等手段那样具有明显的外在形态。如果不是以客观外在形态作为认定违背妇女意志的根据,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完全取决于妇女的主观心理态度,以妇女的主观心理态度作为认定根据,就会出现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所担忧的情形:如果被害人虽然同意,因为动机上存在瑕疵而以欺骗手段成立强奸罪,那么,作出支付嫖资的承诺而又赖账的行为,也构成准强奸罪。〔25〕参见[日]前田雅英:《日本刑法各论》,董璠兴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 年版,第195 页。这种准强奸罪范围扩大化的担忧并非多余。在现实生活中,男女双方相约卖淫嫖娼,发生性关系后,男方拒不支付嫖资,失足女转而控告男方强奸的案件时有发生。如果以动机错误为标准,则都可能将男方的行为认定为违背妇女意志,因而构成强奸罪,这显然不妥。
在我国刑法中,对于准强奸罪并没有单设罪名并规定较轻的法定刑,而是与暴力、胁迫强奸罪适用相同之刑。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严格限制被欺骗而构成的准强奸罪的范围。在我国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以欺骗手段构成的准强奸罪范围是极其狭窄的,主要限于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假冒治病进行欺骗的准强奸罪。假冒治病的欺骗是指使被害人误以为性行为是治疗的必要手段,而实施奸淫。〔26〕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6 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94 页。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对性行为的性质发生了错误认识,被害妇女的同意是建立在对性行为的性质发生认识错误的基础之上。此种情形只能出现在被害妇女极度愚昧无知的场合,较为罕见。假冒治病的欺骗,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患病妇女知道是在发生性关系,但误以为这种性行为是治疗方法;第二种是患病妇女并不知道是在发生性关系,误以为性行为是治疗方法。前者例如是利用妇女愚昧无知,以治病需要为名与之发生性关系。例如,一个人假装是医生,告诉妇女她犯有一种病,最好的医疗手段是与一位受到特殊血清感染的人进行性交,而该人与妇女发生性交。后者是在妇女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治疗为名与妇女发生性关系。例如,一位外科医生告诉一位女病人,她需要进行手术,将在她的阴道里插入医疗仪器作为手术的一部分,但该医生将自己的阴茎插入妇女的阴道。〔27〕参见梁健:《强奸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80 页。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第一种情形,德日刑法认为构成强奸罪,〔28〕日本判例将使被害人误以为性行为是治疗的必要手段而实施奸淫的行为认定为准强奸罪,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这是存在疑问的。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6 版),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94 页。英美刑法则不认为构成强奸罪。〔29〕英美刑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理解她与行为人是在进行性交,因而不构成强奸罪。参见梁健:《强奸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80 页。我国刑法一般认为假冒治病属于强奸罪的其他手段,因而构成准强奸罪。
第二,封建迷信进行欺骗的准强奸罪。封建迷信的欺骗是指将发生性关系说成是修炼、法术或者信仰的要求,在这种对行为的性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被害妇女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我国《刑法》第300 条第1 款规定了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该条第3 款又规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对于这种利用封建迷信奸淫妇女行为,我国学者认为它不属于欺骗,它的实质是利用宗教或封建迷信而实施的精神强制。由于女方在精神上完全为行为人所控制,失去了选择自由,表面上看似自愿的行为其实是一种被迫屈从,因此这种行为是一种威胁,而非欺骗。〔30〕罗翔:《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从性侵犯罪谈起》,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151--152 页。根据上述观点,我国学者将利用封建迷信进行欺骗的奸淫归属于威胁(胁迫)手段的强奸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把这种利用封建迷信的欺骗行为认定为强奸罪的其他手段。例如,在石月福强奸、诈骗案中,〔31〕参见刘树德:《刑事裁判的指导规则与案例汇纂》,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328 页。2006 年3 月至6 月期间,被告人石月福在开县认识巫溪籍妇女王胜珍后,以传授“空纸来钱”为由,先后骗取王胜珍拜师、画符等费用10000余元。同年,被告人石月福在传授王胜珍“空纸来钱”的同时,又以同样的方法先后骗取巫溪县后河乡生基村妇女李发秀拜师、画符等费用10000 余元。同年9 月,被告人石月福在云阳县沙市镇认识巫溪县城厢镇白鹅村妇女吴显翠后,采取上述方法先后骗取其拜师、画符等费用3400 余元。被告人石月福在教王胜珍、吴显翠“空纸来钱”期间,对二人谎称不能和其他男人一起睡觉,只能和他一起睡觉,否则法术就不灵了,并以其封建迷信手段骗取王胜珍、吴显翠的信任,对二人实施奸淫。法院认为,被告人石月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骗取他人钱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了诈骗罪,被告人石月福还利用封建迷信等欺骗手段奸淫妇女,其行为又构成了强奸罪,应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石月福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依照我国《刑法》第300 条第3 款、第266 条、第236 条第1 款、第69 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石月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 元;被告人石月福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20000 元。对于该案,法院判决明确地将这种利用封建迷信骗取信任进行奸淫的行为认定为强奸罪的欺骗手段,而骗取手段明显属于强奸罪的其他手段。当然,利用封建迷信进行欺骗,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演变为威胁或者恐吓,对此可以理解为从欺骗转化为胁迫,应以胁迫手段处理。欺骗和胁迫的区别在于:欺骗只是单纯地陈述虚假事实,使妇女产生对性行为的误解;胁迫则是施加精神恐吓,使妇女出于害怕而不得不屈从。
第三,冒充身份进行欺骗的准强奸罪。冒充身份,也称为身份欺诈,通常是指冒充丈夫的身份,但也不排除个别冒充未婚妻(女朋友)的情形。〔32〕参见罗翔:《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从性侵犯罪谈起》,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150-151 页。冒充身份进行欺骗的准强奸罪,通常发生在妇女睡觉的时候。如果利用妇女昏睡时对性行为没有觉察而实施奸淫,应当认定为是一种趁机型准强奸罪,对此容易理解。但如果是在妇女欲睡未睡的时候,对性行为已经觉察,但误认为是丈夫或者男朋友而与之发生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并没有明显的假冒行为,而是妇女自陷认识错误,对此是认定为趁机型的准强奸罪还是冒充身份的欺骗型的准强奸罪,可能会发生争议。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仍然属于趁机型的准强奸罪而非欺骗型的准强奸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并没有实施冒充行为,而是妇女误以为是丈夫,这是自陷错误。冒充身份的欺骗型准强奸罪,在客观上必须存在欺骗行为。例如,1997 年3 月5 日凌晨,被告人孙某某饮酒后去本厂21 号女工宿舍,在推门进宿舍时,将尚在熟睡的女工赵某某惊醒。赵以为站在床边的孙某某是自己男朋友,便说了一句“站在那干啥”。此时,孙某某意识到赵将自己当成了其男朋友,即将其奸淫,被害人发现被告人不是自己的男朋友时高呼救命,孙某某仓皇逃走,后被保卫人员抓获归案。法院判决被告人孙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33〕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上)》(1992—1999年合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页。对于该案,我国学者指出:被告人孙某某凌晨进入被害人赵某某的宿舍,在明知被害人将其误认为是其男朋友的情况下,非但不申明事实,反而继续强化被害人的认识错误,继而与被害人性交。虽然说被害人事先产生了认识错误,但被告人的后续行为使被害人的认识错误继续得以维持,可以认定为冒充。〔34〕何洋:《强奸罪解构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257 页。笔者认为,该案是从利用妇女熟睡的趁机型准强奸罪转化而成为冒充身份的欺骗型准强奸罪。由此可见,利用妇女熟睡的趁机型准强奸罪与冒充身份的欺骗型准强奸罪是交织在一起的,应当根据被害妇女发生性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受骗还是熟睡加以区分。这两种情形中行为人都是利用妇女的不知抗拒实施奸淫,但趁机型准强奸罪是利用妇女熟睡而自身形成的不知抗拒的状态发生性关系,欺骗型的准强奸罪则是假冒身份致使妇女产生认识错误,处于不知抗拒的状态而发生性关系。
四、趁机型准强奸罪的司法认定
趁机型准强奸罪,亦称偷奸,是指利用已然存在的被害妇女醉酒、昏迷、熟睡、患重病等不知抗拒或者不能抗拒的状态实施强奸行为。上述趁机奸淫的四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是利用被害妇女醉酒状态实施的强奸行为。因此,笔者主要以利用妇女醉酒状态趁机奸淫为切入点展开论述。
趁机型准强奸罪的构造上明显不同于麻醉型准强奸罪和欺骗型准强奸罪。因为在上述两种准强奸案件中,行为人都采用了药物或者酒精对妇女进行麻醉或者欺骗,这些方法与性关系之间存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关系。在刑法教义学中,将这种具有双重行为的犯罪称为复行为犯。我国学者指出:“复行为犯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在实行行为中包含数个异质且不独立的行为的犯罪。”〔35〕王明辉:《复行为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5 页。复行为犯是相对于单行为犯而言的,在单行为犯的情况下,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单一的,只有一种行为。如故意杀人罪中,尽管行为人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但这些方法不是异质的,因而故意杀人罪可以归属于单一的杀人行为。就此而言,故意杀人罪是单行为犯。复行为犯则具有二个构成要件的行为,也称为二行为犯。例如,我国《刑法》第263 条规定的抢劫罪是由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和抢劫公私财物这两种行为构成的,因而属于典型的复行为犯。同样,我国刑法中的强奸罪也是复行为犯。暴力、胁迫的强奸罪,就是由暴力、胁迫的手段行为和强奸的目地行为构成的,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双重行为。在准强奸罪中,麻醉手段和欺骗手段的准强奸,也是复行为犯,其构成要件行为包括麻醉、欺骗等手段行为和性交行为。然而,趁机奸淫的准强奸罪则与之不同,从外观上考察,此种情形下并不存在双重行为。例如,在采用用酒灌醉的手段实施强奸的情况下,用酒灌醉是手段行为,利用妇女醉酒状态发生性关系是目的行为,因而属于复行为犯。在趁机型准强奸罪中,例如利用被害妇女处于醉酒状态与之发生性关系,行为人并没有实施用酒灌醉的手段行为,而是单纯地利用妇女已然存在的醉酒状态与之发生性关系。就此而言,趁机型准强奸罪只有单一行为。我国有学者认为,强奸罪属于相对型复行为犯。所谓相对型复行为犯是指虽然在构成要件中所类型化的行为表现为复数性,但是在实现此犯罪构成的过程中,数个类型行为既可以通过数个事实行为也可以通过一个事实行为来实现的复行为犯。有些强奸罪的客观行为包括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两个行为,而有些强奸罪在客观方面只存在一个行为,并无明显的手段行为。例如,当行为人采取暴力、胁迫手段时,该手段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即手段行为。当行为人采取其他方法时,该手段既可表现为一种行为,如用酒灌醉、用药麻醉,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单纯的行为方法,如趁妇女熟睡之机实施奸淫,此时的所谓其他方法仅表现为奸淫行为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其本身并非一个单独的行为。〔36〕王明辉:《复行为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82-83 页、第214 页、第219 页。笔者认为,在所谓相对型复行为犯的情况下,例如利用妇女醉酒状态发生性关系,其实只有一个行为而并没有数个行为。将这种情形归入复行为犯,不无勉强。这种趁机实施的强奸罪,在犯罪构造上与其他强奸罪存在较大的差别。《日本刑法典》虽然未设趁机性交罪,但其第178 条第2 款将乘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而奸淫的,规定为准强奸罪,这是一个独立于强奸罪的补充罪名。在我国刑法中,这种趁机性交行为被涵括在强奸罪的其他手段之中,属于强奸罪的一部分,在学理上可以将其称为准强奸罪。这种利用无知觉或者无行动能力状态的趁机奸淫妇女的行为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特殊性,因而其司法认定更应严格掌握标准,避免扩大化。
趁机型准强奸罪之所谓趁机,是指利用被害妇女因醉酒、昏迷、熟睡、患重病等而已然处于丧失知觉的状态。因此,趁机型准强奸罪与麻醉型准强奸罪相比,虽然就利用被害妇女处于丧失知觉或者无行动能力状态而与之发生性关系而言,其特征上是相同的,但在被害妇女丧失知觉或者无行动能力状态的形成原因上是不同的:在麻醉型准强奸罪的情况下,被害妇女的丧失知觉状态是行为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该故意行为本身就是强奸罪的构成要件的手段行为;在趁机型准强奸罪的情况下,被害妇女的丧失知觉或者无行动能力状态是行为人以外的原因造成的,行为人只不过利用这种已然存在的妇女不知抗拒或者不能抗拒的状态实施了奸淫行为。趁机型准强奸罪与麻醉型准强奸罪的根本区分在于: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状态到底是由他人(包括被害人和第三人)造成还是由行为人本人造成。根据我国司法实践的经验,趁机型准强奸罪的“趁机”,主要是利用以下四种情形。
第一,醉酒。在麻醉型准强奸罪中,被害妇女的醉酒是行为人灌醉的,而在趁机型准强奸罪中,被害妇女的醉酒原因不能归之于行为人。因此,在醉酒型的趁机型准强奸罪中,醉酒状态是由妇女本人的原因所引起的。醉酒是由人体摄入一定数量的酒精所引起的酒精中毒。酒精中毒时出现的各种精神异常症状,称为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酒精中毒可以分为急性酒精中毒和慢性酒精中毒。急性酒精中毒,是指由于一次饮酒后急性酒精中毒所致的精神障碍。慢性酒精中毒,又称为酒精依赖,是指由于长期较大量饮酒成瘾而造成的慢性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37〕参见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02-205 页。在麻醉型准强奸罪中的醉酒,是指急性酒精中毒而并不包括慢性酒精中毒。
从案件具体情况来看,趁机型强奸罪的醉酒一般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自己或者与他人饮酒而至于醉。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趁机“捡尸”,将醉酒妇女带离原地实施奸淫。第二种则是行为人与妇女共同饮酒,但在喝酒的时候并没有将妇女灌醉实施奸淫的主观意图或者预谋,而是在妇女酒醉以后才临时起意利用妇女丧失知觉的状态实施奸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13.1 条(b)规定以下情形构成强奸罪:行为人在该妇女不知晓的情况下,通过使用药物、致醉物或者令该女性不能抵抗的其他手段,实质减弱该女性对自己行为的理解或者控制能力。这一规定类似我国刑法中麻醉型准强奸罪中以醉酒为手段的情形,不同于单纯利用妇女醉酒状态的准强奸罪。我国学者认为,美国《模范刑法典》的上述规定附加了一个重要条件即“未予觉察”,也就是“不知晓”。言下之意,只有行为人偷偷往被害人食物中掺入药品、酒类,才属于使用麻醉手段,反之两人共饮同食的,哪怕行为人有意将被害人灌醉后实施奸淫,也不能构成强奸。〔38〕郑伟:《刑法个罪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299 页。在此,论者排除共饮同食的情形,只能在偷偷地投放麻醉物品的情形下才可以成立麻醉型准强奸罪。笔者认为,这是过于狭窄地限制了此种情形构成强奸罪的范围。事实上,行为人也完全可以在共饮同食的情况下偷偷投放麻醉物品。并且,我国有学者还认为,在共饮同食情形中,既然被害人是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减损理解力或控制力,就应该预见到可能发生的事情,包括性交在内。如果不希望发生的话,就不会放任自己陷入不清醒状态。双方的关系密切到可以听凭被告人使自己陷入不清醒状态的程度,即使发生性行为,也未必就违背了被害人的意志。〔39〕郑伟:《刑法个罪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299 页。笔者认为,这一论断过于武断。不仅麻醉型准强奸罪可以是在共饮同食的场合趁人不备投放麻醉物品,而且趁机型准强奸罪也可以是在共饮同食的场合因临时起意而成立。因此,当共饮同食之时并没有利用妇女醉酒状态实施奸淫的意图,而是在妇女醉酒处于丧失知觉以后产生犯意,与被害妇女发生性关系的,同样可以构成趁机型准强奸罪。
第二,昏迷。昏迷是指处于丧失知觉的状态,至于昏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可能是病患引起,也可能是饥饿导致。妇女因各种原因处于昏迷状态,对于妇女来说生命或者身体处在某种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仅不予救治,而且趁人之危实施奸淫,其性质十分恶劣。
第三,熟睡。熟睡是指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所谓睡眠状态是指人在睡觉时表现出来的形态。与清醒状态相对,人睡觉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或称第一期)是入睡阶段:从昏昏欲睡开始,逐渐入睡,不再保持觉醒状态。这时候,呼吸变慢,肌肉张力下降,身体轻度放松,此时属于初睡状态,睡眠者较易被外界声音或触动所唤醒。第二阶段(或称第二期)是浅睡阶段,或称轻度睡眠阶段:本阶段睡眠属浅睡或轻度至中度睡眠状态,睡眠者已不易被唤醒,此时肌肉进一步放松,脑电图显示梭状睡眠波。第三阶段(或称第三期)是深睡阶段:这个阶段睡眠者进入深度睡眠状态,肌张力消失,肌肉充分松弛,感觉功能进一步降低,更不易被唤醒。第四阶段(或称第四期)是延续深睡阶段:本阶段是第三阶段的延伸,但不是每个睡眠者都能达到本阶段,也不是每个睡眠周期都可达到这一阶段。〔40〕睡眠状态,参见百度百科(baidu.com),2021 年11 月18 日访问。趁机型准强奸罪中的熟睡是指睡眠状态上述四个阶段中的第三和第四阶段,即深睡阶段以及延续深睡阶段。在熟睡情况下,因感觉功能降低,人对外在事物暂时失去反映能力,因而对奸淫行为处于不知抗拒状态。
第四,患重病。重病是多种多样的,这里的重病是指丧失行动能力的重病,例如瘫痪卧床等状态。在妇女患重病的情况下,由于失去行动能力,处于不能抗拒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的奸淫行为构成准强奸罪。此外,明知精神病人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也属于趁机型准强奸罪。对于奸淫精神病人如何定罪,各国刑法的规定各有不同,主要存在单设罪名和归入强奸罪这两种情形。〔41〕参见郑伟:《刑法个罪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04 页。我国刑法对奸淫精神病人的行为未作专门规定,司法实践中将其作为强奸罪的其他手段,根据下述四种情形认定。其一,行为人明知(包括必然知道和明知可能)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患者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被害人是否同意,有无反抗,均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以强奸罪论处。其二,行为人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妇女在妇女未发病期间发生的性行为,妇女本人同意的,不构成强奸罪。其三,行为人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妇女或者精神病已基本痊愈的妇女,在女方自愿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不能以强奸罪论处。其四,行为人确实不知道是青春型精神病患者(俗称花疯子),将女方的挑逗、追逐等病态反映,误认为是作风、品质不好,在女方的勾引下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42〕参见周峰主编:《新编刑法罪名精释》(第2 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 年版,第1032-1033 页。由此可见,对于患有精神病的妇女,只有达到“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程度,行为人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才能构成趁机型准强奸罪。
趁机型准强奸罪在性质上不仅比暴力、胁迫型强奸罪更轻,而且还比麻醉型和欺骗型准强奸罪要轻。因此,趁机型准强奸罪的成立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利用醉酒、昏迷、熟睡、患重病等情形实施奸淫,而且还要考察是否达到不知抗拒或者不能抗拒的程度。例如,较为常见的利用妇女醉酒状态实施的准强奸罪,只有当醉酒达到丧失知觉的状态,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才能构成准强奸罪。醉酒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它存在一个程度问题,从兴奋到不省人事,依其程度可分为微醉、醉、泥醉。如依其生理、心理及精神变化则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兴奋期,一般在饮进的酒类中纯酒精含量达到20毫升至40 毫升后,表现出眼部充血,颜色潮红,头晕,人有欢快感,言语增多,自控力减低(易受鼓动),情绪不稳,对焦虑的耐受度降低且容易冲动。第二阶段为共济失调期,多在饮酒量较大时出现,此阶段已成酩酊状态,表现为动作不协调,口齿不清,步态不稳,身体失去平衡,辨认能力降低。第三阶段为昏睡期,在饮进酒类中纯酒精含量达100 毫升以上时。此阶段表现为沉睡不醒,谈话几乎没有意义,且令人无法理解,知觉丧失,颜色苍白,皮肤湿冷,口唇微紫,常眼前一片黑暗,走路跌跌撞撞,动作失去目标,有的出现震颤性谵妄(震颤、幻觉、迷惑、流汗、心跳加速),甚至陷入深度昏迷,严重时甚至导致呼吸麻痹而死亡。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醉酒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显著减低,但未致完全丧失之程度。在第三阶段,醉酒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严重降低甚至完全丧失。〔43〕参见黄丁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构造与判断》,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387 页。我国《刑法》第18 条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醉酒的人犯罪的,并不需要考察其是否丧失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一概承担刑事责任。然而,在利用妇女醉酒状态与之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准强奸罪的时候,就应当具体判断醉酒达到何种程度。笔者认为,如果妇女虽然醉酒但并未达到昏睡程度,则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准强奸罪。醉酒只有达到人事不省的昏睡程度,才能认定为不知抗拒状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以此作为构成强奸罪的判断标准。例如,在孟某等强奸案中,〔44〕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版,第825 页。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3 月16 日凌晨3 时许,被告人孟某在某酒吧内与被害人朗某跳舞相识,后孟某趁朗某醉酒不省人事之际,骗取酒吧管理人员和服务员的信任,将朗某带出酒吧。随后,孟某伙同被告人次某、索某、多某、拉某将朗某带至某KTV 包房。接着,多某购买避孕套,并向次某、索某和拉某分发。次某、索某和拉某趁朗某神志不清,先后在包房内与其发生性关系。孟某和多某欲与朗某发生性关系,但因故未得逞。当日,朗某回到任教学校后,即向公安机关报警。经鉴定,被害人朗某双上臂及臀部多处软组织挫伤。同年3 月18 日,被告人孟某、次某、索某、多某、拉某分别被公安机关抓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孟某等五人在被害人处于醉酒无意识状态下,骗取酒吧工作人员的信任,谎称系被害人的朋友,从酒吧带走被害人,预谋实施性侵害,并利用被害人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的状态和不敢反抗的心理,违背被害人意志,共同对被害人实施了性侵行为,其行为均已构成强奸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一审宣判后,五被告人均不服,以被害人无明显反抗行为,系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为由,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中,被害妇女醉酒已经达到无意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妇女不知抗拒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应当以强奸罪论处。
应当指出,如果在被害妇女醉酒但并没有丧失知觉,或者在发生性关系过程中酒醒的情况下,行为人继而采用暴力手段实施奸淫的,应当直接认定为暴力强奸罪,而不是趁机型准强奸罪。例如,在李冠锋等强奸案中,〔45〕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刑初字第1748 号刑事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纵观该案,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接触,开始于2 月17 日零时许的夜半酒吧,截止于当日7 时30 分左右离开湖北大厦,经历了酒吧饮酒、寻找宾馆和实施强奸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被害人与被告人饮酒、唱歌、玩游戏,至3 时30 分许离开酒吧时,被害人已处于醉酒状态,需他人搀扶行走,没有证据表明其间有人询问过被害人是否同意出台,故不能认定被害人跟随众人离开酒吧外出吃饭就是同意出台:从被告人在金鼎轩与他人发生争执,到酒吧张姓服务员离开人济山庄,被害人已能自主行走,但该过程中,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中有人向被害人表明发生性关系的意图。第二阶段中,五名被告人带被害人寻找宾馆,途中被害人发现张姓服务员不在即要求下车,遭到拒绝后遂呼喊、挣扎,但被李冠锋、王某等人摁控并殴打,处于不能反抗状态。第三阶段中,被害人被挟持到湖北大厦,下车前受到李冠锋等人的威胁,下车后被李冠锋、王某夹拉前行,穿过大堂,进入电梯,直到酒店房间。监控录像显示,被害人受到拉拽、击拍,其姿态特征没有任何自愿的表现。在酒店房间内,被害人因不肯脱衣,再次受到殴打,处于不敢反抗状态,后被轮奸。该案事实表明,被告人李冠锋、王某、魏某某(兄)、张某某、魏某某(弟)违背妇女意志,共同使用暴力手段奸淫妇女,其行为均已构成强奸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冠锋、王某、魏某某(兄)、张某某、魏某某(弟)犯强奸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五被告人的行为系轮奸,给被害人身心造成伤害,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大,依法应予惩处。在该案中,被害人在酒吧有陪酒行为,李冠锋等人与被害人共同饮酒致使其醉酒,并强行将被害人带离酒吧。被害人在此期间虽然因饮酒过量,曾在一段时间意识模糊,但在湖北大厦李冠锋等人使用暴力对被害人实施奸淫的时候,被害人处于清醒状态,并进行反抗,李冠锋等人对被害人进行殴打,致其不能抗拒。该奸淫行为并不是利用被害人的醉酒状态而是使用暴力实施的。因而李冠锋等人不构成趁机型强奸罪,而直接构成暴力强奸罪。
在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利用妇女醉酒实施奸淫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存在界限不明的问题,即使是酒醉没有达到丧失知觉的程度,也认定为强奸罪,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当地扩大了趁机型准强奸罪的范围。在其他国家刑法规定中,趁机型强奸罪都以被害妇女处于一定的精神或者心理状态为前提。例如《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91 条规定准强奸罪是指明知被害人为无判断能力人或者无反抗能力人,而与之为性交行为、与性交相类似的性行为或其他性行为的情形。至于这种无判断能力或者无反抗能力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在所不问。因此,在醉酒的情况下,只有当醉酒达到无判断能力或者无反抗能力状态,才能构成准强奸罪。此外,《日本刑法典》规定的准强奸罪,也是乘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而奸淫。这里的心神丧失是针对麻醉型准强奸罪而言的,至于不能抗拒则是针对麻醉型准强奸罪而言的。对此,日本学者西田典之指出:“所谓心神丧失,不同于责任能力中的心神丧失,是指由于昏迷、睡眠、泥醉、高度的精神障碍等原因,而对自己性的自由受到侵害缺乏认识的情形。与之相反,所谓不能抗拒,是指虽然认识到自己性的自由被侵害,但由于手足被缚、醉酒、处于极度的畏惧状态等原因,而显然难以在物理上、心理上进行抵抗的情形。”〔46〕[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6 版),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93 页。因此,在趁机型准强奸罪的情况下,被害妇女处于心神丧失,也就是不知抗拒的状态,对于利用妇女醉酒状态实施的奸淫构成准强奸罪亦如此。在此,可以将趁机型的强奸罪与抢劫罪做一比较。我国刑法中的抢劫罪也分为暴力、胁迫的抢劫罪和其他方法的抢劫罪。其他方法的抢劫罪,也可以称为准抢劫罪。在准抢劫罪中,只包括麻醉型的准抢劫罪,即使用麻醉手段,包括药物麻醉和用酒灌醉的方法,致使被害人处于丧失知觉的状态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情形。如果是利用被害人本身存在的醉酒、昏迷等丧失知觉的状态而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准抢劫罪,而是以盗窃罪论处。然而,利用被害人醉酒、昏迷等丧失知觉状态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则应当认定为趁机型准强奸罪。由此可见,在此问题上,强奸罪的范围已经比抢劫罪更为宽泛,如果再不对趁机型准强奸罪的范围加以限制,则明显有失公正。
五、结 语
我国刑法中的强奸罪包含了行为性质存在较大差异,并且法益侵害具有明显区分的不同强奸行为类型。可以将强奸罪分为以下五个等级的罪名体系:暴力型强奸罪、胁迫型强奸罪、麻醉型准强奸罪、欺骗型准强奸罪、趁机型准强奸罪。其中,暴力型强奸罪具有暴力犯罪的特征,其行为会对被害妇女造成重大人身伤害,甚至造成死亡的后果。胁迫型强奸罪采用精神威胁的方法实施奸淫,通常情况下不会对被害妇女造成人身伤害,其法益侵害性程度低于暴力型强奸罪。以其他手段构成的三种准强奸罪的性质又各有区别:麻醉型准强奸罪所使用的麻醉手段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其性质与胁迫型强奸罪具有相当性。欺骗型准强奸罪是使用欺骗方法在妇女受蒙蔽产生认识错误而不知抗拒的情况下实施奸淫,同时被害妇女本身存在认知上的瑕疵。至于趁机型准强奸罪,只是单纯地利用妇女不知抗拒的状态而与之发生性关系,其危害弱于其他各种类型的强奸罪。因此,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强奸罪不仅应当在构成要件上严格把握定罪标准,而且应当在处罚上区别对待。尤其是对于某些明显不具有暴力性质的强奸罪,应当适用较轻之刑。在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予以减轻处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