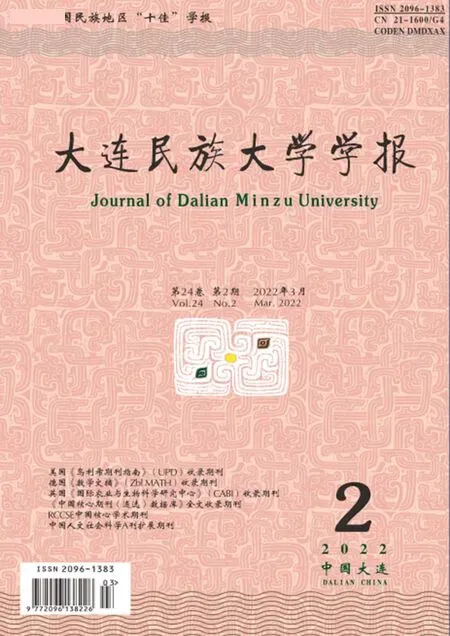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中的才女神异化书写析论
2022-11-21邢小萱
邢小萱
(香港浸会大学 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 999077)
有清一代,经济的发展、家族的助益、闺阃与外界界限的松动等因素的凑泊使规模化的闺秀书写及出版应运郁起。与闺秀诗文集大量出版相随,文人学士、亲族友人、乡党同里等为闺秀诗文集撰序题跋也成为了一项日益普遍的社会性活动。作为闺秀诗文集的先导,序跋(尤其是序)承担着尤为重要的桥梁作用,因其不仅需要将闺秀作品引介至文坛,亦在很大程度上引导、操控着读者对女作家及其作品认知的形成,从而襄助女性文学与主流文学、闺阁作家与读者群体之间的多维沟通的达成。对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学界对清代闺秀文学及文化形成更为全面立体的认识。
序跋文体自魏晋南北朝正式确立以来(1)据石建初的考察,序的写作可追溯至先秦,而将其深化为一种文体则自萧统《文选》始,跋文写作则至迟始于晋。参见石建初《中国古代序跋史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2页。,已历经千余年的发展而形成了自有的范式,其重点论述部分盖不外乎作家论与作品论。其中作家论囊括对作者情性、经历及蕲向的介绍,从而对了解作家风格笔法的形成内外诱因及挖掘作品意旨产生帮助[1];作品论则涵括文本批评、文学史定位、文艺理论提炼等一系列内容。通览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相较于作品论,其于作家论的偏重是极为显著的,这些大篇幅的作家论不仅梳理了女作家生平、重点事迹此类较客观的材料,亦时常包涵一些对女作家本人及其作品的神异化书写,如有不少作者在他们为女性诗文集所撰序跋及传中提出乃至强调,女子的诗文之才多为极高天赋的呈现而非学力的结果。更堪寻味的是,在一些序跋中,一些才女甚至被赋予一定的神异化色彩,以天选之人或谪世女仙的形象与凡俗女子拉开艺术性距离。基于这一观察,本文将首先列举序跋作者塑造神异化才女形象的数种习见方式,继而试图从闺秀诗文集序跋自身文体背景及其所处之文化背景角度切入,探析清代才女序跋中才女神异化书写大量涌现背后的文体期待及文化语境,从而透过闺秀诗文集序跋中的才女神异化书写这一棱镜对清代闺秀文学进行更为全面的观照。
一、夙慧、天选、女仙与自然灵气
通览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时常映现其中的神异化的才女书写的方式主要可归纳为夙慧幼慧说、天选说及谪世女仙说,兹依次论之。
1.夙慧、幼慧说
在论及女作家本人时,诸多序跋作者时常提及她们幼年的经历,这些对童年旧事的叙写往往有着明确的目的指归,即为女作家日后的文学成就归因。在这一回溯讨源的过程中,夙慧、幼慧、早慧是出现频率极高的字眼。如吴宝崖言及闺秀徐昭华“才由夙具,慧自生初”[2],凌誉赞其侄女凌祉媛生而敏慧,“七八岁时即解俪语”[3]。女作家汪端的幼慧事迹则更显奇异,据许宗彦之序,汪端“襁褓中见诗,辄注视”,待汪端年至学步,“乳母将之出庭中,时花初放,对之凝笑,口絮絮若有所讽”,这样殊于常人的禀赋使汪端“七岁遂能诗,愈长愈好,愈好愈工”[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笔者随机抽样检视了100位清代闺秀作家的诗文集序跋,其中被序跋作者叙述为夙慧、早慧者多达46位,近乎半数的比例说明夙慧这一特质几乎已被视为出版诗文集的才媛闺秀的普遍性特征。
2.天选说
夙慧颖悟使得清代能文闺秀有殊于常人,在作序跋者的笔下,有些女作家的生平经历甚至极具神异或诡奇色彩。一些才女在诞生之际便天生异象,似乎有天选之意。据锁开源序,其妹锁瑞芝初生之时“灵芝产于庭,群鹊噪于树”,而至芝弥留之际,“端坐不卧,谈笑如平时”[5]。而这些颇具神异色彩的现象,往往是这些才女超凡颖悟、怀有诗才的原因。苏州才女华浣芳与诗结缘的过程更显奇异,在其夫为其诗集所书弁言中记载了华氏的一段自我叙述:
妾九岁时夜梦朱衣人引至殿上,殿上坐一王者,云是唐朝太宗皇帝,问予“儿欲学诗否?”予茫然不知所谓,未及答,但闻宣一代诗人上殿,随见玎当玉佩者约百计,趋谒毕,太宗因命诸人各授一篇。醒时亦不复记忆。嗣后出口每多五七字语,或曰:此诗也。于是觅唐人诗读之,觉如逢旧识[6]。
唐太宗于梦中命诸仙授诗,梦醒后华即可出口成诗。在这番颇显奇异的描述中,华氏之诗学天赋完全自天选、天授而来。才媛吴山身上则具有略显荒诞的神异色彩,据魏禧为其所作的《青山集序》,吴山偶得奇疾,“疾作则右手自运动,日夜作字不休,或濡笔书纸上,悉成玄理,疾止不复记忆”[7]。在魏禧笔下吴诗似是一种不自觉的天降之作,吴山则是替上天传达玄理的媒介,颇有天选之意味。此类神异化叙写呈现出一种“天选——成才”的简单因果模式,即才学为上天进行选择并赋予的结果,女作家本人对其才能似并无自觉。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学力的重要性被很大程度上抹拭而去,神异化的力量则被推至最为瞩目的位置。
3.谪世女仙说
另有一些才女被描述成偶谪尘世的女仙。林以宁在为徐德音诗集作序时便叙及徐德音出生之时,“家人见旌幢仙乐自空而下,导一羽衣入室,即产”,“夙成仙姥”[8]的徐德音必表现出与寻常女子不同的天资,所以于学语牵衣之时便能作诗辨弦,姿态迥越寻常孩童。女作家郑兰孙更自叙其为谪世女仙的神异经历:
盖予夏间卧疾几殆,迷惘中似为大士引去,戒之曰:“汝本莲座侍香之童,偶谪尘寰,诸宜留意。”并示偈语四句云:“心如明镜不沾尘,慧业无端误尔身。记取本来真面目,莲华会上证前因。”予拟再叩,则觉花雨著衣,旃檀竟体,惕然而寤,疾亦顿瘥。
由这番经历,郑氏遂“感入世之因,悟出尘之妙”[9],并将自己的别集命名为《莲因室集》,可见其对谪世女仙身份的深刻认同与着意强调。如果说夙慧、幼慧尚可视为为一种较为客观的对天赋高低的评判(然而清代闺作家如此大比例的夙慧、幼慧现象似有夸大之嫌),那么天选及女仙传说则直接将女子的资质归于一种神秘且不可控的非自然力量,女作家成为被择取之人,其生平也因此更显非凡神异。
诚然,夙慧、早慧现象并不能被视为清代闺秀作家的独有特质(2)秦汉时期人们便对早慧儿童多有关注,详见崔建华《秦汉社会对早慧现象的认知》,《社会科学战线》,2014第11期,第68-77页。,对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神仙化的现象也至少可以追溯至西汉,如扬雄便称司马相如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10]。唐代诗人李贺早逝后,也流传着他为上帝神仙所召去作新宫记的轶事(3)《太平广记》神仙卷载李贺轶闻:“陇西李贺,字长吉,唐郑王之孙。稚而能文,尤善乐府词句,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以父名晋肃,故不得举进士。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及贺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幸得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从小奉亲命,能诗书,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餙也,且欲大门族,上报夫人恩。岂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养,得非天哉!然某虽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询其事,贺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十九,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 194页。元人辛文房所作《唐才子传》亦载此轶事。见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2-290页。可见不少才女神异化书写都近此模式。。至明清,此类说法屡见于闺秀诗文集序跋之中,可见闺秀诗文集序跋中的神异化叙写方式应在一定程度上绍述了男性文人创建的传统。然而作为部分序跋作者的一种集体性反应机制,对既有传统的择取与规模化应用,实已暗含了序跋作者乃至时人对于此类文章的文体期待以及对女作家及女性书写的认知。并且对这一传统进行取用、推阐、更新,从而使之适应并服务于女性创作及出版这一过程又会生发出新的文学及文化意蕴,故而有必要对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中的才女神异化书写现象进行析论。
二、重点的偏置: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之书写倾向
作为一种非官方文学性传记文体,序跋虽看似以真实性为指归,实则更注重通过对传主生平经历的择汰胪列而形成一个“被塑造后”的传主形象的真实感。这意味着序跋作者无须贯彻如实再现传主生平的要求,而是可以通过选择、删汰、重复等一系列叙述活动构筑一个他所希望呈现的(亦或是传主本人希望被呈现出的)理想化样貌。纵观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大部分作者都企冀将闺秀作家呈现为情性婉嫕、举止端谨的良家淑媛或至贤至孝至慈的地母式形象,这无疑可为闺秀之作制造人以德名、德随诗传的出版契机和传播条件。然而,这一抹拭了个体特性的叠影式传统女性形象纵然可以安全落脚于当世文化境况中,但当这类形象大量涌现于商业出版领域,却难免堕入千人一面的淡然无味。明清时期,随着印刷成本的降低和牟利性私营出版商的大量增加,驱名若鹜的文人们争相出版自己的文稿,这一风气又以江南地区最甚[11],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的才女们也在这股风气的熏染之下纷纷将别集付之剞劂,甚至出现了闺秀“工诗词者皆各梓一编”[12]之盛况。虽然大部分进入出版领域的女作家都自言并不抱有求名之心(4)时常有女作家在自序中表示、或在他序中请人提及,自己本意并不想出版诗文集或获得诗名。如袁绶之子吴师祁便在一篇志中转述了母亲说的一段话:“汝承乏冲要,当尽心民事,毋亟此。况我诗词皆性情触发,意到笔随。少时作无存者,中年草藁散失亦多。今老矣,亲友四散,无复兴致为此韵语。且不自信,恐贻当代知者讥。”出于这些考虑,袁绶对吴师祁刊刻自己(袁绶)诗集的提议“屡请屡止”见吴师祁《瑶华阁集志》,载李雷主编《清代闺阁诗集萃编》第七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4010页。另一位女作家屈秉筠更是命家中女婢焚烧自己的诗稿,据她的丈夫记载,屈秉筠“悉取所作,鐍置一箧,命女奴□诸火,毋留纤迹”。见赵同钰《屈秉筠叙略》,载李雷主编《清代闺阁诗集萃编》第五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2742页。但女作家赵棻在诗集自序中指出,女作家的这种言论或做法很有可能是一种狡猾的合理化行径,赵棻言曰:“其夫若父兄子弟以揄扬于世,曰彼不肯出以示人,吾曹窃为传播云尔。若是则能文之名传,兼得守礼之称焉,视工于炫鬻者,其计更狡矣。”见赵棻《滤月轩集自序》,载李雷主编《清代闺阁诗集萃编》第六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3391页。,但时人对女性作家“香奁袭取浮誉”[13]、“炫鬻以射利”[14]等指摘,以及闺秀自身“好名之心,人不能皆无”[15]的剖白,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立言求名与射利并非不在闺阁作家的出版期待之内。况且,当闺阁作家决意使自己诗文集经印刷进入市场,作者本人与作序跋者事实上都已被吸纳进商业印刷的经济场域,成为图书业中的生产环节中的份子,而消费环节即读者阅读亦是这一产业链条能否首尾相系并使文本获得完整意义的关键[16]。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出版物市场中,诗文集无人问津和作者本人沦至无名想必不是作者和作序跋者所期望的情景,不少序跋作者便都曾直接表示“不忍淹没无传”[17]、“乌可使之无传哉”[18],使闺秀作品之可传这一题序书跋最重要的目的已然呼之欲出。
使作品之可传自然并非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独有的目的,而是放之于整个序跋领域皆然,由这一目的所导致的序跋多沦为“友朋推挹之词”、“无庸之标榜”[19]也受到了一定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为男女两性所书之序跋都难以跳脱程式化的推挹标榜,但如何推挹标榜的书写实践则呈现出判然二分之态势。相较于序跋作者更注重推挹男性作品本身和试图擢升男性作家本人于文学史地位的做法,闺秀诗文集序跋则明显偏重于构筑及经典化女作家自身形象。至于对女作家作品本身的批评往往流于表面,时常用几组词汇简单带过,甚至有些序跋对女作家的作品只字未提,而是对女作家的品性举止进行通篇论述。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对话性质的文体,序跋之最终指向乃女作家诗文集之读者群体,因而闺秀诗文集序跋的书写方式很大程度上便是读者群体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谛视方式的具象化。由此,时人观看女性作家及作品的视角透过闺秀诗文集序跋这一剖面得以展现,即女作家自身形象于其诗文集的增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时人对女作家自身的注视甚至远超她们的作品。从这一角度观之,女作家神异形象的叙写实际上与叙写符合传统伦理价值的闺秀形象有着共通之处,即皆以女作家形象自身为诗文集本身的重要附加值,从而达到诗随人传的目的。李汇群曾指出,晚明以来,文人擅写命途坎坷之才女,除了有自身之投射与寄寓外,也因为才女要有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才值得文人将之纳入书写体系,从而实现垂世的目的[20],已然揭示了男性对才女的注视角度的选择(5)约翰·伯格(John Berger)曾指出,注视是一种选择性的行为,人们只能看见他们所注视的事物,而这样的观看事物的方式是源于知识和信仰的影响和制约。〔英〕约翰·伯格著,戴行钺译《艺术观赏之道》,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4页。。早慧、天选、女仙谪世、灵气所钟等专注于女作家神异化形象言说方式便是这种注视角度的外在呈现方式之一。
对女作家本人进行神异化描写,从而使诗集热销、诗名远播的例子确有其人,此处择取才女夏伊兰为例(6)李汇群曾对夏伊兰其人及其诗作做出述论,其目光主要聚焦于夏氏本人如何受到到明末女性传说中的冯小青形象的召唤,并将自己的人生投寄于小青的故事中。详见李汇群:《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4-147页。。夏伊兰字佩仙,夏之盛女,嘉庆十七年(1811)生于钱塘。慧根夙具的夏依兰“孩时已辨琴弦,髫岁即欣笔札”[21]。道光六年(1826),年甫十五的夏氏罹病早夭。至此,夏伊兰短暂哀凄的一生看起来与其他早逝才女并无二致,但其父夏之盛于夏伊兰夭折同年为其撰写的一篇行略,却让夏伊兰的一生有了异于凡人的色彩。这篇行略最惹人瞩目的便是对夏伊兰离世之前一段奇闻的叙写:
(殁亡)前三日,晨起沐浴更衣,合掌作膜拜状,呼母前,耳语曰:“儿欲去。”母亟问曰:“女将安去?”女曰:“儿谪限已满,仍将归雷庙去,天上差乐不苦,毋以儿为念也。”母泣下,女反劝慰百端,绝无凄楚之色,且以尘世久居为无味……女之殁也,天适酷暑,一昼夜始敛,面色不改,目炯炯如生时[22]。
这段叙写使夏伊兰于明清时期已不尠见的早慧才女形象中跳脱而出,一举跃升为一位周身萦绕着神秘与浪漫色彩的谪世女仙。为夏伊兰的诗集作序跋的人基本也都围绕夏伊兰的女仙奇闻展开叙述,如姚梦星便将夏伊兰的一生描述为“神仙小谪”[23],姚若言其“身本雷女”“去为震宫之仙”[24],黄宪清亦言“小谪红尘,便赴蓬莱之约”[25],并将夏伊兰俦比于早逝成仙的才女冯小青。诸位文士的序跋与夏父所作行略桴鼓相应,使得夏伊兰的女仙身份更显真实传神。颇堪寻味的是,相比于在夏伊兰的身世轶闻上大书特书,序跋中直论夏伊兰作品的语句则寥寥可数,仅有邵正笏评其诗有如“庾开府之清新”“苏眉山之逸宕”[21]之语,然一语带过,转而进入神异化的描绘。罗文鉴虽提及可从夏氏诗中“识其性情”,并扬扢其“年甫十五,而造诣已如是”[26],然并未阐明其性情和诗学造诣究竟如何,甚至连一句对夏伊兰诗风的总体论断都付之阙如,难见其对夏氏作品的真实评断。夏伊兰离世后,其诗集被“争欲传观”[21],夏伊兰本身也由此获得更多关注,“哀之者不惟浙水东西,且遍大江南北”[27]。不可否认,或许有人确实为夏伊兰的文笔所折服,但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女子的文学作品为当世文人如此追捧,仅凭其诗学造诣实为不易,且对于夏伊兰的作品,马履泰曾评曰“方期更加琢磨,洗伐一新”[28],言下之意似是夏氏作品虽显颖悟,然功力犹欠。而夏伊兰的作品仍大受文士追捧并在商业出版领域中赢得一席之地,从而达到夏之盛所言之“未忍听其(夏伊兰诗)淹没”的目的,多有赖于由其父所塑造、作序跋者所推衍的神秘浪漫又凄婉哀绝的仙女形象。从诸多序跋作者对夏伊兰作品“失语”却大肆书写其女仙身份的叙述模式亦可见,序跋作者们自己的目光所至及他们所预设的读者群体的注视对象,都并非夏伊兰的诗作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夏氏神异化的身世轶闻。陈惟亨提及夏伊兰离世后,“夏君(夏父)伤之,叙其梗概,以征当世文学士哀诔”[27],略可推想夏之盛在为亡女塑造神异化形象后广邀名士为其诗集作序,更近乎一次有意的筑塑、推广及经典化夏伊兰神异化形象的社会性活动。在序跋作者们对夏伊兰女仙形象的一次次的叙写之下,夏氏之神异形象得以不断层累并经典化,其作品也因而散发出一种神秘诱人的光华。
夏伊兰的经典化是成功的,而这多倚赖对她本人形象所进行的神异化塑造,相比之下,她作品本身的存在感被大幅削弱了甚至沦至边缘化位置。在清代闺秀诗文集出版场域中,诗之可传以诗随人传的方式进行,似乎成了女作家获得诗名的一种“捷径”,从诸多闺秀诗文集序跋中“不以其闻,而以其人”[29]、“以孺人之贤淑,其传固不必以诗之有无”[30]一类言说即可见一斑。放眼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这一文体总体皆呈现出这样一种“重点偏置”的形态,即对作品的评点及对文艺理论的阐发成为女作家形象叙写的配角,以边缘化的姿态存在于女性诗文集序跋之中,从而呈现出论人远重于论作品、叙事远重于议论的整体趋向。对女作家本人的神异化书写亦是根植于这一基础上的一种书写方式与策略,因而在此有必要对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呈现这一倾向的原因作进一步说明。除了上文述及的序跋文商业性视角下对女作家的观看角度这一因素,闺秀诗文集序跋中文学批评让步于形象叙写这一现象亦与女性诗文集序跋极高的社会性、应酬性不无关系。明清之际,为人作序之风大盛,以文坛灵秀钱谦益为例,其文集中收录集序逾200篇(其中便包括他为黄媛介、吴绡二位闺阁作家所作的诗文集序)(7)此数据为赵宏祥所统计。详见赵宏祥《集序写作的“认题”与“立意”——以钱谦益集序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 169页。。在此风气的浸染下,闺秀诗文集也开始广邀序跋,一集多序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前后序跋共有12篇,而张糹習英所作《澹蘜轩初稿》所含序跋竟多达20篇。除自序之外,题序书跋皆为一种互有往来的交际行为,因此一部诗文集的序跋作者有多少、为何人能在很大程度上展示诗文集作者的交际网络。然而对于以中馈女红、事亲课子为生活轴心的女作家来说,她们较少有筵席分韵、结社倡和的机会,交际圈自然也狭窄许多,再加之闺阁女子不宜与家庭单位之外的男子来往过甚,因而亲自广邀序跋对大部分女作家而言并非易事。在此境况下,与外界及主流文坛交往密切且赏识家中才女之作的男性亲族便成为了为闺秀诗文集贡献序跋的主力(8)笔者随机抽检100位闺秀的诗文集进行统计,其中91.7%的序跋作者皆为男性。在这些男性作者中,与女作家父亲产生关联者的比例约为6.05%,与兄弟产生关联者的比例约为13.4%,与丈夫产生关联者的比例约为17.9%, 与儿子产生关联者的比例约为7.6%。可见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基本为一个由男性主导的文学领域,其中女作家的兄弟和丈夫两种角色尤占重要地位。。一方面他们自己为家中女性书写序跋,另一方面向自己的友人、师生、同里乃至耆硕名儒广邀序跋,因此男性亲族的交谊范围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作家的潜在交际网络可以蔓延至何处(9)以女作家左锡嘉为例,为左氏的别集《冷吟仙馆诗稿》、《浣香小草》、《吟云集》及《冷吟仙馆诗馀》作序跋者共7位,而除姊氏左锡蕙之外,其馀6位序跋作者皆为与左氏之男性亲属包括丈夫、儿子、女婿有往来之男性文人。。如此便意味着诗文集作者与序跋作者呈现出明显的主体分离之态(10)王润英序文作者与书籍编著者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序文的写作走向,并将序文作者与书籍编著者之间的主体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序文作者与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重合,即通常所谓之“自序”;第二类为序文作者与书籍编著者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交关系;第三类为序文作者与书籍编著者无直接交往接触,主体间呈相离关系。王润英:《梓而有序:明代书序文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74页。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作者显然属第三类者居多。,很大比例的序跋作者与女作家实际交集鲜少甚至相当疏远,作序者往往仅是因为女作家的亲属友之托而应承作序。如刘晓华为张糹習英所作的《澹蘜轩诗稿序》对张糹習英本人及其诗作只字未评,而是通篇叙写自己跟从张琦(张糹習英父)和张矅孙(张糹習英弟)问学的经历和自己对老师诗论的追随,至于张糹習英及其作品,刘晓华仅以“晓华固束发授诗于先大父,迄今未有成就者也,不敢轻有所言”[31]一句颇显谦冲之语带过。刘晓华对于张糹習英生平和作品的沉默失语些许透露出他们之间关系的疏远,他校勘此诗词集并为之作序的最重要的原因并非真正赏识张糹習英的作品,而是因夫子“命为序”,可见为女作家作序这一行为中难以避免的被动性和社交属性。如果说男性文人之间互题序跋更近乎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32],那么男性文人为女作家书序作跋显然具有更为强烈的交际性和社会性。
极高的交际性和社会性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因作序跋者与作家之间的疏离,使得请序人转述这一过程变得尤为关键。序跋作者在对作家缺乏直观了解和实时动态更新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叙述空白,只能转而将重点放置于转述的内容上,而转述之内容往往不外乎女作家的生平行谊等客观素材。从前述夏伊兰诗文集中的序作者陈惟亨之言可知,夏伊兰的诗集中所录的其他序跋皆形成于夏父所作行略的基础之上。在这篇行略的引导下,为夏伊兰诗集作序跋的人基本都围绕谪仙奇闻展开,文字之层累不仅使夏伊兰的女仙身份更添真实感,并且这一异闻及其叙写方式亦借由诸多文士之手蔓延至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这一实际操作过程中,对女作家进行神异化这一书写方式一次又一次被重复,才女神异化这一书写传统也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加固。另外,从作品本身出发,因为大部分序跋作者乃出于交际之故而非对女作家作品的赏识而题写序跋,且多数女作家作品总体呈现出缺乏深度与厚度、偏于纤弱的单一取向,在审美意义和思想意旨都稍显短欠的情况下,男性批评者也较难就作品本身进行发微推阐或被唤起共鸣,这便进一步促使了序跋的重点向作家论转移。诚如清代小说家天花藏主人曾言才女“色可夸张,而才难附会”,因色“无可质”而才“不容伪”[33]。闺秀诗文集的序跋作者所书之轶闻奇事正与“色”一样属于“无可质”的范畴,过多地书写此类内容而失语于作品评判或恰恰反映了序跋作者对女作家作品的认同并不甚高。且序跋中对于文集作品的评点本身也是序跋作者本人批评理论及鉴赏水平的具象化表现,当诗文集被授梓并流入市场,序跋将与女作家作品一并进入公共领域并接受世人的谛视。闺阁诗虽以清丽之辞居于文坛,然“或赋新妆而开镜,或吟残月而论钱”、“皆脂粉争妍,未免裙笄结习”[34],其絺章绘句、刿云镂月之脂粉气皆为主流文人所不屑,甚至有序跋作者于为女作家所题序文中直言“不喜妇人诗”[35],可见女性琐碎缠绵而缺乏实际功用的作品风格时常面临质疑。若序跋作者对此类作品表示高度的认可,便无异于公然站到了传统诗教的对立面。当作序者应允为才女诗文集作序之时,事实上就表示了对女作家创作及出版行为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但通过序跋的叙写方式,我们可以认识到这样的认同实则为一种“有限的认同”,当序跋作者对女性作家的创作及出版行为或其品行给予肯定时,并不意味着他们接受并认可女性作品的风格,于作品品评上失语却转而投向神异书写等形象叙写或许正是序跋作者于公共领域中对诗学立场的一种暗自申明。
三、被预设的存在:绾合浪漫与现实的性别期待
序跋书写之本意本应是“序作者之意”[36],但在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这一领域中,由于闺秀游离于主流文坛之外的特殊身份及男性文人在这一文学领域中发挥的枢纽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话语权的让渡,即闺秀将阐释自己及自身作品的极大一部分权利交予她们所信任的男性文人,以此获得被更多人接纳和认同的机会。虽然闺秀文学借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在这一让渡过程中,闺秀作家的主体意志被一定程度上褫解,取而代之的则是从男性文人视角出发的对才女闺媛的性别想象和对闺秀文学的预设期待。作为这些想象与期待的具象化表现之一的神异化书写,便可以清晰地折射出男性文人如何在想象与期待中绾合浪漫与现实两种指向,从而呈现出他们心中理想化的闺秀形象及闺秀文学。
佳人一直是中国文人对女性形象的一种终极想象,佳人时常既疏离于日常生活又与文人有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承载着男性审美意趣及情欲想象。诚如邹流绮所言之“佳人无才,不淂为佳”[37],明清以前,能够展露才情之女子往往以风尘女子为主,因而男性文人对佳人的内心造影时常以兼具美貌与才情的青楼女子为现实归宿。而洎乎明清,青楼文化的沦夷及文化资本由女妓向闺秀的转移使佳人观念及其投射对象悄然产生变化,闺秀俨然已成为部分文人佳人造想的承载者,这一点从明清文人群体对能文闺秀的奖掖扶持及对文学伴侣式婚姻模式的推崇便可略窥一二(11)王绯、毕茗便指出清代文人崇尚妇才为风雅是因为把对理想佳人的向往和红颜知己的期待转化为对女性文本的偏好与推崇。详见王绯,毕茗《最后的盛宴,最后的聚餐——关于中国封建末世妇女的文学/文化身份与书写特征》,《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第26页。此外,清代比屋联吟图的大量涌现及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中对徐淑嘉一般文学伴侣式婚姻的提倡,都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闺秀已逐渐成为男性文人佳人造影的投射对象。。闺秀既成为男性内心造影的现实化身,便自然要承载男性文人的审美意趣。在闺秀步入文学领域之前,针对她们的书写如碑传、行略、墓志更多地指向较为纯粹的记录功能而缺少文学性发挥,故而重应用性而匮乏观赏性。随闺秀文学的郁勃而兴起的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则为书写女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寓所,尽管这一空间里仍延袭着记录妇德的女性书写传统,但却为闺秀文学性书写开辟了新的土壤。我们不难看到闺秀诗文集序跋中对闺秀生活的文学性叙写,如吴本泰为才媛李因作序时曾叙及其“薰四种之好香,濯十样之名锦。琉璃砚匣,自足清娱;翡翠笔林,时供雅玩”[38],又如鲍之钟描写妹氏鲍之蕙一家“置酒张筵,阄题角艺于清娱之阁”,“ 每于酒阑灯炧,搓热掌熨醉眸,才一篇成而和篇旋盈案矣”[39],这些足具美感的叙写展现了传统妇德视角之外的闺阁生活,让以往秘于绮阁的闺秀拥有了清晰灵动的面目,也为以往扁平化的闺秀形象平添一份观赏性。对女作家的神异化书写亦是对闺秀形象进行文学性发挥的途径之一,且在神异化语境中序跋作者的笔端甚至可以衍展至更为广阔的空间。如吴箭南序其妹吴秀珠集曰:“夫宝筏乘来,金光遍体;广寒修到,玉质练颜……今见绛珠属纩时鼻中玉柱两两下垂,颜色娟秀,无异平昔”[40]。欧丽娟曾指出由于家庭秩序的道德制约,针对伦理性的女性成员的仪容形貌的书写往往只能限定在实用取向上(12)欧丽娟此语虽针对中国传统诗歌而言,然其应用范围实则可以扩展至现实语境中的诸多文体之中。详见欧丽娟《杜甫诗中的妻子形象——地母/女神之复合体》,《汉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40页。,而因神异化书写提供了一种疏离于现实生活的语境,吴箭南甚至可以置道德制约于不顾,以纯文学性笔触书写在以往的闺秀书写中避免触及的容貌领域,可见神异化书写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闺秀书写的维度。在这样的感官书写的加持下,女作家不再是谱牒或列女传中的黑白剪影,而是拥有了灵动独特的面目,变成具有美学意味的存在。除了为富有才情的闺秀直接提升视觉观赏性,神异化书写亦时常与早逝相系结,从而为才女更添一丝昙花芬短、浮生朝露的易逝感,使她们更加接近男性文人心中红颜难永年、才福难兼济的佳人形象。如极显夙慧闺秀吴秀珠的父亲便曾叹曰:“是殆有根气,但恐不永年耳。”[41]锁开源为其早逝的妹妹锁瑞芝作序亦言:“夫以妹幼敦纯孝,长明大义,而顾不永其年,岂真天之相厄欤?然观其诞生之先,灵芝产于庭,群鹊噪于树;弥留之顷,端坐不卧,谈笑如平时,非所谓其生也有自来者与?”[5]在二位书序者的笔下,才女神异的表现成为了早逝的前奏,使才女早夭更增命定之感,易逝、易破碎的悲剧美感便由此生发,更引观者唏嘘低叹,心生“美人曼寿,自古所难”[42]的怜惜之情。需承认的是,闺秀诗文集序跋中的神异化书写虽冲破了以往闺秀书写的限制和套式,使闺秀的面目更为丰润圆活,然而作为男性文人内心造影的一种寄寓投射,当序跋作者以神异化为方法使闺秀形象更贴近于他们所预设的佳人形象时,神异化书写的方式及内涵就难免趋向同质化从而将闺秀书写拉入另一种脸谱化的境地。从这一角度观之,神异化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闺秀书写中除妇德之外的另一种性别符号。
尽管男性文人的想象开始逐渐移置于闺秀身上,然而闺秀们仍根植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分工之中,因此相对于纯粹的文学女性或心灵伴侣,更有一份基于伦理结构的现实期冀落诸闺秀身上。因此,即使灵根夙具、偶谪尘世、灵气所钟的奇异才女也终会落脚于现实既有的家庭及社会分工结构之上,这使神异化的浪漫想象和现实期待绾而为一,形成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张力。一方面于家庭分工之中,妇职妇德仍是闺秀的立身之本,诗文只应是女功之余的消遣而不应贻误女红中馈、事亲课子等内务的完成。因而即使闺秀作家被授予殊于常人的异才,也不应脱离现实伦理的轨道,甚至这些异才时而会服务于伦理性行为。如“灵根夙慧”的闺秀杨蕴辉将其卓犖之才主要投注于“翻芸佐读,劳不羡乎赁舂;画荻忘敂,教无烦于徙宅”[43]。如此,身赋异才的闺秀不仅未令其才华妨害妇德,甚至使才华成为实现妇德的辅助之物。通过将神异化书写与妇德书写相结合,使得身怀异才的闺秀终究落脚于伦理生活,现实期待反而更得到了无形的强调。更有如闺秀张玉贞一般的奇女子,其父张棠言与其妻“同梦灯花五色,大如车轮,觉而异之,而玉贞生焉”,伴异象而生的张玉贞自幼“颇聪慧,好读书,并涉琴画,尤精于诗”,虽然张玉贞显示出了高超天赋和广博兴趣,但其“性之所重者,以孝弟为本”,故其最异于常人之处在于对孝悌的极致追求。玉贞及笄后求聘者甚夥,但她却坚持不字以养父母,面对父母的劝嫁,张玉贞并自言自己对孝悌的追求“本天性,非矫情也”,甚至以死相逼遂得以坚守其志。此后张玉贞随父亲宦游,“调停家事,井井有条”,惟暇时吟咏为诗,且其诗多展现其“孝志贞心”[44]。张棠此序以神异化书写发端,继而大篇幅叙写张玉贞坚守孝悌之道以体现其奇异所在,伦理话语压倒性的优势体现了神异化才女最终仍将归于现实道德伦理的轨道。
另一方面于社会结构之中,文化场域仍以男性为主导,在该场域中最为重要的诗文两种文体关乎男性文人仕途前景和名望声誉。通过苦读从而中举入仕、光宗耀祖素来是众多男性文人期望的人生流程(13)曼素恩(Susan Mann)指出至18世纪,读书的实用性被看得更为重要,男性文人通过读书而谋得官位、光宗耀祖的欲望更为强烈,但通过读书取得所期望的成就却愈趋困难。见〔美〕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6页。熊秉真亦指出,四岁的男孩开始接受读写教育在明清时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男童在接受正式的教育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家中受到部分学前教育,而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便是父母期望儿子能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绩。见熊秉真《好的开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家庭进程和政治进程》卷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204-211页。,而非女子的,正因如此,男性文人本身已在文场中委重投艰,若当女性也能通过苦读而获得和男性相当、甚至超越男性的待遇时(虽然女子无法参加科考而进仕,但她们可以通过诗集出版令自己在男性主宰的文学领域获得声誉),男性或许会产生领域被侵犯的焦虑和困窘。因而于成见上,家中女子的诗文成就不应遮蔽家中男性的光彩,从而松动乃至打破固有的家庭体系乃至社会结构。然而清代才媛辈出,一些颇具灵性的才女甚至名声已远超族中男性亲族,这难免使男性文人陷入尴尬的窘境。才女钱孟钿的文学成就便远超她的两位弟弟,钱父于钱孟钿诗集序中直言“汝不事女红,而好吟咏;汝性慧,而两弟俱钝,读书未成,此非余所愿也”[45]1565,显然钱父已为家中秩序被钱孟钿的才华所打乱而感到困扰。然而最感困窘的,恐怕是钱孟钿的两位弟弟,他们不仅要接受父亲对他们“读书未成”的责难,还要面对外界刺耳的评议,如叔父钱维乔便提及钱父“恨(钱孟钿)非男子,未能称汝麒麟”[45]1566,管世铭更直言钱父对钱孟钿“珍惜出两公子右,若恨其不为男子者”[45]1568。或许正是为了缓解这种尴尬,钱父于序言中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强调钱孟钿殊于常人的极高天赋,并提出“男慧女钝,多兴;女慧男钝,多替”[45]1565,既表明了钱孟钿诗才远高于兄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可抗性,又暗中强调了家中女性文学光芒掩过男性的反常理性,在这里,对钱孟钿高于常人的天赋的描写庶几可以一定程度为钱孟钿二位兄长的不才和庭训成果的失衡而开脱,从而消解钱氏男性所处的窘境。更为有趣的是,对才女的神异化书写有时竟会成为对男性文才的衬托。上文述及的因梦中诸仙授诗而获得诗才的女作家华浣芳,其身上的奇闻正出自其夫张荣为其诗集所作的序文,而在张荣在叙写梦中得诗才的奇闻之后的一段描写亦值得寻味。张荣记叙自己听闻华浣芳能诗后遣媒人将自己的旧作送阅,华浣芳对张荣诗作“把玩不释,爱慕无已”。二人因互相欣赏而结缡后,华浣芳感激张荣为自己指授诗法,自言虽偶得仙才但“未尝知诗,幸先生有以教我”[6]。在这番描述中,张荣虽未直接标榜自己的诗才,然透过身赋仙才的华浣芳的赞誉及感激之语,张荣的诗作已然被推挹至一个相当高的境地,华浣芳之诗才则反而沦至次性的位置。在这些个案中,针对才女颖异才赋的书写已然不是纯粹地以提高观赏性及满足读者猎奇心理为目的,而是成为男性不才的开脱理由或男性文才的托衬之物,这些现实目的指向正体现了时人对闺秀作家及闺秀文学有异于主流作家及文学的预设期待。诚如焦袁熹于为才女陆凤池诗集所作弁言中提出的“女功之暇,偶弄笔研,不必多,亦不必工”[46],同时作为子女、配偶及母亲而存在的闺秀作家不得脱离固有的伦理囿限,其妇才不应成为实现妇德的阻碍,因而其作品“不必多”;而闺秀作家的形象及作品却又在某种程度上被预设为男性文人眼中的“文化花边”[47]从而被赋予以被观赏、赏玩为主的基调,且其光芒不应遮掩男性文人作品,因而其作品“不必工”。这样的预设期待使伦理性与赏玩性杂糅共生于闺秀文学之中,而闺秀诗文集中的才女神异化书写正体现了这一绾合了现实与浪漫的性别及文体期待。通过于传统妇德书写中融入神异化书写,传统伦理视域中密不透风的闺阃壁垒得以打破,闺秀作家及其作品都因此更具观赏性,然而由于伦理需求等现实期待,神异化书写最终仍难免归于传统妇女书写的轨道,且传统伦理终究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这便使佳人想象和佳偶要求、浪漫造想和伦理情感绾而为一,并在闺秀诗文集序跋这一既可蕴括文学性发挥又能强调道德伦理的特殊空间达到了谐融之态。
四、结 语
才女神异化书写于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之中得以生存与发展,有其特定的文体因素及文化语境。于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文体的视域内,由于文体自身所具备的商业性要求,使得序跋作者试图营造出疏离于现实的才女形象,以促成闺秀形象或作品的经典化。这一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偏重形象叙写而失语于作品品评的趋向,实则展现了时人对女性作家及闺秀文学的注视角度。此外,这种“重点偏置”的叙写方式亦与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极高的社会性及应酬性息息相关。而跳出文体视野之外,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中的才女神异化书写亦是闺秀文学观赏性与伦理性杂糅之下的产物,在以神异化书写方式为闺秀形象及其作品增添感官观赏性后,部分神异化书写仍以现实伦理为最终依归,体现出男性文人对闺秀形象及其作品绾合了浪漫与现实的双重期待。可见,尽管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中的才女神异化书写本为对男性传统的承袭追摹,但在闺秀诗文集序跋这一新兴文本类型以及闺秀文学这一新的文学空间内,针对才女的神异化书写被赋予了具有时代性质和性别意味的新意涵。